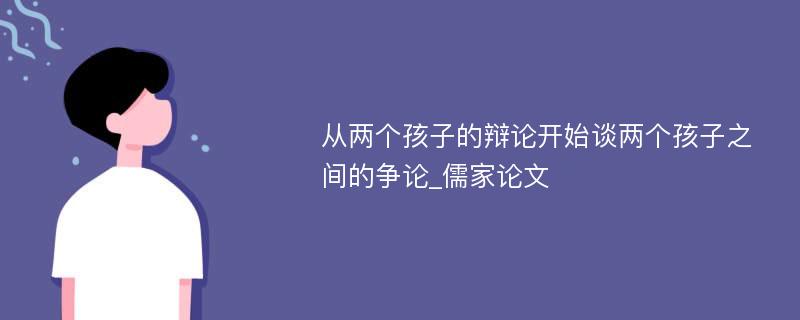
从两小儿辩日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两小儿辩日及其他
中学教材往往采用“两小儿辩日”的故事。故事出自《列子·汤问》: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列子》成书时间意见不一,有人说是晋代的。然而,一般是故事在前,成书在后。即使是晋人编撰,也有约一千七百年了。
早在东汉初年,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提出过与辩日有关的问题。《论衡·卷十一·说日篇》里有这样的叙述: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或以日中为近,日出入为远。
其以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者,见日出入时大,日中时小也。察物近则大,远则小,故日出入为近,日中为远也。其以日出入为远,日中时为近者,见日中时温,日出入时寒也。夫火光近人则温,远人则寒,故以日中为近,日出入为远也。二论各有所见,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
如实论之,日中近而日出入远,何以验之?以植竿于屋下,夫屋高三丈,竿于屋栋之下,正而树之,上扣栋,下抵地,是以屋栋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则竿末旁跌,不得扣栋,是为去地过三丈也。日中时,日正在天上,犹竿之正树,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犹竿之旁跌,去地过三丈也。夫如是,日中为近,出入为远,可知明矣。试复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于屋上,其行中屋之时,正在坐人之上,是为屋上之人,与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东危若西危上,其与屋下坐人,相去过三丈矣。日中时犹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与入,犹人在东危与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温,日出入远故寒。然则日中时日小,其出入时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为效,又以星为验,昼日星不见者,光耀灭之也,夜无光耀,星乃见。夫日月,星之类也。平旦日入光销,故视大也。
这段叙述不仅表明一些“儒者”在思考、辩论这个问题;而且在思索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天文、光学、气象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正确解答是近代科学出现以后的事情。王充的解释,用到了投影,涉及到光学、视觉,甚至提及“日月,星之类也”。不过,他的解释并不正确。
近两千年前,古人就能提出这些深刻的问题并进行思考,这很不简单。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我国古代典籍里有许多闪光的思想。
早在春秋末年,曾子对“天圆地方”之说有过质疑。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单居离问:“天圆而地方,诚有之乎?”曾参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半球天穹如何覆盖方形大地?
众所周知,惯性运动和相对性原理的确立,是近代科学的诞生的标志之一。其实,我们古人对此的认识,比伽利略要早大约一千五百年。古籍《尚书纬·考灵曜》载:“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行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恒动而人不知,譬如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也。”《尚书纬·考灵曜》的著者不详,但成书至少在东汉时代。
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把墨子的“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墨经》)看成是惯性原理的先驱;对此有不少争议。其实,墨子认为:“力,刑之所以奋也。”(《墨经》上)按通常的解释,“刑”通“形”,指物体或身体;“奋”的原意是鸟张开翅膀从田野里飞起。如果将“奋”理解为运动的变化,那么墨子就是说,力是运动变化的原因。也有人认为,“刑”通“行”,指的是“运动”。若作此解,那么这个说法就更接近牛顿第一和第二定律了。墨子对杠杆原理的了解,他在光学和声学等方面知识,比西方也早得多。
二 君子与小人
遗憾的是,我国古代这些科学启蒙的思想和问题尘封数千年,后人一直未作深究,没有发扬那些闪光的思想,并进一步成长为科学的理论。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的儒家传统的束缚,首当其冲。
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辱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如此敬畏“天命”、“大人”和“圣人”;而把“不知天命而不畏”,敢于怀疑、批判“大人”和“圣人”者视为“小人”。曾子显然对方圆之说感到困惑,但他畏“圣人”,答非所问:按孔圣人之意,方圆指天道与地道,而非天地的形状。
儒家也在讲“致知在格物”。所谓“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把“格物而后知至”放在首位。宋明理学家朱熹对这个传统的“致知在格物”还做过如此解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然而,“即物而穷其理”实施了吗?“两小儿辩日”应该怎么解?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难道不应该去“求其理”吗?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最后落在什么上?落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上面。
如果认真“穷其理”,把“中庸”为“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的解释用于机械运动,再联系“闭舟而行不觉舟之运”、联系“力,刑之所以奋也”,离匀速直线运动或惯性定律和相对性原理还远吗?
对“格物致知”的“格”有不同理解,有一种理解是把什么放到一个框框里面。但这些理解你也不用实施,究其原因呢,孔夫子说过了,你不能“狎大人,辱圣人之言”。如果像一些现代物理学人那样,不断追问到底什么是更基本的自然规律,就都成了“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小人”。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大人”、“圣人”,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他自认“五十而知天命”;认为“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对于孔圣人和他弟子,天命是不变的,天道当然也是不变的。在传统儒家看来,有了“大人”、“圣人”之言,“君子”“闻道”即可。
“格物致知”无非是体验“圣人”早就知道的“天命”,还需再去“求其理”吗?
三 关于教育观
这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在教育上表现为师道尊严和学识传承。
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既然天是不变的,道也是不变的。圣人得道,师者传播就是了,学生学习过程中有什么“惑”,老师去解就是了。从不说要去怀疑,从不认为“道”还在发展,还要后人去认识。“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个“师”仅仅是“闻道有先后”的意思而已。
遗憾的是,这种教育观贻害今日。
关于“两小儿辩日”的教案,最后落到什么地方呢?落到两点:第一点,孔子何等谦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当然不错,但显然不够。第二点,你看这两小儿何等狂妄:这个问题把孔子问住了,就自以为得意。这近乎荒唐。如此两点,完全不提小儿辩日的深意和正确的答案,完全不鼓励两小儿对孔圣人的质疑。这反映了我们现在教育中的问题。
现在的小学生,课业负担极重,是不是还能这样观测自然?还能“辩日”,提出难倒孔圣人的问题?
不久前,几位同事在一起议论教育。有人提及一位“国学大师”为一所名校题写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如果把学与师对立起来,一旦成师,仅需“传道、授业、解惑”,不必再学、再上下求索;如果成天想着“行为世范”,畏首畏尾;这必然大大束缚创造性,也恰恰反映了儒家传统教育观里的保守和腐朽。难怪该校一位至今当红的“模范教师”宣称:“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永远是最简单的。”如此宣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连现象和规律都不分的“学术超女”,较之质疑孔圣人的两小儿、或者王充时代的“儒者”,实在相距甚远。
2007年,在一次以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诺贝尔奖为主题之一的会议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主席桑·斯万伯格指出,“传播真理固然重要,质疑传统思维更重要。”恰恰这“更重要”的“质疑传统思维”,在儒家传统典籍中很难找到。
极富挑战精神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则不同。大物理学家费曼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他不断追问什么是更为深刻的自然规律,就是要追问、怀疑和挑战物理学界的“圣人”之言。我国大数学家华老针对“班门弄斧”,明确提出“弄斧必到班门。”何等深刻。这种挑战“圣人”的精神,恰恰是我们所缺乏的。
如何使学子从小就保持对于“未知”的好奇?如何培养无畏地不断探索自然与社会之奥秘的精神?如何不断地实其事、求其是?这是教育界面临的大问题。
四 关于科学观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必然对权威盲目服从,这也表现在某些学人对科学的观点上。
先来看一位时下名人是如何引用被毛泽东称为当代“圣人”鲁迅的一段话的。诸位大概知道《科学成就健康》这本书。翻开几页就有鲁迅晚年的标准照,照片下有这么一段话:“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科学史教篇》)
把原文找来,原来是1907年,26岁的青年鲁迅发表的,离出道还有十来年。文章提到了镭的发现,对此评价极高;但对于量子论、相对论却没有提到。看来,文中所说的基本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革命之前的科学。不仅如此,文章前面还有书中没有引用的一段话:“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即其他事业,亦胥如此矣。”即使在青年鲁迅看来,不“常恬淡,常逊让”什么事都成就不了。然而,一些时下名人恰恰并非如此。
“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这是青年鲁迅“科学救国”的憧憬。有了科学好像整个世界就光明了。鲁迅是当代“圣人”,于是他的话就是真理,科学也就成为“神圣”的了。
有如此神圣的科学吗?从来就没有。回顾科学史就应该知道这一点。近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希望请来的那位“赛先生”并非神而又神的“圣物”。其实,“德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此引用26岁青年鲁迅并非全意的话,配上50多岁时的标准像。用意何在?
还有著名学人强调:“科学研究就是要精确地、无偏见地描述世界”。存在这样的科学研究吗?甚至找不出哪一篇科学论文符合这样的标准。然而,一些学人却以此作为科学的定义。再三请教出处在哪里?才知道来自美国的几个委员会撰写的一本书,里面写下上面的话时,同时写道“社会相信科学家会这个样子”。著名学人就把这个“社会相信”会如此,当作科学的定义。
实际上,科学在不断地发展着。如果科学完美无缺、成了圣物,科学就僵死了,不会再有所发展了。
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革命,科学、特别是作为自然科学中最精确的物理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建立和发展,我们的宇宙是一个演化整体的确认,从对分子、原子和原子核的认识深入到夸克与轻子和光子、中间玻色子与胶子,等等。相关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社会进步。
然而,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一些老大难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引力的量子化、量子力学的物理解释、暗物质的实质,等等;实验和观测却发现一系列的新现象和问题,最突出的是精确宇宙学关于宇宙“暗能量”和加速膨胀的发现,这一发现大大出乎学界意料;还有关于量子纠缠、远程传输等的实质,与相对论定域性的关系;等等;以至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感叹:“知识最大的产品是无知。”
科学具有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应该包括:如何实其事、如何求其是;认识主体是科学家个人,还是科学界的群体;如何辨别真理和谬误;等等。
实其事并不简单。要通过不断地试验、观测与周密的思考,才能逐步实现。求其是,则更是如此。一般以为,物理学讲究逻辑、讲究数学推导、需要实验检验。但是,物理理论的基础,即基本概念和原理却不是从逻辑和数学中来的。用毛泽东的话,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次反复,要有积累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形成,就离不开这个“飞跃”,用爱因斯坦的话,不能“从经验中提取,而只能通过自由创造得到。”(《物理学与实在》1936年)实验检验当然重要。但是,任何实验检验的都是具体的结论或者具体定理的“有用性”,而不完全是“这个体系的正当性(真理内容)”本身;二者之间的关系“只能直觉地领悟”。(《物理学与实在》)
以天文为例,古人的观测仅仅限于视觉,400年前有了望远镜,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今天,天文学的视野已经开阔到130多亿光年。新现象的发现和落实,必然带来追求规律的“求其是”。观测到的“天象”大变,难道“天道”还会不变吗?为什么要阈于孔圣人眼中的上古“圣人”,在离现在五、六千年前所猜测的“天道”或者“天命”呢?
几年前,一些名家以魔术为例,批判“眼见为实”。岂不知,种种望远镜其实就是天文学家的“眼”,如果“眼见为实”不对,天文学还是科学吗?其实,问题的要害在于:何为认识主体?如果把观众和表演魔术的魔术师一起作为认识的主体,他们的“眼见为实”有什么不可呢?不过,仅仅是就“实其事”而言,也还要经过周密的思考。至于区分现象和本质,进而“求其是”,那将更为艰巨。
不妨再次强调,任何时候的科学和科学界,都不那么“神圣”,社会上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科学界大都可以找到。科学界的人首先是社会的人,并不会天然就更为高尚。今天午餐时,说到某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何谦虚。可就是这位先生难以启口之事,让红外摄像机拍了下来,闹得不可开交。个别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剽窃行为,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数十年不休。科学掮客、科学经纪人已经在我们科学界出现了;学界存在的学风问题相当严重、必须解决;不能任其泛滥。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神化科学、神化某些科学家呢?
较之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神学权威的霸道,科学毕竟大有不同。科学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宗教。随着科学的发展,“上帝”的领地越来越小。现代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科学毕竟不是标签,更不是商标。一旦成了标签,多半有假,是用来唬人的。科学史一再表明,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着的。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历史的、发展的科学观。
五 关于方法论
与“三畏”类似的对权威的盲目崇拜,也导致方法论的僵化。
爱因斯坦盛赞伽利略的科学成就和指导思想,他写道:“竭力反对任何根据权威而产生的教条”;“只承认经验和周密思考才是真理的标准。”(《为德雷克英译伽利略的〈对话〉所写的序言》)这里,提出了几个问题:权威、教条和真理的标准。
任何领域都存在权威,这是事实。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更应“竭力反对任何根据权威而产生的教条”。如果把“经验”理解为对于经过实验和观测所确定的事实的认知,爱因斯坦的话就集中体现了从伽利略开始的近代物理学的方法论和指导思想。
那么,思考何以周密?
通常认为,辩证法是个不错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这样理解的辩证法,和刚才爱因斯坦盛赞伽利略的那句话相比较,如果考虑到认识论的内容,在意思上基本是一致的。
这样理解的辩证法,同样应该适用于辩证法自身。如果辩证法对其自身不能适用,岂非咄咄怪事?于是,辩证法就不会崇拜它自身在某个阶段的形态,因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对其自身也同样如此。
那么,什么是辩证法现有的形态呢?经黑格尔的发展辩证法,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改造为唯物辩证法。再经过列宁的概括、突出对立统一、强调“分”和斗争性的绝对性;但没有和当时的自然科学革命联系起来。进而,毛泽东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联系,对其有所发展;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期间,进一步强调了对立统一、突出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当然,也不可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联系。所以说,20世纪整个自然科学发展以及20世纪中期以后的社会大变革,并没有被辩证法予以新的概括和归纳。今天得到认可的辩证法,总体来讲,仍基本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形态。“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哲学上与片面强调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有必然联系。
辩证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源于争辩的古希腊辩证法。与之相应,在我国上古,就有观天象、察地势和辨人事的“易”的起源;发展到春秋,逐渐产生源于农耕,以生、冲、和与反为核心的古代辨证论哲学。“辨证论”与“辩证法”相比较,不仅毫不逊色、且有质的不同,并且融合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与实践之中,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然而,如何与现代科学、现代社会的生产、经济、文化等等相结合,加以发展,这是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古代辨证论哲学仅仅归结为“中”或“和”并不全面,有悖于事物发展的规律。其实,从片面强调“斗争”,到仅仅归结为“中”或“和”,隐约印证了古老的“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的辨证论。
对权威盲目崇拜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哲学的贫困,思想僵化。
表现之一,就是将辩证法等同于机械的两分法。蒲鲁东是一个很有名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于他的辩证法,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批判: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过许多善,但是也做了许多恶。……好的方面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做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个方面而已。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
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白,蒲鲁东式的“机械”两分法不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僵化,就必然失去生命力。
我们今天仍常常能听到这类机械的两分法、两点论。将事物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然后保存好的消除坏的。比如有科学也有伪科学;要做的是保存科学、消除伪科学。于是,科学必须如何完美;“伪科学”必然如何荒唐。于是,就必须有“科学警察”来加以界定、来“执法”,等等。比如有西医也有中医。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要做的是取缔中医。也有自喻既懂科学、又懂马克思主义的名家宣称:“中医百分之九十是糟粕”,要“取精华、去糟粕”。如此等等。
听起来,就像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批判的蒲鲁东式的辩证法。
现在有一种“系统工程”时髦:“系统工程”成了一种模式,到处套用。大力提倡系统科学者,把系统科学提到很高的地位,与数学、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等并列;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位于最上端。这似乎是非常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如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同样会使之僵化、进而断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生命力。
系统科学的产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许多基本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然而,是从具体系统出发,上升到一般系统,不断反复、逐渐成熟;还是从建立“体系”出发,确大有不同。
即使按照某些提倡者的本意,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有理论基础部分,也有应用科学部分,还有在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应用。系统工程本应该属于系统科学的应用科学部分在工程技术中的运用。比如说研发两弹、人造卫星,当然包含着系统工程的要素。强调系统工程,对一些大型项目的管理、指挥和运作的当然会有帮助,甚至大有好处。对于管理或指挥人员来说,至少可以提供一张流程图,什么时间该干什么,各个方面应该如何协调,使得管理和指挥更有条理;等等。这些当然值得提倡。
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模式到处去套,不做具体分析、连部分之间的协调、工作流程图都不画、甚至根本就画不出来、只能编造。“系统工程”成了“套话”,那就不一样了。其实,即使是建筑工程,也有系统工程无法包含的人文、艺术的方面。现在,有人把科学研究也纳入“系统工程”,能讲清楚?英文都难以翻译。
不久前,《百家讲坛》请了几位名家讲中医,其中一位大力宣称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的观念,以此表明中医具有系统观。可是,如果人体是这样,马又何尝不是呢?蚊子又何尝不是呢?什么生物都是。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从“望闻问切”、“三因制宜”、“辨证论治”、“经络腧穴”、“扶正祛邪”等抽出“复杂”、“开放”、“巨系统”的具体内涵,还是用“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来套用,如何才有可能逐步解决问题?
一旦成了一种“模式”,好像一把什么东西说成是“伟大的、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切事情就解决了。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警惕呀!马克思早就警告过的“哲学的贫困”。
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明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对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启蒙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否则,以太说不会与元气说如此相似,提出“互补原理”的量子论大师玻尔也不会如此青睐太极图,等等。
然而,近代科学毕竟没有在东方诞生。反而,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备受凌辱、战乱连连、民不聊生;历尽多年的浴血奋斗之后,才迎来新的纪元。
对比“竭力反对任何根据权威而产生的教条”,对比“只承认经验和周密的思考才是真理的标准”,近代科学精神毕竟与“三畏”、“三不畏”圣人之言相距甚远。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顽强挣脱着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和道德枷锁。不过,总会有一些“三畏”君子,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一味宣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最具有普适性”、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的价值”、“超越时空”的永恒道德规范,等等。明知不是“历史”、不是“真实”;却侈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这是重祭精神枷锁的造神闹剧,是对历史的、真实的孔子的亵渎,也是对中华灿烂文明的亵渎,从而也是对人民大众的亵渎。这表明,对民主和科学、新文化的追求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着思想解放,不断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世界上一切文化的精华,不断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发展、建设着新文化。也只有这样,传统文化和世界上一切文化的精华,才将会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得以继承、弘扬和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