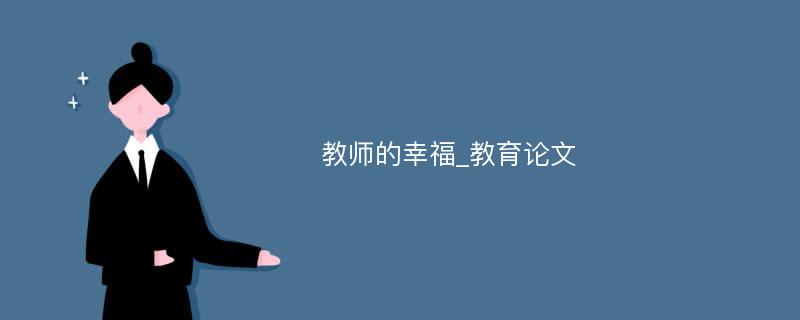
教师的幸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师论文,幸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职业意识的转变
我们传统上把教育(此处仅指教师教方面的活动,本文中的“教育”有时指师生双方的活动,请读者根据上下文做相应的理解)当作一种崇高的职业,是因为教师像蜡烛,像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被认为是对教师职业的形象概括。杨启亮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说,教师的职业境界有四个层次,一是把教育看成是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规范、要求;二是把教育看作出于职业责任的活动;三是把教育看作是出于职业良心的活动;四是把教育活动当作幸福体验。他认为,前两个境界是一种“他律”的取向,后两者是“自律”取向,并建议教师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教师的最高境界是把教育当作幸福的活动。高尚、崇高只是一种来自外在的评价,而幸福是行为主体的内在体验,只有与人的内在情感体验相联系的活动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永恒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各行各业都具有奉献的性质,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活动的奉献性。但能够把工作当成幸福的人并不从奉献中感到有什么损失,实际上,他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奉献,他只从工作中感到生命的充实和生活的乐趣。夸美纽斯把教师看作是太阳底下最光荣最高尚的职业,反映了他对教师职业强烈的情感上的偏爱。“高尚”是一种评价,把教育说成是“最高尚”的职业,也就意味着其他职业不是“最高尚”的;而“幸福”是一种体验,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工作体验为“最幸福”的,教师职业的“最幸福”并不排斥其他职业的“最幸福”。
把教师作为一种幸福的职业有客观依据。教育活动包含了人的一切的主客体关系,当中既有物的客体,也有人的客体,还有教师自我的客体。在人的客体上,教育是一种直接与人的全面本性打交道的职业:既要关心人的生理方面,也要关心人的心理方面;既要作用于人的个体性方面,也要作用于人的社会性方面。其他的职业,要么主要是直接与物的客体打交道,要么主要与人的某一(些)方面的本性打交道。在职业活动的客体内容上,教育无疑具有其特有的优越性。教育的丰富客体内容使它得以能够在职业活动中体验到最丰富的情感内容,因而它也最有理由成为一种幸福的职业。
二、主客体统一的教育过程
但是,教育职业并不必然是幸福的,它的幸福依赖于教师的积极创造,依赖于教师能否在教育过程中把与他相关的主客体内在地统一起来。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教师——教材,教师——学生,教师的角色自我——个性自我。如果说幸福是主客体相统一时的体验,那么,教师的幸福就表现在他与教材,与学生,与自己的融合之中。
(一)教师——教材
我们把教育分析成教师、教材、学生三个基本要素,这是很对的,但不能将三者分割。幸福的教育要求教师在理论上不仅要看到这三要素的分别性,更要重视它们的内在统一性,分别性是表面现象,而内在统一性才是实质。
教材是指根据教学大纲和实际需要,为师生教学应用而编选的材料。其主要形式有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等。教材不只指与知识教学相联系的“书本”,它还是教育活动赖以进行的一切形式的中介。教材是对社会历史经验的价值化形式,当中反映了选编者对原初智慧经验的选择和抽象。但是这个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有选择就有丢失,有对经验的抽象就有对心理的疏远。教师的作用是把“干瘪的”教材丰满起来,抽象的教材生动起来,统一的教材个别化起来。教师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体,他总是要根据自己的素质特点及学生的情况对教材加进主观的改造,这个改造即教师通过理解,把教材内化成自己素质的过程。教材只是一种文本,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理解,这表现了教师的创造性劳动。教师的创造性劳动不仅表现在对教材的理解上,还表现在对理解了的教材的个别化表达上。而经过教师创造后的教材才是真正的作为教育要素的教材。教育不是静态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活动、实践。没有进入教育活动过程的静态教材并不是教育的要素,而一旦进入了教育过程,作为一个教育要素,教材实际上就成了教师素质的延伸,这样,教材并不如我们目前理解的是外在于教师教育活动的“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等”。教师与教材的统一也不仅仅表现为“教师讲授教材”。教材就是教师的内在素质,两者内在地统一于教育活动当中,教材变成了教师之“我的”素质,教育之乐不再是外求,而只是内省。教师只是在用自己的人格素质育人,他不是用外在的知识、规范去训人。不同的教师内化同一种教育内容就会形成不同的教材。所以,教同一年级的同一课程的不同教师就向学生展示不同风格的“教材”,培养出不同风格的学生。那种持外在统一观的人认为教材是教材、教师是教师,教材只是教师的通用工具,他们反对教师对教材作主观改造,宁肯让教师受教材的束缚。受缚于教材的教师于是成了教书匠、传话筒、录音机,教育活动就不再与教师自身的素质有关,教师只是在教外在客观的教科书,而不是在展示自己的内在素质。教育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创造,传统的观念认为教师的备课只是一种认识过程,而我们认为备课更是一种实践,既有客体主体化,也有主体客体化。教师和教材在备课中实现双向对象化。教育是一种创造,创造性的教育要求教师以充满想象的方式表达富有意义的观念,学生也是通过想象联结教师所教的内容,这样教师便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理解水平随时调整教育进程。教育活动也是师生双方不断对象化的过程。教书匠抱着不变的教材、追求精确的预定结果,而教育艺术家则特别注重教育过程中创生出了新结果。如果用一个特征来表达这种创造性教育的话,则可以说,受惠于这种好教育的儿童能够将教师抛在自己的后面。(注:Barrie Barrel, "Classroom Artistry", "TheEducational Forum",Vol.55,No.4,Summer 1991。 )传统的教育使师生滞留在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之内,而创造性教育则赋予师生无限自由的空间。当教师不是机械地重复教育内容,而是将自己的“力”加进了教材时,教育活动对他便不再是被动的、外在的,而正是教师本性力量的流露。宣讲自己的信念,表白自己的真情实意时,人是最生动、最幸福的。
(二)教师——学生
人有三种学习。一是原初的学习,二是教育性学习,三是自主高效的学习。在原初的学习中,学习对象是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它们可能以原初的偶然的状态存在,也可能以一种价值文化的形态存在,但由于学习者的理解水平限制,他没有领会到当中的文化意义,所以它们仍与原初的偶然现象相类同。从人类整体来说,这种学习存在于人类历史早期,就个体发展来看,学习者是人性力量发展不够的个体,他尽管有一定的目的性,但对环境的选择力不大,自主性不强。由于遗传的人性力量在人群之间基本呈正态曲线分布,所以,其学习能力和因学习而获得智慧经验的力量也呈正态曲线分布。教育性学习即常称的“教育”,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教师的参与。教师在学习者与学习对象之间起中介、桥梁的作用。作为一种学习,教育产生于学习者对学习能力的需求,终结于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养成。它与其他的学习一样,也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经过教育性学习后,人不再依遗传的人性力量呈正态曲线发展。布卢姆认为,经过教育后,人若仍依遗传呈正态曲线发展,说明教育是失败的。而自主高效的学习是指学生经过教育以后,把教师“内化”为自身的素质,自己成了自己的教师,所以,他可以摆脱教师的中介,直接面对对象经验,进行自主高效的学习。学生通过教育已经学会了学习,显然,它与原初的学习是形式上相似(即都靠自己的独立学习),能力上、境界上迥异的学习形式。
在教育性学习(以下简称“教育”)中,教师是学生与学习对象的中介。过去有人把教材作为师生双方共同的教育客体,教育就成了师生两个主体共同面对材客体的所谓主——客——主关系;也有人把教育看作以教材为中介的师生的交往活动,这就混淆了教育的发展目的与交往手段的关系。但教育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活动,是学生的一种学习形式,其主体是学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人的任何实践都是为了实践主体的某种需要。把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教育就是为教师服务的,把学生作为教育主体,学生便是教育活动的“中心”。教育的核心结构是学生与学习对象(即教材)之间的主客关系,只是为了能“多快好省”地实现人在原初学习中的目标,教师才得以参与其中,但他的加入并不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作为学习活动的性质。教师只是在原有的学生——教材之间通过中介的作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作为中介,教师就既要与学习对象相通,也要与学生相通。在教师与学习对象(教材)上,我们已经说明,教师通过内化教材,使教材变成了自身内在素质。那么在教师与学习者(学生)的关系上,我们要说,教师是学生的体外大脑。
原初学习的低效能源于学习者在目的活动中主体性相对较弱。教师的作用就是能为学生提出适当的目的,使学生总是处于“最近发展区”内,从而表现出学习的高效率。教师为学生提出目的,帮学生实现目的。教师作为学生的体外大脑,是应该与学生的大脑内在统一的,这种内在统一就表现为教师通过“改变”自己,把自己的头脑化为学生的头脑,把自己的目的意识转化为能让学生认同的目的意识。这样学生才会根据教师的目的进行自己的学习实践。教师只有先根据学生的情况预先改变自己,才能在学生那里见到合目的的改变。被学生认同了的(内化了的)和执行着的目的是教师的目的与自己原有的目的融合物,当中包含了教师的目的,但又超越了教师的目的,因而具有学生自己的个性特征。学生的学习永远是学生自己的学习,教师不可能直接将经验“打入”学生的头脑,变成学生的素质。因此,“把教师的目的化成学生的目的”便是教育是否成功、幸福的关键,教师的不幸常常是因为在两种目的上没有内在统一地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教师认为学生的学习不是学生自己的事,而是他的事,他无视师生间的“大脑”转化环节,直接将自己的目的当成学生的目的,他可以不顾学生的反应,盲目填灌,认为他教得越多,学生学得也越多,教得越深刻,学生理解也深刻。还有一种教师把教育等同于学生的自学,抛弃了自己的责任,不在学生的目的中“出力”,这样,教育的特点被泯灭了,教师自己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就不可能幸福。
把教师看成学生的体外头脑,也就是把学生看成是教师的体外“自我”。教育活动于是是教师使自己“不朽”的过程。教师通过教育将自己全息地“拷贝”到学生身上,将自己的本质外化成无数的体外自我,借此为自己塑造一个不朽的精神,找到一个更永恒的安身立命之所。教育的终结以教师的隐退为标志。但教师的身体可以退出教育过程,精神却永远融入了学生的心灵,滋润着学生的未来生活,他是无法完全从学生那里隐退出去的。学生是教师内在素质的体现者(即此时他成了自己的教师),教师借学生之身巧妙地扩展着自己。在这里,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反映着教师的影子,学生的生命就是教师的生命,学生的成败深切地牵动着教师的心灵。于是教师不再与学生处于对立或外在的关系中,学生与教师的“我”形成了本性层次的联系,教师的劳动在学生身上结出果实(不像自我中心的教师那样使自己的劳动与学生无关),学生的活动再现着教师的精神(不像无责任的教师那样使学生的学习与自己无关)。师生通过内在的联系融成了一种生命共同体,教育不是教师以裁判的角色督促学生学习,也不是以“狱卒”的角色管住学生,它是师生交融的,是师生间无需其他中介的“直觉”合一。教育并不是以损失教师来造福于学生,而就是教师不断超越自我的活动。学生的成长并不是对教师生命的剥夺,它是教师价值的实现、生命的肯定。还有什么东西比自我生命的增殖更让人幸福的呢?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校内外茁壮成长更让教师幸福的呢?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注:《孟子·尽心》。)当作人生之三大快乐(幸福)之一,大概也是出于这种理解吧。
(三)教师的角色自我——个性自我
“日常意识常把生命活动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形式上的、凝固的、僵死的,它属于‘无人称的’社会角色世界;一个部分则是‘个人的’、有感情色彩的,代表着个体不受社会条件影响的‘自己本身’。”(注:科恩著,佟景韩等译:《自我论》,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94页。)幸福的教师是角色自我与个性自我的统一。 作为一种角色,教师更多的是指由教师这种社会职业所要求的客观的规范和原则,而作为一种个性则指教师这个职业因被个人所承担而必然被赋予教师本人的个性特征。一个教师必然要处于这两种矛盾的意识当中。角色意识要求教师以某种社会观念和准则去规范、统理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个性意识则根植于个体的生命存在,反映了教师对自己内在需求、情感世界加以真实的把握。能否将这两个“自我”在工作中统一起来,决定了教师能否主—客矛盾中获得幸福。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把每个人的生活分隔成多种片段,每个片段都有它自己的准则和行为模式”。(注:麦金太尔著,龚群等译:《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自我消解成一系列角色扮演的分离领域。”(注:麦金太尔著,龚群等译:《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而与整体生活相联系的德性却没有了践行的余地。人已被角色自我占据了主导地位。过去,我们多是强调教师是社会的代表方面,要求教师用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规范要求自己,这样,教师多是用角色意识压抑个性意识,扮演一个无个性的、一般化“他人”。角色自我一般停留在人的意识层面由理性控制,所以教师的行为多是出于对角色、规范、要求、职业责任的意识,最多也是出于职业良心,它没有与人的生命意识联系起来。因此,教育多表现为一种非自然的做作、表现,教师只与一定的社会地位相联系,不以他自己的个性特征为转移,教育工作与他的日常生活如同两个割离的世界,互不相通。由于他在学生面前是讲一些冠冕堂皇、并非发自内心的话,所以,工作在合规范、合逻辑、合理性中便无生命,无意蕴。而只有在离开教育活动时,他才如释重负地回到活生生的个人。教师的角色意识太强也让学生形成了一种偏执的观念,即教师是标准的完人形象,教师是没有错误的,没有内心矛盾,没有喜怒哀乐甚至没有自己生活的“超人”。没有缺点,没有“人的”生活的教师,对教师来说并不是一件合乎人性的形象,它在师生之间无形中划出了一道无法逾越、不可沟通的“鸿沟”,教师的个性被角色自我的圣光所吞没。
教育要向人还原,向人的生命存在还原。教师既是一种角色,也是一种个性,就我国目前来讲,尤其要提倡后者。教育不是教师为谋生去表演,它就是教师的生活本身。压抑个性、默默无闻地承受自我异化,可能使教育成为一项让人同情,令人敬而远之的“高尚”职业,只有充分地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才能使教育成为一件让人幸福、令人羡慕的职业。作为一种职业,教育无疑有它的社会规范和要求,但这种规范和要求如果停留在教师的意识层面,它只是以学问的形式存在,于是便表现为去个性化的角色自我;如果进入教师的无意识层面,它便以教养的形式存在,于是便表现为个性自我。对个性自我的凸现并不必然拒斥角色自我、让教师毫无控制地恣意妄为,但它要求超越角色自我,将角色自我审美化、个性化、感性化、情感化,把它沉入个性层次,使规范、要求变成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教育的个性化因而也是教师自身的社会化。教师两种自我是在个性自我之中得到统一,优秀的教师都是在超越了角色自我之后展示出丰富的个性自我的。他们的教育活动,往往是最具个性魅力的艺术。对名师的模仿必然要从自己的秉性中发现创造的依据,不断注入新的养料才能使自己的教育活动不落入亦步亦趋、刻板单调、毫无生机的窠臼。教师一旦把工作扎入“我的”生活之中,与“我的”个性融合起来,才会像热爱自己一样热爱教育事业,才能使角色积淀成个性,达至角色自我与个性自我相统一的境界。这样,角色自我的活动才不对个性自我造成压抑,反而成了肯定个性的活动。
三、与学生共创共享教育的幸福
有一种“无私”的教师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东西,他只是为了学生而活着。尽管他是无私的,他却并不幸福。那么,他的“无私”是否让学生幸福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与他的期望相反,学生并没有从他的自我牺牲中感受到幸福,他们只是焦虑、紧张、愧疚,并急于实现教师的期望,为了不让教师失望,他们不愿批评他,所以同样让这种“无私”的教师困惑不解的是,他与学生的关系并不真正令人满意,双方都没有从相互关系中感到轻松自在、幸福。还有一种教师与此相反,把教育只是当成自己方面的实践,使自己的活动成了教育的目的,他们完全听任自己的兴趣,自我中心地教,不顾学生的反应,认为只要自己“教”完了,教育也就大功告成。有些教师可以把教育变成说“评书”,学生成了他们表演的背景。这种教师其实没有幸福感,他们往往在表演之后体验到深沉的失落,即使他们确有所乐,那也不是“教育”的幸福。教育的幸福应该是全面的——与其他一切客体对象相统一的全面感受。
在幸福的教育中,师生在幸福上是相互感染的,这种感染是以师生间的移情为中介。现代心理学表明,师生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刺激一反应结构,师生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反射环结构。幸福作为一种情感,与其他情感一样包括体验和表情。作为一种内在体验,幸福是独享的,但通过外部表情,幸福又可以与他人分享。当教师的内部体验外化为表情时,教师的幸福就变成了一种可被观察的对象了,学生通过识别教师的表情,在自己内心激起同构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又要外化成学生的表情,教师通过学生表情的反馈强化了自己的幸福体验,学生的幸福感也因此渐次强烈。在幸福上,师生双方相互感应,不断激荡,慢慢消解中介隔离最后达到同悲共欢的融合境界,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情感场和完整的体验。当然这种体验状态既可是以感性情感为主的“热情奔放”场面,也可是以理性为主的“条理”、“系统”、“缜密”、“深沉”的理智情感。情感体验的教育方式激发了对知识、对学生或对教师的爱,丰富了师生间的理解,弥补了因语言表达造成的意义缺失,使教育产生出事半功倍的神效。
师生的幸福是创造与享受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不是外在的:你创造,我享受,或我创造,你享受;先创造后享受;在创造和享受之间计较一种平衡。老式的教师可能以用棍棒教学生为乐,“无私”的教师可能以把自己当作学生的工具为乐。“不过这些都是单方面的快乐,在另一方,这事并不好受。我们已感到这些单方面的快乐不能令人满足,我们相信良好的人际关系应使双方都感到满意。”(注:靳建国等译:《罗素文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只有这样双方的幸福才具有人道的意义和长久的保证。在上述的体验性教育中,教师既是幸福的创造者,也是幸福的享受者;学生既是幸福的享受者,也是幸福的创造者。师生双方在教育幸福的创造和享受上得到了内在的统一。这种统一还表现在师生双方对教育过程的“游戏”态度上。在幸福的教育中教师不会想到这课讲完之后有多少酬金,也不是为了让学生、国家、社会对自己有好印象。学生在幸福之中也不会去计较成绩将因此得到多大的提高,或专心学习将是否获得教师好评。如果把享受从创造的过程中分离出去,享受便与创造过程无关,只成了一种外在的“消费性”结果。当人的注意力移至外在的结果时,他就无法专心沉迷于创造的过程。在幸福的教育中,教育本身就是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有机统一,它把师生从世俗的教育评价中摆脱出来。教育行为本身就是教育的乐趣和动力,就是对教育的最圆满的评价。师生似乎就是为了教育而教育,没有担忧,没有媚俗,他们纯净地迷醉于此时此刻,甚至还忘了此时此刻的“反常”表现。
对于幸福教育的教师来说,教育不是牺牲,而是享受,不是重复,而是创造,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