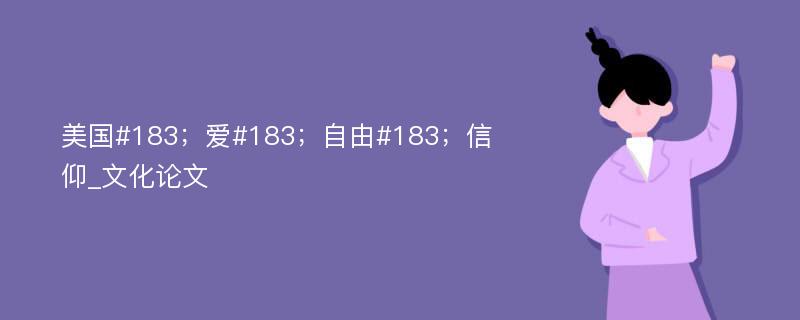
美#183;爱#183;自由#183;信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2-0095-09
2004年,我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美、爱与信仰的关系,不久即被《新华文摘》转载了,随之学术界有不少人作了肯定的回应。不过,也有例外,一位作者竟武断地说我讲的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呢?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在文章中提到了上帝,以及神学中的信、望、爱。我们的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从改革开放之后,比较多地是讲实践、实用、实效,很少讲信仰,包括一些学者在内,许多人根本没有信仰,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奇怪。其实,信仰对于人来讲,是少不了的。人和动物的区别,说到底,如果不是会使用工具,不是具有一般的理性,那么,就是人会反思,有实现自我的需要,有信仰。信仰对于个人是精神支柱,是一切行为的最终指向和根本动力;对于民族是精神的图腾,是民族之所以凝聚在一起,团结奋斗,兴旺繁荣的保证。没有信仰的人,也许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豪,但必定是精神上的侏儒;没有信仰的民族,也许能够统领一个时代,但必定不会有辉煌的未来。古往今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固然是一种信仰;柏拉图的理想国、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也是一种信仰;儒家经典《礼记》中讲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老子讲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是一种信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康有为的“破九界,入大同”的“大同世界”①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科学共产主义都是一种信仰。信仰是一门大学问,是哲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的共同课题。自古至今,凡大学问家,没有一个不有所涉及。今天,我们只谈美学,因为美学在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美学是感性之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信仰之学。
一、信仰,赋予生命以意义
我们先谈谈信仰对人生的意义,或信仰对人生意味着什么。借用基督教的说法,信仰是三位一体的结构,包括信仰的对象、人群、行为。信仰是人的信仰,但必须有一个外在于人的对象。这个对象作为一种实体可以叫做上帝、太一、神,作为一种理念可以叫做道、逻各斯、绝对理念,作为一种境界可以叫做终极境界、涅槃、极乐世界,我们且用一个哲学的术语,统合在一起,称它为融真、善、美为一体的“存在”。存在是对信仰的最高抽象,是超越任何具体经验的东西,但毕竟是对人而存在的,人是信仰的主体,而人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所以人必须超越自己,这是信仰之所以可能的前提。这个超越过程就是信仰作为一种行为的本身。因此,可以说,信仰本质上就是从此岸的、经验的世界向彼岸的、超验世界的超越。当然,这完全是属于精神领域的事。
信仰对于人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意味着在自己之外,在最高层面和终极意义上,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敬畏、崇拜、向往的目标。有一个敬畏、崇拜、向往的对象,无论对于个人或群体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就可能会失去自我约束,自以为是,乃至狂妄傲慢,肆无忌弹,乃至忘乎所以,无法无天。可以想见,西哥特、汪达尔等蛮族攻进古罗马的时候,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也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捣毁炎帝陵、舜帝陵、大禹庙、仓颉墓、孔子墓、霸王庙、武侯祠等的时候,是什么情景!也许那些肇事者中不少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或别的什么信徒,但他们在那个时候完全背弃了自己的信仰,陷入一种不可自制的野性的狂暴之中。不是任何的对象,比如迷信中的鬼、神,都可以成为敬畏、崇拜、向往的对象,只有存在,即我们称作真、善、美的本身和本原才是我们需要敬畏、崇拜、向往的对象。所以叫做本身或本原,不是就事物间因果关系讲的,而是就观念的逻辑关系讲的。就是说,一切被我们称之为真、善、美的事物都是在与它的比照中得以确认的。这是一种价值观,一种评价事物的尺度;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一切尺度中最高的尺度,这种价值和尺度是跨越所有时间与地域的,无论哪个时代或哪个民族,对人和事物的最高赞词无非就是真、善和美。当然,真、善、美只是信仰的对象,不是祈求的对象,它能给予我们的只是一种光明,一种希望,一种呼唤,但就是这点光明、希望和呼唤就很重要,有了它,就有了一种境界,一种寄托,一种归宿,就说明你超离了自己的局限,冲破了物质、金钱、荣誉、地位等等的樊笼,走进了一个自由解放的广大天地。
其次,信仰意味着在存在或真、善、美面前,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和意义。因为你意识到了你既不是一切,也不是中心,在你之外还有另一种你永远无法企及的伟大的存在。只是由于它的存在,你才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真、善和美了,也只是由于它的存在,你的真、善和美才被世界所认同。真、善、美就在你的前面,你是在它的光芒的照耀下,一步步走向成熟并进入人的角色的。从此,你不会沉迷于金钱和美女的享乐,因为你找到了自己的目的和意义;你不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因为你学会了谦逊、敬畏和崇敬。林语堂先生说,一个人如果站在巍巍耸立的高山的面前,就知道什么是伟大了。一座高山的真、善和美就可以让你肃然起敬,自惭形秽,何况是作为最高存在的真、善、美。古人云: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你听不到,看不到,但它却强烈地撞击着你的心灵,让你的心中升起一种无限尊崇、肃穆、幽远之感,并享受着一种静观的愉悦。
再次,信仰意味着你有了一种最高的需求,一种趋向真、善、美的动力。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说法,人有五种需要,自我实现是最高需要。存在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交往和友谊的需要都可以与金钱联系起来。有了钱就能生存,就多几分安全,就会获得很多人的尊重,就可能有一大批同道、情人和“粉丝”追随,但事情常常是钱赚了,自我呢?却失去了。慧律大师在《佛心慧语》中就说:看起来是你赚了钱,实际上是你被钱赚了,赚走了你的青春、时间、体力和生命。所以有的富豪自我调侃地说:“我穷啊,穷到只剩下钱了。”而且,用钱买来的尊重是真的尊重吗?用钱买来的情人还算情人吗?自我实现是人的本质意义的需要,自我不是我的存在或我的意识,而是我的个性与人类性,是我作为个体在人类生活和历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价值。自我实现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掘、发挥自己的潜能,并用因此而改变的现实证明自己的价值。显然,这是金钱所无法撼动的领域。诗人李白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所表达的就是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不是金钱,而是信仰的存在确证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并激励和推动人们去一步步实现自我。这是超越其他一切力量的巨大推动力。孔子之所以周游四国,历经磨难而乐此不疲,是由于有实现“先王之道”的信仰的迫力。康德是近代哲学最伟大的代表,他不信基督教,但有自己的信仰,这就是后来镌刻在他的墓碑上的:“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相信宇宙是有秩序的,是一个伟大的美的整体,相信在这种秩序和整体背后有一种“宇宙理性”存在,世界将按照宇宙自身的规律走向文明,这种信仰支撑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众多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②相信中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经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信念和信仰推动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历经五次反“围剿”,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夺得了政权,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胜利。
总之,信仰意味着你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之外有了一种超越的精神生活,意味着你正在走出自我并踏上通往理想境界的途中。特别是在今天,信仰对我们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见得太多的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是怪力乱神、妖魔鬼怪,是各种版本的厚黑学、博弈术。
二、作为终极指向的真、善、美
不论信仰的是上帝、神、道、理念或绝对理念,其核心的东西都是真、善、美,没有一种信仰是指向假、恶、丑的。柏拉图讲:“所谓神灵的就是美、智、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③圣奥古斯丁称:上帝“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④。现代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说:“与其说上帝拥有善、正义和宽容,不如说他就是这些品质的化身;正如我们所明确指出的,神是完美性的实际表现,他本身就是‘善’、‘爱’。”⑤对于基督教说来,上帝不仅是最高的真、善、美,而且是真、善、美的本原。对于伊斯兰教说来,世上的一切善恶、美丑则都是由安拉安排的。为什么人们要信仰他们呢?就是因为在人们看来,他们代表了最高的真,最高的善和最高的美,因为祖祖辈辈,千千万万的人都相信上帝或神是真、善和美。信仰与一般的信念不同,是群体的事情,信仰的力量是建立在从众心理上的。
真、善、美是对存在,即道、绝对理念、上帝或神的不同表述,它们是统一不可分割的。真就是存在的本体,善就是存在的趋向,美就是存在的表征。当我们把存在当作认识的对象的时候,存在就是真;当作意志的对象的时候,存在就是善;当作情感,确切地说,当作爱的对象的时候,存在就是美。存在是一个东西,人们只是从有限智性和有限的需要出发,才把它区分为真、善和美。
真、善、美既是信仰的对象,因而也就是我们评价人和事物的尺度,同时是完善和实现自我的力量。我们是在这个过程中走向真、善、美本身的。真,要求我们真诚地面对自己和外在世界;善,要求我们善意地对待自己和外在世界;美,则要求我们以自己的整个生命去体验和爱自己与外在世界。
在真、善、美三者中,从认识论的意义讲,应该是真在前,因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象,首先是认识它,有了认识才会去相信;有了认识和相信之后,才会形成自己的意向,去希望,善才进入到意识中;有了相信和希望,即有了真和善之后,才会发现对象的美,才激起对对象的美的爱。但是,从存在论和价值论的意义讲,则首先是美,其次是真和善。从存在论的意义讲,就像杜夫海纳说的,美就存在于生命的根底部,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原始的统一中,存在于前认识或元意识中。从价值论的意义讲,美作为存在的表征,既包含了存在本体的真,也包含了存在趋向的善,也就是既包含了存在的统一、完整、坚实,也包含了存在的次序、节奏、和谐。美就是融真和善为一体所闪烁出来的灿烂的光辉。因此,刚刚故去半个世纪的俄罗斯学者别尔嘉耶夫曾说:“美比善更能表明世界和人的存在的完善。最终目的更多的是以美为标志,而不是以善为标志。”⑥
美就是融真和善为一体所闪烁出来的光辉,这一点孟子说的很明白。他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⑦“充实”这个概念很丰富,一个本身不真实,不完善的东西不能称为充实。所谓“有光辉”,学术界都以为是指“辉煌壮观的美”或“崇高”,其实是照耀、显现的意思。“有光辉”就是不仅自身充实,而且能够显现出来,照亮自己和周边世界。“大”是我们中国古人对美的最高称谓。所以,孔子讲:“巍巍乎,唯天为大。”庄子讲:“古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⑨美之所以成为存在的表征,就是它极其充实地体现了存在的真和善,而且显现出来,投给世界一缕耀眼的光辉。孟子的这一思想与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德国古典哲学、存在主义的观念不谋而合。海德格尔就说过:“美是存在之光所闪现的光辉,是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⑩信仰是对真、善和美的整体,即存在的信仰,这个存在不是认识中的存在,不是意志中的存在,而是审美中的存在,即作为完整的生命个体的“存在者”的存在,所以,早期一位基督教神学家托名狄奥尼修斯提出一个命题:“美是上帝的名字”。
信仰虽然是对一种超验的真、善、美的信仰,但却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正是千百年来的生活经验告诉了人们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真、善、美,以及假、恶、丑的可恶、可恨,真、善、美的可爱、可贵。超验的真、善、美无非是经验的真、善、美万千年来的伟大积淀。它飘浮在精神的天空中,却是由现实的地面上升起。凡是有真、善、美的信仰的地方,就有对真、善、美的生动丰富的体验。人们之所以不满足经验中的真、善、美,只是因为它是有限的、短暂的、虚浮的,而且常常是被扭曲的。格奥尔格·西美尔在《论宗教》中说:宗教之成为一种信仰,是因为经验中固有一种“宗教性”,即与美、崇高、震惊、恐惧等感受俱生的那种难以捉摸的心理张力,那种不透明性、陌生性。“如果说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确是从原因秩序的延续冲动中产生出来,那么,迈向超验的宗教因素也早已存在于因果过程的低级阶段上。”(11)所以,为了确认、追寻、趋近超验的真、善、美,我们只能从体验、感受经验的真、善、美开始。
科学家、道德家、政治家和佛学家、神学家可能有不同的通向信仰的路。通过对人的生命或天体的深入观察,科学家可能会发现宇宙背后的不可理喻的伟大智慧;通过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综合分析,政治家可能揭示潜藏在恩格斯讲的平行四边形中的伟大规律;通过对人以及所有生灵命运的深入反省和沉思,佛学家或神学家或许能够见到普通人所难以想象的生命的奥秘。但是,无论什么人要想确立起对真、善、美作为整体的信仰,都只有从对美的体验开始并最终形成美的意境或境界才有可能。人们相信上帝或神的存在,一般情况下,首先不是确证了它的真,或领悟了它的善,而是首先接触了一个遥远、神奇、美丽的传说,一位创始人的悲壮感人的经历,以及无数信徒对这个传说和经历的有声有色的演绎。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圣奥古斯丁之皈依上帝,据他自己说是一次从教堂出来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时,猛然从一道神奇的闪光中听到了上帝的呼唤,从而引起他对过去九年的无知和荒诞的反省。所以,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导言中说,“真理无论在什么阶段,它进入人的意识首先必须在外在方式下作为感觉表象的、现前的对象;像摩西在烈火的丛林中瞥见了上帝,和希腊人用大理石雕像或别的具体表现使神显示在意识面前那样。不过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真理是不能停留,也不应停留在这种外在的形式里的——在宗教如此,在哲学亦是如此”(12)。这就是说,首先是一种奇妙的距离感、始原感、惊异感和皈依感,加上对生的热望,对死的畏惧促使人们去思索、探寻,去瞻仰、聆听,并最终拜倒在上帝或神的面前。
三、美:从根底、中途到终极
美在生命的根底部,在日常经验中,同时又在信仰里,因此,美成为人们从感性的、经验的世界过渡到康德意义上的理性的、超验的世界的桥梁。这么说,有没有根据呢?有。根据就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人的本质是什么?黑格尔说是劳动;马克思也说是劳动,但与其他动物不同,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关键词是自由。自由的第一层意义就是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超越越多就越自由。而美就是自由的象征。美就意味着超越和自由,因为只有在超越了自己,超越了内在与外在的强制和压力,从而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美的诞生。美与超越不可分割,所以凡是讲到超越的地方总要讲到美。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3);孟子讲“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从人格修养的角度讲美和超越。人类学家马斯洛讲人的五种需要,讲自我实现,是从心理规律角度讲美和超越。康德讲美与崇高,合目的与目的,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黑格尔讲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海德格尔讲诗意的栖居等等,都是在各自哲学框架内讲美和超越。所有这些人都肯定了美的超越性质。
美之所以有超越性质是因为美有由直觉到想象,再到生命体验的逻辑秩序,这个秩序与人的存在、人的心理需要、人的自我实现是交织在一起的。首先,美存在于直觉中。克罗齐讲:“美是直觉”,中国传统美学讲,艺术要靠顿悟,什么意思?第一,直接性,不假思索;第二,瞬间性,没有耽搁;第三,交融性,主客合一。那位讲心理距离的心理学家布洛曾举过一个例子:傍晚,一艘船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船上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惊怖异常,失魂落魄。其中一个坐在船头的人忽然发现,这是非常壮观和具有戏剧性的场面。危险和恐怖在他眼中组合成了一种奇妙无比的美。他是讲心理距离,实际上也是讲直觉。晚清一位学人的随笔中有这么一段:他躺在蚊帐里,但蚊子很猖獗,竟一个个潜入蚊帐,自由自在地在他身边飞舞,并且傲慢地发出嗡嗡的声响。他不能入睡,只好靠在床头抽烟。起初,他欣赏着吐出的一朵朵烟圈和在烟圈里飞舞的蚊子,后来,在他眼里,烟圈宛如天空中的云雾,而蚊子宛如一只只飞翔的仙鹤。他越看越入神,越看越兴奋,竟忘了睡觉。直觉为什么会使人有愉悦感呢?因为它使人从日常境遇中超脱出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主体与客体对立,没有内在和外在迫力的世界,一个新奇的自由游戏的世界。所以说美作为直觉处在生命的根底部,这是因为直觉是作为生命整体的人与同样作为整体的对象之间直接、瞬间的碰撞和交融。人的每一个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每一种生理机能——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无一例外都介入其中。对象也是以其每一种表象——形象、色彩、秩序、节奏、气息、声音进入人的视野。幽深的峡谷,浩淼的海洋,灿烂的星空,苍莽的原野,如果给我们一种美的享受,都是因为我们身临其境,心与物化,既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对象的存在。艺术作品也是如此。欣赏《梁祝》或《二泉映月》,欣赏《茨菇游虾》(齐白石)或《群马》(徐悲鸿),不仅需要眼睛和耳朵,也需要鼻子、舌头和整个肢体。只有你心里有了酸楚,眼里涌着泪水,才会体验到音乐中“梁祝”的哀怨,瞎子阿炳的悲愁;只有你感到了一种悠然自得或紧张兴奋,才能够进入绘画里游虾和群马的世界。由此可见,与感觉、知觉不同,直觉是双向性的,一方面指向客体,一方面指向自身,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对话和交流,是一种显现和自我显现,观照和自我观照。
美使人回到了生命的根底部,回到了没有被分割、被异化的原初的自我。而且唯有美,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回到根底部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在于找到了超越和自由的起点。所谓超越和自由,不仅是感官、欲念、思想的超越和自由,而且是整个生命的超越和自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本质,包括感觉、想象、情感、欲望、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全面解放和均衡发展。在生命被肢解、被异化的状态下,是没有真正超越和自由可言的。金钱是把利刃,它会把人从社会机体中切割开来,撕掉人自身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最终完全失掉自我。伟大的进化论者赫胥黎在著名的《天演论》中称,进化就是“园艺过程”与“宇宙过程”间抗争的过程,认为“园艺过程”即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总是以牺牲“宇宙过程”即大自然生态系统,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禀赋为其代价。但是,“宇宙过程”毕竟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大自然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讨回她的儿子——人——从她那儿借去而加以安排结合的那些不为普遍的宇宙过程所欢迎的东西”。(14)美属于“园艺过程”,但从根本上说,属于“宇宙过程”,美的意义就是宇宙向被文明所分割、异化的人发出的呼唤,让人挣脱工具理性的压抑,回返感性;挣脱一切违反人性的僵化和虚浮的钳制,回返自然。
其次,美又存在于想象中,是一种生命的形式。想象联结着生命的根底部与超越部。这一点,康德讲得最为透彻。人们如何从悟性过渡到理性的呢?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是它“强攫”的结果。康德则认为是靠人的悟性—想象力—理性构成的内驱力。有许多的美不是在直觉中,而是在想象或主要在想象里。比如,小说、戏剧、电影、电视里描写的人物和场景,霸王别姬那种悲壮凄楚的美,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里;贾宝玉、林黛玉的那种欲吐不能的深情,也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里。甚至画面上的蒙娜丽莎的美,音乐中的《春江花月夜》的美,既是在直觉中,也是在想象里构成的。什么是想象呢?想象有许多种,审美活动中的想象是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想象就是将直觉中的一个个镜头、一处处场景、一幅幅画面、一段段旋律依照自己的理解和经验综合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意象或意境的过程。想象比直觉丰富和深邃,因为想象中融入了人的更多的理性、意志和情感的因素。英国的哲学家休谟说,想象是理智和意志间的使者。想象总是代表了一种意向和意志,总是体现了一种认识和理智,并总是以情感的形式逻辑地表现出来。因此,想象实际上是人作为生命整体对外在世界作出的回应。如果说直觉是一种无意识的创造活动,想象就是自觉地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在想象中,理智、意志和情感不再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就是想象自身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因而想象比直觉在更充分、更深刻的意义上实现了自我。所以说,想象是人的生命形式,因为是想象把人生存的空间与时间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不是想象,人凭什么把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看成自己的同类?凭什么把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看成是历史的绵延?如果不是想象,我们就不能肯定我们理解的真、善,就是或近似其他族类理解的真、善,而美在人类中就不具有可传达性。我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变化,翻开童年时的照片,与现在比,迥然是两个人,但是,想象根据零星的记忆告诉我,那就是我;想象并且为我设计了未来,使我能够跨越时间的隧道,形成一种对真、善、美的憧憬。想象不仅记录着我的成长过程,而且引导我超越有限的理智和意志,趋向一种更高、更理想的存在。
再次,美存在于生命体验中,是一种超越境界。这种美是我们直觉和想象不到的,但常常悬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看到一位俊男靓女,认为他(她)美,凭什么?我们走进一处风景,认为它美,凭什么?凭心中悬着的一种美的理想。如果这种美的理想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人类群体或整个人类共同的理想,如果这种理想背后潜隐的不仅是“我”的审美经验,也是人类共有的“原始意象”或“理念”,那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超验之美了。超验之美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所以还在人类童年时期就被认识并表述出来了。马克思讲,古代希腊是人类的真正的童年。所以这么讲,原因之一就是希腊人怀有一种童稚般素朴的信念,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奥林匹斯山上还有一个神的世界,其中每个神都代表了一种自然力,相信就是这些神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却又像人一样充满了矛盾和纷争,具有七情六欲。后来,古罗马的衰败,绵延数百年的民族大迁徙,使人们更多的看到了人类自身丑恶的一面,以致失去了对现实的信心,皈依了基督教。从此诸神退位,上帝降临。超验之美是超越一切美之上的最高的美,是一切美之所以为美的根源;超验之美超越了什么?超越了有限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关有限的理性、意志和情感。由于超越了有限的存在,所以是绝对的、纯粹的,没有了能够与之对应的对立物——丑。由于超越了有限的理性、意志和情感,所以超验之美虽然悬在“我”的心中,却并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整个人类。超验之美之所以进入“我”的心中,不是“我”认识、欲念和期望的结果,而是“我”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体验或体认的结果。
超验之美对人们,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按照基督教神学的说法,上帝在世界的彼岸,又在世界的此岸,在我的心中。按照老庄的说法,道在自然,是为天道;道在人身,是为玄德。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作为客体,叫绝对理念;作为主体,叫绝对心灵。按照存在主义的说法,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此在是与存在相关联中的此在。面对超验之美,人不是一般意义地去欣赏或观照,而是“诗意的栖居”。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既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实践,又是一种崇高的文化精神。外在的与内在的是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所以费尔巴哈讲,上帝不是别的,就是人自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老子讲:“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15)庄子讲:“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16)只是因为有了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人的存在,超验之美才悬在人类的心中,成为人的一种信仰。但一般地说,我们都在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途中。我们心中的超验之美只是我们自己心灵和人格的写照。虽然人们都叫它是上帝、道或绝对理念,但由于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修养和文化水平的不同,所理解和体认的并不相同。如果你还没有学会谦卑,你心中的上帝就还不是真正的上帝;如果你还没有从人类中心主义跳出来,你所谓的共产主义就还是空想的乌托邦。在超验之美面前,我们永远是一个探索者,一个学生。超验之美对于人们的真正意义也就在这里:它是一盏高悬在未来的灯,不仅照耀着,而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行程。
四、爱:从形式、心灵到世界
从直觉之美到想象之美,再到生命体验,即超验之美能够把人引渡到以真、善、美的统一为标志的人生的终极境界吗?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直觉、想象、生命体验的背后有爱,而爱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生命的元素和冲动,是人类完善自我、走向文明的根本的内驱力。我们看到燕子飞来飞去地为它的孩子喂食,觉得很美,因为我们有爱。听说一条狗在主人遇难的地方没日没夜地守着,守了半年,会很感动,因为我们有爱。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那昂扬有力的音乐,那庄严肃穆的人群,那晨曦所投来的最初一抹光明,会使我们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因为我们有爱。直觉、想象和生命体验本身并不能触动我们,让我们感到欣慰和愉悦的是意识或没有意识到的爱的存在,是意识或没有意识到的与对象的亲近和交融。
透过美的秩序,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爱的秩序。美的秩序与爱的秩序实际上是同一个秩序的不同侧面。关于爱的秩序,西方学者讨论得比较多。它在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基督教神学家中几乎是一种传统。现代德国哲学家马科斯·舍勒专门写了一篇长文《论爱的秩序》,其中有一段名言:“爱的秩序是一种上帝的秩序”,“人属于爱的秩序,爱的秩序是人之本己的一部分”。(17)中国从先秦诸子起,历代学人也多有谈论的,是儒家和新儒家的一种基本的信念。所谓“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18);所谓“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19);所谓“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20),“仁民而爱物”(21)。爱和美一样根植于生命的本原处,是人的基本需要。按照马克思讲的,人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蜜蜂、蚂蚁和大部分哺乳动物也是类的存在物,但是,它们没有类的意识,类对于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人则不仅意识到自己的类,而且自觉地从属于类,所以,类成为挣脱自然的局限,获得自由的前提。因为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人借以维护类和自由的就不仅是性,还有爱。性将两性从生理上联结在一起,爱则将这种联结扩大到心理上,因而有了使这种联结能够保持稳定和持久的婚姻和家庭。随着文明的进步,爱超离性的关系越来越远,扩展到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扩展到整个部落、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和自然界。爱记录着人类进步的步伐,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当然,作为唯物主义者,还应该看到,爱虽然处在生命的根底部,但它的孕育和发展却是由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决定的,没有物质生产,没有社会交往,人只能停留在类人猿的阶段,听任性的摆布。
从直觉到想象,再到生命体验,也就是从个别到普遍,从物质到心灵,从具象到抽象,这既是美的秩序,也是爱的秩序。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把爱美看做是通往人的最高境界的途径,认为应从爱美的形体开始,由爱某一个美的形体,到爱其他的美的形体,由爱美的形体到爱形体美的形式。这就是说,爱,首先要靠直觉。然后,由爱美的形式到爱美的心灵,虽然心灵美未必形式也美。由爱美的心灵进而爱美的行为和美的制度以及各种学问知识。心灵和行为、制度、知识是在直觉之外的,所以得靠想象。再以后,爱就不再“像一个卑微的奴隶”,专注于某一个形体、形式或某一个人和行为上,而能“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在“心中起无限欣喜”的同时,“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彻悟美的本体”。到这个层次,就意味着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用生命去体验和享受那种心与物游,物我两忘的境界了。(22)爱的意义是发现美,从而让人走出自己,面向世界;美的意义是彰显爱,从而回返自己,实现自己。这就是人通向信仰之路,即自由之路。自由,一方面意味着融入整体——家庭、种族、国家、人类、宇宙,一方面意味着自我实现——感觉、知觉、记忆、想象、理智、意志、情感,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所有潜能的全面发展。单个的人无所谓自由,或者说根本没有自由。因为你还属于抽象的、自然的人,你或许有人的各种潜能,但这些潜能都不可能得到发挥。你是个男人,如果没有与女人结合在一起,你就不是男人,就没有做男人的自由。你是个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读者和听众,你就不是知识分子,就没有知识分子的自由。你是一个旅游的爱好者,如果没有山、水、森林、草原,没有大自然为你准备的一切,你就不可能有旅游的冲动。自由不是单个人的事,而是群体的事,人类的事。是康德讲的“伦理团体”的事。整体的意义既在于交往和协同,将人的智慧和才能融合在一起,形成文明和进步的力量,又在于为调动和发挥个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提供了可能。古人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又讲“至仁无亲”,“大爱无疆”。自由就是要一步步去发现世界的美,就是要把爱撒向整个世界。而这样就必须不仅从个人的恩怨悲欢中走出来,而且要从家庭、种族、国家走出来,走向人类和自然界。
五、自我确证,自我挑战,自我实现
康德讲,有两种信仰,一种是宗教信仰,一种是理性信仰。前一种信仰基于对人的原罪,即恶的意识,认为人天生就是情欲的产物,是被从伊甸园赶出来的;后一种信仰则基于对人的类本质的意识,认为人生来就是属类的,就有交往、同情和爱的需求。前一种信仰认为生活就是欲望,就是痛苦,世界就是苦难的深渊;后一种信仰则认为,世界处在进化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和社会实践推动着人类不断走向文明。前一种信仰是在人类之上设定一个神,一个救世主,把希望寄托在神——救世主的身上;后一个信仰则将一切原属于神的东西还给了人自己,认为对于善恶是非的最终裁决不是神,而是理性和良心。前一种信仰的目的在于救赎,是通过忏悔、供奉,循守教规以获得神的怜悯与赐福,遵循的是“我给予你,你给予我”交换原则;后一种信仰的目的则是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是为自己树立一种价值标准和理想境界,遵循的是“在奉献中确证自己,光耀自己”的原则。对于前一种信仰,爱与美是神固有的一种性质,神将自己的爱和美撒播在人间,只是为了确证自己并使人类和整个世界回归自己,所以,爱与美的秩序实际上是神彰显和回归自己的运作机制;对于后一种信仰,爱与美则是人类在数十万年中积淀下来的生命体验和经验,是人类用以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解放的心理机制。康德认为,从无宗教信仰到宗教信仰,再到理性信仰是历史展开的三个层次。我们不反对宗教信仰,但提倡和主张理性的信仰。这就是说,信仰,一方面意味着爱向邻人,向自然,向超验世界的逐步展开;另一方面意味着美在事物,在精神,在超验世界的逐步发现。这里有的是对现实和自我的超越,而不是厌弃和决绝;有的是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而不是悲观厌世的心理。人的最终目的是自由,自由就是包括七情六欲在内的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和统一,就是歌德讲的“我在世界中,世界在我身上”。正是在超验之美和对它的爱中,确证、体验自由,并享受着庄子所讲的“与天和”的那种“天乐”。(23)
注释:
①在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同书》中,康有为表达了他对大同世界的信仰,破九界是其基本的内容,包括“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
②这次世博会上,以色列馆里陈列着爱因斯坦1938年的《写给5000年后子孙的信》,上面表达了他对现实世界的忧虑,最后有这么一段话:“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应当怀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来阅读上面这行文字吧。”
③《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斐德若》,朱光潜译,第1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④[意]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4页,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⑤[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第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⑥[俄]别尔嘉耶夫:《美是自由的呼吸》,方珊等选编,第66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
⑦《孟子·尽心下》。
⑧《庄子·天道》。
⑨《庄子·知北游》。
⑩孙周兴编选:《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27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1)[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第70页。
(1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第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3)《论语·泰伯》。
(14)[法]赫胥黎:《天演论》,第8-9页,《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
(15)《道德经》第二十三章。
(16)《庄子·田子方》。
(17)[德]舍勒:《爱的秩序》,第48页,林克等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5。
(18)《论语·学而第一》。
(19)《中庸》第二十五章。
(20)《孟子·尽心下》。
(21)《孟子·尽心上》。
(22)[古希腊]柏拉图:《会饮篇——论爱美与哲学修养》,朱光潜译,见《朱光潜全集》,第12卷,第232-23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23)庄子在《天道》中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又说:“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为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一蓄天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