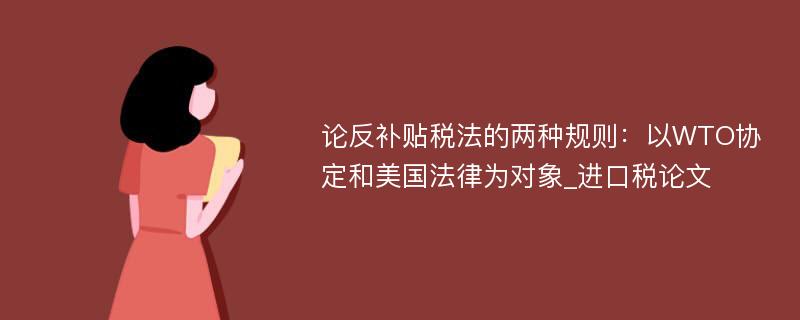
论反补贴税法中的两类规则:以WTO协定和美国法为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法论文,和美论文,协定论文,国法论文,两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反补贴法中,对补贴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涉及两类性质不同的规则: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以下简称《SCM协定》)第19.2条明确指出,就反补贴税的征收问题,进口成员的主管机关可作出:“在所有征收反补贴的要求均已获满足的情况下是否征税的决定”,以及“征收反补贴税金额是否等于或小于补贴的全部金额的决定”。理论上,课税与否规则与税额确定规则的功能有别,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也不全然相同。前者调整的是纳税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用于确定主权国家是否有权对特定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后者调整的是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关系,用于确定征税机构对该进口产品征收多少的反补贴税。①相应地,在理解和分析相关反补贴税法律问题时,也应分别讨论上述两类规则。 但是,受立法理念、技术和历史原因所限,在具体条文表述方面,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往往未能被严格区分。如美国的反补贴法规定,反补贴税的金额应等于净可抵消补贴金额。该强制性规定客观上促成了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的混同,即只要满足课税与否的构成要件,则必然引发征收确定金额反补贴税的法律后果。对于此类规定,更为精细的分析应当分为两步:第一步讨论,当满足何种构成要件时,主权国家才能征收反补贴税;第二步讨论,如果主权国家有权征收反补贴税,则满足何种构成要件时,方能最终确定反补贴税的金额。 表面上看,上述两步分析法显得有些繁琐。但是,正是这种分析上的行必矩步,才能保证法律体系设计的初衷和完整性,并不至于在复杂的争议中迷失方向。特别是,反补贴法的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往往共享两个构成要件——补贴金额和损害。如果不区分这些构成要件的规则语境,则很容易过度夸大或压缩其法律地位和功能。近期,中美之间关于“双重计算”和“双重救济”的法律争议就在一定程度上混同了这两类规则,而与之相关的法律推定、法律分析和法律结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② 由于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就补贴金额的计算设立了特定规则,致使美国可利用本国反补贴法中的规则混同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反补贴税。这意味着,仅仅防止“双重计算”和“双重救济”不足以遏制美国对中国产品的系统性歧视。因此,对于规则混同的反补贴立法和实践,应严格区分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确定补贴金额和损害等构成要件的适用边界,并限制调查主管机关利用规则混同,实施惩罚性贸易救济措施。本文第一部分讨论课税与否规则中的补贴金额和损害问题。在《SCM协定》下,补贴金额是决定是否征税的构成要件之一,上诉机构倾向于采取非扭曲市场基准计算补贴金额。无论在补贴金额的计算方面,还是在损害的确定方面,调查主管机关均被赋予了较大的裁量权。第二部分讨论税额确定规则中的补贴金额和损害问题。在美国反补贴法下,补贴金额是决定税额的唯一尺度,美国商务部采用非扭曲市场基准计算补贴金额,并以此确定最终反补贴税的金额。然而,在《SCM协定》下,补贴金额仅是可收取税额的上限,损害的幅度将影响到税额的最终确定。第三部分讨论WTO上诉机构和美国商务部在分析两类规则时的方法论问题。规则混同要么导致相关构成要件的“越界”,要么导致相关构成要件的“虚置”。但是,上诉机构过度区分两类规则也引发了关于征收反补贴税目的的争议。第四部分则以《SCM协定》的实体规则为对象进行分析,认为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既非保障国内产业利益也非促进全球经济效率,而是救济进口国因补贴所受的不利影响。第五部分则根据救济进口国因补贴所受的不利影响这一目的,对《SCM协定》的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做一合理化说明,并总结全文。 一 课税与否规则中的补贴金额与损害问题 (一)不同的课税与否规则 WTO关于征收反补贴税的规则散见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994)第6条和《SCM协定》第19.1条之中。GATT 1994第6条规定了两类特别关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其中,第6.1条规定了较为完整的征收反倾销税的规则。而关于反补贴税的征收规则则需结合第6.3条和6.6条的规定来确定。根据第6.3条,“反补贴税”一词应被理解为目的为抵消对制造、生产和出口所直接或间接给予的津贴或补贴而征收的一种特别税。根据第6.6条,只有在确定补贴的效果会对国内一已建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建立时,才能征收反补贴税。就此,第6.3条和第6.6条分别列出了两个重要的征税构成要件:补贴和损害。 相对而言,《SCM协定》第19.1条的规定更为明确和详细。根据该条,WTO成员就补贴的存在和金额作出最终裁定,并裁定通过补贴的影响,补贴进口产品正在造成损害时,可征收反补贴税。与GATT 1994第6条相比,《SCM协定》第19.1条特别提及补贴金额。③ 尽管《SCM协定》第19.1条规定了明确的征税规则,但美国反补贴法并不与之完全一致。究其原因,早在WTO成立之前,美国已存在反补贴法,其历史可追溯到《1890年关税法》,其间经过《1897年关税法》的修正,于《1930年关税法》得以定型。④就课税与否规则而言,上述反补贴法仅要求存在补贴即可,并没有关于损害的规定。显然,这与当时《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947)第6.6条的要求不符。然而,基于“祖父条款”,在《1974年贸易法》中,美国仍未改变其原有的课税与否规则。直至东京回合结束,国会才在《1979年贸易协定法》中有条件地加入损害要件,以与《补贴守则》保持一致。其后,反补贴法历经《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以及《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之修正,基本架构未发生根本变化。 当前,美国反补贴法存在两套课税与否规则:一般情况下,只要调查主管机关确定,就进口(或销售用于进口)产品的生产、制造和出口等方面存在可抵消补贴,则应对该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而当相关产品来自于补贴协议国家,则只有在委员会确定,因为该产品之进口(或销售用于进口),美国产业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征收反补贴税。⑤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补贴协议国家,因此,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相关课税与否规则包括两个构成要件:补贴与损害。 (二)补贴金额的计算 如上所述,在美国反补贴法中,只要存在可抵消补贴和损害,就能征收反补贴税,补贴金额并非是课税与否规则的构成要件。但是,《SCM协定》第19.1条明确规定,只有就补贴的存在和金额作出最终裁定,一成员才能征收反补贴税。因此,在WTO的课税与否规则中,补贴金额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SCM协定》第14条就如何计算补贴金额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标题是“以接受者所获利益计算补贴金额”。这意味着,补贴金额的计算应采接受者受益说,而非政府财政成本说。在加拿大——民用航空器案中,就何为“利益”,上诉机构提出一个影响深远,被其后争端反复引用的观点:⑥“我们还相信,第1.1(b)条的‘利益’一词,隐含着某种程度的比较。一定是这样,因为,除非‘财政资助’要使接受者‘好于’没有资助时的情况,否则不存在‘利益’。在我们看来,在确定‘利益’是否被‘授予’时,市场为比较提供了适当基准。因为,通过确定接受者获得的‘财政资助’的条件优于市场中的可获得条件,可以辨认出一项‘财政资助’的贸易扭曲潜能。”⑦上诉机构观点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市场基准有助于确定“利益”是否被“授予”,因而有助于确定补贴是否存在;二是接受者所获“利益”的大小与“财政资助”的贸易扭曲潜能相对应。 上诉机构将市场视为计算补贴金额之基准的观点有其成文法的依据。比如,对于股本、贷款和贷款担保等补贴形态,《SCM协定》第14条之(a)、(b)、(c)三项规定,可与“通常做法”或“可比商业”做比较,计算补贴金额。而对于政府提供货物或服务,或购买货物这一补贴形态,《SCM协定》第14条之(d)项更是明确地采用了市场基准,即“报酬是否充分应与所涉货物或服务在提供国或购买国现行市场情况相比较后确定”。 但是,上诉机构将接受者所获“利益”的大小与“财政资助”的贸易扭曲潜能相对应并没有明确的成文法依据。比如,《SCM协定》第14条的导言要求,任何补贴金额的计算方法应与该条所列举的四个准则相一致。任何方法意味着计算补贴金额不止一种方法,⑧而与准则相一致,意味着计算方法不抵触准则即可。《SCM协定》第14条所列举的四个准则虽然提及市场基准,但并没有说明相关市场应是现实市场(Market-As-Is)还是非扭曲市场(Nondistortion Market)。尽管如此,在如下一系列案件中,上诉机构倾向于将非扭曲市场基准认定为计算补贴金额的主导标准,将补贴与贸易扭曲潜能联系在一起。 首先,对于股本投资,《SCM协定》第14条之(a)项规定,政府提供股本不得视为授予利益,除非投资决定可被视为与该成员领土内私营投资者的通常投资做法不一致。从该条提及“该成员领土内私营投资者”以及“通常投资做法”中,一个直观的印象是,(a)项允许采用现实市场作为基准,计算补贴金额。然而,上诉机构却倾向于采取“理性投资者”和“未受限制”的交易条件等建构的非扭曲市场基准。如在日本——动态存储器(韩国)案中,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当确定破产企业重整所授予的利益时,是否应将投资者区分为内部(现存)投资者和外部(新进)投资者,并依不同的视角确定补贴金额?对此,上诉机构认为,将投资者区分为内部和外部无助于确定适当的计算基准。因为,金融交易的条件必须与相关市场中未受限制的交易条件相比较。而且,只存在单一市场标准,为理性投资者所奉行。⑨显然,这一论述传达着非常明确的非扭曲市场基准信号。 其次,对于贷款,《SCM协定》第14条之(b)项规定,政府提供贷款不得视为授予利益,除非接受贷款的公司支付政府贷款的金额不同于公司支付可实际从市场上获得的可比商业贷款的金额。措辞上,该条明确提及“可实际从市场上获得”,似乎指的就是现实市场基准。然而,在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国)案中,上诉机构赞同专家组的观点,即第14条之(b)项足够灵活,当不能发现“商业”基准时,允许使用替代利率来取代所涉国家中的利率。就何为“商业”基准,上诉机构如此论证:“政府提供贷款这一事实本身不足以说明该贷款不是‘商业’的,也不能因此认为其不能作为《SCM协定》第14条之(b)项下的基准。调查主管机关应当确定,政府在市场中的存在或影响导致了扭曲,从而使利率不能用作基准。”⑩在此,上诉机构明确指向了非扭曲市场基准。 最后,就货物和服务,《SCM协定》第14条之(d)项规定,政府提供货物或服务或购买货物不得视为授予利益,除非相关报酬不充分。报酬是否充分,应与所涉货物或服务在提供国和购买国现行市场情况相比较后确定。措辞上,该条提及“现行市场”,似乎支持境内现实市场基准。事实上,美国——软木IV案的专家组就是这么理解的。然而,上诉机构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调查主管机关可使用不同于提供国私人价格的基准来计算补贴金额。对于这一明显偏离字面含义的解释,上诉机构首先指出,为确定报酬是否充分,可将境内的私人独立交易价格作为分析的起点,然而,如果政府在提供货物中占主导地位,并导致该国市场中的私人价格被扭曲,则调查主管机关可使用其他基准。然后,上诉机构又指出,为确保其他基准与“现行市场”有关,调查主管机构应作出调整,不能将之用作抵消国家间相对比较优势的工具。(11)显然,在上诉机构看来,不管境内“现行市场”有多重要,只要被政府补贴所扭曲,就有可能失去基准资格。 虽然上诉机构基本认同非扭曲市场基准,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其没有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现实市场被扭曲到何种程度才失去基准资格;二是何种非扭曲市场可作为替代基准。就此,上诉机构认为,应在个案基础上,依调查的事实之不同加以判断。无论从国内法角度,还是从国际法角度,这一观点相当于赋予调查主管机关以较大裁量权。(12) (三)损害的确定 如上所述,为履行美国的国际义务,国会修正《1979年贸易协定法》,对来自于补贴协议国家的产品,添加了损害要件。问题是,该添加有所保留,并没有完全体现当时国际协定的要求。如《补贴守则》第4.4条明确要求,应裁定通过补贴的影响,补贴进口产品正在造成损害,缔约国才可以征收反补贴税。而美国的反补贴法仅规定,如果委员会裁定,因补贴进口产品之“进口”或“销售用于进口”造成损害,则应征收反补贴税。就此,《补贴守则》中所要求的“通过补贴的影响”这一要素被忽略了。 WTO的《SCM协定》第19.1条全文承继《补贴守则》第4.4条。因此,就损害要件而言,只有一成员裁定:(1)通过补贴的影响;(2)补贴进口产品正在造成损害,方能征收反补贴税。 1.通过补贴的影响 就损害要件的第一个部分——通过补贴的影响,《SCM协定》第15.5条再次强调,“必须证明通过补贴的影响”,补贴进口产品正在造成损害。理论上,既然上诉机构将补贴接受者获得的利益界定为相对于市场,特别是相对于非扭曲市场所获得的额外好处,那么补贴的影响也应体现在对接受者市场行为的影响之上。(13)为此,调查主管机关应分析,补贴是否降低了接受者生产的边际成本,并降低了补贴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等。(14)然而,实践中,几乎没有调查主管机关进行此类审查。(15)究其原因,除了相关经济数据难以获取,行政成本较高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律上的:《SCM协定》中,针对“必须证明通过补贴的影响”存在一条注释,即“按第2款和第4款所列”。依此注释的表面含义,如果调查主管机关按《SCM协定》第15.2条和第15.4条所列条件进行了审查,就可以满足“必须证明通过补贴影响”这一要求。问题在于,第15.2条和第15.4条仅仅规定如何审查补贴进口产品的影响,并没有指向补贴的影响。如何理解其间的差异? 在日本——动态存储器(韩国)案中,韩国提出,既然《SCM协定》要求证明补贴的影响,则调查主管机关应审查双重因果关系,即补贴导致补贴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或影响价格,并因此而影响到国内产业。对此观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不认同。在它们看来,注释的要求非常明确,调查主管机关只需按第15.2条和第15.4条的要求审查即可,无需再单独证明补贴的影响。上诉机构还指出,《SCM协定》第15.5条规定,调查主管机关还应审查除补贴进口产品外的、正在损害国内产业的任何已知因素,且这些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因于补贴进口产品。这意味着,即使不直接确定补贴与补贴进口产品之间的因果关系,仍可以通过排除法,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16) 不可否认,日本——动态存储器(韩国)案中,上诉机构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上诉机构的解释使第15.2条和第15.4条取代了第15.5条中的“必须证明通过补贴的影响”这一规定,有可能违反条约有效解释原则。(17) 其二,第15.5条的不得归因要求仅针对“国内产业”的任何已知因素,但“证明通过补贴的影响”并不直接针对“国内产业”,而是针对补贴进口产品。因此,在不得归因的要求下,被排除的是那些影响“国内产业”的因素,而非影响补贴进口产品的因素。 因此,总体上,上诉机构在日本——动态存储器(韩国)案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尽管如此,在其被正式推翻之前,上述将补贴进口产品的影响审查等同于补贴的影响审查的观点仍将持续发挥影响。 2.补贴进口产品正在造成损害 对于补贴进口产品正在造成的损害,《SCM协定》第15.1条规定,应包括对两个内容的客观审查:一是补贴进口产品的数量和补贴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二是这些产品随之对此类产品国内生产者产生的影响。 就补贴进口产品的数量问题,《SCM协定》第15.2条规定,调查主管机关可通过三种方式加以审查:(1)补贴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是否大幅增加;(2)相对于国内生产,补贴进口产品的相对数量是否大幅增加;以及(3)相对于国内消费,补贴进口产品的相对数量是否大幅增加。就补贴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问题,第15.2条规定,调查主管机关同样可通过三种方式加以审查:与进口成员同类产品的价格相比,(1)补贴进口产品是否大幅削低价格;(2)补贴进口产品是否大幅压低价格;以及(3)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在其他情况下本应发生的价格增加。就产品对国内生产者产生的影响,《SCM协定》第15.4条规定,调查主管机关应审查包括对影响产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经济因素和指标的评估。《SCM协定》第15.2条和第15.4条均强调,就上述所有审查,相关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均未必能给予决定性的指导。这意味着,对于损害确定,调查主管机关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如欧共体——动态存储器芯片反补贴措施案的专家组认为,任何确定损害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在《SCM协定》未规定方法的情况下,只要相关确定方法不是不合理,则专家组没有理由加以反对。(18)这一观点的实质在于承认,调查主管机关拥有较大的裁量权。 二 税额确定规则中的补贴金额和损害问题 (一)不同的税额确定规则 如同课税与否规则,WTO的税额确定规则也散见于GATT 1994和《SCM协定》之中。相关内容涉及三个方面: 其一,税额上限。GATT 1994第6.3条规定,反补贴税的金额不得超过“此种产品在原产国或出口国制造、生产和出口时所直接或间接给予的津贴或补贴的估计金额”。《SCM协定》第19.4条就税额的上限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即“对任何进口产品征收的反补贴税不得超过认定存在的补贴的金额”,而且,“该金额以补贴出口产品的单位补贴计算”。 其二,最佳税额。《SCM协定》第19.2条规定,如反补贴税小于补贴的全部金额即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该反补贴税是可取的(desirable)。 其三,适当税额。GATT 1994第6.5条规定,不得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补偿(compensate)倾销或出口补贴所造成的相同情况。(19)《SCM协定》第19.3条规定,如对任何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则应对已被认定接受补贴和造成损害的所有来源的此种进口产品根据每一案件的情况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收取适当金额的反补贴税。《SCM协定》第21.1条规定,反补贴税应仅在抵消造成损害的补贴所必须的时间和限度内实施。 与WTO相对复杂的规定有所不同,在美国反补贴税法中,就税额确定不存在税额上限、最佳税额和适当税额等之分,而只有一个强制性要求:对进口补贴产品征收的反补贴税应等于净可抵消补贴的金额。该强制性规定由来已久。如《1897年关税法》在将《1890年关税法》中的从量反补贴税修改为从价反补贴税时,就明确要求,应征收与外国政府给予的补贴相等的反补贴税。(20)其后,虽历经修正,反补贴税额等于补贴金额的规定一直未变。 (二)补贴金额的计算 在《SCM协定》法律框架下,补贴金额既是课税与否规则的构成要件,也是税额确定规则的构成要件。(21)但是,在美国的反补贴法下,补贴金额仅是税额确定的构成要件。 1.《SCM协定》中补贴金额的“当前”存在 根据《SCM协定》第19.4条,作为税额确定规则的构成要件,补贴金额并不决定最终的反补贴税的金额,而只是后者的上限而已。不仅如此,相关补贴金额必须是被“认定存在”。之所以加上该定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发动反补贴调查到作出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之间存在时滞,在这段时间内,偶生性补贴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复存在。而根据《SCM协定》第21.1条,“反补贴税应仅在抵消造成损害的补贴所必须的时间和限度内实施”。在日本——动态存储器(韩国)案中,日本调查主管机关将发生于2001年的偶生性补贴分配在2001~2005年期间,但直至2006年才征收反补贴税。就此,专家组首先承认,为确定补贴的存在,调查主管机关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过去的调查才能得出结论。但是,调查期间的状况只是征税时相关状况的映像,就偶生性补贴而言,如果经审查,在征税时,调查期间的补贴不复存在,那么,在调查期间存在的补贴不足以证明征税时存在“当前”补贴。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的观点,并指出,如果在补贴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征收反补贴税,则税收金额必然超过补贴金额,从而直接违反《SCM协定》第19.4条的规定。(22) 总而言之,不同的规则对补贴金额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仅就数量而言,课税与否规则项下的补贴金额并不必然等同于税额确定规则项下的补贴金额。特别是对于那些偶生性的补贴而言,当调查主管机关确定对补贴进口产品征税时,必须还要确定还有多少相关补贴仍然继续存在。不仅如此,根据第19.3条,如对任何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则税额应符合“适当金额”的要求。因此,即使对于那些持续存在补贴而言,并非所有的补贴金额均应被相同数额的反补贴税所抵消。 2.美国反补贴法中补贴金额的计算 与《SCM协定》第19.1条不同,在美国反补贴法下,补贴金额是税额确定要件,而非课税与否要件;与《SCM协定》第19.3条不同,在美国反补贴法下,补贴金额就是征收反补贴税的尺度,而非上限。这一制度上的不同,直接导致补贴金额的计算问题与贸易救济的强度问题相挂钩。也使得《SCM协定》的精心设计——严格区分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并严格限制补贴金额的适用范围——变成了马其诺防线。而由此导致的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是,原本在课税与否规则下就充满争议的非扭曲市场基准可否继续用于确定反补贴税的金额?就此,美国的立法和实践均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如前所述,早在GATT和WTO就反补贴设立规则之前,美国已经存在反补贴法。但是,长期以来,美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计算补贴金额,这就赋予了相关主管机构以较大的裁量权。而补贴金额的计算基准也屡经变迁。 (1)市场基准的确立 美国早期的反补贴立法既没有界定补贴的定义,也没有说明如何计算补贴金额,而只是强制要求,反补贴税的金额应等于补贴的金额。直至1979年,为履行东京回合所达成的各类守则,美国国会通过《1979年贸易协定法》修正《1930年关税法》若干条款。其中,就反补贴条款,添加了出口补贴和国内补贴的例示清单。在国内补贴例示清单里,相关措辞为引入市场基准计算补贴金额创造了空间。具体而言,《1979年贸易协定法》以例示的方式提及四类国内补贴:(1)以与商业考虑不一致的方式,提供资金、贷款或贷款担保;(2)以更为优惠的报酬,提供货物或服务;(3)为弥补特定产业所遭受的经营损失,提供资金或减免债务;(4)承担生产、制造和分销的任何成本或费用。(23)上述(1)所提及的“商业考虑”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基准,而(3)和(4)也隐含着市场基准。不过(2)却提到另一个标准——优惠基准。按照美国商务部在加拿大木制品案中的解释,所谓优惠指的是在同一管辖区内,优于其他人。(24)据此,优惠基准中,比较的对象是“其他人”而非“市场”。 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乌拉圭回合协定法》,几乎逐字逐句将《SCM协定》第14条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这意味着,在立法层面,市场基准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新的反补贴规章。就政府提供的补助、贷款、贷款担保和股本等,采用市场基准计算补贴金额;对于政府提供货物或服务,或购买货物,美国商务部采取了三个层次的市场基准来确定相关报酬是否充分:(1)被调查国境内实际交易的市场价格;(2)被调查国购买者可能获得的世界市场价格;或(3)评估政府价格与市场原则是否一致。(25)依此,《1979年贸易协定法》所提及的优惠基准几无立足之地。 (2)现实市场基准与非扭曲市场基准之争 为计算补贴金额,需要借助市场基准已成为共识。但是,市场既可能是被补贴所扭曲的现实市场,也可能是未被补贴所扭曲的市场。那么,在计算补贴数额时,应以何者为准? 尽管美国立法并未明确提及何种市场基准,但社会环境已经为非扭曲市场基准入侵美国反补贴法做好了准备。1981年,美国里根总统上台,新古典经济学进入鼎盛时期,相信市场力量,反对政府干预成为共识。在此背景下,1983年11月,美国大西洋、大陆、乔治城和力登四家钢铁公司代表美国钢铁业协会,要求对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碳钢盘条实施反补贴调查,此为著名的波兰碳素钢盘条案。该案被美国商务部视为一次契机,使其“第一次有机会初步裁定,就所谓非市场经济(NME)国家政府的行为,是否会授予可抵消的利益”。(26)也就是在界定补贴的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引入了非扭曲市场基准。 该案中,美国商务部先是设想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完美竞争市场,即“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稀缺资源被分配到他们最有效率和最盈利的用途之上”。然后,认为补贴具有市场扭曲效应,即“我们相信,补贴(奖励或补助)应被定义为一种扭曲或颠覆市场过程并且导致资源错配的行为,它促进无效率生产并降低世界福利。”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现实市场符合上述特征。对此,美国商务部以非扭曲市场来替代完美市场,认为只要私人拥有资源是规则而非例外,政府仅仅干预而非取代资源配置,则补贴行为就从作为背景的市场体系中被辨别出来。企业所获得的补贴金额相当于市场待遇和特殊待遇之间的差额。(27)因此,在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学理论中,非扭曲市场而非现实市场成为计算补贴金额的基准。 对于中国产品,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b)条明确规定,如果适用《SCM协定》第14条遇有特殊困难,“则该WTO成员方可使用考虑到中国国内现有情况和条件并非总能用作适当基准这一可能性的确定和衡量补贴利益的方法”。(28)这一规定为美国商务部普遍适用非扭曲市场基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9)实践中,以2007年的铜版纸案为开端,(30)在针对中国产品的一系列案件案中,美国商务部就贷款补贴、投入补贴、土地补贴等事项,使用非扭曲市场作为计算补贴的基准。对此,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国)案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不反对美国这一做法。美国商务部的裁量权获得充分尊重。(31) 从优惠基准和市场基准并立,到市场基准一枝独秀,再到非扭曲市场基准独占鳌头,其间的是非曲直还有待法律史家钩沉。在补贴金额计算基准的演进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商务部一直持有完美市场之尺,并以此来测度现实市场,合则留用,不合则摒弃。如美国商务部所言,此类模式的方法论根基,在于将补贴界定为对市场过程的扭曲。(32)既然用于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是完美的,则扭曲市场过程的补贴必然本身为恶。那么,相关反补贴税的金额等于补贴金额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损害的影响 根据美国反补贴税法,最终确定的反补贴税金额应等于补贴金额,与损害幅度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进一步讨论损害问题似乎有些多余。然而,《SCM协定》的税额确定规则却明文提及损害问题。如何确定损害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计算损害幅度,成为法律争议重心所在。 1.损害的法律地位 在《SCM协定》的税额确定规则中,首要的问题是,损害是否为其中的一个要件?就此,《SCM协定》第19.2条、第19.3条和第21.1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提示。 第19.2条指出,如果反补贴税小于补贴的全部金额即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该反补贴税是可取的。该条为典型的倡导性条款,并无法律拘束力。在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国)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第19.2条的目的是鼓励调查主管机关将实际的反补贴税金额与拟移除的损害相联系。第19.3条规定,应对“造成损害”(causing injury)的补贴进口产品收取适当数额。对该强制性要求,上诉机构指出,一旦证明补贴进口产品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收取反补贴税就不能脱离对相关损害的考量。第21.1条的规定更加明确,反补贴税应仅在抵消造成损害的补贴(subsidization which is causing injury)所必须的时间和限度内实施。结合上述条款,上诉机构认为,反补贴税的目的之一在于:抵消或中和损害性补贴,并且移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这意味着,“反补贴税的适当金额并非与所造成的损害无关”。(33) 2.损害幅度的计算 受案情及事实所限,在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国)案中,上诉机构就反补贴法的目的做出上述界定,并指出损害可能影响到税额的确定之后,并没有将分析进行下去。 然而,既然上诉机构将反补贴的目的界定为抵消和中和损害性补贴、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那么,反补贴税金额并不必然等于补贴金额,甚至并不必然与补贴金额存在比例关系。而更为合理的推定是,反补贴税的金额应与补贴进口产品所造成的损害幅度成正相关关系。易言之,在税额确定规则中,应当主要由损害幅度而非补贴金额来确定税额的适当性。 不同于补贴金额的计算,《SCM协定》并未就如何计算损害幅度制定准则。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第15条的若干规定中窥得一斑。具体而言,根据《SCM协定》第15.1条、15.2条和第15.4条,损害幅度可通过如下几个指标加以表示:补贴进口产品的数量;补贴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影响;这些产品随之对此类产品国内生产者的影响。由于《SCM协定》强调,在确定这些影响时,相关因素的一个或多个均未必能给予决定性的指导,因此,调查主管机关将具有较大的裁量权。 三 规则的混同与区分 (一)规则混同中的要件“越界”和“虚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课税与否规则与税额确定规则同属反补贴税法律组成部分,但两者在构成要件上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某些要件——如补贴金额和损害同时出现在不同的规则中,其法律地位、功能和作用也不完全相同。而美国反补贴法的问题是,在立法层面混同了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在实践层面则造成相关要件的“越界”或“虚置”,既降低了征税的门槛,又增加了税收负担。 首先,在美国反补贴法的课税与否规则下,尽管也存在补贴和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等要件,但在相关要件的完整性方面存在问题。如就补贴要件而言,《SCM协定》要求,调查主管机关在决定是否征收反补贴税之前,应裁定补贴的存在和金额,而美国的反补贴法仅要求商务部裁定存在补贴;就损害要件而言,《SCM协定》要求,调查主管机关应裁定,通过补贴的影响,补贴进口产品造成损害,而美国的反补贴法仅要求委员会确定补贴进口产品造成损害即可。仅从构成要件而言,(34)补贴金额和通过补贴的影响两个因素被“虚置”,实质性地降低了征税门槛。 表面上看,在课税与否规则下的补贴要件中加入补贴金额要素似乎毫无意义,毕竟,在美国反补贴法的语境下,一旦美国商务部决定征收反补贴税,必然要计算补贴金额。但是,2007年发生的GPX案较为典型地说明“虚置”构成要件导致的后果。该案源于泰坦和普利司通两家美国生产轮胎的公司就代表美国轮胎生产业向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产非公路用轮胎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2008年8月和9月,商务部与国际贸易委员会分别作出肯定性终裁,中国轮胎生产商被同时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2008年9月,因不满商务部的裁决,GPX联合兴茂轮胎以及其他中国轮胎生产商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开启了GPX系列诉讼之路。(35)在 GPX II案中,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认为,由于商务部计算补贴金额的方法存在潜在的重复计算问题,在解决该问题之前,商务部不应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36)以执行GPX II案的判决为名,商务部采用了分别计算、单独剔除和汇总确定的方法来避免双重计算问题。具体而言,首先,商务部分别确定NME国家产品的补贴金额和倾销幅度;其次,商务部在反倾销税额中扣除反补贴税额;最后,商务部加总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以确定保证金率。这一计算方法固然有助于防止双重计算,但也使得反补贴调查无意义。就此,商务部认为,根据反补贴法,其负有强制性的义务实施反补贴调查。而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认为,根据成文法条款以及此前的案例,商务部拥有裁量权,因此,在未能解决好双重计算问题之前,不应对NME国家产品实施反补贴调查。(37)显然,商务部倾向于将补贴金额视为税额确定要件,而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似乎将补贴金额视为课税与否要件。如果是前者,即使存在双重计算问题,仍然可以决定征收反补贴税,并在税额确定阶段进行调整;(38)如果是后者,如果存在双重计算问题,则不应施加反补贴税。 其次,在美国反补贴法的税额确定规则下,损害要件被排除,仅通过补贴金额来确定反补贴税额。问题在于,《SCM协定》仅将补贴金额作为税额的上限,而非要求两者相等。实际上,如果要使《SCM协定》中补贴金额的上限要求发挥作用,则必然存在依其他标准确定反补贴税的金额,并且该最终金额有可能超出补贴金额这一情形。而按照美国反补贴法的强制性要求,虽然反补贴税的金额不会超出补贴金额上限,但也必然排除了依据其他标准,比如损害幅度来确定反补贴税金额的可能性。而按照损害幅度来确定反补贴税的金额并不必然超出补贴金额。因此,通过补贴金额的“越界”和损害幅度的“虚置”,美国反补贴法实质性地提高了反补贴税的金额。 综上所述,通过混同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美国反补贴法实质上对补贴进口产品构成了系统性歧视,与《SCM协定》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规则区分中的一致性问题 《SCM协定》第19.2条明确规定,调查主管机关应分别就是否征税和征收多少税额作出决定。这里传达了极为明确地区分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的信号。而上诉机构也在一系列案件中,澄清了两类规则中的一些关键性法律问题。然而,在分析中,上诉机构就不同的规则下采取了不同的学说,从而引发规则间逻辑上的不一致。 1.课税与否规则中的贸易扭曲潜能说 总体上,《SCM协定》19.1条是一条非常完备的关于课税与否规则的条文。《SCM协定》第14条和第15条则分别对课税与否规则中的两个关键要件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就补贴金额的计算问题,争议主要集中在市场基准特别是非扭曲市场基准的选择之上;就损害的确定问题,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需要直接证明补贴的影响之上。 首先,就补贴金额的计算,上诉机构以补贴的贸易扭曲潜能来说明市场基准的合理性。但这一观点必然引发现实市场是否已经被扭曲,是否有必要引入非扭曲市场基准等的争论。如在影响深远的加拿大——民用航空器案中,为判断“利益”之存在,上诉机构引入了市场基准,这本身无可厚非。毕竟对于贸易活动而言,市场天然是衡量利益的基准。问题在于,上诉机构为市场基准所提出的理由——通过确定接受者获得的“财政资助”的条件优于市场中的可获得条件,可以辨认出一项“财政资助”的贸易扭曲潜能——则并非那么明确。理论上,将利益等同于贸易扭曲潜能需要满足两个前提要件:一是补贴本身为恶,必然具有贸易扭曲性;二是被接受者所获得的利益将全部传导到补贴进口产品之上。然而,《SCM协定》本身就承认某些补贴无贸易扭曲性;(39)而利益全部传导到补贴进口产品之上需要满足极为严苛的条件。(40)因此,上诉机构的贸易扭曲潜能说本身已经隐含了一种对补贴的偏见。其后,在一系列的案件中,上诉机构基本认同调查主管机关采取非扭曲市场基准,这显然将支持采取市场基准的理由当成了结论。原本隐含的对补贴的偏见成为分析补贴金额计算问题的持久立场。 其次,就损害的确定,上诉机构认为,通过审查补贴进口产品的影响,可以证明补贴的影响。这一观点完全忽略了补贴特有的传导机制,并夸大了补贴的贸易扭曲效应。如在日本——动态存储器(韩国)案中,上诉机构无视补贴金额并不必然全部传导到补贴进口产品,以及即使传导到进口产品,也并不必然影响出口价格等事实,在面对“必须证明通过补贴的影响”这一规定时,扩张解释相关注释,主张调查主管机关可通过审查补贴进口产品的影响这一中介,来满足该证明要求。如果撇开狭义的字面解释方法,为上诉机构的解释寻找合理性的根基,则贸易扭曲潜能说再一次映入眼帘。换言之,在计算补贴金额时,上诉机构认为,相关计算结果可以反映出补贴的贸易扭曲潜能。这一观点必然隐含地假定,补贴会影响补贴进口产品,并通过后者扭曲贸易。这意味着,在贸易扭曲潜能说下,根本无需证明补贴进口产品所造成的损害是通过补贴的影响所致。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就如何理解和适用课税与否规则,上诉机构持有贸易扭曲潜能说,该学说实质性地影响到补贴金额的计算与损害的确定。它倾向于夸大补贴金额,并倾向于认定损害的存在。其直接后果是,WTO成员征收反补贴税的法律门槛被降低。 2.税额确定规则中的移除国内产业损害说 《SCM协定》中,第19.2条至第19.4条以及第21.1条均涉及如何确定反补贴税的金额。除第19.4条指出,补贴金额应是反补贴税金额的上限外,其他三个条款均涉及损害与反补贴税金额的关系。在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国)案中,上诉机构不仅认为,“反补贴税的适当金额并非与所造成的损害无关”,更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一个制度层面的理由,即反补贴税的目的之一是抵消或中和损害性补贴,并且移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41) 将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认定为抵消和中和损害性补贴,有其直接的成文法依据。(42)考虑到上诉机构倾向于将补贴进口产品的影响,视为补贴的影响,则即使在补贴前面加上“损害性”的定语,该反补贴的目的仍然能与上诉机构补贴贸易潜能说并存。但是,上诉机构还将反补贴的目的界定为“移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无异于与补贴贸易扭曲潜能说相决裂。具体而言,长期以来,就反补贴税的目的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学说:经济效率说和权益保障说。前者认为,补贴之所以需要规制,因为它们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经济效率。因此,规制补贴的首要目的,不在于救济补贴所造成的不利后果,而是阻止使用补贴。(43)后者认为,出口国可以选择其认为适当的方式给予补贴,但是进口国同样有权采取反补贴措施抵消此类补贴对本国产业所造成损害,从而保护本国生产者的权益。因此,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不是阻碍补贴的实施,而是中和补贴的不利影响。(44)因此,如果上诉机构认为,反补贴法的目的在于移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必然面临类似于权益保障说的困境,即该目的同样不能解释,为何要确定补贴金额,特别是使用非扭曲市场基准计算补贴金额,并将之作为征收反补贴税金额的上限。换言之,在权益保障说下,国内产业所遭受的损害幅度将决定反补贴税的金额。 综上所述,就课税与否规则,上诉机构采取了类似于经济效率说的贸易扭曲潜能说,就税额确定规则,采取了与类似于权益保障说的移除国内产业损害说。而经济效率说和权益保障说可谓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相对于美国商务部的一以贯之,上诉机构的“矛盾”立场更易引发争议。 四 回归反补贴税的贸易救济本色 (一)经济效率说和权益保障说的不足 相较于此前的规定,《SCM协定》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界定了补贴的定义。不仅如此,在单边的反补贴措施之外,《SCM协定》还详细规定了多边的补贴反措施。在多边的补贴反措施中,相关补贴按其性质,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三类。针对不同类型的补贴,存在不同的多边救济措施。其中,禁止性补贴被认为本身具有贸易扭曲效应,成员方不得给予或维持此类补贴。在贸易争端解决程序中,“专家组应建议进行补贴的成员立即撤销该补贴”。(45)对于可诉补贴,只有相关补贴对其他成员利益造成不利影响时,才可受制于多边救济程序。并且,给予可诉补贴的成员可在“采取适当步骤以消除不利影响”或“撤销该补贴”之间作出选择。虽然在禁止性补贴的行为标准和可诉补贴的效果标准之间也存在内在紧张关系,但这一法律区别主要针对对象性质之不同而设,具有逻辑一致性。 然而,与多边的补贴规则不同,单边的反补贴规则并不区分补贴的类型,而是施加了统一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由此造成,单一的经济效率说或权益保障说只能部分说明相关规则的合理性。申言之,在经济效率说下,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被界定为抵消具有贸易扭曲潜能的补贴;而在权益保障说下,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被界定为移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如果采取前说,那么,理论上,反补贴规则应借鉴补贴规则的立法模式,区分有效率的补贴和无效率的补贴,并将前者排除在反补贴法的适用范围之外。而实际的情况是,无论是《SCM协定》还是美国的反补贴法,既未能就补贴作出类型区分,还施加了在经济效率说毫不相关的损害要件。如果采取后说,那么理论上,应通过损害幅度确定反补贴税的金额,而且不应受到补贴金额上限的限制。而实际的情况是,《SCM协定》并未明确损害幅度将决定税额,美国反补贴法则强制要求税额等于补贴金额。因此,无论采取何种学说界定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均导致相关实体法规则在逻辑上的不一致。 上述学说间的争议不仅仅是“茶壶里的风暴”,还直接影响到各国反补贴的实践以及司法审查。比如,长期以来,美国商务部一直采取经济效率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则主张权益保障说,(46)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则支持模棱两可的竞争权利保障说。(47)但是,受“雪佛龙遵从”(Chevron deference)原则所限,(48)尽管反补贴中的经济效率说已被证明不具经济合理性,(49)商务部的抽象分析方法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国际争端。(50) 不仅如此,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中,就如何计算补贴金额这一问题,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依据的是GATT 1994和《SCM协定》,并且是从规则分析,而非抽象理论中得出可以使用非扭曲市场基准计算补贴金额等具体结论。但这些分析和结论毕竟会影响到此后案件的审理,并使经济效率说逐渐被接受。比如,在多哈回合中,在试图推行统一改革方案未果后,谈判小组采取了保守策略,借鉴现有案例,仅对相关规定作出澄清。而澄清的依据主要是上诉机构在现有案件中的观点。其中,就有建议提出,就《SCM协定》第14条,应依据上诉机构的一系列观点。明确非扭曲市场基准的使用等。(51)从积极的角度看,上述建议有助于澄清相关条文的含义,可以增加法律规定的确定性;从消极的角度看,上述建议则将上诉机构的贸易扭曲潜能说成文法化,反而促使了反补贴措施的滥用。 (二)重新理解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居中裁判者,上诉机构只能受理而非挑选案件。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其所分析的法律问题以及在分析中的相关观点将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相关调查主管机关的具体实践。在反补贴调查中,一方面,立法者并没有在条文中明确反补贴调查的政策目的,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拥有较大的解释法律权限,这种集立法者和执法者角色于一身之情形常使其倾向于采取抽象理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具体问题。当相关争议被提交到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时,上诉机构只能依据WTO协定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以补贴金额的计算为例,虽然《SCM协定》第14条大大扩充了GATT 1994相对简单的规定,但其所列举的计算方法仍只是“准则”。这意味着,在审查时,上诉机构只能顺着美国商务部的思路,具体判断其行为的合理性。而这样一种问题处理方式,必然限制了上诉机构的视域。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去指责上诉机构的偏见,而应在上诉机构判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重新理解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 如上所述,《SCM协定》第19.2条将反补贴税的规则分为两类: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无论就前者还是后者,经济效率说和权益保障说只能提供部分合理化的说明。其中,经济效率说主张对补贴施加和收取相当于补贴金额的反补贴税,具有浓厚的公法规制色彩;权益保障说主张对补贴进口产品征收足以消除国内产业损害的反补贴税,以维护国内生产者的权益,具有明显的私法补偿色彩。而将经济效率说或权益保障说强加在两类规则上的后果是,相关学说不仅自身具有经济上的不合理性,还导致两类规则之间以及各规则内部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 实际的情况是,《SCM协定》第19.1条所确立的课税与否规则兼具公法规制和私法补偿色彩,相关的构成要件不仅包括补贴的存在和金额,也包括补贴进口产品所造成的损害。同样,第19.2条至第19.4条的税额确定规则一方面主张较低征税的可欲性,另一方面又为最高税额设立了强制性的上限,而更为重要的是,最终税额应符合“适当金额”的标准。这些规定说明,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不单单是抵消补贴,否则,没有必要将之作为施加反补贴税的损害要件,并影响到最终税额的确定。同时,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也不单单是移除损害,否则没有必要计算补贴金额,并将之作为税额上限。 本文认为,在《SCM协定》下,将抵消补贴和补偿损害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是如何认识损害的性质。具体而言,在反补贴法中,损害专指进口国国内产业所遭受的宏观不利影响,而非生产者所遭受的微观损失。究其原因,国际贸易法关注的是各国间的市场开放、相对公平的贸易机会以及国家整体的福利问题。(52)因此,微观层面具体生产者的损害并不在贸易法的考虑范围之内。即使考虑到生产者的损害,相关损害的认定和计算也是在宏观层面的国内产业的基础上进行。特别是,为防止公法救济的私法化,《SCM协定》做出了两方面规定: 其一,就反补贴调查的发起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条件。第11.4条规定,除非调查申请是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起,否则主管机关不得应申请发起反补贴调查。第16条则就国内产业做出界定,即“应解释为指同类产品在国内的生产者全体,或指总产量构成同类产品国内总产量主要部分的国内生产者”。(53) 其二,就补贴所能采取的救济措施,进行了严格限制。《SCM协定》第32.1条规定,“除依照由本协定解释的GATT 1994的规定外,不得针对另一成员的补贴采取具体行动”。在美国——伯德修正案中,上诉机构指出,一成员可就另一成员的补贴采取四种具体行动:(1)确定的反补贴税;(2)临时措施;(3)价格承诺;以及(4)多边反措施。除此之外的行动,如将征收的反补贴税用于补助本地竞争厂商,或者用于补偿法律成本费用等均属于非法。(54) 正是因为损害要件具有丰富的贸易政策含义,《SCM协定》第19.2条并没有强制要求反补贴税的金额等于国内产业的损害幅度。而这也说明,作为贸易救济手段,反补贴税征收不能仅以惠及国内生产者为着眼点,而应以救济进口国的不利影响为目的。其中,国内产业损害只是衡量进口国受到不利影响的有力指标而已。(55)同时,作为国际条约的产物,《SCM协定》必须在贸易自由化和国内产业保护之间作出衡量,即使一国进行贸易救济,也应存在一定的上限——补贴金额。因此,从《SCM协定》的具体规定中,我们虽然能看到经济效率说和权益保障说的影子,但真正能说明课税与否规则和税额确定规则合理性,并将两者协调一致的是救济进口国因补贴所受不利影响这一目的。 五 结语 参照上述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SCM协定》中课税与否构成要件的法律意义可表述如下:补贴的存在和金额这一要件用以说明,其他WTO成员提供了可能影响到进口国利益,特别是进口国国内产业的补贴;而通过损害的影响,补贴进口产品正在造成损害这一要件用以说明,进口国因补贴受到不利影响。一旦上述构成要件得到满足,则进口国可以决定是否征收反补贴税。同理,《SCM协定》中税额确定构成要件的法律意义可表述为:损害要件用以说明,进口国受到补贴的不利影响的程度;而补贴金额要件用以说明,进口国实施救济的最大程度,以与《SCM协定》的多边救济措施相协调;而“适当金额”用以说明,公法救济应当符合比例性原则。根据上述要件,进口国可确定用以救济不利影响而非惩罚补贴行为的适当税额。 在将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界定为补救进口国因补贴所受不利影响的情况下,美国反补贴法的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如就课税与否规则,美国的反补贴法虽然也规定了补贴和损害要件,但分别缺乏补贴金额和通过补贴的影响这两个因素。该规定不仅降低了施加反补贴税的门槛,也难以体现征税在于补救补贴所致不利影响这一目的。就税额确定规则,美国反补贴法要求税额等于补贴金额,完全“虚置”损害要件,由此导致相关救济针对的是补贴,而非进口国因补贴所受的不利影响。此外,根据美国反补贴法,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来确定损害是否存在这一事项,而由美国商务部负责其他事项。这一职能分工直接导致美国商务部仅关注补贴问题。而其所持有的经济效率说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 将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界定为补救进口国因补贴所受不利影响不仅有助于说明,《SCM协定》中两类规则所含构成要件特有的法律意义,以及美国反补贴法存在缺陷,还可以为反补贴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一个坚实的出发点。具体而言,在多边层面上,就可诉补贴,《SCM协定》第5条规定了不利影响要件,并且国内产业损害是判断是否存在不利影响的重要指标。而根据《SCM协定》的注释35,“对于进口成员市场中一个特定补贴的影响,仅可采取一种形式补救”。这些规定均说明,单边征收反补贴税在很大程度上是多边补贴反措施的替代手段。虽然《SCM协定》并没有就单边措施和多边措施的优劣作出评判,但是GATT和WTO的实践充分说明,单边措施更容易被进口国所滥用,成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因此,将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界定为补救进口国因补贴所受不利影响,有助于促使单边反补贴措施向多边补贴反措施的回归。而无论是以补贴反措施替代反补贴措施,(56)还是将反补贴措施、反倾销措施以及保障措施合并为国家专向性的保障措施,(57)这些改革方案均能与抵消因补贴所受不利影响的目的相容。 注释: ①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类型,可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92~100页。 ②See Wentong Zheng,“Counting Once,Counting Twice:The Precarious State of Subsidy Regulation”,(2013)49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7,pp.439~449. ③GATT 1994第6条并未明确规定,在决定是否征税前,调查主管机关应裁定补贴的金额。上诉机构在US—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EC Products案中指出,根据GATT 1994第6.3条的规定,调查主管机关应在征收反补贴税之前确定补贴的金额。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EC Products,para.139. ④参见黄东黎:《美国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第29~30页。 ⑤19 U.S.C.§ 1671. ⑥在WTO的贸易争端中,一般情况下,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应被其后的专家组所遵从。除非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cogent reason),不适合采取该解释。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Stainless Steel(Mexico),para.161; Appellate Body Report,US-Oil Country Tubular Goods Sunset Reviews,para.188; Appellate Body Report,US-Continued Zeroing,para.362. ⑦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Canada-Measures Affecting the Export of Civilian Aircraft,para.157. ⑧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Softwood Lumber IV,paras.91~92. ⑨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Japan—DRAMs(Korea),paras.172~174. ⑩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China),paras.475~480,490. (11)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Softwood Lumber IV,paras.90,108~109. (12)See Wentong Zheng,“The Pitfalls of the(Perfect)Market Benchmark:the Case of Countervailing Duty Law”,(2010)19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p.28. (13)See Wentong Zheng,“Counting Once,Counting Twice:The Precarious State of Subsidy Regulation”,p.451. (14)在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China)案中,专家组在分析“双重计算”问题时,谈到补贴的影响这一问题。专家组认为,依据非市场经济(NME)方法所计算倾销幅度,“不仅反映出被调查的生产者在国内和出口市场的价格歧视”(“倾销”),还反映出“影响生产者生产成本的经济扭曲”……因此,基于NME方法计算的反倾销税,可能会“救济”或“抵消”一项国内补贴,其程度相当于出口价格因该受补贴影响而导致的降低幅度。See Panel Report,para.14.70. (15)See ITC,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Handbook(13 edition),1I-28-II-41,Publication 4056,December 2008. (16)See Panel Report,Japan—DRAMs(Korea),para.7.411; Appellate Body Report,Japan—DRAMs(Korea),paras.264~268. (17)See Isabelle Van Damme,“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WTO Appellate Body”,(2010)21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05,pp.635~639.提及有效解释原则的案例包括,但不限于Appellate Body Report,US-Gasoline,at 21; Appellate Body Report,Japan-Alcoholic Beverages II,at 106; Appellate Body Report,US-Underwear,at 24; Appellate Body Report,US-Shrimp,para.131; Appellate Body Report,Korea-Dairy,para.81; Appellate Body Report,Canada-Dairy,para.133; and Appellate Body Report,Argentina-Footwear(EC),para.88。 (18)See Panel Report,EC—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DRAM Chips,para.7.336. (19)在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China)案中,就GATT 1994第6.5条为什么单单提及“出口补贴”,而未提及“国内补贴”,这一省略的法律含义是什么等问题,上诉机构指出,“相同情况”是理解该条款的关键,特别有助于说明,为何未就国内补贴作出特别规定。首先,就出口补贴,上诉机构认为,“原则上,出口补贴会导致产品出口价格成比例地减少,但不会影响到该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这意味着,补贴将导致价格歧视的增加和更高的倾销幅度。就此,补贴的情况和倾销的情况就是‘相同情况’,为补偿或消除该‘相同情况’而同时征税会导致‘双重救济’。”其次,就国内补贴,上诉机构认为,“原则上,国内补贴会以同样的方式和同等程度影响到生产商在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销售价格。既然任何可归因于补贴的价格降低均能反映在倾销幅度的计算上,那么总体倾销幅度不会受到补贴的影响。就此,同时征税不会补偿‘相同情况’,因为倾销幅度任何部分均不可归因于补贴。”根据上述分析,上诉机构指出,“只要这些推定是正确的,那么,在[GATT 1994]第6条中,明文禁止征税以抵消倾销或出口补贴所造成的‘相同情况’,同时未提及与国内补贴有关的情况是符合逻辑的——至少当正常价值以国内售价为基础如此。”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China),paras.567~569. (20)参见[美]布鲁斯·E.克拉伯:《美国对外贸易法和海关法》,蒋兆康、王洪波、何晓睿、竺琳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421页。 (21)正因为如此,在分析中,常出现两类规则混同的问题。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Certain EC Products,para.139. (22)Panel Report,Japan—DRAMs(Korea),paras.7.356~7.358; Appellate Body Report,Japan—DRAMs(Korea),para.210. (23)19 U.S.C.§ 1677(A)(ii). (24)See Final Negative Countervailing Duty Determinations; Certain Softwood Products from Canada,48 Fed.Reg.24159,24167(Dep't of Commerce May 31,1983). (25)See 19 C.F.R.§ 351.511. (26)See Carbon Steel Wire Rod from Czechoslovakia; Preliminary Negative Countervailing Duty Determination,49 US Fed.Reg.6773~6774(1984). (27)See Carbon Steel Wire Rod from Poland:Final Negative Countervailing Duty Determination,49 Fed.Reg.19370,19371~19375(1984). (28)有学者认为,这一条恰恰表明,美国商务部不能对中国同时采取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但实践证明,该观点存在问题。参见苟大凯:《美国对华实施“双反”之违法性分析》,载《法学》2010年第3期,第119~122页。 (29)尽管美国计算补贴金额的目的不是确定是否征税,而是确定征收多少金额的反补贴税。 (30)See Coated Free Sheet Paper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72 Fed.Reg.60645(Dep't of Commerce Oct.25,2007). (31)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China),paras.458,490. (32)See Countervailing Duties: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54 Fed.Reg.23366,23367(Dep't of Commerce May 31,1989). (33)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China),paras.557~563. (34)之所以加入这一限制定语,主要原因有两个:(1)实践中,一旦美国商务部决定征收反补贴税,必然会计算补贴金额;(2)WTO上诉机构指出,“通过补贴”的影响,可通过补贴进口产品的影响这一中介(proxy)加以替代。 (35)GPX国际轮胎公司(GPX)是美国一家轮胎进口商,在中国全资拥有河北兴茂轮胎有限公司(兴茂轮胎)。See GPX International Tire Corp.v.U.S.,587 F.Supp.2d 1278(Ct.Int'l Trade 2008). (36)GPX Intern.Tire Corp.v.U.S.645 F.Supp.2d 1231(Ct.Int'l Trade 2009). (37)GPX International Tire Corp.v.United States,715 F.Supp.2d 1337(Ct.Int'l Trade 2010). (38)2012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新法案(PL 112~99),采取的就是税额调整法。19 U.S.C.1677f-1. (39)如《SCM协定》的8条中的科研补贴、环保补贴和地区发展补贴并不必然具有贸易扭曲性,或者虽然具有贸易扭曲性,但与该补贴带来的其他效用相比,微不足道。需要说明的是,第8条已经失效。 (40)See Seth T.Kaplan and Joseph F.Francois,“The Pass Through of Countervailable Subsidies to the Export Price”,(2013)21 Tul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467,p.484; Brian D.Kelly,“The Pass-Through of Subsidies to Price”,(2014)48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95,p.321. (41)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China),para.563. (42)比如,《SCM协定》第21.1条明确规定,反补贴税应仅在抵消造成损害的补贴所必需的时间和限度内实施。 (43)See Charles J.Goetz,Lloyd Granet & Warren F.Schwartz,“The Meaning of 'Subsidy' and 'Injury' in the Countervailing Duty Law”,(1986)6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y 17,pp.19~20. (44)See Richard Diamond,“Economic Foundations of Countervailing Duty Law”,(1989)29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767,pp.780~782; E.Kwaku Andoh,“Countervailing Duties In A Not Quite Perfect World:An Economic Analysis”,(1992)44 Stanford Law Review 1515,p.1538. (45)《SCM协定》第3.2条、第4.7条。 (46)Continental Steel Corp.v.United States,614 F.Supp.548,550~551(1985). (47)Georgetown Steel Corp.v.United States,801 F.2d 1308(Fed.Cir.1986); Zenith Radio Corp.v.United States,437 U.S.443(1978). (48)Chevron,U.S.A.,Inc.v.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Inc.,467 U.S.837,842~45,104 S.Ct.2778,2781~83,81 L.Ed.2d 694(1984). (49)See generally John J.Bareeló III,“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Analysis and a Proposal”,(1977)9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779; Richard Diamond,“A Search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incipl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United States Countervailing Duty Law”,(1989)21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507; Alan O.Sykes,“Second-Best Countervailing Duty Policy:A Critique of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1989)21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699. (50)如近期中美之间多起反补贴措施案件均源于美国商务部采取抽象分析办法,从而对中国产品形成系统性歧视。参见彭岳:《美国对华产品适用反补贴法中的行政方法和司法方法》,载《北方法学》2015年第2期。 (51)See New Draft Consolidated Chair Texts of the AD and SCM Agreements,WTODoc.TN/RL/W/236,19Dec.2008(Chair Text). (52)See Nicholas Dimascio and Joost Pauwelyn,“Nondiscrimination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Treaties:World Apart or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2008)102 Amerc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8,pp.54~55. (53)在Mexico—Olive Oil案中,专家组认为即使没有实际投入生产,相关生产者仍被计算在国内产业之内。这无形中提高了“生产者全体”的门槛。See Panel Report,Mexico—Olive Oil,para.7.204. (54)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US—Offset Act(Byrd Amendment),paras.269~274. (55)“不利影响”一词来自于《SCM协定》第5条。进口国因补贴所受的不利影响包括三个方面:(1)国内产业的损害;(2)在GATT 1994项下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的丧失或减损;以及(3)本国利益的严重侵害。 (56)See Debra P.Steger,“The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greement:Ahead of its Time or Time for Reform?”(2012)44 Journal of World Trade 779,p.789. (57)See Wentong Zheng,“Reforming Trade Remedies”,(2012)34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51,pp.19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