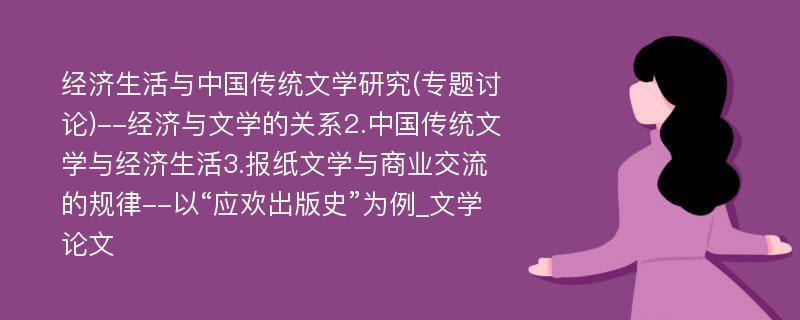
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专题讨论)——1.经济与文学之关系——2.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3.报刊文学与商业交换规则——以《瀛寰琐纪》的出版史为分析个案——4.经济视角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5.文学生成与传播的经济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经济生活论文,经济论文,中国传统论文,瀛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5-0120-14
经济与文学之关系
章培恒
(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433)
文学的形态和发展都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要对某种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其演变加以描述时,自然应着眼于文本本身;但我们要研讨某种文学何以呈现此等形态及作这样的发展时,就不能不把文学与文化的其他部门,尤其是经济联系起来了。经济对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对人性的影响而影响文学的内容,以及通过推动人的生活方式及需求的变化而影响文学的发展这两个方面。
文学是人性的表现。但人性并不是凝固不变的。马克思曾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① 这也就意味着,在通常所谓的人性中,既包含着“人的一般本性”,也包含着“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后者无疑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推动时代变化的,首先自然是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为了说明“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现在举例如下:
第一类例子包括《诗经》中的两篇作品:《召南·摽有梅》和《郑风·将仲子》。前者表现一个青年女子悲叹青春的日渐逝去,盼望及时婚嫁: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矣。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矣。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郑风·将仲子》则描写一个女孩子因其父母、兄长等不愿她与恋人往来,她就请他不要再来: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诗经》时代的人性。
第二类例子分别出于明代后期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的《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旍》。前文写的是少女杜丽娘对爱情的强烈渴望与追求。后文写的是青年女子罗惜惜与一个男青年相爱,但她父母却为她另许人家,她在婚前约恋人夜夜来私会,并准备以身殉情;后来事情败露,她也几乎死去;幸而事情发生了变化,两人才得团圆。
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光阴。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山坡羊]……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牡丹亭》之“惊梦”、“寻梦”
“而今已定下日子了(按:这是罗惜惜与其恋人所说的话;“定下日子”即指其父母为她定下的婚期。——引者)。我与你就是无夜不会,也只得两月多,有限的了。当与你极尽欢娱而死,无所遗恨。”
“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什么?”
——《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旍》
比较一下以上的两组作品,就可以清楚看到先秦文学里的女性与晚明文学里的女性的巨大差别:同是渴望婚恋、悲叹青春的逝去,《摽有梅》的女性是如此温婉,只以树上梅实的逐渐减少暗喻年华的逐渐迟暮和求偶愿望的悄然升温,不但“哀而不伤”,连“哀”都很隐约;《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却是如此激烈,发出了“淹煎,泼残生除问天”的绝叫,而且公然表示:只要让她自由地去恋爱,即使落入酸楚的处境她也不怨,为此而死去她也情愿!与《摽有梅》里的女子真有天壤之别。同是恋爱遭受了阻碍,《将仲子》里的女孩子是逆来顺受,不但对父母的意旨不敢稍有违逆,连“诸兄之言”和旁人的说三道四她也屈从;而《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旍》里的罗惜惜却不惜以死来反抗,无怨无畏地以生命来换取短暂的爱情的欢乐。较之《将仲子》里的女孩子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生境界。可以说,《诗经》里的这两个女子与杜丽娘、罗惜惜之间的区别,正是“每个时代里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变化所造成的。
当然,这些都见于文学作品,并非现实生活里的人物。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所表现的都是当时正常的思想感情。《牡丹亭》则无论在晚明或清代都受到广泛的欢迎,凌濛初的“二拍”也是当时的畅销书,足见这两部作品也是与那个时期的人性相契合的。因此,说这两组作品的区别是反映了两个时代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差别,并非无据臆说。
如果从这两组作品来看,那么,先秦时期和晚明时期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差别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自我意识的强弱。在《摽有梅》、《将仲子》中的女性身上,看不到那种植基于个人欲望的对幸福的强烈而勇敢的追求,而是轻易屈从于别人的命令乃至议论;晚明的杜丽娘和罗惜惜则强烈追求这种个人幸福,甚至为此进行宁死不屈的斗争。这二者的区别就正是自我意识强弱的体现。
再进一步来分析,那么,对欲望、享乐(罗惜惜的所谓“极尽欢娱而死”)等的大力肯定,对束缚个人发展的某些社会规范的反拨,对个人幸福的狂热追求,正是在晚明已有了相当力量的市民的思想特色;因此,在杜丽娘、罗惜惜身上所显示出来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其实是跟当时的市民的意识相联系的。如没有这样的市民的意识,就不会有此种形态的杜丽娘和罗惜惜。而市民意识的产生和增长,当然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至于《摽有梅》、《将仲子》中的女子的自我意识的薄弱,跟当时的经济形态也是不可分的。请看《诗经·周颂·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三十里”面积的土地上,一万人在从事着耦耕(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谓之耦耕),这就是周成王时代的耕作状况。不是这样大规模的集体生产,是难以从土地上获得足以维持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粮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要生存和发展,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个人的作用真是微不足道;就是以具体的耕作方式来说,也必须两人一组,快慢一致,绝不能抛下同伴而独自向前。正因如此,就一般人来说,根本谈不上个人地位——即使家长的权威也是因为作为某种集体的代表并依靠集体的支持而获得的,自我意识的薄弱也就成为当时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具体内涵。
所以,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之一,乃是经济通过对人性的影响而影响文学的内容。
另一方面,文学的形式(包括体裁)的演变也与经济有关。
到宋代为止,中国的文学(这是就文学的严格意义而言,不包括《尚书》、《左传》等书和类似的文章)一直是以抒情文学(尤其是写实性的抒情文学)为主的,《诗经》、汉魏两晋南北朝诗、唐诗、宋词等都属于这个范围,而从金元起则逐渐变为以虚构性的叙事文学为主了。到了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当时的诗歌、散文作品。就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虚构性的叙事文学(包括小说、话剧、电影乃至电视剧)的成绩和影响也超过了诗歌和散文。而金元时期虚构性叙事文学的逐步兴盛,一方面是由于诸宫调、杂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从唐宋起就已出现的“说话”的演进。如所周知,无论是诸宫调、杂剧抑或“说话”,都是应市民的需求而产生、壮大的。市民阶层的形成固然缘于经济的发展,“说话”和诸宫调、杂剧的主要表演场所——较为繁荣的城市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再以今天来说,随着电视机在城市的普及,产生了大量的电视剧,并获得了广大的观众。这些电视剧对中国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奠定的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冲击,从50年代以来确立的教育意义第一的文学观念至少已受到了娱乐性第一的文学观念的有力挑战。这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普遍提高,从而改变了人民在生活上的需求和趣味;同时也是因为经济体制的变化,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加强了企业的自主能力,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广告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并要求相应的回报,被企业在广告上的需求所支配的电视剧不得不把收视率放在第一位,从而也就不得不在娱乐性上大下工夫,不少电视剧假如不是放弃、也是降低了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作品教育意义的坚持。
不过,我们在重视经济对文学的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夸大这种影响。因为文学的发展除了受经济的影响以外,也受文化方面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正面的与负面的。这里也举一个例子:中国在现代文学之前存在过一个漫长的现代文学酝酿期。简捷地说,当时已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因素,其形成的先决条件是市民阶层已壮大到使市民意识得以导致文学中的这些与现代文学相通的因素的产生。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文学酝酿期发端于金末元初,其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好问的某些诗词。今天为不少人所熟悉和喜爱的那首“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词,就出于元好问的手笔。虽然它的推广是由于金庸在《神雕侠侣》中的引用,但其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也就是因为其词中存在着与今人思想感情相通的成分。需要注意的是,南宋的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达是超过金代的,市民阶层的力量至少不会比金弱小,然而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酝酿期的开始的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却不产生于南宋而产生于金末,那原因当然要求诸经济之外了。
[章培恒,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相当丰富,这项研究可做的事情很多。目前,我们可以迈步入门的途径有四:一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与作家头脑里的经济意识与经济理念;二是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三是经济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四是文学史人物的微观具体的经济活动与其文学活动的关系。然限于篇幅,我在此着重谈两点:经济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
关于经济生活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我举两个大家易于认同的例子。一个例子是书坊对于文学创作的导向和文学流派形成的影响。刻书是可以赚钱获厚利的,坊间出版经济的性质正如今天的书商。然而,坊间刻书又是需要文化眼光与胸襟识力的。老板个人为了经济赢利的选题策划似乎直接在接受层面上发生巨大的社会导引作用,在文学的选择与流传上影响一个时代。宋代“江湖诗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江湖诗派这么一支广大的诗歌创作队伍,以宝庆初年陈起始刻“江湖诗集”(《江湖集》、《江湖小集》)算起,至宋亡也有五六十年历史。……尤其值得再提一下的是陈起这个人的文学意识和组织能力,没有他编撰刻印“江湖诗集”,这一批人的绝大部分恐怕就难以留下姓名和作品,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叫江湖派的诗人群体的命名。他有点像现代西方的某些出版商和电影制片人,往往是一种文学潮流或风气客观上的直接推动者。他懂诗,自己也做诗,当然也懂出版经济。联络诗人为了刻书,刻书为了出售,出售为了挣钱,同时也为了诗的事业。为了诗的事业还吃官司,坐流配。刘克庄《赠陈起》诗云,“陈侯生长纷华地,却以芸香自沐熏”,高格调、大目光可见。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一个出版商组织甚至可以说开启一个文学流派的恐怕绝无仅有。上海财经大学的朱迎平教授呈送“全国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宋代刻书产业对文学的影响》,谈到刻书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人文集刊印普遍。文人自刻、弟子刻、亲友刻、乡邑刻、书坊刻、官府刻,途径多样,而且家刻、坊刻多于官刻。二是历代文化经典大量刊布。除经史子部典籍外,《文选》、《文苑英华》等前代文学总集和唐人诗文别集也都大量刊印并广泛流传。三是文学文体演变与选择深受时代影响,如词集在南宋的大量刻印促进了词的大发展。同时,各类书籍的刊刻又使“序跋”空前繁荣。这当然又间接推进了文论、诗论、词论的发展,为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审美观念的演进与流行作出贡献。四是文学流派借刻书而形成,《西昆酬唱集》之于“西昆体”,《江西宗派诗集》之于“江西诗派”,《四灵诗选》之于“四灵”(它的前贤《二妙集》之于“姚、贾”),《江湖集》、《江湖小集》之于“江湖诗派”——宋代重要文学流派的形成无不与相关文集的刊刻关系密切。不但是宋代,愈是后来,如明清时期,印刷业愈发达,出书愈多,对于文学的影响也愈大。
另一个例子意在说明寺院经济对于佛教和佛教文学的影响。佛教及其领袖人物的号召力和寺院经济的实力、信誉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曾对国家朝廷的政治军事大局发生影响,甚至发生扶危济困的功能。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禅宗七祖神会和尚在“经济”大局上为朝廷效劳而获厚报的故事。李唐王朝差一点被安史之乱所颠覆。“九重城阙烟尘生”时,唐玄宗只能“翠华摇摇西南行”,逃到峨眉山下去了。他不得不逊位后,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便积极组织军事力量以图匡复。在唐王朝戡乱战争中,政府的财政异常拮据,士兵无饷可发,朝廷筹款的主要方法之一便是发放佛教的“度牒”,百姓之中有欲皈依佛教者(可以免徭役、免赋税),可以向政府纳款领取“度牒”(即百姓出钱买和尚身份)。当时,每一“度牒”索款十万钱,很像是一种国家公债。朝廷为了推销这种“度牒”,借重年高德劭的神会和尚在东都洛阳帮忙。神会和尚名声大、资望高,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眼光,推销实绩最大,佛寺经济创收最高。筹款的成功为戡平安史之乱奠定了经济基石。肃宗皇帝亲召神会和尚入宫酬谢,为神会在洛阳重修佛寺隆其驻锡。而实际上神会也借助了皇家的政治势力打败了北宗禅宗,不仅自己当上了南宗七祖,还让自己的师父慧能追封成禅宗六祖。——这不仅是中国禅宗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诗学史、艺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禅与中国文艺的关系太大了,佛寺经济便是成就这件大事的主角!同样是呈交会议的一篇论文《唐代寺院经济的转型与佛教文学的新变》(上海财经大学李贵),论述了唐代寺院经济的转型是如何促进了佛教文学新变的。寺院需要争取城市市民,为此,佛教传播的方式必须迎合市民的审美趣味、信仰或求助的需求,玩弄形式技巧,实现世俗化、商业化。这当然也有助于打败道教的宣传势力。另一方面,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为佛教文学艺术的创新和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障。——这样的视角无疑是新鲜的,在厚重翔实的史料的支撑下很可以开拓出一条研究佛教寺院经济形态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新路。
以上两例意在说明,“经济生活”与“经济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事业影响深远,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与流播关系密切。
现在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
由于儒教趋义避利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入人心,一谈钱财孳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而不谋其利”的教训便嗡营一片。其实,儒家着眼点在符合“义”的基础上是可以接受富贵与财势的。所以,它谴责的是“不义而富且贵”,要求的是“临利毋苟得”。而宋儒则把“义利之辨”推到了极致。在理论的层面上呼应这种义利观的似乎还应加上“道”的生计迂阔、思接神仙,“释”的人事疏远、不问富贵。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板起面孔说教时,充斥对金钱财富义正辞严的排拒,正人君子们对金钱财富不屑一顾,累及“经济”一科自来无学术可言。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之后,几乎全没有纯粹经济的研究与理论。但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却一直在摆弄着政治与历史,主宰了世俗社会一大部分的人心。经济活动事实上充斥在世俗的文学现实中。尤其是秉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高手,大都遵循生活原则的指导,相对客观地正面表现经济生活与世俗人心。《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都是现世经济生活的活样板——忠于生活原则的文艺必然直面经济生活,当然也客观反映了经济形态。杂剧《庞居士误放来生债》可以骂尽金钱支配下的世道人心、“仁者无仁”,可以悟出“富极是招灾本,财多是惹祸因”的训世箴言,而《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则以清醒的理性描述了经济运筹的高明与成功,同时又流露出馋羡捡漏暴富的世俗心态。《一文钱小隙成大祸》可以见出“一文钱”的争执对世俗人心的巨大伤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又从“百宝箱”的放弃看到人性爱情、信誉承诺的夺目光芒。——“生活”的本相千姿万态,“经济”的教训则是棱角多面的。宋儒以来,孔教可以在书本文字与警世教训中骂尽钱财,但钱财实际上的巨大力量则足以掀翻世道人心,把孔圣人的教训轻轻搁置。明代朱载堉有一支小曲《骂钱》:“孔圣子怒气冲,骂钱财,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这里正可看见宋儒以来的孔门关于钱财的教义被凌辱亵弄的危机。“吾门弟子受你压伏”抒发的怨屈几乎是千年一贯,而“忠良贤才没你不用”又点到了俗世吏治的腐败与正人君子的苦涩。——中国传统文学浸润着经济生活的鲜活因素,也活现了义利之辨这类传统理论在现实生活面前所遭遇的似是而非的处境。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不只是将经济现象钩稽出来、罗列展览,搭挂在文学发展的链条上,平面地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用传统文学的材料来作中国古代经济学的论文,更不是要构筑我们自己的别出心裁的经济理论体系。我们要做的是在对象的学理评判和伦理断制中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高格调的价值诉求,融注我们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批判。尽管我们人文学者讨论的“经济”后面的知识体系与经济学界谈的那一套很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学理感知具有强烈的人文气息与正义质性。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设定了这个研究方向须持有的文化立场,并连带提出了适应其逻辑要求的言说姿态。
[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报刊文学与商业交换规则
——以《瀛寰琐纪》的出版史为分析个案
陈大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市场经济因素与小说创作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报刊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直接。自近代出现报纸杂志以来,文学,特别是虚构性的叙事文学(以小说为最)格外受到出版商的青睐。可是,刊载什么样的新作,却往往以读者喜好为取舍标准。于是,作者迎合出版商,出版商迎合读者,因为唯此方能赢利,方能生存。这种以赢利为目的的报刊文学便具有了文学与商品的双重属性,而商品—经济性成为直接关系报纸杂志命运和报刊文学命运的重要因素,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在此得以实在而充分的体现。今以《瀛寰琐纪》的兴衰史为个案加以剖析说明。
清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1872年10月14日),《申报》刊载了《刊行〈瀛寰琐纪〉自叙》,预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刊物的诞生。这实际上还是第一个连载小说、甚至是首先连载翻译小说的刊物。申报馆为什么要办《瀛寰琐纪》?那篇《自叙》介绍说,《申报》创办后,文人雅士来稿甚多,无法一一或全文刊登:
奈日力之有限,致篇幅之无多。花类折枝,仅悦一时之目;玉非全璧,谁知千古之心。断烂之朝报堪嗤,闻见之羼录难遍。用特勤加搜讨,遍访知交,积三十日之断锦零缣,居然成幅;合四大洲之隋珠和璧,用示奇珍。拟为《瀛寰琐纪》一书,凡已登《申报》者不录。
《申报》创刊伊始,曾刊载过一个“条例”,其中第二条对文人们颇有吸引力:“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申报》一问世就得与已创办十年的《上海新报》竞争,留出篇幅刊载文人雅士的作品,既可抬高声望,同时又可吸引文人们的关注与购买。同样是因为激烈的竞争,《申报》又十分注重刊登广告,以便维持并逐渐增强经济实力。当时,《申报》几乎每天第一版上都有广告刊登的收费标准:“足五十字或五十字以内者,刊一天取资二百五十文,第二天取资一百五十文。字如多,每加十字,照加钱五十文,一礼拜后,每字照第一天减价一半。”按此计算,即使刊登一首七律,加上题目与作者名,就相当于四百文广告费的版面。当时的《申报》售价八文,即等于白印五十份报纸。随着报纸社会影响日益扩展,广告业务越做越红火,《申报》自然不愿意扩大免费刊载文学作品的版面。可是对文人来说,在《申报》刊登作品“概不取值”,无疑是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扩大作品影响的新途,于是他们的积极性顿时被调动起来。但可供刊登的版面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申报》为追求读者数量的增长,又很注重通俗性与公众性,更乐意推出较通俗的竹枝词之类,所谓高雅的词章却很少能发表。文学来稿随《申报》迅速扩大的社会影响而递增,越来越多的被积压的稿件给办报人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为此申报馆曾解释说,“凡送稿已久而未及刊行者,其中别有苦心,尚希诸君子原谅为荷”①。所谓“苦心”,版面与利润的考量当占相当大的成分。
不过,那些作者及其影响圈却多是值得关注与争取的读者。《瀛寰琐纪》的创办,可使被积压的作品有个发表处,也可平息投稿人的不满;同时,创办这个刊物可扩大《申报》在缙绅间的影响,士大夫的关注则又可转化为报馆的利润。《瀛寰琐纪》每本售价八十文,但不付稿酬,仅赠送作者刊物一本。第一卷刊印了两千本,这表明申报馆对这本刊物也有赢利的盘算。第一卷出版十日后,“除发售各处之外,申报馆中尚余五百余本”②。有人据此认为,第一卷刊印后没几天就卖出一千五百本,这其实是个误解。该“告白”只是说明近一千五百本已送往各售报处或代售处,并未言及那些地方在十天内的销售情况。当然,各处乐意销售或代售,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本刊物发刊时受欢迎的程度。
十月十一日,《申报》刊载启事:“《瀛寰琐纪》之刻也,蒙大雅君子不弃固陋,时有投赠之作。或崇论宏议,大逞韩潮苏海之观;或短咏长谣,别写残月晓风之趣。谨已镌之玉版,用作金针矣。”此时距九月十三日预告刊行《瀛寰琐纪》还不足一月,可见文人来稿之踊跃;此态势还曾持续过一段时间,因为类似的告白后来又出现过几次。从第二卷开始,刊物又有所改革,“议论愈加开拓,词章益加繁富。兹已比前次所出之篇幅加宽,改为二十四张矣”③。同时,还向社会征聘画师,“本馆近拟出《瀛寰琐纪》一书,其中山川、人物、器具等皆当绘有图像,使人豁目醒心。特欲延请精通画学之人,以襄厥事。凡挟绝艺者不妨屈驾来馆面订一是,是所盼切”④。这表明,申报馆确曾想将《瀛寰琐纪》办得图文并茂,精益求精;再加上来稿又十分踊跃,刊物刊行顺利,该刊运行的前景甚是看好。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该刊从第一期起无一期能按时出版。《自叙》称,该刊“每月以朔日出书一卷”,以往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它是按期,至少是按月出版,可是当时《申报》上有关该刊的数十则广告表明,实情并非如此,甚至刊物的第一卷就没有按时出版。
十月初二日(11月2日),即原定《瀛寰琐纪》第一卷出版的翌日,《申报》上刊载了一则“本馆告白”:
本馆印行之《瀛寰琐纪》,原拟十月朔日出书。第其中考据引证必当广稽载籍,而非可率尔操觚,即议论纪叙之文,亦必详询时宜,博咨掌故,而后可笔之于书,何敢卤莽从事,致贻疏略之讥乎?况排印者亦复不能迅速刻期蒇事,故十月朔日难以告成,应俟稍缓数日,始能呈教。
该卷实际出版时间是十月十一日。第二卷出版延误至十一月十三日,申报馆曾作解释:“本月所出之《瀛寰琐纪》,现已排印都齐,校雠既毕,可以出而问世矣。惟裁笺穿线之功,一时未竣,俟装订齐全后再行布闻,大约本月望前定可呈教。”⑤ 对第一卷延误的解释中也有“况排印者亦复不能迅速刻期蒇事”之语。第三卷又延误了十二天。从此卷开始,申报馆基本上不再作解释,刊物不准时出版反已成了常态。下面列上根据《申报》在各卷出版时的广告制成的日期表,以便观察该刊愆期的情况。
《瀛寰琐纪》各卷出版日期表
卷数 原定日期实际日期 卷数 原定日期实际日期
同治十
一年十 同治十一十一月 十二月十
1月初一 年十月十
15
初一日 七日
日 一日
十一月 十一月十十二月 同治十三
2初一日 三日
16
初一年二月初
四
同治十
十二月 十二月十三年正 三月十七
3初一日 三日
17
月初一 日
日
同治十
二年正 同治十二
4月初一 年二月初 18二月初 五月初二
日 二日一日日
二月初 三月初二三月初 六月初十
5一日日19一日日
三月初 四月初二四月初 七月初六
6一日日20一日日
四月初 五月初二五月初 八月初四
7一日日21一日日
五月初 六月初四六月初 八月十八
8一日日22一日日
六月初 闰六月初七月初 八月二十
9一日七日 23一日九日
闰六月 七月十三八月初 九月十七
10
初一日 日24一日日
七月初 八月初九九月初 十月十五
11
一日日25一日日
八月初 九月初八十月初 十一月十
12
一日日26一日一日
九月初 十月初二十一月 十二月初
13
一日日27初一日 八日
十月初 十一月初十二月 光绪元年
14
一日二日 28初一日 二月初六
日
从创刊到终结共二十八卷,《瀛寰琐纪》从未按时出版过,而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卷出版的延误,甚至还超过了三个月。
在解释第一卷为何延误时,申报馆强调“第其中考据引证必当广稽载籍,而非可率尔操觚”,但笔者以为,其后那句“况排印者亦复不能迅速刻期蒇事”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此后卷卷延误,申报馆解释时不再提及“考据引证”一类话,如第二卷延误的唯一理由便是“惟裁笺穿线之功,一时未竣”,第十八卷是“因他事忽忽,开手稍迟”⑥,第二十八卷是“为因岁事忽忽,开手稍晚”⑦,这些都证明问题出在印刷装订环节,申报馆也明确表示“勿责其编排之缓”⑧。尽管许多卷出版时未说明延误原因,但《申报》刊载的“告白”往往会强调某卷《瀛寰琐纪》“现已排印齐全,装订周备”⑨,其实都可看作是婉转地暗示延误的原因。于是,这就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当时申报馆印刷装订的状况。
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申报》时筹资银一千六百两,数目虽不小,但据此创办一份近代化的报纸却实是艰难。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曾评论说,“这点点本钱买铅字和印刷机器也不够”,并加注云:“同年王韬和黄平甫在香港筹出《循环日报》,出资盘进英华书院原属伦敦会的印刷设备,代价是二万一千元。美查办《申报》时集资一千六百两,按当时兑率折成银元,约二千三百元,是《循环日报》投资的11%。”因此,《申报》在开始时规模并不大,每天只印报三千份,周日还停刊(八年后,即光绪五年闰三月方有周日版)。以当时有限的印刷设备与人手另再办一份印数为两千本的月刊,还要准时出版,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资金周转也是个大问题。加办一份月刊后,申报馆便很快感受到资金匮乏的窘迫,于是就在《瀛寰琐纪》第四卷出版之日,宣布《申报》涨价:
本馆《申报》自去年三月杪举行,于今十阅月矣。……蒙各士商不弃弇鄙,肯赐垂青,计每日所消(销)不下三千余张,亦云多矣。惟本馆一切费用浩繁,所入者几至难敷所出,竟不得不稍谋长价,以补不足。今拟于二月初一日起,每张加钱二文,计上海零售每张十文,趸卖每张八文;各码头亦照式递加。夫笔墨生涯,原不同于贸易,况本馆举行《申报》,意在将瀛海见闻,搜罗登载,俾得广行宇内,并非视之为利□也。今则迫于不得已而稍昂其值焉,然大非本馆之初心矣。所愿惠赐诸公,原其苦衷,仍赐观览,□勿谓本馆唯利是视,贪得无厌。幸甚,幸甚!⑩
也正是从第四卷开始,延误一个月已是家常便饭,到后来延误已超过三个月,而《四溟琐纪》与《寰宇琐纪》的出版更时常延误半年之久。
确保每日报纸正常发行,再编辑出版刊物,这是理所当然的决策。可是到了后来,虽同样是延误,原因却截然不同。如《四溟琐纪》第四卷的出版延误了三个月,申报馆对此解释道:“嗣因《经艺新畬》、《(诗句)题解韵编》四集二书亟于排印,暂将《琐纪》停缓。”(11) 这纯是因为要赶印他书而将耽搁了刊物的出版。而且,此时申报馆已购置了新的“直活字版印书机器”,印刷条件已大为改善(12)。有条件准时出版月刊,但却将力量置于其他书籍的出版,原因则是这样做能较多也较快地获取利润。发现新的财源似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事。那年九月,申报馆用铅字排印了一千部《儒林外史》,售价每部五角,结果“不浃旬而便即销罄,在后购阅者俱以来迟弗获为憾”(13),于是半年后便有加印一千五百部之举。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申报馆第三次再版《儒林外史》时解释道:“本馆前曾照印数千部,今已售尽,而来购者犹踵趾相接。”(14)
一千部《儒林外史》不到十日就已换成五百个大洋,约合三百五十两银,而一个月的《申报》销售所得,按每日三千份,每份十文钱计(扣去周日不出版),共为三百八十两银。这组数字的对比,必定会给美查造成极大的冲击。美查创办《瀛寰琐纪》原先也想赚钱,每卷出版两千本,每本售价八十文,如果销售顺利,每月可得约九十两银,一年便是约千两银。但这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事实上《瀛寰琐纪》与后来《四溟琐纪》、《寰宇琐纪》的销售都不如人意。最有力的证据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初四日《申报》刊载的那则“各种书籍照码折扣出售”广告,那三种刊物的标价都是三十文。卖了三十年还在打折出售,其销路如何,不问可知。
实际的经济利益决定了经营者的选择,就在《四溟琐纪》与《寰宇琐纪》出版严重延误的两年间,申报馆出版的书籍中仅小说就有二十余种,其中《萤窗异草》的初、二、三集还需再版,《快心编》后来更是印到第四版。《申报》从一千六百两银资本起家,很快发展到实力雄厚的沪上第一大报,印书获利是重要因素之一。以追逐利润为最高准则的商人自然不愿舍弃这样的利益,去将印刷力量集中于保证难以赢利的月刊的准时出版。
《瀛寰琐纪》出版至第二十八卷,在版式稍有变化后改名为《四溟琐纪》继续出版,理论上是光绪元年正月出版第一卷。一年后,又改名为《寰宇琐纪》出版。此时,出版延误极为严重,使人感到似乎只是为处理被积压的稿件而勉强应付。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初二日,申报馆终于宣布应在去年九月出版的《寰宇琐纪》第九卷即将出版:
丙子年之《寰宇琐纪》,尚余四卷未经印出,兹已次第排竣,所有诸君寄来大著,半皆选入。业将第九卷之《琐纪》先为装订,准于月之初三日出售。每本实价制钱八十文。
拖了七个月才出版,明显是一种敷衍的姿态。在接下来的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却又及时将拖延的四卷全部出齐了。在出版刊物的四年半里,申报馆有关的广告或“告白”有数十则之多,可是唯有这次特地声明“所有诸君寄来大著,半皆选入”。这些举动显然是策略的施展。刊物拖延许久不出版,人们慢慢地失去了投稿的兴趣,而预先告知短时期内将出齐拖延的四卷,而且积压的稿件又全部处理完毕,这实际上已在暗示刊物的命运。果然,当五月十六日《寰宇琐纪》第十二卷出版后,这本延续了四年半的刊物终于停刊了。几乎与此同时,《申报》上所刊载的文学类作品逐步减少,从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干脆暂停了相当长的时间。但申报馆并非与文学绝缘,它成立了申昌书局、点石斋石印书局等机构专门从事书籍的出版与销售,其中多数为文学类著作,而小说尤为大宗。至此,晚清时申报馆经营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瀛寰琐纪》的命运后来曾反复地被复制。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申报馆又发行了韩邦庆个人承办的文学期刊《海上奇书》。开始时是半月刊,出版了四个月后,韩邦庆感到难以维持,遂改为月刊:“半月之间出书一本,刻期太促,脱稿实难,若潦草搪塞,又恐不厌阅者之意,因此有展期之恼。兹于六月朔日出第九期书以后,每月朔日出书一本,庶几斟酌尽善,不负诸君赏鉴之意。”(15) 可是再过四个月,刊物不仅出版延期,后来更干脆停刊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苏州又出现由杨紫驎、包天笑等人创办的文学刊物《励学译编》,它因连载《迦因小传》曾名噪一时,但它出版了一年后也未能继续办下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小说》创刊,在其影响下,一时间各种文学刊物陆续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等,但它们坚持不多久,又都纷纷停刊歇业。在晚清创办的文学刊物中,只有较后问世的少量杂志如《小说月报》等,才能作较长久的经营。
在对这一历程作了解之后再反观《瀛寰琐纪》出版的延误以及后来的停刊,我们的理解或可更深一层。最初的《瀛寰琐纪》、《海上奇书》等刊物,形式如同传统的书,这可看作是一种象征,即在旧传统的氛围中以旧的形式出现了新的出版物种类,而其内容则是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主,但也时有崭新的内容,如《昕夕闲谈》与《迦因小传》的连载。那些刊物不是突兀而起的全新事物,而是新旧的混合体,而且旧的形式与内容在开始时还占据了主要地位,即刊物的萌生与发展是以渐变的方式在嬗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不得已的。如果不能适应当时的环境与氛围,那么刊物的创办就毫无意义。同时,这些刊物中所包含的“新”,也有着逐渐改变环境与氛围的作用。这里既有如《新小说》那般的冲击,但更多的恐怕还是以一点点量的积累的方式在逐渐改变。商业上的考虑,使开始时旧的传统占了上风,那是为了吸引传统的士大夫,争取他们的认可,但这毕竟是一个很小的读者群,于是同样因为商业上的考虑,又使得刊物停刊。由于是新旧的混合体,在办刊过程中,其中新的成分毕竟使读者的口味有所变化,同时也使读者群有可能多少有点扩大。一个刊物停刊了,后起的另一刊物又重新重复这一过程,而重复时又或多或少有一些新因素的羼入。这一环一环的衔接,显示出阅读市场近代化的过程,而其中的推动力量,则是文学发展的冲动与商品交换法则的制约的结合体。
总之,晚清文学作品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刊载在报刊上。当时,文学作品或样式的产生与变化毫无疑问地要遵循文学发展的规律,但那些报刊本身却又是商品,它们的生存与发展又受到商品交换法则的制约,两种约束形成融为一体的合力。若对晚清文学只作纯文学的考量,那只会造成许多难以解答的疑案。《瀛寰琐纪》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停刊,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此。在当年,理解并较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的文学报刊,方能较长久地生存与发展;而在今日,理解并较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的研究,对一些现象或问题方能较切实地诠释或解决。
[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注释:
①《本馆告白》,载《申报》,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②《本馆告白》,载《申报》,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③《本馆告白》,载《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
④《请画友告白》,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⑤⑧《本馆告白》,载《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
⑥《告白》,载《申报》,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二日。
⑦《告白》,载《申报》,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
⑨《告白》,载《申报》,同治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⑩《本馆告白》,载《申报》,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二日。
(11)《告白》,载《申报》,光绪元年七月十六日。
(12)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刊载《本馆告白》云:“启者:本馆置直活字版印书机器,于排印各书籍较为便捷,如远近诸君子藏有珍函密帙,意图筹世,尽可□□前来,以凭本馆酌夺排版。一俟装订竣工,当持赠一二百部,借申谢悃。或鸿才硕彦好制说部,等书制成后,亦可寄来代印,但书之体裁必如《儒林外史》,一气相生而又无淫乱语者为佳。若逐篇逐段如《聊斋志异》者,概从割爱。至于如何酬谢,亦以印成之书一二百部奉送。如京都诸公有书欲印,可即交经理《申报》人寄来不误。”
(13)见光绪元年四月十五日《申报》刊载的“《儒林外史》出售”广告。
(14)见光绪七年二月十七日《申报》刊载的“重印《儒林外史》出售”广告。
(15)《〈海上奇书〉展书启》,载《申报》,光绪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经济视角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董乃斌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于文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这里试举近年出版的两部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史教材以窥一斑。
先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唐代文学史》。在该书第一章“唐代文学总论”第一节“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中指出,鼎盛的时代是实现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鼎盛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自然便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达,“繁荣昌盛的封建经济,为唐代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书中具体论述了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使脑力劳动者人数增多、生活和劳动条件更好,使中小地主乃至寒素士人得以掌握文化登上文坛,从而打破门阀世族的垄断;并反复将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并提,以之作为统治者实行“文治”、重视发展文化事业、文人心态健康奋发、中外文化交流密切、南北文风融合加快等等的先决条件。在论述元和文学再度繁荣时,首先叙述杨炎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以及“二王刘柳”革新、李绛与裴度为相,使“遭受战乱破坏的经济,也在这时得到了某些恢复。特别是在南方,工商业发达,城市繁荣”的情况,明显有意识地将经济发展作为文学繁荣的前提。这些都说明,作者非常认真地贯彻了经济是基础的观念。
再看袁行霈主编的作为高校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二卷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的“绪论”,也在第一节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力的强大与中外文化的交融”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而国力强大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至天宝中上升达于顶点”。并在注释中引用《贞观政要》和《新唐书·食货志》的资料作了补充说明。之后,在叙述杜甫的第四章,先讲安史之乱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然后才讲诗歌的变化;在十二章“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第一节“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第一段更明确写道:“词的兴起,与唐代经济发达,五七言诗繁荣,有密切关系。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兴盛,为适合市井需要的各种艺术的萌生与成长,提供了温床,‘歌酒家家花处处’的都市生活,不仅孕育了词,而且推进其发展与传播。”由此可知,该书的撰写者同样十分重视经济与文学的关系。
另外,以前的研究也注意到了经济生活状况对某些唐代作家人格特征和创作风格的影响。李白家境富裕,“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上安州裴长史书》),为人轻财好施与诗风豪迈雄放相当一致。杜甫十年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涯和一生的颠沛穷困,则促使他愈来愈走向民众。王维购买辋川山庄,亦官亦隐、亦儒亦佛的生活方式,跟他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关系密切。而孟郊的赤贫应是其诗悲酸风格的重要成因。李商隐到处做幕僚以谋生,杜牧不肯在朝为官而请求外放以养家,经济状况决定着他们的人生踪迹,也影响着他们的创作道路。
那么,这些是不是说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经济视角已经运用得很充分了呢?当然不是。现在看来,文学史书中关于经济对文学制约与影响的叙述,毕竟比较简单笼统,多数只限于触及和提示,而缺乏足够的阐释和论证。当我们从唐代文学丰富多彩的现象出发,研究与其相关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外部要素时,较多地是从政治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心理层面进行论析,而对于经济只作适当涉及。但是,若要真正解决问题,首先就需要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两家携手共抓关于经济与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搞深了,文学史书中自然会反映出来。这也正是我认为现在应重提从经济视角研究古代文学,并提倡对此做专门研究——是一种学术深入的理由。然而,文学史研究者注意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应有必要中介(而且中介还不一定是一层),不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作生硬机械的联系,从而避免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却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
政治、制度、文化等等都属上层建筑,关注文学与它们的横向联系十分必要;进一步探索文学与更深层次经济基础的关系也很重要,但难度将更大。首先是史料不足,唐代经济史资料远比不上政治史资料丰富和研究充分。其次是唐代的农业经济本来就不像后世商品经济那样与文学的关系直接而明显,唐代经济与文学(从作家个人到整个文学的运动)的关系以何种形态表现出来,从经济到作家、再到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流传等等需经过哪些中介来发生联系和相互影响,都还缺乏实证(更不必说量化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再次,研究者在把握经济与文学关系时既要使论述具体深入,又要力避把复杂曲折的问题简单化庸俗化,绝非易事。也许正因为这些,所以在近年蓬勃发展的唐代文学研究中,尽管课题广度有极大的开发拓展,新题目新领域层出不穷,但从经济视角所作的深入研究却相对显得冷清。
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开拓了很多新的课题和研究方向,其中唐代文学与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系是拓展的重点。如唐代文学与科举制度,与道教佛教,与各种姊妹艺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与外来文化,与交通贸易,与民俗生活等等;还有像士人的翰林际遇、贬谪生涯、幕游经历、集会宴聚、唱酬往还、地方性的士族承继和家族传统,以及各种园林山庄与文学的关系等新课题,都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显示了唐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良好趋势。所有这些课题,若从运用经济视角的要求来审视,有的研究已经涉及或有所阐发,如唐朝的庄园经济、寺庙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等,当然也有许多研究尚停留在诸多中介性的层面上,距更基础的经济层面尚隔一间。所以,重提和呼吁文学研究的经济视角,力求使研究更深入一些,对唐代文学研究而言,绝不是无的放矢。从理论上说,上述种种现象,无论表现为政治、制度,还是表现为宗教、文化,在它们背后或深处,归根到底都应该有一个经济的原因。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也就生活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之中,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包括文学现象之产生,都有一个经济的或者说利益的驱动在。我们在研究中所关注的经济问题,无非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状况,它是一切非物质的、精神产品生产的基础,制约着精神产品生产的量与质。经济作为文学生产深层次的原因和驱动力,虽然可能很隐蔽,但既然是客观存在,就应予揭示,也能够揭示,这是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反思自己过去的研究,经济视角确非所长,也考虑得很少。我和程蔷合著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一书,虽然讲了唐代很多民俗生活问题,但对民俗背后的经济原因思考阐述很不够。其实,文学创作是精神劳动,民俗的本质也是精神性活动,在它们背后都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民俗的形成和传承更是如此,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不是为了某种共同的实际利益,许多民俗不会形成,也不会是那个样子。如端午的吃粽子和划龙舟,如除夕春节的家庭团聚和饮食风俗,均需在一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前者号称纪念先贤、传扬崇高品质,但实际的好处是品尝风味食品、锻炼身体、培养和加强团队精神;后者的节俗关目更多,归根到底则是一年辛劳的总补偿、人际关系的大调谐和对来年安丰的祈祝禳求,都要落实为某些实际物质的和精神的收益。至于各地民俗的特色和异同,也总是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分不开。精神生活与经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物质生活发生变化时,精神生活(从民俗文化到文学)也或快或慢地随之变化,虽不一定同步,但迟早会表现出来。如果能更自觉地运用经济视角审察唐代民俗及其与文学的这种动态关系,我们的论述应该会比现在更深入些。经济视角给这一研究深入持续的发展指出了可行的途径。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从文人的游幕和贬谪,发展出文学向文化弱势地区流动,对这些地区的文学和唐代文学的总貌产生影响的问题①。把唐代全国的文化状况作出强弱、次强次弱等区分,注意到唐代文学在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注意到游幕之士带来的文学流动对整个唐代文学的影响,我觉得这其中有不少新概念。它们的提出既是研究深入的表现,又有助于研究的继续深入。而这一研究思路也天然地与经济视角联系着。谈文化的不平衡、文学的势强势弱,首先不能回避的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的强弱。而且,既有文化弱势地区,也就必有文化强势地区,对两者的研究应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上述概念的提出,也会促进对长安、洛阳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及扬州、成都(益州)、金陵、广州等大都市在唐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之研究。当然,难点仍在于经济与文学的联系表现得很复杂,实质不像表象那样容易把握。然而,表现得再复杂曲折,内在规律仍然可寻,研究起来也更有兴味,更有前途。
文体的演变,尤其是新文体的产生,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当然与社会需求、与文体本身的演变关系密切,同时也与经济发展有关。事实上,在唐代获得文体独立的小说,萌芽雏形阶段的说唱、戏剧和市民文艺,包括寺庙中发达的演说经变和俗讲,以及一度极为兴盛的敦煌文学,都和其时的经济状况(从唐朝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城市的急速发展,特别是大都市的形成,到中外交通的便利、海陆丝绸之路的漫长、商业贸易的繁荣等等)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些方面若要从一般笼统的认识上升到具体化和更深刻的论述,就需要自觉采用经济视角,发掘新材料,寻找新思路。
经济视角不仅对研究作家个体有效,对研究唐代文学许多方面的问题有效,而且对研究唐代文学整体的发展演变同样有效。历代研究者习惯把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不仅是政治的标志,也是经济的标志和文学史的标志。即使不赞成这样划分,但总得有另一种分期。那么,每一阶段的文学状况与经济形势有什么关系?是否对应?如何对应?无论对应与否,原因何在?从一个阶段过渡演变到下一个阶段,有种种原因,有种种表现,这些又是否能与经济状况的变迁相联系?这一系列问题,也许以前不是没思考过,但还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给出更深更新更明晰的表述。文学研究的经济视角对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可以大有作为。
说经济视角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可以大有作为,并不等于说经济视角就是文学研究的唯一,甚至也不能说是第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多元化。经济视角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运用不好易落入庸俗化陷阱。这或许就是新方法、新视角层出不穷的今日,经济视角仍欠发达而急需提倡的原因。科学研究就是知难而上,既然古今文学运动都与经济基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关系又是重要的、有规律可循的,是人们确信其存在而又尚未确切把握的,那么,文学研究者就一定要努力把它揭示出来,就像天文学家无论费多大气力也一定要把已经从理论上计算出但尚未确切发现的星星在辽阔无垠的宇宙空间里找到一样。
[董乃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注释:
①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戴伟华教授已就此写出论文,将发表于广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东方丛刊》上,笔者有幸先睹为快。
文学生成与传播的经济动因
许建平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中国文人的传统价值观念是“君子谋道不谋食”,故而中国文人向来是重“道义”轻“财利”。表现在文学研究中,总是将文学视为道义与精神的载体,研究文学不外乎发掘其内在的精神文化内涵,似乎文学始终与经济无关。之所以如此,主要病因在于只看到了文学的精神属性而未看到精神属性所内含的物质—经济属性。然而,看不到的并不等于不存在。经济在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到底如何?文学的属性只是精神的吗?有没有经济属性?在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文化背景下,这些问题应该有个客观的回答。文学研究被遗失的部分应该还原,文学经济属性的研究应该“回家”。
所谓生活,指人的生命活动。生命活动不外乎由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活动与满足精神需求的精神活动两部分构成。前者生理的需求——对食、色、货的需求——处于第一位置,后者精神的需求——对贵、名、道的需求——处于第二位置,是由第一位派生出来的。
先说“贵”。贵——读书做官,乃食、色、财、货等生理需求的扩张、升华。因“书中自有千钟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故要读书做官。所以追求贵的目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生理需求得以满足和得以合法的保障,从而在这类需求的满足中出人头地。可见,贵的需求,精神是其冠冕,经济是其实体。
再说“名”。名——好的名声,是精神的需求。从精神层次看,有排除财货的倾向。然而,追求名的目的不外两个,一是名垂青史,一是获得富贵。名垂青史是儒家使人的有限生命得以延长下去的重要方法。说到底还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表现,是以精神的传递来弥补肉体生命短暂之缺憾。其出发点还是生理欲求,是生理欲求的另一表达方式。然达到永垂青史的毕竟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是冲着功名富贵来的。古人所谓名,不出两类:德名、才名。而德才是获取官位所不可少的。文人读书、修德、行文、习武的直接目的是获得“美名”;修身、修德、做“内圣”就是要“治国”、“外王”,实现政治理想;出世、修道、做隐士,也是为了保洁、扬名,最终得到帝王的招聘,走的是终南山捷径。故而有名则有官,有官则有利,最终名利双收。
最后说“道”。“道”——文人的价值家园,说到底就是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而不做“黑漆漆”之人。而在“道”上的明白,就是政治之理的明白,人生之理的明白。道的明白既可在精神上获得自由,也可在政治上获得自由,而对于持儒家人生理想的人来说,还是最终在政治上同时在经济上获得自由。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并非君子不谋食,而是不为谋食而谋食。谋食等而下之,没有更好的前途,而谋道最终可谋得最大的富贵,不求食而食自得,这是志向远大的君子的谋食之道。
由上可见,精神需求是从生理—经济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经济需求伴随精神需求过程的始终。它有时成为人生的目的,而名、道、贵等精神的东西则成为人生的手段;更多情况下,经济与精神的需求共同成为人生的目的。所以,人的生活中,经济生活占据着首要和主导的地位,文学研究者应将经济生活纳入学术的视野,不但纳入研究作家的视野,更应纳入研究作品的视野。在这方面,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是从六朝名士饮酒、吃丹药、穿衣等经济生活之特征研究文学风格之形成的一个成功范例。可惜,此后这类研究渐渐销声匿迹了,近来才有研究商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论著面世。
说文学是精神产品,似无可置疑。然如果追问,文学仅仅具有精神的属性吗?它有无经济的属性?却很少有人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是人们不愿回答这一问题,似乎谈经济属性就降低了文学乃至降低了文人的品格,这是“君子谋道不谋食”传统价值观——农耕文化价值观——作祟的结果。精神对于文学的创作具有主导作用,而经济对于文人的生活、文学的创作、对于文学样式的产生与兴盛,对于文学的刊刻、传播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学的活动是在精神力与经济力合力作用下进行的。只不过有时精神作用处于主导、显赫地位,经济作用处于次要或潜伏地位,有时则相反罢了。
首先看文学的创作。文学的创作是需要条件的,若将其视为精神产品,似乎只需精神条件,无须经济条件。然而,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风”诗中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直接表明百姓所“歌”直接来自“饥”和“劳”的经济生活,且那些歌辞并不是在疲惫的劳动中写出的,而往往是在田间地头休息之余创作出来的。文人的创作也如此,有闲时间是创作的条件。但客观现实是,有钱方有闲,有闲方有文。这说明,文学的创作需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看一看古希腊时代悲喜剧之作、文艺复兴时代的文艺经典大多出于富豪之手,中国的文学也大多是不愁吃穿的士大夫所写,就会明白,文学创作是离不开经济条件的。
其次看创作动机的产生。情感的冲动似乎是纯精神的东西,与经济无关。特别是那些因感动人而流传千古的名作,往往是“不平则鸣”的“发愤”之作。“不平”与“发愤”与经济何干?的确,“不平”与“愤”是情感的。然而,若再进一步追问,因何“不平”?因何“发愤”?就会发现,大多与政治遭际、人生命运直接相关——或仕途多舛而不达,或蒙受不白之冤而未雪……在中国,对于文人来说,政治地位之贵与经济之富总是连在一起的。《儒林外史》写中举前的范进,穷到了卖母鸡的地步;中举后,尚未做官,就有送房的,送银子的,送丫鬟的。这说明,政治地位提高必然伴随经济地位的飙升。仕途不达,理想破灭,同时也是经济滑落的前奏,共同形成欲求的缺失,造成情感的冲动。故而“不平”与“愤”的情感、精神内涵是富贵失落的心理反映,其最深层的东西同样离不开经济问题。只不过情感、精神处于主导地位,经济处于深层的潜藏状态而已。
再次看创作的过程。创作的过程是作者的欲望不能满足后的一种想象的满足,一种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作家的“白日梦”。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创作,单从作品分析,作者在什么地方关注最多、花笔墨最多、投入的情感最多的,必定是他人生最缺失的东西或最得意的东西。缺官位的写做官,缺功名的写功成名就,缺钱财的写经商致富,缺情爱的写郎才女貌、花前月下……写来写去,终不脱生理的需求、经济的渴望,总不出财、色、食、货。
再其次看中国文学史上的现象。某一文学形式所以兴或所以衰,一方面是文学自身的原因,一方面又与文人的兴趣相关。而文人的兴趣,说到底总是与“功名富贵”四字相连。能获得功名富贵往往是文人的兴奋点所在。文人对富贵钱财的向往促成中国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的生成、更迭与繁荣。春秋战国,有志才士为了取得富贵,悬梁苦读,著书立说,纷纷游说诸侯君主,促成了诸子散文的百家争鸣和艺术成熟。汉武帝喜赋,能者擢官,文人趋之若鹜,“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汉赋因之而大兴。汉末建安之时,“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才士因之而贵,“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同上),文人云集响应,五言盛极一时。到了南朝的梁代,皇帝萧氏父子酷爱美诗,能诗成为做官的捷径,于是诗人聚集于皇权周围,宫体诗大兴。唐代则将写诗纳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制度形式确定写诗成为获得功名的必备条件,这无疑成为唐诗得以兴盛的重要一着。宋词的兴盛是词在城市歌楼酒肆的消费中找到了广阔市场,从而也打开了文人消愁遣情的大门。元代杂剧热闹于大都市、明清小说在发达的商业都市泛滥,又是文学借助于市场财力而逐渐商业化的产物。由是观之,文人对财富功名的追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
最后看文学的传播。文学的传播与文学内在形式与审美趣味的变化虽是精神性的表现,然而支配其变化的东西则是书商与出版商之赢利动机。因为,文学的传播的必经之路是文本的刊刻,不刊刻则不可能广泛流传(手抄本能流传下来的毕竟是少数),而刊刻则是商业活动,受商业交换规则、规律的支配。而赢利则需有读者市场,则需满足读者阅读的兴趣。正是读者的好奇心理与审美意趣导引,最终支配着书商、出版商直至作者的活动。中国古代小说长于叙事,尚奇趣,注重声音效果和动作描写,设扣子、置悬念、情节曲折、场面活脱、细笔写衣着的表现特征,正是说听的方式与读者心理需求的形式凝练。戏曲的演出也同样如此。由此可见,文学的传播起主导地位的是商业经济,经济性主导精神性。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力在文学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同精神力在文学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不是外在的、外加的,而是内在的、自生的。以往研究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时,大都将经济作用视为文学之外的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其实这是对于文学性质的阙读,即只将文学看作具有精神的单一属性的缘故。事实上,文学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精神的属性同时又具有经济的属性,就像人的需求既有生理的层面又有精神的层面一样。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就不应该只是精神属性与层面的研究,还应是物质—经济属性与层面的研究。如是,文学的研究才能还其本原。
[许建平,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上海 200433)]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摽有梅论文; 牡丹亭论文; 申报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