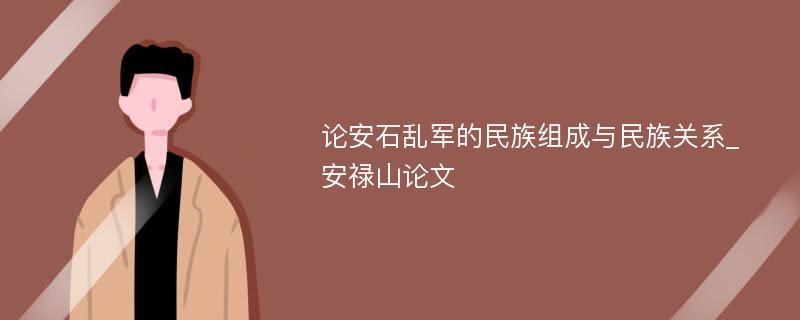
试论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试论论文,关系论文,安史乱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史之乱是造成唐朝由盛转衰甚至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产生很大影响的一次大事变。而探讨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则是分析安史之乱产生、性质、持续8年之久的原因以及藩镇割据形成等问题的关键。本文拟对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安史乱军中的胡化与汉化的两种趋向以及安史乱军中的民族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
关于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陈寅恪、岑仲勉、韩国磐等前辈学者都曾作过一些探讨,但因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这一问题未免给人留下片面化和简单化之憾。
由记载看,参加安史乱军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契丹、奚、回纥等族。其实,只要我们仔细检诸史籍,就会发现安史乱军的主要成员还远远不止这些民族或部落。
《资治通鉴》卷217称:天宝十四载(755),“禄山发所部兵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旧唐书·郭子仪传》称:突厥人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固五千骑出塞,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据《新唐书·韩游环传》记载,“河曲九府”即“河曲九蕃胡”。
《旧唐书·尚可孤传》载:“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代居松、漠之间。天宝末归国,隶范阳节度安禄山,后事史思明。”
安禄山的女婿归义王李献诚(注:参见《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原是黑水靺鞨都督,开元十六年(728)由唐玄宗赐名,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注:参见《旧唐书》卷199《北狄传》。)
黑水靺鞨是活动在西至突厥、南邻高丽、北接室韦区域内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
《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天宝元年(742),“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两蕃即指契丹和奚。渤海国是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以隋末唐初先后迁居至今辽宁省朝阳地区的两批粟末靺鞨人联合部分高丽等遗民建立起来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武则天时吸纳了一些在安东的高丽旧户,并借用高丽兵抗击契丹。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国建立后,“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武艺继立后,“东北诸夷畏臣之”。
《旧唐书·地理志》载:“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诸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而幽州、营州界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契丹、奚、突厥、靺鞨、室韦及其他胡人。
《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安)庆绪献奚、契丹及同罗、阿布思等。阿布思者,九姓首领也……代为蕃首……后为回鹘所破,禄山诱其部落降之。自是禄山精兵无敌于天下。”(注:参见《新唐书》卷125《张说传》称阿布思为“河曲降虏”;同书卷193《程千里传》称其为“突厥首领”;《资治通鉴》卷215称其为突厥西叶护。)
《旧唐书·李怀仙传》称怀仙“柳城胡人。世事契丹,降将,守营州。禄山之叛,怀仙以裨将陷河洛”。
综上所述,安史乱军具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靺鞨、九蕃胡、居住在回纥的昭武九姓、(注:参见《新唐书》卷224《李忠臣传》。)
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扶余、新罗等民族成份。
那么,我们是否就可据此说安史乱军全是由少数民族和已经胡化的汉人组成的呢?是否就能得出“安禄山利用其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笼络诸不同之善战胡族,以增强其武力”(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的观点呢?是否就能得出“贼军之中坚,大半为外来异族”(注:桑原隲藏和岑仲勉都持这一观点。见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8页。)
的观点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第一,在史书中被称为安禄山、史思明“腹心”、“宾佐”和“心手”的最核心人物有高邈、何千年、许叔冀、吉温、张万顷、孙孝哲、曹将军、徐归道、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等11人,能够考清是少数民族的,只有孙孝哲和曹将军两人。
第二,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过程中和称帝时所重用的主要是汉人。《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十一月,反于范阳……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腹心。”而高尚、严庄“专居(安禄山)左右以画筹”。(注:《安禄山事迹》卷中。)
在这五个关键人物中,只有孙孝哲是少数民族。安禄山称帝时,大燕政权的左相达奚珣、右相张通儒、中书侍郎高尚、御史大夫严庄,前者为鲜卑人,后三人均为汉人。乾元二年(759)四月,史思明称帝时的宰相周挚也是汉人。除了上述几个核心或关键人物外,在安史政权中担任过重要角色的一些人物几乎全是汉人。如安史政权的宰相陈希烈、平冽、张垍,尚书敬荣,中书令王伷和张均,全是汉族人。
第三,在安史乱军中领兵打仗的将领主要有崔乾祐、蔡希德、尹子奇、牛廷玠、徐璜玉、安守忠、安俊雄、李秦授、李归仁、毕思琛、周万顷、安晓、李钦溱、李立节、李庭伟、张孝忠、王武俊、申子贡、荣先钦、阿史那承庆、范秀严、阿史那从礼。这些将领能够考清是少数民族的仅有张孝忠(奚)、王武俊(契丹)、阿史那承庆(突厥)和阿史那从礼(突厥)等人。其他如安守忠、安俊雄、安晓疑为安禄山的同一种族人。如此,安史乱军中领兵打仗的将领多数还是汉族人。尤其是安禄山被杀后,率兵打攻坚战的多数是汉族将领。至德二载(757)一月,史思明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从大同,牛廷玠从范阳,共率兵10万人围攻太原,这四路将领中只有史思明为胡人;在乾元年(758)十月安庆绪分三军营救卫州时,崔乾祐领上军,田承嗣领下军,安庆绪亲领中军,只有安庆绪为胡人;上元元年(760),史思明准备实施全面进攻计划时,“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注:《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
这四路将领全是汉人。
第四,安禄山起兵后,令贾循留守范阳,吕知诲守平卢,高秀岩守大同,以后每攻占一地,大都派汉族将领镇守该地。如令安忠志(奚)领精兵驻扎土门,张献诚(张守珪之子)守博陵,李钦湊守井陉口,李庭望守陈留,武令珣守荥阳,张万顷为河南尹,崔乾祐守陕郡,张通儒之弟张通晤负责睢阳,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有的记载为田乾真为京兆尹),安守忠镇关中,牛廷玠屯安阳,安太清守怀州,周挚、许叔冀屯福昌,史朝义守冀州,令狐璋戍滑州。这些为安、史镇守要地的官员中,除了安忠志和安禄山、史思明之子能够考清为胡人外,其余大都是汉族人。
第五,从安史乱军内部的四次政变来看,起决定作用的也是汉族人。杀安禄山是汉人严庄的计策,契丹人李猪儿具体执行。史思明杀安庆绪兄弟、高尚、孙孝哲、崔乾祐、安守忠、李立节,拘捕阿史那承庆,则是判官汉人耿仁智的计策。史称耿仁智是“忠谋之士”,(注:《旧唐书》卷200《安禄山传》。)
跟随史思明长达30年之久。史朝义杀史思明是汉人骆悦和许叔冀之子许季常的计策。参与史朝义杀史朝清的有向贡、阿史那玉、高久仁、高如震等4人,除了阿史那玉为突厥族之外,其余全是汉人。
第六,从安史乱军内部官兵的向背情况来看,汉族官兵对安禄山和史思明比少数民族官兵还要忠诚。从安禄山发动叛乱到被平定下去,汉族人先后虽有严庄、能元皓、高秀岩、王暕、宇文觉等主动叛离乱军的,但也有贾循犹豫不决最后被叛军所杀的。而少数民族将士不仅有许多人非常绝情地脱离乱军,而且有时还会毫无区别地残杀同类。如安禄山攻陷长安后,“同罗、突厥从安禄山反者屯长安苑中,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谋邀结诸胡,盗据边地”。(注:《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
这无疑是对安禄山的致命打击。再如史朝义即位后,突厥人阿史那玉败走武清,“(史)朝义使人招之,至东都,凡胡面者,无少长悉诛”。(注:《新唐书》卷225《史思明传》。)
又据《安禄山事迹》卷下记载,突厥人阿史那承庆离开洛阳后,史朝义的燕京兵马使高鞠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尽殪,小儿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
第七,安史乱军中尽管也有一些回纥、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将士,但回纥人最后成了唐朝平定叛军的坚定支持者,被唐肃宗称赞为能为国家就大事成义勇者。契丹和奚也先后加入了唐军的平叛之列。(注:《全唐文》卷42《还京减省供顿诏》。)
第八,从安史乱军的士兵构成来看,既有少数民族人,也有汉族人。在不同的将领所率部众中,有的可能少数民族士兵占多数,有的可能汉族士兵占多数。如张通儒屯守在长安的10万人中,多数是奚人。(注:《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
张献诚所率的万余人多数是由汉族人组成的团练兵。(注:《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李庭望在东袭宁陵、襄邑时,率领“蕃、汉二万余人”。(注:《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
安禄山攻取河北后,“郡置防兵三千,杂以胡兵镇之”。(注:《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
针对乱军中时有反叛现象,安庆绪曾下令,“凡有谋归者,诛及种、族”。胡注说,“胡人种诛之,华人族诛之”。(注:《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三月。)
说明乱军士兵中胡、汉都有。即使在少数民族将领所部的士兵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如史朝义杀史朝清导致叛军内讧后,阿史那玉“领诸蕃部落及汉兵三万人”,(注:《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三月胡注。)
与叛军衙将高如震战于宴设楼前。
第九,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种种原因,唐中央的不少汉族文官武将加入了叛军的行列,使叛军的势力大为增强。如陈希烈、张均、张垍等中央官员投降叛军后,“贼势大炽,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注:《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
进一步滋长了叛军的嚣张气焰。再如雍丘令狐潮投降叛军后被封为将军,率领叛军精兵围攻雍丘,继而又多次劝说张巡以城降贼,并筑城切断张巡的后援,使睢阳城内出现了人食人的悲惨局面。
那么,如何解释李泌所说的“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注:《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二月。)
呢?笔者认为,一方面,李泌是在为唐肃宗鼓劲打气时所说的这番话,当然会故意夸大唐军的势力,缩小敌军的势力。只要我们看一下他说的不过两年就可以平定乱军的话,就能明了这一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距他所说的平定乱军的时间还有六七年。另一方面,李泌说的“华人为之用者,独周挚、高尚等数人,余皆胁制偷合”,指的是乱军的最核心人物才能够甘心情愿、死心踏地为乱军所用,其他都是被胁迫的。他在同一份疏中也说过“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注:《全唐文》卷378《劝肃宗破贼疏
)的话,其实追随安禄山的少数民族人很多,岂止阿史那承庆一人!
二
安史乱军中虽然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靺鞨、九蕃胡等少数民族将士和居住在回纥的昭武九姓、柳城胡以及归属于渤海的高丽残部、新罗等人,但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汉族人。安史乱军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民族结构,原由固然很多,但如下几方面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作为蓄谋叛乱已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其根本目的是要推翻李唐王朝,(注:刘昫曾说:“大盗作梗,禄山乱常,词虽欲诛国忠,志则谋危社稷。”见《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
建立一个统治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新政权。基于这一目的,他们当然要充分考虑当时唐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民族结构。我们知道,虽然在唐朝的北方、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活跃着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而且有的已对唐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从总的布局来看,汉人生活的地区占绝大部分。这种布局势必会使安禄山、史思明充分考虑汉族人的能量和势力,不致于把视野仅仅放在少数民族身上。
第二,安禄山、史思明在叛乱之前和叛乱之后都曾广泛搜罗汉族中有能力的人物为其所用。安禄山、史思明虽是胡人,但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唐王朝统治地区内汉族是主要民族,汉族人是其依靠的主要力量。为此,他们广泛搜罗唐朝宗室、汉族名流、儒学贤才以及唐朝名将的后代为己所用。例如,唐太宗四世孙李之芳“有令誉,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注:《新唐书》卷80《太宗诸子传》。)
天水略阳人权德皋是后秦尚书权德翼之孙,“少以进士补贝州临清尉。安禄山……假其才名,表为蓟县尉,署从事”。(注:《旧唐书》卷148《权德舆传》。)
诗人王维九岁“知属辞”,开元初进士及第,“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瘖。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注:《新唐书》卷202《文艺·王维传》。)
中山无极人甄济“早以文雅,见称于时”,安禄山对其颇为赏识,推荐为范阳郡节度掌书记。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派蔡希德“领行戮者李掞等二人,封刀来召“甄济,安庆绪”亦使人至县,强舁至东都安国观”,(注:《旧唐书》卷187《甄济传》。)
强迫甄济为其效劳。宦官高力士就对安禄山搜罗汉族能人为其所用的用意和做法看得非常清楚,他曾提醒唐玄宗说,“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为禄山所器”。(注:《新唐书》卷125《张说传》。)
可惜唐玄宗当时正庞信安禄山,根本没有领会高力士这番话的深刻用意。据《新唐书·郑虔传》记载,安禄山曾“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被挟持的百官中就有一些儒学贤才,如郑州荥阳人郑虔著书80余篇,是当地有名的博学多识之才,就在这时被安禄山授为水部郎中。唐朝名将张仁愿、薛仁贵的后代张通儒、薛嵩也被安禄山拉到了自己的阵营,张通儒曾任大燕政权的左相、西京留守;(注:《旧唐书》卷200《安禄山传》。)
薛嵩不仅参加了安史之乱,而且还为史朝义防守相州。(注:《新唐书》卷111《薛仁贵传》。)
张仁愿和薛仁贵都是唐朝有名的军事将领,张仁愿为了断绝“南寇之路”,主动承担起筑“三受降城”的重任,“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注:《旧唐书》卷93《张仁愿传》。)
薛仁贵在与高丽、契丹、九姓突厥战争中大显身手,战功卓著,军中传有“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赞歌。经薛仁贵的出击,“九姓(突厥)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注:《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
他们的后代能被安禄山拉入叛军队伍更能说明安禄山对汉族人才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禄山叛乱后,尤其是在叛军攻陷两京——长安和洛阳后,唐王朝的一些文武官员,或由于对唐玄宗和杨国忠表示不满,或由于官场失意,或看不清局势发展的前景等原因,主动投降了叛军,这正如《旧唐书》作者所说的那样:“禄山寇陷两京,儒生士子,被胁从、怀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顺,毁家为国者少焉”。(注:《旧唐书》卷111。)
这些“儒生士子”在安史乱军中十分活跃,无论是对唐朝平叛还是乱军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安庆绪、史思明和史朝义为了建立、巩固自己的叛乱政权,也都大量搜罗汉族人为己所用。乾元二年(759),史思明“聘儒生讲制度”。(注:《新唐书》卷225《史思明传》。)
《新唐书·邵说传》载:“庆绪遁保西城,搜胁儒者为己用。”河南洛阳人裴宽“有重名于开元、天宝间”,其子裴谞在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后逃匿于山谷。史思明“素慕(裴)谞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骑数十迹逐得谞。思晚见之,甚喜,呼为郎君,不名,伪授御史中丞,主击断”。(注:《旧唐书》卷126《裴谞传》。)
相州安阳人邵说进士及第,颇受史思明的器重,被史思明封为判官。邵说也为史思明父子尽心尽力,成了史氏政权的有功之臣,唐金吾将军裴儆说他“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判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注:《旧唐书》卷137《邵说传》。)
当然,笔者这样立论并不是否定少数民族在安史乱军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安禄山、史思明能够迅速攻陷东都洛阳,入兵西京长安,少数民族将士的剽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笔者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靠少数民族将士,安史乱军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叛乱初期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更不会坚持8年之久。
三
既然安史乱军是一个民族成份非常复杂的军事集团,那么,在这个军事集团里,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如何呢?韩国磐先生认为,河朔一带“少数民族和汉族存在着矛盾,所以少数民族将领就利用这种矛盾,起兵来夺取政权。安禄山在起兵前,尽力排斥汉将,提升少数民族将领……所以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注: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9-260页。)
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河朔地区的民族关系一直就比较缓和,即使到安史之乱接近尾声时安史乱军中的民族关系仍然比较缓和。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安史乱军中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将士在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渐趋一致。
学者每每谈论河朔地区,皆称胡化。《新唐书》作者说:“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注:《新唐书》卷148《史孝章传》。)
近人倡导这一观点而且影响深远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注意了河朔地区的“胡化”趋向,而忽略了河朔地区的“汉化”趋向,即忽略了河朔地区汉文化的保持和提高的趋向。
《新唐书·李光弼传》称,“范阳本贼巢窟”。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范阳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情况。
《新唐书·卢怀慎传》载:“卢怀慎,滑州人,盖范阳著姓……及长,第进士,历监察御史。神龙中,迁侍御史。”文化水平不高是难以考取进士的。
《新唐书·张嘉贞传》载:“本范阳旧姓,……以五经举。”其子张延赏“虽早孤,而博涉经史”,受到了大臣苗晋卿的器重,娶苗氏女为妻。
《旧唐书·卢粲传》载:“卢粲,幽州范阳人……祖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行于时,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学涉,高宗时为雍王记室。粲博览经史,弱冠举进士。”卢粲祖孙三代都是博览群书、颇有名望的文人。
被称为“唐初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是幽州范阳人,照邻“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注:《旧唐书》卷190《卢照邻传》。
说明范阳不乏传授学业的知识阶层和浓厚的学习气氛。
与陈子昂私交很深的卢藏用也是幽州范阳人,史称藏用“能属文,举进士”。其弟卢若虚“多才博物”。(注:《新唐书》卷123《卢藏用传》。)
《新唐书·张仲武传》载:“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陈寅恪先生在解释这条资料时说:“张仲武受汉化较深,在河朔颇为例外”。(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0页。)
陈先生所下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其实,除了前面所引资料外,关于河朔地区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史料还有很多。例如:
卢景亮,幽州范阳人,“少孤,学无不览。第进士、宏辞,授秘书郎”。(注:《新唐书》卷164《卢景亮传》。)
卢商,范阳人,“少孤贫力学,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四年(809),“擢进士第,又书判拔萃登科”。(注:《旧唐书》卷176《卢商传》。)
卢商虽出身贫寒,仍能“力学”考取进士,不仅说明幽州人有获取功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说明这里的人有较强的求知欲望。
卢钧,“本范阳人。祖旻,父继。钧,元和四年进士擢第,又书判拔萃,调补校书郎”。(注:《旧唐书》卷177《卢钧传》。)
卢钧祖父卢旻也“涉猎书史”。(注:《旧唐书》卷114《卢炅传》。)
这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
卢携,“范阳人。祖损。父求,宝历初登进士第。……携,大中九年进士擢第,授集贤校理”。(注:《旧唐书》卷178《卢携传》。)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
刘蕡,幽州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沉健于谋,浩然有救世意。擢进士第”。(注:《旧唐书》卷178《刘蕡传》。)
上述这些幽州籍人士都通过考取进士获取了功名。当然,有一些人并没有考取进士,但因其受幽州学习氛围的影响,也是自幼就致力于学业,最后获取了功名。如范阳卢群“少好读书”;(注:《旧唐书》卷140《卢群传》。)
卢征“少涉猎书记”;(注:《旧唐书》卷146《卢征传》。)
幽州良乡人李景略“阖门读书”。(注:《旧唐书》卷170《李景略传》。)
列入《新唐书·儒学传》的卢履冰也是幽州范阳人。即使卢彦衡之女也能“略涉书史”。(注:《旧唐书》卷193《列女传》。
由上述可见,幽州并非“全是胡化”,汉文化继续保持和提高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贝州汉文化的保持和提高的情况。
《新唐书·儒学传》载:“路敬淳,贝州临清人。……少志学,足不履门。居亲丧,倚庐不出者三年。……后擢进士第。天授中,再迁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崇贤馆学士。”路敬淳不仅是一个受儒教影响很深的孝子,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学、进取心很强的有志之士。
《新唐书·崔邠传》载:“邠字处仁,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献赋行在,肃宗异其文,位吏部侍郎。邠第进士,复擢贤良方正。”邠的四个弟弟就有三个考取了进士。崔郾“中进士第,补集贤校书郎”;崔鄯“擢进士,累迁至左金吾卫大将军”;(注:《旧唐书》卷163《邠传》。)
崔郸进士及第,后为集贤殿学士。类似这样刻苦学习并且出了几个进士的家庭在其他地区实属罕见,就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和洛阳也是比较少见的,由此可见汉文化在这里保持和提高的程度。
原居贝州安平后徙卫州的崔宁,“世儒家”。(注:《旧唐书》卷144《崔宁传》。)
另据《新唐书·崔群传》记载,崔群为“贝州武城人。未冠,举进士,陆贽主贡举,梁肃荐其有公辅才,擢甲科,举贤良方正,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数陈谠言,宪宗嘉纳,因诏学士:‘凡奏议,待群署乃得上。’”
唐代河朔地区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趋势是普遍存在的。唐中期大臣颜杲卿说:“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注:《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四载十二月胡注。)
揭示了河朔地区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真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下问题:(1)河朔地区具有浓厚的学习氛围,“阖门读书”者和书香门第并非孤立现象,有的人虽穷困潦倒,但仍能刻苦读书,以获取功名。(2)河朔地区有从师受业的风气。(3)儒家思想对河朔地区影响很深。如幽州范阳人卢氏在其丈夫死后全家逼其改嫁时,她先是“称疾不许”,后又“粪秽蔑面”,“断发自誓”(注:《新唐书》卷205《列女传》。)
不嫁。如果这位卢姓妇女不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唐代改嫁已成风气的情况下,很难设想她会顶住家庭的巨大压力。
那么,河朔地区为什么会出现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情况呢?
第一,门阀士族的影响。范阳卢氏是山东门阀氏族之一。门阀氏族虽经唐太宗和武则天时的多次压抑和打击,但其心理、习性、崇尚等潜在的东西并非经过一两次压抑和打击就可以全部改变的。唐文宗就曾经说过,“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注:《新唐书》卷172《杜兼传》。)
说明崔卢大族到唐代后期还有一定影响,还受到许多人的仰慕。所以,门阀士族所一直保持和炫耀的礼教、儒家思想及皓首经书等传统还沿袭不断。
第二,科举制度激励人们发奋学习。有的人尽管出生或年青时生活在河朔地区,但他们所学内容除了儒家经典、史书、诗文之外,毫无疑问,绝不会是少数民族比较落后的文化。当时的河朔地区,对在长安不得志的个别官吏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对原是河朔地区的大部分有抱负的青年来说,他们所迫切希望得到的是中央官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然以中央政权所要求和鼓励的道德规范和文化标准作为自己的修身准则和追求目标,以跻身于中央官僚之列。所以,原来汉文化水平较低者则急起直追,力图赶上水平较高者;原来汉文化水平较高者,仍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持和提高。由此可见,当时的河朔地区并非“全是胡化”,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趋向是非常明显的。
第三,营州地区是隋唐时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近长城,是塞内外汉族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集中交流地。(注:参见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3页。)
粟末靺鞨的厥稽等八部在隋末迁居到营州(即柳城)后,很快就受到了汉文化的浸染,普遍喜好汉族的“冠带”等风俗习惯,社会得以迅速发展。“本高丽别种,后徙居营州”(注:《唐会要》卷96《渤海》。)
的渤海靺鞨,也很快浸染了汉族文化,在武则天时期即筑城以居,渤海国建立后,“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注:《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还遣使到唐“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注:《册府元龟》卷999《请求》。该书此处年代误作开元三十六年,《三十六国春秋》中的“三”也应为多出之字。)
唐代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诗就曾说,“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注:《全唐诗》卷583。)
而安禄山和史思明分别是营州柳城杂种胡和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他们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文化中心和文化的集中交流地,无疑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浸染,再通过他们去影响其他少数民族将士。
当然,河朔地区的胡化趋向以及汉文化保持和提高趋向的发展速度并非一致,但总的来看,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汉人和胡人经历许多摩擦、了解、妥协,逐渐进入相互适应阶段。从总过程来看,摩擦、妥协比了解、适应时间要短一些。一般说来,在适应阶段,两种类型的人相处比较融洽,关系相对平衡,面对突发性事件会团结一致。安禄山自阴谋叛乱直到被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十分注重搜罗博学多才的汉人为其所用。这些汉人对那些愿为安禄山卖命的少数民族官兵来说,是汉化的熔炉和鼓风机,所以,少数民族官兵在安史乱军中逐渐被汉化,在与唐中央抗争中,他们既具有剽悍、勇猛善战等特点,又学到了汉族人的作战方式,遂在战场上所向无敌。如阿史那承庆本为突厥人,但在与唐军作战时,主要采用了汉族人的作战方式。《旧唐书·薛愿传》载:“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徹殆尽,而外救无至。贼将阿史那承庆悉以锐卒并攻,为木驴木鹅,云梯冲棚,四面云合,鼓躁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余日,城中守备皆竭,贼夜半乘梯而入。”这种作战方式,在此之前,突厥尚无先例,可见这是从汉族将士那里学来的东西。
(二)汉族和少数民族将士积极配合。
由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将士在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渐趋一致以及他们长期相处,所以,在许多方面他们能够积极配合。在关键时刻,一般由汉族人出谋划策,少数民族人具体执行。如安禄山被杀,由汉人严庄出谋划策,契丹人李猪儿入帐行刺;史思明杀安庆绪兄弟、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9位高级官员,则是汉人判官耿仁智的计策;史思明被杀,由汉人骆悦、蔡文景、许季常共同谋划,由胡人曹将军深夜率领部下前往史思明住宅捕杀,骆悦、曹将军和骆悦的麾下周子俊配合得比较默契;史朝清被杀,由汉人向贡出谋划策,突厥人阿史那玉和汉人高久仁、高如震具体执行,他们配合也比较默契。
再从乱军与唐军作战的总过程来看,汉族将士和少数民族将士也能密切配合。乱军攻陷长安后,安禄山派史思明、尹子奇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将领率10万劲兵“并力攻河北诸郡”,(注:《全唐文》卷514《鲁颜公行状》。)
“先陷苍瀛,次陵德隶,猛若燎火,冲若如决防”。(注:《全唐文》卷394《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
随后相继攻陷了饶阳、河间、景城和乐安。在安史乱军逃离长安、仆固怀恩率领少数民族将士奋力攻打叛军时,严庄“自将兵十万与(张)通儒合,钲鼓震百余里。尹子奇已杀张巡,悉众十万来,并力营陕西,次曲沃。先是回纥傍南山设伏,按军北崦以待。庄大战新店,以骑挑战,六遇辄北,王师逐之,入贼垒,贼张两翼攻之,追兵没,王师乱,几不能军。(李)嗣业驰,殊死斗,回纥自南山缭击其背,贼惊,遂乱,王师复振,合攻之,杀掠不胜算,贼大败,追奔五十余里,尸髀籍籍满阬壑,铠仗狼扈,自陕属于洛。庄逃还,与庆绪、守忠、通儒等劫残军走邺郡”。(注:《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
在攻打博陵和常山时,混血儿史思明和汉人李立节“将蕃、汉步骑万人”,(注:《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二月。)
很快将其攻克。安庆绪率领中军在卫州之南与唐军交战时,“孙孝哲、薛嵩佐之”。(注:《新唐书》卷225《安禄山传》。)
孙为契丹人,薛为汉族人。帮助史思明之子史朝清留守幽州的阿史那玉、向贡、张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东武等少数民族将士和汉族将士也密切配合,积极协作。这些都增强了安史乱军的作战能力。由此可见,安史乱军中的民族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如果这一复杂的军事集团中的民族矛盾比较突出,那么作为蓄谋叛乱已久且智商很高的安禄山,在正式发动叛乱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只与严庄、高尚和阿史那承认三人“密谋,自余将佐皆莫之知”。(注:《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十月。)
持民族矛盾观点者常以如下史料作为论据:“(天宝)十四载五月,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注:《安禄山事迹》卷中。)
我认为,结合安禄山的提拔官员政策来看,这条资料只能说明安禄山唯才是举,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矛盾问题。据《安禄山事迹》卷中记载,天宝十三载(754)元月,安禄山“奏前后破奚、契丹部落,及讨招九姓、十二姓等应立功将士,其跳荡、第一、第二功,并请不拘,付中书门下批拟。其跳荡功请超三资,第一功请超二资,第二功请依资进功”。很明显,安禄山提拔官员的标准是功劳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而并非民族成份。有功受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安禄山登上政治舞台到他被杀的约20年的时间里,很难找到他改变这一标准的具体史料,所能看到的则是大量有才能、有名望、治军严肃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士,或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步入仕途,如“颇笃学,赡文词”(注:《旧唐书》卷200《高尚传》。)
有智谋的高尚就曾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任平卢掌书记;或受到安禄山的器重而得到提拔,如田承嗣“世为卢龙小校,禄山以为前锋兵马使。尝大雪,禄山按行诸营,至承嗣营,寂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者,禄山以是重之”,(注:《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载二月。
)遂将其提拔为将帅,委以重任。所以,所谓被蕃将代替的32位汉将应当是才能低下、功劳不大或者与安禄山意见相左者,并不能以
此说明安史乱军中的民族矛盾。
标签:安禄山论文; 史思明论文; 唐朝论文; 安禄山事迹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契丹论文; 突厥论文; 新唐书论文; 旧唐书论文; 司马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