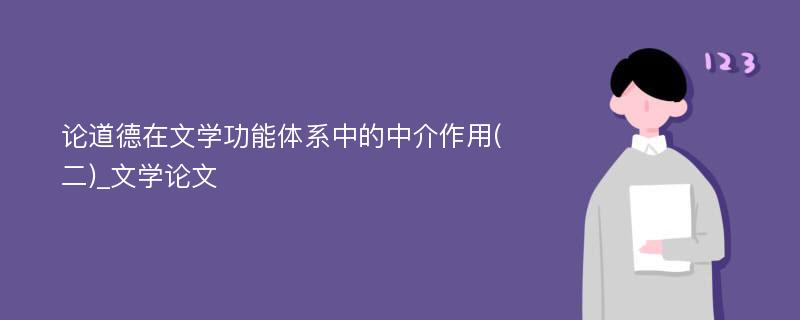
通向审美的中介——论道德在文学功能系统的中介作用(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介论文,作用论文,功能论文,系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的功能系统是复杂的多元的。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一受构成文学作品的多种内容要素所决定,二受文学活动与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外部联系所制约。然而,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部门,文学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审美的。这就决定了一切因素进入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审美转化的问题,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文学活动(包括创作活动和鉴赏活动)的对象。至于文学和其它社会生活领域的联系,无论方式、形态有多么不同,都不能不或浓或淡地带上审美的色彩。然而,各种因素向审美方向转换,好像在多数情况下都要经过某种道德的中介,或者说,先要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化,然后才能成为作品艺术总体的构成部分。另外,文学作品要产生社会影响,也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鉴赏,并进而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才有可能实现。读者在阅读中,通过美的享受,获得了某些新的人生启悟,或完全接受作者的价值观念,或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人生道路有所反思,有了新的认识与评价。当这些收获作为新补充进来的,或经过丰富了的行为规范,影响他的生活以及他与周围人们的关系时,道德的中介作用也就看得相当明显了。
道德之所以在文学活动中会起某种中介作用,其理论根据主要有两条:一是文学作品主要是以人、人的社会行为和人的心态为描写对象的;二是美和善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是重叠的,有时甚至是合一的。
以政治因素进入文学作品情况而论,作家并不要像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那样,去研究政治运作的特殊规律,也不必像历史学家去记载政治事件的一般过程,而是主要着眼于政治活动中的个人,着眼于个人特殊的政治命运、政治行为,以及这行为后面的动机,特别是通过具体遭遇而表现出来的品格、节操等等。屈原的《离骚》是一首有浓厚的政治抒情味道的长诗,但政治因素之进入此诗,却不是赤裸裸的移置,而是经过了充分的审美转化。这种转化的中介是诗人以火样的激情,抒写了自己高尚的品德。他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这里的“内美”,指的就是忠贞不二的道德素养与情操。司马迁评价这首诗时,也着重于对诗人政治品德的肯定,说他“上称地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老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贾生列传》,见《史记会注考证》卷84,文学古籍刊行社版,第3840—3841页。)司马迁可以说是屈原身后的第一个知音。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作为政治抒情诗,表现的则是浩大的政治胸怀和视死如归的政治气节。当代长篇小说《红岩》所描写的是共产党人在狱中可歌可泣的政治斗争。但罗广斌和杨益言两位作者落墨的重点却是那些革命者在敌人刑讯、屠杀面前表现出来的政治节操。读者在对作品的鉴赏中,首先接触到的也是许云峰、江姐以及其他英雄人物的品德,这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下通过他们英勇不屈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品德。他们的品德在读者心里激起一种崇高的美感,使之受到教育和感染。在这里,对人物品格的道德评价,同时也是对他们的审美评价。人物的品格,潜移默化地为读者树立了榜样,人物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也因而变成读者的追求目标。这样,先是政治在作品中道德化了审美化了,体现在人物的行动和心理活动中,然后,通过鉴赏,这审美化了的政治道德,又以道义的和审美的力量,把作品所携带的政治信息传递给读者,影响其社会行为。这大致就是政治因素在文学活动的全过程中所经历的功能转化。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理性,道德也属于理性范围,它们都有着冷静的,以至冷酷利害权衡。但是道德行为,只要出于真诚,总带有较强的情感倾向;政治不讲情感,不需要情感,也无所谓同情和怜悯,所以鲁迅说他当不了政治家。通常所说的政治情感,其实主要是一种政治道德情感。艺术活动的根本特点之一是情感。创作、鉴赏,均无例外。因此,理性的政治因素进入文学作品,产生审美效应,就有一个情化的问题,这就要通过道德的中介。
不仅文学的政治功能,常常是通过道德的中介,以真挚的政治道德的情化方式,影响读者,就是作品中对某些宗教观念的宣传,也往往是这样。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的基础上的,宗教理想都带有彼岸的性质,而人们在现世的苦修、苦行被看作是换取身后彼岸幸福的条件。宗教为了维持其绝对的权威,为了对付异教徒和异端,固然也运用如十字军东征那样的战争,运用如宗教裁判所火烧布鲁诺那样的酷刑,但对广大信教者的约束却主要还是通过宗教道德信条,如“戒律”等来完成。宗教戒律对信徒的约束,实际上起着一种类似于世俗道德规范的作用。一方面它建立在信仰、崇拜、盲从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它也依赖由于对神的敬畏而来的自我戒惕。那些苦行僧,之所以能够长期忍受禁欲的痛苦,弃绝一切人世享乐,压制作为人的本能的七情六欲,原因也在这里,不过他们比一般信徒做得更极端、更绝对罢了。一切宗教宣传,要最终在信徒身上起作用,要使非信徒变成信徒,要使动摇的信徒变成坚定的信徒,都不能不使他们达到心甘情愿接受宗教道德的约束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对神、对彼岸世界的信仰,落实为行动,才能算是皈依。至于以文学形式宣传某些宗教观念,更是离不开对人的行为和作为的动机的描写。还是以托尔斯泰的《复活》为例,这部作品体现作家的宗教观念,是相当明显的。第一部一开始,便引用了四段《圣经》的原文作为卷首题辞,这固然给了读者以很强的宗教提示,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把自己的宗教观念化入人物的命运和人物行为的血肉之中去了。贝奇柯夫在评论《复活》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托尔斯泰认为,只要人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生活的重要性——照他看来,生活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奉行‘主’也就是说——‘上帝’的意志,——那么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人类天性的种种歪曲现象,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不道德现象,就会立刻消失无踪。必须承认‘主’,这样每一个人的眼前才会显出明确的生活道路,这样大家才会和平、友爱,彼此和睦地过着生活,人对人的一切暴力迫害方式也就不会存在。人会摆脱一切恶习,世界上不再会有谎言和欺骗,人会变得像孩子们那么天真、幸福。由此可见,并不是社会性的变革,而是每一个人对上帝的个别的皈依,才注定了在人类天性的改造和人类新的道德伦理准则的确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托尔斯泰评传》第528页。)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让读者感受到的是带着感情、带着作家强烈的主观爱憎和思考,具有毛茸茸的生活形态的道德化了的宗教,或宗教化的道德,而不是抽象的、干巴巴的宗教教条的说教。托尔斯泰宣扬的以爱、以人与人的平等为核心的宗教道德纲领,也许是幼稚的、可笑的、荒唐的,在本质上也是虚伪的,但他自己却真诚地相信着。他把虔诚的宗教道德感情,溶进人物悲欢离合的遭遇和内心生活中去,使作品具有一种纯净的、美的道德境界,从而增强了感染读者的力量。
文学的认识功能有没有道德化的问题呢?虽然不能说一切知识因素在通向审美的阶梯上都要经过道德的中介,但至少有相当部分会与道德因素发生关系。这是因为,认识功能源于作品的艺术真实。但艺术真实是作家的真诚和描写对象所提供的客观真理性相结合、相统一的产物。从客观真理性的一面说,作品的描写必须符合于客观事物的实际,这关系到读者获得的知识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实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从主观的真诚性或真挚性来看,则又不仅仅是认识问题,它还涉及敢不敢面对真理的问题,有没有勇气追求真理的问题等,这又不能不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鲁迅说刘和珍“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指的就是一种道德的和人格的境界。这种境界,同样也适用于作家。
对于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来说,创作主体的真诚往往显得更重要。单纯地给人们以知识,这不是,或主要不是文学的任务,科学、哲学、史学、经济学等,在这方面都远优于文学。所以,文学作品一般在揭示某些自然和社会的真理时,不像科学著作那样一定要做到尽可能客观,而是着重写人对真理的追求,探索,以及在这过程中的奋斗精神。布莱希特的《伽里略传》,描写了物理学家伽里略因为证明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而冒犯教廷,而被判管制的故事。剧作家的着眼点没有放在展示这个人物论证诸如月球表面凸凹不平,木星有四个卫星,太阳黑子,银河由无数恒星组成,以及金星水星的盈亏等现象,而是重点放在他的人格所受到的严峻考验上。作为科学家,他的良心要求他坚持被他发现和证实了的真理,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样,他便很难逃脱布鲁诺那样的命运。最后,他屈服了。他明知道这个黑暗的时代需要以自我牺牲去唤醒人们科学良知的英雄,但他作不到,于是,只能长叹“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不幸的”而低下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高贵的头颅。由于布莱希特以惊心动魄的力度,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内心剧烈的冲突,就使伽里略的悲剧显出很强的道德色彩。在舞台上,观众是眼看着主人翁的人格是怎样被压弯、压折的,走出剧场,他们当然会痛恨那个残暴、黑暗的时代,同时也不能不为伽里略的屈膝而感到深深的惋惜,他毕竟太不争气了。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虽然不可能说出一切进入文学作品的因素在完成审美转化中,都要通过道德的中介,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超越这个中介,无法回避与道德的联系与结合,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应把道德中介理解为赤裸裸的道德说教。那样,不仅无助于各种非审美因素向审美方向的转化,反而会扼杀了艺术之美,让人生厌。这种让人生厌的情况,即使在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的作品中,也时有发生。所以,作者所要宣扬的道德原则,除了其本身的价值之外,还要与文学的其它社会功能相结合,形成综合的审美效应,寓教于乐,寓庄于谐,否则就没有鉴赏价值,就不易为读者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