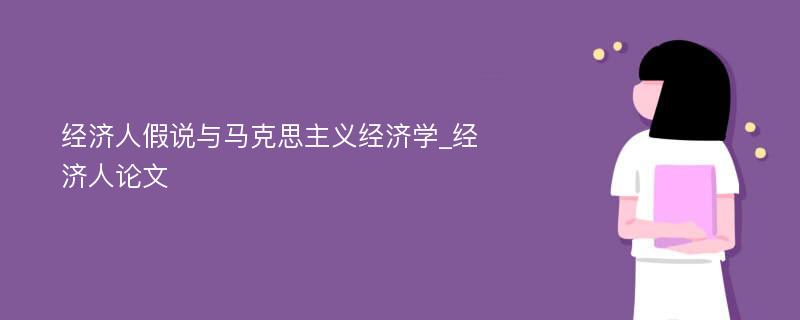
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待经济人假设大体有以下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力图彻底否定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定地位,把该假设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对立的;①另一些学者则在批评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同时,承认马克思经济学也继承了源自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②理论上的这种分歧,为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预留了空间。
本文第一节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概念,认为在斯密的经济人概念中存在着两面性,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别继承了斯密经济人概念的不同侧面。第二节分析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透过资本一般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做了基本规定。第三节通过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引发的争论,分析了竞争即“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并探讨了下面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如何从一个普遍的动机出发解释竞争中的不同行为。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追求剩余价值和追求利润,在意义上是不同的。第四节介绍了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利润最大化假设的批评,指出这一批评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这一节还扼要地讨论了马克思对不确定性的分析,以及在他看来这种不确定性如何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目标和行为。第五节简略地评论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与行为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所可能有的指导意义。
一、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谈起
经济人概念滥觞于古典经济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判功利主义时,曾这样评论了功利主义和新兴的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革命时期,即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最初两次斗争中,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出现了这种理论。当然,这种理论早已作为心照不宣的前提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是这种功利论的真正科学;它在重农学派那里获得了自己的真正的内容,因为重农学派最先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个体系。③
古典经济学家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假定,是以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前提的,关于经济体系与经济人概念的关系,捷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西克曾做过如下深刻的评论:
经济人的概念以系统的观念为基础。经济人就是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的人,作为系统的一个功能要素的人。这样的人必须具有开动这个系统所必不可少的本质属性。……古典科学(指古典经济学——引者)赋予“经济人”若干基本特性,其中包括理性行为的利己主义等等。如果说古典科学中的“经济人”是一个抽象,那它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它的抽象性取决于系统,在系统之外,经济人才变成一个没有内容的抽象。④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也做了类似的评论,他说: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一个内在地自立的、自身封闭的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只有按照在固有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设定的目的和确定的手段,才能进行现实的实践。‘经济人’这个术语的产生既绝非偶然,也绝非纯属误解;它恰当而具体地表达了人在社会化了的生产世界中的直接必然行为。”⑤
经济人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最经典的表达。但是,斯密对经济人概念的规定,包含着下述两面性。一方面,作为《国富论》起点的利己心范畴实际上是从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的行为中得出的抽象。譬如,在《国富论》第二篇中说:每个人都有改良自身状况的持久愿望,而通过节俭积贮并增加资本是实现这一改良的最适当手段。另一方面,利己心又被看作是抽象的人性,被定义为“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⑥恩格斯曾这样总结了体现在古典经济学家身上的两面性,他说:“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⑦
斯密力图把利己心当作人类学的抽象概念来处理,是他的经济人思想中的庸俗成分。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赫希曼所指出的,“利己心”概念(self-interest)中的利益(interest)一词,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一开始并不限于指人的物质利益,在16世纪,这个词的意义“涵盖了人类的全部欲求”;16世纪以后,“利益一词的含义通过某种过程正在被狭义化为对物质经济利益的追求,这就是英语史和德语史的趋同点。”⑧斯密提出“利己心”概念,意味着赫希曼所指的上述词义改变过程的最终完成。
斯密经济人思想中的矛盾,反映在其具体经济理论、特别是分配论中。正如日本学者大河内所看到的,“在‘利己心’表现在经济生活中的时候,它不是‘经济人’一般,也不是‘交换人’一般,而是土地所有者、工商业者,也是‘贫穷劳动者’”。⑨不同阶级的“利己心”在其利益上是互相对立的。例如,斯密在讨论工资的形成时这样说:“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立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还说:“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提。”⑩这表明,斯密在具体分析中事实上放弃了抽象的经济人概念,转而通过具体的经济关系来规定人的动机和行为。
在我们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分别继承了斯密经济人概念中的不同侧面。马克思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概念中的合理成分,主张在特定经济关系下分析人的行为和目标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从某种先验的人性出发,推演出经济关系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曾指出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所含有的以下悖论:一方面,经济人是原子化的、非道德的个人,另一方面,经济人又不能采用强力和欺诈来实现个人利益。因此,表面上看来脱离了社会环境、原子式的经济人,事实上是以特定制度为前提而形成的概念,在这一制度下,他只能凭着绅士般的手段(即交易)来为自己谋取物质上的利益。格兰诺维特就人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以下论点:“行动者并非是外在于社会环境,如原子般行为和决策的……相反,他们进行有目的的行动的尝试,是嵌于具体的、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11)在我们看来,这些看法,和马克思的观点是近似的。
二、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
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始终只把经济人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具体总体中的人的行为的抽象(马克思代之以“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个提法),他们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只有在相应的生产关系得到阐明之后才能被规定。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人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反思下面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的叙述逻辑中,人,是在什么时候登场的?
在《资本论》第一章,我们首先遇到的不是人,而是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的商品。商品不是一般的物,而是某种生产关系的结晶。人是在第二章,即“交换过程”里出现的。马克思在那里这样写道:“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12)
在商品交换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商品所有者被互相尊崇为平等的私有者。在人的身份被这样规定之前,马克思已经在第一章分析了使商品生产者作为平等的所有者来对待的价值关系。随着叙述的进一步发展,人的身份又获得了进一步的规定。在引入劳动力商品后,“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13)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他所属阶级的代表,其行为和动机是由其一般存在条件,即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结构,马克思假定:(1)资本家的动机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2)积累是资本家特有的行为,积累的源泉仅仅来自剩余价值。他说: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4)
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15)
由此派生出马克思针对资本家的消费提出来的观点,“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16)
再来看看雇佣工人。由于积累只是资本的职能,与之对应,马克思假设雇佣工人没有储蓄。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解释,这一假设有如下合理性:第一,如果工人普遍进行储蓄,就会向资本家表明:工资普遍过高了,他们得到的工资超过了劳动力价值。也就是说,工人普遍储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例外情况。第二,工人在经济繁荣时期进行储蓄,在经济危机时期又会失去自己的存款。(对此还可以加上,工人在就业时期进行储蓄,失业时又会失去存款;在退休前进行储蓄,退休后又会失去存款)第三,工人储蓄的要求和雇佣劳动关系相矛盾,还体现在这一点上:工人的储蓄要变成资本,本身就要求劳动与资本相对立,“于是,在一个环节上被扬弃的对立又在另一个环节上重新建立起来。”工人的储蓄作为资本,增强了资本的力量,让资本从工人的储蓄中获取利润。“这样,工人只是加强了自己敌人的力量和他自己的依附地位。”(17)正是基于这些考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工人的储蓄抽象掉不予考虑。
马克思的上述假设在分析上有助于我们透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结构。由于有这种优点,卡莱茨基接过了马克思经济学里的这些假设,将其运用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一些追随卡莱茨基传统的现代后凯恩斯主义者,如明斯基,还在工人不储蓄的假设外,增添了资本家的利润不用于消费支出这一“勇敢的”“极端行为假设”,以论证卡莱茨基的投资决定利润的观点。(18)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马克思那里,人并不限于是其阶级的代表。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一般”的考察规定了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行为,而且还力图通过竞争即“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来做进一步的规定。倘若过度强调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同一性(如D.K.弗利(19)),就会走向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所称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s),按照这种概念,“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十分机械的:一旦我们知道了个体的社会阶级或其在劳动市场的位置,其行为中的其他一切都自动可知”。(20)在以下各节里,我们不仅要讨论竞争给资本家的动机和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变化,还会论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所带来的影响。
三、竞争和企业的赢利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和追逐利润这两个提法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在这一节,我们想发展一种观点,强调这两种提法在概念上的差异。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置盐定理(Okishio theorem)和技术选择的标准而发生的一场争论。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置盐信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力图通过数学模型证明,资本家在采纳了降低成本的新技术后,平均利润率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因此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是错误的。谢克则指出,置盐的模型忽略了固定资本,因而没有区分两种衡量赢利能力(profitability)的尺度,一个是利润边际(profit margin),另一个是利润率(rate of profit)。利润边际是利润和成本价格的比率,是一个流量对流量的比率;而利润率是利润和预付资本之比,是流量对存量的比率。如果考虑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利润边际就不同于利润率。竞争会强迫资本家采纳能带来较低成本价格的新生产方法。但在给定价格下,较低的成本价格会带来较高的利润边际。个别资本家采纳新技术后只是提高了过渡性的利润边际,而非提高了过渡性利润率(指新的平均利润率出现之前,个别资本因为采纳新技术而获得的利润率)。如果过渡性利润率比以前更低了,一旦新的生产方法占据统治地位,新的平均利润率也会降低。(21)
反对谢克的观点认为,由于资本家作为理性化经济人偏好更高的利润率,因此他们所能接受的新的生产方法,必须能提高过渡性利润率。在这种条件下,新的生产方法一旦被采纳,最终将在实际工资给定的条件下提高平均利润率。
谢克指出,在决定选择哪种技术的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标准,一个是竞争标准,另一个是最优化标准,只有前一个标准符合马克思的竞争概念,后一个标准体现了新古典完全竞争概念的影响。根据竞争标准,只要由新技术所降低的价格能够使企业支付包括利息在内的运行成本,企业就能采用这种新技术,并通过降低价格在市场上争夺销售份额,挤垮其他竞争者。
谢克的观点适用于解释使用大量固定资本的经济,并且和经济史上的下述事实相契合。在 19世纪末期,出现了铁路这样需要大规模固定资本的部门。对铁路部门的大量投资带来了生产能力的闲置,进而改变了竞争的形式。19世纪美国的铁路公司通过降价来增加运货业务,运输价格往往低得只能补偿运行成本,无法偿付固定资本的费用。(22)
谢克的观点表明,赢利能力在竞争中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追求利润边际和追求利润率有时是矛盾的。由此派生出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在一个普遍动机的基础上解释个别资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目标和行为呢?
在我们看来,可以利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所做的区别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马克思讨论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型。和剩余价值不同,利润是基于表面现象而形成的经验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23)也就是说,它被看作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并且表现为资本家账簿里的数目字。另一方面,马克思把剩余价值规定为剩余劳动的物化,剩余劳动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支出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劳动没有得到偿付。占有剩余价值意味着获得了一种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因此,这个概念所指涉的,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尽可能地扩大这种权力关系。
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不同意义做出以上界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斯密提出了他的生产性劳动和资本积累的学说,他用资本所能支配的生产性劳动来衡量资本的增殖程度。斯密对生产性劳动的基本定义是与资本直接交换的劳动。如马克思所说:这一定义,“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但是,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动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这一区分,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24)
受一定量资本推动的生产性劳动,为原资本带来一个“增加值”。(25)这个增加值分解为利润和地租,倘用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便形成资本积累。在斯密看来,生产性劳动是新增价值的源泉;在积累过程中,这一增加值又悉数用以推动或雇佣生产性劳动。在这里,斯密把生产性劳动当作资本价值增殖的衡量尺度来对待。(26)而且,他还把这样衡量的价值增殖和资本家的利润动机做了比较和区别,认为资本家并不能认识到哪种行业年产物的增加值为最大。(27)
斯密将资本悉数用于推动生产性劳动,丝毫没有考虑购买追加生产资料的问题,这很容易给人带来误解。不少人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解读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斯密这样做,是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严重短缺,劳动在当时是最便宜、最普遍的生产要素。这类解读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甚至似乎也见于马克思。(28)
在我们看来,斯密有关资本积累的上述理论有如下特点,第一,这个理论并不是一个解释再生产过程的实证性理论。事实上,斯密只是想借助于这个理论把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劳动宣布为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斯密才能在提出资本悉数用于推动劳动时,撇开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斯密在表达该理论时,还不断地与封建贵族用收入来购买仆役的非生产性劳动相对照,并对后一行为给予严厉的谴责,这也凸显出这一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点。
第二,通过这个理论,资本积累被把握为一种以价值为主体的增殖过程。西斯蒙第曾经十分精彩地表达了斯密所提出的这个思想,他写道:如果一个农场主多出来的小麦“作为他所雇佣的生产工人的食粮”,“那末,这部分小麦的价值就变成永久的、逐渐增多而不会再消耗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资本。”资本作为价值“永远是一种形而上的、非物质的东西,永远掌握在同一个农场主手里,只不过是外表形式不同罢了。”(29)资本作为运动中的、永不消失的价值,事实上是不断得到再生产的、凌驾于劳动之上的社会权力。
按照斯密的本意,资本所支配的劳动量在理论上衡量了资本的增殖程度;这与利润或利润率那样的经验尺度是不同的。这个乍看起来难以理解的规定,若站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上是不难理解的。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衡量了一种社会权力,斯密在此从权力的扩大再生产角度规定了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要以这个标准为参照,才是有意义的行为。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事实上把当事人的行为在特定社会存在中的客观意义与该行为的经验动机区分了开来,两者并不是必然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前者始终像参照系一样,对主观的经验动机起着校准的作用。换句话说,经验动机只是前者的表现形式,而行为的客观意义则可以成为理论上所假设的普遍动机。
总之,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规定为尽可能地获取剩余价值,和把这一目的规定为体现在一个货币额上的利润、或者会计账簿中的数目字,是决然不同的。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经验动机的理解上,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规定了这些当事人行为的客观意义。追求剩余价值,即谋求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作为一种处于特定社会存在中的行为的客观意义,被假设为普遍的动机,或支配行为的普遍准则,而实现某种水平的利润或利润率,则是外化的经验行为。如果采纳这样的诠释,对于谢克所碰到的问题,就可以求得如下解答:无论是追求更高的利润边际还是更高的利润率,都不违反获取剩余价值这个普遍的动机。而且,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即将看到的,在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行为的意义规定为获取剩余价值,使马克思得以把不确定性引入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模式的分析中去。
四、利润最大化假设和不确定性:来自演化经济学的批评
新古典经济学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动机,为此要求生产按照边际原理来进行。1939年,两位英国经济学家霍尔和希琪对38家企业进行了访问调查。调查不是随机选择的,而是由于管理卓有成效,才被选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第一,企业并不企图获得最大利润;第二,企业也不使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的原理,而是使用平均成本原则来确定价格,价格是在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固定成本之上再加上正常利润而形成的。此后,美国也有经济学家做了结果类似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促成了一场有关“边际主义的辩论”。(30)
在一篇发表于1953年的论文里,米尔顿·弗里德曼借用生物学类比对新古典利润最大化假设做了一个经典的辩护。如他所说:
不管明显地、直接地决定企业行为的因素是什么——习惯性的反应、随机性的机遇,或难于归类的一些东西——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一决定因素碰巧导致了与理性的、精明的收益最大化相吻合的行为,企业就会兴旺,并获得进一步扩张的资源;若非如此,企业就会失去资源,而且只有从外界引入新资源才能维持存在。这样一来,“自然选择”过程有助于证实这个假说(引者按:指最大化假设)——或者毋宁说在给定自然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接受该假说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即该假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生存的条件。(31)
这就是说,不管企业在实际中是否追求最大化,经济演化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过程,为最大化假设奠定了基础:那些生存下来的企业“仿佛”(as if)是在进行最大化。
理查德·纳尔逊和西德尼·温特这样的演化经济学家虽然也在经济分析中采纳了来自进化论的类比,但在他们看来,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包含着理论上的重大缺失。在发表于1964年的一篇论文里,温特率先对此展开了深入的分析。(32)他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温特指出,弗里德曼事实上把企业表现出来的行为看成是随机产生的,但这样一来,就没有理由假定一个碰巧实现最大化的企业在下一个时期仍会选择最大化;而且,这样的随机性还意味着,一个已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可能由于机缘巧合一变而成为利润最大化者。弗里德曼假定,演化过程会根据企业表现出来的行为对企业进行甄别,但他没有进一步对支配企业行为的规则进行分析。若要选择机制发生作用,就必须把基因型(支配行为的规则)对表现型(行为本身)区分开来,并强调前者对后者的约束作用。换句话说,要让选择生效,就必须有某种可继承的特质或基因,以便保证竞争所选择的最大化者的行为模式能存续一段时间。
第二,弗里德曼的上述类比体现了19世纪生物学的“最适者生存”原则,也就是说,进化过程总是会选择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优越或更有效率的个体。然而,20世纪理论生物学的新进展事实上已经颠覆了这个原则。温特在其1964年的论文里指出,考虑到频率依赖效应、新迁入者的特性以及规模报酬作为初始条件的影响等原因,那些表现出最大化特征的企业,可能不会被经济演化过程选择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
纳尔逊和温特后来一起发展了这样的思想(33):企业是在各种惯例或常规(routine)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这些惯例会获得相对的持久性,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基因。在他们看来,惯例和由这些惯例派生的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像生物学里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关系。除了将惯例类比于基因,纳尔逊和温特还采用了“搜寻”(searching)概念以反映企业惯例中的变化。“搜寻”概念是生物进化论中“变异”概念的对应物。在他们看来,企业事先会确定一个有利可图的界限,如果有充足的盈利,他们就试图维持现行的惯例,根本不去“搜寻”。纳尔逊和温特采纳了西蒙的“令人满意的”原则:行为者试图达到一个给定的“抱负水平”而不是进行最优化。如果企业赢利率掉到这个水平之下,企业就会在逆境的压力下被迫考虑其他选择。他们会投资于研发,努力开发新技术,以图恢复利润率。显然,他们的这些思想考虑到了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学习过程的重要性。
不确定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摧毁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进行最大化算计的可能性。除了凯恩斯、熊彼特、奈特等西方经济学家外,马克思也分析了不确定性问题,这一点似乎常常被人所忽略。在《资本论》第二卷的一处地方,马克思分析了价值运动的独立性和价值革命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影响,他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34)
在这里,用科西克的话说,资本积累表现为“一个由‘无意识主体’(价值)的运动构成的系统。……‘人们’戴着这个机构的官吏和代理人的面具出场,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和要素行动。”(35)科西克谈到了两种主体,一方面是无意识的主体,(36)即价值运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是持有自己的“先见和打算”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后者是“嵌”于前一运动中的,其“先见和打算”要受到前者的制约。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非但不能确知将获得多少剩余价值或利润,甚至不能预料固定资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因价值革命而贬值。若着眼于此,一切和利润最大化有关的算计,不啻是要把房屋建立在流沙之上。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把资本规定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在第二卷则把资本规定为“运动中的价值”。随着研究视角的这种变换,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规定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第二卷,借助于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这个概念,马克思又把不确定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有限理性引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模式的分析。(37)在第一卷,资本家“像害了相思病一样”贪恋剩余价值,这种表述初看起来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之间似乎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细究起来,这里有两点基本差别:第一,正如上一节里指出的,追求剩余价值指的是力图扩大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关系,这在经验上是不可以账本上的数目字来衡量的。第二,由于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受到价值革命的威胁,追求剩余价值的行为是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对个别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来说,最大化计算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
五、制度多样性与行为模式的多样性
近年来影响迅速扩大的实验经济学据称也提出了不利于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结论。“最后通牒游戏”实验(the ultimatum game)是其中著名的一例。最近,几位美国研究者对这个实验做了进一步的推广,他们在15个文化差异巨大的社会中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处于不同社会的被实验者表现出很大的行为差异,而这些差异可以从制度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得到解释。(38)例如,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奥和格瑙人(Au and Gnau people),常常提出一半以上的分享动议。这样的动议在接受实验的美国学生那里几乎从没出现过。而在巴拉圭的阿切人(Ache people)和印度尼西亚的拉马莱拉捕鲸者(Lamalera whale hunters)那里,他们的分享动议常常近于平均数。
为什么这些人群在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表现会如此不同?几位学者发现,印度尼西亚的拉马莱拉捕鲸者需要大规模地集体捕猎,习惯于平等地分配所得。巴拉圭的阿切人打猎和采集获得食物后,在成员中平均分配所得到的食物。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奥和格瑙人在提出较高的分享动议时,是在寻求提高他们的地位,而拒绝动议的人则是在拒绝接受一个较低的地位,尽管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根据这几位学者的意见,一般的结论是:第一,在不同的集体中,标准的行为也是不同的,上述集体中的人有的表现得比欧美学生更慷慨,有的则更吝啬。第二,在这些集体中,并未发现新古典经济人的行为具有典型性。第三,不同集体间的行为差异反映了不同集体中的人在谋生方式上的差异。(39)
上述结论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但这类实验及其结论却可能招致以下反批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概念就是个抽象,它撇掉了人的行为的其他社会特征,以利于经济分析。可是,参与上述实验的人却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实验参与者的行为中体现了某种公平价值观的影响,但这不足以驳倒经济人假设,因为这个假设涉及的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思想实验构造出来的抽象的人。
在我们看来,这些意见还关涉到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一抽象的适用范围问题。和古典经济人概念一样,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也是一个抽象(即“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利用这个抽象,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可是,这类抽象都有某种可以称作“结构主义”的特点,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构件,执行着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所要求的功能。而这样一来,在这类抽象的基础上似乎就难以解释,第一,该系统本身的重大制度性变革;第二,制度的多样性以及相应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多样性。
卢卡奇曾对第一个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在他眼中,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直是作为客体存在的。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工人一直听凭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摆布。这样的工人阶级只是自在的阶级。一旦工人阶级经过外部灌输获得了阶级意识,将拒绝这样的客体地位,一变而成为历史的主体,起来结束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统治。(40)在我们看来,卢卡奇在方法论上已经察觉到把人规定为经济关系的承担者所包含的局限性,并力图将实践的主体性又重新赋予工人阶级。最近,赵磊教授曾在一篇短文里探讨了马克思的人性观,他也提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并认为马克思人性观的本质是强调实践。他指出,第一,在马克思那里,人性是不能先于社会存在而给定的,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可以概括为“存在决定本质”。与之相对立,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则属于“本质决定存在”的本质主义观点。第二,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存在不仅是指生产的社会关系,而且最终还原为实践。“从实践的角度来把握人性,才是马克思‘人性论’的真谛。”他还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就此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性归结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1)
赵磊教授在这篇短文里概括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在方法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看来,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规定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并没有涵盖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部本质特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决定论”的一面,即制度的一般特征决定了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人性归结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人性的这一维度推动着制度本身的改变。可以推想,从这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中才可能产生出演化经济学所注重的“新事象”,即人的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和制度的多样性。在分析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和这一制度的多样性时,也许有必要超越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样的视角,在对人的行为模式的解释中接纳来自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
在《资本论》序言里,马克思曾明确地表示,他所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对他而言,工业上先进的国家向落后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意见意味着,他在当时还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问题提上分析的议程,更谈不上考察制度多样性与人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42)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阿尔贝尔、多尔、拉让尼克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推进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值得国内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和借鉴的。在他们看来,20世纪的资本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另一方面是以德、日等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用法国作者阿尔贝尔的话说:“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来。”“它们互相对峙,形成‘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43)在这两类资本主义模式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企业目标和行为模式,“一方是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建立在股东和短期利润优先之上;另一个是莱茵资本主义,优先考虑长期利益和首先把企业看作一种连接资本与劳动的共同体,是它的首要目标。”(44)
在阿尔贝尔之后,多尔、拉让尼克等人更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问题。(45)他们指出,在当代英美模式中,看重的是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价值,利润率即资本的收益率被资本所有者或其代理人看作衡量企业绩效的关键尺度。根据这个尺度,劳动被看作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只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项目,越是压榨工人,生产成本越低,企业的绩效也越高。他们发现,和英美企业比较,日本企业在股票市场的价值和资本收益率方面表现平平,但是在诸如储蓄、增长率、世界市场的份额和就业等其他指标上,日本企业做得更好。
多尔等人在理论上提倡用另一个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即企业的净增加值(net added value,或NAV),来代替利润率。NAV等于总销售额减去购买和折旧。或者说,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减去为生产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在他们看来,和利润核算相比,这个指标能更好地反映企业职工的价值创造。按照他们的计算,欧洲大陆企业的人均NAV(生产率)高于英美企业。另一方面,英国企业付给持股人的收益占NAV的比率,比欧陆企业要高三到四倍。(46)
通过对两种资本主义体制的细致比较,发现了不同体制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差异。多尔在他的著作里这样写道:“这本书并不符合新古典主义教科书的标准,在这类教科书里写道的‘人性’仿佛到处都是一样的,经济‘规律’是从到处都一样的人类共同的最大理性行为中总结出来的。我的这本书是关于活生生的人的,家庭、学校、烟草广告、电视剧、政治家的演说和工作友谊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个体,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特殊的国家共同体。而且,他们的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的结果也不同。”(47)
多尔批评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但他的评论也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借鉴。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多样性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这样的抽象是可以兼容的吗?是否为此需要发展一种更为具体的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理论?笔者本人还无力勾勒出这一新理论的具体轮廓,但我们相信,要制定出这样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和新兴的演化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以汲取他们所提供的理论营养。
近年来,国内关于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理论探讨,常常是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认同新古典经济人假设,往往导向业主私有制崇拜和MBO(管理者收购)这样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反对盲目私有化的学者则强调人的行为和动机的多样性与特定制度之间的联系。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经济人”假说。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益于我们在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48)
程恩富教授的观点,和英国学者多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后者在谈到中国国企改革时指出,自从1993年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展开有关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争论,这样的争论经常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以为真正的‘现代’商业公司的形式只有一种。”(49)在多尔以及拉让尼克等人的著作里,我们看到,基于抽象的人性而设想出来的制度安排,碰到了来自现实的制度多样性的挑战。经济当事人在行为、动机和信念上体现出来的差异,是与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和企业制度、甚至特定的文化相适应的。那种把私有化看作国企改革的万能钥匙的观点,既反映出对人性的褊狭理解,也没有扎根在坚实的经验土地上。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2006年初国内《商务周刊》杂志曾经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向丰田学习管理》,里面引用了日本米其林轮胎公司一位生产总监的观点。他发现,在中国推广丰田生产方式遭遇到困难,而这种困难来自于他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的美国式的个人主义:
以我些许的经验为依据,是否可以假设中国人在引进精益生产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困难?丰田本身在中国就曾有过一段艰难历程,中国的员工在接受丰田的价值观方面感到不太容易,中国的个体原则和日本的集体原则不容易匹配。……丰田有一种无私奉献的意识,但同时有一种将团队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的意识。而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人具有相同的理性主义。……我有时感觉,精益生产的内容不太容易被中国公司和人员接受,因为精益生产的精神不太容易复制到中国的公司。(50)
丰田生产方式的核心是企业对职工技能的长期投资,而这之所以可能,又取决于以终身雇佣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构成日本企业制度特色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为一线员工参与企业的组织学习提供了支持,企业员工也乐于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展开合作、贡献其技能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不少人忽视了这一点,以为丰田生产方式就是零库存(Just In Time)、看板生产等等。这样一来,他们所看到和模仿的,就只是表面的管理实践,而不是构成这一生产方式灵魂的制度基础。实际上,没有企业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整合,JIT和看板管理都是无法实施的。(51)《商务周刊》所引述的那位日本经理的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他在中国人身上所观察到的那种崇尚“个体原则”的“理性主义”,是传统集体主义价值式微的产物。在中国当前的学术语境中,要想驳倒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也许最后的困难是在这里。
注释:
①参见周新城《决不能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刘瑞《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②参见曾启贤《经济分析中的人》,载《经济研究》1989年第5期。笔者的观点也可视为后一种。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9页。
④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3-65页。
⑤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91-92页。
⑥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15页。
⑦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3-494页。
⑧赫希曼:《欲望与利益》,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7-32页。
⑨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6、113、90页等。
⑩《国富论》上卷,第60、90页。大河内尽管注意到斯密的这些观点,却不曾认识到斯密的经济人概念有两重性,力图为他的经济人思想的逻辑一致性辩护。
(11)M.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vol.91,no.3,pp.487-48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2-10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650、65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8、246页。
(18)H.P.Minsky,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4-147.
(19)D.K.弗利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那里,“经济当事人基本上是他的阶级的代表,……这些当事人的个别行为本身只有在反映了其阶级的社会地位时,才具有重要性。……把许多个别工人或资本家加总,以得到相应的阶级行为的问题几乎不会出现,因为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同一性是被严格地论证了的。”见D.K.Foley,The Strange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Agent,The New School Economic Review,2004,vol.1,no.1,p.3。
(20)M.Granovetter,op.cit.,pp.483-487.
(21)A.Shaikh,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Notes on Dobb's Theory of Cri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8,vol.2,pp.233-251; A.Shaikh,Marxian Competition versus Perfect Competition:Further Comments on the So-called Choice of Techniqu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vol.4,pp.75-83.
(22)参见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石磊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0-85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页;第26卷第Ⅰ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6页。
(25)《国富论》上卷,第25页。
(26)参见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8-69页。
(27)《国富论》上卷,第344页。
(28)马克思:“斯密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把生产资本的量同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量等同起来。但这同他所了解的大工业实际上还只处在萌芽状态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第269页。其实,马克思是从产业革命前夕资本有机构成很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指出了斯密错误之所以出现的社会经济根源。
(29)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6页。
(30)相关介绍和评论,参见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胡代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9页以下;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经济秩序》(三联书店,1998年)第188页以下。
(31)参见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载《弗里德曼文萃》,高榕、范恒山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年,第209-210页。译文根据弗里德曼原文有改动。
(32)Sidney G.Winter,Economic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Yale Economic Essays,1964,vol.4,pp.225-272.以下有关温特的内容还参考了G.M.Hodgson,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Cheltenham,UK:Edward Elgar,1999,Ch.8。另见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33)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本论》英文本(Penguin版)中,这里的“算计”一词被翻译为calculation。
(35)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第137页。
(36)“在G-W-G流通中,……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5页。
(37)在先前的著述中,我们曾着力指出,马克思借助于劳动价值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与目的、条件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参见孟捷《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38)参见Joe Henrich,Robert Boyd,Samuel Bowles,Ernst Fehr,and Herbert Gintis,Foundations of Human Reciprocity:Economic Experiments and Ethnographic Evidence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S.Bowles,Richard Edwards,Frank Roosevelt,Understanding Capitalism,Oxford:OUP 2004,Ch.2。
(39)引自S.Bowles,Richard Edwards,Frank Roosevelt,Understanding Capitalism,3[rd] edition.,Oxford:OUP 2004,pp.40-41。
(4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41)赵磊:《马克思对人性的把握最终归结为实践》,《光明日报》2006年7月8日。马克思的话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42)对这一点的讨论,参见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载《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
(43)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杨祖功、杨齐、海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 17页。
(44)阿尔贝尔,前揭书,第66页。
(45)可参见Ronald Dore,William Lazonick and Mary O'Sullivan,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15,no.iv,1999; William Lazonick,Ronald Dore,Henk W.De Jong,The Corporate Triangl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7;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46)William Lazonick et al.,The Corporate Triangle,pp.36-37,89f,95-96,98.
(47)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中文版序言,李岩、李晓桦译,第2页。
(48)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1期,第24、26页。这些观点,事实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就读道:“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64、265页。
(49)多尔:《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第3页。
(50)《向丰田学习管理》,《商务周刊》2006年1月20日,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ArticleShow.asp? ArticleID=1444。
(51)参见拉让尼克、奥苏丽文《公司治理与产业发展》第四章“组织学习与国际竞争——日本制造取胜美国的根本法宝”(黄一义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第88-89页。
标签:经济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企业利润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