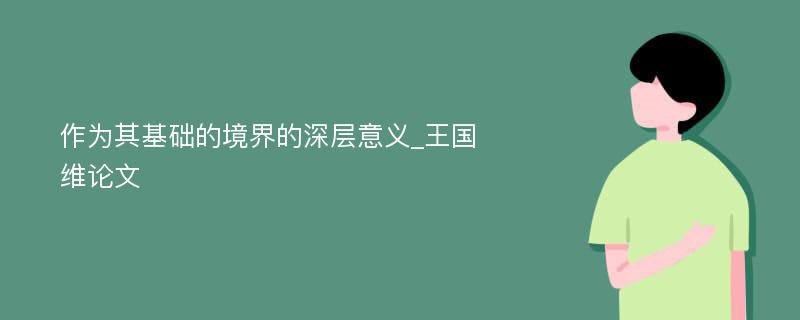
境界“为探其本”的深层意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界论文,意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3-0101-08
诚如陈寅恪所言,王国维从事文学批评与小说戏曲研究,主要基于“外来之概念与固有之材料”的“互相参证”法。所谓“外来之概念”,主要是来自西方古典哲学、文论以及心理学等领域中的重要理论概念及其运思方式;所谓“固有之材料”,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哲学、古代文论和诗词歌赋中的思想资源和名句范例。由此看来,这种“互相参证”法,可以说是一种跨文化参证法(transcultural cross referential approach)。如今,人们在解读王国维诗学思想的过程中,也照样离不开这种跨文化参证法。否则,就容易落入理论困惑、语义误读或逻辑强辩的陷阱之中。这种跨文化参证法的运用,主要是在特定语境中通过相关的概念追溯(conceptual retrospection)与二次反思(second reflection)予以展开的。本文所参证和释论的对象,主要是境界“为探其本”的深层意味及其目的性追求。
一
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境界说为圭臬。所著《人间词话》,开篇即论“境界”:“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① 显然,“境界”被奉为评价诗词艺术及其价值的最高标准。举凡诗词有了境界,其高妙的格调与精彩的名句就会随之而生。故此,王国维断言:“沧浪所谓兴趣,阮事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② 我们知道,严羽(沧浪)所言“兴趣”,盖指盛唐诸人在诗中“吟咏情性”之时,注重诗歌的兴发感动作用,讲求“言有尽而意无穷”,所用形象或所写情景具有如下特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镜中之象。”③ 这其中潜藏着以禅喻诗的用意,同时也包含着诗道妙悟或禅道妙悟的暗示,但终究是专论触景生情、委婉含蓄的诗歌创作手法(兴)与意趣盎然、情深旨远的诗歌艺术韵味(趣),同时也是对唐诗艺术特点的归纳和强调,以此来反衬和贬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④ 的文坛时弊。
至于王士祯(阮亭)所谓“神韵”,是在严羽提出“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⑤ 等言说的影响下,先后有所论及。如在《池北偶谈》里,王士祯借用孔文谷之说,认为“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上”。在进而讨论“清”、“远”与“清远兼之”的三种诗歌风格之后,认为三者“总其妙,在神韵矣”。⑥ 另在《渔洋诗话》中,王士祯列举了一连串律句,认为其妙在于“神韵天然不可凑泊”⑦。比较而言,基于“清远”诗风的“神韵”说,盖指景物诗所抒发或表达的一种情思意趣使人有所感悟与体会;基于“神韵天然”的“神韵”说,“因其能由外在之景物,唤起一种微妙超绝的精神上之感兴,而写诗的人却只提供了外在的景物,并不直接写出内心的感兴,于是便自然有一种含蕴不尽的情趣。如果从这种兴发感动的作用而言,则阮亭之所谓‘神韵’与沧浪之所谓‘兴趣’,实在颇有可以相通之处”⑧。不过,王士祯标举“神韵”,也是有感而发,虽有抑少陵而扬王孟之嫌,囿于清远冲淡而忽略飘逸豪放之偏,但终究看出当时文坛的主要弊端,试图以此来矫正明代前后七子复古风流于肤廓之弊与公安派失于浅率之病。
那么,与上述两种诗论相比,王国维为何认为自己提出的“境界”说就高出一筹呢?就是“为探其本”呢?对于这两个问题,国内学界的看法颇多,大体上可归为三点。其一,一般认为“兴趣”与“神韵”两说各有偏重,但不如“境界”一说具体而清楚。颇具代表性的说法是:“沧浪之所谓‘兴趣’,似偏重在感受作用本身之感发的活动;阮亭之所谓‘神韵’,似偏重在由感兴所引起的言外之情趣;至于静安之所谓‘境界’,则似偏重在引发之感受在作品中之具体呈现。沧浪与阮亭所见者较为空灵,静安先生所见者较为实质。……沧浪及阮亭所标举的,都只是对于这种感发作用模糊的体会,所以除了以极玄妙的禅家之妙悟为说外,仅能以一些缪悠恍惚的意象为喻,读者既对其真正之旨难以掌握,因此他们二人的诗说,遂都滋生了许多流弊;至于静安先生,则其所体悟者,不仅较之前二人更为真切质实,而且对其所标举之‘境界’,也有较明白而富于反省思考的诠释。”⑨ 其二,“境界”之所以为“本”,主要是因为其作为新的审美标准,要求“诗人在审美观照中客观重于主观,在艺术创作中再现重于表现,两者密不可分”⑩。具体说来,“境界”偏重于对某种客体之观照与“妙悟”所凝成的一幅生动而富意蕴的“图画”之再现,而诗人的情感意兴自在其中;“兴趣”则偏重于“妙悟”中某种“意兴”之一唱三叹的表现,其中也有“水月”、“镜像”般的“图画”;“神韵”则偏重于某种“兴会”之缥缈的表现,其中的“图画”只在若隐若现之间。简言之,后两者偏于主观表现,不讲“再现”,往往“境”、“象”未曾立牢,辄欲高骞飞举,出神入化,故易变成“虚响”,这才使王国维以“境界”取而代之。(11) 其三,大多认为“兴趣说”与“神韵说”不像“境界说”那样深刻而准确,因为后者抓住了文学中“情”与“景”这两个“最具普遍性”的“原质”,把“真情感”的审美表现与“真景物”的艺术形象视为“境界”的构成要素,并且进而将此两者“对立统一的关系”推演到“和谐化一、彼此不分”的程度。(12)
上述解释,有助于回答境界说“高出一筹”的问题,尚不能回答“为探其本”的问题。因为,情景作为文学的“二原质”,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属于常见的议题,“兴趣”、“神韵”与“境界”对此均有涉及和思考,只不过表述的方式和明晰的程度有别罢了。另外,王国维是大家公认的中西兼通的思想家与学者,其“境界”说的提出与论述,是中西诗学与美学思想资源会通创化的成果。如果仅限于用中国诗论传统来解释“境界”说,那显然是单向度的,不够全面的。譬如,王国维所用“境界”一词,较早见于1904年发表的《孔子的美育主义》一文,实则源自文德尔班《哲学史》转引席勒《美育书简》里的一段话。王国维据英译本将其译出:“谓审美之境界乃不关利害之境界,……审美之境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13) 在此,把“aesthetic state”译为“审美之境界”。其中所用“state”一词,是德文“Staat”一词的英译,原本表示“状态”、“形态”或“国家”(故有人将其译为“王国”)。王国维将其引申为“境界”,是借用了中国诗论和佛教所用的这一特殊语汇。此前,唐人王昌龄在《诗格》中谈到“意境”;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论及“境界”;王国维父亲王乃誉在《画衍》中论及创作,认为唯有“卓绝之行,好古之癖,乃能涉其境界,否是徒学无益也”(14)。不过,意义是人给的;对于特定概念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在王国维这里,“境界”一词就被赋予了诸多新的含义,成为一个独立的美学概念,成为衡量诗文作品和评论诗人作家之本——即基本的美学标准。(15)
那么,境界成为衡量诗文作品和评论诗人作家的基本美学标准,是否可以说此乃“为探其本”的要义所在呢?我想恐怕还不能如此等同。因为,严羽标举“兴趣”,王士祯推崇“神韵”,不仅仅是总括盛唐诗歌的杰出特点或清远冲淡诗风的要妙所在,而且也是将各自学说奉为衡量相关诗文作品与评价相关诗人作家的基本美学标准,只不过此两说涉及范围较窄,限于盛唐诗歌与清远诗风的讨论,而境界说涉及范围较宽,关乎历代诗词佳作的生成。更要紧的是,我们既然承认王国维的境界说兼容外来影响,是中西诗学或美学会通创化的结果,那么,以上阐述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立足于中国诗论传统的内部比较,并未真正追溯外来影响在创设“境界”一说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要知道,在王国维当时沉醉于“新学”(西学)的阶段,源自西方的“外来之概念”对其理论探索和思考的影响虽不能说举足轻重,但对理解“境界”何以“为探其本”的问题,委实是不可跳过的重要环节。
二
那么,这个重要环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王国维1907年发表的《〈人间词〉乙稿序》中可以见出端倪。其云:
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馀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16)
这段话包含数层意思。其一,以诗词为代表的文学有没有意境或境界,就要看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与形象能不能“观”;就审美主体而言,面对“能观”的意境,观赏者不仅要有审美和感知和敏悟能力,而且要有“超然于利害之外”的自由心境和无欲态度。所谓“‘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17)。其二,以“观我”为主导的诗词作品,其情思意趣的表现多于景色物态的描绘,或者说其“情语”胜过“景语”,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欧阳修等人。其三,以“观物”为主导的诗词作品,其景色物态的描绘多于情思意趣的表现,或者说其“景语”胜过“情语”,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秦少游等人。其四,物我虽然有别,但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两者是互动的,“观物”与“观我”是相互交错的,犹如“景语”与“情语”也是相互转换的。只不过在不同的诗词作品中,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此两者各有侧重,但绝不能有所偏废。其五,文学或诗词作品的好坏、格调的高低以及价值的多寡,均取决于意境或境界的有无及其深浅的程度。以上解释,虽然触及关键词“观”,但依然没有作出具体的说明。
那么,“观”到底所指何物?在《说文解字》中,释“观”为“谛视也”,意即细察、详审。所以,后有“常事曰视,非常曰观”之说。这里所谓的“观”,作为一种特定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视”或“看”,而是意味着仔细、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观察或审视,《易·系辞》中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就含此意。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在“观物”或“观我”时,是带有情感与灵思的“观”,这就近似于西方所谓的“凝神观照”,其中包含专注、凝思、品味、观赏等意。另外,宋儒邵雍曾经提出过多种观法,其中“以物观物”与“以我观物”影响最大。他认为“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18)。看来,“以物观物”,是从物性细察详审物性,这样基于客观的事物本性,就能搞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以我观物”,是从观者的情感好恶角度观察事物,这样基于主观的情感好恶,就难以明白事理、了解真相。邵雍在《伊川击壤集》里,也曾将观物之法用于作诗,但主要因循的是宋代道学或理学的基本思路。因此,我以为上述偏于笼统简约的说法,虽然会对王国维产生某种启发作用,但不能真正解释王国维所言的“观”之本意。于是,我们还得进行概念追溯,并在对相关概念的二次反思过程中,逐步揭示所用概念的实质性内涵。在这里,我们可从王国维的《文学小言》中找到某些线索。此文论及文学中二原质,即景与情,认为“景”“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情”乃“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诗人或作家若“心中洞然无物”,则“观物也深”,“体物也切”,故基于“激烈之情感,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19)。 其关键处在于引出“直观”这一外来概念。
何谓“直观”?王国维在1905年撰写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对此有过颇为详细的说明。即:
“Idea”为“观念”,“Intuition”之为“直观”,……夫“Intuition”者,谓吾心直觉五官之感觉,故听、嗅、尝、触,苟于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皆谓之“Intuition”,不独目之所观而已。“观念”亦然,观念者,谓直观之事物。其物既去,而其象留于心者,则但谓之直观,亦有未妥,然在原语亦有此病,不独自译语而已。“Intuition”之语源自拉丁之“in”及“tuitus”二语,“tuitus”者,观之意味也。盖观之作用于五官中为重要,故悉取由他官之知觉,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Idea”之语,源自希腊语之“Idea”及“Idein”,亦观之意也,以其源来自五官,故谓之观,以其所观之物既去而象尚存,故谓之念。或有谓之“想念”者,……其劣于观念也,审矣。(20)
由此看来,王国维所言的“观”,不仅与“直观”(Intuition)有关,而且与“观念”(Idea)相涉,此乃三者之间的共性使然。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源意义上讲,“直观”与“观念”均含有“观之意”,只不过“直观”“不独目之所观”,除了眼睛观察之外,还有听、嗅、尝、触等其他感觉和心思的参与,所以是“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的结果。至于“观念”,则属于“直观的事物”或直观的对象,也是来源于五官的观察或心智的感知活动。之所以称其为“观念”,那是因为“以其所观之物既去而象尚存”之故。这就是说,观念是直观物象之后存留在心目中的念想、意象或形象。王国维有时将“Idea”译为“实念”(21),有时也将其译为“理念”(22)。现在,也有学者将其译为“理式”或“相”(23)。
据此,所谓“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这一断语,就等于说诗词是否有意境,主要在于能够通过五官和心思的“直观”而发现其中所表现出的艺术“观念”或“理念”。另外,构成“境界”的“真景物、真情感”,也正是“能观”(能够直观)的对象,是通过真切生动的艺术描写,将“所观之物既去而象尚存”的“观念”,还原为眼前可观可赏的景象。因此,诗人词家要想取得“能观”的效果或感染力,就必须在创构和营造艺术“意境”或“境界”上多下功夫,在描写心意所感、耳目所触的“真景物、真情感”上多下功夫,以便使自己至少具备如下三种能力——“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24)。唯此,情景的“真”与“不真”、“隔”与“不隔”或“工”与“不工”之类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从跨文化参证法的角度来进行概念追溯,不难发现王国维所言的“能观”,同叔本华的直观观念说和康德的审美观念说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从王国维的两篇《自序》里,我们得知他本人前后四次研读“汗德(康德)之书”,从《纯理批判》(今译《纯粹理性批判》)入手,“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因“苦其不可解”,而“嗣读叔本华之书”;后假道叔本华《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今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接通康德哲学,第四次再读其书时,方感“窒碍更少”(25)。可见,王国维是深入研读过叔本华与康德的主要著作的,而且还专门撰写过相当数量的译介文章,其中篇幅较长、影响较大的有《叔本华与尼采》和《汗德之知识论》等。这里,我们不妨参照王国维对“观念”(Idea)的上述译释,先从叔本华的直观观念(理念)论说起,随后再联系康德的审美观念(理念)论予以旁证。
三
叔本华的直观观念论,是其意志哲学与美学思想的要核之一。所谓“直观”,是指一种相对于“抽象”的认识方式,用以直接审视、感知和把握与主体相关联的表象世界,旨在洞识其中蕴涵的“观念”形态与“意志”作用。所谓“观念”(Idea),是指表象世界里作为意志的直接而恰如其分的客观化结果。这类“观念”是人类认识的根本内容,是“唯一真正本质的东西”,是“世界各现象的真正内蕴”,是“不依赖一切关系”,“而在任何时候都以同等真实性而被认识的对象”(26)。对“观念”的直观认识,“就是艺术,就是天才的任务”。艺术复制着通过纯粹凝神观照得以感悟的永恒观念,即世界一切现象中本质而常住的要素。艺术的唯一源泉就是对观念的认识,其唯一目标就是传达这一认识。(27) 如此一来,“观念”就成为“艺术的对象”;直观观念就成为“天才的任务”;同时,天才的考察方法也就成为“艺术上唯一有效而有益的考察方法”(28)。这一切都是天才的本性与禀赋使然,因为天才具有“立足于纯粹直观地位的本领,能在直观中遗忘自己,能使原来服务于意志的认识摆脱这种劳役,能够完全抛开个人的利害、意欲和目的,使自己成为纯粹认识主体,成为明亮的世界之眼(the clear eye of the world)”(29)。此时,主体在直观中沉浸,在客体中自失,将一切个体性忘却,同时也将遵循充足理由律与只顾各种关系的那种认识束之高阁。此时,主体已然超出“时间之流”,摆脱了“生命意志”或大限意识的干扰,进入到物我两忘与自由体验的超然心境。因此之故,他无论是从牢狱里还是从王宫中去观看日落,其感受都是一样的。(30)
王国维深知,叔本华哲学的出发点在直观而不在概念,因为叔氏本人重直观而轻理性。王国维还发现,叔本华教育学说的核心也在直观,并“以直观为本”,贯穿到智育、美育和德育等各个领域。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4年)一文中,王国维指出,“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就是说,叔本华几乎将直观等同于真理。在谈及美术的直观问题时,叔本华列举了“建筑、雕刻、绘画、诗歌或音乐”等五种艺术。“诗歌”原本列在“绘画”之后、“音乐”之前,但王国维特意将“诗歌”凸显出来,并联系中国诗论传统中的“比兴”说,断言诗歌“价值全存于其能直观否”(31)。这一点很容易使人想起王国维对意境的界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无论怎么看,“其能直观”与“以其能观”,可谓同义无别;以此来判定诗歌的价值或意境,在王国维看来算是抓住了根本。总之,叔本华对直观的重视与喻说,对其特殊功能的详述与诠释,的确对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融贯在《人间词话》的境界本于直观一说里,同时也表露在其成果甚丰的文学评论或诗词创作中。譬如,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及其悲剧意识来解析《红楼梦》,同时还将喻示“直观”的“世界之眼”转换为“天眼”,借此倡导“以开天眼而观之”的鉴赏方法。(32) 在王国维自视甚高的词作中,也能看到包含“天眼”字样的诗句,譬如,“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33) 这足以表明王国维对天眼直观的妙用不仅情有独钟,而且运作自如。
叔本华的直观观念说,与康德的审美观念说关联密切,特别是在强调直观认识作用方面,两者可谓一脉相承。(34) 这一点对王国维的影响甚深,对境界论的发展推进作用甚大。在《判断力批判》里,康德认为审美观念与直观相关,所依据的是认识能力(想象力和知性)之间相互协和一致的单纯主观原则;天才也可以说是展示审美观念的能力。(35) 在康德心目中,(感性)直观属于一种使对象直观化或形象化的感觉能力,审美观念就涉及这种(感性)直观。从词源学上讲,“审美”一词本身就意味着“感性”、“感受”或“感觉”;“观念”一词本身也具有“观之意味”,是“物既去象尚存”而令人“想念”的东西。由“审美”与“观念”两词合成的“审美观念”,是想象力的直观或表象结果,也可以说是借助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感性形象。另外,“审美观念”可通过想象力的创造性和联想性功能,开拓出一个由诸多相关表象组成的“无限场域”,以此推动想象力去思索更多、更丰富、更深奥的东西。这样便使审美判断主体进入到一种类似于“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自由想象境界。再者,“审美观念”可以作为审美判断的对象,也可以作为天才展示的对象;前者经由感性直观而产生审美体验,后者通过想象创造而成就艺术作品。
尤为重要的是,“审美观念”关系到艺术作品的“精神”。德语“精神”(Geist)一词包括“生命”、“气息”、“心灵”或“才智”等义,在此主要是指艺术作品的精神性实质或内在生命力。康德将其视为一项原则或一种能力。(36) 作为一项原则,艺术“精神”能够振奋鼓舞心灵或激活心理机制,能使知性和想象力这两种脑力功能积极地运作起来,进入到一种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和不断强化的游戏状态。这种游戏状态,代表一种比喻性的自由运作活动。正是在此活动中,主体的审美体验得以持续和深化。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看,真正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应当是具有真情实感的艺术形象及其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另外,作为一种能力,艺术“精神”能够“把审美观念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指天才艺术家“展示审美观念”的聪明才智,也就是艺术家用来创造出另一个自然或人工艺术作品的“富有想象力的才能”。正是凭借这种才能,天才艺术家把不可见的理性观念,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审美观念,也就是把诸如天国之福、地狱之祸、永生、创世等理性观念予以感性化,把死亡、嫉妒、仇恨、爱情等抽象概念予以具体化,使其转化为直观可感的艺术形象或审美观念,成为在大自然里找不到与之相仿的东西。在康德看来,这种“精神”关系到艺术作品的优劣。一首文词漂亮或韵律工整的诗歌,一部叙述精到而有条理的故事,一幅色彩华丽且构图精巧的绘画,都因为缺乏“精神”内涵而失色不少。(37) 康德对“精神”的强调,自然使人联想起王国维对“境界”的推崇,因为这两种因素分别决定着作品艺术价值或格调的高低。
四
本文从“境界”决于“以其能观”一说入手,结合“固有之材料”和“外来之概念”,对“能观”与“直观”的认识特征及其思想来源进行了追溯与比较。那么,境界“为探其本”的要义到底何在呢?若参照叔本华的思路,“境界”可以说是本于直观或静观外在表象的“观念”,继而认识内在的“生命意志”这一本体。若追随康德的思路,“境界”可以说是本于感性直观“审美观念”,继而体认艺术的“精神”。但王国维绝非食洋不化或食古不化的庸才,而是立意创化、“凿空而道”的大家。故此,按照我们目前的理解,王氏所谓“境界”,应当是本于直观宇宙人生之真谛。这便是境界说“为探其本”的深层意味,也是其目的性追求。需要说明的是,这“直观”,是指诗性直觉与诗性灵思的融会贯通能力,是由感性、知性、想象或迁想妙得的灵思等质素综合而成的一种洞察敏悟能力;这“宇宙”,是指一定历史时空背景下的大千世界;这“人生”,是指容含七情六欲的人类生存状况;这“真谛”,是指真正的意义、真实的情景或内在的本质。当然,通过艺术境界来直观宇宙人生之真谛,不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与审美愉悦感,而是让人们在获得思想启迪的同时探求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那么,境界本于直观宇宙人生之真谛的说法,到底有何根据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佐证。其一,从王国维的天性与兴趣来看,他生来体弱且性情忧郁,对宇宙人生问题甚为关注且极其敏感。譬如,他在“自序”中坦言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38)。可见,王国维开始主动研究哲学的动力或动机,是出自思索和解决人生问题的内在需要与心理情结。于是,“时人间究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而《甲稿》词中‘人间’字凡十余见,故以名其词”(39)。这里所谓“人间”,是王国维自己启用的别号,其意表示人世间、人间世或人类生存活动的世界或场所,实际上也可看做“宇宙人生”的简要别称。王国维用此别号,不仅表示他所关注的对象,而且意指人类及其个人的生存状况,同时也暗含诗人作为人类代言人的特殊角色。在这段时间里,他专门探究人生哲学问题,静观人生的喜怒哀乐,并且有感而发,填词良多。据本人初步统计,他的《人间词》前后两集共使用“人间”一词多达37次。依照相关语境来看,“人间”意指甚广,有表示叹世或喻世的,如“人间哀乐,这般零碎,一样飘零”(《水龙吟·杨花》);“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谁道人间秋已尽,衰柳毵毵,尚弄鹅黄影。落日疏林光炯炯,不辞立尽西楼暝”(《蝶恋花》);等等。其中也有表示悦世或游世的,如“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踏莎行》);“绣衾初展,……不尽灯前欢语。人间岁岁似今宵,便胜却,貂蝉无数”(《鹊桥仙》);“天公倍放月婵娟,人间解与春游冶”(《踏莎行·元夕》);等等。其中也有表示疑世、警世或醒世的,如“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鹧鸪天》);“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一霎新欢千万种,人间今夜浑如梦”(《蝶恋花》);“蓦然深省,起踏中庭千个影。依旧人间,一梦钧天只惘然”;等等。值得指出的是,王国维在词作中所描写的“人间”,有时是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特殊)转化为广义或普世的东西(普遍)。总之,“人生哀乐”或“宇宙人生之问题”,确是王国维词作中反复吟诵的主题,同时也是其词话或哲学随笔中经常探索的对象。无论是在《人间词》、《人间词话》里,还是在《〈红楼梦〉评论》、《论近年之学术界》、《人间嗜好之研究》和《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文中,他对宇宙人生之本质的追索精神以及对宇宙人生之问题的忧患意识,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二,从王国维对哲学与诗歌的态度来看,宇宙人生问题是其深感彷徨和忧心的主因。王国维在遭受“可信而不能爱”、“可爱而不能信”的困惑与烦恼之时,曾游离往复于哲学与诗歌之间,并且发出过这样的叹谓:“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40) 因此之故,他在“由哲学而移于文学”时,曾毅然决然地漫步于“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41)。但实际上,他本人并未因此而摆脱萦绕于心的宇宙人生问题,而是在文学研究与诗词创作中兼顾诗歌与哲学的融合,借以缓解自己思想情感以及学术兴致所遇到的烦恼。因为,他深知诗歌与哲学,都与宇宙人生问题有着不解之缘。如他所言:“诗歌者,描写人生也。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诗人之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42) 至于哲学,王国维更是将宇宙人生问题视为其要务或天职。他以叔本华哲学为例,强调其“所以凌铄古今者,其渊源实存于此。彼此以天才之眼,观宇宙人生之事实……然其所以构成彼之伟大之哲学系统者,非此等经典及哲学,而人人耳中目中之宇宙人生即是也。”(43)
其三,从王国维将诗歌与哲学等同的立场来看,宇宙人生问题在本质意义上是这两者的共性所在。在这方面,王国维既受到来自中国老庄哲学与诗赋词曲的影响,也受到来自西方哲学与日本思想的影响。譬如,王国维本人译介过诸多西方思想家的名著,同时也翻译过一些日本思想家的作品,这其中就包括桑木《哲学概论》的部分章节,有些段落是专论诗歌与哲学之异同的。如:“抑诗歌者,就其广义言之,乃人就天地自然之风景,或人事之曲折波澜等,而以美妙之文(散文或从音律),叙述其所感想、经验者也。通常分为三种:叙事、抒情、剧诗,人人之所知也。其中特如抒情诗,以述作者之感慨为主,一路直观,蓦然吐露诗人之对人生世界之观念。其思想之幽玄深邃,尤与大哲人只所辛苦思索者符合。……故天地大宇宙,哲学者小宇宙也。……哲学者于此,可谓与大诗人。其揆一也。”(44) 王国维翻译此段文字,显然欣赏其中所陈的观点立场,认为诗歌艺术与人生哲学无异。其后,于《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中,他在上述论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如文学中之诗歌一门,尤与哲学有同一之性质;其所欲解释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不过其解释之方法,一直观的,一思考的;一顿悟的,一合理的耳。”(45)
其四,从王国维对“诗人之境界”的相关论述来看,宇宙人生问题及其真谛似乎只有诗人才能洞透、表达和传布。如他所言:“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46) 这一方面表明诗人是天才,是人类的代言人,是敏悟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另一方面也表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在诗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王国维为此举例说,“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之类的诗句词行,就包含着诗人浓厚的“忧生”意识与发人深省的追思;而“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与“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之类的具体写照,则表达的是诗人深切的“忧世”意识与不平则鸣的叹喟。(47) 另外,王国维还从创作的角度,对诗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48) 这实际上是在介绍如何感悟和创造“诗人之境界”的方法与经验。
从以上所述可以推断,“为探其本”的境界说,其深层意味并非囿于其作为“根本性的诗词艺术法则”或“衡量诗文作品与评论诗人作家的基本美学标准”,而是在于直观宇宙人生之真谛。至于境界说的目的性追求,一方面是指诗人基于真景物真情感的诗性直观和灵思,能洞察宇宙人生之真谛,能以真切生动的方式将其表现在形象化的艺术境界之中;另一方面是指这种艺术境界能以不隔能观的方式,引发鉴赏者的共鸣、反思与觉解,进而使其养成一种良好的审美趣味,找到一条应对人生哀乐的可能途径。据此,我们也可以将王国维的诗学视为宇宙人生论诗学,或者干脆简称为人生论诗学。因为,从王国维所思所感所写的内容来看,“宇宙人生”的落脚点主要是在“人生”之上,也就是把“人生”放在“宇宙”的多维时空背景下及其历史文化意识中予以凝照追思了。
注释: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41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② 王国维:《人间词话》,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43页。
③④⑤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五),第26、2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⑥⑦⑧⑨ 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287、288、288—289、29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⑩(11)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2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 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第154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13)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156页。
(14)(15) 转引自陈鸿祥:《王国维传》,第146、147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16) 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76页。
(17)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4页。
(18) 邵雍:《皇极经世全书解·观物篇》,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第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 王国维:《文学小言》,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25—26页。
(20)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0页。
(21) 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21页。
(22) 王国维:《汗德之知识论》,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07页。
(23)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4)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389页。
(25) 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1905年),“自序”(1907年),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69、471页。
(26)(27)(28) Arthur Schopenhauer,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36,p.184.另参阅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58、258、259页。
(29) Arthur Schopenhauer,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36,pp.185—186.为了呈现这一直观认识过程,叔本华还特以欣赏自然美景为例详加说明。Cf.Arthur Schopenhauer,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38,pp.197—198.另参阅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75—276页。
(30) Ibid.,38,pp.196—197.另参阅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74—275页。
(31) 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24—330页。
(32)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5页。
(33) 王国维:《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98页。
(34) 事实上,叔本华本人尽管对康德哲学的含混性、晦涩性、不确定性及其喜好玩弄概念游戏的论述方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却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以康德的思路为前提或出发点的。他在《康德哲学批判》这一附录中坦言:“我的思路尽管在内容上是如此不同于康德的思路,但显然是在康德思路的深刻影响之下,必然以康德思路为前提,并由此出发的;并且我还要坦白地承认:在我自己论述中的最佳部分,仅次于这直观世界的印象,这一切我都要感谢康德的著作所给的印象,也要感谢印度教神圣典籍和柏拉图对话集所给的印象。”参阅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67页。
(35) Immaneul Kant,Critique of Judgment(trans.Werner S.Pluhar,Illinois:Hackett Publishing Co.,1987),section 57,342—244,pp.214—217.
(36)(37) Immaneul Kant,Critique of Judgment,section 49,313—314,pp.181—183.Immaneul Kant,Critique of the Powers of Judgment(trans.Paul Guy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section 49,p.192,p.181.另参阅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58页,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8) 王国维:“自序”(一),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71页。
(39) 罗振常:《〈人间词甲稿序〉跋》,据墨迹,转引自陈鸿祥;《王国维传》,第138页。
(40) 王国维:“自序”(二),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73页。
(41) 王国维:《青玉案》,参阅《人间词·苕华词》,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98—199页。
(42)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30—31页。
(43) 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25页。
(44) 桑木:《哲学概论》,第2章第6节,见佛雏:《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第11—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5)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72页。
(46) 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第十六则,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73页。
(47)(48)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六十则,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47、155页。
标签:王国维论文; 叔本华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康德论文; 蝶恋花论文; 审美观论文; 人间词话论文; 哲学家论文; 诗歌论文; 意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