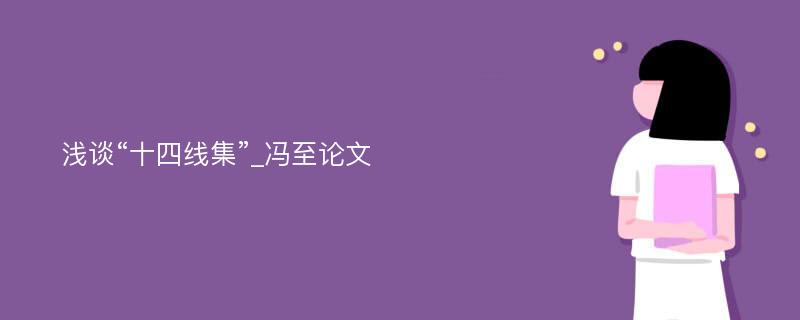
简论《十四行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行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26.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1999)03-0040-(06)
以《北游》为代表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诗作,是冯至从伤感的浪漫主义诗人向现代主义的沉思者的过渡阶段。由《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十四行集》,这一条思想和艺术循序发展的轨迹是清晰可见的,这是量变的积累,而不是突变的过程。要准确地理解和评价《十四行集》,就有必要联系这些“过渡”时期的作品,从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超越。
1928年前后一年的北游经历对冯至来说,是他走上社会伊始学习人生哲学的第一课,他经历了幻灭的悲哀,也体验了觉醒的沉重。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地向亲密的朋友诉说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任什么也不能享受,任什么也不能把住,任什么也不能归依,任什么生活都没有,归终是什么也不是。”孤独、焦虑、虚无、困惑等种种生存困境横亘在他面前,使他感到异乎寻常的苦闷、烦恼。但可贵的是,他从不自暴自弃,而且常常进行反思,让理性来控制情感。他认识到:“前边固然是没有光明,能够说是完全的黑暗吗?”“我想,一切事不能躲避,该担的就得担,只要我的‘生命力’未死”。这样就初步拟定了方向:“如果还打算生存呢,恐怕非‘重新打鼓另开张’不可了。”(注:以上引文均见《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生存”、“把住”、 “担当”等存在主义哲学常用语汇的出现,预示了后来思想的发展。
在《北游》这首长诗中,诗人写到了《死室回忆》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把自己关在房中”,面对着这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鲁迅语)的相片发闷,对自身的存在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在《死室回忆》的作者启示下无情地拷问自己:
我望着宁静的江水,拊胸自问:
我生命的火焰可曾有几次烧焚?
在几次烧焚里,
可曾有一次烧遍了全身?
二十年中可有过真正的欢欣?
可经过一次深沉的苦闷?
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
认定了一个方针?
可真正地读过一本书?
可真正地望过一次日月星辰?
欺骗自己,我可曾真正地认识
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于是他回首前瞻:“回头看是一片荒原,/荒原里可曾开过一朵花,涌过一次泉?”“前面看是嵯峨的高山,/可有一条狭径让我走,一座岩石供我攀?”“匆匆地来,促促地去,什么也不能把定,/匆匆地来,促促地去,匆促的人生”!“我到底要往哪里走去?”……这种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索,在他十年后创作的《十四行集》中得到更深刻的延续,而且更发展为对整个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注了。然而,处于《北游》时期的诗人还只是停留在个人命运的沉思与反省之中,他决心抛弃空虚的梦幻,“不要总是呆呆地望着远方,/不要只是呆呆地望着远方空想!”他要“埋葬”自己的过去,企盼一次“涅槃”式的新生。在《北游》的几行诗中,他这样宣示:
我不能这样长久地睡死,
我要打开这阴暗的坟墓,
我不能长此忍受着这里的阴沉。
诗人在1933年写的《无眠的夜半》达到了这种认识的最高峰:
在这疲倦无眠的夜半,
总像远方正有个匆忙的使者,
不分昼夜地赶他的行程。
等到明天的清早刚一朦胧,
他便跑到我的门前,
指着我的姓名呼唤。
他催我快快地起来,
从这张整夜无眠的空床;
他说,我现在有千山万水须行!
我不自主地跟随他走上征途,
永离了这无限的深夜,
像秋蝉把它的皮壳脱开。
歌德“蜕变论”的思想在这里已露端倪。诗里抒写他在先行者的呼唤指引下,“永离了这无限的深夜”,迎着朦胧的曙光去跋涉千山万水的征程,追求远大的理想去了。这的确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蜕变。早期的“抒情时代”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经过整整十年的体验、积淀、反思,整整十年的学习、工作、忍耐,诗人才可能从理性和哲学的高度去洞察社会人生,把握住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思考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去获得生命的圆满与充实,战胜人类生存的困境和缺陷。
从30年代初开始,诗人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直到1941年,他才以生命沉思者的姿态复出诗坛,出版了一部被誉为“4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一座奇峰”的《十四行集》。1930年到1935年,他在德国学习文学、哲学和艺术史,“听雅斯丕斯讲存在主义哲学,读基尔克郭尔和尼采的著作,欣赏凡诃和高甘的绘画,沉溺在以里尔克为代表的现代派的诗歌里”。(注:冯至:《自传》。)这些养分奠定了他创作《十四行集》的哲学和诗学基础,使他由一个感伤的浪漫主义诗人蜕变为沉思生命的诗化哲人。
在《十四行集》的序言中,冯至谈到了他这部诗集的创作动因和之所以采用十四行体的考虑。他说:“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都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于是,萌发了创作的冲动。“这开端是偶然的,但是自己的内心里渐渐感到一个要求: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的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正如李广田在论《十四行集》时所说的,‘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正宜于表现我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而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这些自述,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这部诗集的思想和艺术,提供了一把钥匙。
翻开《十四行集》,首先吸引我们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和现象中所发掘的哲理和诗情。
在第26首中,诗人写道: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
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
因为是平常的生活和现象,我们司空见惯了,感觉麻木了,就常忽略它们深处所隐藏着的启示意义,更谈不上对它们有什么“新的发现”了。第6首诗写在原野里看到村童或农妇“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 是太普通不过的一件事了,而诗人却由此想到许许多多卑微的平民百姓的命运:他们的“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与“人生”、“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他们活在那样“一个绝望的宇宙”里,命中注定“好像从古来就一任眼泪不住地流”。从这平静的不动声色的叙写中,读者深悟到充满敌意的黑暗世道对生命的摧残与压抑。第5 首写“桥”和“窗”,也是人们平常习见的事物,但诗人却发掘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道理。他以世界名城威尼斯的见闻为基础,揭示了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水城之所以紧密地结成一个“集体”的秘密:“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水上的桥;当你向我笑一笑,便像是对面岛上忽然开了一扇楼窗”。“桥”,在这里成了岛与岛交往的纽带,而“窗”,却是人与人传递友情的媒介。诗人说威尼斯“是个人世的象征”。让个个岛屿“都结成朋友”,就要多造些“桥”,多开些“窗”。推而广之,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如果都有“桥”和“窗”来沟通连接,那么,相互间的隔绝与疏离就不存在了。第23首写的是“几只初生的小狗”,它们自降生以来一直遭遇着“潮湿阴郁”,但一旦它们“第一次领受光和暖”后,这经验“会融入将来的吠声”,“在深夜吠出光明”。这些卑微的动物尚且如此,那么,作为“灵长”的我们人类,不也曾走出过“潮湿阴郁”、领受过“光和暖”吗?“在深夜”时刻又该如何呢?……这些日常生活平常现象,经过诗人的洞察和沉思,“发现”了如此之多的深意,给读者以意外的启迪。在以往创作的《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它》里,诗人偏重于从个人的遭遇来感受社会和人生,而现在,随着知识和人生阅历的丰富,生活体验的深化,我们感到诗人的诗思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内心天地,开始深切地关注现实社会,思考人生真谛了。他在第22首中,深挚而迫切地呼唤:“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十四行集》所表现的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彼此生发的整体,其基本主题可以用诗人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连与不断变化的关系。”(注:《外来的养分》、《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这里没有什么玄奥哲学的阐释,流转在诗里行间的, 是诗人对社会人生深刻的心灵体验和感性思索。
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
在我们梦里是这般真切,
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
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
可是融合了许多的生命,
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
谁能把自己的生命把定
对着这茫茫如水的夜色,
谁能让他的语声和面容
只在些亲密的梦里萦絗?
我们不知已经有多少回
被映在一个辽远的天空,
给船夫或沙漠里的行人
添了些新鲜的梦的养分。
——《十四行集》第20首
这里写人与人“在生命深处”的关连。诗人告诉我们,别人的面容和语声,“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当他们出现在我们梦里时都是真切的,就如同自己的生命的分裂一般。而我们自己的生命,不也是“许多生命”的融合、“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从出生、成长到知识的吸取、事业的成就,哪一样能离开别人生命的给予和关爱?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让自己的语声和面容,“只在些亲密的梦里萦絗”?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给予和关爱投射到更广大的人群中去?
诗集的第16首则主要表达人与自然的关连与呼应: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站立山巅,“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甚至于“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也和“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产生关连(指留下一些记忆和印痕),真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交融、契合,休戚相关,患难与共。
“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连”的主题,除了在上述诗作中得到比较集中完整的表现之外,在第5、7、15、17首中,也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触及或深化了这一体验与感受。如第17首,从“原野的路”曾留下“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联想到“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曾经被许多相识或陌生的人踏出过“几条宛转的小路”,要珍惜和纪念“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因为他们曾和自己的生命的某段经历“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注:冯至:《一个消逝的山村》,收入散文集《山水》。)
至于那些“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的不断变化的关系”的作品,感性的生活体验已寓于理性的思辨之中,但理性中仍然蕴蓄着深厚的感情。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冯至所受雅斯贝尔斯、里尔克、歌德等人的哲学思想的熏陶和影响。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对存在本质的思索和对生存困境的体验,里尔克的生命和死亡观,歌德的蜕变论,都经常或隐或现地出现在诗作中,并得到形象的表现。诗集的第一首唱出了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对生和死的深沉思索是整部《十四行集》的一个庄重而严肃的主题。在这首诗里,诗人要“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的奇迹是什么呢?“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只是一种暗示、一种意象的曲折呈现,它的实在含意是指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或者巨大的灾难、痛苦和牺牲(注意“彗星”、“狂风”这两个关键词的性质)。只有这样,才需要我们用“整个生命”来承受,就像小昆虫“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而死亡一样。坦然地面对“那些意想不到的”死亡、痛苦和牺牲,才能在“这一瞬间”凸现生命的壮丽辉煌。在这里,即使是死亡,也丝毫不带悲剧意味,而是一种自觉的奉献精神。因为,“死只是一个走向更高的生命的过程。由于死而得到新生,抛却过去而展开将来”。(注:《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这样,诗人的诗思就很自然地伸入了歌德的蜕变论。对此,诗人有过一段自述:“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我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要,所以我每逢读到歌德反映蜕变论思想的作品,无论是名篇巨著或者是短小的诗句,都颇有同感。 ”(注:《论歌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对“蜕变论思想”的感悟与思索,在上述第一首中已见端倪。蜜蜂经过交媾而结束生命,是为了延续后代;为抵御危险而献身,是为了保卫同类的生存,它们虽然死了,但它们的生命却在后代或同类身上得到了永生。在第二首诗里,诗人“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要求,表达得更具体、真挚: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娥,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通过“蜕变”来获得新生,对诗人而言,既是“迫切的需要”,也是自觉的“安排”。让旧的东西从身上“脱落”,毫无留恋地“化作尘埃”,像树把枯黄的树叶和凋残的花朵都交付给秋风,让树身伸入严冬去经受磨炼,有如“蜕化的蝉娥”,把残壳弃于泥土。对“未来的死亡”,也作好了自觉的“安排”:宁静从容,像“一段歌曲”。当歌声消逝后,留下“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能够如此从容优雅死去的人,是有福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获得了永生。因为,“那些临死时还能保持优越姿态的人,有如稽叔夜最后一曲〈广陵散〉,我们只有景仰赞叹。”(注:冯至:《忘形》,《冯至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在呈献给歌德的第13首诗中,诗人对“蜕变论”作了具体而形象的概括:
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
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
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
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
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
它传达出生命转化的信息。蜕变是痛苦的,一如飞蛾投向火焰,蛇脱去旧皮,但却是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这正如诗人所说:“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要用前一个阶段痛苦的死亡换取后一阶段愉快的新生。”(注:《论歌德·代序》。)
《十四行集》是一部“沉思的诗”(李广田语),是诗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语的境况里”(注:《论歌德·代序》。)对社会人生自然的深沉体验与感悟。他宁静从容地面对生命的有限与无常、刹那和永恒、生与死、存在与命运等庄重严肃的问题,并力图给予诗性的阐释,开辟了一个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生命、哲学的诗歌领域。在进入这一领域中,他自己的思想品德也得到净化、升华,在纷乱的人世中,始终维系了向上的人生信念,从而在诗中展示出阔大的心胸与旷远的文化视野,洋溢着深沉的哲理意蕴。
从《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到《十四行集》,冯至走过了漫长的人生和诗歌求索之路,无论是思想或艺术,都可以明显地区分为两个时期。写《昨日之歌》时,冯至正迷醉于郭沫若的《女神》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读《女神》使他的“思想和感情得到很大的解放”(注:冯至:《我在四中学习的时候》,《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而《少年维特之烦恼》却领引他“接近了狂飙突进过后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注:《外来的养分》、《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上大学后,由于学德语,有机会读到德国浪漫派的作品, 其中尤其是涂上一层淡淡的神秘色彩的叙事谣曲,给他后来的诗作以不少熏陶和影响。与此同时,王尔德的《沙乐美》及表现世纪末独特情调的英国画家毕亚兹莱的黑白线条画,也在潜移默化中沁入他的审美意识,他爱上了在“空虚里寻求,在幻影里造楼阁”。(注:冯至致杨晦信,《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他早期的诗作可以说是在以独特的抒情方式,“用语言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注:鲁迅:《挑色的云·序》。)这时期的叙事诗,为几个封建重轭下的爱情悲剧或人性沉沦的故事唱出了一支支凄怆的挽歌,萦绕在诗里行间的依然是浓重的浪漫气息的情调。《北游》虽说增添了不少现实主义精神,但总的来看,“还是用了浪漫主义的笔,蘸着世纪末的墨汁,抒发了个人在这个不东不西、畸形怪状的大城市里的种种感触”(注:《外来的养分》、《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以伤感的抒情来宣泄忧愤交并的情怀。
十年过去了。从《北游》到《十四行集》,中间相隔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他在学习——向歌德、里尔克等思想家、文学家学习,吸取他们的哲学和诗歌精华;也向生活学习——回国后的万里转徙,丰富了他的社会人生阅历。他也在思索。更学会了沉默和忍耐。随之而来的,是诗歌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他一向认为诗是情感的抒发,在读了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后才悟到“诗是经验”,这经验“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苦恼一般。”(注: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因此,他改变了一任情感放纵的习惯,学会了情感的节制、收敛,把情感隐藏在深沉的理性哲思里。歌德揭示艺术辩证法的名言:“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也给他以莫大的启示,使他更注重诗歌形式的规范与约束,为飘忽不定的思想情感“定形”,并从平面的情感宣泄过渡到具象的呈现,正像他在论里尔克时所说:“他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注: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
罗曼·罗兰对荷马艺术的要素曾作过如此的概括:“简洁、单纯、明白”,把它移来评价《十四行集》也是适合的,不算是溢美之词。如果说《昨日之歌》等早期诗作的总体风格是幽婉柔美,那么《十四行集》则可以概括为沉郁素雅。它语言朴实无华,却富有力度与弹性;它诗思深邃,却不玄奥晦涩;它“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里寻求哲理和智慧”(注:《外来的养分》、《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却不在云端构筑幻想阁楼。不少《十四行集》的研究者对其作了很深奥的解读,从现代主义艺术、存在主义哲学等角度发掘出许多“精妙”的诗意,把读者引向一个个迷宫。但这恐怕不一定符合诗人当时当地的思想及创作实际。
《十四行集》的思想内容是平凡的,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来自自然界和日常生活。它说明:“诗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现象中,却不一定是在血与火里,泪与海里,或是爱与死亡里。那在平凡中发现了最深的东西的,是最好的诗人。”(注:李广田:《沉思的诗》,《诗的艺术》,开明书店1943年。)
《十四行集》的艺术又是美的。美在它自然、质朴,不可雕琢。这点,可借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明:“真实的造化之工却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棵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包含无限的永恒的美。”(注:《论歌德·代序》。)
最后,让我们引证郑敏先生的一段话来作为对《十四行集》的总的评价:“这是一部从形式到内容反应了中国新诗与世界诗潮的交流和渗透,是四十年代新诗现代化的一座奇峰,它溶汇了古典诗人杜甫的情怀,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歌德的高度哲理和奥地利早期现代主义诗人里尔克的沉思和敏感。这本诗至今还没有被广大的读者所完全认识,原因是在冯至和广大的读者之间还存在着文化沟。随着我们教育文化的普及和提高,人们会理解它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中国新诗走向世界的一个路标的意义。”(注:《回顾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展,并谈当前先锋派新诗创作》。)
收稿日期:1999-04-06
标签:冯至论文; 外国文学评论论文; 十四行集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诗歌论文; 歌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