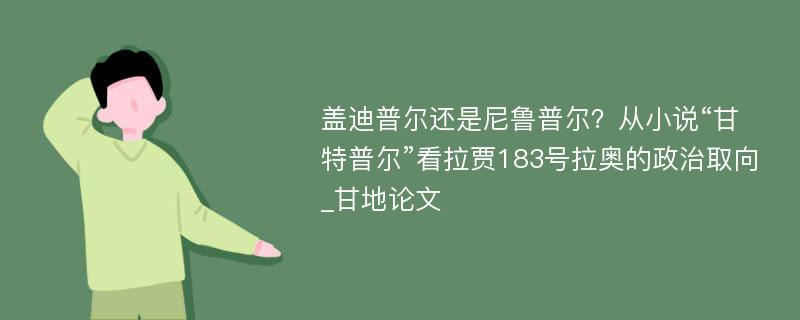
甘地浦尔还是尼赫鲁浦尔?——从小说《根特浦尔》看拉贾#183;拉奥的政治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地论文,尼赫鲁论文,取向论文,政治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贾·拉奥(Raja Rao,1909—)是印度当代最杰出的英语小说家之一,他的第一部英语小说《根特浦尔》1934年刚面世即声名鹊起,被英国著名的反殖民主义自由作家E.M.福斯特誉为“近年印度最好的小说”。《根特浦尔》从主题、写作技法到语言风格在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这部反映甘地领导下的不合作运动的政治小说,其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尚处该运动的高峰时期。虽然彼时作者远在法国,却能潜渊洞虚,对当时印度的非暴力运动以及种姓制度、殖民地经济和民族文化心理等作出及时的剖析和冷静的反思。
自小说发表以来,众多研究者认为《根特浦尔》就是“对甘地的赞美诗”①,是“甘地村的画像”②,有人更将根特浦尔直接称为“甘地浦尔”(“浦尔”是村庄的意思)。从内容看,这部小说以甘地领导的两次不合作运动为写作背景,主人公穆勒蒂被称为“咱们村的圣雄”,“圣雄胜利”的口号在文中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将根特浦尔理解为甘地浦尔是言之有据的。只是这一阐释带来了新的问题——为何拉奥要安排穆勒蒂离开全身心信奉甘地主义的村民,最终转向虽然也是甘地主义者,却和甘地有明显不同的尼赫鲁呢?拉奥是如何看待甘地和尼赫鲁的呢?笔者认为这是理解《根特浦尔》的一个关键点。正是由于评论者忽视了对《根特浦尔》中尼赫鲁的形象分析和对甘地与尼赫鲁两位领导人的异同及传承关系的梳理,所以近年来对这部小说价值的质疑也出现了。在2003年8月的国际期刊《印度文学》上,有学者发文讨伐《根特浦尔》,认为这部小说“字里行间明明白白地表露着原教旨主义以及对甘地主义的扭曲,令人诧异的是小说如何逃过了(评论家的)法眼,免于这些指责。这部小说顶多只是甘地主义的拙劣仿制品,它断然宣称甘地主义在印度是行不通的。”③ 为此,下文将从作品出发,逐步分析1934年以前拉奥的政治取向。
一
小说的主要场景是在南印度群山环抱中的根特浦尔。根特浦尔可以说是当时南印度村落的缩影——二十四所房子是高等种姓的居住区,此外还有划分严格的贱民区、陶工区、织工区和首陀罗区。根特浦尔一带虽然偏僻却物产丰富,盛产咖啡、豆蔻、橡胶、椰子、油棕、甘蔗等热带经济作物。村民们恪守传统的劳作生息方式,然而殖民经济的代表模式——种植园已经包围了村子,大大小小的豆蔻种植园、咖啡种植园在村庄四围林立,在不知不觉中蚕食着村社的公共土地。
从清晨到深夜,牛车满载货物吱吱纽纽地穿过根特浦尔,这些川流不息地运载外销农产品的牛车昭示着外来商业贸易对自给自足的印度村社的冲击。可以说,对于印度农村赤贫现状的根本原因,作家在小说的开篇就给出了自己的解答。“蜿蜒的狭道”,宛如印度发展的历史轨道,在穿越崇山峻岭所护卫的本土文化发展阶段后,来到远航而至的西方殖民者打开的缺口处。为经济扩张而四处出击的海洋文化对于相对封闭的内陆文化的影响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在对外贸易中,交换、分工并不是平等、经由协商可随时改变的关系,它会逐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内相应地形成一系列从属关系。印度在对外贸易的初期的确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出口到欧洲廉价精美的印度花棉布曾直接刺激了肇始于纺织业的英国工业革命④,但18世纪以降,印度受四分五裂的政府统治、落后经济和守旧文化的掣肘,在经济上逐步沦为英国的原料生产国,在政治上被剥夺自治权利,甚至在文化上亦不得不俯首臣服。由于拉奥在小说的前言中声称《根特浦尔》沿袭了往世书的古典叙事方式来讲述一个村庄的历史,同时他将叙述权给予了村庄里一位目不识丁的婆罗门妇女阿恰卡,所以,出于叙事方式的限定,作家并没有详尽分析英国殖民剥削的残酷和殖民地劳动人民的惨状,而是直接摆出叙述者眼见的事实——劳动成果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宗主国——来有力地概括印英关系,简洁生动地做了全文的历史背景铺垫。
拉贾·拉奥认为,印度的往世书神话有效地把曾经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和丰富多彩的人性融会到每一个故事传说中。他把往世书的叙事方式称为“印度叙述”。在这部小说中,这一叙事方式被拉奥出色发挥。他通过乡村妇女絮絮叨叨的讲述,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里的神话以及南印度丰富的地方神话结合起来,并使神话和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勾连起真实与想象的世界。这样,文章可以容纳更为广泛的题材,引发了读者更丰富的联想。从阿恰卡的叙述看,故事历时只有三年,仅仅为几个连续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然而它所涵盖的背景事件却包括了不合作运动、纺车运动、十月革命对印度的影响及印共的发展、“到农村去”、甘地入狱、食盐进军、解救贱民运动等印度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书中有迹可循的真实历史背景从1920年到1930年,历时超过10年。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与村民的个体经历相融合,反殖民斗争被寓言化,人神合一的处理方式与叙事的纵横交叠,这样的文本建构方式反映了作家在有意汲取印度宗教传统和古典叙事美学而对小说叙事方式进行自觉探索。
二
如同印度的其他村庄,根特浦尔也有自己的保护神——肯昌玛女神。故老相传,哲人陲普拉通过苦行将她从天上请到人间,降伏了肆虐根特浦尔的妖魔,从此她就成为与村民的一切哀乐息息相关的神祇。然而,从故事开始的时候,带有地域限制性的肯昌玛女神已经渐渐被具有更广泛民族认同的湿婆神取代了。主人公穆勒蒂“偶然”发现了一个半埋在土里的林伽,在他的号召下,从城里放假回来的年轻人建起了这座湿婆林伽庙,而所有的村民争先恐后地为这一整年的颂神仪式提供斋饭。建庙这一宗教活动成为故事的开端,可阿恰卡却说,湿婆庙是“纷乱肇始之地”⑤,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如果说肯昌玛女神是村社之神,是印度封闭的村社生活的象征,那么湿婆神庙可以看作是民族之神,是民族精神认同的体现,它暗示了村民将走出村庄,投身广阔的民族运动之中。事实上,这座庙宇的确被赋予了独特的作用,是根特浦尔国大党集会以及向村民宣传政策、组织斗争的总部。
随着宗教活动的开展,国大党领导的政治活动也在根特浦尔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穆勒蒂在村民中筹款邀请了著名艺人贾雅拉玛查来演唱神迹故事。贾雅拉玛查并非普通的艺人,据说他在圣雄面前演唱过。面对听惯了湿婆、黑天、罗摩故事的村民,他巧妙地将甘地的奋斗生活编成神话传说。他说,一天,蚁垤仙人来求告大梵天派大神去解救大梵天的掌上明珠——印度,蚁垤首先描绘了一番令所有印度人自豪的壮美河山,提到了著名的历史英雄和哲人,然后讲述了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国人如何践踏他们的国土,如何污蔑他们的传统美德。大梵天因此派湿婆大神化身为甘地降生在古吉拉特,教人民以爱、真理和纺织运动与英国殖民者斗争。由于小说政治层面的主题是甘地主义对印度村庄的影响,因此,作者以这种方式引出甘地作为圣雄、哲人和湿婆化身的救世主形象,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印度人民对甘地的崇拜,而且成功地将甘地作为一个神秘的符号来塑造。作者一再写到:“湿婆本人将会下凡并将我的爱女从奴役中解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们紧紧跟随他,宛如他们追随着吹笛子的黑天大神”⑥。这样,印度追求自由的斗争也成为了一个现代的史诗神话,可以与罗摩和黑天故事相媲美。
贾雅拉玛查所讲述的甘地神迹故事是这部小说最主要的主题象征。如何理解甘地在小说中一再被塑造成湿婆的化身呢?这一方面是国民的普遍崇信和政治家借以推行国民运动的策略,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有意为之。在拉奥的笔下,历史与神话、传统和现实的自然交融是通过村民们的思维来运作的。西方殖民者给印度人民带来的不仅是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而且还带来一套有关“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理论,企图以此来证明其殖民统治的合理性。此时,“蒙昧”村民的宗教情感成为与强势殖民文化抗衡的精神武器。在吃尽了殖民统治苦头的普通民众看来,英国人是魔鬼派遣来的,某位大神的降临将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挺身而出与英国殖民者做斗争的甘地成了为消弭黑暗势力、为无所适从的印度人民指明道路的大神的化身。根特浦尔村的市集上,人们买卖着“罗摩、黑天、商羯罗和圣雄的小像”。⑦ 追随甘地投身民族独立运动被村民们视为争取神恩的宗教行动。
村民们通过贾雅拉玛查所讲的甘地神话初步认识了甘地和民族主义运动,但真正让他们对甘地主义产生具体认识的是穆勒蒂。穆勒蒂在卡纳达方言中意为“偶像”和“形体”。在小说中,村民认为他“活得像一头圣牛,宁静、慷慨、安详、尊重他人,真正具备婆罗门修养,他真该是一个王子”,⑧ 并把他称为“根特浦尔的圣雄”。
穆勒蒂本来在城里念大学,极有可能成为政府的助理税务官或者助理专员。直到有一天他聆听了甘地的演讲,为甘地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听从甘地的指示,焚烧了洋服,从外国人办的大学中退学。同时,他响应甘地的号召回到家乡根特浦尔。在此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形象已经隐现其中。在《尼赫鲁自传》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记载了他自己提出“到农村去”口号的来龙去脉。1920年6月,200名帕太浦岬的村民到阿拉哈巴德向甘地和其他国大党领导反映农民的生活惨状。尼赫鲁和其他几位国大党人到了他们的村庄考察。短短三天时间,尼赫鲁亲眼目睹了在英国殖民者和地主们的双重压迫下印度农村的赤贫和农民们呼吁变革的高涨热情。回到城里,他立即呼吁国大党联合广大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号召农民参加反英的不合作运动。
促使穆勒蒂成为甘地主义者的另一个契机是贾雅拉玛查的被捕。贾雅拉玛查还没有完成他在根特浦尔的神迹故事讲演就被警察抓走了。穆勒蒂从此开始领导根特浦尔一带的民族运动。他通过一系列宗教活动启发村民的独立意识,然后又从城里拿回纺车发给村民,号召大家穿用土布、开展手纺运动。他希望以此一方面改善村民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则教育村民,使他们明白英国殖民统治者是如何通过低价购入原料、高价倾销成品来进行剥削的。尼赫鲁记述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时写道:“(甘地)派我们到农村去,农村地方就有了无数传播新的行动真理的人在生气勃勃地活动着。农民被摇撼醒了,并且开始从他们的静寂无为的蜗壳中挣脱出来。”⑨
拉奥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甘地在团结印度教徒上体现出来的巨大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也忠实地反映出利用传统宗教信仰来进行现实斗争的缺失。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在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的阶级社会,国民精神认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民族、阶级甚至性别的影响。湿婆林伽庙作为根特浦尔国大党政治活动的舞台,是团结国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阵地,但也存在贱民能否进入庙宇的问题。穆勒蒂的解决方法是让贱民们站在庙门外做祈祷、宣誓及参加国大党工作会议。作者以此暗示甘地发起的哈里真运动虽然对提高贱民阶级地位、团结贱民很有帮助,但在强大的宗教陋习面前还是举步维艰。更大的问题在于,甘地这一宗教色彩这样鲜明的形象会否影响到他对非印度教徒的吸引力?甘地是印度教的圣人,但仅仅依靠这一身份是无法吸引、影响穆斯林或其他教派成员的。实际上,面对由来已久、怨愤深积的教派斗争,甘地的良苦用心不惟不足以感化其他教派的顽固人士,就连一些印度教人士亦未必接受。
当穆斯林警察巴德·汗来到根特浦尔时,根特浦尔村民表现出了对他的排斥。巴德·汗告诉村庄的头人高达,政府派他进驻根特浦尔。高达冷漠地拒绝给他找住地。虽然这主要是高达识破了巴德·汗是英国殖民政府的鹰犬,他进村的目的是监控国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但是在婆罗门阿恰卡的理解和叙述中,巴德·汗不能待在村里毫无疑问是因为他是一个穆斯林,“作为一个穆斯林,他既不能够待在陶工区,也不能待在首陀罗区,更别说是婆罗门区了”⑩。高达甚至连贱民区都不让他去。为英印殖民政府办事的印度教徒还是他们可团结的兄弟,但是他们对穆斯林就可能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拉奥通过村民们对待穆斯林警察态度的描写,揭示他对以宗教作为争取独立斗争的利器的忧虑:在多元宗教的国家中,它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巴德·汗虽然被村子的头人驱赶,无法在村里立足而不得不投靠斯克芬顿咖啡种植园的英国庄园主,但是印度教村庄内部也不是团结一致的。婆罗门祭司薄塔和村子里几个保守的上层婆罗门就极力反对、破坏民族独立运动在村里的开展。薄塔并非一开始就与穆勒蒂为敌,他也曾自觉地参加建庙、颂神等活动。但是当这个婆罗门祭司看到民族运动的矛头所向不仅仅是村外的英印殖民政府,而且在甘地的呼吁下还要进行拯救贱民运动,动摇种姓制的根本,触及到了他的直接利益后,他马上转到与穆勒蒂对立的阵营。
薄塔是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得益者。薄塔最初只有“一块缠腰布裹在腰间和一只铜盆拿在手中”,靠在红白喜事时为人打杂和沿门托钵度日。他的父亲去世后,他成为村中的婆罗门祭司,积攒了点钱,开始放高利贷。第一个妻子不知何故掉到了井里淹死后,薄塔立即娶了一位嫁妆丰厚的新妇,开始发达起来。他通过放高利贷,通过和城里的律师、官员攀上关系,千方百计敲诈村民,贿赂长官,渐渐成为村里最大的地主。一天,他因为金钱利益的驱动到城里去,并拜见了斯瓦米。由于斯瓦米本人早被英国人收买,在他的劝说下,财迷心窍的薄塔开始和殖民当局勾结在一起,指使村里的上层婆罗门和穆勒蒂作对。薄塔不仅伙同斯瓦米将穆勒蒂开除教籍,而且勾结殖民当局将穆勒蒂送进监狱。村民们背地里纷纷谴责薄塔。为避锋芒,薄塔离开村庄到圣地迦尸朝圣,村里的妇女们编了首歌谣嘲讽他:
清瘦的是婆罗门祭司,妈啊
但是这个薄塔却肥又胖,妈啊
这个薄塔他肥又胖,妈啊。
他将要踏上前往迦尸的路
因为金子沉甸甸地压着他的胃
他将要踏上前往迦尸的路。(11)
连称赞他聪明的阿恰卡也不禁说道:“罪人即使去到汪洋大海中(洗涤罪孽),海水也只浸到他的膝盖。”(12)
薄塔这一堕落婆罗门人物形象代表了印度教内部的“伪君子”。拉奥通过刻画这一婆罗门形象,进一步揭示了以传统文化作为针对西方殖民扩张的制动力量这一策略明显蕴含了负面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T.J.阿卜拉罕对拉奥是原教旨主义者的指责很难成立。拉奥对于宗教固有的排他性及可能导致的危害并不讳言,对于印度教内部的弊端也没有盲目护短。
窥一斑而见全豹,作家毋需对印度历史和现状逐一分析,只通过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刻画,便能使人见微知著。对于英国殖民统治的罪行,拉奥也是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写作方式揭露。斯克芬顿咖啡种植园不仅是殖民经济在印度高速扩张的体现,还是殖民地人民悲惨生活的一个剪影。种植园的规模一年年扩大,它不但逐步包围了根特浦尔及附近的好几个村庄,还一步步向上发展,蚕食着村民们的圣山。种植园每年都派出印度的工头四处招揽劳工。他们编造谎言,把种植园说成稻米满仓的乐园,哄骗衣食无着的农民们背井离乡、扶老携幼地奔向种植园。然而,“当他们越走越远时,路越来越崎岖,工头也越来越凶恶。”(13) 当苦力们都被关进种植园时,工头狰狞的面目全暴露出来了。这些印度工头对白人唯唯诺诺,对同胞却拳打脚踢、穷凶极恶。实际上,作家对英国殖民者很少直接描绘,几乎所有的冲突、镇压都是直接在印度人之间发生。全书直接刻画的英国殖民者只是斯克芬顿咖啡种植园的两任庄园主。由于作家是从被压迫的印度人的视角出发描写这两个白人,因此他们的形象是漫画式的,并没有像福斯特或吉卜林那样全方位地细细雕凿。但是,作家的寥寥几笔,却重如千钧,每一个看似信笔写来的细节都使两个白人殖民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第一任庄园主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地资本家。他面带笑容,满口道理,一手拿着糖果,但是另一只手却始终攥着皮鞭。第二个种植园主是原来老庄园主的侄子。与老种植园主相比,他对苦力们的剥削似乎更有技巧、更隐蔽了。但他为了抢一个婆罗门的女儿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了婆罗门。
因为这一血案,逆来顺受的种植园苦力和婆罗门职员真正觉醒了,他们和殖民统治者的矛盾白热化。种植园里的婆罗门职员开始团结苦力们,他们带领苦力们到山下的根特浦尔学习,同时也把穆勒蒂请到山上种植园来。
当穆勒蒂来到斯克芬顿咖啡种植园时,苦力们和驱赶穆勒蒂离开的穆斯林警察巴德·汗发生了冲突。然而最终蜂拥而上的种植园打手们占了上风,穆勒蒂无奈地返回了根特浦尔。因为出现了暴力行为,穆勒蒂认为主要是他的过错,所以到村子的庙宇禁食三天以自我净化。在这个时期,穆勒蒂可以说是“全盘甘地化”的。他和所有甘地主义者一样,为非暴力的思想而倾倒。
穆勒蒂信奉的这种道德乌托邦在现实中能否成立呢?他说服了根特浦尔的头人高达在村子里建立了国大党的党组织,开始了不合作运动。为了团结和发动不同等级、不同种姓的村民,婆罗门穆勒蒂不仅走进贱民的家里,还像对待亲姐妹般给死去的贱民妇女扶灵送葬。为此,穆勒蒂被薄塔和斯瓦米开除了教籍,成为失去种姓的人。作为积极的国大党成员,他还屡次被捕入狱。敌对势力的这些伎俩吓唬不了觉醒了的印度村民,在兰甘玛等新的国大党人领导下,村民和种植园的苦力们一起英勇地参加了冲击种植园的运动、禁酒运动、抗租抗税运动等。在小说的结尾,村民们被殖民当局派来的警察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冲突中一位小孩被枪杀。附近的伽尸浦尔村民收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地主和政府勾结,将土地卖给了孟买来的商人,商人们没有在原来的村庄落脚,而是在百布尔小丘处建起新的房子。除了一位妓女外,“在根特浦尔,不但人踪杳然,连蚊子也不剩一只了”。(14) 故事在甘地1931年9月赴英参加第二次伦敦圆桌会议的时代背景中结束了。虽然作家有意留给读者一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结尾,但是众所周知,无论是“甘地—欧文协定”还是第二次伦敦圆桌会议,圣雄都没能为印度千千万万渴望独立的民众圆梦。作者告诉我们,“从冈仁波钦到科摩罗海角,从卡拉奇到卡查拉”(15),农民被从自己的家园赶出来的悲剧在印度许多地方上演。在关系到农民最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上,他们的“罗摩”甘地虽然向总督欧文提出了归还抗税地区农民被没收的土地的要求,但是欧文只答应归还没有拍卖的部分,至于像根特浦尔那样被转卖的土地,协议中并未提及,只空洞地答应会研究解决。由此可见,作家的政治取向已经很清楚。
三
作家认为甘地的个人魅力和他的思想主要源自文化古国印度的传统大智慧。以甘地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在借助政治手段立国的关键时期,主要强调印度民族精神的历史层面,是为了以印度的光辉历史传统为利器,鼓舞民众的整体观念,发挥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小说中一再描绘的各种宗教仪式都指向历史的神圣化。
从《摩奴法论》强调只有婆罗门可以教授吠陀开始,婆罗门阶层一直是印度集体记忆最合法的阐释者,他们维护着世代相因的身份与荣耀,被视为传统价值的担纲者。甘地是新一代的秩序担纲者,小说中,他作为拯救印度的湿婆化身,作为第二个罗摩被印度人民配乐四处诵唱。这一被神化的身份决定了甘地对于印度传统文化的基础——种姓制是没有足够的打击力量的。甘地真正得出“种姓制应该消失”的结论已是1935年,距他1915年提出要反对贱民制,时间已流逝了20年。正如穆勒蒂所认识到的那样,甘地虽然是一个充分了解印度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点和缺陷的圣人,但是,依靠吱吱的手纺车是没有办法消除印度农村普遍的贫穷和等级压迫的。通过历史、作品与史诗典故之间的互见,作家暗示着某些传统日渐过时与失效。甘地的乌托邦距离20世纪的印度确实太遥远了。但是,因为作家对甘地的乌托邦建构可行性提出质疑,而认为作家是背离、扭曲了甘地主义,又未免过于武断了。
对穆勒蒂选择尼赫鲁作为新的追随对象,作家的处理看似突兀,却顺理成章。尼赫鲁在20年代末就被认为是国大党内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第一次公开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是在1929年。那是在国大党拉合尔年会上,他作为主席,在致词中说:‘我必须公开承认,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说要‘根除印度的贫穷和不平等’,必须采取‘社会主义纲领’。不过,那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在形成中,其社会主义概念是指什么,还是十分模糊的。”(16) 尼赫鲁信奉的社会主义是和以剥削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制度,他极力赞扬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兴盛,但却没有接受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事实上,穆勒蒂给拉特娜的信完全可以看作尼赫鲁1929年在拉合尔年会上所发表宣言的翻版。尼赫鲁在这一年经甘地提议,被任命为国大党主席,但他在年会上的发言并未完全得到甘地的认同。
表面上看,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建设方案对穆勒蒂等人的吸引是突然的,但实际上作家在小说的第三章对这一转向已经有所铺垫。而穆勒蒂和甘地、尼赫鲁三者间的关系,作家也已在一次访谈中作出了解释和分析:
穆勒蒂是一个在受到挫败后感到不满的年轻人。在这一刻,他对甘地的信仰动摇了。但是这部小说的确是把圣雄当作主要的感召力量来规划的。在某一时期,尼赫鲁也一样不满甘地的斗争方式。但是,如果尼赫鲁不是一位真正的甘地主义者的话,印度就不会成为我们今天这样的国度。你最好说穆勒蒂是一位偏离轨道的甘地主义者。尼赫鲁,同样的,也是一位偏离轨道的甘地主义者……穆勒蒂和尼赫鲁是相似的。(17)
也许真正成就这部小说重要地位的并非完全是它的反殖民政治主题。它所呈现的虽然都是当时的热点问题,即西方殖民强权对殖民地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觉醒的殖民地人民波澜壮阔的反殖民运动,但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唯一的主题,读者们看到的常常是发生在印度人民之间为了种姓、经济利益等的冲突。换言之,写在30年代的这部小说关注的并非仅仅是印度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斗争,而是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净化,以及探讨一个有深厚文化根基的民族在西方冲击下如何自处并发展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根特浦尔》不仅是印度的,更是属于所有被压迫民族的。
注释:
①Shiva Niranjan,Raja Rao,Novelist As Sādhaka,published by Vimal Prakash Gupta for Vimal Prakashan,413-A Ram Nagar,Ghaziabad-201 001,first edition,1985,p.42.
②Mallikarjun Patil,Kanthapura:A Portrait of Village Gandhi,The Fiction of Raja Rao,edited by Rajeshwar Mittapalli and Pier Paolo Piciucco,published by Atlantic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2001,p.61.
③T.J.Abraham,Flawed Gandhism or Hindu Fundamentalism? No Cheers for Kanthapura,Indian Literature,July-August,2003,p.162.
④此观点见于费尔南·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Fernand Braudel:Civilisation matérielle,économie et capitalisme,Librairie Armand Colin,Paris,1979.
⑤Raja Rao,Kanthapura,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Bombay,the fourth printing,1967,p.7.
⑥Raja Rao前引书,第11-12页。
⑦Raja Rao前引书,第39页。
⑧Raja Rao前引书,第5页。
⑨贾·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77页。
⑩Raja Rao前引书,第13页。
(11)Raja Rao前引书,第94页。
(12)Raja Rao前引书,第94页。
(13)Raja Rao前引书,第46页。
(14)Raja Rao前引书,第182页。
(15)Raja Rao前引书,第159页。
(16)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第5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7)Shiva Niranjan,An Interview with Raja Rao,p.23.quote from Shiva Niranjan,Raja Rao,Novelist As Sādhaka,p.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