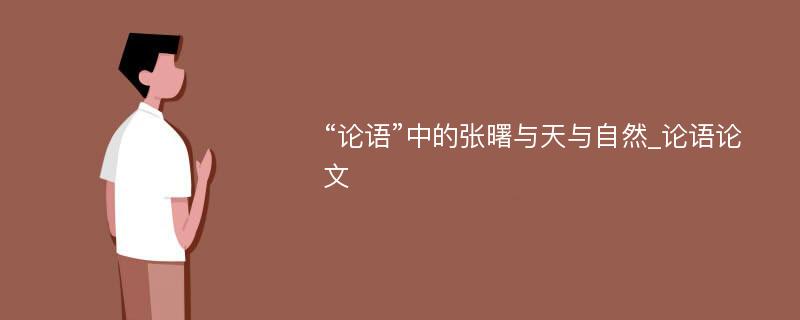
《论语》“性与天道”章疏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天道论文,章疏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语·公冶长》篇所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章,由于“性与天道”的形上性,也由于子贡的“不可得而闻”,致使历来注解者聚讼纷纭,表现出经典文本的意义多重性以及诠释者基于各自时代背景和自身学术倾向的多样性(复杂性)。一句看似可以不求甚解地轻易跳过的话,经历代注解者的不断爬梳或纠缠,才知其所蕴藏的问题之多、之深,诸如“言”是作动词“言说”解,还是作名词“言语”解?“与”字是“和”、“及”的意思,还是“合”、“洽”的意思?文章与性、天道的关系是一还是二?夫子是否言说过性与天道?子贡是否得闻过性与天道?这些问题实有必要一一加以疏证。
一、“言”、“与”:词性问题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语,其中的“言”字当作名词还是动词?“与”字当作动词还是连词?不同的词性意味着不同的语义,不同的诠释立场也必然将此二字定位为不同的词性。
汉代的注释中,只存郑玄对此句的解说:“性,谓人受血气以生,贤愚、吉凶。天道,谓七政变动之占。”①由此并不能推断郑玄对于“言”与“与”二字做何词性的判定。此后,魏何晏注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②何晏把性与天道并列,并谓其深微而不可得闻。故可知何晏是将“与”界说为连词,意为“及”。由此也可推知其以“言”字为动词,言说的内容为性与天道。但凡以“与”为连词,以性与天道为并列关系者,则“言”字理所当然地被界定为动词。
延至南梁皇侃,其《论语义疏》第一次将“言”、“与”二字的词性及含义问题凸显出来。皇侃疏曰:“夫子之言即谓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禀以生者也。天道谓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③此处,“言”字被皇侃解释为名词,而非动词;“与”字被解释为动词,意谓“与……合”。按皇侃的解释,“性”不是孔子“言”之所指的内容,而是孔子言说时之性,它与天道相合。依皇侃之疏,此句当标点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皇侃对“言”、“与”二字的词性的界定以及相应的解释,在《论语》诠释史上是比较少见的,惟唐代李翱继承了此说。李翱解曰:“天命之谓性,是天人相与,一也。……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与天道合也,非子贡之深蕴,其知天人之性乎?”④由此可知,李翱也以“与”为“合”之意。
然而,此后学者多摒弃皇侃、李翱之说,而以“言”为孔子之说性与天道,以“与”为性与天道之并列。如北宋邢昺在其《论语注疏》中曰:“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与,及也。子贡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⑤南宋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⑥又如元代袁俊翁之《四书疑节》曰:“性与天道,夫子非不言也,特不载之《鲁论》耳。”⑦明代吕柟之《四书因问》也曰:“性与天道皆寓于文章中,但人不能识耳。”⑧很明显,以上注解都以“言”为动词,以“与”为连词。
但至清代宋翔凤,推尊汉学,而对汉以下之通行观点不以为然。宋翔凤在其《论语说义》卷三中,先引用《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论语》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谓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学者误谓孔子之言自然与天道合,非唯失于文句,实乃大乖意旨。”然后,宋翔凤写道:“按,如颜意,则汉以后学者以性为自然之理,与天为合,故曰自然与天道合。”⑨又引证《后汉书·管辂别传》“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及《晋书·纪瞻传》“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之说,进而曰:“何平叔亦无以与为及。至皇氏《义疏》始以与为及,然犹说自然之旨。自后遂一变而同颜氏之解矣。”⑩按,宋翔凤谓皇侃以“与”为“及”,非是,上文已述皇侃之解,可证宋氏之误。宋氏引他典“与”作“合”解之例,固然有其史据,但是一个语词的词性与意义既要视其当时通行之例,更要视其在所在文本中之上下语境。就《论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句而言,把此处的“言”视为名词,作言语,把“性与天道”之“与”视为动词“合”,于“不可得而闻也”之说实多悖谬不通,颜师古所谓“非唯失于文句,实乃大乖意旨”,可谓切中肯綮,毋庸多辩。《后汉书·桓谭传》载桓谭上疏光武之文曰:“观先王之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11)此早已以天道、性命为并列之内容,只不过为孔子所难言者。可见以“言”为言说,作动词,以“与”为“及”,作连词,乃汉代早已有之之正解;而以“言”为名词,以“与”为动词的观点则颇为怪异,亦为少数。
二、文章与性、天道之关系:一或二?
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从句式上理解,是把文章与性、天道视为二,一为可闻,一为不可闻,二者判然。但文章与性、天道之关系问题亦由此而生,并引出历代注解者的争议或发挥。
汉代流传下来的郑玄《论语注》,囿于古文经学专注于字词的训诂上,根本未对文章与性、天道之关系措置一词。较早论及此关系,并语出惊人的是三国时魏世荀粲。荀粲“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视文章所传为象内之意,性与天道则为象外之意,非系表之言不能道出。此是将文章与性、天道判为毫无牵连的绝然二物。此观点以有无相分的本体观为基础,崇无贬有,表现出魏晋玄学早期的理论特点。但王弼不同于此说,其所谓“得意忘言”的观点则以言诠为达意的工具,视言(文章)与意(性与天道)仍有必要的联系。其《周易略例·明象》中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亡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12)
在这段文字里,王弼首先承认“言”、“象”对于“意”的重要作用,并明确表示“可寻言以观象”、“可寻象以观意”。这是在言意之辨中对语言和文本的作用给予的充分肯定。王弼像庄子一样,视言、象为筌蹄,即传达意义的工具,所以他认为重要的是抓住意义而不是工具,而且,惟有忘言、忘象,不执滞于言象,才能真正得到意旨。这又是在言意之辨中对意义予以根本的重视。这样,王弼既不是割裂语言(文本)与意义的关系,也不是舍本逐末执着于语言文字,而是以语言为用,以意义为体,既重视体,又兼顾用。依王弼之论,则文章与性、天道亦是言与意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关联的。荀粲和王弼关于语言与意义关系的讨论,是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它虽然与文章、性与天道有关,但并不能完全代替后者的关系。
文章与性、天道关系的问题到宋代才开始受到重点关注和探讨。北宋陈祥道《论语全解》中曰:“夫子之道,出而致广大则为文章,入而极高明则为性与天道。子贡得其言,故于文章可得而闻,未得其所以言,故于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颜子殆庶几者也,故于言无所不悦;子贡非殆庶几者也,故于其言不可得闻。”(13)陈祥道首次用“言”与“所以言”来解说文章与性、天道的关系,又用“出而致广大”与“入而极高明”来把文章与性天道统一到夫子之道上,这种观点是体用论的运用,理论已较前人更为深刻。杨时也持文章与性天道统一的观点,他说:“夫子之文章,与言性与天道,无二致焉,学者非然而识之,则不可得而闻也。子贡至是始与知焉,则将进乎此矣。”(14)杨氏明言文章与性、天道是一不是二,“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与天道,非有二也,闻者自异耳。”能默识者则文章、性与天道皆可得闻,不能识者则止乎文章而不能于文章中识得性与天道。由此可知,杨时也是以性与天道为文章之“所以言”者,与文章之为“言”相对,这与陈祥道的观点相近。
与陈、杨强调文章与性、天道之统一性不同,理学代表朱熹解释说:“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15)朱熹以“理”统性与天道,归于同一本体,但并未进一步说明文章与性、天道是何关系。依朱熹“教不躐等”之说(后详),则朱熹仍倾向于二者的分别。
张栻《癸巳论语解》卷三曰:“文章谓著于言辞者。夫子之文章,人人可得而闻也;至于性与天道,则非闻见之所可及,其惟潜泳积习之久而有以自得之。自得之,则性与天道亦岂外乎文章哉?”(16)张栻认为文章乃是见于言辞者,人人可识,但并非人人可从中进一步领会到性与天道,而经过长久的修习与领悟进而体认到性与天道的人,则自然也能从文章言辞中得闻性与天道。如此说来,张栻是在两个层面上谈文章与性、天道的关系:从闻见之知的层面上说,文字是文章,性与天道超乎其上;从德性之知的层面上说,若既已洞见性与天道,则其亦与文章不二。换言之,文章与性、天道既可以是二,也可以是一,关键在于主体(人)的认知水平在何种高度上。
以上三家,代表了三种观点。陈祥道、杨时从言与所以言的体用论上界定文章与性、天道的统一性,其差别性则表现在人的认知和德性水平上。朱熹从教不躐等说立论,认为文章与性、天道不仅本身有层次差别,在施教程序上也应有区别对待。张栻认为二者有层次差别,但主体一旦识得性与天道,则其与文章原不为二。陈、杨与张栻的观点近似,但在理论基础和深度上,张栻之说仍不如陈、杨。
明代吕柟的观点又与以上三家不同,更显圆融而平实。吕柟《四书因问》卷三载:
问:文章、性与天道之谓何?
曰:性与天道皆寓于文章中,但人不能识耳。子贡之得闻性与天道,其亦自文章中来之乎,不然则夫子之道荒矣。
象先问:文章、性与天道是一样否?
先生曰:性与天道只好在文章上求。如孔子有姊之丧尚右,门人皆尚右。夫子曰“丘有姊之丧”,由是门人皆尚左。一拱手是文章之见于威仪,而尚左、尚右便是性与天道。冉求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曰“有父兄在”。答二子之间,是文章之见于言词,而一进一退便是性与天道。故遗却性与天道而求文章,恐涉于粗迹;离却文章而求性与天道,恐入于窈。此是个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道理。(17)
吕柟可以说是第一个较系统地运用体用关系阐述文章与性天道关系的人。他并不认为文章与性、天道是截然二分的两样东西,也不像张栻甚至杨时那样只从个人体认的角度强调二者的联系,而是认为性与天道本身都“寓于”文章之中,并且也只可在文章中求。二者相依相存,不可或偏:若求文章而遗性与天道,乃涉于粗迹,不得要领;若离文章而求性与天道,则入于窈?,不切实际。故二者是个“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吕柟“体用一源”之说,是对文章与性、天道关系阐释得最为圆融深刻者,后来学者或有类似之说者,(18)然皆不及吕柟之论周详、精到。实则文章与性天道不可截然分作无关联之二物,亦不可视文章与性天道全然没有分别,二者一体一用,既是一,又是二。文章中既有“用”之表面意,又有“体”之深含意;性与天道既有其超然物象而自存的一面,又有显于物象而著落之一面。此方为文章与性、天道关系之正解。
三、性与天道:夫子言否?子贡闻否?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如其中之“言”字作动词用,则夫子到底言性与天道不言?子贡既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则子贡究竟闻性与天道不闻?此亦为向来学者所纠缠深辩之问题。
两汉至魏晋数百年间,注解者皆以孔子不曾言性与天道,因性与天道乃圣人所难言。《史记·天官书》云:“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性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所谓“传其人不待告”,是说不以言语传性与天道;“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意谓于天资浅者告亦无用,故不如不言。后汉之初,议郎给事中桓谭上书世祖,以摒谶纬之说,有言曰:“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19)天道性命虽非如谶纬之怪诞,然圣人之言说乃以仁义正道为本,性与天道为圣人所难言,故当罕言或不言。
魏晋人士以老庄玄言解经,视孔子为“体无”者,故亦以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其理由固然亦以性与天道为难言者,但非因其与仁义正道无关,亦非因其与怪力乱神相类,而是因其乃本体之“无”,非言诠所能训致者。用荀粲的话说,乃因其系“象外之意”;用何晏的话说,乃因其“深微”,故不可言。此是玄学之一大转折,与汉学不同。此说延至唐孔颖达、宋邢昺依然沿用。
唐代韩愈始质疑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之说,他在解《阳货》篇“子曰予欲无言”章中说:“吾谓仲尼非无言也,特设此以诱子贡,以明言语科未能忘言至于默识,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贡使进于德行科也。”(20)这虽然不是直接断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中夫子已言性与天道,但仍可据此推知韩愈否定不言之说。韩愈认为,孔子是想激励子贡等人不要拘泥于言语,而要能默识心会,以上达于天道。因之,孔子言性与天道完全可能,只是如果不能默识,不能深会,即便言了也未见得能领会。但韩愈究竟未能正面详说孔子如何言说过性与天道,以及子贡究竟听闻过没有。
及至宋代理学兴起,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之说方见盛行,然辩议亦见激烈。朱熹《四书或问》、《论孟精义》及《四书集注》等书集中保留了这些辩议之言,《四书或问》卷十载曰:
程子、张子、吕氏以为圣人未尝不言性命,但其旨渊奥,学者非自得之,则虽闻而不喻也,此说善矣。然考之《论语》之书,则圣人之言性命者盖鲜焉,故门人又记之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窃恐子贡之本意,亦不过于如此也。范氏以为圣人教人,各因其材,性与天道,实未尝以语子贡,则亦近矣。但不察乎罕言之旨,而以为圣人之教,有屏人附耳而后及之者,则误矣。抑如子贡者,夫子尝告以一以贯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则固不可谓未尝以告之。谢氏、杨氏以为性命之微,圣人未尝言,而每著见于文章之中,要在学者默识而自得之,则亦误矣。使圣人果绝口而未尝言也,则学者何以知夫性与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晓然号于众曰:“吾有所谓性与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学者之自得。”则其言之已甚,而又骎骎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谓之未尝言而不可闻哉!(21)
按程颐、张载、吕氏(希哲、大临)之说,孔子盖不讳言性命,于子贡等人皆有言及,要在学者自得与不得耳。但朱熹本着子贡“不可得闻”之“本意”,索考《论语》,认为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并非与其言其他物事一样频繁或随意,而是罕言、鲜言。范氏(祖禹)则认为孔子实未尝对子贡言过,因子贡之材尚不足使孔子语及天道性命。朱熹则批评说,孔子之“罕言”不是要因人而密授之意,子贡当亦有闻听之时。谢氏(良佐)、杨氏(时)又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天道性命其旨深微,孔子未尝言说,但每每寓于文章之中,只待学者默识领会方可得。朱熹认为此说逻辑不通:既然夫子绝口不言性与天道,则“性与天道”之目又从何而来?
朱熹对程、张、范、谢诸子观点的评析,甚为确当。朱熹继而在《四书集注》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解说:“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22)其意是说,夫子实尝言性与天道,但圣门教不躐等,所以夫子并非泛言、常言性与天道,而是因材施教,由浅入深,对颜渊、子贡等人均有适时之言,对其他人恐未有言,故是“罕言”。后之宋明诸儒,如蔡节、袁俊翁、赵顺孙、吕柟、高拱、刘宗周等,率皆以夫子有言性与天道之实,只是并非逢人便说,亦非人人皆能易得而已。要之,宋以后学者多持夫子有言性与天道之说,但系“罕言”。
然而在究竟何为“罕言”一点上,学者们的理解仍有分歧。概言之,一派以为“罕言”之“罕”是范围、对象或时机之“罕”,一派认为是程度、领会之“罕”。朱熹之“罕言”论,以教不躐等说为基础,认为孔子之言性与天道是有所选择、有所秩序的。朱熹的观点为后来多数人所继承和繁演。如明代吕柟曰:“盖夫子于人,有不可与言者,有欲无言者,有与终日言者,自有多少等级,不似今人逢人开口便道一贯也。”(23)又如清儒陆陇其在《四书讲义困勉录》卷八中说:“此章须味注‘罕言’字。谓夫子之日言而学者不可得闻,非也。谓夫子之竟不言,唯即文章以为言,而听学者之自悟,亦非也。使其日言,则有躐等之病,且学者仍不可闻,不亦多此言乎?使其竟不言,唯即文章以为言,而听学者之自悟,则圣人之教初无高下之分,而亦不见所谓不躐等之妙矣。”(24)又在《松阳讲义》卷六中说:“此章是说夫子有教人文章之时,有教人性天道之时,不是说文章内的性天道也。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的,亦不是常言的,要玩注中‘罕言’二字,看学者火到时,方与之言;若火未到,则不轻与言。故曰‘罕言’。”(25)这些解释都是基于朱熹的观点,只是解说更为详尽而已。
另一种“罕言”说,与朱熹等人的观点不同,是以性与天道之义旨精微不可易言以及听闻者自身识见能力有限为主旨。早者有张载、吕氏(大临),如张载曰:“子贡谓夫子所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既云夫子之言,则是固常语之矣。圣门学者,以仁为己任,不以苟知为得,必以了悟为闻,因有是说。”(26)吕氏曰:“性与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自有所不闻。”(27)继有蔡节、袁俊翁,如蔡节《论语集说》曰:“夫子之文章形于平日之训言者,学者可得而闻之。至于言性与天道,有不可得而闻者,盖性与天道,夫子未尝轻以告人,然非学者潜心之久,亦未易以得之也。”(28)袁俊翁解释“性与天道”章曰:“徐考子贡立言之初旨,非谓夫子不言也,特谓夫子所言性与天道之精微不可以易闻耳。”(29)
两种“罕言”说亦有直接交锋,其中以东郭子与吕柟、高拱之辩论为代表。
东郭子曰:圣人之言,学者皆得闻,只是人之领略有不同。如一贯之传,众人非不闻,惟曾子能唯之,而门人则曰“何谓也”。又如子贡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谓之言性与天道,则非默然矣。而子贡言其不可得而闻,非真不可得闻也,闻之而不能解则是不闻,非圣人有与言,有不与言也。(30)
按,东郭子信奉王阳明之学,此说颇与阳明学说主旨相合。然此说受到吕柟的批评(见上引吕柟文),高拱在《问辨录》中又对此说进行了批评:
(问)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世儒有云:“谓其言性与天道,则非然然矣,而子
贡言其不可得闻者,非真不得闻也,闻之而不能解则是不闻。非圣人有与言、有不与言也。”然否?
曰:“子罕言命与仁”,非言之而人不知为罕言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非吾固语之而中人以下者,虽闻而不知为不以语也。后儒如此曲说甚多,乃自以为穷理,遂将圣贤明白之说入于晦昧不通之境,则亦无贵于穷理也已。(31)
东郭子之说代表了自张载、吕氏以及蔡节、袁俊翁一系的观点,以听者领受程度之异界定“罕言”之“罕”;吕柟、高拱则代表朱熹、陆陇其一系,以言者顾及听者之对象范围或时机来界说“罕言”之“罕”。总体而论,两种“罕言”说,朱熹为代表的解说更为平易明畅,而以自得、领悟为基础的罕言说虽则于义理上更深入了一步,但于《论语》文本本身而言,似过于曲折缠绕。如此,则夫子究竟言与未言性与天道及其如何言,大抵可以王夫之的疏解为正说:“有云‘性天即在文章之内,人自不能于文章见性天’,及云‘性天不可以言言,不可以闻闻’者,皆邪说也。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则实有其言矣,特不轻以告学者耳。盖必下学之笃行已至,而从事于知性知天之学,乃可因而示之。若本不知性与天道,则闻言而非其心之所及,非茫然无所持循,则拘于言语而成妄僻,故必待其愤悱将通而后语之,此教道之当然也。”(32)
既然在夫子是否言过性与天道这一问题上有言与不言两种观点,则子贡是否曾闻夫子性与天道之言亦大致有两种观点:闻,不闻。而依后来宋明诸儒的辨析,“闻”当又有“听闻”与“得闻”之分别。听闻是耳闻,得闻是心闻,此是其分判处;听闻之后亦可得闻,得闻亦非不可听闻,此是其相连处。若夫子不曾言性与天道,则子贡自然不曾听闻,亦不曾得闻。然则,若夫子曾言性与天道,子贡亦有听闻与不听闻、得闻与不得闻之两种可能,即两种观点。
程颐认为子贡得闻夫子性与天道,但是并非初始即得闻,而是后来经默识之功而得闻。他说:“此子贡闻夫子至论而叹美之言也。”又说:“性与天道,非自得之则不知,故曰‘不可得而闻’。”“性与天道,子贡初未达此,后能达之,故发此叹辞。”(33)程颢虽与程颐一样认为得闻的关键在默识自得,程颢并不认为子贡已完全得闻性与天道。程颢虽曰“子贡盖于是有所得而叹之”,但此处的“有所得”并非完全已得。程颢在解释“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一句时说:“雅言,雅素所言也。至于性与天道,则子贡亦不可得而闻,盖要在默而识之也。”(34)程颢之所以不认为子贡已得闻夫子性与天道之旨,乃因他觉得子贡比较“钝”:“以子贡之才,从夫子如此之久,方叹不可得闻,亦可谓之钝矣。”(35)杨时基本继承了程颢之说,他说:“夫子之文章,与言性与天道,无二致焉,学者非默而识之,则不可得而闻也。子贡至是始与知焉,则将进乎此矣。”(36)杨时虽不谓子贡已得闻,但也认为子贡已识此理,将来庶几仍可得闻。前引东郭子之言,亦可见东郭子持子贡不“得闻”之观点:“子贡言其:不可得而闻,非真不可得闻也,闻之而不能解则是不闻。”此不得闻之说,虽以解与不解为主旨,与程颢、杨时之默识说又有不同,但其思路则是一致的。
朱熹没有采纳程颢的观点,而是基本上接受了程颐的观点,以为“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但因朱熹所持之“罕言”说乃以教不躐等为基础,故此处所言之“得闻”恐仍与程颐之意有精微之差别。按程颐(包括程颢)之“得闻”是指子贡经过一段时间的工夫方才真正自得于心的,而朱子之“得闻”更多地是从孔子因机而发、因时而发这一点上讲子贡到一定时间才“听闻”孔子之言的——当然不排除子贡可能当下或最终能因“听闻”而“得闻”了。
明儒刘宗周又与以上诸家不同,他虽持“得闻”说,然其议论又自有一番新意。《论语学案》卷三中曰:
夫子设教洙泗,无非阐明性天之蕴。盖无言非性,无言非天道,历历在人耳边,而学者终不可得而闻,滞于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则有当面错过者矣。其云文章可得而闻者,何也?以夫子无言非性,无言非天道,则夫子之言皆性天发见流形之妙,如四时之行,如百物之生,秩然灿然,文而且章,故曰文章云尔。子贡盖曰“夫子之言可得而闻,夫子之所以言不可得而闻也”云尔。一夫子言耳,闻之中有不可得而闻,不闻之中未始不可闻,始知夫子之以言教也,而乃其以无言教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子贡则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正可互相发明。子曰:“天何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默而不能藏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语而不能显处。合之,见圣道之妙。夫子言性与天道,惟子贡得闻之,惟颜子得闻之,而且发挥之,其余诸人皆死言下矣。(37)
观刘宗周此段文字,知其乃以“言”与“所以言”相对,以文章为“言”,性与天道为“所以言”。言必有所以言,因其言必可循其所以言,故要在不执于言而在求所以言,止于言则不能得闻所以言。颜渊、子贡能得夫子之所以言,故是得闻者;其余“皆死言下”,只得夫子之言,故是不得闻者。较之前贤,刘子之论更显深刻、圆通。
综上,关于性与天道夫子究竟是否言过,子贡又是否闻过的问题,因时代学术思潮背景不同,因学者自身学养和立足点不同,而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汉至魏晋南北朝多以性与天道深微,不可言,故认定夫子不曾言、子贡未得闻。宋明以后诸儒,多认为夫子曾言性与天道,子贡也听闻过此道,但是否得闻则有不同观点。在言与不言问题上,宋以后学者的解释显然在逻辑上更圆通,讨论也更深刻。在子贡闻与不闻问题上,宋以后诸儒二派观点各有特点,亦皆具合理性,朱熹一派也许更符合文本意义,但刘宗周等之说却更具思想创发性。
要之,中国传统的学术史、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以对经典加以注解的形式而呈现的。对经典的注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制性行为,而必然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创造行为。在这种创造的诠释活动中,思想和学术得以更新和发展。固定为文字形式的经典文本,因其与原始作者生活经验、创造经验的抽离,因其在历史演进中的时空距离,致使文本的意义保持为一种既可以不断生发,又总是不断回溯的张力。经典的语词总是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继而表现为意义的歧义性,而在后来的诠释中又转化为意义的多样性,诠释活动因此也具有了创造性。可以说,“过度诠释”或“误解”往往是思想创造性的必然方式,也是经典意义生长的必然途径。
注释:
①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②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第10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③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第10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0-291页。
④韩愈、李翱:《论语笔解》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邢昺:《论语注疏》,《儒藏》(精华编)第10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47页。
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儒藏》(精华编)第11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⑦袁俊翁:《四书疑节》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吕柟:《四书因问》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宋翔凤:《论语说义》,《儒藏》(精华编)第10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6页。
⑩宋翔凤:《论语说义》,《儒藏》(精华编)第105册,第556页。
(11)《后汉书·桓谭传》,中华书局,2007年,第262页。
(12)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4609页。
(13)陈祥道:《论语全解》,《儒藏》(精华编)第10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14)朱熹:《论孟精义》,《儒藏》(精华编)第10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儒藏》(精华编)第110册,第112页。
(16)张栻:《癸巳论语解》,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
(17)吕柟:《四书因问》卷三。
(18)如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卷八载:张彦陵:“文章性道亦非二件,文章是性与天道之著,性与天道是文章之蕴。”“翼注曰:文章即性天显设处,性道即文章隐微处,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又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七曰:“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19)《后汉书·桓谭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262页。
(20)韩愈、李翱:《论语笔解》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朱熹:《四书或问》,《儒藏》(精华编)第110册,第722-723页。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儒藏》(精华编)第110册,第112页。
(23)吕柟:《四书因问》卷三。
(24)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録》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陆陇其:《松阳讲义》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朱熹:《论盂精义》,《儒藏》(精华编)第109册,第147页。
(27)朱熹:《论孟精义》,《儒藏》(精华编)第109册,第147页。
(28)蔡节:《论语集说》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袁俊翁:《四书疑节》卷十一。
(30)吕柟:《四书因问》卷三。
(31)高拱:《问辨录》,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9页。
(32)王夫之:《四书笺解》卷三,《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198页。
(33)以上均见朱熹:《论孟精义》,《儒藏》(精华编)第109册,第146-147页。
(34)朱熹:《论孟精义》,《儒藏》(精华编)第109册,第217页。
(35)朱熹:《论孟精义》,《儒藏》(精华编)第109册,第146页。
(36)朱熹:《论孟精义》,《儒藏》(精华编)第109册,第148页。
(37)刘宗周:《论语学案》,《儒藏》(精华编)第105册,第196-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