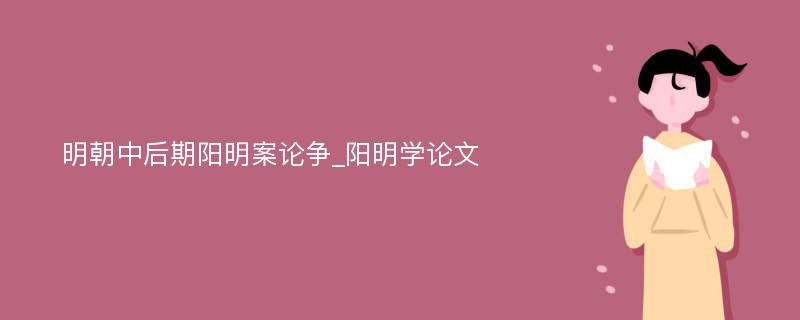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晚明阳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4)01-0059-08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诠释,或许是最能反映阳明学与朱子学不同取向的一个方面。不过,即使在中晚明阳明学的系统内部,不同学者对“格物”观念也有互不相同的理解并且相互之间进行过辩难。格物之辩不仅是一个经典诠释学的问题,更多地反映了不同学者对工夫问题的各自看法,构成中晚明阳明学工夫之辩的一项具体内容。明末的刘宗周(这起东,号念台,称蕺山先生,1578-1645)《大学杂言》曾谓“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1](P771)。这当然是就整个宋明理学传统而言,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应当是中晚明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在此,我们无法也不打算对中晚明的格物诸说一一分析求证,而是希望通过考察一些学者之间有关“格物”的论辩,进一步掌握中晚明阳明学在展开过程中工夫理论的某些动向与特征。
一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1472-1528)摆脱朱子学的笼罩,确立其一生精神方向的转折点。而龙场之悟的核心内容,正是对“格物”观念有了不同于朱子学的崭新理解:“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2](P1228)尽管朱子未必将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其思想学说的终极追求,但“格物”观念在朱子学的解释中的确主要在于探究外在客观事物的规律,所谓“穷理”[3]。阳明龙场之悟对“格物”的重新诠释,正是将对外在客观事物的认识转向内在自我意识的端正,所谓“正念头”。这一基本取向的转变,体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在工夫问题上的基本差异。并且,中晚明阳明学工夫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便是继续“鞭辟入里”,不断向主体意识的深层发掘,直至最后的终极实在。然而,阳明学这种内向的道德修养工夫如何避免将道德实践封限于单纯自我意识的领域,不仅是儒家“万物一体”基本观念的必然要求,在当时也是圣学工夫区别于佛老的标志之一。
事实上,阳明在提出其有别于朱子对“格物”的解释之后,便立刻面对了这一问题。当时学者如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1466-1560)、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47)、顾璘(宇华玉,号东桥,1476-1545)等人与阳明关于“格物”的论辩[4](PP.135-151),核心也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在湛若水和罗钦顺看来,阳明“正念头”的“格物”说既与《大学》“正心”、“诚意”的说法有文义上的重复,又难以与释老的自我修养工夫划清界限,总之不免“局于内而遗其外”。经过这些论辩,阳明的“格物”说表现出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单纯自我意识的端正转变为道德实践中行为的正当化。前者如正德年间所谓“‘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2](P6),后者如嘉靖年间所谓“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2](P45),“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2](P972)。由于阳明始终认为不能离开人的意识活动来谈事物,所谓“意之所在为物”,因此,即使在晚年强调“格物”是在行事过程中的为善去恶,将良知的发用流行充拓推广到事事物物当中使之皆得正当化,阳明对“格物”的理解也并没有因为在有关格物之辩中受到朱子学者或认同朱子格物说学者的批评而回到认识客观事物的道路上去。阳明“格物”说的发展过程,其实反映出阳明对“格物”观念理解的深化。就此而言,作为工夫论而非认识论的格物说,其最终内涵应当说既非单纯探究外在客观事物而与朱子学的“格物穷理”有着根本的不同,又非单纯内在自我意识的端正而与“诚意”有别。不过,阳明对此尚未有明确的分疏。这一点,在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与一些学者的“格物”之辩中,则得到了进一步明确的揭示(详见后文)。
相对于朱子学,阳明的“格物”说在整体上毕竟体现出主体主义的倾向。因此,随着阳明学影响的日渐深远,许多学者无形中受到阳明正德年间以“正念头”诠释“格物”这种说法的影响,在对“格物”观念的理解上又走到了朱子学“格物”观的对立面,确实出现了将“格物”工夫收缩于单纯自我意识领域的倾向。对此,王艮(字汝止,号心斋,1483-1540)的“淮南格物”说可为一例。对王艮而言,自我与天地万物都可以说是“物”,但二者是有本末之别的。所谓“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5](P712),“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5](P711)。因此,“格物”的根本涵义便是“正身”,身正则天地万物、家国天下也就随之而正,所谓“格,挈度也。挈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5](P712),“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5](P712)。尽管“正身”思想中的“身”还容纳了感性甚至肉体生命的向度,但更多地仍然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因此,将“格物”的工夫限定于主体自身,是“淮南格物”说的基本特征所在。正如王栋(字隆吉,号一庵,1503-1581)所谓:“格物之学,究竟只是反身工夫。”[6]这一倾向的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了湛若水的门下。如湛若水的再传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1535-1604)认为:“格物之说,彼谓‘待有物而后格,恐未格时,便已离根者’,此其论似高而实非也。若得常在看到方寸地洒洒不挂一尘,乃是格物真际。人有血气心知,便有声色,种种交害虽未至目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诚意工夫透底,是一格物。孔子江汉以濯、秋阳以暴,胸中一毫渣滓无存,阴邪俱尽,故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非圣人,不足以当格物之至。”[7](P982)这实际上是将“格物”等同于“诚意”。而明末师承许孚远的刘蕺山称赞王艮的“格物”说,所谓“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8](P1539),并将“诚意”、“慎独”作为“格物致知”的实质内容,无疑也是将“格物”工夫收缩于自我意识领域的表现。当然,这一倾向更为鲜明的反映,是聂豹(字文蔚,号双江,1487-1564)“格物无工夫”以及王宗沐(字新甫,号敬所,1523-1591)以“无欲”解“格物”的主张。但是,这一倾向并不能代表所有阳明学者对“格物”的看法,而正是在与聂双江、王宗沐的格物之辩中,王龙溪进一步阐发了阳明晚年的“格物”思想,显示了中晚明阳明学中“格物”说的另一种致思取向
二
聂双江与龙溪曾经展开过系统的往复辩难,其中涉及到了阳明学的许多重要方面。除了有关现成良知的问题之外,“格物”观念也是双方辩论的问题之一。聂双江对“格物”的理解,是与其“致知”观念紧密相关的,《大学古本臆说序》说:“致知者,止至善之全功。格物者,止至善之妙用。意也者,感于物而生于知者也。诚言其顺,格言其化,致言其寂也。寂以妙感,感以速化,万而一者也。”[9]显然,双江从体用的角度来理解“致知”与“格物”的关系。而既然“致知”是“立体”的“全功”,“格物”便不过是致知工夫所取得的效果,本身并不具备工夫论的意涵。严格而论,双江的“格物”其实应当是“物格”。在与龙溪论辩的书信中,双江便明确提出了“格物无工夫”说法。《答王龙溪》第一书云:“愚夫愚妇之知未动于意欲之时与圣人同,是也。则夫致知之功要在于意欲之不动,非以‘周乎物而不过’之为致也。镜悬于此而物自照,则所照者广。若执镜随物以鉴其形,所照几何?延平此喻未为无见。致知如磨镜,格物如镜之照。谬谓格物无工夫,以此。”[9],在双江看来,工夫如果落在“格物”而不本于“致知”,就会像“执镜随物以鉴其形”那样所照有限。而如果工夫本于“致知”,即将着力点落在良知心体,就会像“镜悬于此而物自照”那样,收到“所照者广”的功效,《答王龙溪》第一书所谓“充满乎虚灵本体之量,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则自此而发者,自然中节”[9]。当然,如果双江强调“格物”须本于“致知”的重点在于指出格物工夫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在良知心体,格物工夫的实践须预设良知心体的先在性,则龙溪并不能反对,龙溪致良知工夫尤其先天正心之学的重点也正在于此。不过,由于双江是二元论的体用思维方式,因此,“致知”与“格物”便不会是相互蕴涵的关系。既然双江归寂说的宗旨在于“充满乎虚灵本体之量”的“致知”、“格物”失去其独立的工夫论意义,便是必然的理论后果。
由于双江的“格物”说关联于“致知”,龙溪也从“格物”与“致知”关系的角度表达了他对“格物”观念的看法。龙溪全集中共收录两封给双江的书信。其中都谈到了“格物”的问题。在《答聂双江》中,龙溪指出:“所谓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实用力之地,不可以内外分者也。若谓工夫只是致知,而谓格物无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绝物,便是仙佛之学。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发之知,其流之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离之学。争若毫厘,然千里之谬,实始于此,不可不察也。”[10]在这封信中,龙溪讲得比较圆融,既批评了只讲“致知”不讲“格物”的“绝物”,又批评了只讲“格物”不讲“致知”的“逐物”。对龙溪来说,“格物”与“致知”其实是相互蕴涵的关系。在《与聂双江》中,龙溪则进一步针对双江归寂立体的主张强调了“格物”的工夫论意义。龙溪指出:“然欲立定命根,不是悬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实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则,良知所本有,犹所谓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应上参勘得过,打叠得下,终落悬空,对境终有动处。良知本虚,格物乃实,虚实相生,天则常见,方是真立奉也。”[10](卷9)由龙溪与双江的格物之辩可见,双江“格物无工夫”的主张完全将道德实践的工夫收缩到了自我意识的领域。针对双江之说,龙溪对“格物”的强调在于工夫不能只限于主体自身,还必须落实到人伦日用的各种实事上去,否则不免产生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如果道德实践仅仅封限于自我意识的领域,一旦与外物交接,便难以保证实际的行为仍然符合道德法则,所谓“若不在感应上参勘得过,打叠得下,终落悬空,对境终有动处”。另外,佛道两家的基本特征便是缺乏“经世之学”而将修养的工夫限于个体自我。双江只讲“致知”而否定“格物”的工夫论意义,在龙溪看来,就不免同样是将道德实践封限于个体自我而难以与佛道两家划清界限。所谓“若谓工夫只是致知,而谓格物无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绝物,便是仙佛之学”。而龙溪强调致良知工夫必须落实到不离伦物感应的“格物”上去,与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中要求“必有事焉”的告诫,是完全一致的。
王宗沐师事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1596-1554),属于阳明学的第二代。他曾将“格物”中的“物”字解作“欲”,将“格物”解作“无欲”。这种将“格物”解释为消除欲念的工夫,显然与朱子学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接近于阳明正德年间“正念头”的立场。但是,当王宗沐致书于龙溪时,龙溪并不以是说为然。在《格物问答原旨——答敬所王子》中,龙溪更为明确地强调了“格物”不能离开人伦日用而限于自我意识的领域。
龙溪指出,将“物”解作“欲”在经典诠释的传统中并无依据,《格物问答原旨——答敬所王子》所谓“兄径以物字作欲字看,从古无此训释”[10]。但是,对龙溪来说,问题的关键尚并不在此。在龙溪看来,作为“诚意”工夫的“格物”并非一种与外界事物无关的单纯自我意识活动,而是必然要关联于“伦物感应之实事”。“物”泛指人伦日用中的各种行为。不符合道德法则的行为实际上是人们私欲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为善去恶”的“格物”工夫,也可以说就是要消除人们的私欲的“无欲”工夫。不过,这种“无欲”的“格物”工夫是要消除人伦日用中不合乎道德法则的行为,而不是要取消人伦日用的各种行为本身,使道德实践的工夫仅仅退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正如龙溪所谓:“即如颜子非礼毋视毋听,视听物也,非礼之视听,方谓之欲,毋视毋听,正是克己无欲工夫,亦非并视听为欲而欲格去之也。”以“无欲”为“格物”,不免有导致离却“伦物感应”的可能。因此,针对王宗沐将“格物”解作“无欲”,龙溪格外强调了“格物”中“即物”的一面,《格物问答原旨——答敬所王子》所谓“无欲须于人伦事物上磨。……在人伦事物上磨,格其不正以归于正,正是无欲工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良知是天然之则,物是伦物感应之实事。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则;有视听之物,斯有聪明之则。伦物感应实事上循其天然之则,则物得其理矣。是之谓格物”[10]。显然,这里龙溪对“格物”的界定,所谓“伦物感应实事上循其天然之则”,与阳明晚年所谓“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的说法是一致的。
不过,无论在与聂双江还是王宗沐的论辩中,龙溪在“格物”问题上对不离“伦物感应之实事”的强调,决不意味着龙溪回到了朱子学“格物穷理”的思想。龙溪的“格物”说无疑继承了阳明有别于朱子学的基本取向,如他在《与万合溪》中所谓:“意之所用为物,是吃紧要语。物之善恶无定形,意善则物善,意恶则物恶。格者,正也。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为困勉立法。正与不正,皆从意根上用力。故曰格物者,格其意之物也。若在物上求正,即为义袭之学,非大学本旨矣。敬所兄认物为欲,似抑之太过;吾丈训格物为至善,似扬之太过,恐皆未得孔门立言之旨也。”[10](卷11)不论万合溪“训格物为至善”的涵义究竟是什么,龙溪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显然是反对朱子学的“格物”说。进一步说,龙溪认为格物工夫的着力点不应当落在外在的客观事物上,而应当放在主体的意识活动中,否则道德实践的自律性不免丧失。所谓“正与不正,皆从意根上用力。故曰格物者,格其意之物也。若在物上求正,即为义袭之学,非大学本旨矣”。当然,龙溪将“格物”工夫理解为主体的意识活动,并非意味着这种主体的意识活动仅限于单纯自我意识的领域。对龙溪来说,作为主体意识活动的“格物”工夫始终必须关联于自我之外的各种事物。正如前文所论,龙溪对聂双江、王宗沐“格物”说的批评,强调的无非都是这一点。
三
笔者曾经指出,龙溪致良知工夫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将阳明对朱子学外向工夫的内向扭转继续推进,贯彻到了最为根本的良知心体这一向内追究的逻辑终点。但是,通过以上龙溪对聂双江、王宗沐“格物”说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到,龙溪的致良知工夫论尽管立足于最内在的良知心体,却又并非离却伦物感应而退居于单纯自我意识的领域,而是必然要展开于由自我而家、国、天下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正《格物问答原旨——答敬所王子》所谓“非即其物而格之,则无以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谓不离伦物感应以致其知也”[10],如此才能最终达到四无论所揭示的万物一体与天德流行的圆善之境。
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穷理”不免“忘内求外”的话,聂双江的“格物无工夫”和王宗沐的“无欲”说所代表的倾向则均不免“务内遗外”。这两种“格物”说的取向都不为龙溪所取,在龙溪看来,“格物”工夫应当是一种“合内外之道”。在上引《答聂双江》书中,龙溪对“支离之学”“逐物”与“仙佛之学”“绝物”的两方面批判,便已经显示了龙溪在“格物”观念上的基本立场,而在万历三年乙亥(1575)的新安斗山书院之会中,七十八岁的龙溪对此更有明确的表达,《新安斗山书院会语》云:“或问格物之义:或以格物为至其理,或以格物训作无欲,其旨何如?先生(龙溪)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良知是天然之则,物是伦物所感之应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则;有视听之物,斯有聪明之则。应感迹上,循其天则之自然,而后物得其理,是之谓格物,非即以物为理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为物。意到动处,遍易流于欲,故须在应迹上用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于无,是之谓格物,非即以物为欲也。夫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只是一事。身之主宰为心,心之发动为意,意之明觉为知,知之感应为物。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此虞廷精一之旨,合内外之道。物从意生,意正则物正,意邪则物邪。认物为理,则为太过;训物为欲,则为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也。”[10]由此可见,在格物的问题上,龙溪采取的是双谴两边之见的中道立场。既不将工夫的实践对象系于外在事物,又不取消外在事物客观实在性以至于将其化约为纯粹的自我意识。通过对“格物”观念的阐发,龙溪使阳明学的工夫论在继续针对朱子学“格物穷理”外向路线不免削弱道德主体性这一问题的同时,又力图避免将致良知工夫化约为单纯自我道德意识的修养,以便与佛道的心性工夫划清界限。后者从龙溪与聂双江、王宗沐的格物之辩来看,在中晚明阳明学的展开过程中更具有理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作为阳明晚年成熟的“格物”说的进一步展开,龙溪这种将“格物”工夫作为“合内外之道”而指向“我”与“物”之间感应关系的立场和取向,在中晚明的思想界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反映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说发展的另一个基本方向。龙溪传人周汝登(字继元,号海门,1547-1629)后来便对王艮的淮南格物说提出批评,所谓“心斋格物之说,自是归根之旨,然亦不能舍却家国天下心意,另求一物。阳明子所谓致吾心之知在事事物物之间,格其不正以归于正。夫事物非迹,即是吾知;吾知非虚,即是事物。工夫即格即致,本末难分。如此修证,于孔门博约中和之训,无不合辙。故区区谓惟当遵阳明子之说,着实做去,不必别立新奇也”。[11]这显然是秉承龙溪“合内外之道”的格物宗旨,认为王艮之说不免会限于自我意识。“舍却家国天下心意”中的“心意”是虚说,“家国天下”才是实指。海门是龙溪之后最能发扬龙溪思想的弟子,在格物工夫上与龙溪保持一致是很自然的。此外,我们可以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1496-1554)、王时槐(字子植,号塘南,1522-1605)对“格物”的看法为例加以说明。这两个人物既分别属于阳明学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传人,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但在“格物”的问题上均与龙溪持论相当,应当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对于聂双江“格物无工夫”的说法,欧阳南野也曾经作出过回应。南野在给聂双江的书信中指出:“夫知以事为体,事以知为则。事不能皆循其知,则知不能皆极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然后为全功。后世以格物为功者,既入于揣摩义袭,而不知有致知之物;以致知为功者,又近于圆觉真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去道愈远矣。”[12]在南野看来,朱子学“以格物为功”,不免入于“揣摩义袭”,而双江主张“格物无工夫”,仅“以致知为功”,又不免沦于佛教的沉空守寂之学,所谓“近于圆觉真空”。将南野此信与前引龙溪《答聂双江》相对照,我们立刻会发现,就对双江的批评而言,无论在基本立场还是论证方式上,南野与龙溪简直可谓如出一辙。
由于二元论的体用思维方式,江右阳明学的再传王时槐(字子植,号塘南,1522-1605)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所见并不同于龙溪、南野,并开启了脱离阳明学典范的契机[13]。但是,在对“格物”的理解上,塘南却又与龙溪、南野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首先,在对“物”的理解上,塘南认同阳明“意之所在为物”的说法:“阳明以意之所在为物,此义最精。盖一念未萌,则万境俱寂,念之所涉,境则随生。且如念不注于目前,则虽泰山觌而不睹;念苟注于世外,则虽蓬壶遥阁而成象矣。故意之所在为物,此物非内非外,是本心之影也。”[14]在此基础上,塘南也认为“致知”的工夫必须落实在“格物”上。当有人提出“致知焉尽矣,何必格物”这一认同聂双江“格物无工夫”主张的问题时,塘南回答说:“知无体,不可执也。物者知之显迹也。舍物则何以达此知之用?如窒水之流,非所以尽水之性也,故致知必在格物。”[14]这种从“格物”与“致知”关系的角度对于前者的强调,也与龙溪、南野相同。另外,塘南还曾说:“盈天地间皆物也,何以格之?惟以意之所在为物,则格物之功,非逐物亦非离物也,至博而至约矣。”[14]这种“非逐物亦非离物”的“格物”观,与龙溪既反对“逐物”又反对“绝物”的立场也是完全一致的。
四
由以上的讨论可见,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虽然总体上有别于朱子学而具有主体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在其内部仍然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如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的“格物”说。另一种则是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亍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这是从阳明到龙溪等人的“格物”说所代表的方向。这一方向不再像前一种那样构成朱子学“格物”说的简单对立,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朱子学重视探究外界客观事物的精神。当然,这种对外界事物的重视如果在朱子学那里更多地具有认知主义意味的话,在阳明、龙溪等人这里,则完全服从于伦理中心的原则。
从阳明到龙溪,“格物”说不再仅仅作为朱子学“格物穷理”的对立面表现为单纯自我意识的端正(正念头),而是发展成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其实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彼此反对到相互吸收的动向。事实上,阳明本人格物说之所以会有一个从“正念头”到“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转变,正是与湛若水、罗钦顺和顾东桥等朱子学立场或倾向于朱子学立场的学者相互论辩的结果。此外,这种动向并非仅仅发生在阳明学之中,中晚明的朱子学者或倾向于朱子学的学者在“格物”的问题上,也修正了朱子的看法,而在实际上对阳明学主体主义进路的“格物”说不无所取。这一点,在罗钦顺、顾宪成和高攀龙等几位中晚明的主要人物那里都有鲜明的反映。如罗钦顺在与阳明辩“格物”时曾批评阳明将“格物”解释为“格心”的说法不免“局于内而遗其外”,但罗钦顺最终对“格物”的解释也并非完全采取朱子学的立场。朱子学以“至”训“格”,阳明正德年间以“正”训“格”,而罗钦顺则将“格”解为“通彻无间”。所谓“格物之格,正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虽合字亦不用矣”。[15](P4)如果说阳明正德年间的“格物”说与朱子的“格物”说分别有内外之偏的话,罗钦顺这种将“格物”工夫既不推向外物又不收回内心,而是强调心物交融、物我交融的“格物”说,显然是吸取了阳明“格物”说的结果。这种将“格物”理解为物我之间彼此相通的看法,在阳明学中甚至颇有同调,如晚于罗钦顺的杨起元(字贞复,号复所,1547-1599)曾说:“格亦有通彻之义,通而谓之格,犹治而谓之乱也。格物者,己与物通一无二也。如此,则无物矣。有则滞,滞则不通;无则虚,虚则通。物本自无,人见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归其本无也。”[16]这也向我们透露了阳明学与朱子学在“格物”问题上渐趋融合的消息。东林的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1550-1612)与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1562-1626)虽然对“格物”的看法不尽相同并进行过讨论[17],似乎顾宪成强调格物要落实在性情上的看法受到阳明学的影响,而高攀龙则更接近朱子学的立场而肯定了格“一草一木之理”的意义,但是,由于根据自身的内在体验而预设了心与理同一的前提[18],高攀龙对格“一草一木之理”的肯定其实并不同于朱子,而是将“一草一木之理”纳入到自我的心中,如此则“格物”工夫的基本取向仍在于反观自得,所谓“才知反求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19]。也正是因此,黄宗羲认为高攀龙这种诉诸于主体的“格物”说“是与程、朱之旨异矣”[20],反而与阳明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先生之格物,本无可诤,特欲自别于阳明,反觉多所扞格耳”[20]。如此看来,顾、高二人虽对阳明均有批评,但在“格物”的问题上,却也都不免在实际上受到阳明学的影响而注意到了心与物之间的融通。此外,甚至连归宗气学的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1474-1544)在解释“格物”时也有可能受到阳明的影响,批评朱子学解“格”为“至”而认同阳明以“正”训“格”。所谓:“格物之解,程朱皆训‘至’字。程子曰‘格物而至于物’,此重叠不成文义,朱子则曰‘穷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穷”字。圣人之言直截,决不如此,不如训以“正”字’。”[21](P838)“格物者,正物也,物各得其当然之实则正矣。”[21](P775)当然,不论是罗钦顺、顾宪成、高攀龙还是王廷相,其“格物”说的具体内涵都值得深入探讨,但由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中晚明的阳明学,因此,这里只是指出他们的“格物”说都或多或少有取于阳明学这一一般特征,以便与前面所论以龙溪等人为代表的阳明学在“格物”问题上吸收朱子学这一发展方向相对照,使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中晚明阳明学与朱子学互动交融下所产生的新的发展动向与特征。
当然,正如阳明与湛若水、罗钦顺以及龙溪与聂双江、王宗沐的论辩所显示的那样,由于在“格物”的过程中是否能够作到“及物”而不“绝物”在当时还是圣学工夫区别于佛老的一个标志,因此,格物之辩还纠结着儒释之辩的因素,而不是一个只限于儒学内部的问题。事实上,除了朱子学之外,与佛老的互动交融,同样是制约中晚明阳明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