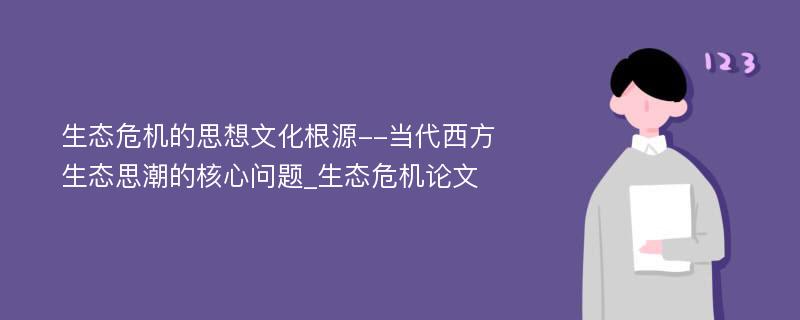
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思潮论文,根源论文,当代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人类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生态思潮越来越波澜壮阔。生态的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和生态的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成为普遍采纳的思维方式,从生态的角度探讨问题,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建立了与生态相联系的新的交叉学科。有人预言:鉴于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问题,21世纪必将是生态思潮的时代。
生态思潮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存在危机这个大背景下形成并壮大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人文社科学者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形成阶段,主要成就是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怀特的《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1967)、罗马俱乐部学者佩切伊的《深渊在前》(1969)和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1972)、莫斯科维奇的《反自然的社会》(1972)、奈斯的《浅层的生态运动与深层和长远的生态运动》(1973)、帕斯莫尔的《人类对自然的责任》(1974)、莫兰的《自然之自然》(1977)、约纳斯的《责任原理》(1979)等。八九十年代以来为发展阶段,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出现了影响很大的著作,主要有莫尔特曼的《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1984)、泰勒的《尊重自然》(1986)、拉夫洛克的《该亚:地球生活的新视野》(1987)、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1988)、克利考特的《捍卫大地伦理》(1989)、布克钦的《生态社会学理论》(1990)、庞廷的《绿色世界史》(1991)、伯林特的《环境美学》(1992)、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1993)、沃伦的《生态女性主义》(1994)、格罗特费尔蒂等人的《生态批评读本》(1996)、戴利的《生态经济学与经济生态学》(1999)等。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生态思潮进行回顾与总结,代表性的著作有马歇尔的《自然之网:生态思想研究》(1992)、诺顿的《走向整体的环境主义者》(1994)、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1994)、齐默尔曼的《环境哲学》(1998)、本顿等的《环境话语及实践》(2000)等。
我国学者在80年代开始关注生态思潮,陆续翻译了一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神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学、生态美学、生态史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学、生态经济学著作,并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
国外学者在回顾和总结生态思潮时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生态思潮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沃斯特明确地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整个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然的经济体系已经被推向崩溃的极限,而‘生态学’将形成万众的呐喊,呼唤一场文化革命。”[1] 27,356生态思潮要探究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生态思潮的目的是思想文化变革,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研究和发展模式的变革,建立新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具体的生态治理实践,但他们却能够为挖掘乃至铲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之根和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贡献。这就是生态思潮的意义和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观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根源,是当代生态思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本文要分析的主要问题。
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人类中心主义
第一个对人类中心主义发起直接批判的是生态思潮的始作俑者、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文学家卡森。卡森认为,人类竭泽而渔地对待自然,其最主要的根源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2]
在卡森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阵营。美国史学家怀特在他那篇被誉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的文章《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3] 生态社会学家威尔森更是愤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4] 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是狂妄自大的,“这种狂妄自大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世界里一直延续,它使人把自然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创世纪》就是我们的起点。”“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的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基督教的这种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人类中心主义。”[5] 另一位生态思想家马歇尔在《自然之网:生态思想研究》一书里也指出,“《创世纪》里最重要的词语kabas和rada在整部《旧约》里都有使用,意思是残酷的殴打或压制。这两个词都被用来描述征服和奴役的行为,都给人这样一种意象:征服者获得了完全的统治,并把脚踩在被打败的敌人的颈项上。因此,出现这样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基督教徒把《创世纪》里的这些话传统地解释为神对人的授权,允许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征服、奴役、开发和利用自然。”[6] 98著名的生态神学家考夫曼1998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有80多位世界一流神学家参加的“基督教与生态学”研讨会上指出,“我们所接受的大多数关于上帝的概念和形象所蕴含的拟人观——深深地根植于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残留至今——需要被解构。”唯有这样才可能消除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7]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并不等同于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主张以人为本,另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以人为本、为中心、为主宰。后者才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想家要批判的决非人类社会里的以人为本,而是在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以人为本。生态思想家赞成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坚持人本主义原则,尊重人、维护人权、捍卫公平正义;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的自大狂妄,反对人类自诩为世界的中心、万物的灵长、自然的随意掠夺者和统治者,反对人以征服自然、蹂躏自然的方式来证明自我、实现自我、弘扬自身价值。
那么,能否彻底否定和完全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呢?一些人认为,人类不可能不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不可能不首先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环境保护是为了人而保护环境,而不是为了自然而保护自然;为保护环境付出一些代价,目的是人类长久的生存和长久的从环境中获利。于是,有人提出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改良,改良成所谓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开明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现代人类中心主义”。[8] 与之相联系,也要对传统的人道主义进行修正,建立“新人道主义”。佩切伊认为,“新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把我们同其他生命形式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从人的总体性和最终性上来看人,从生活的连续性上来看生活”。[9] 还有人提出“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的概念,这种新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爱、谦卑、尊重与合作,正如威斯特灵所说,“生态人文主义将恢复并赞赏人在自然面前的谦卑态度,……强调人类合作性地参与整个星球的生命共同体。”[10]
另一些生态思想家则认为,要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和所有物种的生存危机,人类——作为地球生态危机的酿造者和责任者——必须跳出自我中心这个局限,努力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并以这样的思考约束自己的生活和发展。于是他们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其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
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把生态整体主义称为“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这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用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误解生态整体观。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中心都没有,何来“中心主义”?最早阐述生态整体主义的利奥波德所强调的就是整体性价值判断标准:“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11] 此后许多思想家都赞同利奥波德的“ISB原则”(integrity,stability and beauty)。著名的“该亚假说”(Gaia hypothesis)用一个神话原型作为隐喻来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拉夫洛克解释道:“关键的是星球的健康,而不是有机物种个体的利益;……人类只是物种之一,而不是这个星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与该亚的关系,而不是自身利益无休止的满足。”[12] 泰勒在《尊重自然:生态伦理学理论》里讨论对生物的伦理关怀时,也强调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禁止干预这些同一体,意味着我们决不能试图操纵、控制、改变或‘管理’自然的生态系统或者在其他方面干预它们的正常机能。”[13] 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都倾向于整体考察生态问题,在他们看来,整体主义是生态思维的核心特征。德沃尔和塞欣斯在《深层生态学》里说,要“清楚地认识到‘小我在大我中’(‘小我’指人类——引者注),而‘大我’代表有机整体。”当整体面临危险时,“没有一个个体能够获救,除非全体都得救”。[14] 罗尔斯顿并不强调任何一个物种、小生境乃至子系统的重要性,而是要以系统和谐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来考察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生存发展。他坚持的是系统的思维、联系的思维和整体的思维,而不是要在自然界另立一个新的中心来取代原来误认为的中心。他指出,“具有扩张能力的生物个体虽然推动着生态系统,但生态系统却限制着生物个体的这种扩张行为;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员都有着足够的但却是受到限制的生存空间。系统从更高的组织层面来限制有机体(即使各个物种的发展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生存空间,直到‘被阻止’为止)。系统的这种限制似乎比生物个体的扩张更值得称赞。”[15] 221他还为生态整体主义补充了“完整”和“动态平衡”两个原则,强调要以这些原则约束人类的活动、需求和发展,使“所允许的选择都必须遵从生态规律”。[16] 克里考特虽然也借用过“生态中心主义”一词,但同时又强调,这是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不同的思维方法,是“更重视整体性”的方法。[17] 马歇尔指出生态思维“应当是整体的。它应当把个人看作社区的一部分,把社区看作社会的一部分,把社会看作人类的一部分,而人类则是生物社会的一部分,最终是更为广阔的存在共同体。”[6] 460
生态整体主义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是生态危机的现实强迫,促使人们提出这一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保护事实上已经陷入困境,因为如果不能超越自身利益而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终极尺度,人类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保护生态并重建生态平衡,不可能恢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只要是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以人为中心,人类就必然倾向于把自身利益和地方、民族、国家等局部利益置于生态整体利益之上,必然倾向于为自己的物欲、私利和危害自然的行径寻找种种自我欺骗的理由和借口,生态危机也就必然随之而来,并且越来越紧迫。只有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才会有真正的自然保护。
有人批评生态整体主义“与自由主义核心观念背道而驰”,“侵犯了我们生活的最私人化的方面”,颠覆了最基本的个人自由,例如发财致富的自由、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自由。[18] 142这些批评严重地脱离了生态危机的现实,无视生态整体主义产生的语境。个体与整体既是相互矛盾又是相互依赖的,什么时候更多地关注个体和什么时候更多地关注整体,什么时候更多地关注人类和什么时候更多地关注自然,并不是单凭抽象思辨和逻辑推导就能作出正确判断的,提出一种观点必须充分考虑所产生时期和所适应阶段。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在以往还有其进步的历史意义,那么,毋庸置疑,时至今日,作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人类已经极其严重地恶性膨胀了,已经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和稳定,已经极其严重地危害到整个星球和它上面的所有生命的存在了。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危机时期,在这样一种刻不容缓地保护所有生命的生存环境的语境下,还要继续强调人类作为自然整体之一类个体的个体利益,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填充其无限欲壑的所谓利益,还不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其有害性就非常明显了。
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绝不是不可分割、变化和修正的教条。生态整体主义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是主张根据生态承载力限度对其进行必不可少的限制。“自由是可以分割的……如果我们想保存可以剩下的自由,我们就必须限制一部分自由。”[19] 在人类的自由发展直接导致生态危机的情况下,必须限制人类的部分自由。为了自然的持续存在和人类的持续生存,人的有些权利是必须放弃的,至少部分地放弃,特别是要放弃追求无限物欲之满足的权利。限制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某些自由和权利,并不意味着也限制其他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人类要选择的是:究竟是要现存生活方式的自由,还是要未来长久生存的自由?“与对我们的生活、健康乃至存活的巨大威胁相比……对自由追求现在选择的生活方式的强调简直没有任何价值。绿色思想家强调的则是,限制我们追求现已选择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限制,那么自然将会以更残酷的方式来限制。”[18] 146-147
那么,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并确立生态整体主义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呢?人类是否可以做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进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考察问题呢?人类是否能够做到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并以其约束自己呢?和其他生物一样,人具有从自己的角度认识事物并为自身的利益攫取生态资源的本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人类不能、也不该为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考虑和作出牺牲的理由。因为,人是惟一有理性的物种,人“是这个世界中惟一能够用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来指导其行为”[15] 96的物种,人的理性能够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人还是具有同情心的物种,同情心使人类能够超越自身的视野、经验和利益的局限去认识和关怀万事万物。普鲁姆伍德在《人类中心之外的道路》一文里说得好,同情心能够“将我们置于他者的立场上,在一定程度上从他者的角度看世界,考虑他者的与我们自己相似和不同的需要和体验。”这里的他者不仅可以是其他人,也可以是其他物种,甚至是整个地球。正是有了这种同情,我们才可能“扩大自我,超越自身的地位和利益”。[20] 生态社会学家布克钦指出,人类“用概念思考和深深的同情感来认识和体验整个世界生命的能力,使他能够在生态社会里生存,并恢复、重建被他破坏了的生物圈”。[21] 如果人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者考虑,那么,即便在人类社会的范围里,人们也不可能做到超越个人中心、男性中心、白种人中心、欧洲中心。否认人类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与否认人类应当抛弃极端个人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只有勇敢地承担起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责任,人类才真正堪称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高贵、最有价值的生命。如果说人类只能像猪羊那样只为满足自己欲望而生存,那才是对人类最大的不敬。
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二:唯发展主义
学界一般认为,罗马俱乐部在六七十年代首先对“增长癖文化”提出质疑和批判,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25年,利奥波德就批判了经济第一、物质至上的发展观。他把这种发展形象地比作在有限的空地上拼命盖房子,“盖一幢,两幢,三幢,四幢……直至所能占用土地的最后一幢,然而我们却忘记了盖房子是为了什么。……这不仅算不上发展,而且堪称短视的愚蠢。这样的‘发展’之结局,必将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死于过度’。”[22] 利奥波德指出,人类要在大地上安全、健康、诗意和长久地生存,就必须抛弃发展决定论。
生态作家和思想家艾比在20世纪50年代就使用“唯发展主义”来称呼发展至上论,他指出,“为发展而发展”(the growth for the sake of growth)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激情或欲望,却没有人看出这种唯发展主义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23] 在《沙漠独居者》里,艾比再次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言:“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疯狂裂变和扩散。”[24] 在艾比看来,唯发展主义将推动现代文明从糟糕走向更糟,导致“过度发展的危机”(crises of overdevelopment),并最终使人类成为过度发展的牺牲品。[25]
诚然,与任何一种生物都有生存与进化的权利一样,人类作为这个星球的一个物种,自然也拥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生活得越来越舒适,同样也无可厚非。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人对物质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如果再不限制发展,结果只能是加速奔向灭亡。人类不可能脱离生态系统而存活,至少从目前来看,人类开发替代资源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枯竭的速度,加剧环境污染的速度远远高于治理污染的速度,而且,科技的发展也还达不到在地球生态系统总崩溃之前建造出人造的生态系统或迁移到另一个星球的水平;那么,人类目前就只有一个选择: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当然,生态的制约可以是动态的、相对的,即随着人类在开发替代资源、治理污染、重建生态平衡等方面的不断进展,生态对发展的制约可能不断放宽;但制约却是必需的、绝对的。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发展无异于直奔死亡。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就是发展的制动器。
唯发展主义将人类在人性解放、人格完善、安全和诗意地生存、与自然休戚与共、与他人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适度改善等多层面、全方位的进步和完善之需求,缩减成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严重忽视了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发展。莫兰切中肯綮地剖析道:“‘发展’的概念总是含有经济技术的成分,它可以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加以衡量。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技术的发展自然是带动‘人类发展’的火车头。”“‘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计算、量度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或爱情。它唯一的满足尺度是增长(产品的增长,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货币收入的增长)。由于仅仅以数量界定,它忽视质量,如存在的质量,协助的质量,社会环境的质量以及生命的质量。”“‘发展’忽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捐献、高尚、信誉和良心。‘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宝藏与古代传统和文明的知识。‘欠发展’这一漫不经心的粗野提法将人类文化智慧与人生艺术贬得一钱不值。”[26] 6-8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经济发展服务。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过程或手段。其目的是人更安全、更健康、更诗意的生存,更自由、更解放、精神更为充实、人格更加完善。“发展”的目的化,即为发展而发展,必然导致“发展”的自足化和“发展”的异化。“发展”异变成一个对人具有极大压迫力的自足体,必然会要求甚至迫使人为其牺牲最主要的追求、最重要的普适价值和最基本的权利,必然会以“工业的合理化”、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最高化、“都市化、官僚制度化、技术化”等等发展之理,取代人性之理和自然之理。于是,发展“合理化的无度的粗野性”便“在地球上汹涌扩张”。[27] 124-12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世人广泛谈论的“可持续发展”,在翻译和理解上有严重问题。“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翻译成“可承受的发展”。“可承受的发展”的重点在于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其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把这一思想翻译和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就将重点从“限制”转到了“发展”,不但没有强调发展的制约性条件,反而还给人以一种虚幻的可持续假象。唯发展主义有了“可持续”的美名作掩饰便更具有危害性,因为它能够轻易地使人们丧失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理性判断以及对生态整体和包括人类后代在内的所有生命未来生存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生态思想家强调,可持续首先必须是“生态可持续”(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必须“持续地反对生态的不可持续”,因为唯有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存在,才可能有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28] 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思想家莫兰一针见血地指出,“‘可持续发展’,仅仅是生态环境压力下的暂缓发展的一种考虑,并未挖掘发展逻辑的根源。”[26] 7生态哲学家贾丁斯说得好:“可持续的说法太普遍了”,“让我们先停下来”,先问“可持续什么?”“很显然,可持续经常被认为是‘持续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这样的可持续生活模式只是持续现在的状态。但是目前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在消费驱动的工业经济中的消费方式,正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元凶,现在的消费情形正是要改变的东西。……我们要警惕,不要只是简单地把可持续发展当作时髦词来谈论经济和消费的继续增长。”[29]
针对唯发展主义,艾比在《请珍惜生命》一书里阐述了生态发展观的两个主要标志:一是“以开放、多样化、宽容、个人自由和理性为基本价值”,二是“自然界必须被当作平等的伙伴对待”。[30] 生态发展观敦促人们不要把发展局限在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方面,而要向另外两个维度扩展。其一是精神生活的充实丰富和人性人格的解放完善,以及为实现它所必需的社会变革——走向更为公正、更为民主、更加自由和更加和谐的社会。这才是人类发展的真谛。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给人带来更多更大更长久的幸福。其二是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进而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地和谐共处。这是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三:科技至上观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进入了“巨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力量,具备了能够轻易地将整个地球及其所有生命彻底毁灭的威力。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关乎全人类的命运,关系到所有生命和整个地球的生死存亡。于是,科学技术已经不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情,也绝对不仅仅是有权力、有财力操纵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利益集团的事情;人类的每一分子都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监督权和批判权,全体民众具有对科学技术的制约权和改造权。莫兰再三强调:“科学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情,不能惟一地交由科学家来处理。……科学已变得极其危险,不能全凭政治家来处理。……科学已变成了一个国民的问题,一个公民的问题。我们应当诉诸公民们。不能容许这些问题与外界隔绝,不能容许这些问题成为在小圈子内策划的。”[27] 101
文艺复兴以降,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技术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反宗教和倡理性的革新进程,赋予科学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不二法门的重大意义。“人们心甘情愿地称科学为现代的宗教,认为它远比被其取代的诸多宗教要神圣得多。”[31] 5“对很多人来说,从正面来讲,科学‘永远正确’,从反面来讲,‘科学永远不会犯错’,正是这一专断信条使科学容不得半点批评。”[31] 7“科学不仅凌驾于公民之上,也远离了公开的辩论”[31] 47,在制造了大量不可根除的污染和无法挽救的环境灾难之后,它竟然还试图让人们相信科学家“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和技术是万能的”[31] 27。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科技绝对不是永远正确的,科技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罄竹难书,科学万能论和技术乐观主义是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科学依据的自欺欺人的假说。“人们不能采用导致危机的手段来解决危机”,[31] 36人们不能相信在数百年的短短时间里就把人类家园搞得资源枯竭、全面污染、濒临崩溃的科学技术,能够在已经是十分有限的未来时间里引导人类摆脱危机——如果科技自身不进行深刻变革的话。
莫兰指出,“这个释疑的、致富的、征服性的和硕果累累的科学也愈益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带来奴役人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生机勃勃的认识也产生着消灭人类的威胁。”“科学的进步既产生造福的可能性又产生奴役或致死的可能性”;而且,更为麻烦和更为复杂的是,这两种可能性不是分离的而是密切相关的,“科学造福的方面的进展与它有害的或甚至致死的方面的进展相关联”。科学技术有害的方面主要包括:自大狂妄地与自然对立,以违背自然规律、干扰和扭曲自然进程为能事,造成全球范围日趋严重的、难以根除的污染,核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及其应用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等等。除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外,还有一个特别危险的现象,即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被金钱势力和政治势力所左右,“科学家们被完全剥夺了对这些从他们的实验室里产生出来的力量的控制权;这些力量被集中在企业的领导人和国家的当权者的手中。今后在研究和强权之间将有着前所未见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莫兰警告人们:“科学已变成……新的撒旦!”[27] 3,5,95,69
生态思想家还对一些科技工作者缺乏社会责任、人类责任和生态责任提出了严厉批评。卡森“质疑了我们这个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32],揭示出“隐藏在干预和控制自然的行为之下的危险观念”,[33]“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34] 卡森一再强调,科技能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35]。莫兰对当代科技现状的基本判断是“既缺少科学的责任性又缺少关于责任性的科学”[27] 87。全世界的科学家“每年差不多把两百万个小时用于破坏这个星球的工作上,这个世界上有30%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从事着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开发”,“在缺乏伦理控制的情况下,必须意识到,科学和它的产物可能损害社会及它的未来”。“一方面是闪电般前进的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冰川式进化的人类的精神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以世纪为单位来测量的话。科学和良心之间、技术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冲突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它们如果不以有力的手段尽快地加以解决的话,即使毁灭不了这个星球,也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36]
莫兰分析了许多科学家缺乏责任感的根本原因: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的经典科学观念认为,科学从原则上将事实与价值分离,“也就是说从它的内部排除任何伦理学的管辖权;在消除科学认识的主体的基础上建立它的客观性的公设”。科学把“为着认识而认识”当作自己的绝对律令,只要认识,不计后果。这一律令促使科学把任何戒律、禁忌和责任排除在科学之外,于是,“责任性因此是无意义的和非科学的。研究者从原则上和从职业上来说都是不需负责任的。”这种把科学与伦理责任分离的绝对律令,如果说在科学受到宗教政治排挤和威胁的时代还有其正确性和时代意义的话,那么,“在科学处于统治地位和威胁着其他事物的存在的时代就不再是正确的了”,“认为价值判断不适于科学研究活动的思想具有积极意义的时代结束了”。莫兰进一步指出,与社会和自然责任感分离,必然导致科学不能认识自己,“不能科学地思考它本身,不能确定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不能预见它在当代的发展会导致什么——毁灭、奴役还是解放”,造成了可怕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还不知道反省和自我批判。[27] 87-104
人类绝对不能把科学技术置于被监督的范围之外,必须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重审、批判、监督、制约和改造。科学技术头上的光环绝不意味着不受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一切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公民监督的特权。“科学家并不是比他们的同胞崇高、超脱的人。他们有同样的渺小性,同样的犯错误的倾向。”“一些很高超的头脑、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杰出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之外如其他为激情所驱使的好冲动的人一样行动,对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持有与随便哪个公民都一样平庸的观点。有时可悲地看到他们享有很高的威望却传播着错误的见解。”他们自诩超越伦理、超越价值、超越政治,标榜自己“漠视所有的政治—经济的利益,实际上却被后者所利用”。[27] 11,26-27,90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科学技术,就像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权力一样,肯定会失控,肯定会走向专制(科技专制)和疯狂。在高科技具备了将地球毁灭N次的巨大而令人恐怖能力的时代,一旦科技发展失控,它所导致的后果很可能比政治集权的后果更为严重,很可能是整个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毁灭性的灾难!生态思想家莫斯科维奇指出,“过去,人们为科学的自由而斗争,今天,他们应当奋起限制科学的权力。”[31] 47即使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真正的热爱,也要努力限制其权力,使之不至于迷失自己,不至于成为人类生存的威胁。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监督、制约和改造,是对科学技术负责,更是对人类、对所有生物、对整个地球负责。科技必须“绿化”,“绿色科技”才是科技进步的未来。
1988年,近百名一流科学家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庄严地承诺不再参与任何干扰和破坏生态的科技活动,并呼吁科技的绿化。他们要证明科学技术工作者不仅能够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治理污染、开发替代能源等方面作出贡献,而且也能为揭示生态危机的科技思想根源、进而树立生态的科技思想、实现绿色科技作出贡献。
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唯发展主义与生态发展观、科技至上观与绿色科技观之外,生态思潮对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探讨,还包括深入研究征服掠夺与和谐共享、占有与生存、二元对立与整体合一、自然对象化与自然主体化、欲望满足动力与人格完善动力、消费文化与简单生活观、走向现代与回归自然、违反自然规律与遵守自然规律,以及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生态责任与社会责任、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与人类的价值和权利、自然关怀与人类关怀、敬畏自然与有限度利用自然、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征服控制自然与征服控制人等问题。
由此可见,生态视角的思想文化重审、批判、重评和重建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基本问题,它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也还有许多理论上的难点。同时还应当看到,有些生态思想过于偏激,有些则受到其产生环境的局限,并不具有普适价值。不过,从总体上看,西方生态思潮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生态危机是全人类的危机,只有所有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参与,才有可能缓解并最终消除它。面对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系统总崩溃的日趋逼近,盲目乐观、消极逃避甚至末日狂欢都是丝毫无益和极其有害的。即便最终还是不能消除生态危机,人类也必须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至少也要缓解它,至少要延缓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大限的到来。人类既然已经把这个地球弄得满目疮痍、乌烟瘴气、危机四伏,就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就必须义不容辞地重建生态的平衡与稳定。每一个人文学者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不能丧失人类良知和社会使命感;她/他还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的儿女,更不能丧失生态良知和自然使命感。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连同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人文学者怎么能够不直面如此严重并还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怎么能够不反思人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
只要多数人文学者还没有丧失良知和使命感,生态思潮就一定会波澜壮阔蔚为大观。只要这个星球的生态状况依然在总体上持续恶化,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投身到这股洪流之中;只要地球母亲和她的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子孙仍然面临生态灾难的威胁和灭绝性危险,生态思潮就一定会持续高涨。
标签:生态危机论文; 人类中心主义论文; 生态系统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地球质量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科学论文; 生态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