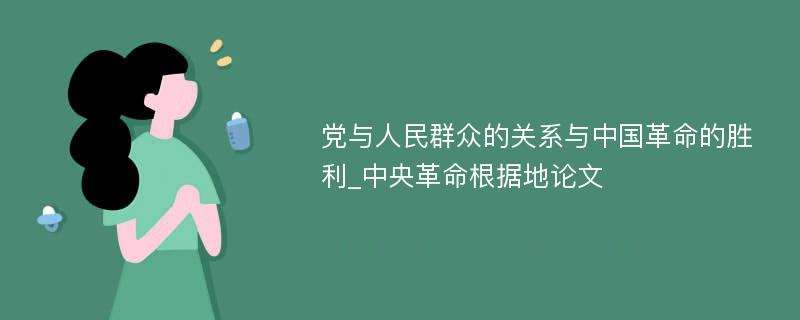
党群关系与中国革命胜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群关系论文,中国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为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14年。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共曾两度遭受严重的挫折,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这两次挫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遵义会议后14年,中共的发展则十分顺利,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遵义会议后中共能发展壮大,最终取得全国政权,自然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最根本的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起因于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顿时退潮,与中共在大革命后期既犯了右倾错误,也存在“左”倾偏差,失去群众的同情与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革命后期中共出现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示在对国民党一再妥协退让。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为了不因工农运动而刺激国民党右派,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强调: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①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②“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③
当时的中共领导机关为了维持国共关系,千方百计地迁就国民党右派,为此不惜给工农运动泼冷水甚至进行压制。可是,在工农运动进入高潮后,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过“左”的做法,又没有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制止。例如,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到1927年1月,全省农会会员已猛增至二百万人,直接掌握的群众达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于是“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猛烈冲击和荡涤了农村的旧有秩序,“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④。但不可否认,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枪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⑤甚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扩大了打击对象。同时,随着北伐军占领两湖地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工人运动也就迅速发展起来。此时,在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过左的做法,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⑥
农民运动中的某些过左做法“容易失去社会的同情,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到不便”。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也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⑦。武汉工人运动中的“左”倾偏差,致使“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⑧刘少奇后来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说:“群众中的‘左’倾现象与领导机关的右倾,结果使群众与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情绪被打落。”⑨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兴起迅速,而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之后又顿时低落,固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运动的残酷镇压,但与运动中那些过左行为失去社会同情亦不无关系。不但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各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致使工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遭受重大牺牲。“左”右倾错误都是对群众根本利益的损害,都会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懂得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相继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建立若干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开始复兴。到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全国红军发展到约30万人,全国党员总数也发展到近30万人。但是,在接下来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却遭受了严重失败,被迫放弃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后来的长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当然与博古、李德等人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不无关系。在经历第一至第四次“围剿”之后,蒋介石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不再使用长驱直入之策,而是步步为营,在根据地周围广筑堡垒,同时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1933年9月,即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作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不懂军事又十分崇拜共产国际,于是李德一到来,就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蒋介石的“围剿”策略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却提出所谓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作战方针。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国民党修碉堡,红军也修碉堡,待敌人从碉堡中出来,推进至距红军碉堡二三百米,红军进行短距离的突击,迅速猛扑上去将国民党军消灭。“短促突击”的战术对于红军来说,显然是扬短避长。“短促突击的结果,使1933年红5月直到1934年9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⑩在国民党军不断地压缩包围下,博古和李德又不采纳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外线作战打破“围剿”之策,使原本善于灵活作战的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最终在中央苏区无法立足只得进行战略转移。
除了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一套“左”倾路线方针政策,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例如,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之下,肃反严重扩大化,而肃掉者大多并非真正的反革命。登贤县(1934年3月,中央苏区为了纪念在白区工作牺牲的罗登贤,划出原于都、赣县、安远、会昌四县的一部分,另设该县)的情况亦是一个例证。当时,“白区的老百姓来畚岭圩卖盐,登贤的干部说他们是来赤色区域探听消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捉起来杀掉”;“捉到嫖妇女的男人,不是采取批评教育,让人家有机会改正错误,而是作坏人杀掉”;“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只要一听是‘AB’团分子,就拿去杀头”;“招待客人在家住宿,也要作坏人论罪”;“有部分群众逃往白区,这些人捉到统统作为反革命分子杀掉”(11)。登贤的情况或许不能代表中央苏区肃反全貌,但此间肃反的严重扩大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土地政策上,将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肉体消灭富农的政策套用到根据地,实行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强调在分配土地中,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富农已分得的土地,应交出来重新分配,好田应当转分给雇农、贫农、中农而把他们的坏田调给富农”(12)。这实际上是不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实际上,中央苏区自开展土地革命以来,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个别地方土地分配不公的问题,稍作调整即可。由于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去查土地、查阶级,这要么就是将已斗争倒了的地主富农再拿出来斗争一遍,要么就是在清查所谓漏网地主富农的名义下,人为地将中农拔高成富农,富农上升为地主,扩大斗争对象,结果出现了“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13);“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14)。仅在查田运动全面展开的6、7、8三个月,中央苏区就查出了“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这些人显然并不是真正的地主富农,严重地扩大了打击对象。
苏区肃反的扩大化和查田运动的“左”倾错误,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其中最直接的是造成苏区群众的恐慌和对革命政权的不信任,破坏了苏区良好的党群关系和民(众)政(权)关系,不但影响到根据地人民对反“围剿”胜利的信心,而且影响到他们对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支持度。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还与根据地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那时“共军坚壁清野,民众悉被裹胁入山,探索未得一人,最后捕获一共谍,佯哑不言,经再三审讯,始供龙冈以东以北山地均有伏兵”。“但苏区遍布共谍,国军行动,均被侦悉,而国军对于共军行动则甚少明了。”(15)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情形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群众产生了离心倾向。例如,于都县在查田运动中“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利用来煽惑群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16),万泰县“发生二千六百群众逃跑”(17),甚至还有“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18)。这与前几次“反围剿”那种密切的军民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不但为根据地群众所反感,也失去全国人民包括中间阶级的同情与支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就势成必然。
遵义会议后,中共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召开会议,顺应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如将“工农共和国”改称“人民共和国”,对富农的土地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用比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随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下,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合作关系,实现了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而事变发生后中共从民族大义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从而停止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号召。在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军队大幅度后撤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却主动开赴敌后,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在经历日伪残酷的反“扫荡”后巩固下来。敌后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坚持抗战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
除了坚持抗战,中共还努力改善民生、发展民主。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中共将土地革命时期执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这是一个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抗日固然是他们的要求,但如果不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不给其一定的物质利益,其抗日的积极性便难以激发,即使激发了也难以持久;对于广大地主富农而言,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作为中国人,多数人也是不愿当亡国奴、卖身求荣去作汉奸,他们也有一定的抗日愿望,但如果延续以往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的政策,又会使其根本的经济利益受损,以至于打消其参与抗日的愿望。减租减息的政策则既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得到了物质利益,也使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没有受损。这一政策的执行,使根据地的民众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共还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例如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广泛的普选制,在1940年晋西北根据地的村选中,一般村庄参加选举的村民达到80%以上,甚至高达95%以上。为了便于不识字或老弱病残的选民参选,各根据地还创造了诸如“划圈圈”、“点豆子”和由选举委员会派人背选举箱上门等办法。“因为农民不识字的居多,所以用种种通俗的办法代替写票,有的地方叫选举做‘烧香窟窿’,那就是用香在被选人的名字下烧一个窟窿;有些地方的习惯,候选人各有一木箱,选举人在他要选的人的箱子里投一颗黑豆,也就算选举;有些地方,则由一个人背一只箱子,巡回到选民家里去请他们投票,这叫做背箱。”(19)为了团结广大中间阶层一道抗日,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还推行“三三制”政策,即在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和各级参议会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主要是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
此外,中共还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工作,尽可能减轻根据地群众的战争负担;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在地方开展拥军优属(抗日军人家属)活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如此等等,密切了中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抗日战争是中共发展史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抗战八年的结果,中共不但在敌后战场坚持下来了,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党员达到120万人,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根据地已有19个,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了近1亿。之所以中共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最根本的是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抗日根据地群众所拥护。
抗战胜利后,中共高举和平民主的大旗,倡导建立各党各派参加联合政府。在蒋介石拒绝和平、决心发战内战的情况下,中共又接过当年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口号,及时启动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获得了解放区农民的坚定支持。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中共明确宣布实行保护民族工商的政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重申,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要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这不但稳定了解放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商业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消除了他们害怕“共产”的疑虑。这就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群众基础。
总之,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取得巨大发展,在解放战争的国共较量中最终打败国民党,最根本的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通过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赢得民心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那天起,就立志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什么时候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认同和真正支持,革命事业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如果路线方针政策不符合群众愿望与要求甚至损害群众利益,革命事业就会受到挫折。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群众关系发展史。回顾中共革命历史,至少能为我们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共产党人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人都始终是少数。抗战之初,全国党员仅三、四万人,这些党员分散到全国,党员与群众极不成比例。经过1938年、1939年两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共党员也只有50万人,即使到抗战胜利时也只有120万人,而且相当多的党员集中在军队。为此,毛泽东一再告诉全党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决不可脱离群众。他指出:“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21)他还说:“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22)树立群众观点,最重要的是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符合实际,需要群众的实际要求。
第二,必须维护群众利益,努力为群众谋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提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23)后来,就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24)“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25)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其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二者缺一,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26)只有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和切实感受到的政治权益,人民群众才真正认可共产党是为其谋利益的,才会认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真心实意地跟共产党走。
第三,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认真听取民意,及时调整方针政策。1940年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1941年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征粮20万担,这虽然是不得已之事,但比1940年征收的公粮9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27)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采纳党外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意见,在各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同时组织大生产运动,局面很快改观。1947年的土地改革在复查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曾一度发生侵犯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乱打乱杀的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这一种情况及时开展纠“左”,强调中农的利益不得侵犯,必须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新解放区停止急性土改,在老区迅速确定地权,结束土改,从而稳定了农民情绪和解放区社会秩序,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
⑤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⑥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⑨刘少奇:《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1942年10月10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版,第707页。
⑩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11)《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450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9—561页。
(13)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14)刘少奇:《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斗争》第34期,1933年11月12日。
(15)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第二篇·江西时期),(台北)京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569页,第574页。
(16)项英:《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红色中华》第168期,1934年3月29日。
(17)转引自张闻天:《人民委员会为万泰群众逃跑问题给万泰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红色中华》第173期,1934年4月10日。
(18)张闻天:《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前面的狂乱?》,《红色中华》第208期,1934年6月28日。
(19)赵超构:《延安一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21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125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526页。
(2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页
(2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25)毛泽东:《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的题词》,《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页。
标签:中央革命根据地论文; 红色中华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历史论文; 根据地论文; 国民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