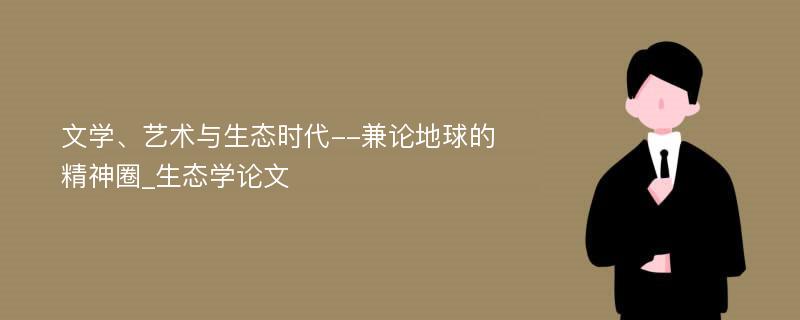
文学艺术与生态学时代——兼谈“地球精神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文学艺术论文,地球论文,精神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面对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种种灾难与困境,现代生态学应运而起。它已远远超出海克尔1866年提出这一概念时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的涵义,不仅是一门学问,一门科学,而成为一套完整的观念系统,包容生命与环境、人类与自然、社会与地球、精神与物质的世界观。以这一世界观为基础形成的生态学时代更注重关系、交往、精神在世界中的整合和升华作用。人不仅是物质性、经济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存在,也是情感性、宗教性、艺术性和精神性的存在。精神在现象上的超越将取代精神在物欲中之沉沦。精神的进化将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
文艺在生态学时代将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它是沟通人类的精神通道。艺术融入生活,人与自然的对立得到缓解,地球上的生态将更美、更有生气。
面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有这样两个悲喜交加的预言:
下一个世纪将是“精神障碍症流行”的时代;
下一个世纪将是“生态学时代”。
文学艺术则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出现的重大而又严峻的前景作出自己的判断。
一
关于第一个预言,日渐深入的生态危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地球上,人类社会中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正在不知不觉中向人类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迅速蔓延。从地球上现实的人类生态状况看,下一个污染,将是发生在人类自身内部的“精神污染”。
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迅速推进,“精神的失落”、“精神的衰败”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其中有惆怅,有痛心,有抱怨,乃至不乏愤怒。
文学家乔依斯在一篇论及文艺复兴的文章中说:“与文艺复兴运动一脉相承的物质主义,摧毁了人的精神功能,使人们无法进一步完善。”“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中化为一滴泪水! ”〔1〕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逝所决定,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2〕。
心理学家弗洛姆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3〕
神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说:“我们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4〕。
系统论的创始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则更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是却在征途中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5〕。
正式提出“精神污染”这一概念的,却是一位生态学家、比利时生态学教授P·迪维诺(Paul Buvigneaud),早在70年代初,他在他的《生态学概论》的最后一章中就明确指出:存在着一种“精神污染”:
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活跃,运输工具越来越迅速,交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于是高血压患者出现了;而社会心理的紧张则导致人们的不满,并引起了强盗行为、自杀和吸毒。〔6〕
迪维诺所说的“精神污染”与我们国家后来谈论的那种作为政治斗争概念的“精神污染”不同,他针对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文明对于人的健康心态的侵扰,物欲文化对于人的心灵渠道的壅塞,商品经济对于人的感情的腐蚀等。当代人的许多精神问题,都是随着社会发展同步俱来的,“精神污染”在这里是个超越了国度、民族、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一个生态学的概念。我国当代小说家张承志不久前写下的一篇颇有影响的散文《清洁的精神》,其实并不是鼓励人们都去做刺客,而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舍身取义的极端例证中,为发热发昏的现代人找回“一种清冽、干净的感觉”,“为美的精神制造那怕是微弱的回声”。其着力点似乎也在于清除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精神污染”。
精神领域内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可能比我们估计的还要严重。西方的科技史学家通常把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划分为三次浪潮或三次震荡。在第一阶段,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造成了森林锐减、草场退化、水土流失、物种消亡,人的外部生存空间受到剥蚀,人类最初开创的一些文明圣地终于随着大地的沙漠化而化为历史陈迹;在第二阶段,随着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的发达,大气污染、水源污染、噪声污染、现代战争、交通事故则给人的机体造成直接的伤害;到了第三阶段,第一、第二阶段的生存危机仍在持续蔓延,新的威胁又卷土而来,随着集成电路、激光电缆、生物工程的开发,电脑、电视、机器人、卡拉OK、 MTV、基因再造、试管婴儿、人造器官等微电子产品、生化产品正滚滚涌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也在日益加剧。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巨大的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引起人类生存的再度危机、再次震荡。这第三次危机,是人类“精神空间里的危机”,这第三次震荡,是人类的一次“脑震荡”,甚至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次震荡”。如同海德格尔时常警告的那样:在原子弹、氢弹毁灭掉人类之前,人类很可能在精神领域已经先毁灭掉自己。
种种征兆已经出现。比如,精神病的发病率一直在随着社会的富裕程度看涨,据统计,我国精神病的发病率已从50年代的2.8‰, 上升到目前的10.54‰〔7〕,而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比如日本,每1 万人拥有的精神病床位是我国的40倍。这是否真的应验了弗洛姆的一句话:“在精神上,现代人比以往病得更厉害”。
二
关于第二个预言,只要看一看本世纪末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一次次聚集在日内瓦、墨西哥城、斯德哥尔摩、里约热内卢热烈地讨论着环境与生态,就不难感到“生态学”显赫的时代色彩。是什么力量驱使如此多的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政体、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亲切友善地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热烈地谈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
那就是地球上的生态危机和与此相关的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生态学(Ecology)在1866年刚刚由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来时,只不过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 一门研究“三叶草”、“金龟子”、“花斑鸠”、“黄鼠狼”的生动有趣的小玩艺。100 年过去了,随着生态危机的日渐酿成,“生态”同时成为人类言语活动中一个显赫突兀的关键词语。“生态学”已远远不仅是一门学问、一门科学,而成了一套完整的观念系统,成了一个包容生命与环境、人类与自然、社会与地球、精神与物质的世界观。
面对严重受到伤害的地球,当代最优秀的哲学家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指向“生存的状态”和“人的状态”,分析哲学开始为自己的逻辑实证感到羞愧;思辨哲学自觉放下了“绝对权威”、“最终模式”的臭架子;现象学无形中懈怠了“把哲学科学化”的热情;各种类型的唯物主义也开始丢开“还原论”的“普遍规律”的条条框框。生态问题开始成为哲学的课题,而哲学话题的转换可能意味着时代的转换。
贝塔朗菲这样宣告: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创的西方文明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的伟大创造周期已告结束〔8〕。新的文明, 将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文明。
如果说已经过去的文明时代的代表是物理学,那么新的文明时代的代表则可能是生态学。生态学与物理学一个很大的差异在于,传统的物理学中并不包含人的因素,人始终是物理学之外的一个观察者、研究者、实验者、操作者,人站在自然和事物的对立面,从自然与事物中榨取对自己有实际用途的东西,通过技术,制造出光怪陆离的商品;通过消费,制造出一个人欲横流的商品社会。在物理学中,自然成了人们“进军”、“攻克”、“占领”、“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处于严峻的敌对关系之中。尤其悲惨的是,人在与自然对抗的过程中,在看似节节胜利的同时,却输掉了原初意义上的由自然赋予人的神性或灵性。而在日益拓展的生态学研究中,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链环,人与蓝天白云山川河流森林草原飞禽走兽昆虫虻蚧在存在的意义上,是平等的、息息相关的,如果有所不同,也只是因为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一个思考者、发现者、参与者、协调者、创造者,因此人的责任更为重大,人将同时通过自身的改进与调节,努力改善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更和谐、更富有诗意的世界。
一则是“精神的危机”,一则是“生存的智慧”,两则预言之间其实存在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获救的希望,哪里有困厄,哪里也就有突围的生路。
人类以及地球如何才能走出生态困境的危途,生态学家、环境学家及其他方面的科学家已经设计过许多出路,比如:提高工艺水平、加强科学管理、开辟新的能源、搞好废物利用等,这些无疑都对缓解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科学家们对于手中操持的科学武器有时也未免过于自信了。比如,有人试图运用生物工程的先进技术将现代人类的体格缩小一半,以减少对物质、能量的消耗;有人试图借助航天技术的力量,有朝一日当地球完全破烂彻底报废时,就把人类集体送往火星、木星之类的外部空间天体上;还有人设想炸毁月球,还有人设想在地球正中穿一个洞……这些设想即便能够实现,也必然同时带来更多棘手的问题。事实也是这样:科学技术虽然在飞速发展,而人类生态系统中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接踵而来。解救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怕是不行的。
面对人类与自然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在环保领域,在生态系统内部能否引进一个新的维度呢?
三
生态学家们喜欢用“多层同心圆”的系统模式描摹地球上的生态景观,认为在这个独一无二、美丽奇妙的天体上是可以划分出许多层“圈”的。“物理圈”,即山川、土地、矿产、空气、水源;“生物圈”,即森林、细菌、昆虫、飞鸟、走兽以及人类;“科学圈”,即科学、知识、工具、仪器、技术;“社会圈”,即政体、制度、司法、教育、军队、议会等。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圈”了呢?
也许,在地球之上,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上空,还悬浮着一个“圈”,一个以人的信念、信仰、理想、想象、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圈”。这个虚悬着的“圈”,该是地球的“精神圈”。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经指出过:在人类社会结构的更高层面上存在着一些“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这些“悬浮于空中的”“精神形式”,是否可以看作地球的“精神圈”呢?
法国社会学家戴哈尔特·德·夏尔丹曾经明确地使用过“精神圈”这个概念。他说,地球上除了“生物圈”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通过综合产生意识的精神圈”,“精神圈”的产生是“从普遍的物质到精神之金”的变化结果,是通过“信仰”攀登上的“人类发展的峰巅”,它体现为“对世界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不朽的信仰和对世界中不断增长的人格的信仰”。夏尔丹的“精神圈”似乎更倾向于“基督教的宇宙幻想”〔9〕。
贝塔朗菲从人类在生物圈内的特殊性出发,则更强调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的地位与作用,“只有有了符号,经验才变成了有组织的‘宇宙’”,人类才有了历史传统和对于未来的憧憬,“符号系统使这个宇宙变得稳固了:‘在悬浮的现象中漂忽不定的东西,在思想中安定了下来’”,这个“符号宇宙”对于人类来说是唯一的,“各种符号世界的进化等同于一个人类‘宇宙’的开创,这个‘宇宙’与克斯屈尔(生物学家)的动物‘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动物‘圈’是由动物的天生的、有解剖学的功能的有机体预先决定的。”〔10〕贝塔朗菲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精神圈”的概念,实际上他已把“符号宇宙”作为人类生态系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独具一格的精神层面。而且,按照贝塔朗菲的说法,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麻烦、许多失控、许多灾难、许多困境,很少与人的“天性”相关,更多地则是由于人类“符号系统”的迷狂与紊乱引发的,也就是说,是由精神层面的故障引发的。
人类生态系统中不能没有“精神”的位置。
人类既是自然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还应当存在着一种“精神生态”。
我们在此之所以如此强调“精神”在人类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因为科技时代的“精神问题”并不会随着科学技术向着尖端的发展而自行消失。如果生命的价值、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理想和信仰都已经衰竭,那么,无论是原子能发电站或电子计算机也都搭救不了我们。多年前,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谈到,解救现代人类困境的“钥匙”,不仅只在于技术上的尝试,也不是“单靠改革一种社会体制或机构便能立刻解决的”。“人们首先应该从进一步探讨构成自己行动准则的价值观念本身着手”,“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其实质就是人性本身的革命”,“唯一有效的治愈方法最终还是精神上的”〔11〕。
从现代物理学研究中频频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新一代的物理学家已经开始向生态文明靠拢,他们在一个更宏阔的世界或一个更幽微的世界里发现了人与物的密切相关性。一位名叫基特·派得勒的电视剧作家说,他发现像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狄拉克这样一批现代物理学家,当他们面对世界时,并不是冷静的局外人,而是一些富有想象力、富有诗意、笃信宗教的人。正是他们把“精神”引进现代物理学的视野里,把精神看作现代物理学舞台上一个必不可缺的重要角色。
与物理学时代的重技术、重物质不同,生态学时代更看重的是关系、交往,更看重精神在世界中的整合、升华作用。人们在生存的困境与危机中开始承认,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经济性的存在、政治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也是情感性的存在、宗教性的存在、艺术性的存在、精神性的存在。在生态学的时代里,精神在现象之上的超越将取代精神在物欲之中的沉沦,精神的进化将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精神这一内在的尺度将冲破物质的牢笼,同时作为人类世界的支撑点,到那时人们才会突然感悟到,“人的生存原来是作为一种精神来确保自由和永生,去克服自己限定者的限定作用的”〔12〕。这就是说,人类向自由世界的飞升,主要凭藉的还是那精神的羽翼。
四
“平衡”,至今仍然是生态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然而,地球上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早就从人类学会使用工具那一天被打乱。一些生态保护激进分子曾经指出,一切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这并不全错,然而并不能因此将人类驱逐到地外空间。重新整合生态平衡的想法类乎梦幻。对于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个问题更加麻烦,因为我们既不能停下经济发展的步伐,又不能听任生态环境的恶化;既不能无视国民道德的沉沦,又不能退回传统伦理的子宫。如何才能摆得平?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生态平衡要走出进退维谷的境地,就必须引进一个“内源调节”机制,在动态中通过渐式的补偿,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而这个“内源”就是“心源”,就是人类独具的精神因素。人类的优势,仍然在于人类拥有精神。
精神领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方面,按照通常的说法,“宗教”、“哲学”、“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最高层、最集中的体现,位于所谓“人类精神三角形”的顶端。
为了拯救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精神文化界也曾设想过一些门路。比如,有人希望给东方人接引过来一位蓝眼睛的上帝,有人则希望给西方人介绍一位禅宗的佛祖。其实,更具世界意义、更易为世人接纳的精神通道,应该说是文学艺术。
我忘不了1987年的秋天,著名诗人作家王蒙在意大利第13届蒙代洛国际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讲话时迫切的发问:“诗歌是否还有能力挽救蓝天绿树,是否还有能力挽救我们同时代的心灵?”那时节我恰恰也在意大利,我看到万神殿里的诸神与威尼斯桥头的但丁,对此发问都是满脸的游移。文学和艺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都曾经是人类生存的“绝对需要”,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然而也正是这位黑格尔做出的断言,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里将日趋解体,因为市民社会、工业社会的一般状况对于文学艺术的存在是不利的。这或许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走过的道路上的部分事实。然而,这并不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文学艺术自身的必然结局。我国著名学者薛华先生在他研究黑格尔这一艺术难题的专著中,曾引述海德格尔的话说:关键在于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自私,他们更勇敢,更有意志,并且能够看清对人的本质的威胁。这是一些敢于达到深渊的人,他们颠倒对世界整体的背离,使对象内化,转向自然”,这样一些敢于言语的人,便是“诗人”、“歌者”。“正因为时代现在是个贫乏的时代,所以会有一个‘未来’,而艺术和艺术家也就负有非同寻常的使命。”〔13〕
“道在途中”,一切还都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文学家与艺术家应当首先振奋起来,成为这个精神贫乏时代里的“更敢为者”,敢于拯救大地,敢于挽回人心,乃至敢于扭转一个时代的偏向。
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
现代社会里,随着印刷复制技术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占有的“艺术品”似乎越来越多,从街头雕塑到饭店的壁饰,从舞台时装模特到精品屋里的小摆设。但人类拥有的“艺术精神”却越来越稀薄。文学艺术不仅有实用的一面,文学艺术不只是一种游戏娱乐,文学艺术还是人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精神需求,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一种人类生命活动辉煌灿烂的景观。文学艺术也不是某些天才人物的专利,从创作心理学的意义上讲,当你心头泛起一层审美的激动,涌出一股清新的诗意时,你就是一位诗人、艺术家!
文学艺术与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
从本体论上讲,文学与艺术之花总是植根于大自然的泥土之中的。
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远离自然的原野,四周全是砖石,没有了风中的树林,没有了林中的飞鸟,没有了河里的游鱼。花木被栽到盆里,飞鸟被关在笼里,游鱼被装在缸里。作为宠物的小猫小狗只不过是华丽客厅里的一种摆设,真正的城市生物群落,除了人,只剩下苍蝇、蚊子和老鼠。都市里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旅游?或许正是渴望从大自然中寻回生活中的诗意、审美中的情趣。托尔斯泰在小说《复活》的开头一段便恨恨地对城市进行了严厉地谴责:“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不大的一块地方,千方百计把他们聚居的那块土地毁坏得面目全非”,在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看来,大地的沦丧与人心的沦丧是同时降临的。
艺术的生殖力得之于大地的生殖力。刘勰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可以看作我们先人的遗训。“向你致敬,大地母亲!”则是古希腊诗人荷马虔敬地唱出的“颂歌”。“生态学”(Ecology )这一概念的希腊文oicos原意中含有“居所”、“区位”、 “环境”的意思。惯常的解释,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群落的生境聚居地的学科,研究生物体彼此间及其与环境之间交互关系的学科。生态学的这一概念,使我想起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栖居”(拉丁文为colcrc),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体系中,这是一个极富生态学意味的诗学命题。“栖居的本质特征是解放、保护”,这种栖居的保护是四重的:拯救大地、顺应苍天、祈盼诸神、正视人生。“栖居通过把四重整体的在场带到万物中来对它进行保护”,“栖居是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14〕“栖居”显然也应当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而“生态学”同时应当被接纳进诗学的领域。
从思维方式上讲,文学艺术活动中运用的那种形象的、情绪的、直觉的、感悟的、模糊的思维方式,恰恰可以弥补科学技术思维活动中的抽象性、单一性,从而滋润丰富着人的心灵。如果说科学思维曾长期被用作向“大自然进军”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利刃,那么艺术思维则有可能成为熨贴抚慰大自然累累创伤的女神。
在《超越语言》一书中,我曾经说过,人类的思维曾经在原始的幽晦不明的状态中持续了许多万年。后来,思维便在语言的层面上出现了第一次岔道:一条道路的路牌上标写着“心灵性”、“情绪性”、“意象性”、“游移性”、“模糊性”、“直觉性”;另一条道路的路牌上则铭刻着“实证性”、“理智性”、“概念性”、“稳定性”、“确切性”、“逻辑性”。一是艺术思维的语言,一是科学思维的语言。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和利益,科学思维也日益增值、倍受人们推崇,而艺术思维渐渐被当做原始落后幼稚荒谬的思维遭到忽视冷遇。这种偏差甚至表现在人们对人类左右大脑半球的命名上:主管概念推理的左脑半球被誉为“优势半脑”,主管情境直觉的右脑半球被贬为“劣势半脑”。人类的作为整体存在的大脑被人类自己割裂并且片面地发展了,我们的教育观念是左脑型的,我们选拔人才的尺度是左脑型的,已经在各个领域普及推广的计算机也是左脑型的,在这个问题上,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统统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左派幼稚病”。这也是酿成地球上生态危机的一个思维机制方面的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偏颇将会给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带来灾难性的“脑病变”,“开发右脑”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发右脑”的最佳方式还应当是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及鉴赏活动。为了文学艺术的创造我们必须开发人类的大脑活动,从而丰富人类的本真的心灵,涵咏人类美好的天性。当人类具有一颗本真的心灵一片美好的天性时,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许就指日可待了。
从能量消耗上讲,文学艺术的生产可能比任何一种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消耗的能量都少得多。而一个“文学人”在物质和能量方面的消费则比任何一个“工业人”、“商业人”的消费要节省得多。
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对于外部物质生活总是较少地依赖。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没有乘小轿车、没有排放一路的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并不影响他留下一路优美诗篇。托尔斯泰,为全世界的几代人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食粮,自己到头来只是一袭布袍、一根拐杖,随风化解在俄罗斯的田野树林间。丹麦的那位克尔凯郭尔,没有上过高速公路,没能睡过豪华宾馆,一辈子孤独地静观着自己的内心,却为“存在主义哲学”开挖了历史的先河。曹雪芹喝稀粥、吃咸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照样写出千古绝唱《红楼梦》,创造的精神财富不可计量。而在高度工业化、商业化的美国,一个普通公民一生中的消费,据有关部门统计,为:60000公斤汽油、7000公斤煤炭、500000公斤石料、5100 公斤塑料、19740公斤钢铁、700公斤铜、350公斤锡、300公斤锌、1500公斤铝、26000公斤谷物、8468磅肉类、17500个鸡蛋,还有115双鞋子、250件衬衫、750个电灯泡、28600个易拉罐,与此同时制造11000公斤垃圾。 这样一位现代工业社会公民的消费标准可能是曹雪芹、托尔斯泰们的千百倍,然而,这位公民究竟又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奉献出多少创造呢?当然,我们不可能把现代人拉回原先时代的生活中去,但你不能不承认,“诗意地存在”这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着的生活方式,一种真实存在着的生存智慧。人类在诗意的生存中对于自己精神生活的内开发,将减缓人类生存对地球的压力,有利于地球的休养生息。
若是从生产投入看,生产一只易拉罐消耗的物质能量不知要比印刷一首诗歌消耗的物质能量大多少倍。但是,现代人宁愿一箱又一箱地品尝那些内容不详的罐装饮料,而无心去欣赏那些诗坛上盛开的精神花朵。饮料的消费是“一饮而尽”,随手一扔则又多了一份垃圾;诗歌的“消费”决不是纯粹的消费,则必然是一种精神的再创造,一册在手时读时新。“罐装饮料的消费”可以说是一种“高物质能量的低层次运转”,而“诗歌的消费”则是一种“低物质能量的高层次运转”。在能源如此紧缺的今天,我们不能说服人们少喝些“饮料”,多读些“诗篇”吗?
从价值意义上讲,审美愉悦差不多是人类能够体验到的最丰富最强烈的愉悦。在一些文艺心理学的著述中曾经具体描述过文艺创造及文艺鉴赏中产生的那种生理—心理层面上的快感:“耳聪目明、浑身清爽、呼吸顺畅、精力饱满、激情冲荡、心绪昂扬、神思勃发,充满了精神上的优越感和接近于骄傲的自信心”,神魂颠倒、灵感迷狂、似梦非梦、如痴如醉、甜蜜的颤栗、美妙的震撼……人的整个机体、感官全部投入艺术之中,心脏的跳动、血液的流动、呼吸的频率、肌肉的张弛随之变化,压抑的心情因此得以畅开,精神的懈怠因此得以振作,淤积的块垒因此得以排遣,机体的不适因此得以化解。1987年11月12日,文森特·梵高的一幅《鸢尾花》在美国纽约卖5390万美元、然而,这还不是梵高作品的最高售价。1990年5月,梵高的另一幅画《加歇医生肖像》, 被一个日本大亨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购去。两幅画的画布、颜料加在一起不值两个美元,其余全是梵高艺术精神的价值。然而,梵高的艺术精神只值这上亿美元吗?或许更多,或许根本无法用金钱换算。画商可以用亿万美元收购梵高的作品,却不能拥有梵高创作这些作品时的心境和体验。梵高在世时一贫如洗,然而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却拥有这么多的真、善、美,拥有一座五彩缤纷的精神乌托邦!梵高又是最富有、最幸福的人。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下一个世纪里,艺术将融进我们的生活,诗意将化入我们的生命,人类的个体将得到全面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对立将得到缓解,人将变得更优秀更丰富更卓越,地球上的生态景观将变得更健全、更美丽、更加朝气蓬勃。如果不是这样,人类不就太愧对“地球—生命”这一宇宙的伟大奇迹了吗?
五
按照新一代物理学家的说法,整个宇宙都是一个不断膨胀收缩着的球形体,没有直线,只有曲线,时间与空间都可以是弯曲的,那么人类社会能够一往直前地发展吗?近两百年来,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强有力的推动下,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直线运动,突然撞到了“生态困境”这块难以逾越的岩石上,人类社会是否已经到了必须“就地转弯”的时候了呢?
一位叫E ·拉兹格的美国社会学家曾经在他的《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一文中谨慎地标识了人类社会可能出现的“转向”:
过了现在这段杂乱无章的过渡时期,人类可以指望进入一个更具承受力和更加公正的时代。那里,人类生态学将起关键的作用。
在人类生态学时代,重点将转移到非物质生活领域中的进步。这种进步将使生活的质量显著提高。〔15〕
稍晚一点,1986年8月25 日在瓦尔纳召开的“生态学与和平”国际理论讨论会上,在大会发布的《呼吁书》中强调:“要把生态学方法引进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
人类的“生态学时代”果真就要到来了吗?
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在《现代化与协商一致》一文中,则充满激情地进一步谈到“美学原理”在生态学时代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无足轻重的事件可能会决定时代的命运:“美学原理”可能有一天会在现代化中发挥头等重要的历史作用;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这些都是有关未来环境整体化的一种设想,而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知识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16〕
文学艺术以及文学艺术家终究还是不能脱离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文学艺术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态学时代,生态学的观念、理论、方法如何走进文学艺术的创作、研究中来?应当说这是文学艺术在新旧世纪之交遭遇到的一个意义重大且饶有兴致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正在转型,正在从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从严格的计划性经济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社会转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型的、大众消费型的工业现代化社会。这一转型应当说是已经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显著成绩。然而,我们不能不从一个更大的构架中细心察看:西方的社会也在转型,整个人类社会也可能正在转型,正在从经典的发展模式转向新的发展模式,从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渐进转入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从工业型社会转向生态型社会。
如果说中国社会目前正在进行的转型尚且带有某些“补课”性质的话,那么,西方社会面临的新的转型难题则给中国乃至发展中的东方国家提供了一次“超越”的机遇。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或汉文化圈中某些曾经被认为是历史的包袱、因袭的重担的东西,则有可能成为营造新型社会的精神文化方面的契机,比如:传统的哲学思想、传统的价值观念、传统的思维模式、传统的人际关系等等。其中,自然还应当包括传统的文学艺术。
在人类生态系统的“精神圈”中,文学艺术无疑是一道色彩奇妙、魅力无穷的光环。
瞻望即将到来的“生态学时代”,东方不应当自卑,东方的精神文化不应当自卑。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界应当首先振奋起来。
注释:
〔1〕詹姆斯·乔依斯:《文艺复兴运动文学的普遍意义》, 载《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第6期。
〔2〕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 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3〕Erich Fromm:The Some Society,New York,1955。
〔4〕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5页。
〔5〕冯·贝塔朗菲:《人的系统观》,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第19页。
〔6〕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1974),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7〕见《中国检查报》1993年5月29日。
〔8〕冯·贝塔朗菲:《开放系统论与人类社会、 人文科学系统》,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7年第2期,第71页。
〔9〕转引自G·R·豪克:《绝望与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10〕冯·贝塔朗菲:《人的系统观》,第85、91页。
〔11〕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49页。
〔12〕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13〕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14〕海德格尔:《诗·语言·思》,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155页。
〔15〕E·拉兹格:《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 载《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0期。
〔16〕J—M费里:《现代化与协商一致》,载法国《神灵》,198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