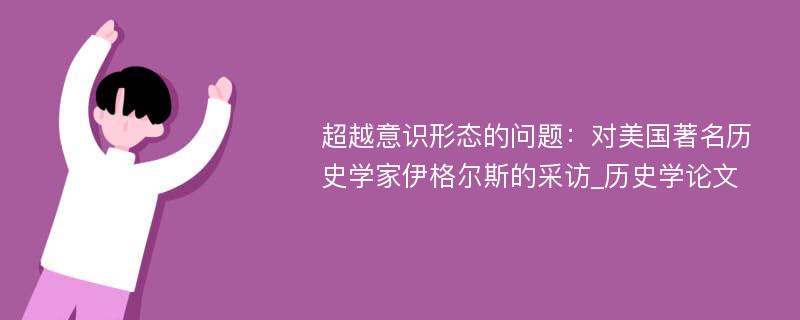
超越意识形态的追问——访美国著名史学家伊格尔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访美论文,著名论文,伊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您一生参与了很多社会政治活动,比如小石城案、南方民权运动,芝加哥反越战运动,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冷战的对抗依然存在,您还非常积极地组织了史学史的国际研究会,与东西方历史学家讨论问题。这是一种跨越意识形态分野的尝试。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您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
伊格尔斯:我坚定地相信存在着对一切社会都行之有效的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价值。所以我参加了民权运动,也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所以我参与了反越战的运动。我不信仰暴力对抗,而信仰和平手段。在战争中我曾对几百名反战人士提出过建议。我总是感到在我的学术工作中有一种伦理承诺。那种认为历史学家应当只关注文献、要避免政治立场的看法,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历史写作都建立在某些价值设想之上。历史学家可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些价值假设仍然塑造着他的史识,并且为他的历史写作抹上色彩。历史学当然要求严肃的研究和诚实。一切历史学家都受到哲学和伦理假设的指引,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无视历史真实。过去历史学家常常过多地服膺于支持种种历史神话,而且历史学曾被独裁国家用于支持那些很少有事实基础的意识形态。历史学不能超然物外,可又要是诚实的;历史学一定不能变成一种宣传的工具。至于人际间的交往,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学问超越了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线。
记者: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您长于史学批评,在您的史学生涯中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某些史学家的影响,从马克斯·韦伯,到詹姆斯·路德·亚当斯(James Luther Adams)、兰克、卡尔·波普尔、马克思。您对他们有什么独到见解呢?
伊格尔斯:在我的一生中,不只一位学者影响了我。我阅读了大量社会学和哲学作品,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没有一位思想家完全符合我的立场,虽然他们在智力上帮助了我的发展。我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一位是具有决定性的。我不仅曾经学习过韦伯和特尔慈,而且我在《德国的历史观》中,从批判的角度详细地讨论了他们的思想。韦伯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试图将自然科学的逻辑与人文科学的逻辑连接起来。我最要感激的学者是我的老师詹姆斯·路德·亚当斯(James Luther Adams),一位神学家,他深深地沉浸在20世纪早期的德国思潮之中,这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恩斯特·特尔慈(Ernst Troeltsch)以及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
在美国,兰克被理解为科学史学之父,他本质上是一位实证主义者,认为基于经过批判性检验过的文献,就可以把历史写成“实际发生的历史”,避免任何哲学的预设或道德的判断。兰克历史写作的思想背景被误解了,他植根于德国唯心论,德国唯心论哲学塑造了他的历史学,超越了尊重事实的精神。而美国历史学家正是因为认为他尊重事实,才在1885年他去世前不久,授予他新成立的美国历史学会的首位荣誉会员资格。
历史学家可能在有限的假定和学说之上建立一门经验社会的或历史的科学,只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卡尔·波普尔曾经认识到这一点,但也对轻易下结论发出了警告。他强调一切具有科学有效性的命题都必须用它们可以被证伪的形式来表达。波普尔和亨佩尔制定的覆盖定律的问题是,它不容易用于解释构成人类历史的那些目的和意志,这些目的和意志无法用覆盖定律设定的因果关系术语来加以理解。波普尔思想的另一方面是对的,他警告历史学的思辨哲学以及这些哲学所服务的政治目标,但我不认为他对所有的国家干预或计划的彻底拒绝是对的。
记者:马克思在中国一直有很高的思想地位,如今,西欧很多国家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您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思想?
伊格尔斯: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社会充满活力且有用的一种重要思想传统。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为形成一门分析的社会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基于两点原因,我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有重要意义。第一,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早于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以及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转的。第二是他的批判笔记,他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功能失调,而且指出资本主义以人为代价,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牺牲人的价值的商品拜物教。但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局限。从目前的观点看。他所预言的事情大多有不同的发展。他看到了资本的世界性集中,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对于这一趋势,他的看法有点简单化。他正确地指出了经济力量的社会影响,但是对于其他也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如思想、文化和宗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也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民族主义的负面因素。实际上,19世纪的发展与马克思的预言是不同的:他和恩格斯所期待的共产主义革命,发生在不发达国家而不是在发达国家。根据他的过于乐观的历史哲学,世界应该走向人类解放和冲突终结,而世界亦没有如此发展。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代社会充满活力和有用的一种重要思想传统。他关于进步的想象已经废弃了,他的阶级概念太过简单,无法解释社会的复杂构成。但是,现代化的鼓吹者们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视为历史的高点和终结,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主张,他们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这种剥削在今天达到了全球范围。特别是在前殖民地世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光明的资源,而且也是批判资本主义给它所造就的世界带来的后果的资源。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条的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属于过去,但它的核心部分,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强调资本主义对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力量、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就无法存在这一事实,都仍然有效,仍然被很多不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在现代条件下仍然继续马克思主义者的承诺的声音所接受。
记者:后现代主义声称,历史学是一种文学的形式,它根本不是一项科学的事业。不存在历史的真实,只有虚构。您认为,历史学是一项科学的事业吗?有历史真实吗?历史学家能把握真理吗?
伊格尔斯:现代的专业历史学研究起源于19世纪普鲁士的大学。历史学家声称,他们已经把历史学提升为一门科学,虽然是一门人文科学,但是它忠实于客观现实,摆脱了偏见。德国模式被大量地接受,因为国际历史学体制的专业化跟随了德国模式。我在《德国的历史观念:从赫尔德至今的历史思想传统》中驳斥了德国专业史学的这样一种论断。即它是不偏不倚的、科学的史学。我力图证明德国史学参与构建一个民族的,或者说相当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试图寻求一条有别于西方民主的能实现带有半独裁性质的制度和价值的现代性德国道路;也批评了德国的历史相对主义,它否认存在着评价历史制度和政治实践的普世人权标准。在美国,这本书主要被视为一本学术著作。而新一代德国人开始对德国的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进行批判性的重估,他们理解这本书的政治方面的性质。
海登·怀特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主要鼓吹者,我多年以来一直与他交换意见。后现代主义断言,历史学是一种文学的形式,根本不是一项科学的事业。不存在历史真实,而只有虚构。这对我刚才说的那些思想是一种极端的反面陈述。“科学的事业”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它意味着像自然科学一样地探寻因果规律的科学,那么历史学当然不是一门科学。我同意海登·怀特和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说法,每一个历史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叙述性的。但我不同意他们的另外一些说法,即历史学仅仅是一种想象的形式,是虚构的文学,历史学的陈述无法得到验证。真理,当然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术语。我相信,存在着一个过去的历史的真实,那是曾经生活过的男人和女人的事实;但是对过去的重构从来就不是完美的,而是反映着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和他们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来自文学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拓宽了过去曾被忽略的那些课题范围,如历史、女性、少数族裔、边缘人群以及人口的广泛的部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化主义和语言学转向将历史学和文学等同起来,又伤害了严肃的历史研究的种种努力。
记者: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您认为历史学可以做些什么?全球性史学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
伊格尔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历史研究增加了全球化特征,没有排斥后现代主义提出那些新研究课题,而是回过头来用更严格的方法论来处理全球化世界,这个世界既在全球化,又在抵抗着全球化。
今年,我与王晴佳合作完成了一部关于全球史学的书《全球近现代史学史》。我们尝试研究18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和非西方历史思维和编史的交互作用。我们对西方化的影响以及对它的抵抗感兴趣,也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存在及其力量感兴趣。一部完整的史学的全球史是可能的吗?我的回答是,史学的全球史是可能的,完整的史学的全球史则可能性小得多。
我对21世纪的希望很简单,期望一个更健全的、更人性的世界,战胜了暴政、战争和贫困,人类有尊严地活着。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乌托邦。因此,经历了我们这个世纪之后,我对世界的期望非常悲观。但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应当消极被动。对年轻学者,我鼓励他们具备全球眼光,要了解发生在国内外的当前史学研究,参与、学习、贡献于国际性的讨论。
标签:历史学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美国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