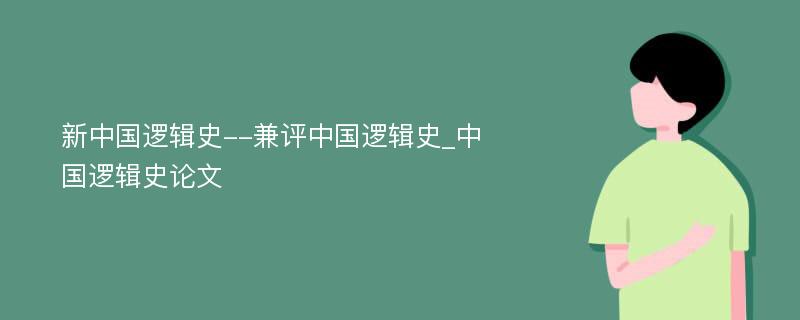
一本有新意的中国逻辑史——评《中国逻辑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逻辑论文,一本论文,新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一股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在神州大地波澜叠起。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也不例外,专著和学术论文越来越多,学术成果硕果累累。这股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也许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在西风大举东进的形势下的寻根心态在文化层面的反映。当然,任何民族,尤其是曾经拥有过骄人的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的民族,都会以先人的光辉业绩来鼓舞后人。
在这股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潮流中,张忠义先生所著的《中国逻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版)确实是一本颇有新意的学术著作。在该书中,作者不但对中外逻辑史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更着力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比较研究中,张忠义先生不但发现了在中国名辩与古希腊逻辑、古印度因明的异中之同,更重要的是,也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的同中之异,从中勾勒出中国逻辑的独特的魅力。作者处处运用比较方法,站在现代逻辑的高度,发掘出了许多中国逻辑史中被人们忽略了的宝贵思想,取得了崭新的学术成就。具体说来,以下几点尤为突出:
一、逻辑形式是从语言形式中概括出来的。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很不发达,但是,这并不妨碍古代先贤运用抽象的方法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讨论思维的逻辑形式(及逻辑规则、规律)。张忠义先生在众多典籍中探颐索隐,钩深致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名辩尤其是墨辩中已经以“彼”、“此”、“之”、“然”等表示逻辑变项,以“且”、“或”、“若,则”、“不可”、“非”等表示逻辑常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墨家是如何表述和论证矛盾律、排中律等对思维具有不安意义的基本规律的,研究了名辩学者是怎么运用这些逻辑常项和变项来讨论其它逻辑问题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值得称誉的发现。因为,中国文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因此,中国的先贤们不可能以拼音文字中词的开头字母作为略缩语,进而使之普遍化来表示逻辑变项,但这并不妨碍这些贤哲们以其它方式,例如以具有普遍性的名词或代词来作为变项探讨逻辑问题。我们不能独断地认为,只有“S”、“M”、“P”,“p”、“q”才是逻辑变项,而“此”、“彼”、“之”、“然”等就不是逻辑变项。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矛盾律和排中律时,并没有如现代逻辑那样使用逻辑常项和变项构成的公式,而是使用自然语言,例如,他对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表述就是:“所有第一原理中最确实的原理是:同样东西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事物”,“在矛盾的两部分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东西的,对任何一个事物必须肯定一种东西或否定一种东西”,“对每一事物不须肯定或否定”,“事物不能同时存在而又不存在”等等。“东西”、“事物”都是任指的、具有普遍性的变项。只有在三段论的形式理论中,亚里士多德才运用了字母作为变项,表述三段论的形式。当然,这是逻辑学中的一次伟大的革命,由此树立了古希腊逻辑的丰碑。无可否认,在思维形式的符号化方面,古希望逻辑留给后人的东西更多,更值得继承和发扬。但是,中国逻辑史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式用于表示普遍性的逻辑变项,这却是无容置疑的。张忠义先生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在思维的形式尤其是推理的形式方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无疑是人类逻辑史上值得称颂的成就。但是,三段论是建立在划分基础上的简单词项的类逻辑。而在中国逻辑史上,墨家的“侔”式推论在对形式结构的刻画方面虽不如三段论理论,但是,“侔”式推理却是关于复杂词项的类逻辑理论。而这种复杂词项的类逻辑,用现代逻辑的观点看,是建立在“映射”理论上,进行复杂的逻辑运算后形成的类逻辑理论。因此,两点各有自己的优点,也各有自己的不足。但总的来讲,“侔”式推论无论在推理形式的刻画方面,还是在推理规则的表述方面,确实不够形式化,然而,在逻辑理论的深度即它研究了更为复杂的推理方面,却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更何况只有在19世纪才出现的关系逻辑,在古中国名辩中已有萌芽,这更值得大书特书了。而张忠义先生即事穷理,还历史本来面目,确实是有独到之见。
三、对中外推理理论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张忠义先生指出,三段论是建立在包含于关系上的推理,而因明的三支论式则是建立在真包含关系上的推理,而这两者都是关于简单词项的类逻辑。可是,三支论式是省略了一个前提的四段推理,“侔”式推论则是二段推理。与三段论和三支论式相比,“侔”式推论是关于复杂词项的类逻辑。这些看法,突破了前人所谓的三者只是外在顺序不同,实质上都是三段论的旧说。这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真知灼见,确实难能可贵。
在这本专著中,还有许多令人称道的成果,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启发的,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对于一本探索中国逻辑史的学术著作,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由于研究角度不同,或者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学术界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进行商榷。例如,对张忠义先生提出的“侔”式推论的作者采用了跟“彼”、“此”有相同或相近含义的“是”、“然”来作为“侔”式推论的元逻辑变项,本人就持有异议。具体地讲,在“侔”式有效式和非有效式的元逻辑的断定规则中,“是而然”这条规则断定了如果肯定(采纳、同意、接受、“是”)具有“S、P也”形式的前提,就必须肯定(采纳,同意、接受,“然”)具有“R”S,R“P也”形式的结论,“不是而不然”这条规则断定了如果否定(“不是”)了“S,P也”形式的前提(即“S,非P也”),则必须否定(“不然”)具有“R”S,R“P也”形式的结论(即“R”S,非R“P也”)。在这两种有效式中,如果对前者肯定(“是”)前提而否定(“不然”)结论,对后者否定前提而肯定结论,不然会导致逻辑矛盾。而在“侔”式推论的排斥规则中,“是而不然”则断定了肯定(“是”)前提“S,P[,1]也”,却不能肯定(“不然”)结论,“R”S,R“P[,2]也”,肯定前提到肯定结论,不然会导致非有效的推理,因此,墨家就在结论中加了一个“非”字,从而取消了推论关系。因此,“是”“然”,“不是”、“不然”是对前提或结论的肯定或否定,是对作为前提式结论的命题的一种态度,不能把它算作元逻辑变项。作为元逻辑变项,有一个困难,即它的值是哪个逻辑变项?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是可以和张忠义先生探讨的。类似的观点,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尽管有些观点可以商榷,但是,张忠义先生的这部《中国逻辑史》,材料翔实,立论严谨,具有许多新颖,独到的学术观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我们期望,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面,应当如张忠义先生这样,既要不拘泥于前人的旧说,大胆创新,又要材料翔实,即事穷理;既要发前人之所未发,又要立论严谨,具有科学性。果能如此,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当会出现一片百花盛开、斗紫争妍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