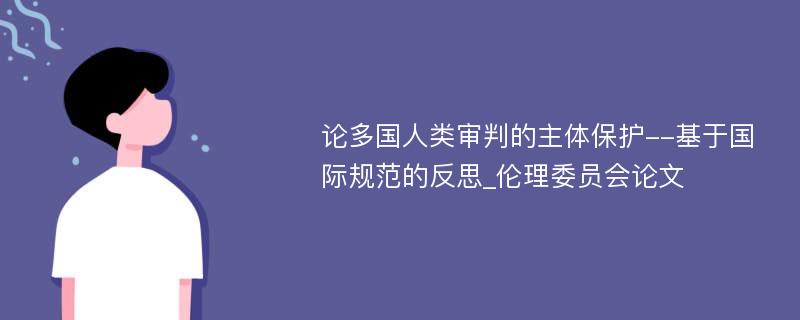
论跨国人体试验的受试者保护——以国际规范的检讨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受试论文,人体论文,基础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7月,跨国制药巨头美国辉瑞(Pfizer)公司与尼日利亚卡诺州政府,就1996年进行的抗脑膜炎药特洛芬(Trovan)试验造成的损害,达成了数额为7500万美元赔偿协议。当年,辉瑞公司在尼日利亚卡诺地区进行了据称治疗脑膜炎疗效显著的特洛芬的试验,约200名病童接受了试验,11名病童因药物反应死亡,19名病童丧失了听力和思考能力。2007年5月,卡诺州政府将辉瑞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20亿美元。双方经反复协商终于达成协议①。这一事件,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跨国人体试验受试者保护的关注。
一、跨国人体试验的激增及其法律和伦理争议
人体试验即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医学试验(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指在生物学、医学领域内,以自然人作为试验的对象,以验证科学推理或者假定为方法,进行新药物、新医疗设备、新治疗方法试验的研究行为。跨国人体试验是试验发起人在本国之外发起进行的人体试验。近年来激增的跨国人体试验,引起了法律和伦理的重大争议。
(一)跨国人体试验激增的成因
1994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放弃了新药试验数据必须在美国国内取得的规定,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研究机构和医药企业将人体试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②。2003年,辉瑞、葛兰素史克和阿斯特拉捷利康先后宣布将在印度建立其全球临床试验中心,并将大量人体试验转移至印度、波兰等国家③。葛兰素史克、惠氏等世界医药巨头预计今后他们半数以上的人体试验将在国外进行④。
跨国人体试验激增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主要为以下几点。第一,客观需求。医药企业在研发新药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受试者进行试验。据统计,医药公司每研发一种新药,需要在65个试验中的141个阶段使用超过4000名以上的受试者⑤。由于有良好的医疗保障,以及担心人体试验的风险,发达国家中可招募的受试者在不断减少。在美国,只有不到5%的人口愿意参与人体试验⑥,只有不到4%的癌症患者愿意作为抗癌药物试验的受试者。“每年有几千万妇女死于乳腺癌,试验者却找不到100名受试者进行试验。”⑦而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患有试验目标疾病的患者数量多,如撒哈拉沙漠以南某些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和HIV病毒携带者占全部人口的30%—40%,无疑是进行艾滋病药物试验的“最佳”地点。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患者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较少接受药物治疗,“进行人体试验时,你会希望患者没有其他的疾病,也没有接受其他治疗,这样你就可以比较明确的了解试验药物对于患者所起的作用”⑧。大量潜在受试者的存在,正是跨国人体试验的诱因之一。第二,经济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可以用低得多的成本获得试验所需的器材、设备和研究团队,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医疗标准,进一步降低了成本。在美国每名受试者的成本平均为10000美元,在俄罗斯为3000美元,在更加贫困国家则更低⑨。第三,逃避监管。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对于人体试验的严格管制,法律在这一领域往往陷于空白,可以使发起人得以进行一些在本国不被允许的试验,也可以使发起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研发工作。第四,接受国的意愿。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于跨国人体试验往往持积极甚至主动的态度。与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医药企业共同进行研究,不仅能给他们带来学术上的声誉,更会有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经济上的利益。有的国家由于缺乏应对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主动要求接纳人体试验换取医疗服务,如1994年乌干达卫生部长就宣称该国“准备为艾滋病人体试验研究提供受试者以换取健康服务”⑩。有的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生物医学科技和产业的发展,也鼓励他国医药企业和研究机构来开展人体试验。
(二)跨国人体试验激增引发双重医疗照顾标准的争议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公众健康服务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引发了跨国人体试验中的双重医疗照顾标准问题,即跨国人体试验应当适用发达国家较高的医疗照顾标准还是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医疗照顾标准的问题。例如,在发达国家,对感染HIV的孕妇高剂量使用药物AZT以降低母婴传播几率,已成为常规治疗方法。然而由于其价格昂贵,发展中国家的孕妇根本无力承担此种治疗。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CDC)和国家健康研究院(NIH)为此在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短期、小剂量的AZT研究试验,以降低其使用成本。试验中,约半数的孕妇作为对照组使用了安慰剂。试验的反对者认为,根据《赫尔辛基宣言》(11)的规定,对于对照组中的试验受试者应当给予“已经证实的治疗”,只有在没有现有治疗方法的情况下,才可以在对照组中使用安慰剂。AZT预防HIV母婴传播在发达国家是“已经证实的治疗”,因此安慰剂对照组不符合人体试验伦理要求。(12)试验的支持者则主张,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受试者“如果不是因为参加试验的话,将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治疗”。对于他们来说,“现有的治疗方法”就是没有治疗。(13)另一个例子是Surfaxin试验。一家美国公司计划分别在欧洲和拉美的几个国家对一种治疗早产婴儿呼吸窘迫综合症(RDS)的新药Surfaxin进行人体试验。欧洲试验拟对Surfaxin与现有的四种治疗药物进行对照组试验,而在拉美的试验拟进行安慰剂对照试验。在早期审查中,FDA认为,对于像RDS这样的致命性疾病不向受试者提供可行的治疗是违反伦理的。医药公司主张,由于在拉美国家没有治疗RDS的常规方法,受试者不参与试验也不可能获得有效的治疗,安慰剂试验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医疗标准的。这些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法律界和医学界的关注和争议。
(三)跨国人体试验激增对知情同意与伦理审查机制产生极大挑战
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是人体试验中保护受试者的两大核心机制,但在跨国人体试验中,两者都面临着重大挑战。由于发展中国家公众的文化水平和科学认知程度较低,以及对医疗服务的迫切需要,其知情同意权易于遭到侵害。在上述AZT试验中,“当孕妇Siata Ouattara第一次被告知她是(HIV)病毒携带者后几分钟内,明显还没有从这个噩耗中回过神来的她被快速的告知了有关试验的细节。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其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她根本没听说过的‘安慰剂’,之后,失业且不识字的Ouattara就同意参加试验了。当问她为什么要参加试验时,她回答‘为了他们答应我的治疗’”(14)。又如,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千禧年制药厂在我国安徽地区进行大规模人类基因采集研究中,在试验者的要求下,当地政府动员农村居民参与试验,以换取体检和接受医疗服务的机会。很多受试者参与试验的同意表格是倒签时间的,而且明显是第三人的笔迹(15)。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有关人体试验伦理审查方面缺少完善的法律制度,如我国直到2007年才由卫生部颁布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试验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这种情况,造成发展中国家对跨国人体试验的管制和伦理审查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人体试验成为很多发起人规避本国法律管理和伦理审查的手段。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其抗癌药物M4N研究在美国受到FDA的禁止后,秘密在印度继续进行人体试验。当位于加利福尼亚的Maxim制药公司研究的一种新药由于FDA认为需要获得更多的动物试验数据而拒绝其人体试验请求时,却在俄罗斯开始进行了人体试验。(16)鉴于发展中国家伦理审查机制的不完善,有意见认为,应当由发起试验的发达国家对试验进行伦理审查。反对者认为这种意见完全是父权主义的,是“伦理帝国主义”,主张应完全由试验接受国进行伦理审查。
(四)跨国人体试验激增带来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等
根据正义原则,试验的收益与试验的风险应当成比例。作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人体试验,应当在要求发展中国家人民承担风险的同时使其享有试验所得的利益。而在现实中,发达国家发起人所关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医药市场,其目标疾病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健康问题,而对于某些只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疾病,则少有人关心和研究。1975年至1997年间,世界医药工业总共只有0.3%的人体试验研究目标为热带疾病,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药物人体试验在世界各地进行(17)。1993年,仅英国在癌症研究上就花费了2亿美元,而同期全球用于疟疾研究的费用仅为8700万美元。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疟疾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健康问题。2000年,美国共发生了1200例疟疾病例,绝大多数是移民或者从疟疾疫区回国的旅行者。而与此同时,在非洲、印度、中美洲等疟疾流行区,每年有超过100万的人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正是生物医学研究和人体试验这种以发达国家市场为核心的做法,决定了进行人体试验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能直接从试验中收益。此外,试验所研发的药物在经过批准后,马上会被发起试验的医药公司注册专利并投入市场。这种专利保护下的药品价格,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所无法企及的。即使是上述AZT药物短期试验,其小剂量、短期疗程的价格,也远远超出了进行试验的非洲国家一般民众的承受能力。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受试者和其所处的社区在承受人体试验的风险和损失后,却无缘分享人体试验的成果,“为他人作嫁衣”。人们不禁要问,发展中国家的受试者是否应有权分享试验成果呢?试验的发起人是否有义务保障这种结果分享权呢?
二、对跨国人体试验国际规范的检讨
当前,对于跨国人体试验的国际规范,主要包括赫尔辛基宣言和CIOMS(18)指针。此外,2007年7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生物医学HIV预防试验中的伦理意见》(以下简称“HIV伦理”),涉及跨国艾滋病预防试验的伦理要求。此外,2003年2月,欧盟关于科学和新技术伦理的专家小组(19),向欧盟委员会提供了名为《关于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临床试验的伦理问题》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欧盟意见书”)。该意见书虽然不具有欧盟法律规范的效力,但对于欧盟下一步的立法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对医疗照顾标准问题国际规范的检讨
对于人体试验中的医疗照顾标准问题,1996年版的赫尔辛基宣言规定:“在任何医学研究中,所有的患者——包括对照组中的患者——应当确保获得经证实的最佳的诊断和预防方法。”伴随着AZT试验引发的论战,2000版赫尔辛基宣言第29段将其修正为:“新方法的益处、风险、负担和有效性都应当与现有最佳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作对比。这并不排除在目前没有有效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存在的研究中,使用安慰剂或无治疗作为对照。”但是,这个表述仍然没有解决“现有最佳”这词所引发的争议。为此,2001年11月,WMA发表了对该段的“说明”:“WMA认识到修订后的《赫尔辛基宣言》第29段所引发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可能的困扰。……在下列情况下,即使有现有的治疗方法,安慰剂试验也是可以接受的:基于不得已的和在科学上具有可靠方法论基础的原因,使用安慰剂对于确定一种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必要的;或者当试验是为了验证对某种轻微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而其受试者不会因为接受安慰剂而遭受任何严重的风险和不可逆转的伤害时。”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个说明并没有起到澄清的作用,反而让人更加困惑。问题主要在上述第一个条件中。批评者认为,该条件有三处错误。第一,缺乏对“不得已的(compelling)”原因的判断标准;第二,“在科学上具有可靠的方法论基础”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据赫尔辛基宣言,所有的人体试验都必须在科学上具有方法论基础;第三,这种规定可能导致受试者遭受严重风险和不可逆转的伤害。(20)针对此种批评,2008年10月,WMA取消了第29段及其说明,将该内容修改为第32段:“一种新的医疗手段的收益、风险、负担和效果必须与现有最佳的医疗手段进行对比研究,以下情况除外:当没有现有经证实(current proven)医疗手段存在时使用安慰剂或不给予治疗;或者基于不得已的或者在科学上具有可靠的方法论基础的原因,使用安慰剂以验证一种手段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必要的,而且接受安慰剂或者未得到治疗的受试者不会遭受任何严重的风险和不可逆转的伤害。必须极其谨慎的避免对此的滥用。”该规定克服了2000年版宣言及其说明存在的问题。然而,“现行经证实”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试验国范围内的治疗方法?这个问题似乎又把我们引领回了原来的争论中。
关于使用安慰剂进行试验,2002年版CIOMS指针第11条注解认为,只有在试验接受国由于经济或者供应上的原因缺乏在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确定有效的手段,试验的目的是为了研发一种可以使该国受益的新治疗手段时,或者根据该国家的情况,使用确定有效的手段作为对照组将使试验数据非常不可靠时,方可以考虑使用安慰剂进行试验。而HIV伦理第14条则指出,在试验中感染HIV病毒的受试者应当获得国际上公认的最佳治疗方法。第15条规定,在试验组和对照组中的受试者都应当获得确定有效的减少感染HIV风险的方法,只有在没有与试验中的疗法形式相同的预防措施时才能使用安慰剂;欧盟意见书第2.10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原则上不得进行安慰剂试验。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当某种标准治疗在试验接受国因为供应或者成本原因不能获得时,为简化治疗或者降低治疗成本而进行的试验。
笔者认为,对于人体试验单一标准和双重标准的争议,反映了正义原则中平等的正义(justice as equality)和公正的正义(justice as equity)的分歧。自贝尔蒙特报告以来,正义(justice)原则是人体试验中的基本伦理原则。(21)平等的正义要求对同样的事情予以同样对待,无论每个人有什么特殊情况,如同工同酬。公正的正义要求对同样的事情予以同样对待,但要考虑每个人特殊需求,如在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对弱势者的特殊照顾。在跨国人体试验中,对于受试者权利,特别是生命权、健康权的保障,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基于“将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永远不能仅仅看做是手段”的伦理原则,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当获得同样对待。因而,在人体试验的照顾标准问题上,首要的原则应当是平等的正义。不论是发达国家的受试者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受试者,在试验中都应获得同样的照顾标准。坚持平等的正义,不仅可以保护受试者的利益,也可以以此为契机逐步推进发展中国家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当然,平等的正义有时也需要考虑每个个体的现实需求,即需要与公平的正义相结合。例外情况下,如为了验证一种可以造福发展中国家患者的、更易为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医疗方法时,某些组别的受试者所受治疗可以偏离或者低于国际上通行的常规方法。
(二)对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问题国际规范的检讨
对于跨国人体试验中的伦理审查,CIOMS指针第3条规定:“外部发起组织和个人试验者应当在其本国提交试验方案以接受伦理和科学审查,且所适用的伦理标准不应低于在该国进行试验时所适用的标准。接受国的卫生机构,以及全国性或者地方性伦理审查委员会应当确保试验对于接受国的健康需要和迫切需求具有回应性并符合伦理标准。”该条指针明确规定跨国人体试验必须接受发起人本国和试验接受国的双重伦理审查,其伦理标准必须符合双方要求。
HIV伦理第3条指出,试验各方和有关国际组织应当合作帮助试验接受国建立科学和伦理审查的能力,使其得以做出有意义的自主决定,并成为与发起人具有平等地位的伙伴。
欧盟意见书第2.8条规定,对试验方案的科学和伦理评估必须由试验涉及国家的伦理委员会共同进行。试验接受国需要建立法律和伦理的框架以有效和独立的参与对试验的评估。
对于在发展中国家中受试者知情同意的特别保护,欧盟意见书2.6条规定,发起人和试验接受国双方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都应当得到考虑,但不应当牺牲基本的伦理原则。第2.7条规定,根据当地的情况,可就试验方法寻求受试者的代理人或者社区、家庭中权威的同意,但是每一个受试者也必须做出自愿的知情同意。
笔者认为,在跨国人体试验的审查与管理上,应当采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双重审查的机制。发达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将逐步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有效的人体试验管理和审查机制,如美国的IRB制度、荷兰的中央和地区人体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制度等。确保试验获得发起人本国的伦理审查和批准,是发起人的基本义务。但是,发起国的审查机构,可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缺乏了解,也难免会产生“自扫门前雪”的风险。因此,仅由发达国家对试验进行伦理审查是不够的。而发展中国家普遍没有建立完整、系统、有效的人体试验管理和伦理审查机制,公众缺乏对人体试验伦理的普遍认知,也缺乏足够数量和能力的伦理审查专家。特别是在经济利益和其他诱因的驱使下,伦理审查往往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对此,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必须尽快建立健全自身管理和伦理审查机制,使其真正能够充分发挥保护受试者合法权利的作用,对此,发达国家有义务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发起国与接受国的双重伦理审查机制,以达到取长补短,互相制衡的作用。
在知情同意领域,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结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众的科学认知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发起人、试验者必须尊重试验接受国的现实与传统,以受试者能够真正理解的方式向其全面告知试验的目的、过程、风险、可能的不适等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用灵活方式进行告知同意,如征询家属、家族成员的意见等,但是最终必须获得每一个受试者在完全知情下的自主同意。决不能允许只通过政府、社区、家族动员的形式完成知情同意程序。
(三)对试验利益分享问题国际规范的检讨
对于受试者个人在试验结束后所应受到的照顾和利益分享,2000年版的赫尔辛基宣言第30段规定:“在研究结束时,每个人组病人都应当确保得到经该研究证实的最有效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然而,这一段规定也引发了争议。反对者认为,此种强加的今后医疗照顾义务将使医药公司迫于高昂的费用而放弃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人体试验,从而阻碍了通过试验为困扰贫困人口的疾病寻找治疗方法的途径。赞成者认为,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在承担试验风险的同时却得不到分享试验成果的机会是不正义的。为解决这种争论,2004年第55届WMA大会根据美国医学会的提议,决定为该条增加一个说明:“WMA于此重申,在试验的计划过程中,考虑(indentify)受试者在试验结束后可以享受作为试验成果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流程或者其他适当的照顾是必要的。”
反对者如加拿大医学会认为,该说明是不适当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医药试验中,能很容易的想象出,试验的发起人会‘考虑’了让受试者在试验接受后分享试验成果,但是由于经济原因无法实现。然后他们就可以说不会有什么试验后的照顾。”(22)
2008年版的赫尔辛基宣言取消了2004年的说明,将上述内容规定在第33段:“试验结束时,参与试验的受试者应当有权被告知试验的成果并分享从中获得的任何利益,如获得作为成果的医疗手段或者其他适当的照顾和利益。”从而确认了受试者对于试验成果的分享权。但是分享权的主体范围应当为谁,与受试者属于同一人群的其他人是否得以分享成果,仍然值得讨论。
2002年CIOMS指针第10条规定:“在资源有限的人群和社区中进行试验,发起人和试验者必须采取措施,以便回应接受试验的人群和社区的健康需要与迫切需求;保证人群或社区可以合理地获得试验取得的治疗、产品或知识。”CIOMS要求发起人应当与试验接受国就试验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和“合理的可获得性(reasonable availability)”进行协商。如果试验药物的有效性得以证实,发起人应当在试验结束后继续向受试者提供药物,同时向接受国管理机关申请药物批准。
HIV伦理第5条提出,伦理原则要求早期试验一般应当在发起人本国进行。第19条要求,试验的发起人和接受国,应就向所有受试者以及该国HIV高风险人群提供经试验验证的安全和有效的预防方法,及其他有利于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利益达成协议。
欧盟意见第2.5条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应考虑:试验的目的在于解决该国特殊的健康需求,如治疗热带病;或者试验的目标在于解决在各国都有、但是在该国发生率更高的疾病;或者试验的目的对该国具有特殊的利益。第2.13条指出,试验结束后受试者无法通过常规医疗系统获得经验证有效的新药时,发起人应当向所有受试者免费提供这该药物。试验者应以试验社区能够承受的价格供应药物,或帮助社区提高医疗能力。
笔者认为,有关跨国人体试验的利益分享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哪些人体试验可以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根据人体试验研究目标与接受国的关系,试验可以分为与接受国无关、只与接受国有关和与双方都有关系的试验。与接受国无关的试验不应在该接受国进行,因为这样意味着接受国的受试者及其他人群不是试验的目的,而仅仅试验的手段。与双方都有关系的试验,也应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医疗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保护,如《HIV伦理》中所要求的,不应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风险较高的早期试验。应当鼓励那些目的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特殊医疗需求的研究,如热带病研究等。但是,在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下,作为营利组织的医药企业很难投入到难以获得经济利益的研究中去。这就需要有关发达国家的政府担负起减小南北差距的国际义务,推动有关试验的进行。第二,是对于受试者的利益问题。如果试验的治疗是安全、有效的,为了受试者的利益考虑,应当保证受试者有条件继续接受此种治疗。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经济上和医疗条件上的原因,受试者往往无法以其他途径获得该治疗。此时,试验的发起人有义务为受试者提供充分的治疗,直到其不再需要为止。要避免对于受试者用完即弃的态度和行为。第三,是对于接受国的整体利益分享问题。当前,发起人在获得试验药物的批准后,随即申请专利。由专利和市场机制所形成的高昂价格,使试验药物对于接受国的民众来说遥不可及。而且,即使没有专利或者专利过期,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自己的医药工业体系以生产这些药物。这样就把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健康需求都有重要意义的药物,专美于发达国家。这种不合理的体制必须加以改变。发起人在进行人体试验之前,必须就试验结果如何造福于接受国人民做出计划和安排。这种计划和安排,必须通过发起人与接受国有关当局、机构、组织之间充分协商来确定和落实。
三、对建立我国跨国人体试验受试者保护机制的建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人体试验所引发的伦理、法律问题,提醒我们,我国必须及时建立跨国人体试验受试者的保护机制。笔者认为,必须尽快建立四个方面的机制,即双重伦理审查机制、沟通与谈判机制、利益冲突协调机制和国际合作监管机制。
(一)建立双重伦理审查机制
双重伦理审查机制要求,国外发起人的试验方案在其本国获得法定伦理审查机构的审查批准,是在我国将试验提请进行伦理审查的必要条件。卫生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第26条规定,“境外机构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进行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其研究方案已经经过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伦理委员会审查的,还应当向我国依照本办法设立的伦理委员会申请审核。”易言之,即使试验未经发起人本国或者地区伦理委员会审查,仍得向我国的伦理委员会申请审查。这实际仍是单一的国内伦理审查机制。笔者认为,为了确保在我国进行的跨国人体试验在伦理上的可接受性,发起人在我国提出审查申请时,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本国的法定伦理审查机构根据其本国法律与伦理规范要求和国际通行的伦理标准,对试验方案进行了审查批准。未经其本国和我国伦理审查机构审查批准的人体试验不得在我国开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我国进行人体试验成为其他国家发起人逃避本国伦理审查的手段。具体包括:第一,建立统一的跨国人体试验审查机构。境外发起人欲在我国进行人体试验的,必须向该机构提出申请。审查机构应审查试验方案是否符合试验发起国、我国以及国际公认的伦理标准。第二,重点进行人体试验必要性审查。试验必须有助于解决我国公共健康领域的迫切需求。试验目标并非我国公共健康领域的迫切需要,或者对于试验成果我国公众将无法获得分享的,则不应予以准许。第一期临床试验由于对受试者没有直接利益,一般不应允许国外发起人在我国进行。第三,强化对我国受试者权利的保护。除了特别为我国研究成本较低的治疗方法的试验外,其他试验中受试者所受到的医疗照顾水平,必须与试验发起人本国对同样疾病的医疗照顾水平相当,并且不低于我国现有的水平。试验方案应当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情况下,以适当的方法和受试者可以理解的方式,真实、全部的向受试者告知试验的有关情况,并取得受试者自主的、独立的同意。
(二)建立与国外发起人对话与协商机制
根据上述国际伦理规范的要求,发达国家的发起人在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人体试验之前,必须就有关试验的利益分享等问题,与试验接受国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商。这首先要求我国必须建立起一个能够代表我国利益与国外试验发起人进行对话和协商的机构和机制。为了确保其代表性,应当由中央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主体(以下简称协商机构)承担此项职责。该协商机构必须独立于试验者及其利益相关方。国外发起人在向我国伦理审查机构提出审查申请之前,必须与协商机构就试验的潜在利益造福于我国受试者和社会公众的可能性进行对话和协商。对话和协商的内容包括:第一,试验中的医疗水平。包括发起人为进行试验,特别是使试验的伦理和医疗照顾标准达到发起人本国和我国标准所做出的安排,包括医疗基础设施的建立、试验者和医疗人员的专业与伦理培训,以及试验过程中受试者可接受医疗照顾水平。第二,试验结束后受试者可以获得的利益。试验结束后应对受试者予以继续照顾,特别是当试验药物经验证安全有效时,试验发起人应保证按照需要免费向受试者继续提供试验药物,直至受试者不再需要该药物为止。第三,对受试者可能的损害的赔偿安排。即试验进行中和试验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受试者因试验遭受生命、健康损害时,发起人和试验者对受试者及其亲属的赔偿方案。其赔偿标准应当不低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并应当提供保险以保证其承担责任的能力。第四,试验对于我国公众的收益。包括试验结束后试验设施对于我国公众的开放和作用,试验内容的治疗经验证安全有效时在我国的推广方案,包括上市计划、可能的价格等。发起人可以根据其本国和我国法律对试验成果申请专利,但应保证及时向我国药品监督部门申请上市,并在获得批准后以我国公众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可以承受的合理价格在我国提供有关产品或治疗。还应当就相关技术进行转让的可能性进行协商。
(三)建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
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对于跨国试验的中方合作者而言,与国外著名研究机构、医药企业在尖端生物医学科研领域内的合作,不仅能为他们带来职业上进展和声誉,更有经济上的直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形成试验者与受试者的利益冲突。试验者,有时包括伦理审查机构,不再是在试验发起人与受试者之间保持独立和中立地位的主体,而成为试验发起人的代理人或合作者。这就产生了试验者与受试者的利益冲突问题。特别是从我国现行体制看,人体试验的伦理审查主体是“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技术应用活动的机构,包括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疾病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机构等,设立机构伦理委员会”(23),即将伦理审查机构设置于研究机构组织结构之内。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期待机构组织内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能够独立于研究机构而避免陷于的利益冲突是不现实的。为了避免这种利益冲突影响试验者和审查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包括:第一,利益冲突的及时披露和告知。对于在试验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包括发起人向试验人及其所在机构提供的经费、物质帮助以及试验者的其他收益情况,必须向主管部门登记,在伦理审查中应向审查机构作出具体的报告,并应在招募受试者过程中向受试者详细说明。第二,维护伦理审查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维护伦理审查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是避免利益冲突损害受试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根据我国实际,应当改变伦理审查机构附属于研究机构的设置,建立独立的人体试验伦理审查机构,特别是建立跨国人体试验的集中审查机构。第三,对跨国人体试验经费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管。发起人根据国际伦理要求为提高伦理审查机构审查能力和试验者研究水平所提供的经费,不应直接拨付与具体的伦理审查机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而应交由中央人体试验者主管部门,由其根据试验需要进行拨付等。
(四)建立国际合作监管机制
跨国人体试验问题,是当前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医学研究以及卫生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为解决其带来的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合作。特别是在目前有关人体试验的国际规范缺乏国际法地位、更缺乏执行力的情况下,更凸显出这种合作的重要性。在这种关系中,发达国家作为人体试验的发起国和主要受益国,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在医疗设施、科学技术、伦理教育和审查、法制建设和执法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则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保障本国人民的健康和促进生命医学的发生为目标,建立健全各种合作机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建立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监管机制,包括:第一,执法机关的共同监督与管理。通过与试验发起国的执法机关共同对人体试验的方案设计、试验执行和后续工作进行共同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试验整个过程中的不当行为。第二,伦理审查机构的双重伦理审查。加强与发起国人体试验伦理审查机构的沟通和合作,确保跨国人体试验符合发起国与我国的法律、伦理准则和国际规范的要求。第三,建立试验信息的共享机制。与试验发起国及时就相关信息进行交流,防止试验发起人利用各国间在信息上的不对称和沟通上的不顺畅攫取不当利益。第四,积极开展在试验成果分享方面的合作。鼓励主要研究目标为我国公众健康问题的试验在我国开展。确保试验结束后受试者有条件和机会分享试验成果,推动试验成果尽快造福我国公众。人体试验的监督管理机关,负有监督落实有关利益分享安排的职责。第五,加强在跨国人体试验国际法律伦理规范制订中的合作。积极参与UNESCO、WHO、CIOMS等国际组织有关人体试验问题的行动和研究,推动建立具有执行力的人体试验国际立法。
收稿日期:2012-03-26
注释:
①Pfizer,Kano State Reach Settlement of Trovan Cases,New York Times,July 30,2009.
②Ruth Macklin,Double Standards in Medical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7.
③"GSK Cuts Costs with More R&D Abroad,Electronic Data Capture," Drug Industry Daily,November 6,2004.
④Julie Schmitt,Cost,Regulations Move More Drug Testes outside USA,USA Today,May 16,2005.
⑤Sonia Shah,The Body Hunters-Testing New Drugs on the World's Poorest Patients,New York:The New Press,2006,p3-4.
⑥Kathleen B.Brennan,Pharma Wants You:Clinical Trials Are Agencies' New Proving Ground,Pharmaceutical Executive,April 2003,P 83-84.
⑦Sonia Shah,The Body Hunters-Testing New Drugs on the World's Poorest Patients,New York:The New Press,2006,P 4.
⑧Ruth Macklin,Double Standards in Medical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7.
⑨William Dubois,New Drug Research,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DA Regulations,and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January,2003.
(10)Charles Henderson,Uganda Will Provide Vaccine Subjects in Return for Services,Infectious Disease Weekly,Mar.4,1996,p1.
(11)《赫尔辛基宣言》是世界医学大会(WMA)针对人体试验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于1964年6月在芬兰赫尔辛基制定通过的《关于以人为对象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指导原则》(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一般通称“赫尔辛基宣言”。后经多次修改,现行有效的为2008年版。
(12)Ruth Macklin,Double Standards in Medical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4-15.
(13)Jay Dyckman:The Myth of Informed Consent:An Analysis of the Doctrine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Its(Mis)Application in HIV Experimentations on Pregnant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olumbia Journal of Gender and Law,1999.
(14)Jay Dyckman:The Myth of Informed Consent:An Analysis of the Doctrine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Its(Mis)Application in HIV Experimentations on Pregnant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olumbia Journal of Gender and Law,1999.
(15)William Dubois,New Drug Research,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DA Regulations,and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January,2003.
(16)William Dubois,New Drug Research,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DA Regulations,and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January,2003.
(17)Ruth Macklin,Double Standards in Medical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9.
(18)CIOMS即“医学研究国际组织理事会”,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1949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1993年CIOMS和WHO共同制定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各项国际伦理指南》,即“CIOMS指南”。
(19)由欧盟委员会任命的专家组织,其任务是研究科学和新技术方针带来的伦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准备和制定欧盟立法或者政策的意见。
(20)Ruth Macklin,Double Standards in Medical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48.
(21)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The Belmont Report,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p9.
(22)Jeff Blackmer,Henry Haddad,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an update on paragraph 30,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2005(9),p1053.
(23)《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第6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