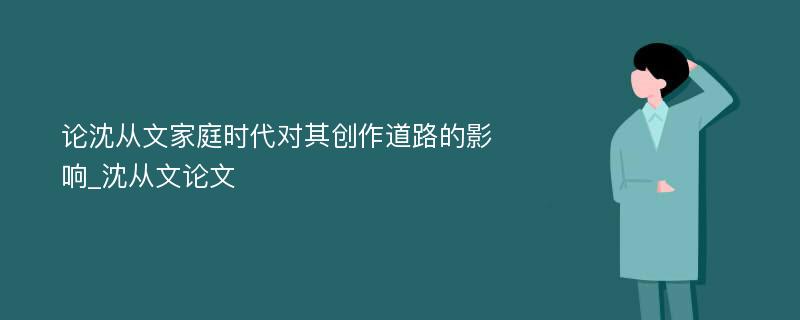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其论文,家世论文,道路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少论者都谈及沈从文的“自卑情节”,认为“自卑情节”对其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这是对的。 但若进一步问:自卑情节又缘何而起?自卑感的产生要有一定的“落差”和“参照系”,这“落差”和“参照系”是什么?在作家整个创作中是什么东西站在不易望见的远处,“遥控”着他的生活道路并渗透在他的作品风格中?答曰:是他特殊的家世。倘说“自卑情节”是他创作道路的近因,那么深深沉淀在作家心灵底层,隐于作品深处的远因则是他的家世。他从军队出走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作品中所显露的贵族气息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关系。
1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沈洪福曾一度作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因创伤而病死家中。他所“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他的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个较优越的地位。”〔2〕祖父因无子息而过继来叔祖父和一个苗族姑娘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因此,沈从文有一部分苗族血统。父亲从体魄到气质都令家人以“未来将军”相期许,但因社会变故,终其一生只作了个极普通的军官,后在土著部队里作一名上校军医。
外祖父黄河清是本地最早的贡生,“守文庙作书院山长。”故母亲极小就认字读书,懂医方。他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母亲教他认字,教他思考和判断。沈从文兄弟姊妹共九个,他排行第四。这样一个在当地较显赫而受人尊敬的军人家世伴随着牵藤绕蔓、地位差不多上下的亲戚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一位研究沈从文的外国专家曾说:“他(指沈从文)跟当地掌权者大都不是认识就是亲戚关系。因此,他的小说可以构成一套家世小说的简史。”〔3〕的确, 沈从文有些作品就直接描写他家族和亲戚关系。“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4〕所有这些无疑从小培养着他的优越感。加之他父亲因他明慧,自小便告诉他“祖父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周围人也以大器目之,潜移默化,无形中把他的人生砝码加高。可以说沈从文的优越感这时已经成形,在心灵上刻下了一层不可磨灭的印迹。
若往后他家世的炉火依然旺炽,且不说更好,沈从文可能躺在这优越感上平静安宁,然而可能一事无成地抵达人生黄昏的彼岸。他那些充满艺术魔力的作品就不可能问世,正如他自己所说:“假如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作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县,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5〕但自父亲“谋刺袁世凯”未遂而隐姓埋名辗转东北后,家庭败落了,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既已到了把老屋字契到处借钱度日的情形。”〔6〕沈从文再也不能躺在贵族式的优越感大氅里作安宁无忧的梦。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撼动童年的他那颗顽皮贪玩、充满幻想和猎奇意识的心,那么在14岁时家里送他去当兵,为曾在他父亲手下当差而今升为团长的女儿莲姑当差,给她“装烟倒茶”,他才模糊地意识到摆在前面的路是多么狭窄和坎坷!这可能是沈从文第一次感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只有这时他才开始思索一些人生的意义。他感叹道:“有人从大族中把家从中落到破产么?有人在小孩时正当着这个顶坏的命运吗?从这个来的,都能体会到那种情形。我的家,在我出世那一年,是还正给爹爹大抖特抖,让一个姓庞的抚台到家为我取名的,谁知这个名字却在他14年后给人作副兵喊叫用!在口北的爹爹,也许还在儿子身上做着那好梦,谁知儿子却应在15岁以前来把时间消磨在供人使唤的工作中。”〔7〕千年田地八百主,十年穷富多少人! 家庭的变故使他小小年纪就“要把母亲同姐姐用眼泪洒在上面那小小包袱背起,跟随家乡中的叔叔伯伯到外面来猎食”〔8〕, 在生活漩涡里起伏低昂。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卑感向他袭来!
但他并不甘心给莲姑当差,要是一般人会觉得理所当然,顺理成章,而且还会因给团长家的小姐当差感到庆幸,觉得“被抬举”,但沈从文丝毫不觉得宠幸,反觉得极大的羞辱,因为自己家世的参照系像一只眼远远地盯着他。
在部队当兵,依崇武的湘西人来看,本也不是很卑贱的职业,相反倒是一般“年轻人唯一的出路”,但从作家传记和作品描写来看,沈从文在军队时总是忧郁的、内向的、有所思的。倘说沈从文以前还是一个顽童,那么到这时已完全懂事了,他背负着家族对他的期望,要“好好的做人”,“我找钱,我找名誉”,不能让家人和娘“长此随到亲戚飘荡”。因此,他不像一般兵士那样随波逐流,放任自己。他并不甘心作一个无名兵卒,这绝不是他的家族所期望于他的。因此,他经常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与周围人并不合群,他的心常是孤独落寞的。他虽然对绑架勒索、杀人剿“匪”等军队中家常便饭的事不能作出很清晰的判断,但他总与这些保持距离,“不安于当前事务”而为人生远景而凝眸。他常“爬上一个山,傍近一条河,躺到那无人处去默想,漫无涯涘去作梦,所接近的世界,似乎皆更是一个结实的世界。”〔9〕他因身体的瘦弱不能与人较力,便拼命写字,并以此“拔擢我到司令部作司书生,薪水加到九块三毛钱一月,名册上写的是上士,名义上我已经是师爷的。”〔10〕然而也终不过一个“上士司书”,将军梦早已破灭。土著部队绝非他终生寄食之地,恰巧“五四”运动波及到了遥远闭塞的湘西,这呼应了他心灵中沉睡已久的向善向美的精神基因,于是他毅然决定抛撇了耗去他五六年青春的土著部队,只身来到北京。“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11〕
然而来到北京后,一下火车,都市的气势给了他巨大的威压。他原以为能到北京读书,结果考燕大得了零分。北京的亲戚对他又不冷不热,他又无固定经济来源,常到同乡、朋友处蹭饭吃。在他早期小说里就强烈流露出这种穷的窘迫和性的苦闷。郁达夫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信》里曾向像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指明三条路,最上是找一点事情做,比如拉洋车,当土匪等;第二是弄几个旅费回湖南老家;第三是去当兵,或作贼。但这三条路沈从文都没有走。他的家世在他心灵上刻下的优越感,他父亲给他讲的祖父一些“勇敢而光荣的故事”及家庭对他的期望促使他要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他说“人虽是个动物……究竟和别的运动不同,还要生活尊贵。”家世的光荣记忆不许他去干那些偷鸡摸狗、为人爪牙、充当炮灰的事情。他决心拿起笔来,用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用一些文白杂糅、甚至语句不通的文字来写文章,写曾精心培育了他的优越感的故乡湘西,写他家族过去的光荣。从他的作品里,一起始便显出一种高雅、清新脱俗的气质,而隐含在那少年的忧郁、伤感情思中的则是一颗向善向美的心。
2
从心理学上看,人们总愿意选取自己一生最光荣、最受人尊重、最具心理优势时的眼光去看待大千世界的人和事,因为在那时,人世的一切以最好的程序定格在他的记忆中。综观沈从文的整个创作,可以看出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对自卑感的躲避和驱遣以及对优越感的追求,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
(1)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读完沈从文的作品, 在我们心里总浮出一座孤城,一座封建宗法式的庄园,四面群山重叠,城下溪流环绕。在作家营造的这座庄园里,水整日长流,葱茏佳木,无言山巅,崖边白塔敛日静思,河中辗房逐水而歌,公家渡船悠然来去。这景象是一种时间抹洗不掉的牧歌图景,是留在诗人心底的梦幻,是以一种艺术意象符号形式,将那勾魂荡魄的远古记忆和种族体验转换成恒定的存在。你看,在这庄园式的牧歌图景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湘西·凤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敬神守法,“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并很乐意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税”。一切事情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人们都纯朴善良,不以苦难为苦,连妓女也那么浑厚,土匪、山大王也通人性。统治者并不骄横跋扈,反而为人公正无私、慷慨大度,济人危难。
读到这儿,我们总排除不了这样的感觉:《边城》掌水码头的顺顺及所描绘的人事秩序其实是他父辈们及由父辈们所建立的庄园式的等级格局在他心灵的折射,虽然它们乔装打扮扭曲变形,但从中还可依稀辨认那一点原初的影子。而他笔下的船夫、水手、仆人其实就是以他们家的仆人为雏形,当然他们家不可能有那么多仆人,但湘西下层贫民整体上可说是湘西统治者的奴仆。作为一个世家子弟,家中的二少爷,沈从文童年自然处处摆满鲜花,充满和蔼的笑脸,左右逢源。他童年所见的即他笔下所描摹的样子。沈从文这种对于封建庄园式牧歌图景的摹写,虽是在“述祖”意识的驱使下,对家世的回溯,对一种优越感的追求,但客观上为人们勾勒出一个理想世界的远景,让人们“从喧嚣的尘世退出来,沉浸在一种艺术梦幻的静谧遐思中”,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的作品至今仍具有诱人的魅力所在。
(2)“少爷”形象。沈从文本是一个少爷。虽后来家道日衰, 这一切皆成昨日黄花,但在他心底那份优越感,那种定格在脑海中的“少爷”的记忆,仍然刻在他大脑皮层里。到部队后,先前做过他家仆人现在是他“头头”的因他是少爷,与团长是亲戚,仍然客气地喊他“四少爷”,且安慰他说:“你一年两年就是官了,我要喊你做老爷,不止是少爷”(《阙名故事》)。所有这些,沈从文就借文学这个“白日梦”表现出来。最典型的如《灯》,且不管这个老战兵是实有其人还是作者虚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沈从文优越感里本来就有这样一位仆人,为他饮食起居,为他个人婚姻大事操碎了心,把自己生命全部系附在他家族的兴衰荣辱上。而沈从文则俨然一少爷,对他颐指气使。读完这篇小说,若对作家及其家世一无所知,我们脑海中一定会把沈从文幻想成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在部队当过兵、高大英俊、眼睛深邃而面带忧郁,蓄着一撇莱蒙托夫式小胡子的贵族军官,多少有点玩世不恭的世家子弟。
我们知道沈从文曾一度追慕郁达夫“自叙传”的写法,尤其是他早期作品,虽后来转向了,但在其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到作家自己的身影,或者完全是他本人,或者是变换了人称、身份、略加伪装而虚构的人物,但在精神气质上与作家本人吻合。如《冬的空间》中的“我”和《主妇》中的男主人公等。王尔德在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里曾借人物之口说:“凡是怀着感情画的像,每一幅都是作者的肖像,而不是摸特儿的肖像,模特儿仅仅是偶然因素。”若这个前提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看到沈从文很多小说写到的男主人公大都是有教养的世家子弟,禀性高贵,富于牺牲精神。如《凤子》写那个离开北京来青岛的“年轻男子”,“纯洁如美玉,俊拔如白鹤,为了那种对于女人方面的失意”,尊重别人,牺牲自己,保持到一个有教养男子的本分。“无边的大海,扩张了他思索的范围,使他习惯于向人生更远处了望。”而且后面一章《一个被地图所遗忘的地方,被历史所遗忘的一天》点明这位年轻男子出生于湘西凤凰县。我们难道不能从中看出沈从文本人的一点影子吗?
(3)附在“臣民”身上的优越感。 不少论者证明沈从文在刻意表现那蕴藏在湘西下层人民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倾注着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也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这是事实,至少在客观上或者说在读者眼中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然而我们掀开这层伦理评判的帘幕向作家隐秘的内心窥视,向作品更深处漫溯,难道不能发现点别的什么吗?表面上看,如有的论者所说的,沈从文企图构筑一个纯洁的湘西世界以与“昏天黑地”的都市文明相抗衡。除此之外,我们难道不能说他是在寻求那久已失落的优越感吗?美学家桑塔耶纳曾把艺术表现区分为彼此相关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种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我们考察当时沈从文自卑的心态就可明白这一点。在他《第二个狒狒》、《棉鞋》、《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等小说里,便可见到那流露在字里行间遭受屈辱与压抑的卑微感。他曾愤慨道:“到这世界上,像我们这一类人,真算得一个人吗?”〔12〕他的确无所凭依,四顾茫然。然而人是不惯于长久用自卑心理去构筑他的梦幻,而总想把整个世界置于他的眼目下,以高贵的姿态瞰视之。于是他把笔伸向他的故乡湘西,伸向下层人民的情感和道德世界,寻找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将火一样的颜色涂在他们身上。然而在描写湘西人民美好品质的同时,作家不易察觉地在上面建筑起自己的优越感,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王国”,笔下的人物就是他的臣民。他自己可能意识到然而多半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沈从文在他的同乡面前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这时他作为一个城里人,城里的绅士俯视湘西下层人民所带来的优越感这个因素。倘要细分的话,作为城里人,后来甚至作为城里的绅士的沈从文更多地意识到了湘西儿女自由舒展的人性中存有的致命弱点:既单纯又麻木,是天真又似浑噩,浪漫中含野蛮及在未来社会中的不折则曲前景。但我们绝不可忽视、否认他的受人尊敬家世,曾用优越感温热了他的童年,并使他产生超越的欲望。故作为前者更多的是清醒的理智,作为后者更多的是一种获得了优越感迷醉的热情。这里我们可以拿鲁迅和沈从文作一比较。他们都是从败落的家庭中走出来的子弟。鲁迅童年时因祖父下狱而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他作为长子不得不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一直沉淀于鲁迅心灵里,对他“孤独阴冷”性格的形成有极大影响,使他忆及故乡和亲人时,总难免有萧索败落之感,使其乡愁蒙上一层厚重的冷色调。好在他母亲的娘家在农村,“使我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自序》)。朴实的农村环境,诚挚的农家伙伴,田园风景,民间社戏……又从小给鲁迅敏感的心灵以难以忘怀的慰藉和温暖,“都曾是使我思乡有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朝花夕拾·小引》)。这才使他的作品现出一片亮色,尤其是后来当46岁的鲁迅那满是伤痕的心终于接纳了许广平后,在爱情转笃之时写就是《朝花夕拾》才有那么多恋乡怀旧的柔婉华章。
而沈从文呢,也亲历了家族的衰落带给他生活和心灵的震荡,但他的心与周围环境却是相融的。他在家中是老四,衰败及炎凉之感被他母亲和上面的兄姊过滤了。他只知贪玩,由于受人尊敬的家世那架子还搁在那儿,椽木已破损,但瘦了的骆驼比马大,优越感依然像大氅一样包裹着他的心,就是后来他到军队,第一次体味了世态的炎凉,但他对于现实人生残酷的那一面只是看而没有亲历,而且在部队像藤蔓一样的亲戚关系依然护卫着他。比方说他舅父就是县长,卸任后不久又作了“警察所长”;姨父“在本地算是一个大姆指人物,有钱、有势,从知事起任何人物任何军队都对他十分尊敬,从不敢稍稍得罪他”(《从文自传·女难》)。这些亲戚即或对沈从文及其家庭无任何垂顾,但就往那儿一站,对周围人无疑是一种威慑力。《从文自传》最后一段写到他把读书的打算与上司说及时,上司让他拿了三个月的薪水,还给了一种鼓励:“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试问,无一些关系和背景能得到这样关照?我们不会忘记《我的教育》里一个不愿作炮灰的逃兵第二次被抓回枪毙的情景。而这些恰恰成全了沈从文对故乡湘西及其人生形式的眷恋与怀念,加之他又是那样一个重感性的人,不习惯用理智的分析来弥补体验的不足,造成了他那“向远景凝眸”的性格。
按一般心理逻辑,沈从文因自己显赫的家世,可能瞧不起他的“臣民”,与他们在情感上有一道鸿沟。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为何他要把湘西下层人民写得纯朴善良,充满无限的温爱情调呢?这一方面是归因于沈从文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我们试想一想,若他鄙视、否定了他笔下的人物,也就否定了支撑他的优越感的艺术世界,他再到何处寻觅他的优越感呢?此时支撑他活下去,与“昏天黑地”的都市抗衡的恰恰是这宝贵的优越感呀!他当时正受着自卑情结的困扰,他曾这样愤慨道:“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多少文章就是多少委屈。”(《虎雏》)而在故乡纯朴的人事中,他则是这人事的中心。因此,沈从文当然要借助文学之梦重新飞到故乡,借故乡的人和事,重新活在“他所主宰的环境中”,而把自卑情结赶出心灵的视野。
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沈从文作品大都是以悲剧氛围结束的,其中人物皆被无常命运捉弄,最后皆伫立于空茫中。正如刘西渭所感叹的:“当我们放下《边城》那样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我们的情思是否坠着沉重的忧郁?我们不由问自己,何以和朝阳一样明亮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为什么一切良善的歌颂,最后总理在一阵凄凉的幽噎?为什么一颗赤子之心,渐渐褪向一个孤独者淡淡的灰影?”〔13〕究其因,一方面是沈从文所描绘的湘西在现实中不存在,现代文明已剪破了湘西人生画幅的边角。另一方面难道不能说是他家族的式微在他童年心灵上刻下的凄凉色调在作品中的表现?
(4)梦中的爱情。我们再看作品中关于男女爱情的描写。 众所周知,沈从文小时患过病,这场病使他身体瘦小羸弱,这使现实中的沈从文在爱情上极度自卑。他在一封信中说“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上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你的。”〔14〕然而这可是他所期望于自己的么?不!他绝不甘心如此!然而这又是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事实。这样,他的身体和心灵产生了矛盾,它们像拉锯一样在沈从文生命中斗争着。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沈从文采取“寻梦”的办法,把笔伸到他的故乡湘西,决心去寻回那在受人尊敬的军人世家的护卫下应属于他的那份年轻、健硕和英俊,应得到的那份美轮美奂的爱情。有时我们禁不住要这样假设:《边城》中的傩送其实就写的是沈从文自己,只不过拐了一个弯让人不易察觉而已。而翠翠则是作家梦幻中的理想的情人。虽然我们不愿作这样“索隐”式的联想,但作家的自白又隐约地透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当他写完《边城》后,他在《水云》中说道:“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排泄与弥补。”就是当他在现实的爱情上获得成功时,但“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这份情感其实就是自童年起一直沉淀在沈从文生命中想实现而没能实现的压抑已久的爱情。虽然现实中的沈从文是个“苍白脸眼睛羞涩”〔15〕的人,总把自我形象置于一种很卑下的地位,但他写到的爱情,全都是大胆、勇敢甚至粗野的爱。笔下的男子大都是完美无瑕、“神工锻造”的,从他们身上“我们立即可以认出‘自我陛下’,他是每一场白日梦和每一篇故事的主角。”〔16〕
另外,沈从文对故乡湘西的女子从来都有一种优越感。在《湘西散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曾描写一个叫夭夭的小妇人对他“一见钟情”的场景。“我几乎本能的就感到这个小妇人是正爱着我的。……我们若稍懂人情,就会明白一张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同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在一个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是一种如何的幻想”,而当他上船后,这女子还为他唱《十想郎》,他“竟站在河边寒风中痴了很久”。沈从文似乎又一次回到那优越的梦中。经过上面的考察后,我们必须说明下面两点:
第一,不能说沈从文所有的作品都笼罩着他家世的影响,都是他对优越感回溯的体现,但他家世所带来的优越感(或者说是一种自卑感,这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的确影响着他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从中兴到败落家世中变迁出来的子弟往往终生都在竭力寻那家世辉煌的旧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曹雪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现代文学史上如鲁迅、胡适、巴金、曹禺、何其芳等都可说是循着这条心迹,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有的正面寻觅,如沈从文;有的负面摒弃、否定,如巴金,但家世对作家生活、创作道路及作品风格起着重要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第二,家世的影响往往沉淀于作家内心深处,它往往乔装打扮,穿上一件厚重的“迷彩服”,显露出来的面目已扭曲变形,这为我们的考察带来了困难,常有捉襟见肘之感,但在沈从文整个生活、创作道路中,我们仍能看到其家世或隐或显的影子。
注释:
〔1〕孔庆东:《试谈沈从文的自卑情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第180—190页。
〔2〕〔4〕〔5〕〔9〕〔11〕沈从文:《从文自传》。
〔3〕〔美〕金介甫:《应该怎样认识沈从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2期,第181—184页。
〔6〕〔7〕〔8〕沈从文:《卒伍》,见《沈从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333页。
〔10〕沈从文:《夜》,见《沈从文小说选》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
〔12〕沈从文:《老实人》,见《沈从文文集》第1卷,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13〕刘西渭:《咀华集·篱下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第69页。
〔14〕《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15〕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见《新文学史料》1988 年第4期,第157页。
〔16〕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