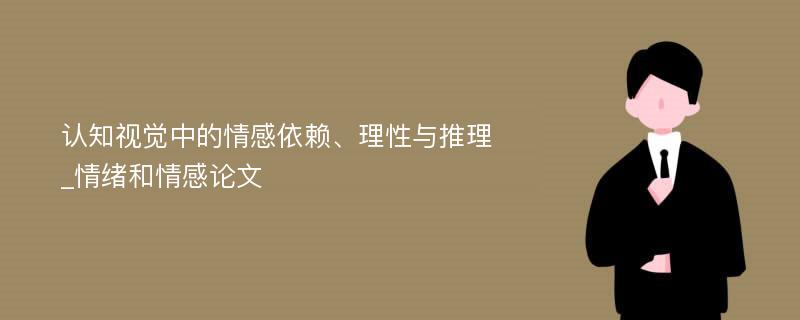
认知视野中的情感依赖与理性、推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视野论文,理性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千百年来,理性被看作是人类的本质属性,而情感作为一种身体对行为在生理反应上的评价和体验,也一直被视为人类灵魂或精神存在的基础。尽管人们已经认同理智的过程融合了非理性的因素,但在生命最本质的意义上揭示它们的内在关联机制,却是在生物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20世纪末,情感现象及其与其他认知过程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代认知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已能够解释一些潜藏在道德判断与伦理考量背后的大脑运行机制,然而,理智与情感是否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以及情感如何影响推理和判断,依然是备受关注的学术话题和颇具潜力的研究领域。
一、情感在何种意义上是理性的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虽然情绪和情感有区别,但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将它们统一起来,取其共同之处,即把它们都看作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身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文中对二者的差别不再加以区分,从而在很多地方将它们互换使用。这一理解也是受斯宾诺莎的启发,斯宾诺莎把动机、情绪和感受等概念总体上都称作情感,他认为这是人性的核心方面。在探讨相关问题的著作中,他既不是用情绪(emotion)一词,也不是用感受(feeling)一词,而是使用情感(affects)一词来指代所涉及的概念,因为他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情状。
自古希腊始,理性主义就认为,情绪的侵扰会误导诸如理性和决策这样的高级认知功能。柏拉图曾在《斐德罗篇》借苏格拉底之口描述人的灵魂犹如一辆由两匹飞马驾驶的战车。这两匹马中,一匹是白马,代表人的道德和节制;另一匹是黑马,代表人的情感和欲念。而这战车必由人的理智来驾御方能完美。①在他看来,只有圣人和精神病人能成功地克服狂热的激情与欲望。情绪或激情不断挣脱理性的控制,成为人类灵魂的潜在威胁。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会说,各种激情是改变人们判断的情感。当然,他并不仅仅认为情感像头脑中的噪音干扰了纯粹理智的思考与表达,而是较为全面地理解情绪的功能,例如,情绪可以使行为再次出现;情绪对回忆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情绪激动时会妨碍记忆,因为激动会失去意志的控制,使回忆不能按照要回忆的方向进行,不过,愉快的情绪是会增加记忆效果的。②
尽管如此,作为日常生活基本素材的情感体验,仍被认为对人们理解认知活动并非不可或缺,人的理性思维是一项独立的心智活动,无需情感的影响。譬如,我们劝人要理智客观,不能被感情所左右。但斯宾诺莎认为,情感和情绪与认识或思维相伴。他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通过情绪,我们能理解身体的变化,身体自身行动的力量以及有关身体变化的观念一起,或得到增强或被减弱,或得到帮助或被阻碍。③
及至休谟,情感和情绪已被纳入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过程之中。在休谟看来,情感是一种原始的存在,它构成了行为活动的最初动力;理性则不一样,它属于观念的范畴,是对最原本的情感和意志的一种复本。正是理性的这种自身本质的规定性,才使得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单独构成任何意志活动的动机,在指导意志方面也不能反对情感。抽象的或理证的推理只在指导我们有关因果的判断的范围内,才能影响我们的行动。④比如雨天带伞,从理性上说是为了保持衣服的干燥,但感觉告诉我们被雨淋湿衣服是件不快的事。也就是说,只有出现了我关心的事、我的爱好或某种对我有吸引力的东西,符合情感、在情感的推动下,那些理性原则才能在我身上发挥一定作用。所以,休谟说“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⑤休谟并不否定理性对人的意志行为的作用,但他认为,只有理性与情感共同作用,才能产生完整的或者说正确的意志行为。
不过,即使人们认可情绪是动机中的有力因素,但是对于情绪能否有助于理性行为则仍感到怀疑。有人认为,情感就像生理的干扰,无法构成行动的理由。因为情感的内容是空洞的。也有人认为,情绪虽然具有认知内容,但是过于个人化,是生理(或甚至病理)反应的产物,无法提供行为可靠的理由。不过,近年来许多哲学家开始为情绪在理性或行动理论中的地位平反,并提出应重新评估情感的重要性。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甚至主张,情绪本质上是理性的,在这种背景下,“理性的”这个术语不是指外显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种对有机体表现情绪有利的行动或结果的连接。这种回忆性的情绪信号本身是非理性的,但它们促进了可以理性获得的结果。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词可以说明情绪的这种特点,它就是“合理的”(reasonable)。⑥神经学家科林·卡默勒(Colin Camerer)等人在进行行为研究后提出另一形象的比喻,他们指出,人的认知力是小马驹,情感则是高头大马。
理性的推理已被证明难以通过计算实现,因为,汇集一套解释数据的假说,其所需的时间,随着参与命题数量的增加而呈指数性增长,就此而言,没有一台电脑可以穷尽所有的搜索。然而,人类思维模式和当前的计算模型利用的是启发式技术,如反向规则的链接和激活概念的传播,它可以缩小假设搜索的范围。而情感是人类启发式搜索的宝贵部分。一旦要解释的某个事实被标示了重要的情绪特征,那么解释它的相关概念和规则也被赋予了情感方面的特性。例如,当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的结构,他们对于双螺旋的想法异常兴奋,而后者与结构推测具有密切的关联。
可能有人会对情绪的功能进行反驳:即使情感在发现语境中发挥有益的作用,它也必须排除在辩护的语境外。对于语境的这种区分最早可追溯至逻辑经验主义。卡尔纳普和赖欣巴哈等人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信念的连贯系统,这些信念通过逻辑推理的链条与经验证据相联。这些链条提供了科学知识得以辩护的“语境”,逻辑经验主义者为自己规定了充分阐释这种辩护语境的艰巨任务。此外,他们把辩护语境与另一语境区分开,这就是科学信念得以形成的发现语境。在他们看来,与辩护语境不同,科学发现的语境是不需要理性的,它是情绪、愿望和社会利益的积聚所在,应由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去分析研究。也就是说,促使科学理论产生的心理、社会、政治、历史等外在因素属于发现语境;而基于中立观察基础上的理性计算则属于辩护语境。科学发现是一回事,对科学理论的证明则是另一回事。两种语境之间的区分推进了如下观点,即:无论科学理论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都只允许被可获得的证据的准确推理(reasoning)所证明或反驳。
然而,情感在推理过程中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作用。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之后,科学家个人的心理因素已成为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评价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情感可以使某一前提突显出来,从而使个体更偏好这一前提所得出的结论;还可以对各种事实的存储予以协助,使得我们能够在无需仔细考虑的情况下迅速作出反应。推理通常是由惊异引起的,这是一种我们的预期被扰动时所发生的情绪反应。我们在遇到与原有的信念不符的事实时,会产生由情感的不一致所带来的惊喜,于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令人惊讶的事件。在解释性假说的评价中,面对某一假说,你确信它具有解释力,这种评价往往是由一种愉悦感引发的——高度一致的学说以其优雅美丽而受到科学家的好评。在此,从一致性中产生的欣喜就成为我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评估的一部分,而焦虑感可能暗示着现有的理论不十分融贯,它可能引发人们寻找新的假说。可以说,一种代表了情感的直觉可能是评价相互竞争的诸多假说是否具有高度融贯性的一个有效预示。此外,我们知道,类比有助于推理,而情绪往往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类比。例如,要解释的事实F1与已经得到解释的事实F2相似,且科学家在用假说H2解释F2时拥有积极的情感态度,那么他们可能会兴奋地用H2去解释F1。类比把正性情绪从一个理论转移到被看好的另一个与之相似的理论。当然,它也可以传递负面情绪。因此,无论选择所要解释的事实还是指导寻找有用的假说,情绪都是产生解释性假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对情感与理性分离传统的挑战,并非针对发现语境与辩护语境这一区分本身。相反,它代表着认识上的一种转变,即从把知识看作由抽象的逻辑规则捆绑在一起的统一的信念系统,转变为把知识看作一种设置了适当的程序和目标且连接较为松散的一系列认知实践。事实上,认识论最近几年发展的知识模型已不再符合最初遵循的语境区分的假设。⑦例如可靠主义。它认为,一个信念如果通过一个可靠的方法形成,那么它就被证明为合理的。而情绪在科学信念的形成中发挥了可靠的作用。
二、理性选择:“满意”而非最优
传统的行为学理论认为,如果人们能够获悉所有相关信息,那么他们就可以确定并做出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理性人假设(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甚至假定了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任何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会运用各种运算法则和规范化的逻辑程序进行有意识的认知加工,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为自己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然而在真实的行为中,人们往往追求的是“满意”而非最优。这里的“满意”指的是,选择一个最能满足个体需要的行动方案,即使该方案不是最理想或最优化的,这就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⑧按照理性的要求,行为主体应该具备关于每种抉择的后果的完备知识和预见。由于后果产生于未来,他们必须凭想象来弥补尚未发生的体验,除此之外,还要在全部备选行为中进行选择,但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而言,他们只能想到全部可能行为方案中的很少几个并且无法对未来的状态进行正确的预测。完全的理性导致决策人寻求最佳措施,而有限度的理性导致他寻求符合要求的或令人满意的措施。
人们力求达到完全的理性而又被束缚在其知识限度之内,这恰恰是情感发挥作用的地方。有限度的理性行为产生了比按逻辑和计算方式行动更合理也更真实的结果。神经经济学研究发现,人们面对短期决策时,非理性冲动因素在人脑决策中的作用与猩猩毫无二致。还有实验表明,人类的大脑在被迫根据极少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或证据做出决定时往往感情用事且不合逻辑,甚至不能达到冲动性与自我控制的平衡。最后通牒游戏较好地展现了情感和理智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游戏是这样的:先给参加者甲10美元,然后让他决定从这10美元中分出一部分给参加者乙。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给乙1美元的情况下甲的收益最大,他能获得9美元。而乙则应该接受甲的这一建议,因为得到一美元总比一分钱都没得到要强。可是,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家乔纳森·D.科恩进行的实验揭示,实际情况与“理性最佳方式”相去甚远。充当乙角色的参与者在听到甲只给他们1美元或2美元的建议时,无一例外都拒绝了甲的提议,超过半数的人都拒绝接受低于20%的价码。充当甲角色的参与者约2/3的人提议分给对方的比例都在40%—50%之间,只有4%的人开出低于20%的价码。⑨
跨文化研究还显示出,无论国别、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或计算能力如何,实验结果都没有明显差异。这是因为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自私行为相比,全世界大多数人更崇尚公平公正。参照实验把甲替换为电脑,结果不论电脑给出了分多少钱的建议,角色乙都很乐意接受。对此,科学家的解释是:在与人作此游戏时,人会觉得钱太少,自尊心因此受到伤害;而在与电脑游戏时,则不存在这一感受。研究人员借助。fMRI(功能磁共振成像)可以从屏幕上观测到在整个游戏过程中人的大脑的运作情况。当角色乙接到甲少得可怜的提议时,其大脑岛皮层(insular cortex of the brain)部分就会变得活跃起来。岛皮层是大脑中相对简单的部分,它与愤怒、厌恶等负面情绪有关。研究发现,做决定的过程中,前额叶皮层促使人做出选择:扮演角色乙的参与者其岛皮层越不活跃,他们就越倾向于拒绝甲给出的1美元提议。⑩
那么,人脑中主情感与主理性分析这两部分区域相冲突的迹象是如何的呢?格林(J.D.Greene)与科恩(J.Cohen)等人发现,当人们苦思冥想要在牵涉到徒手杀人的两难困境中作抉择的时候,他们大脑中的几个网络会被激活。首先包括脑前叶的中央延伸部分,该部分涉及对他人的感情;其次还包括前叶的背外侧部分,该部分涉及持续的心脑计算(包括非道德推理);还有第三个区域,那便是前扣带皮层,大脑某个部分的冲动与另一个部分的忠告之间的冲突就在这个区域中体现。但是当人们思虑一个不需要亲自插手的两难困境时,人脑的反应则大为不同:只有涉及理性计算的部分被激活了。另外有研究表明,因前叶受损而感情迟钝的神经病患者只会从功利角度思考。该研究支持了格林的理论:我们的非功利直觉是感情冲动战胜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11)
再思考一下著名的“电车难题”:设想你是一辆有轨电车司机,电车正高速运行,刹车突然失灵。前方是道路岔口,岔口左边轨道上有5名工人正在维修轨道,右边轨道上只有一名工人。如果你听之任之,电车将拐到左边轨道上撞死那5名工人。拯救这5名工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扳闸改变电车路径,那么你将撞死1名工人。你会做何选择呢?另一种情形:你正站在天桥上目睹那辆失控的有轨电车,但这次轨道上没有岔口,你旁边正站着一名工人,如果你猛地把他推下天桥,他将摔死,他的尸体将阻挡电车前进,你是杀死这名工人来拯救5条性命,还是活生生看着5条性命魂飞天外?
从逻辑上看,这两个问题应该得到相似的答案。但大多数人更愿意扳闸换轨而不愿把别人推落天桥。那么,为什么在一种情形下是正确的事,在另一种情形下却变成错误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道德判断的逻辑规则而在于判断者的情绪。正是情绪推动着道德判断的选择。尽管两种选择都能拯救5个人的生命,但它们触发的脑部机制不一样。直接用手去杀死别人,任何时代都被看成是不道德的,它会唤起那些古老的、占据压倒性地位的负面情绪,从而否认杀死那名工人能带来任何好处。而做出扳闸换轨的选择,则是我们的祖先所未遭遇过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原因和结果被一系列机械和电子所分隔,因此选择扳闸换轨不会触发突然的道德选择。我们依赖于抽象理性思维——例如权衡代价和后果来判断是非。(12)可见,人们的理性抉择追求的并非“最佳”而是“满意”。
三、情感影响推理的神经基础与进化解释
情感是对主体的内部状态的感受。通常情况下,感觉的产生起因于外部事件。推理所作的决定是以事实为依据,它要求做到公正和明智,但它也往往基于什么感觉是“良好的”或“合适的”。这样,推理发生的基础必然涉及整个身体。躯体标记就是作为以前情感经历的化学记录,存储在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访问它们,把它们与我们遇到的情形进行匹配,判断出哪种选择是最好的。(13)
能否设想,一旦离开情绪的指引,完全诉诸理性与逻辑时,人类的行为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20世纪90年代,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研究了因中风、肿瘤或脑部遭到重击以致额叶皮层部分功能受损的病例。眼窝前额叶皮层(简称额皮层)专司情绪判断控制,这部分结构受到损伤时,病人会丧失大部分的情绪功能,他们在面对可怕景象或美景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产生正常身体反应。
这样的病人在接触外在世界时,不受情绪干扰。那么,他们是否会变得非常讲求逻辑,是否能看穿蒙蔽常人的情感迷雾,走向完全理性之路?情况刚好相反,虽然基本注意力、记忆、智力和语言能力都完好无损,但他们却很难做出决策,甚至连简单的决定都无法做出,任何一个小的目标都无法实现。造成这一麻烦的根源或许在于,患者情绪的丧失使得他无法赋予不同的选择以不同的价值,无法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形成一个正确的定位。换言之,他们的内心没有喜恶之感,以至于做每一项选择都必须用理性逐一分析对错。而正常人面对这个世界时,那充满各种情绪的大脑会立即自动地评估种种可能性,并且做出最佳选择。只有在两三个方案都不错的情况下,才需要用理性衡量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14)
这些患者的推理缺陷以及管理自己生活的缺陷,是由与情绪相关的信号受损所造成的。这使他们不能够使用自己在生活中累积的与情绪相关的任何阅历,也就是说,在面对一个给定的情境时,他们无法激发与情绪相关的记忆来帮助自己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达马西奥的研究也证实,即使最基本的智力和语言能力看起来没有受到损害,脑损伤也可能导致患者丧失已习得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规则。由于情绪已成为决策者决策时的一个重要信息源,如果与情绪有关的大脑区域受损,那么,患者可能在社会性计划和决策上出现严重缺陷,而大脑健全的个体则会由情境诱发的情绪更好地做出决策。情绪在个体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已为科学实验所证实。
在某商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考察了经理人在执行MBA项目中对虚构的战略和战术管理困境的反应,并用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测量他们的脑活动。通常被认为与战略思考相联的脑区是脑额叶前部皮层,它使得人类能够从事预测、模式识别、概率评价、风险评估和抽象思维。然而,在这些被试中,即使是表现最佳的战略执行者,其脑额叶前部皮层神经活性也比与同理性、情绪智力联系在一起的脑区(如脑岛、前扣带皮质等)显著减少。换句话说,意识执行功能在淡化,而无意识情绪区域的加工操作就自如多了。同时,战术推理不仅依赖于前扣带皮质,还依赖于与解析感官刺激、预期他人想法和情绪相联的区域,如颞上沟。(15)可见,通过对认知和情感的神经基础的研究,既可了解某一个特定的认知和情绪活动在大脑的哪个区域以及在什么时间发生,也可了解认知和情绪的发生是否涉及相同大脑部位的活动。
事实上,大脑中没有专门负责处理认知和情绪的区域。即使被奉为情绪中枢的“边缘系统”(如杏仁核)也具有认知功能。对颅骨的相关研究揭示出,推理并非存在于某一个脑区,它依赖几个具体脑区的协同配合。从前额叶皮层到下丘脑和脑干,即无论是高级还是低级脑区,都参与了推理过程。正如达马西奥指出的那样:推理和情绪实际上是依赖于相同神经系统的不同心理机制完成的。(16)因此,可以说我们用来思考和用来感觉的组织结构在生理系统中相互交织在一起——逻辑性思考与情绪感觉使用的其实是同一种类型的细胞和化学物质,生理基础决定了完全独立的推理任务很难实现。
不仅如此,而且所有更为高级的理性计算过程实际上都事前受到躯体标记的影响。达马西奥认为,情感被躯体感觉皮质记录时会产生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后者对情感进行评价并长期保留在躯体中,这样,躯体信号在遇到新情况时就能够指导有机体的行动。例如,有些产生负面情感的行动会被自动屏蔽。这种影响可能发生在各个层次的神经系统中,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因此,身体在建构情感等认知活动的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17)也就是说,情绪这一有组织的状态,不仅起着动机的作用,而且也起着知觉的作用。
达马西奥描述了他所参与的如下实验:给一个患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实施中枢神经手术,手术破坏了部分中央前回皮层,其与情绪通路的神经传递有关,但对通向皮层体表感觉区的神经通路却没有影响。结果该病人报告虽然类似的疼痛来自相同的部位,但疼痛的强度却减弱了。达马西奥提出了这样的假说:任何一种感受都是由两个心理特征结合而成——一个是由某种刺激引起的在神经中枢的初级映像,另一种是伴随的情绪。这两个心理特征是由两个不同的神经通路产生的,然后在第二级神经映象区中结合起来,由此产生关于这一刺激的完整的感受。可以说这是对“感受”的组织结构的新的发现和解释,揭示了感受的深层本质,并且表明了情绪在具体的感受中的独立性。(18)
从演化的角度看,在大脑的演进历程中,情感引起的躯体标识机制比人类高级思维更早地形成,情感过程不仅先于理性过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理性过程。作为进化遗产的一部分,情绪在与认知和思考的互动过程中,导引我们的行为朝向生存以及繁衍的目标。(19)人类智力还不发达的时候,情绪就已经在帮助人类“思考”并做出抉择,以便反应敏捷地进行自我保护。事实上,情绪存在的意义就是忠诚地为我们争取生存以及采取利己行动。达尔文很早就指出,情绪具有优化人们互动方式的进化价值。(20)人类是群居动物,人类以群居的方式进化了几千年,并以群体共同合作的方式一起工作。像所有的群居动物一样,人们需要快速地判断和读懂种群里的其他人。而情绪告诉人们,可以接近哪些人,需要避开哪些人,以及人们当前的状况是同自身价值需求保持一致,还是背道而驰。
人类在演化过程中获得了远此一般动物更复杂、更精致、从而也更强大的情感能力,例如,进化使人类具备了一种反感粗暴对待无辜者的本能情绪,这种本能倾向于压倒一切关于人命得失的功利的计较。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经受住了严格的自然选择,达尔文将其原因归纳为三:首先,情绪能够在环境未提供客观分析所需的信息时给予实际上有用的指导;第二,情绪促进决策的情形比阻碍决策的情形更常见;第三,情绪有助于人们的行动快速而果断。显然,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观点,理性是生物个体面对没有先例的事物时的一种神经反应模式,主要用来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其能量消耗要超过本能和情感。因此从效率角度看,如果生物个体的所有行为都采取这种方式,显然是不经济的。
四、情感影响推理的可能机制
近十几年来,理智与情感之间的交互影响逐渐成为国内外认知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行为和神经科学研究证明,情绪对认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心理功能与神经机制两个层面上。在心理功能层面,情绪对诸如记忆、注意、言语、决策等认知过程都具有明显的影响。在神经机制层面,传统理论所认为的认知脑与情绪脑的分离已经被大量研究证据所否定,新近许多研究发现,参与认知加工的重要脑区参与情绪加工过程,而在情绪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脑区也参与认知加工过程。(21)情感和认知是一种更为宽广的系统的组成部分。感情激发动机或目标形态,而后者反过来又会影响未来过程的程度和本质。研究证实了理智与情感存在交互作用,那么,这种交互作用的具体机制是怎样的?
已有研究表明情绪对推理影响存在三种可能的机制:一是情绪影响工作记忆,二是情绪影响条件归因陈述的解释方式,三是情绪影响即时决策。Forgas提出情绪浸润模型(the Affect Infusion Mode,AIM)。(22)所谓情绪浸润是指在个体学习、记忆、注意和联想等一系列认知过程中,情绪有选择性地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甚至成为信息加工的一部分,从而使得个体认知结果产生情绪一致性效应。这表明,情绪在个体的认知活动中能够发挥组织作用。
关于情绪对认知活动的组织作用,过去人们曾认为,一般来说,正性情绪如愉快、兴趣等,对认知活动起协调、促进的作用;负性情绪如担忧、沮丧等,则起破坏、瓦解或阻断的作用。但新近的研究却发现,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情绪都对条件推理起到了抑制作用。例如,Oaksford的研究表明,积极的与消极的情绪抑制了推理是因为在情绪的诱导下,中央执行加工系统会自动加工一些与推理不相关的任务,后者占用了一定的执行加工的空间,从而导致推理的缺损。(23)亦即根据认知资源分配理论,可推断抑制作用产生的原因是,演绎推理加工主要是在工作记忆中完成,而情绪的启动占用了工作记忆中的认知资源,减少了用于推理的资源,从而导致更多的推理错误或推理失败。
对于与心境相关的记忆削弱作用,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解释是埃利斯和阿什布鲁克(Ellis & Ashbrook)提出的理论,其依据是注意和认知干扰概念。它认为,悲伤或任何一种情绪状态可能引发以下机制:(1)间接的情绪引起与思维无关的任务,这会干扰到任务的完成;(2)直接发生的情绪改变了可获得的大量空间,降低了分配到记忆任务上去的认知资源。无论哪种机制,无关思维与相关的记忆任务相竞争都会导致注意容量减少,从而对记忆任务的操作产生不利影响。(24)
当情绪诱导事件与推理任务同一时,一定强度的积极情绪会提高被试推理的能力。而即便如此,正性情绪对认知的促进作用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取决于情绪的强度水平。研究表明,认知操作与情绪强度呈倒U型的关系,中等强度的情绪状态可以使认知操作达到最优水平,过低或过高的愉快唤醒均不利于认知操作。这一不同唤醒水平的情绪对认知活动的不同效应称为叶克斯—道森定律(Yerkes-Dodson Law)。
情绪导致诸多特殊的认知倾向。一般情况下,正面情绪注重人们的内部、主观的数据、提示探索性的加工;负面情绪注重人们的外部、客观的数据,提示系统性的加工。研究发现,生气会使人关注的范围变得狭窄并使其注意一些特殊的事情,悲伤可以导致对影响目标完成的障碍的偏重。负面情绪比正面情绪更多提示对信息进行系统的搜索。并使人把注意力集中于细节和问题的特定方面,运用更多的个体化信息。这大概是由于正面情绪的个体往往会依据诸多表面信息做出判断,而负面情绪的个体对这些表面信息并不满意,因此,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信息。(25)不仅如此,认知过程在情绪的影响下变得有选择性。人们倾向于回忆那些与他们进行回忆时的心境保持情感一致性的信息(即心境一致记忆,mood congruent memory),例如,高焦虑个体倾向于注意威胁性刺激,并将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和情景解释看作是威胁性的,而悲伤会使人们高估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与此同时,个体提取何种信息还可能取决于回忆时情感状态与对信息进行编码时情感状态之间的一致性(心境依存记忆,mood dependent memory)。(26)可见,情绪对个体获取信息的范围和选择信息的倾向有重要的影响。
在心境和记忆的关系问题上,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联结网络理论,它是分别由鲍尔(Bower,1981)、克拉克和伊森(Clark & Isen,1982)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特定的情绪状态,如抑郁、愉快或焦虑,都以特定结点或单元来表征。这些结点或单元包括与每一种情绪有关的方面。情绪结点能够被许多事件激活,而且活动很容易扩散。因此,当一种情绪被激活以后,情绪结点就会把这种兴奋扩散到与之相连的记忆结构,(27)导致信息的搜索产生偏向,从而出现与心境一致的记忆或者思维。
图式理论指出,一个人占优势的心境状态可以看作是加工、组织信息和指导回忆的功能结构。悲伤和抑郁的个体具有一种占优势的抑郁图式,这种图式会有选择地组织信息,并为与心境有关的特定的记忆指引回忆方向。贝克(Beck,1979)指出,抑郁是由某种特殊的压力引起的,是这种特殊的压力激活了一种主导图式,抑郁与注意偏好和对带有消极信息的记忆有关。
情绪不仅影响对信息的选择和加工,还规定了认知策略与风格。人们会因所处的情绪状态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思考历程,例如,人们在正向情绪下会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采用一般性的知识和经验法则,行动上也依赖于常规;而当人们处于负向情绪状态时,则倾向于改变现状以改变当下的负向情绪,表现为仔细、小心地采用逻辑分析的思考方式去处理信息(Schwarz & Clore,1996)。受试者个人的情绪状态也会影响决策。被引发哀伤情绪的受试者会倾向做出能够改变现状的决策;而被引发厌恶情绪的受试者会倾向做出排斥或拒绝性的决策。Forgas发现,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人比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人在人际感知和传递信息方面更有效。(28)
大量实验表明,愉悦的情绪状态倾向于使个体采用快速节俭启发式策略,进行自上而下的加工,较少注意加工对象的细节。所谓快速节俭启发式利用最低限度的时间、知识和运算能力做出现实环境中的适应性选择。它们能够通过设定目标或选项来解决系列搜索问题,使用易于操作的决策引导它们对目标或信息的搜索。这种方式仅仅进行选择性的搜索,但可把尝试的次数减到最小,以便迅速、经济地解决问题。(29)这种自上而下的加工(top-down processing),又叫概念驱动加工(conceptually driven processing),亦即知觉者的习得经验、期望、动机引导着知觉者在知觉过程中的信息选择、整合和表征的建构,也称为建构知觉(constructive perception)。此时,大脑中的观念和期望会影响到,哪些刺激被注意、如何将刺激组织起来以及大脑如何解释它们,即对刺激的解释有引导作用。与此相反,消极的情绪状态倾向于使个体进行自下而上的加工,较少依赖原有知识结构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刺激物的细节上。自下而上的加工(bottom-up processing)也称数据驱动加工(data-driven processing),是指个体接受外部刺激后,将环境中细小的感觉信息以各种方式加以组合形成知觉。总之,这些迅即的情绪反应能够中断现有的认知加工并将其重新引向最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从而影响个体认知策略。
五、情感:一种内化的行动
情感对推理的影响前文已述,这里强调的是,本文不是在二元论的意义上讨论它们的,也就是说,不是把“情感”和“推理”表述为相关的两个并行过程,而是说明情绪是推理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人内在的心理向导,与推理的网络交织在一起,体现了“心灵与身体的统一”。换言之,情感“寓于”推理,推理依赖处于环境中的大脑和身体系统,心灵和精神是生物体的一种活动方式。
如果推理不是脱离身体的独立实体,如果情感不仅仅是“对推理起作用”的存在于理性之外的心理现象,那么,能否尝试一种“基于情感的推理”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在于:推理不仅不是脱离身体的某种实体或者属性,而且原本就是行为或者身体活动。推理系统是作为自主情绪系统的延伸进化而来,行为的产生以及做出有利于自己生存和进步的决定都需要规则和策略方面的知识和特定脑系统理智的完整性。这意味着情感是理性和推理的基础。如果把二元论支配下的心灵称为实体之心,那么“基于情感的推理”所强调的是:心灵与能动身体活动的等同。
也许有人会怀疑:理性与情感之间如此的紧密联系揭示了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着生物机制,这是否在把人类行为简单地还原成具体的生理机制,把社会现象降低为生物现象?回答是否定的。虽然文化和文明都源自生物个体的行为,但是,这一行为却是某种环境下相互作用的个体共同产生的,因此它们不可能被退化到生物机制层面。对它们的理解不仅需要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还要对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生物物理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进行足够的了解。
这要求我们建构一种对于人类行为的多重层级解释的图像。在此我们仅以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为例予以比较和说明。认知科学关注心智能力是如何工作的,比如,情感是怎么一回事?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怎样影响了认知?这些问题都在问“如何”,它们是关于某一类生物的现实问题,而无关非现实的或可能的生物类别。也就是说,认知科学根据特定的心智能力所对应的神经生理学基质来探讨产生这些能力的基本心理组分。而心灵哲学要问的却是,什么是如此这般的心智能力或心智状态?譬如什么情感?什么属于理性?我们追问这些“什么”的问题,是针对所有具有相关心智能力或心智状态的、现实的或可能的生物,关心心智能力或状态的共性或普遍特征是什么。所以,神经科学并不直接为心灵哲学所思考的问题提供答案,因为那些普遍性的问题理论需要在更宽泛的层次上进行思考。
许多情绪是行动的动机,这不是因为它们是行动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表明了与“相信”有关的东西以及“相信”的构成组分;用作为动机的情绪驱使来解释某一行动,不是在某种解释(如愿望、习惯和倾向)中引入另外的因素,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渗透到人类的普遍行为中。
当涉及行为选择时,人们的合理性原则常常诉诸贝叶斯决策理论,后者的目的是“使预期的获利最大化”。作为一个规范的原理,贝叶斯法则对于所有概率的解释是有效的,但概率不足以产生对于实践问题的明确结果。面对复杂而笼统的问题,人们往往依据可能性而非概率来进行决策,从而产生了行为结果对经典模型的系统性偏离。这也说明了逻辑是有缝隙的,而情感的作用恰恰在于填补纯粹理性决定行为和信念所留下的空隙。
我们知道,知觉经验有表征的功能。但是经验以什么方式表征主体环境中的事物、性质和关系?它是如信念、判断等心理状态一般,以概念性的方式来表征世界,还是以一种非概念的方式进行表征?近年来,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以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和布鲁尔为首的概念主义者主张经验要为信念提供理由,起到知识确证的理性作用,其内容必须完全是概念性的。而皮考克(Christopher Peacocke)和克瑞(Tim Crane)等非概念主义者通过经验信息的丰富性、一致性与细致性等论证表明,经验内容具有非概念性的组成。(30)
相对于概念内容,非概念内容的表征比较困难,也缺乏任何类似语句的结构,而且不能作为信念或判断的内容。非概念性内容虽然不属于理性空间的片段,但它们提供了心灵与世界的因果性协调,(31)一些属于情感类的经验就包括在此类。情绪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丰富细微且具有非概念内容,一个人的思想、知觉或内心影像常常可以描绘出来,但情绪却经常缠绕纠结难以厘清。
情绪的作用之一体现在它确立了问题。情感中包含着识别(recognition),其间存在着将人们吸引到判断或欲望之中的诱惑,从而为信念和欲望做了铺垫——对于情感所问的问题,判断是用信念来回答。正如问题对于答案具有密切关系一样,在这方面,情感可以说就是判断,其意义在于人们往往藉情感来观察世界并帮助理性做出判断。这种机制使个人把通过经验获得或加工的知识与后来的感受体验联系起来。与未来行动结果有关的情绪暗含了对将来的预测和行动结果的期望。情绪和感受虽然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但在适当情境中,可以成为事件的一个先兆性提示。这种预期性的情绪和感受可以部分或完全发挥作用,也可以显在或隐蔽地发挥作用。
情绪里的认知是某种方式的判断,包括命题式的、非命题式的和无意识的,甚至连情绪的感觉本身也是一种判断,它可以不是事件的(episodic),而是程序性的(procedural)。情绪的认知判断形式有着高度的多样性,但大抵分为两大类——思想或知觉,前者是抽象的判断,涉及的判断明确、单一,后者是具体的影像,涉及的判断丰富且包含多方面。认知的一个高层次呈现方式是思想。思想在人心理上的意义,绝不只是命题那样的一个逻辑建构。思想可以是事态或事件,也可以是如信念那样的倾向性判断;知觉可以是程序性的(procedural),也可包括像运动的判断或情绪的感受等等。(32)各种情绪感觉的彼此区分造成情绪感受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在这个意义上,它本身成为某种判断。这样的判断有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其客观方面是表达外在环境关于生存的状况,例如害怕的感受反映出外在环境里有让人惊骇的危险状况,因此产生了意向性。其主观方面本身构成生存和幸福的一部分,例如,害怕的感受本身令人难堪。人总希望平安,不愿让内心惊恐、接受快乐避免悲痛——平安快乐的内在感觉也是一种价值。
但是这样的判断与一般的认知判断非常不同:它既非抽象的命题、概念,也不是知觉或与知觉类似的内心表象,甚至在其中没有对象与性质的区分,也不描述外在世界的状况。它是一种具有评价性的判断。情绪评价是一个认知与感觉联合的关系,评价本身并不直接表达外在世界的状况,它所直接表达的是情绪主体关于个体生存发展的状况。情感也评价欲望的前景,有些欲望或其成分本身就可归为情感。情绪中思想性与非思想性的各种认知判断构成多样式、多层次的洞察体系——洞察外在环境关于个人安危的状况,从而提供情绪评价。
作为一种评价式的诠释,情绪引导着一个经验模式或场景。只要我们假设了某些基本的或预先存在的欲望,动机将指导控制注意力,突显特性、偏好以及推理的策略。情绪的判断系统并不构成观点或观察的框架,情绪营造着一种景象或情境,事物在其中以某种方式被看作或想象成某个样子。因此,情绪是一种内化的行动(internalized actions),在这个行动的情境中,人与他所关心的世界联结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情绪可以解决复杂环境所呈现的很多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情绪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对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无益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推理过程的混乱。情感可能不适当地缩小搜索解释的范围。如果科学家沉迷于某种特定的假设,他们可能会被蒙蔽而变得盲目,从而阻碍他们去发现非同寻常的假说来解释一些特别令人费解的事实。情感在缩小假设搜索范围方面具有宝贵的认知功能,但是,像所有的启发机制一样,它们也可能会把搜索引入歧途。尤其当挑起激情的目标是私人性的而又缺乏审慎的态度时,这种误导更加容易发生。如果科学家对于能使他们富有和出名的假说特别兴奋,那么他们不大可能去寻找那些少利可图的假说,但后者却有更大的解释力。可见,即使在科学中,也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个人的情感偏见通过情绪感染蔓延到他的同行。正是由于情感可能放大认知扭曲的影响,因此,基于情感的推理和决策存在改进完善的余地。
情绪所展示的结论非常直接和迅速,但情绪信号并没有替代正常推理,它只是起到一个补充作用,以增加推理的效率和速度。这是因为,行为决定的中间步骤或知识是不能缺失的。在推理过程中,由于决策环境的不同和决策者经历的不同,情绪必不可少地参与可能产生有益或有害的结果。情绪和感受是生物调节机制的表达,而推理策略的有效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要依赖后天发展出的感受能力。
同时,推理对于情感的依赖并不意味着推理没有感受重要或推理处于次要地位,也并不能否认自由意志的作用,相反,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我们需要对自己脆弱的内部世界给予更多的关注。了解感受的重要地位会让我们懂得如何增强它们的积极效果,减少它们的潜在干扰,从而免于计划和决定过程中的非正常感受所带来的危害。
此外,情感的变化是透过操纵个体“想什么”和“注意什么”来起作用的,但这样的操纵并不总是可行,它可能被先前的情感所阻碍。即使某一情感已占优势,情感和注意力在因果上的顺序也并未确定。情绪对于决策是促进还是阻碍还要取决于情境,尤其是当我们试图把推理计算运用于社会决策时,更是如此,因为许多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是很难进行评估和比较的。例如,邀请一位有魅力的陌生人约会,如果把“被拒绝”看作是一种损失,“被接受”则被看作是一种收益,那么,要给约会的结果赋值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我们只知道存在着被拒绝的概率,但却无法确定准确的数值。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社会环境的反应是主观易变的。可见,理解人们在自然情境中的选择要比理解实验室游戏规则困难得多。
情绪的影响机制极其复杂微妙,随着无损伤技术在心理学中的应用,我们将会看到阐述情绪对推理作用的更加精致和详细的理论。因此,关于正在加工的情绪内容是通过何种精密机制影响逻辑推理的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正如哈蒙德所说,直觉与分析是同一谱系上的两端,重要的是弄清楚情绪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使直觉与分析的成分比例在两极间发生变化,以及在什么情境或背景影响下情绪的直觉和认知的系统分析分别占主导位置,对这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33)
责任编审:柯锦华
注释:
①《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163、168页。
②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09页;《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1页。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3-244、142页。
③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8、165页。
④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51-453页。
⑤休谟:《人性论》,第453页。
⑥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寻找斯宾诺莎》,孙延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⑦Jeff Kochan,Reason,Emotion,and the Context Distinction,http://www.univ-nancy2.fr/poincare/documents/CLMPS2011ABSTRACTS/14thCLMPS2011_B1_Kochan.pdf.
⑧H.A.西蒙:《管理行为》,杨砾、韩春立、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0-21页。
⑨陈光宇:《奇妙的学术“联姻”》,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5439000.html,2007年3月5日。
⑩"Interpretation of the Human Bra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http://en.uuuwell.com/article-1064284-1.html.
(11)史蒂芬·平克:《道德本能》,朱力安译,http://www.infzm.com/content/38475,2009年12月10日。
(12)J.D.Greene,et al.,"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 Science,vol.293,no.14,2001,pp.2105-2108.
(13)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8、144页。
(14)乔纳森·海特:《象与骑象人》,李静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15)Roderick Gilkey,Ricardo Caceda and Clinton Kilts,"When Emotional Reasoning Trumps IQ," 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88,no.9,2010,p.27.
(16)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第60页。
(17)Antoine Bechara and Antonio R.Damasio,"The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A Neural Theory of Economic Decision,"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vol.52,2005,pp.336-372.
(18)A.Damasio,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New York:Harcourt Brace,1999.
(19)薛莫(Michael Shermer):《狗摇尾巴》,潘震泽译,《科学人》2008年第75期5月号。
(20)参见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10-214页。
(21)刘烨、付秋芳、傅小兰:《认知与情绪的交互作用》,《科学通报》2009年第54卷第18期。
(22)J.P.Forgas,"Mood and Judgment:The Affect Infusion Model(AIM),"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117,no.1,1995,pp.39-66.
(23)S.C.Moore and M.Oaksford,"Some Long-Term Effects of Emotion on Cogni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vol.93,no.3,2002,pp.383-395.
(24)H.C.Ellis and P.W.Ashbrook,"Resource Allocation Model of the Effects of Depressed Mood States on Memory," in K.Fiedler and J.Forgas,eds.,Affect,Cognition and Social Behavior,Toronto:Hogrefe,1988,pp.25-43.
(25)王翠玲、邵志芳:《国外关于情绪与记忆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综述》,《心理科学》2004年第5期。
(26)J.D.Mayer,"Mood-Congruent Memory and Natural Mood:New Evid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vol.21,no.7,1995,pp.736-746.
(27)P.A.Lewis and H.D.Critchley,"Mood-Dependent Memor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vol.7,no.10,2003,pp.431-433.
(28)J.P.Forgas,"When Sad Is Better than Happy:Negative Affec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ersuasive Messages and Social Influence Strateg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43,no.4,2007,pp.513-528.
(29)哥德·吉戈伦尔、彼得·M.托德:《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刘永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30)Tim Crane,"What Is the Problem of Perception?" Synthesis Philosophica,vol.2,no.40,2005,pp.237-264.
(31)Michael Tye,"Interview for Mind and Consciousness:5 Questions," Patrick Grim,ed.,2009,https://webspace.utexas.edu/tyem/www/5questions.pdf.
(32)R.Solomon,"Emotions,Thoughts,and Feelings:Emotions as Engagements with the World," in R.Solomon,ed.,Thinking about Feel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76-88.
(33)K.R.Hammond,Beyond Rationality:The Search for Wisdom in a Troubled Tim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55-262.
标签:情绪和情感论文; 情绪理论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推理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