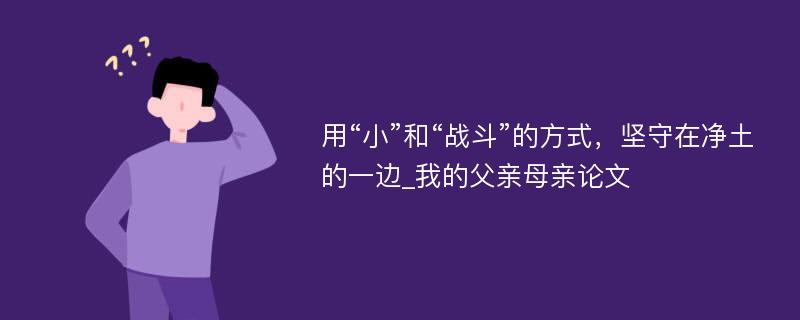
以“小”搏“大”坚守一方净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净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访:张艺谋
采访:黄式宪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李尔葳 影评人、电影制作策划人
时间:1999.10.18
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咖啡厅
张艺谋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扬威威尼斯。在手捧金狮奖回到北京之后,他的另一部新片《我的父亲母亲》也开始宣传发行。与此同时,一本名为《张艺谋神话的终结》的书中的某些观点也激起了我们想和他一起谈谈的兴趣。
滴水见太阳:呈现本土化传统美学风范
黄 对现在的电影市场,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而不是盲目地自信,我们会看到它可悲的一面。这是一个无序的市场、一个非良性的市场、一个非文化性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现状下,你说你要以小搏大,除了把握影片的娱乐性以外还在追求一部影片的文化品位。《我的父亲母亲》很朴素,很能打动人。许久以来,这是我又一次被你的影片深深打动。“母亲”扶着门框的微笑可以比作蒙娜丽莎。你的真情是非常可贵的。所谓的文化品位就是你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放到了你的银幕形象里,这不是商业片的做法。为什么你会这么固执地追求这种“心动”?这种追求和你以往的影片有什么关联?你怎么来看“以小搏大”中的“小”和“大”?
张 简单来说,我所说的“小”,首先是指制作规模。我目前拍的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小制作”电影。第二是指题材。我选择的不是那种特别重大的题材。因为我知道,凡属重大题材,它必定跟老百姓关系不大。我更希望在题材上贴近普通人,表现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命运。我想我指的“小”主要是这两点。尤其是在第一点上要很清楚,因为它是市场所决定的。我们曾经被观众无数次地热烈呼吁和强烈要求:拍一部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一部类似于《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电影。观众完全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呼吁,他们也希望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但我本人非常清醒。因为今天的中国电影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今天在海外市场能卖得好的,能卖得比较稳定的,中国只有几位导演。年轻导演现在是有一下没一下。大部分年轻导演的作品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院线。哪怕是艺术院线,能进入的也很少。他们还都在一些国际电影节或某些研究机构徘徊。也许将来会进入电影院线,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制作对于中国电影不太现实。而且你去骗人家的钱拍一部“大制作”,事实上也骗不来,因为人家很清楚这个市场。我们反复地谈中国电影如何如何,也为我们中国电影的获奖而欢呼,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我们到国外市场去看一看就知道,国际市场对中国电影的需求量非常少。他们不需要,没有看的强烈欲望。市场安排不进去。
李 现在的状况是不是比前几年好一点?
张 我觉得也不行。我们只能在自己市场的良性循环中来考虑我们的制作规模。只有“小”才能保证我们的市场是良性的,投资人才会有信心继续投资电影,我们的导演才有机会获得经济来源拍电影,才能一部一部拍下去。就算市场不景气,但因为你的电影“小”,它就能生存。当然,谁都知道“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道理。小题材、小制作未必不可以搏大,求大未必就一定能拍得成功。有的时候,越是收缩起来拍一个小东西,如果你拍得很透彻,可能更有穿透力。
黄 我注意到,你这次拍《我的父亲母亲》是追求一滴水的光芒,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朴素,却很深刻。其实,像齐白石、梅兰芳的作品就是由繁到简,后来越来越简。
张 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华所在。这可能也是东方人思维的一种定势,所以我认为“以小搏大”,或者收缩起来,以小单位进军,以小团体作战,可能是在经济规律上、在生存的现状上、甚至是在保持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美学特质上恰恰都是好的。因为中国人是讲小不讲大。我们虽然老讲“搏大”,但很多东西都是从小处入手,从形而下入手,于细微处见精神。
黄 这叫“在微尘中见大千世界”。
张 这是传统。所以我们这种收缩到以小单位进军,其实恰恰是从纯国粹的角度找到自己。
黄 你这个以小搏大,是不是想以中国的小制作与好莱坞抗衡,以此作为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引导?
张 我还没有这样想。我们还不能跟好莱坞争市场。可以举日本的例子。我的片子十几年一直在日本做后期。你可以在五年或七八年前看到,日本的电影几乎是死亡的。日本有一年只拍五部电影。但现在的日本的电影却有一点回升。像《情书》、《弹弹琴、跳跳舞》这样的电影是在日本首先轰动并获得高票房的。日本电影为什么回升?是因为日本观众看好莱坞太多了,反而倒了胃口。而中国观众还刚开始看好莱坞,兴趣还大着呢,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抗衡呢?我们只能保持自己。守住自己的阵地,守住自己一方净土,我们的价值在于:大家吃腻了汉堡包和麦当劳之后回头看,也许在五年、十年之后回头看,那时他们才明白:哎哟,他们那时候还拍了这种颇具中国本土文化气息的“小”电影,很不容易。
黄 其实真正能抓住中国人心理的电影还是会有观众的。所以你说的“以小搏大”实际上也还有一个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问题。
张 其实人家就是大,我们就是小。我们不能以小装大。
黄 你拍电影有你自己的方位。一位年轻的学者把你的方位定位在“过去、边缘、本能”,这显然是在拿西方的理论去套你的电影。我并不认为你的电影全都是描写性本能的,或是只讲“往昔”,不讲现实的。你谈的“小”一是体现了你的美学追求,另外也体现出你对小人物和普通人的关注。《我的父亲母亲》做得非常平易、单纯。只要静下心来,人们就能体味到那种苦难中的纯情。而且也是你对世纪末心态的一个挑战,是对“一切向钱看”这种市民心态的挑战。你这种境界是怎样悟出来的?
张 这是我逐渐悟出来的。我最初也不是这种心态。实际上我在最初的时候也是壮志凌云,总希望振聋发聩。像“武则天”这个题材,高蒙公司追了我差不多七八年了,拿着几千万的美金一直等着我,一直催我拍。如果换了一个导演,如果看到这么大的制作,又是这么大的公司在请,可能早就慌慌张张地拍了。虽然我已经在剧本的操作上花了很多钱,但我一直把这件事拖下来。因为我始终对大制作不太踏实,我总觉得它不能激起我真正的冲动。当然作为导演来说,谁都愿意大把花钱,在千军万马中当一个领袖,指挥那么多人、调动那么多人,可能很过瘾。但除了大之外,我好像就没有更多的冲动。我反倒觉得,人们现在渐渐麻木,越来越迷失很多东西。我倒很珍惜我去年看到的这两个小制作的文学原作,珍惜它们带给我的那种朴素的、真切的、细微的、点点滴滴在心头的这些东西。我为之动心。所以,像《我的父亲母亲》从抓了《纪念》这个小说开始,我们就组织了多次剧本讨论会,但包括主创人员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太看好,都说要加强剧情。改了好几稿剧本,一直在加强情节,甚至加强了它的文化内涵,它的历史重量,把父亲的故事从50年代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就像《活着》那样。但后来越写越没有感觉。最后我也弄明白了:你如果喜爱《父亲母亲》,你将喜爱它的单纯,将喜爱它在大千世界无比浮躁下的那种单纯、那片净土。如果你不喜欢,你也不会喜欢它的单纯,认为它过于简单。也可能落得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在观众的反应跟我们原来估计的一模一样。拍摄时我就想:鲍十的小说《纪念》最初打动我的是什么?我对此并没有做出理论的分析,当初打动我的就是那种点点滴滴,是一些平实的温暖,一点点眷恋之情。当时我心里曾为之动了一下。所以我后来要求所有主创都不再谈剧本,只是跟大家说:你们走着瞧,这部电影要用减法拍,而且有一半人会说它太简单,将有一半人欣赏它的简单。那时候(拍之前)我们就料到了观众的反应。
李 这样说来,这种减法最后还是你找到并决定使用的?
张 对。因为它简单,所以它美丽。
李 这种决定是不是来源于国际上其他电影风格对你的影响?
张 其实不是。我倒没太想世界。我只是在考虑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况。还有我们自己的心情。人在很浮躁的情况下要清醒。
黄 你曾经跟媒体谈过,你在《我的父亲母亲》里融进了你父母的故事。是吗?
张 有一点,但很少。我爸我妈的历史我知道得特别少。
黄 但你是不是想借这部影片说明一点:父母一辈子不容易。
张 是。父母一辈子不容易。养育之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感受都一样。我在影片中拍摄的彩色部分,与其说是对父母年轻时代的回忆,不如说是集中了男主人公对父母的一些印象。我们当时是想把回忆部分、彩色部分拍成一种印象。我记得莫奈的《日出印象》,我更愿意把回忆部分看成是一种印象。我觉得应该是印象。我也回忆过我的父亲母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事,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成了印象,没有完整的故事,我们要的就是这些印象。
黄 你的这些印象是通过细节扩展开来的。这些细节又是内在情绪的一种外化。比如那个头发卡子,那个青花瓷碗。
张 这也是我们的设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东西。如何拍一个爱情故事?通常情况下,如果要把一个爱情故事拍好,一定要撕心裂肺、荡气回肠,并且要三角四角,要强烈的矛盾冲突和激烈的情感,要爱得死去活来。只有这样,这个爱情故事才能感人。而我们这个爱情故事是什么呢?还没有开始“爱”哩!如果说,爱情的道路从眉目传情开始到生命结束,是从第一步到第一百步,我们这部电影刚走了“一”,他俩这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哩!好像是单相思。而且刚刚在眉目传情阶段就停止了。然后再跳过来是黑白部分,是一个活着的人在为死去的人做一些事情。这中间是个空白。我们只选择了第一步和第一百步,而没有中间的故事,没有其余的九十八步,我们留下了最大限度的空白。
黄 国画里就叫“留白”。这就有美学境界了。
张 我们最大限度地“留白”。这就是我们想拍的一个独特的爱情故事。这恰恰是跟《泰坦尼克号》最不一样的地方。美国人绝对不会这么拍故事,这么想故事。他不把故事弄透,就不可能拍。而我们的这个爱情故事是很东方式的。或者讲“意境”,或者讲“尽在不言中”,或者讲“留白”,都可以。这是中国传统美学带给我们的对人生和生命的观照。以一当十,这也是我在搞了《图兰朵》以后得到的启示。
李 全世界每年有无数部的爱情故事在拍,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讲爱情。恐怕像《我的父亲母亲》这样的爱情故事并不多见。
张 他们可能都是在抓主体,抓主体的情节纠葛和矛盾纠葛。所以我们想:父母亲从20岁开始恋爱到现在已经70多岁,这中间有多少故事?但我们只留下了漫天大雪中人群抬棺的那种感觉。母亲说:要把父亲葬在井台;母亲说:她将来也要和父亲葬在一起。
李 这种选择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减法”。
张 什么是减法?电影的手法不是减法。应该是创作者观照人、观照自己、观照生活的角度。所以你这么去想一个故事,你马上就知道什么当拍,什么不当拍;什么意见可以采纳,什么意见不要听。
李 这个选择过程用了你多长时间?
张 时间比较长。
黄 你的《红高粱》是戏剧式的,而11年后拍的这部《我的父亲母亲》的主体部分却是对你的《红高粱》的叙事方法的一个挑战。你从那种戏剧式的叙事方式演变为这种散文结构,以表现人物情绪状态为它的叙事方式,这似乎是你自己对自我的一种挑战。
张 对。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谈到过。我们把人的命运进行了“留白”处理。如果拿《我的父亲母亲》和《活着》比较,“留白”是最不同的一点。《活着》就是娓娓道来,是各个历史阶段人物命运的展示。你可以想象“留白”中的故事很多。我知道这种“留白”会丧失一部分观众。但我自己悟到这儿,我就只能按自己的意思去办。我不能按照《还珠格格》的观众层面去给他们拍个故事,那我就损失了我自己感悟到的生命的另外的现实。我是把它看作和《活着》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两个人的故事,两个人的命运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这种方式看起来挺有意思。
李 其实《我的父亲母亲》有它很浓郁的情感。
张 当然,它距我们原来想的还不一样。我们原来想的,在情感方面还应更凝重一点。但一般年轻观众喜欢从表面来看。我觉得也未尝不好。我们这部影片还有另外一个意境:就是听那个读书声。我特别希望把那读书声做成交响诗一样。我觉得,招娣对那位年轻老师的那种感情与其说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对有文化的人的一种仰慕。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谈的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一定有的那种爱慕之心。我认为招娣喜欢那男孩是对文化的一种崇拜。韩美林最近送给我他的一个雕塑。他告诉我:古人总结了人类七种最美丽动听的声音,而其中的一种就是朗朗读书声。我们有意回避了上课的细节表现,主要抓住读书声来表现。其实,我拍这个戏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自己要神定气闲,排除所有的杂念,让自己回到一种特别安静的心态中去拍。因为你知道,那年9月5日,《图兰朵》在北京公映,9月7日我就到了河北坝上的外景地。9月12 日,《图兰朵》的旋律、观众的万众欢呼、媒体的疯狂炒作还在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的这部戏已经悄悄地开机了。对我来说,心态平和最重要。直到现在,我导《图兰朵》的工钱都还没有要回来。因为我忙着拍戏,什么都忘了,也忘了向意大利人要钱。我们在《图兰朵》中追求辉煌,追求灿烂,但我也能一下跳到《我的父亲母亲》的这种单纯的境界。我不太在意《图兰朵》的鲜花和掌声。我觉得那些不重要。我倒在意一部作品的具体创作过程。
记得我在导《一个都不能少》时,《图兰朵》组有一大帮人跑到我所拍《一个都不能少》的农村外景地去谈置景、谈服装,他们带了很多东西去谈。美术师带着华丽的设计图纸去找我。其中一件衣服的价值就值我们在那里拍摄的那个村一年的收入。就是这么大的反差。而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图兰朵》的那些服装还要再绣花,还需要更亮丽。
黄 这是欧洲的大制作和中国的小制作之间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才能静下心来,在这个“小”里面如何找到自己的情感点呢?
张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拍电影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确实要有平常心,确实要有和普通人稍微贴得近一点的情感,确实要让这些普通故事从你的内心深处打动你,而不是说为了电影而拍电影。为了你的电影你才会去关注什么,这样就可能没有一种真正的动心在里面。
李 即使你有条件拍不同风格的电影,要寻找到适合你内容的风格,其实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知你是如何把握这两部新片的风格的?
张 我有一种直感。这种直感可能是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我读完小说,立刻会生出两三种想法。这些想法对将来的电影都是极为重要的。记得我最开始看施祥生的小说《天上有个太阳》,第一直觉就是:要用非职业演员。我看完《纪念》,当时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散文诗。
黄 这就好比种子,如果种子错了,那就根本结不出果实,长不成大树。
张 我特别重视第一反应。这第一反应常常就是你未来影片的纲。有了直觉,你还会有很多审时度势,逐渐把这种直觉具体化。
黄 你是否有意想跟传统对接,比如吴永刚、费穆的电影?
张 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拍一个最含蓄的爱情故事,拍一部最不一样的爱情故事,俩人连手都没拉一下。既然含蓄是我们的特点,那么它在爱情电影中就是一个另类。你在“减”的同时其实是坚守了东方真正有个性的东西。
黄 你的减法是从哪一阶段开始的?是从剧作阶段就在开始吗?
张 一直在“减”。比如我们减掉了招娣和那位年轻老师的很多直接交流,使那层纸一直没有被捅破。这是一个含蓄到极点的爱情故事。既使拿到国际市场上去他们也会觉得很独特。哪有这样谈情说爱的影片?我相信他们将会被感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的个性。我们坚守住了自己最本体的东西。这种“留白”,这种“尽在不言中”,这种“含蓄”,就会使这部影片跟1000部西方电影不一样。我相信每个观众看电影都希望看到“独特”。这部电影就很独特。电影有两类:一类是主流电影。这类电影需要功力,需要做得地道;另一类就是有独特风格的电影。我个人偏爱后者。后者甚至有重大缺点,甚至有败笔,但我还是偏爱。因为我觉得功力这个东西是永远无法达到完美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更喜欢独特性。我觉得独特性是最可贵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太有规矩有方圆了。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气质都太缺乏独特性。我们的祖先最鼓励独特性。而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独特性,在艺术上毫无个性。所以我反复强调:今天电影的形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何谓“百花齐放”?连形式都没有,还谈什么独特性呢?形式就像衣服,如果永远只有蓝的、黑的、灰的那几种颜色,那你还谈什么独特性呢?
李 有一点是你的每部影片都具备的共同特点,那就是无论是你的影片风格还是人物个性,你都会往极致去做。你之所以会有这样不变的追求,是否和你的性格有关?
张 我想是吧!“极致”是我的一贯追求。我要“含蓄”也会含蓄到极致,要独特也会是“极致”的独特。
黄 你所说的“小”也是一种独特。有人说《我的父亲母亲》借鉴MTV的表现手法,你认同吗?
张 我觉得不是。MTV其实是从电影中学习、借鉴、演变而来的。 电影是它的妈妈。MTV也多种多样,有表现性的,有叙述性的, 有游戏性的。风格是五花八门的。这种技巧包括叠化,我个人一直很喜欢。我的《摇啊摇》也用了叠化。我最近去澳洲拍的一个广告也用的是叠化。因为我觉得叠化能给人一种连绵不断的感觉。尤其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用叠化就达到一种韵味。
黄 那一段在风雪中等待,没有叠化就不能渲染那种气氛。
张 这部影片和《红高粱》有异曲同工之处。《红高粱》中九儿在高粱地里走,这部影片是招娣在白桦树林里奔跑,只有意境不一样。
黄 那是戏剧的意境,而这是诗的意境。有一次,凯歌曾经在关锦鹏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说:“第五代”其实是一群浪漫主义者。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张 我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五代”身上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且是从理想主义走向浪漫。他们挺务实的。因为他们一上来就面临着一个务实的时代,而我们经历的“文革”该是多么浪漫。那是残酷的浪漫,但那是浪漫。可那有意思啊,甚至说是荒唐。
黄 是不是有一个境界的问题:浪漫的人能看得远,而务实的人看不远。
张 我觉得一个人浪漫会有很多幻想,你的电影也会有相当的想象力。不一定很写实,但很有想象。直到今天为止,“第五代”导演的作品的想象力要比“第六代”丰富。“第六代”的作品大多在针砭时弊,或者在表现个人的彷徨、苦恼,都很实在,却甚少有想象力。《黄土地》是很有想象力的,《红高粱》也是很有想象力的。我们今天的电影也还是很有想象力的,即使我们的年龄已经大了。
黄 在这样一个务实的年代,你身上的理想和浪漫会不会在现实中流失?
张 我觉得不会。我们经历了“文革”十年那么残酷的浪漫之后走到今天,我们不会丢掉身上的烙印。十年“文革”给我们的烙印是时代给我们的,而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机会去体验。我觉得人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幻想”,而电影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梦幻”。
李 其实很多观众看电影,就是希望从电影中寻找到一种梦想。
张 所以电影就应该给观众梦想的东西。我的很多电影中就有很多梦想的东西。有人说《我的父亲母亲》是一部纯情电影。
黄 你的“纯”就纯在一个“稚”字,有一种“稚”气。这是很不容易的。《我的父亲母亲》针对现在社会的缺情症,实际上是在对社会发出质询。
张 我相信我们这个作品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的那种纯真,它对文化的那种仰慕,这一点使得喜欢它的观众觉得它是最好的电影。
李 还有其他的反应吗?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
张 有人不喜欢,是觉得它太简单了。有趣的是:喜欢的人都很受感动。它勾起很多人至真至纯的久远回忆。这点在观众中反响非常强烈。我相信有阅历的人会喜欢它。因为只有有阅历的人才会感觉这里的“返朴归真”。否则他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这次去全国走四方的感受是:对《一个都不能少》,观众的感受是悲悯,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悲悯。而这次的《我的父亲母亲》,观众是想到自己后的感动。这很不容易。尽管都是让他们感动。
理论的“妙语”:谁在制造“张艺谋神话”?
黄 说到“张艺谋神话的终结”这个话题,有人认为你一直是在迎合西方,而且把你装在“后殖民”的框子里。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张 对于“后殖民”和“后现代”这些词,我至今还弄不懂它的精确含义。但所谓“迎合西方”这种说法已是由来已久。我老说:再有10年大伙肯定就不会再说了。就像当年大家在讨论李谷一的“气声”,《人民日报》都曾讨论这“气声”是不是靡靡之音。现在大家觉得这种讨论很可笑。10年之后,针对我的这种所谓“迎合西方”的说法也会很可笑。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心态。提出“迎合西方”这种论点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西方人,而恰恰是中国人自己。老说我迎合外国人,那我是迎合谁?法国人和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外国到底是指哪一国呢?不能把外国人很武断地类型化。把100多个国家的外国人说成一种类型, 还把电影观众分成内外两种。实际上,电影的实际观众已经没有内外之分了。最早提出的这个概念已然“三人成虎”了。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扎根在这儿了。到今天,这个概念挥之不去了。这是假设敌。
黄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制造神话?
张 我制造什么神话?我觉得电影就是电影,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
黄 最近媒体比较浮躁。评论没有太多发言权。有人说这是评论的倒退。
张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影评。这点是大家公认的。只有记者们的简单报道,似乎是一些特别简单的报道文章在引导观众看电影。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去香港,发现香港报纸上登的那些文章非常之糟糕。倒是我们大陆的很多文章在分析电影的语法,那文章读起来很精彩。但我今天来看大陆报纸,恍若一梦醒来,发现变得像香港一样。对此我们只能议论,可能无法改变。
李 媒体都在说:“观众爱看这些,我们没有办法”。
张 我反对那种说法,说观众的口味是至高无上的,观众的鉴别是至高无上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对。毛主席的话是对的:要普及也要提高。我们的观众是谁呢?观众不是特定的一群。观众是你、我、他,观众是所有的人,是我们人类。那么,人类有缺点吗?人类是完美的吗?我相信:谁也不能说人类没有缺点。人类不但有缺点,而且有致命的缺点。那么,倒过来说,观众有没有缺点?当然有。庸俗化就是人类致命的缺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庸俗的东西。我们喜欢看暴力的东西,喜欢看刺激的东西。这就是俗的体现。如果我们永远去迎合人类的缺点并为迎合这缺点而去制造、去生产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把这些人类缺点给放大了。我主张电影是商品,但应该是精神商品。它有双重属性。它有帮助人类克服自身缺点,引导和激发人类去摆脱自己身上的庸俗的任务。不是说我们自己就高人一等。我们也很俗。我们在创作的同时也在自律和自省。普及是我们的手段,提高是我们的目的。而今天我们本末倒置了。我们抛弃了提高,把普及当成了终极目的。
黄 这是很可悲的。电影既是商品,又是文化。如果纯粹只是成了商品,那就只有一种类型了。
张 而我们现在说出这种论调来,会被别人耻笑为“故作文化状”,“故作高深状”。其实我看到:中国文化正在渐渐丢掉自己独有的特质。我们今天对十几年前非常看不起的东西奉若神灵。人家没有变,我们变了。该留的没留住,不该学的却学到了,甚至我们比别人更异化、更放大、更夸张,普及得更快。我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还一定得有。没有这个过程还没有提高。
李 目前国内影评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你拍电影是套着西方的某种模式去的,而实际上你是在自己对某个题材有冲动的前提下才去创作的,你的电影是从你的情感中生发出来的东西。
张 理论的人尽可以从理论的角度去设想,但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是两种类型的人,是完全两种类型的人。如果他们在用那种类型来套我,那就很可能把我这个人估计错了。搞创作是什么?必须尊重自己的情感,必须从情感入手。如果不是这样,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血没有肉,也谈不上由这个血肉而延伸的理论。我们不可能先从理论上设定,然后按照一种理论设定的路子走。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当然,一部电影出来以后,谁都有讨论它的资格,某些评论家也有他的道理。你根据我的作品去总结点什么,那是你的事。这与我的创作状态和创作观念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所有的理论都可能是过眼云烟,很可能过时或者被时间证明是错误的。作为创作者,我越来越重视的是情感。看一部作品,选择一个东西,我现在只有一个标准:我的情感能不能被它打动。
黄 你认为如果要重建电影理论和创作的那种和谐,回复到80年代中期那种理论和创作互动的状态,我们应该怎样努力?
张 我也不知道,也开不出什么药方。我觉得现在不需要。因为社会没有需求。首先社会不关心。你如果办一个刊物,专门写好的评论,这刊物也一定要赔钱。连个广告都没有。80年代是因为社会如饥似渴的需求,才有当时的评论和那时可爱的局面。现在既使有个老板拿出五个亿办十本杂志,没有需求,这杂志也办不下去。说起来,“需求”是一个虚词。“需求”是怎么造成的?一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我们报刊的引导,是我们自己的鼓噪,自己的庸俗化造成的;二是社会变化的结果。面对这些“需求”,我们无法责难。就我自己来说,我只能在自己的作品中保持一块净土,最好不要同流合污。既然我已经在观众中建立了我的口碑,我就要用这个做我喜欢的事。当初如果每一个导演,如果每一个写文章的记者都能负责任地做好自己那点分内的事,也许局面还不会是今天这样。但社会发展都有它的规律。我们可以等待新的转折点。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庸俗期后,总会有新辉煌出现。
李 在这样漫长的庸俗期内,如何把握自己,这也是一个难题。
黄 你也是随时在面临各种挑战。你要是重复,大家都不会满意。
张 所以我尽量使自己很清醒。我还是按我自己的路线走。我不会被批评所挫伤。
黄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当它在不慎中伤害了创作者的艺术灵性而陷于“泡沫化”泥淖之时,事实上也伤害了媒体自身的文化纯净性。
张 我们作为创作者,应该锻炼自己的承受能力和韧性,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困难面前,我们一定要锻炼自己的韧性。
面对世纪末的“浮躁”:以平常心完善每一次创作
黄 你在投身电影创作之后,似乎性格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是否觉得你的艺术生命也在升华?
张 那我没有理论地想过。但导演这个职业倒是让我变得比以前开放,因为你非要跟别人交流不可。所以由原来的不说话变得爱交流了,离了交流不行了。
李 你现在的表达能力也很强,给我的感觉是很能说。
黄 像你这样追求平常心的人,不知如何看待媒体的做“秀”,媒体的世纪末“浮躁”,媒体对某些作品的过分炒作。《还珠格格》第二集播出以后,满世界的人都在唱《你是风儿我是沙》,实际上这是很浅薄的东西。
张 我们今天还在开玩笑说:赵薇可比赵丹火多了。今天的创作环境已经不如过去,文化的意识在淡薄。有价值的东西在贬值,而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大行其道。我是觉得:我们不可能改变什么。我们只能保持自己的清醒,去认真对待每一次创作。我只能这么做。我们对一哄而上的东西只能发表些议论而已。剩下的就是坚持自己。
李 其实你也一直面临这样的问题。自从成为电影人之后,你也已经无法真正去体验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苦难。
张 你说得对。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面很窄。除了拍电影、搞剧本、跟朋友聊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圈子里的人打交道。今天电影圈的生活其实跟大众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态。你不可能要求你回到老百姓中间去生活,这是现实,但你可以用心态来弥补。
李 很多人都在谈论你平和的心态。不知你是如何保持自己这种心态的?
张 这我也不知道。慢慢来吧。像《一个都不能少》这种电影是很难拍的。你要没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你早就急了。所有的人都会不耐烦,因为这部影片的非职业演员要求我们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去面对他们。我觉得我真是心平气和地一遍一遍地拍,最多的时候一个镜头拍了70多遍。所以说,最近拍的这两部电影是对我的一个考验。我拍这两部电影的最大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锻炼了我的一种平常心,锻炼了我们能静下心来进入一种状态,锻炼了我自己怎样去寻找一种朴实和真情的东西。不求大而求小。
黄 你似乎是在有意识地寻求一种平常心态。
张 我是有意识地这样。
黄 你如何保持平民心态,保持和平民百姓在心态上的贴近?
张 要说平民,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也都是平民。别的不说,我每次回家,我爸我妈就特别老百姓。还有我们家的亲戚也都是老百姓。人的性格、个性除了遗传基因外,都是环境造成的。我也并没觉得自己就成了什么特殊的人。
面临新世纪的自我定位:求诸中国文化的底蕴
李 对于下个世纪的中国电影,你如何预测?
张 我预计国产电影市场还将继续滑坡。可能会到一个真正危机的关头。由于观众口味的变化,由于观众不满足于现状,会刺激电影在另外一个新的原点上重新开始起步。这个过程不会有多长。我们从日本、欧洲、台湾、香港电影身上都可以看到我们将来的自己。我们不可能走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台湾沉寂了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起来,日本已经起来了一些。香港正丢掉昔日的辉煌。
李 你觉得你还能拍多久的电影?
张 我希望我能再拍20部电影。如果身体好的话,我可以拍到七八十岁。这是我的理想。有一次和大学生座谈,他们也给我开处方,也谈到什么“神话的终结”之类的话题。我说:你们不要过早地下结论。我刚拍十几年电影,我大把的好时间还在后头。他们都笑。
黄 面临新世纪,你如何定位呢?中国人吃汉堡包还没有吃腻。你怎样来站稳这个市场,和观众保持持续的联系?
张 我还是想雅俗共赏。因为电影是从杂耍开始的。它注定有其通俗性在里面。这是没有办法的。电影的通俗性是电影的本质之一。你必须尊重一个事情的本质。我认为: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电影导演最通俗。我们看过大画家、大作家、音乐家,他们都比我们有才华、有学问、有艺术家气质。我们导演则挺通俗的。(笑)所以我觉得通俗是电影的特质。
李 就本世纪的中国影坛来说,你可能是最具有国际影响的或者是最有创新纪录的导演。在下一个世纪中,可能会有新的技术和外国电影的侵入。在这种状况下,你如何为自己定位呢?
张 让我想得很远也不可能。有些问题我想也想不到。计划还赶不上变化哩!我只是有时候会这样想:如果我的电影没人看了我该怎么办?我想这是很有可能的。那才是真正的“张艺谋神话的终结”,那才是真正的“俱往矣”。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也非常正常,因为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我只是尽可能保持我的创造力,尽可能地减少失败的可能性。但人总是要老的,人都是要过世的。没有谁会成为永远的弄潮儿。当你明白这个人生的基本道理时,你也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忧虑的。一切顺其自然吧。俗话说:“郎中要老,木匠要巧”,而导演这行却不一定。全世界的电影大师在晚年拍的作品都不如他们在青壮年时拍的作品。要知道这是规律,知道这职业不会让你“越老越值钱”的话,你也就会很镇静了。我想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尽可能也延展自己的弹性。为什么我老拍不同风格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信誉,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些信誉去进行一些大胆的尝试并以此来拓展自己的思路呢?我们应该可以进行一些语言上的变化、形式上的变化。现在没有人再谈电影本体。我们为什么不能对电影本身多做一些尝试呢?因为中国电影在题材上是没有太多变化性的,就剩下电影本体可以变化。如果再不从这方面去做一些探讨,那电影拍出来就没什么价值。
很多导演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是可以尝试这个,我们没法尝试这个。我们在压力之下只能拍这一种类型。而我只想跟大家讲:你自己的市场信誉是靠你自己挣来的。在做导演的最初期,也有压力,所以我才把《红高粱》拍成那样,目的是为了挣钱。果然那片子挣了很多的钱。只要你坚忍不拔,只要你不气馁,只要你有能力,你的市场前景会大大超过我。到那时候,你比我还自由。但你现在还不能这么做。现在中国导演能这样自由的还很少。大部分人必须按照市场的需求去拍电影。坚实的墙是一块块砖垫起来的,不能放弃,不能抱怨。
黄 香港很多电影人步入好莱坞,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张 我觉得,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好事。对于香港电影业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觉得是美国需要,是好莱坞需要。所以我开玩笑说:好莱坞再过五年会需要印度导演。再过三年需要韩国导演,它需要变味,并以此赚钱。这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黄 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中国电影如何生存,你对此有何考虑?
张 怎么考虑?也就是个人的一家之言,不是开什么药方,我也开不出什么好药方。以小搏大,仅是一种求生之道。或许另有高人,另有高招。
标签:我的父亲母亲论文; 一个都不能少论文; 活着论文; 红高粱论文; 爱情故事论文; 纪念论文; 图兰朵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