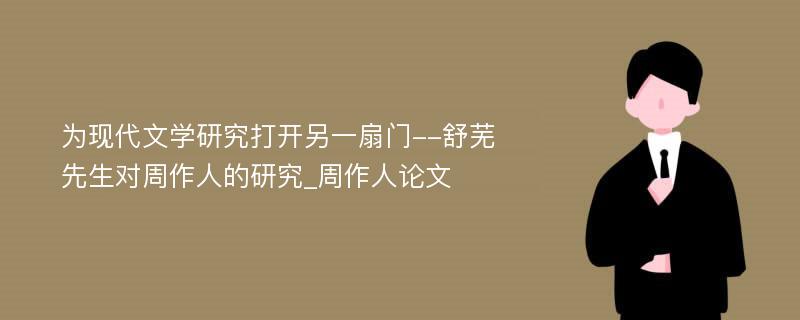
为现代文学研究打开另一扇大门——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大门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他之前我国学术界可以说还没有开展真正的周作人研究,因此他的研究是具有里程碑式开拓性的。通过自己的认真读书大胆探索,他具有远见地指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① 大家知道鲁迅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通过鲁迅再来研究周作人,就可以全面地统观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他的研究远见和开拓性的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拓宽了视野,从而为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早在1985年他就发表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应该研究》的重要论文,指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充分肯定了周作人研究的价值。次年4-5月,他的《周作人概观》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刊载,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周作人是非功过以及周作人研究重要性的论文,可以说此文的发表是新时期周作人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11月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根据当时某刊发表的所谓“周作人的一组新材料”,举行研讨会。舒芜先生在会上应邀作了发言,全面驳斥了这组颠倒历史事实的所谓“史料”。由此开始,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周作人研究成了舒芜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先后出版了《周作人概观》、《知堂小品·序》、《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版)、《回归五四》等重要学术著作,把周作人研究推向成熟;此后又不断扶植新人,为后来的研究者的新书作序写评论,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绩为学界所瞩目。他的周作人研究的精彩论断和基本观点,成为后来从事周作人研究的学者们绕不开的重要参考文献。
统观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鲁迅
鲁迅研究一直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显学,多年来一些研究者虽然不断地利用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作为重要资料,也有个别文章以批判周作人来弘扬鲁迅精神的所谓比较参照,但是还没有开展真正的文本对比式的比较研究。舒芜先生指出:“鲁迅的存在,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不了解周作人,也不可能了解一个完整的鲁迅。”② 很长时间以来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于鲁迅的研究几乎都是孤立的、单独的研究,很少拿他的弟弟周作人来作为参照系;而在五四时期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作为“周氏兄弟”同时出现的,且相互配合、共同承担着启蒙的工作,成为我国新文学史上的双星。但由于周作人后来在政治上的变化,使得长期以来,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思想史上,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是回避了。回首“五四”前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并肩战斗、互相配合,在与封建文化对阵的战斗中打了几次漂亮的大仗,那个时候他们堪称“兄步弟亦步,兄趋弟亦趋”③,正是由于二人同心同德的努力和配合,在那一场场论辩和一次次创作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又同时获得了卓著的声名,然而最终却同出殊归,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充满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最终成为了民族英雄;一个遁入苦雨清茶的隐士生活中转而经营“自己的园地”,最终沦为了文化汉奸。如此天差地别的对比,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和沉思。
在这种情形下,还原那段尘封的历史,将周作人重起于地下,恢复他的本来面目,寻找他与乃兄亦步亦趋的战斗历程,印证兄弟失和前的那段鲜活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从而映照出鲁迅的那段独特的人生和同胞情谊的经历,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舒芜先生的鲁迅和周作人比较研究正是立足于此,正如舒芜先生陈述到其必要性时提到的那样:“我们只有在矛盾的统一中才能更好地研究矛盾的两面,而鲁迅、周作人就是一个统一的矛盾的两面……鲁迅、周作人所走过的道路,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当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④。
毋庸置疑,周作人的研究本身就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视野,从而为鲁迅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领域,这就是研究鲁迅与同时代人,而鲁迅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研究的起点就是从他自己身边的胞弟开始。这一领域的拓宽对于鲁迅研究的丰富性起到了极大作用。何况作为兄弟,周作人与鲁迅出身于同一家庭,有着相似的成长历史、教育背景、读书经历及文化结构,在南京和日本求学的时代,互相督促扶助,回国后又共同历经辛亥革命和投身五四运动,北大教书生活、女师大事件的共同态度,共同的写作生活,这其中最了解此时期鲁迅的人无疑就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因此周作人的回忆无疑是重要的,当然研究周作人和鲁迅的关系与这一阶段的历史、文章与生活对鲁迅研究的意义非同小可。舒芜先生深切地指出:“可惜解放以来……对周作人一生的是非功罪,研究得太少了,结果是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一半,致使我们对整个新文学史,对于三十年代的右翼文学,对于鲁迅,都理解得很片面,很模糊”⑤,这是舒芜先生高屋建瓴的精彩之笔,他不但指出周作人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鲁迅,而且还另辟蹊径指出这一研究对于了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化史的独特意义。当然对于周作人的研究不能仅仅着重研究他们兄弟怡怡、紧密合作时期的方方面面;舒芜先生更提醒人们还应该注重研究弟兄失和、决裂之后,在他们二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异同。他通过对比大量的资料充满信心地指出:“尽管他们越来越走上相反的道路,先前的不明显的差异一一显现和扩大,在现实的急剧发展中更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对抗,纵使如此,他们之间仍然有许多相同:相同的回忆,相同的印象,相同的论点,相同的判断,甚至所用的语言也往往不约而同”⑥。舒芜先生1989年发表的《不为苟异》就是以辩证方法研究得出的成果,这篇论文从九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二周失和之后仍不自主地表现出种种相同之处,分析了共同经历、知识结构、性格异同等对兄弟二人造成的影响。与一般研究中总是习惯性地着眼于挖掘兄弟失和之后的相悖之处相比,舒芜先生这种目光是独到的,见解也是深刻的。
通常我们只说鲁迅是历史乐观主义者,他相信进化论认为将来总是好的,而周作人是个历史悲观主义者,对于兄弟失和后二周仍然存在的相似之处,几乎鲜有人提及。舒芜先生在《不为苟异》一文的篇末,特别谈及到周氏兄弟有相同的悲观史观,他说:“鲁迅虽然同样如此悲观,但是,他又不断地同自己的悲观作斗争……鲁迅的乐观,不是廉价的不解悲观,而正是不断向着大悲观作战的英雄式的大乐观。悲观是外界的反应,英雄则是主动性的发挥。我们只有不讳言鲁迅与周作人有着同样的悲观,方能更明白地看出他们的不同的主动性,如何决定他们的不同道路”⑦。这种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鲁迅、理解鲁迅式的那种深邃的思维模式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在研究中我们不难见到这种观点:因为后来弟兄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便简单地认为好的从开始就是好的,坏的从根基上就有腐败的源头,相比这种表面化、空论化、模糊化的结论,舒芜先生的潜心研究就显得格外弥足珍贵,他本着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注重文本并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客观看待二周的异同,力求发现历史真实的样貌,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一个立体的、全面的鲁迅,而不是将鲁迅塑造为雕像化、神圣化的符号。舒芜先生自己就曾说:“鲁迅的存在也离不开和周作人的既矛盾又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不了解周作人,也就不可能全面地认识鲁迅”⑧。以周作人研究为切入点,他探讨了二周失和前的兄弟关系、失和后的间接联系,从文章中找出兄弟的异同,而且更重要的地方还在于他注重文本和资料,特别辑录和评价了后期周作人在各个方面对鲁迅的影射和贬损,从而看出兄弟的异同。周作人眼里的鲁迅是另外的一种视角,但毕竟是兄弟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认识鲁迅,对于长期以来有着固定思维定势的研究者来说,那种启发、借鉴、清醒与回归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当然舒芜先生对于鲁迅的研究是客观的、坚实的,他从鲁迅那里得到的精神遗产都反映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比如多本著作中都有精当的研究论文,特别是关于鲁迅的思想轨迹、女性观、人生道路的分析等,较集中收录于《回归五四》一书中。
通过周作人研究,舒芜先生对鲁迅的认识也超出了同时代人,他的研究文章比一般人高出一层也深入一层,与此同时通过周作人的研究,也促使了他对整个五四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思索,这些应是毋庸置疑的。
二、“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对周作人这样的作家到底应该怎样对待,是一批到底还是实事求是,从他身上总结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特征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有的人认为研究周作人没有任何意义,更有甚者将周作人研究贬斥为“屎中觅道”认为浪费时间毫无意义。舒芜先生不是这样看,他的观点是不应因人废言,也不应该因言废人,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率先在《周作人概观》一书中指出:“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对周作人的全盘否定,也未尝不是历史的正义惩罚之曲折的体现。这当然不是说忘掉他的历史功绩就是科学的态度,不过是说这种不科学的态度仍然曲折地体现了历史的正义罢了。今天已经是新的时期,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该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忿怒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⑨,这段话道明了他从事周作人研究所本的心态。“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是鲁迅在回忆刘半农时说过的话,当时的刘半农被一些人狂捧,而鲁迅却认为刘已经落伍,远不如五四时期的半农,鲁迅尖锐地指出:“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⑩。面对有争议的人物,这是一种十分大气、豁达、客观的态度,表现了论者的充分自信,也是研究者最起码的素养,作为清醒的研究者必须首先具有这种对史实尊重、对民族负责,实事求是的心态,当然还要警惕鲁迅所说过的所谓“陷沙鬼”,借周作人而抹杀掉现代文学历史的另一面,轻而易举地将周作人的功绩和罪行一同否定,这种思维定式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科学研究态度。
必须承认,如果想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思想史,周作人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之一,正如舒芜先生的评价:“对周作人先前的历史功绩,我们要实事求是的给以肯定,要肯定个够,不怕承认他在‘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都是当时最高的水平,没有人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11)。这样的评价并没有过度拔高之嫌。鲁迅在和周作人绝交多年以后,依然向1936年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周作人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家,阿英、郑振铎、郭沫若、冯雪峰等也曾对周作人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学翻译、小品文创作等方面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舒芜先生认为对周作人的成就估量尚未完整,除此之外还应全面认识到周作人在文化思想和文化建设上的贡献:“他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功绩,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才高出于当时一般的水平,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尽管两人的思想不尽相同,各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则是一样的。”(12) 舒芜先生正是以这种宽广的眼界和深刻的认识为本,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
《周作人概观》最初于1986年刊载在《中国社会科学》4、5期上,当时的周作人研究仍然停留在表面,多是将周作人作为一名成就较高的散文家来对待,或是将其与鲁迅比较异同,或是比较其前后期的差距,而没有整体、深入的研究,舒芜先生此文一出,则将思想史、文化史意义的视野引入了周作人研究,确有开先河的胆识和眼光,无怪曾被研究者评价为“改革开放后周作人研究进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13)。在《概观》中,舒芜对周作人在文学作品译介、小品文创作、文学理论及批评、思想体系、精神结构、文化学上的贡献做了探讨和评价,涉及了二周的对比研究、周作人前后期转变等方面的研究,强调了周作人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以如此全面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为基础,以及作者缜密的论述和独到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周作人研究的最高水平。《概观》中的观点是有着开拓意义的,如当时普遍认为周作人的成就主要在于前期,后期则退回书斋远离社会去经营“自己的园地”,思想与创作都变得狭窄化了。舒芜先生却认为,周作人在译介外国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思想革命、新诗理论和创作、小品文文体建立上的成就,确乎都是前期的贡献;唯有小品文是不一样的,“因为思想固然从根本上决定了文章,但又并不是那么机械的‘同步的’关系,并不是思想一走下坡路,文章立刻就坏了。周作人的小品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我们检视和举证的时候,无法硬性断开。而且我们正好把小品文作为一座小桥,从周作人的前期跨到他的后期去”(14)。周作人前期的散文当然是现代中国散文的经典,有着绝对的不可替代性,用钟敬文的话说周作人的散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周作人那里白菜萝卜比玫瑰花还要可爱。而舒芜先生则指出周氏散文不可替代的地方还在于“只有他后期用小品文画出整个世界,代表着一大部分彷徨苦闷的知识分子的最深刻的情绪,而这些知识分子谁都没有把适合他们的看法的整个世界画出来,在这里周作人才是唯一的一个。阿英说‘我要申说,就是周作人的小品文,在给读者影响方面,前期的是远不如后期的广大。’当时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们研究周作人的问题,也要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15) 通过周作人小品文这座“桥”,舒芜先生提出了周作人思想除了上升期和下降期之分外,在中间还应该有1924—1927年这个“过渡期”的观点,他认为在此期间,周作人并未完全消极,依然有着可贵的“战士余风”,这些见解是颇具有创新性和理论勇气的。
对周作人的小品文风格,在“冲淡平和”的公认评价之外,舒芜先生还发现周作人对平和冲淡的追求,他细致地指出我们看到的是周作人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平和冲淡,而周作人自己追求的是他尚未达到的平和冲淡;对于作品的细读功夫由此可见一斑。此外他还率先以“清淡而腴润”来概括知堂小品,他认为“周作人的小品文的清冷苦涩,并不是‘郊寒岛瘦’那一流,相反地,这种清冷苦涩又是腴润的”(16),不管是从内容、笔法、心境都使文章不枯槁而充满了腴润之美。在周作人散文素雅的表象之下,他认为其特殊意趣是在于雅中有俗,俗中见雅、化俗为雅:“这不是传统的士大夫式的雅,而是化俗为雅,其思想体系是属于现代的民主主义的范畴”(17)。他另外还从周作人散文中总结出了对读者的亲切温暖与无限的意匠经营,这样的深入分析就从单纯的文学鉴赏上升到思想和文化观研究的层面了。对周作人后期散文中备受争议的“文抄公体”,他还有不同以往的见解:“周作人这样‘百中得一,又于其百中抄一’而成的文章,最难得的是所引古人文字简直就像周作人自己写的,可以证明他确是用了他自己的标准,凭着敏锐的感觉挑选出来的……这是周作人的真功夫,不是一般学步者轻易学得到的”(18)。对“文抄公体”体现出的作者的学识、文章和摘引的功夫都做了非常恰当高妙的评价。
舒芜先生对于周作人的研究是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的,他在开始阶段认为周作人是右翼文学的代表,这一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没有再出现;其次他在1987年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个作为总结的《学习发言》,他说自己的《周作人概观》谈到周作人思想发展比较笼统,而那次学术会上有论者把周作人的思想的分期划为两个阶段,即以“四一二”政变为界限,说“政变前是战士加绅士而以战士为主,政变以后是战士加绅士但绅士逐渐占主导。这个分法比我的说法具体多了。”舒芜先生当时似乎对于这个观点是同意和肯定的,他曾说这个观点比自己的更明确云云。但是后来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在为《周作人平议》写的序言中对于这种说法进行了修正。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舒芜先生对于周作人的研究是与时俱进、尊重事实和资料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新进的研究者观点与文章的密切关注。
舒芜先生对周作人的小品文,也并非一味的赞赏而不加以客观的评价,例如周作人小品文中所体现和倡导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冲淡平和”美学的过分张扬等,在文章写作和鉴赏中当然都是对的;但是周作人所处的时代是应当注意的,在那个饥殍遍野炸弹满天的时代,过分强调小品文而不注意实事就很不应该了。他严厉地批判道:“第一,周作人所领导的小品文运动,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宣传一种对人生对文艺的倦怠和游戏的态度,这是一切悲观主义中最坏的一种。第二,它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其实践的效果只能是消磨他们的斗志”(19)。这种研究态度正是“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立场的体现。毋庸讳言,周作人曾是活跃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将文学革命引导为思想革命,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建立开辟了道路,身先士卒进行白话文创作,并奠定了现代小品文的创作高峰和理论机制。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作品离不开时代,就是周作人的小品散文艺术再好,也应该将其镶嵌在他所处的时代框架里。在感时忧国方面,舒芜先生的骨子里流动的是鲁迅的血液。
而舒芜先生对于周作人投敌的史实是从不讳言的,从他对周作人附逆前后的研究中,我们亦能窥见一斑。
三、历史本来是清楚的
舒芜先生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对于周作人的研究是实事求是的,他经常说严肃的研究应该是让研究对象没有话说,也就是起周作人于地下他也应该对于我们的批评无话可说。这就是说坚实的研究应该是可以和周作人进行精神的对话的。
1986年某刊披露一组“关于周作人的史料”,这组“史料”大致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周作人不是汉奸;他出任伪职是由中共地下组织授意;他在附逆期间基本上贯彻了“在积极中消极,在消极中积极”的中共指示。该“史料”一出,便传播开来,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由于流往海外,被一些海外刊物拿出来作为攻击我国文化开放政策的理由。由此“周作人不是汉奸”的说法不胫而走,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影响十分不好。该年11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了首届“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会议围绕周作人出任伪职问题、周作人在敌伪时期的思想和创作问题进行了研讨,舒芜先生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后来整理为《历史本来是清楚的》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舒芜先生以科学态度和翔实的史料根据,进行严密的逻辑推论,反驳了周作人附逆是受中共派遣打人敌人内部的这一说法,并描述了周作人这一时期逐渐堕落的具体过程,痛斥和批判了他的附逆行为。在文中,舒芜先生分别从逻辑可能、外部论据、主观变化三个大的方面证明了周作人的附逆是他自己个人气节的堕落,并列举了周作人下水前后的生活、交往、日记等重要材料,用铁的事实来证明周作人的附逆非有什么高尚的目标,也并非是受到了哪方面的派遣。文中详细解读和剖析了这组“史料”的具体语言并与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比较,特别是辅引周作人日记、回忆录和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为证,十分有力地驳斥了“周作人不是汉奸”的说法。
他首先从逻辑上分析,揭示了这组“史料”的三大疑点并逐一反驳,认为周作人“之出任伪督办,并没有得到中国抗战力量方面的什么劝告和委任”(20),将他的附逆称为“共产党的意思”更是缺乏根据的。其次舒芜先生从周作人日记入手,重点研究了日记中透露出的周作人附逆前后的社会活动、交际范围、当事人心态等,论证了这组“史料”的可疑性,得出了“所谓‘周作人不是汉奸而是中共派遣打入伪政府的’的惊人新说,并无根据”(21) 的结论。除此之外他还深入地探索了周作人这个时期的日记和作品里传达出来的各种复杂信息,包括思想、情绪、行为、生活上的种种改变,从一开始的辞不出任、心态苦闷,到后来的接受伪职、亲善和赞同敌伪政府官员、生活奢靡,一个享誉文坛的大作家如何堕落为文化汉奸,在舒芜先生笔下被毫不留情地勾勒出来。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舒芜先生是从周作人身上寻找“内证”:首先是周作人对于华北汉奸汤尔和、大汉奸汪精卫等人的态度,其次是他出任伪职以后家里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最后是周作人用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对待他担任的伪职的地位。他从大量的日记、书信和研究成果中列举许多事例,在铁的事实面前说明“历史本来是清楚的”!由此舒芜先生严肃地指出:“决定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的,主要是他自己的这种思想状态,而不是别的什么”(22)。
除此之外,舒芜先生还多次批判周作人附逆的行为。他在“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就曾公开评价:“周作人是个文化汉奸,没有杀人放火,从政治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作为文化人来看,周作人在道义上文化上所犯的罪过比这一切都大。那就是‘丑’。这个丑在当时给整个中国文化都丢了脸……(他)把全国知名的清高的苦茶庵主人的形象变成一个丑恶的汉奸,这是周作人对于民族欠下的道义上的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23)。
他最有代表性的对周作人的定论是在《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中的第一篇《改观》,该篇的第十五十六两节,就专门论及周作人的叛国投敌,他尖锐地指出:“周作人自己将自己从英勇的战士和高雅的隐士的形象,变成这么丑而又丑的汉奸形象留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当然也就永远对国家民族欠下了这笔债,不是他自己的种种辩解和别人帮他辩解所能抵折的。”
正因为周作人曾经有着那么大的成就和名声,他附逆的行为不仅不因此得到抵偿,反倒更见其丑、影响更加恶劣。这样意思的话自舒芜先生从事周作人研究以来强调过多次,他的周作人研究是在具备这种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扎实进行的,周作人既已投敌,从此就是欠下国家民族重债的千古罪人,如此有悖于道德良心的行为谁都不能为之翻案,这个案铁证如山是谁都翻不了的。因为历史本来是清楚的。
但是研究不等于翻案,把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等同起来的观念是非常有害的。以舒芜先生为首的研究者的诸多著述对于周作人的种种丑行,包括专搞大批判的武断者们知道和不知道的,都没有超出他们的研究范围和所举的资料,因为周作人研究者并非对这些一无所知,才研究周作人;也不是以为读者一无所知,可以替周作人掩护隐讳的。从各种的文章中可以找出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充满了一种既痛惜又悲凉的沉重情感,他一贯反对偏狭独断和苛酷之风,提倡宽容精神与理论思辨勇气,这是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健全和发展功不可没,他给研究界开拓了新的思路,那便是从鲁迅研究和其他作家研究转到或者重新开启了周作人研究,使得现代文学研究变得丰富也避免了单打一的惯性思维模式,其意义十分深远。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从另一角度拓宽充实了鲁迅研究,与此同时对于与周作人相关的其他作家的研究也相继展开,以往不提或被忽视的那段尘封的历史和那些作家又重新引起重视,有利于全面认识现代中国文学史,特别是有利于抗战期间沦陷区文学的发掘,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宽阔视角,去全面认识现代文学史中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思想论争及其他方面全貌,促进形成一个实事求是丰富多彩的文学研究环境。
舒芜先生以一种宽广、公正的学术胸襟从事周作人研究的业绩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他的那种开放态度更值得后人学习。他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一点也不袒护,在各种压力和误解中,他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从而为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因为他始终知道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对于各种现代作家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和研究,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应该是留给后人的警示。
注释:
①②⑨(15) 舒芜:《周作人概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3、3、5、45页。
③ 李景彬:《鲁迅周作人比较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23) 舒芜:《参加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学习心得》,《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第7、8页。
⑤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罪应该研究》,《读书》1985年第1期,第65页。
⑥⑦ 舒芜:《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494页。
⑧(11)(12) 舒芜:《周作人概观》,《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页。
⑩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13) 何亦聪:《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53页。
(14)(16)(17)(19) 舒芜:《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审美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第5、16、20、31页。
(18) 舒芜:《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20)(21)(22) 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第25、32、35页。
标签:周作人论文; 鲁迅论文; 小品文论文;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舒芜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