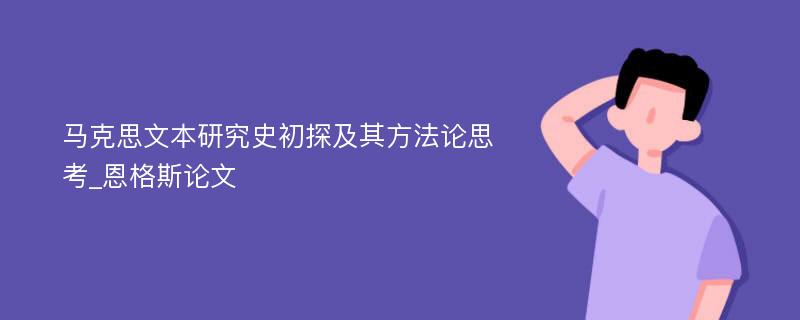
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初步清理与方法论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基于两种作用的合力:一是对经典文献的翻译、出版、阐释和宣传;二是由其后继者特别是政治家所推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二者之间当然是内在关联、不可分割的,但也不能把它们完全看作是一回事。因此,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就是对经典文本研究史的反思。而且,在新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获得深化和突破,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对研究历史的清理和方法论的反思。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初步的分析,以引起学界的注意。
一、马克思重要文本的刊布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重要“事件”的梳理
在宽泛的意义上,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史是由其文本、文献材料的保存、收集、翻译、出版、解读、阐释、宣传的历史构成的。马克思文本的特殊性在于,它们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其生前公开出版的,大部分是他去世之后才首次陆续面世,其中20世纪又占了绝大多数。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这些文本的保存、面世历经坎坷,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囊括他所有著述的全集出版。(参见埃斯纳尔)因此在这断断续续的刊布中差不多马克思每一部重要文献的发表,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持久的争论。这里根据我自己所搜集到的显然还不完备的资料,将马克思身后其重要文本首次刊布的情况列表如下:
马克思身后其重要文本首次刊布一览表
文本篇目
时间整理者编辑者
刊布处
《资本论》第2卷1885
恩格斯
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88
恩格斯
斯图加特(作为恩格斯《费
尔巴哈论》单行本的"附录")
《资本论》第3卷1895
恩格斯
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
《工资、价格和利润》
1896
爱琳娜
伦敦
《给父亲的信》 1897 《新时代》第16年卷(1897) 第1卷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
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
然哲学的区别》 1902
梅林 《马克思恩格斯遗著》
(博士论文)
给库格曼的一批书信 1902《新时代》第20年卷第1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903
考茨基
《新时代》第21年卷第1卷
《巴师夏和凯里》
1904
考茨基
《新时代》第22年卷第2卷
《剩余价值理论》 1904-1910 考茨基
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
(给左尔格和丹尼尔逊)1906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4卷1386封信) 1913 倍倍尔、
伯恩施坦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
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1926《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2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1927苏共研究院
《<自然哲学>提纲》1929苏共研究院
全集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流亡中的大人物》1930苏共研究院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卷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932朗兹胡特 全集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卡
迈耶尔
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集》
《德意志意识形态》 1932 苏共研究院 全集考证版第1部分第5卷
《数学手稿》
1933 苏共研究院
《法兰西内战草稿
(初稿、二稿)》 1934 苏共研究院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8卷
《编年摘录(Chronologi
che Auszüge)》("历史 1938-
学笔记")
1940、1946
苏共研究院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8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857-1858年手稿) 1939-1941 苏共研究院 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单行本)
"摩尔根笔记"1946苏共研究院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2卷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 1956苏共研究院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
1958 《苏联东方学》杂志第3、4、5期
;
1959苏共研究院 《苏联东方学》杂志第1期;
1962
《亚非人民》第2期
"菲尔笔记"、"拉伯克 1972 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
笔记"、"梅恩笔记"(阿森版)
在上表所列的情况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事件:
1.马克思辞世时留下数量极为庞大的手稿和藏书,其中手稿包括数千万原稿、1542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和4400封他人致马克思的信,藏书中则有马克思众多的眉批、评注等等。历经磨难,藏书保存已经不太完整且较为分散,幸运的是手稿比较完整而集中地保存下来了,原件主要保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院,原苏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存着最全的手稿复制件。
2.表征马克思“新世界观”基础、核心、纲领和重要思想构架的文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于1888年、1932年发表。
3.作为马克思毕生用心之所在的《资本论》第2卷、第3卷、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及其手稿的整理、出版。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发表,引发了把马克思思想做人本主义化解释的思潮,孕育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5.被称为“历史学笔记”的《编年摘录》和“人类学笔记”(包括“摩尔根笔记”、“菲尔笔记”、“拉伯克笔记”、“梅恩笔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发表拓展了对马克思研究视域的认识,但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马克思晚年为什么不集中精力完成《资本论》的实际写作而关注起远古与东方的情况。
6.由梁赞诺夫主持、旨在供专家学者研究所用、力求囊括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第1版(MEGA1)于1924年开始编辑,1927年正式出书。原定四个部分共40卷,后来实际共出版12卷(13册),中途夭折。第2版(MEGA2)1972年出了试编本,1975年由柏林狄茨出版社正式开始出版。原计划100卷,1990年代出齐。后来,卷数扩大至120-170余卷,完成时间推延到21世纪。在前苏联东欧事件后,MEGA2的出版受到严重影响,后来转由新成立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组织出版。1995年在“基金会”的领导下,制定了新的出版计划,卷数确定为114卷,载至2002年4月共出版52卷,至今尚未编竣。
7.旨在供宣传、学习所用的俄文版第1版1928年起出版,1948年出齐,共39卷;第2版1955年出版,至1969年出齐,共50卷。以此为蓝本,参照、翻译出版了德文版39卷、中文版50卷。
8.1959年,法国巴黎社会学研究中心的米里安·吕贝尔创办《马克思学研究》,认为“马克思的大宗思想遗产、他的大量社会活动、他的众多门徒、他的著作发表的曲折历史,加上至今尚无一个包括了他的全部著作的可靠版本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巨大意识形态分歧,使马克思学的存在成为必要”。
9.对由《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第1卷构成的一套文本系列,和由博士论文、《莱茵报》以及《德法年鉴》等报刊上的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等所构成的另一套文本系列的解读,形成两个不同的马克思形象、两套解释模式、两种现实策略。
二、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不同类型的初步评论
在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历程中,由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情形、千差万别的研究动机、错综复杂的社会氛围,对马克思文本的关注程度、探究重点、解释思路、观点阐发等方面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差异,形成了多种派别或研究类型。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由于与马克思的特殊关系(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而对其文本的写作背景、经过、观点有经验性的实际了解和把握,拥有为后来的研究者不可能具有的条件、优先解释权和权威性。这当然首先是指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之一的恩格斯,也包括马克思的亲属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所做的阐释、宣传和研究。
不言而喻,马克思身后恩格斯是其文本最权威的解释者,他将自己的整个余生都用来处理自己的伟大朋友的遗著。他非常清楚自己无可替代的作用,有极为庞大的设想和计划,准备写马克思的传记和1843—1863年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第一国际史,准备刊印马克思全集,再版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并为它们写序;特别是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完善化和系统化是个相当急迫的任务,因此在一系列著述中开始了这一艰巨的工作。当然恩格斯的上述愿望,只实现了很少一部分。总体上看恩格斯是通过《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等著述和晚年大量书信,通过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3卷和再版第1卷来向世人展示马克思思想的。通过恩格斯的论述来了解马克思,是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接受者的一条途径。这里有争议的问题是,恩格斯是否把马克思的思想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公允地看,我认为,第一,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恩格斯是有意偏离更不用说歪曲、篡改马克思的思想,相反他在接受亡友的遗嘱编辑整理其遗著的时候,是极为慎重、甚至可以说是诚惶诚恐的。他曾经写信给人说:“在编辑出版时,我最关心的是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版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得出的各种新成果……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自己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5页)第二,我们又必须说,从1883年马克思辞世到1895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阐释又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他只能结合自己的工作,突出那些有现实针对性或他认为非常急迫的部分给予强调,或者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去考虑、补充或完善那些马克思生前涉足甚少或论述不够的部分,梳理或系统化那些分散的环节,而不可能面面俱到,也许有些甚为重要的方面,他认为只是常识而没有予以重视。第三,退一步说,即便恩格斯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文本,完整地表述了马克思的思想,在接受者那里也未必就能形成一一对应的理解或接受。
爱琳娜是马克思遗嘱的另一位委托人,她以《东方问题》文集的形式再版了马克思论克里木战争的文章(1897年,伦敦),首次刊印了《工资、价格和利润》报告,还发表了马克思的一些书信。此外,狄慈根、梅林、考茨基、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也对马克思的原始文献做了较为通俗、详尽的阐释,扩大了马克思著述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对思想体系的全面性分析,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有关哲学探究的对象、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哲学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内涵的理解,他们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水准。
2.由于复杂的局势使其无法在短时间内无选择地将手稿全部公布,而只能在现实斗争中首先刊布那些不容易引发大的争议但又有利于论证其政治主张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篇章。这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马克思文稿的保存、刊布所做的工作。
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的手稿和书信由爱琳娜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保管,没几年爱琳娜也去世了,它们便全部落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手里。由于革命策略上的严重分歧,过去前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著述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马克思遗稿这段历史颇有非议,特别指责其领导人“拖延”著述的发表或有意“篡改”马克思的原意,“在政治思想性上和技术上都很差”(列文,第120页)。现在看来这种指责多是不准确的。在1895年至1914年期间,作为马克思的遗嘱的主要出版者和发表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公布了马克思的许多手稿,以文集的形式再版了一些很少为人知道的著作,翻印了一些最重要的作品。在十月革命之前这些版本都成了各种外文译本的原始资料,并为各国(包括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广泛利用。他们出版了《新时代》(Neue Yeit)杂志,使其成为发表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主要出版物。
这里要特别谈到考茨基整理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其体力严重不支,整理马克思留下的庞大手稿的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而剩余部分马克思的字迹更为凌乱,这样就急需培养能够辨认马克思手迹的后继者,考茨基就是这样参与到对《资本论》第4卷的整理中来的。应该说,经过恩格斯的悉心指导,考茨基本人也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和心血,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手迹的规律和特点,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造次,因此在恩格斯去世近10年后才陆续推出他所整理的《剩余价值理论》。列文指责考茨基任意挪动原文的某些部分,破坏了马克思的著作的结构,这是言过其实了。事实是,在马克思留下的手稿中,有些逻辑结构顺序和自己编的页码不符合,考茨基就调整了页码,并且仅限于几处,并且特意加了注解予以说明。列文还指责考茨基对原文“做了重大删节”,并且举例说,在两个地方把马克思的原文删去了大约半个印张,有一章(半个印张)整个被略去,更不用说个别的页码和段落的删节(同上,第12页)。事实是这两处是马克思手稿中重复的部分,马克思在先写了第1遍后,自己划掉了,后来可能是感到还是保留下来好,就重新写了一遍。我认为不能因为政治见解的不同而抹杀上述工作的价值。
3.由于职业和身份的特殊性质(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家)而在现实斗争中突出了马克思文本中那些特别有利于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篇章,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传播,扩大了它的影响。
列宁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现象,这就是经典作家的职业和身份发生了变化。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首先是政治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学说与政治活动融为一体。他们的思想家资格不容怀疑,但却是归属政治家类型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也显示着一个政治家特有的思路和视角,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新特点。他们倾其一生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对时代的鉴定源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革命策略的选择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他们十分注重在普通民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效果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4.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而使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对其文献材料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的收集、整理、考证、翻译、出版和研究,在具体解读和阐发中形成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苏联模式”。
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出版、普及和研究的规模在苏联空前扩大,并且纳入国家发展的计划。前苏联学者在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取得很大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特别是在梁赞诺夫主持时期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功勋卓著”。诚如有的论者所说:“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科学,首先是因为有了梁赞诺夫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第20期,第117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稿中,生前公开发表、成型的著述所占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大量的是未发表、未完成甚至散乱无序的笔记、书信、手稿、札记、批注等等。前苏联学者对此进行艰苦的整理、考证和辨析,取得了大量成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参照。当然也必须注意到,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分析“模式”,特别是其中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每当政权制定出新的策略,便从经典文献中寻找依据,从理论上作出论证;过分突出了经典文本的“论战”色彩和至尊地位,以“正统者”的姿态,否认异己观点和解释的合理性,而在具体操作方式和话语系统方面又极为单一化,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社会发展体制上的“苏联模式”在文本研究中的渗透、体现或反映。
5.针对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存在的特殊情况(即所谓“意识形态歧解”)而强调手稿的原生形态和惟一价值,致力于文献考证而力图排除甚至索性放弃主观评价,这是以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版的编纂原则为代表的文本研究类型。
西方“马克思学”专门以马克思的生平和著述作为研究和阐释对象,力图不抱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学科上的局限性。吕贝尔在创立这一学派之初,就自命要继承K.格律恩主编《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和梁赞诺夫主持俄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时所形成的研究规范和传统,“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完全是独立的”。他所主编的《马克思学研究》所刊载的研究文章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纪念第一国际100周年专辑、纪念《资本论》发表100周年专辑、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沙皇制度和俄国公社专辑、论共产主义专辑等,以及由吕贝尔本人或其他人写的有关马克思的各种文章或专论,严格依据马克思原始文本的论述梳理线索、概括观点,澄清了许多不符合马克思思想而由后来者附加上去的见解。此外,吕贝尔长期致力于重新编辑出版他认为能反映马克思“本来面目”的《马克思文集》,也居功至伟。特别是1946年由他编辑的《卡尔·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伦理的论述》、1956年与他人合编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著作选》,以“马克思文集”为书名的大型法文版丛书(1963年出版了《经济学》第1卷,1968年出版了《经济学》第2卷,1984年出版了《哲学》卷)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国际考证版的编纂原则与“马克思学”的学术取向是一致的,梁赞诺夫组织进行这一工作的初衷就是要按马克思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第2版在70年代上马时学者们也秉承了这一学术宗旨。由于较之第1版工作量增大了不知有多少,学者们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心血也就更大、更多。以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为例,为了完整地呈现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本来面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成立了第1部分第5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卷)工作小组,由德国学者汉斯·佩尔格、英格·陶贝特和法国学者雅克·格朗让组成。他们为了考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原初结构、手稿笔迹等,不间断地工作了15年,对比了数十种版本,才初步拟定了新的纲目。在文本研究中他们确实以文献考证见长,而为了学术则真正到了不计名利的程度。
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派别和类型我们不应抱一种先定的主观成见,单纯做“善意”维护或“恶意”攻击的定性,而应该仔细甄别情况,具体言说和分析。
三、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方法论的省思
处于21世纪的我们如何研究19世纪马克思的文本,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马克思的文本研究虽然并不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的全部,但始终是这种研究永恒的基础。毫无疑问,在新的时代马克思的文本研究也需要有新的突破和深化。要对过去的文本研究历史进行清理和总结,对过去的文本解读方法进行反思和更新。我认为需要在方法论上做如下的思考:
其一,在文本解读的方式上,过分强调文本的现实价值和意义阐发是否会影响对文本本身完整性、准确性的把握?从以前苏联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情况看,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是那些对文本写作过程的甄别、版本的考证、结构内容的分析等等。诚然,我们不可能如洛克所说的带着一块“白板”式的心灵去解读文本,而是必然会有自己的主体认知模式、自己预设的观念系统,“嵌入”和参与到具体的解读过程当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无限膨胀自己的先验观念的理由。换句话说,这种主体性究竟应置于什么程度,而不致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本解读,一定是要以文本本身为本位、把其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探究的。这种解读应包括对诸如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翔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而不应当人为地舍弃某一部分,或过分突出某些方面。
其二,当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是否需要充分估计到思想与文本之间的复杂情形?就是说,思想家的思想与表述其思想的文本之间是否就一定会存在完全契合、一一对应的关系?思想家在形成其思想、观点之后,要借助适当的体裁与方式表述出来,形成文本;然后解读者通过对呈现在他面前的文本表层结构(文字、声音、图画等)的解读,来理解潜藏于其中或其后的深层意蕴,进而达到对思想家思想的把握。由于这些复杂因素的加入,使思想与文本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完全契合、一一对应并且为解读者全部理解的情形反倒成为非常特殊的例外。这就要求我们面对文本时要有足够的清醒,同时也充分凸现出过去被视为“繁琐”的“掉书袋”而弃如敝屣的文本细节考证的意义与价值。
其三,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解读者角色、身份意识是否有强化与限定的必要?对于同一文本,身份不同的人解读的动机不同,关注的部分、突出的观点、作出的解释会不一样,这虽然也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以此为理由取消或否认对“真正解读者”角色的期待却是不对的。在我看来,真正的文本解读者应当是研究者;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他必须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评判和感情因素的干扰,只服从理性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结论,而不随意与权威和时尚趋同;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不奢望自己结论的绝对性和普遍适应性。那么,对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能不能也作如是观?我想,答案也是肯定的。
可以预料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将更加专业化、学术化。马克思的全部文本将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这将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马克思专业研究的深化,要求研究者完整地再现经典作家真实而复杂的心灵,不再仅仅将其视为历史规律的宣布者,还应当看到他也是理论思维的艰辛探索者;他不仅善于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解释与分析纷纷复杂的社会现实,而且对这种理论本身也经常进行反思与检视;而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也常常会处于两难境地的选择与各种困惑的打扰。而揭示构成经典作家这些复杂性格的多个侧面,单靠几部成型的大著显然不够,那些卷帙浩繁的书信、札记、谈话记录等颇具历史价值,亟待下功夫梳理。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相当数量的新文本(即大量的遗著、手稿和笔记)陆续面世之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其思想的理解会更为客观与科学,而这也必将瓦解那些强加于其身上的某些教条和一些片面、极端和庸俗的见解。马克思的文本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宝藏,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显示出不同部分的新价值与新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永恒基地。
标签:恩格斯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资本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