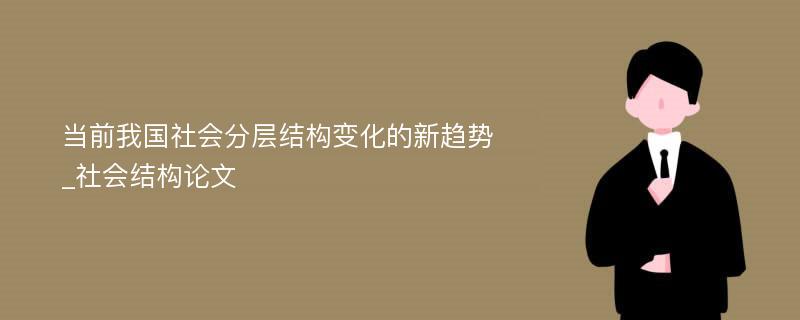
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趋势论文,当前我国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55年了。在过去的55年中,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世之罕见。先是共和国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尝试了打碎阶级体系的实验。后来,从1979年底开始又改变航向,实行市场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二十五年来,财产层的分化极为迅速。可以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至学者的分析也常常跟不上变化的速度。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探讨出现了什么新的趋势。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笔者认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有如下几方面新的趋势。
一、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比较严峻
前一阶段的不少研究都已经证明,改革以来的贫富财产和收入的分化是十分迅速的。为说明近几年的变化,还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变迁的历史。我们所采用的测量方法仍然是基尼系数的方法,我们知道,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测量的对象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收入,测量财产比较复杂,测量收入简单一些,所以,我们就用测量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来表示。我们知道,关于我国的贫富差距,可以用来作为基数比较的1979年的改革以前的数据十分稀少,相对较好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80年对于中国经济考察后所写的报告。根据该报告,1979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城乡合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该报告还指出,当时中国最富的1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22.5%,最富的2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39.3%。如果以此为基数的话,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的数据,1988年为0.382,根据笔者的数据,1994年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到2003年,笔者根据多项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并且与其他一些学者的数据做了比较,认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的水平,这应该是不为过的,从趋势上看,还在进一步上升。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仅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已经朝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方向发展了。
以上是对于社会分化现象的数据描述。从社会现实生活看,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现象也变得比较突出。中国的富人在中国就业人口中虽然比例很低,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虽然是很低的百分比,却仍然是一个人口巨大的群体。比如,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注:余明:“解读财富报告:中国富人到底有多少?他们有多富?”http://finance.tom.com2004年09月12日,工行特约报道,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另外,许多超级豪华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量居然居全球第一或亚太区第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富人张扬、奢华的生活方式。西方的富豪多数都热衷于慈善事业、捐款等,而中国的多数富豪还没有达到这个档次,中国的富豪很多还是以“摆阔”的方式来消耗他们的金钱。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年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则贫困人口的数目完全不是这个局面。按照国际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那么,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竟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到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
二、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
按照上文的分析,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比较严峻了,那么,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也是笔者在做社会分层研究时,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人们还经常问起的另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比如基尼系数)有没有一个临界值或警戒线,超过了这个警戒线,社会就会出问题?其实,早在1994年,当分析全国调研数据,发现基尼系数达到了0.434时,笔者就曾指出我国的不平等程度“超过了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即指基尼系数维持在0.3-0.4之间的水平;换言之,超过0.4就是高于临界值了。如上文所指出的,我国现在已经达到了不低于0.5的水平,当然,可以认为是超过警戒线了。人们自然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超过了又怎么样了呢?社会真的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吗?因此,本文的这一部分就是试图探讨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笔者试图分析,贫富差距究竟是怎样引发社会问题的?其引发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笔者以为,贫富差距引发社会矛盾的机制比较复杂,其机制具有“间接性”。什么是直接性和间接性呢?举个例子吧,近来城市的拆迁引发了很多的社会冲突,拆迁直接侵害了一些居住者的利益,这种引发社会矛盾的特点具有直接性。再比如,城市化扩张中的征地,造成了很多农民失地,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其机制也具有直接的特征。而贫富差距的机制就不是这样了,贫富差距的现象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它有时候引发社会矛盾,有时候并未引发什么矛盾。即使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如果贫穷群体和富裕群体相互之间没有比较,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或其他环节,两个群体也可以相安无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固然,富人买宝马车、买888万元一辆的宾利车、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只要他没有与其他人发生矛盾,就不存在引发冲突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穷人,其收入虽然很低,如前所述,人均年收入甚至低于637元人民币,在云贵的山区确实有不少这样的群体,但是,只要还能吃饱饭、生活还能过下去,他们也并不与北京、上海、广州的某些巨富群体发生矛盾。既然是这样,那么间接的机制是怎样引发社会矛盾的呢?
笔者以为,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客观的“社会结构紧张”,第二个环节是人们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也可称为:“不公正感”。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证明,贫富分化之所以威胁到社会稳定,是因为,分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紧张”,而结构紧张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那么,既然贫富分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什么样的分化更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紧张,什么样的分化不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紧张呢?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也证明,当贫富的分化过大的时候,虽然富人集团和穷人群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矛盾,但是,巨大的差距使得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下。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墨顿(Robert Merton)。墨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笔者使用这个概念是想说明,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距,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换言之,不是任何一种贫富分化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只有当贫富差距太大了,其张力已经形成了结构紧张的局面,这时候,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时候,矛盾容易激化,冲突容易发生。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从0.434发展到现在的不低于0.5的水平,就是“结构紧张”的客观证明,应该说是处于比较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状态下。
那么,“结构紧张”是否就一定会激化社会矛盾呢?笔者认为,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结构紧张”是一种客观结构,发生社会矛盾有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矛盾是否出现,还要看第二个环节,这就是“公正失衡”。“公正失衡”说的是一种民众的主观心态。社会学传统上有“相对剥夺”的研究,指在与其他更为富有的群体相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心理状态。其实,如果细究的话,“相对剥夺”的观点有漏洞。富人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们就没有相对剥夺感,有的时候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呢?笔者以为,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时候总是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相关联的,所以,更深层次的看法是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在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下,如果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为“社会不公”,这就是“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笔者以为,我国近来发生的诸多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正失衡”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宝马车在世界各国很多,但是,因宝马车而引发社会冲突的却并不多见。近来,国内发生了几起宝马车引发的冲突。先是去年10月在哈尔滨发生的所谓“宝马撞人案”,我们暂且不论事情本身的事实究竟如何,单就一点而论,该事件在网上的评论点击率超过了对SARS的点击率,这确实使人惊讶,如此多的公众对此事情感兴趣,确实显示了因财富失衡而引发了公众对于“财富、权力”与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另一件“宝马案”是最近发生的,起因本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在某高校内,一辆宝马车向后倒车,碰倒了一名学生,学生并没有受什么伤,只是要求车主道歉。如果车主道歉了,本来就是小事一桩,成不了什么新闻事件。但是,车主不道歉还开车就走,后来又提出“花钱摆平”,学生一方认为:“这些仗着有钱或权的人,以为钱就可以摆平一切。”因而拒绝钱的条件,坚持要求对方道歉。于是,酿成了新闻事件。笔者查了一下网络上的评论,大部分都抨击金钱权力和不公正的。剖析这两起“宝马撞人案”,宝马成了权力、金钱的象征符号,所以,只要宝马欺负人的符号出现,马上引起群情激愤。这个个案印证了笔者关于“结构紧张”与“公正失衡”关系的观点。
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如,近来炒得很热的“郎咸平事件”,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出现了不公正现象,国有的企业内部人和外部人,以压低国有资产价格的方式,在内幕交易中侵吞国有资产。我们暂且不论郎教授观点的是非曲直,仅从该事件引发的全社会关注的程度、该事件争论的激烈程度看,符合了本文所说“结构紧张”的社会背景,以及笔者所说的第二个环节,很多赞成郎教授观点的人将产权改革归结为“公正失衡”,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郎教授观点的人,都是在争论,新的产权格局、财产分布的格局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
此外,当前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热点事件都可以在“结构紧张”与“公正失衡”的框架下来理解。大的问题比如,三农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社会犯罪问题等等,小的事件,比如,近来关于“机动车是否应该负全责”的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
所以,笔者认为,近来,分层、贫富差距的特点是,该问题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比较激烈的社会矛盾、社会争论和社会冲突,对此,我们要十分小心,应尽量采取缓解社会矛盾的对策。
三、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注:本文使用了“阶层”或“阶层结构”的概念,主要是考虑阶级概念常常受到很大误解。)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处于剧烈变动过程中,定型化的特点不突出。内战、日本人的入侵、解放战争、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造成中国各阶层出现巨大变迁,以往的研究也证明,中国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
80年代初的改革以来,再次出现巨大变迁。笔者曾经表述为:政治分层的社会结构转变为经济分层的社会结构(注:李强:《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北京〕《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这一时期社会流动的特点仍然是,阶层之间的流动率颇高。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富裕阶层产生和膨胀比较迅速的时期,原先经济地位低下者后来跻身于富裕阶层者比例较高。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地位低下者进入富裕阶层的比例明显下降,富裕者来自同阶层或临近阶层的比例上升。换言之,80年代,一个穷人想变为富人的话,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9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此种机会大大减少了。
对于社会阶层以及阶层之间的关系愈来愈趋于稳定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阶层结构定型化”。对于阶层结构定型化现象的研究,可以参见,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一书,在该书中,吉登斯使用了“阶级关系结构化”(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等概念。中国的情况与吉登斯所说的情况有些相似。笔者使用“定型化”的概念,反映经济分层成型的现象。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阶层定型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50年代中国进行了打碎阶级的实验以后,阶层变得界限不明显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各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性不很大,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80年代初的市场改革以来,直到90年代中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比较频繁,阶层之间的界限也仍然不很清晰。当时,有一大批原来经济地位比较低下、生活十分贫苦的人,甚至是社会边缘群体,在市场经营中赚了很多钱成为富有阶层的成员。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以来,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显,富有阶层准入的条件比以前严格多了,包括注册资本的限额、土地或铺面房的价格等,这些准入标准越来越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从产业结构看,80年代进入市场的多是小商品经营者,这些小商品经营者有些逐步积累做大,到了90年代成为富有阶层。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兴起,进入这些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该阶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数据证明,从学历等看,经营层、企业家层,大多有了较高的学历、文凭,这些也成为阶层定型化和界限形成的重要标志,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作用开始出现。
第二,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阶层界限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阶层之间流动率发生变化。8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也可以竞争进入高收入层,笔者曾经将此种现象称为市场转型的一个“特殊阶段”:“社会边缘群体从市场中获得利益”;当时的研究发现,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比社会上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还高,甚至引发了“脑体倒挂”的现象。到了90年代末期,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春玲博士等人通过全国调研的数据证明,总的流动率虽然比较以前的流动率高,但是,如果区分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则社会上层向上流动的比率更高,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比率较低,机会减少。笔者分析一些区域调查的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社会下层群体、社会边缘群体获利明显下降,向上流动比例减少。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形成一些作为本阶层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在50-70年代打碎阶级实验的时期,中国城市的居住模式是阶层混杂型的。比如,在城市里“单位大院”的居住模式中,高层人员和低层人员都居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甚至同一幢楼房里。由于当时采取的非市场型的“分房模式”,将家庭人口、是否结婚、参加工作年限等看作最重要的分房记分标准,所以,分房、居住与经济分层没有关系。近来,随着居住房屋的市场化,因房地产价格的巨大差异造成的阶层区隔正在形成,城市中形成了一些高档社区、高档物业小区,在这里,房屋的价格和物业管理的价格都十分昂贵,只有一些富有阶层可以承担。另一方面,社会边缘群体聚集的地方,也形成了一些低收入和边缘群体的社区。从消费上看,不同的消费档次开始区分开来,从富有者消费的极高档次的商品和服务,直到专为社会边缘群体服务的小商店、小理发、小诊所等,各个档次等级次序分明。对于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品位,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作过详细描述(注: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 (Massae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8-129.)。其实,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文化模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过去有一段时间里,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下,分层的文化模式受到了严重冲击,而在稳定的社会局势里又出现了复归的倾向。
第四,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阶层之间流动率的下降与阶层内部互动的加强几乎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富有阶层的交往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组织,比如,近来有一些高会费的俱乐部、会馆等,如果要进入这些俱乐部、会馆就要交纳很高的费用,从而将低收入者阻挡在门槛之外。又如,目前一些大学开设新型高学费的E-MBA教育,学费高达25-26万,结果许多企业的经理、老板以参加这样的学习组织为荣,在学习中加强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互动,促成了富有阶层内部的社会网络。当然,这些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建立商业信任关系的作用。
如何评价阶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呢?虽然在现阶段出现了一些阶层向上流动率的下降,但是,阶层结构定型化本身,也并不一定造成长久的流动率下降。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主要作用是使得社会流动循着一定的标准进行,因而更有规律。中国过去的社会流动确实没有规律,并表现为阶级、阶层瓦解所造成的社会流动,但现在不同,随着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其社会流动也会变得常规化。记得大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曾经讲过,阶层就好比是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成员就好比是从这些车厢里上上下下的过客,他讲的就是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社会流动的特点。阶层结构定型化以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更有规律性,人们争取地位的上升采取更为常规型的手段,比如考试、文凭、职务晋升等,其结果是社会变得更为稳定。
四、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
近一段关于中产阶层的讨论比较多。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产阶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确实起了重大作用,其意义不可忽视。中国中产阶层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还是有巨大差异性的,对于这种差异性笔者曾经撰文指出,西方新式中产阶层的主体是由受雇人员构成的,而中国新产生的中产阶层的主体是大批非受雇阶层,如大批中小工商业层、独立经营者阶层。其实,差异不止于此,下面试分析一下中国中产阶层的构成,由此可以更进一步观察这种差异性。笔者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构成的。
第一,中国大陆中产阶层中最为稳定的力量,是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将所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干部)都算在内的话,占就业人口的1.67%。当然在这1.67%的人中,有一小部分属于比中产阶层更高的阶层,由于其人数甚少,我们暂时将其忽略不计。虽然,新近的研究证明,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出现分化,比如,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体制之内的,但是,近些年来市场的发展,也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吸引到了体制之外。所以,干部的全体还可以算作体制内资源,而知识分子的主体很难说属于体制内资源了。将知识分子看作体制内与体制外平分秋色比较符合现状。
当然,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如果将所有专业技术人员都算在内的话,目前占就业人口的5.7%。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在政府、机关等国家部门,学校、医院、研究机构等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公司等经营单位工作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这里所说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统计上,与前述的占就业人口的1.67%的单位负责人完全没有交叉,这两部分人加在一起占就业人口的7.37%。专业技术人员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并不完全吻合,笔者只是为归类方便暂时将他们归入知识分子大类。
第二,所谓“新中产阶层”。笔者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大城市中正在出现一个新生的“新中产阶层”(注:李强:《市场转型与我国中等阶层的代际更替》,〔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年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由于该群体处于产业结构的高端,技术含量高,体制上又多属于外资、外企,所以,收入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生活方式上也开始形成所谓新的“格调”。近来流行的所谓“小资”、“BoBo族”、“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等就是指以该阶层为主导的一种生活方式。新崛起的一代人实际上是一种标志,它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从全体人口的角度看,新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并不快,但是,在大城市里他们人数的持续上升还是明显的。当然,近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激增,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中产阶层内部的激烈竞争。该部分人数不多,没有确切统计,估计占就业人口的1-2%。
第三,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公司、单位的职工层。笔者以往的研究曾证明,从相对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国营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笔者曾称之为“类中产阶层”。无论与当时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非国营企业的劳动群体相比,当时,国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占有明显优势。改革以来,尤其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国企职工队伍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很大一部分传统中间层的国企职工成为城市失业、下岗、离岗、内退等等大军的主体,被淘汰出中间阶层的队伍。
经过90年代中后期的震荡,到了新世纪初叶,国有企业的分化已经大体结束,因此,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公司职工的经济地位也是比较稳定的,大约占就业人口的3-4%。
第四,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在农村里包括那些经营比较成功的富裕起来的阶层,在城市里包括大批下海的、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中产阶层的这个部分的构成最为复杂,这也正体现出变迁中的中国社会阶层重组的特点。近来,中产阶层的这个组成部分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目前大约占就业人口的5-6%,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中小工商业经营者有可能上升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构成群体。
以上四部分人,有些是交叉的,比如专业技术人员就与“新中产阶层”和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职工相交叉,所以,中国中产阶层的总比例比上述四部分之和还要小一些,估计总数不超过中国就业人口的15%。
对中产阶层以上四个阶层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具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各个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四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形成统一的中产阶层具有巨大的难度。换言之,中国中产阶层很难有所谓统一的利益要求。
第二,中国中产阶层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从人数比例上看,前述的中产阶层的四大群体,不管是哪一个,与全国就业者、劳动者、工人、农民比较,都显得人数很小,全部加起来不足15%。所以,中国社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长期短缺,使得“结构紧张”在一段时期内还难以消除。为此,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中产阶层的社会条件。
第三,从“世界体系论”(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3卷),尤来寅、路爱国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的角度看,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是受到制约的。如果中国作为出口初级产品的边缘国家,而接受核心国家的高端产品,那么,中国因被大大压低了价格的初级产品而造成的广泛的低收入者阶层就不可避免,其结果只会是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中产阶层,而不会在本国产生庞大的中产阶层。所以,这成为制约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五、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与“碎片化”特点
从上述对于中产阶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分割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实,中国不仅中产阶层,社会其他阶层也出现了利益分割甚至利益碎片化的趋势。
笔者过去的分析已经指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分化开始的,分化也具有某些正向的、积极的作用。过去人们以为,分化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其实不尽如此。我们知道社会分化如果是简单的两极分化,那当然是不好的,但如果社会分化是利益的“碎片化”,人们的利益是多元的,那样,反而不容易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比如,过去,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就业于按照全国统一工资标准的国营集体企业中,那时候,长工资都需要中央颁布全国长工资的命令。如今,绝大多数就业者就业于各种类型的公司、企业之中,长工资是千百万公司、企业自己的事情,大家不用“齐步走”、不会产生“共振”。就业者的利益被众多类型的公司、企业所分化。
然而,最近的变化表明,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在此,笔者试剖析利益分化的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阶层分化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多元利益群体。如上文所述,经济利益确实分化了,产生了贫穷与富裕的巨大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与身份群体交织在一起,是环环相交叉的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笔者以前分析过,中国80年代初的市场改革以前,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身份制关系。比如,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等,他们之间的区分主要不是市场型的经济地位差异的区分,而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异。改革以后,经济指标作为社会地位区分的指标愈来愈突出,最终形成了上文所说的“阶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但是,新的阶层产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身份制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实际情况是,阶层结构定型化与传统的身份制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阶层与身份并存,在阶层内部会有很多身份群体。比如,二十余年来,我国工业化速度很快,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膨胀。然而,由于原有的身份制的存在,中国产业工人内部有众多不同的身份群体,其内部的差异性一点不小于外部的差异性。目前在中国工人的内部,既有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也有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在乡镇企业劳动的工人,有相当多的家庭企业劳动的工人。即使在同一个单位里面,也存在着几种不同身份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总人数虽然十分巨大,但是,却分化为很多小的利益群体。
第二,户籍、地域的差异与阶层差异交织在一起,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改革以后,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弱化,在有一段时间里甚至还有所加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公安部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的实验,但是,大城市的户籍管理和控制还是很严格的。新近的改革特点是将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区分为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如上海、广州、北京等特大城市曾推出了“蓝印户籍”,“A、B、C户籍”等区分多种户籍的政策。因此,其结果是,在同一个阶层的内部,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户籍利益群体。比如,同是在一个城市里经商的老板、经理,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就形成阶层内的小的利益群体。除了户籍以外,还有地域的巨大差别。近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造成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反而是差异更大了,比如,到2002年底,北京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3.62倍,而上海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8倍。所以,中国不同区域的农民有巨大差别,虽然都叫农民,其内部的分化是很厉害的。从大的地域上看,中国东北、华北、华中(或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省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都有显著的经济差异,虽然都是农民,在不同区域经济地位会有巨大差别,很多情况下,区域的差异远远大于阶层的差异。
第三个特点是体制的差异与阶层的差异交织在一起而产生了多元化利益群体。近年来,在我国阶层分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体制变迁和体制分化。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体制改革大步前进,迄今为止,由传统的国有、集体体制覆盖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新产生的体制五花八门,包括私营、个体、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合资企业、香港、澳门、台湾商人投资企业等等。这些还仅是一些大的分类,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实际运作中的体制比这些要复杂得多,比如:承包的、转包的、出租的、租柜台的、包工队式的、挂靠式的、交管理费式的,除了登记了的正式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没有登记的非正式单位,其管理方式更是花样繁多,不同体制的单位,其工资制度、收入体系、福利体系均有巨大差别。中国目前的收入构成、工资体系、福利体系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由于体制的“碎片化”与阶层分化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利益的碎片化。比如,失业本来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群体,但是,在我国当前却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和利益“碎片化”的群体,很难说有什么边界。且不说笔者以往的调研已经证明失业与“隐性就业”和“隐性失业”的群体交织在一起(注:参见,李强、肖光强:《“隐性就业”现象研究》,〔北京〕《新视野》2000年第5期。),仅就失去工作这种现象看,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比如分为:下岗、离岗、内退、买断等等情况,再加上,不同单位对待曾在本单位工作的下岗者待遇很不一致,失业者的利益也碎片化了。
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比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注:Ralf Dahrendorf,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239.)。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是,正如达伦多大所讲的减缓的方面。由于社会利益结构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壁垒森严的裂痕型的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阶层利益的碎片化、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减小了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我国的贫富分化很严峻,但另一方面,却没有发生巨大的社会不稳定。
标签: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分层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基尼系数论文; 经济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贫富差距论文; 社会矛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