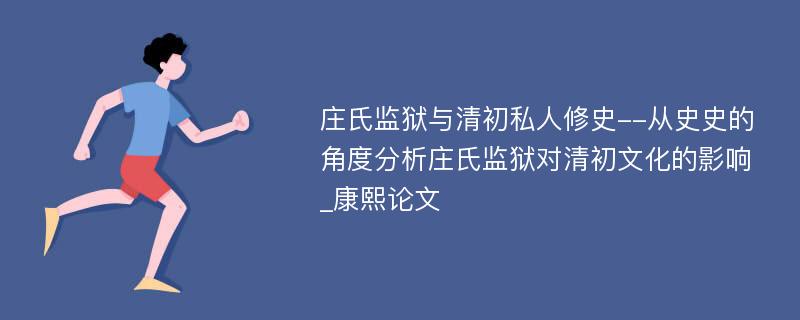
庄氏史狱与清初私家修史——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角度论文,文化论文,史学史论文,庄氏史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7)03—0074一O5
“庄氏史狱”① 是发生在清初的一起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文字狱,其研究得到学界广泛重视,前辈学者多从文化高压政策角度予以评析,代表性的观点为,“清初的庄氏史案,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即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一己的政治需要出发,而肆意践踏学术,摧残人才。这种文化上的短视,经过雍正、乾隆问的封建专制而推至极端,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终于酿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1]。诚然,庄氏史狱确实对清初学术,乃至清初文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那么,破坏的程度如何,消极影响的范围有多大,清初学界对此做出了哪些反应,一些具体问题亟盼学术解答。史狱因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引起,因史狱而遭受直接波及的,亦为清初的私家修史,本文拟以此为线索,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史狱的文化影响以及清初史家对此的不同反应。
一
顺治十八年(1662),史狱案发。康熙二年(1663)五月,杭州城内的弼教坊,约计七十余名江浙地区的文人、名士被凌迟、重辟和处绞,一时之间,学界震动。庄廷鑨私修明史而致惨祸,参订者亦遭连坐,不啻惊雷,令清初埋首修史的众多史家目瞪口呆。据朱彝尊记载,史狱之后,时人视明季史书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
“先太傅赐书,乙酉兵后,罕有存者,子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萧然,无书可读。及游岭表归,阅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之满一椟。既而客永嘉,时方起《明书》之狱,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问囊所储书,则并椟亡之矣。”[2](卷三十五,《曝书亭著录序》)
收藏史书者尚且如此战战兢兢,修史者的惶恐不安可见一斑。庄氏史狱对清初私家修史的消极影响,具体为以下几点:
首先,史狱直接影响到一些私史的成书与流传。直接受其影响而未能成书者多部。吴炎、潘柽章主持编写《明史记》②,因二人同罹史祸而致夭折,潘耒《松陵文献序》云:
“亡兄与吴先生(吴炎)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划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其详且慎如此,庶几不失古人著书之意”[3](卷七,《松陵文献序》)。
吴潘二子之史书,史料详实,诠错得当,未能成书,而历浩劫,为清初史学之遗憾。
受史狱影响而遭搁置,或藏之名山,不敢刊刻,影响其流传者为数更多。查继佐的《罪惟录》本名《明书》,因受庄氏史狱的影响而韬晦其名,更名为《罪惟录》,修史者辗转流离,备极辛苦,据查继佐自序云:
“此书之作,始于甲申,成于壬子中,二十九年,寒暑晦明,风雨霜雪,舟车寝食,疾痛患难,水溢火焦,泥涂鼠啮,零落破损,整饬补修。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口哦而不闻声者几何件,掌示而不任舌者几何端,以较定哀之微词,倍极辛苦。兼以他诡误而连狱,方椟藏而无山”[4](《自序》)。
受史狱牵连,出狱后能不改志向,终成其书,查继佐此举足以不朽,而《罪惟录》不能端正本名,令作者只能仰天长叹,“若夫《罪惟录》得复原题之日,是即左尹得复原姓名之日,静听之天而已。”[4](《自序》) 其后,查继佐本人及其门人对修纂一事守口如瓶,不敢对人透露,更不敢刊刻,直到查继佐临终前才痛下决心,对此书进行最后的清理,无奈体力与精力均大不如前,整理只能草草结束,故《罪惟录》一书只有稿本存世③,史书篇章结构未能完全清理,内容也多颠倒错乱。至乾隆时,文字狱盛行,收藏者惧罪,多所涂改,张宗祥跋文云,“是书谏议传,无杨涟等,隐逸传仅至孙一元,奸壬传无马士英,阙帙至多。盖原书每传不连写,又经后人任意装订,先后倒置,无目录可查,故虽阙而不知也。”[4](《罪惟录跋》) 改易书名,深自晦匿,《罪惟录》虽幸而流传至今,却面目大非,给后人的整理与利用带来困难。幸得张元济苦心整理,才使得《罪惟录》虽历劫无算,终免沉沦④。
费密《荒书》⑤,亦曾因史狱而搁置。此外,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史书因不见于记载,在史学史上没能留下应有的轨迹。
其次,受史狱间接影响而搁置成书甚至未能成书者亦大有人在。顾炎武修史亦受到史狱波及,吴、潘本为顾之好友,二人惨遭刑戮,顾写诗以表达悲愤之情:
“露下空林百草残,临风有恸奠椒兰。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5](卷四,《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
顾曾把史料借给吴炎等人,史狱后史料无存⑥,加之生活不安定,文字狱阴影犹在,最终放弃修史的夙愿,他在写给潘耒的信中说:
“吾昔年所蓄史事之书,并为令兄取去,令兄亡后,书既无存,吾亦不谈此事。久客北方,后生晚辈,益无晓习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谈旧事,十七年不见旧书,衰耄遗忘,少年所闻,十不记其一二。又当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难置喙。退而修经典之业,假年学易,殊无大过。不敢以朝野之人,追论朝廷之政也。”[5](卷四,《与次耕书》)
顾炎武甚至还为潘耒写下了“犹存太史弟,莫作嗣书人”[5](卷十一,《寄潘节士之弟耒》) 的凄切之句,因二子惨遭史狱而产生的心理伤痛,于此可以想见。以顾之渊博学识,史学素养,未能修成有明信史,为清初史学的又一缺憾。
另外,吴潘二人为修史之事曾求教于钱谦益,并深得其赞许⑦。钱于《复吴江潘力田书》之札尾,谈到,“《东事纪略》,东征信史也。人间无别本,幸慎重之。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诸侯陆续寄上,不能多奉”[6](卷三十九,《复吴江潘力田书》),可见,吴潘二人于史料方面,得到过钱的帮助。钱谦益一生以史官自居,修史为任,最终史书未成,固然由于绛云楼之火,史料付之一炬,二人因修史致祸的震动亦不无影响。
再次,史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史家之间的修史交流。清初,浙江海宁出了两位著名史家,谈迁与查继佐,分别修成有明一代编年体史书《国榷》、纪传体史书《罪惟录》,二人著书年代相同,居又同里⑧,志同道合,却无一言提及对方,若互不相识。张宗祥分析清初历史环境,认为:
“(二人)所不同者,查豪放结客,谈抱朴守约耳;何以二人若不相识,各无一语及之也。意者谈氏载庄氏史狱之前,早已谢世;而查氏既经史狱,幽囚二百日之后,虽奋笔成书,不欲表暴于世,深闭固拒,以史为讳,即知谈氏之书,亦惟有铁函深井,藏之已耳,敢引以贾祸耶。”[7](《张宗祥跋》)
史家各据传闻,史料发掘不广,本为私家修史先天之不足,惮于史狱影响,清初史家各自隐讳,不互相交流,难免会影响到对传闻及史事的判断和论定。清初私家史著虽众多,但多据传闻,鱼龙混杂,难免有失实害史之败笔,潘耒对此提出批评,“国史之鄙,其由野史之杂乎?野史者,国史之权舆也。微野史,则国史无所据依。然古之书苦少,今之书苦多,古之作史者难于网罗,今之作史者难于裁择”[3](卷六,《交山平寇始末序》),并提出,“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3](卷六,《国史考异序》)。受史狱影响,史家各守门户,惮于互相交流,于清初私史之质量不无消极影响。
二
综上可知,庄氏史狱确给清初私家修史造成了恶劣影响,但对其破坏程度作定论时仍应慎重。毕竟,史狱的爆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此后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狱相比,“庄氏史狱”并非清朝统治者对知识界刻意吹求,有心罗织;当时统治政策基本上仍然以怀柔为主,官方惩戒并不主要针对私家修史,“清初禁网尚疏,有志著作之人,裒集明代史实,并不甚知有忌讳。庄氏乃家富遭忌,又修史之名太震,致掇奇祸。”[8](P141) 蓬勃发展的清初私家修史,亦未因此中断。
对史家而言,罹祸者与惧怕者毕竟为少数,尽管有死亡的阴影笼罩,仍有相当一批史家毅然决然地继续修史。
首先,直接受史狱波及的一些史家并未因此中断或放弃修史。对遗民来说,以生命之魂纂修有明信史是其生存价值的体现。史狱的发生,无损遗民修史之志向。故查继佐虽亲历史狱,仍续修《罪惟录》不辍,查从狱中获释后即继续此前的修史工作,“乙巳先生六十五岁,始杜门手辑,前稿名《先甲集》,近稿名《后甲集》,著《鲁春秋》上下两卷。”[9]受其影响,查之弟子沈起,明知其师因修史入狱,仍醉心其业,可惜命运多舛,未竞其书。
另一位幸免于史狱的史家陆圻,亦撰有《陆子史稿》二册,谢国桢先生云,“圻曾参与庄氏修史之役,以自陈得免于难。是书为其所撰史稿,存食货志、舆服志,及杂记明季三案及弘光、隆武朝遗事,与圻所撰《纤言》多同。”[11](P14—15)
在史狱中遇难的潘柽章之幼弟潘耒,不仅未隔绝于史学,反而秉承亡兄志向,以修纂有明信史为己任。遗民钱澄之感叹年华已逝,修史事业难成,叹息之余,得知潘耒修史之志不衰,寄诗潘耒,寄以修史之厚望。
“松陵才子早知名,握手燕台气不平。未受国恩甘避世,偶谈家难为伤情。
诗篇半是尊前就,史学偷从帐里成。顾叟不归余亦老,江东此事属潘生。”[12](卷二十二,《与潘次耕》)
固然,一批学者受史狱影响而犹豫踌躇,但仍有更多的史家修史不衰,尤以遗民为中坚。
其次,受史狱震慑,一批史家改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修史。史狱酷烈,为全身存史,一批史家由公开转入暗处。全祖望记述史家林时对修史,尤强调其隐蔽性:
“公讳时对,字殿飏,学者称为茧庵先生,浙之宁波副鄞县任。以崇祯己卯、庚辰连荐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赧王起南中,以吏科给事中召。南都亡,从戎江干,累迁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踰年事去,杜门不出,乃博访国难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随所见闻,折衷而论定之。先公尝曰:吾年十五,随汝祖拜公床下,语予:‘野史之难信者有二:彭仲牟《流寇志》伪错十五,出于传闻,是君子之过;邹流绮则有心淆乱黑自,是小人之过;其余可以类推。’先公问曰:‘然则公何不著为一家以存信史?’公笑而不答。盖是时公方有所著而讳之。然自公殁后,所谓《茧庵逸史》者阙不完。”[13](附录)
此外,遗民著作还有内集、外集之别,内集者,有隐讳而不示人,“残明甬上诸遗民,述作极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转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内集。夫其内之云者,盖亦将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泄,百年以来,霜摧学剥,日以陵夷。”[1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杲堂诗文续钞序》) 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内集固然可以全身存志,但多湮灭不传者。
低调修史,集分内外,是遗民史家有效的文化反击,方式略显消极,而修史存史之行为仍具积极意义。
再次,非遗民亦以气节相标榜,清初私家修史并未因此中断。以邹漪为例,甲申乙酉之间,刻《启祯野乘初集》,34年后,又作《启祯野乘二集》,并标榜气节:
“慨自世道衰微,廉耻渐灭,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士卖其友,弟子背其师,妻妾委弃其夫,不知忠孝节义何合物”,因此钩稽条贯,诠次成篇,“或亮节清风,品崇山岳;或鸿猷伟绩,业沛江河;或厚泽深仁,著龚黄之遗爱;或直言敢谏,追徵黯之嘉谋;或艺苑流芬,经经纬史,翰墨昭同云汉;或沙场灑血,断头决腹,忠贞喷薄日星;乃至故国遗民,旧邦吉士,剖肝孝子,截发贞妻,皆得论定焉。”[11](邹漪:《启祯野乘二集》自序)
此外,史狱后形成的史书还有朱克生《明代宝应人物志》(康熙元年,1662)、陈弘绪《南昌郡乘》(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刘心学《四朝大政录》(康熙七年,1668⑨)、王雯耀《全桐纪略》(康熙八年,1669⑩)、计六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康熙十年,1671(11))、马驌《左传事纬》、《绎史》、王夫之《永历实录》、黄宗羲《明儒学案》(12)、邹漪《启桢野乘二集》以及约成书于康熙十八年之前的戴笠、吴殳的《流寇长编》(13) 等等。可见,史狱虽对清初私家修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心理恐慌,但并未从根本上阻止私家修史的继续发展。
密歇根大学明清史教授司徒琳指出,庄氏史狱残酷而血腥,“然而,同样有趣的是,尽管1661到1663年发生的庄氏史狱造成了浙江七十多位学者的惨祸,但17世纪60年代的修史工作并未因此顿减。”[14](P103)
三
综上可知,史狱引起的文化恐怖气氛,确曾弥漫全国,令史家屏住呼吸,震慑其心理,影响其判断,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行为。然而,史狱之消极影响不足以遏制清初私家修史的发展。清初私家修史,沿着史学自身的运行轨迹,一直持续发展到康熙统治末年,在遗民凋零、官修《明史》冲击、史料信息萎缩、私修史书自身整合、官方文化政策钳制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方告走向衰落。
史狱对史家的震慑与打击因人而异,对史学的消极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通过分析考察史狱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有如下启示:
其一,文字狱对士人的心理打击从来不是一贯的,而是因人、事、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具层次性特征。士人阶层因政治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的差异会对同一起文字狱事件产生不同的反应,委屈顺从者有之,消极抵触者有之,冷静漠然者有之,公开反抗者亦有之。因此,对文字狱个案的分析与研究应力求具体化,层次化,过于简单,强求概括,难免会有失客观,影响对文字狱消极影响的判断。
其二,文字狱对学术发展及走向的影响是渐进的,渗透式的。一方面,文字狱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决定学术发展的走向,往往与其他因素联合发生作用,或者成为学术发展的催化剂;另一方面,文字狱的消极影响是长期作用,不是短期行为,研究文字狱,不仅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客观公正的学术分析尤为重要。
其三,对文字狱的研究应注意政治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双向互动。文字狱是政治与学术,统治者与知识层之间互相作用与反作用的产物。一方面,学术作为社会与文化的构成要素,必然受到官方统治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术自身的张力和弹性也会反作用于政治,影响统治阶层的决策与判断。
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因庄氏史狱,可以看出,一起骇人听闻的文字惨狱对清初史家的心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影响其修史行为,导致不同的学术抉择,由此,庄氏史狱视野下的清初史学展现出富有层次的立体画面。
收稿日期:2007—01—26
注释:
① 关于庄氏史狱的研究,前辈学者成果有:谢国桢《庄氏史狱参校诸人考》《中国书籍考论集》(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周延年《庄氏史案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杨林《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饯茂伟《庄廷鑨任史考论》(《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3期)等。
② 吴炎《今乐府序》云:“明兴三百年间,圣君、贤辅、王侯、外戚、忠臣、义士、名将、循吏、孝子、节妇、儒林、文苑之伦,天官、郊祀、礼乐、制度、兵、刑、律、历之属,粲然与三代并隆。而学士大夫,上不能为太史公序述论列,勒成一书,次不能为唐山夫人者流,被之声韵,鼓吹风雅。今予两人故在,不此之任,将以谁俟乎?因相与定为目,凡得纪十八,书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传二百,为《明史记》,……且自乐府成后半岁,而得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有奇,盖史事已过半矣,余与子固可谢息壤盟也。”(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可知吴炎、潘柽章等人所修的《明史记》到顺治十一年(1654)已有部分成稿,但由于二人死于庄氏史狱,《明史记》未能成书。
③ 查继佐自序言其书起于甲申,成于壬午,而沈起《查东山年谱》却讳言,“乙未先生五十五岁,讲学敬修堂,始著《罪惟录》,历二十年始成”。康熙元年,查继佐受史狱波及入狱,次年获释。至查去世前一年,沈起年谱记载,“乙卯先生七十五岁,春,《罪惟录》成。”
④ 据张元济跋文,整理之前的《罪惟录》,“阅时既久,虫鼠为虐,大者或连篇累牍,首尾不完;小者亦零乱散片,破碎支离,装工无识,妄相凑合,文义乖舛,不可卒读,反覆追寻,棼丝稍治,此不可谓非艺林幸事。”
⑤ 费密《荒书》“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费密《荒书》自序),直到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广泛征集有关明朝史料时才整理旧稿,完成全书。
⑥ 据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云,“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余所蓄书千余卷,尽亡。”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⑦ 据《碑传集补》卷三十五《潘力田传》,“私家最难得者实录,柽章鬻产购得之,而昆山顾炎武、江阴李逊之、长洲陈济生皆熟于典故,家多藏书,并出以相佐,间出其稿质之钱宗伯谦益,谦益大喜之,叹曰:‘老夫耄矣,不图今日复见二君。绛云楼余烬尚在,当悉以相付。连舟载其书归。”
⑧ 谈迁居硖石紫薇山西南麓也是园,查继佐自粤归浙筑敬修堂于杭州,又筑幽居于硖石沈山东麓万石窝,紫薇山即西山,沈山即东山。
⑨ 纂修时间见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第127页。
⑩ 王雯耀在《全桐纪略》自序中所标时间为康熙八年。
(11) 计六奇在二书自序中都署为康熙十年。
(12) 黄宗羲自称书成于康熙丙辰之后,即康熙十五年(1676),但并未刊刻。
(13) 《流寇长编》即戴笠、吴殳所修《怀陵流寇始终录》,据其书,始于崇祯元年(1628),终于康熙三年(1664年),成书时问当在康熙三年之后。又据谢国桢考证,“戴笠,字芸野,初名鼎立,字则之,吴江人,冒沈姓。弱冠受知章之圻,以冠邑军得县庠生,撰流寇长编。会庄氏史祸起,人以著述为讳,笠如故,与顾炎武、潘耒交。”(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264页。),又据戴笠卒年为1682年,可见成书时间当在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十八年之间。
标签:康熙论文; 清代文字狱论文; 史学史论文; 历史书籍论文; 历史论文; 查继佐论文; 罪惟录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