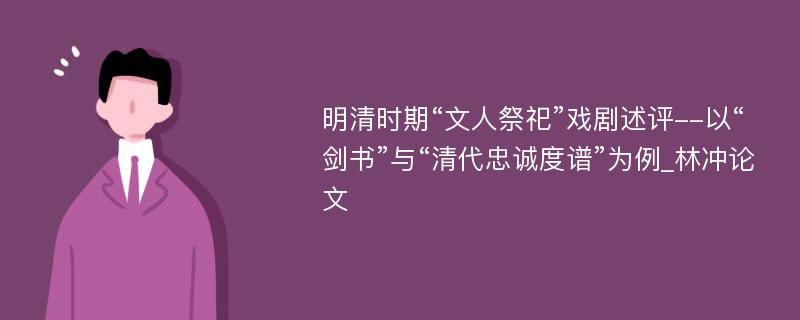
明清易代之际“士子献祭”戏剧审视——以《宝剑记》、《清忠谱》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子论文,为例论文,宝剑论文,明清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西方戏剧理论传入中国始,中国近现代戏剧理论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一个纷争不断且至今未有明确结论的问题就是,以戏曲为主体的中国古典戏剧,究竟有没有悲剧?针对此一问题,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笔者发现无论是认为中国有悲剧者还是认为中国无悲剧者,似乎都忽略了中国古典戏剧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戏剧群落。
这一戏剧群落的主人公基本都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如比干、伯夷、叔齐、介子推、伍子胥、申包胥、屈原、豫让、董宣、苏武、张纲、尉迟恭、狄仁杰、褚遂良、颜杲卿、张巡、许远、赵普、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杨涟、杨继盛、海瑞、周顺昌等,他们几乎无不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智识才俊,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锻造的社会精英。他们每每代表着社会的良心,点燃着时代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仁人志士、豪杰英雄。而在剧作中,他们往往更加生动、更加完美地再现着共同的生命轨迹——以踌躇满志的政治抱负步入仕途,以不容践踏的心灵准则面对挑战,鄙视邪恶,捍卫道义,无惧无悔,不屈不挠,不惜以生命的消逝、肉体的毁灭奉献于理想的祭坛。这类人士实际就是中国古代的“士子”阶层,更有鉴于这些剧作所体现的是一种可以称作“献祭”的承当精神,在这里姑且将这一戏剧群落命名为“士子献祭”戏剧。在“士子献祭”戏剧中,悲剧的两大元素即道德感和崇高感,没有丝毫欠缺。可以说,这些悲剧的主人公是中国戏剧中真正具有“崇高”意味的典型形象,他们身上体现的无疑就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悲剧精神。
一、“士子献祭”戏剧的基本认知
如果将中国戏剧史资料认真检索一番,就能发现中国戏剧从真正形成、发展到鼎盛、没落,“士子献祭”戏剧从未缺席过。据我的初步统计,在南戏、杂剧、传奇中,这样的剧目至少也有七八十部,其中以《赵氏孤儿》、《比干剖腹》、《屈原投江》、《苏武牧羊记》、《张巡许远双忠记》、《鸣凤记》、《精忠记》、《清忠谱》、《朝阳凤》、《党人碑》、《崖山烈》等影响较大。这一类剧目,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杂剧十二科”中,列为“忠臣烈士”、“叱奸骂谗”两科,还有相近的“披袍秉笏”、“逐臣孤子”两科。剧作之主人公,无不都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子”,胆识过人的知识精英。剧作所展现的多是在朝政晦暗、政事紊乱时期,或者异族入侵、社稷危亡时刻,这些“士子”为了捍卫道义,抵御邪恶,扭转不幸的危局,怀着神圣的使命感,无所畏惧,奋起抗争,甚至坦然面对死亡,毅然将宝贵的生命奉献于血与火的祭坛。这种自觉的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殉难”精神,显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宗教般的承当精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献祭精神”。
这一类剧目,总令人联想到某些研究者经常提及的“忠奸戏”①,但其实“忠奸戏”并不能完全涵盖此类剧目的美学属性。许多研究者往往并未重视此类剧目的“崇高”属性,对其美学高度的认知也存在严重缺失,观照视角不免肤浅片面。至于那些否定中国有悲剧存在的研究者,可能对此类剧目根本未曾考虑,未曾注意到其丝毫不逊于西方戏剧的悲剧内涵。那么,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士子献祭”戏剧的基本性质呢?这需要从该类戏剧的文化渊源谈起。
杜维明说过,儒家思想中有一种“强烈的抗议精神”。所谓“抗议精神”,就是指一种独立的人格,是指能为老百姓争取权益的天下精神。《尚书·周书·泰誓》中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即“天”的看法就是“民”的看法,“天”的感受就是“民”的感受。据此杜维明认为,“儒家的自我形象应是以悲天悯人的道德关切来转化政治,而不应依附在现实政权上,成为现实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工具”。体现这种精神的“士子”,“并不是来自政治权威的认可,而是文化抱负道德理想所引发的超越感,是脱离政治权势之外而凌驾其上的名幅其实的权威”②。而张灏认为,这种儒家精神更像是一种“烈士精神”③。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思想的要义与道德命脉,并熔铸为中国“士子”阶层厚重的“文化人格”。
须知,儒家思想从发端起,就与中国古代的社会乱象深深纠结。“士”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产物,兵燹不绝的春秋战国反倒是其崛起的沃土。儒家创始者孔子一生奔走、呐喊的目的是为扶起那根断裂了的天柱——西周初始制定的“礼乐”。然而,他却偏偏遭遇了一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④的时代,这是一个伦理体系大规模崩坏的时代。或许是出于一种以完善个体品行再造社会秩序的美好希冀,孔子将对“礼乐”的崇奉转向对人内心的“仁”的吁唤。在孔子的阐述中,“仁”的概念是多层面的,标准也是很高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⑤。倡导的是对苍生的关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⑥,倡导的是对道德的自觉;“三月不违仁”⑦,倡导的是对操守的坚持;“士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予议也”⑧,倡导的是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⑨,“不降其志,不辱其身”⑩,倡导的则是仁者的刚强和尊严的不可动摇;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1),则透露出他对生命和仁义的权衡取舍,此时的孔子已然为“仁”蒙上了一点“献祭”的色彩。
继孔子之后,儒家“亚圣”孟子则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视为人生之最高境界,让后代的士子看到了一种更为豪迈、更为磅礴的追求。“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12)。从这里,我们已经明确地感受到一种“儒家抗议精神”的浩然正气,感受到一种对理性自觉的依存,对意志坚定的强调,一种心灵刚健与优美道德的糅合,正义之感与凛然志行的和谐。所谓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13),与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4)相比,孟子更为明确地崇尚以身体的毁灭挽救天下之道的“献祭精神”,并将“献祭”这一极具悲情色彩的行为视为每一个大丈夫之必然选择。
然而,到了宋明时期,儒家思想被进一步理学化,其践行理想、引领社会的使命也被进一步经典化。为此,理学大师们更将“士子”的德行要求提升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地。朱熹曾言:“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15)他进而声言:“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16)所以,朱熹主张“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并说“使圣贤本自高,而己别是一样人”(17)。较朱熹更早的周敦颐,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说法(18),将“士”的样板由“贤”至“圣”,乃至提高到“天”的地步,认为只有将“圣贤”之道作为身体力行的终极理想,“振三纲,明五常,正朝廷,励风俗”(19),这才是生命的最高准则、价值的最高体现。这样的理念,又经过明代理学家的发扬光大,对中国“士子”的人格塑造影响巨大。
被理学化了的儒家,对社会义务的应尽之责进行了更为苛刻的强调。也将以其作为正邪判断的悠久传统,通过成功的教育,深入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潜意识中,进而固化为一种非常强势的纲常伦理观。这样,所谓的“仁”、所谓的“义”,就不仅仅是“士子”需要永远恪守的人生通则,更是必须无条件捍卫的社会公理。而且,他们深信,他们的抱负是尊贵的,心志是优越的,他们的举措是正义的,情怀是无私的。于是,在这个“士”群体中,就形成了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的千古不变的“集体意识”。所以,当现实与他们的向往无法协调时,当不幸的世道冲击了他们认定的准则时,当朝政晦暗、政事腐败或者异族入侵、社稷危亡时,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就会成为他们中的佼佼者的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断然选择;而退却自保、苟且偷生,则被视为其最大的耻辱和失节。这一切,奠定了“士子献祭”戏剧最能体现的悲剧精神的文化源起。
当然,欲考察“士子献祭”戏剧不可能与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危机情境分开,尤其不能与江山“易代之际”的士子文人心态割裂开来。之所以放大江山“易代之际”的古典戏剧创作,是因为这样的情境不仅仅是一个结点,还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勾连,因为国祚变故的因果并非仅孕育于此刻。也就是说,“易代之际”的“士子献祭”戏剧的悲剧精神,固然可以进行微观考察,但更应该在此基点上进行顾及前因后果的宏观观照。赵园说过:易代“‘之际’既是中国史重要的时间点,又与民族史交集,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民族间的遭遇虽非始于此种时刻,却在这一时刻,一个(或不止一个)民族深入到另一民族内部,民族生活发生了长时间大面积的交接,此种‘之际’意义岂不重大!”(21)所以,如果仅止于微观目光所及,因了一个点而忽视了“大面积”的全局性探究,视野无疑会是局促的,也是很难得其要义的。
如果我们将古典戏剧自南宋真正成熟之后的几次国祚更迭时的剧坛情境稍加放大,就会发现,无论从戏剧发展的成熟度上,还是从“献祭”的动机上,明清易代之际的“士子献祭”戏剧是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并且,其时的戏剧均伴随着家国环境和士子心态的变化而鲜明地变化着。换句话说,在清代“花部”戏剧产生之前,明末清初的“士子献祭”戏剧仿佛就是一条与其时的中国“士子”思想史同生共息的并行线。从中不仅能够窥测出中国士子阶层所具有的充满悲剧精神的英雄原型特质,也能够勾连起传统文人与“士子献祭”戏剧之间的风云际会,并从中感受到他们在心灵最为撞击时刻的精神选择。
下面笔者选取明清易代前后的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进行初步论述,以期对“士子献祭”戏剧作一审视。
二、《宝剑记》:“以乐事系其心”
从明代大量或存或佚的“士子献祭”戏剧中可以看出,以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开先创作《宝剑记》为界,传奇作品历经明朝百余年发展后,从僵化的教化剧开始向宣泄人之真性情、表达社会心声、具有现世精神的创作转变。与表达英雄主义气质以及赋予隐忍、复仇主题的元代“士子献祭”戏剧大相径庭的是,以李开先《宝剑记》为开蒙贯穿至清前期的大量“士子献祭”戏剧,更多表达的是朝纲的混乱、忠奸的对决、忠义的投报无门、献祭者的傲骨。同时,在创作中往往以疏泄创作者“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适。夫既不得显施,譬之千里之马,而困槽枥之下,其志常在奋报也,不得不足而悲鸣,是以古之豪贤俊伟之士,往往有所托焉,以发其悲涕慷慨、抑郁不平之衷”(22)。林冲即是李开先选择的一个“坐消岁月”、“以乐事系其心”的典型。
“水浒戏”起于宋,发育于元,成于明,其中的一群草莽英雄群像,带着每一个朝代的独特印迹渐渐丰满。在元代,他们是孱弱而卑贱的文人幻梦中的英雄典型;在明代,他们则是“足以寒奸雄之胆,坚善良之心”(23)的士子代表。《宝剑记》是李开先根据《水浒》英雄林冲的故事改编而成,开篇即宣唱:“诛谗佞,表忠良,提真托假振纲常。古今得失兴亡事,眼底分明梦一场。”(24)短短几句,传统士子对奸佞的蔑视、对忠义的执著、对世事的感怀与无奈,充溢而出。这已经预示,作为披着“水浒”外衣但主题已经完全现实化了的作品——《宝剑记》,的确堪称是一部假林冲之躯的代表众多“士子”“发其悲涕慷慨、抑郁不平之衷”的心灵自况,是一部具有引领时代风潮的标志性力作。
李开先的人生轨迹应该是明代中后期士子境遇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年轻时以出仕入世为抱负,身怀经世救国之志,存“鞭挞四夷、扫除天下、安事一室”(25)之心。为官期间,因其文名和才干而受嘉靖帝褒奖,敕命为承德郎,然终因“负才气,居铨衡要路,素伉直,不善事权贵人”(26)而成为政治党争的牺牲品。李开先壮年时由于“九庙灾”被罢,但入仕之心却并没有就此泯灭,对君主仍心存希冀,这固然是李开先个人的局限,同时也是传统社会下深受儒家思想浸染之文人的迷津:不反天子,仅反权奸。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昏君和权奸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实的遭遇、局内人的身份,必然使李开先将权奸误国设定为《宝剑记》的主旨核心。在施耐庵小说中,从第七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至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一个武艺高强却生性安分、步步遭遇挑衅却力求息事宁人、本无心与朝廷针锋相对的军事教官,却因为遭遇陷害受辱、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的林冲,跃然纸上。而作为《宝剑记》中的林冲,显然与小说中的林冲形象大异其趣。以生角行当出现,注定脱掉一介武夫的外衣而晕染浓重的士子悲情。且看开场时林冲好一副抱负远大的抒怀:
[风入松引](生上唱)儒冠误我甚堪悲,笃志玩兵机。烟尘万里平胡骑。勋业徒劳心力。袜线未能补衮,寸草且报春晖。
[鹧鸪天]脱却儒衣褂战袍,学文争似督龙韬,才冲霄汉星芒动,啸倚崆峒剑气高。悲贼子,笑儿曹,争夸朱紫占中朝。十年塞北劳千战,汗马秋风尚未消。
[醉翁子]豪放,匣中宝剑无尘障,知何日诛奸党?自奖,虽不能拜将封侯,也当烈烈轰轰做一场。
[酹江月](生上唱引)晓风吹雨战新荷,可惜明珠进碎。闲启宝匣看古剑,紫电照人睛碧。僭榻妖狸,渡河胡马,眼见的太平非昔。空怀忠义气,为君等闲流涕。
[梁州序]埋轮的因何缘故?挂冠的为谁归去?只恐豺狼当路,虚张声势,朝市怎安居!又有心非口是、行浊言清,此辈真穴鼠!天下人皆醉,倩谁扶?笑倒三闾楚大夫。
剧中林冲一出场即消弭了小说中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单纯的武吏形象,一个立志“僭榻妖狸,渡河胡马”的儒将形象立于眼前。他拥有激情贲张之血性,拥有慷慨激昂之豪情,一身的豪气和正气促使他立志为君王分忧,于是“仗剑投于军门,生擒斩首,次第成功”,被授“征西统制之职”。纵然屡次因谏诤奸臣而被贬谪也没有毁损他心中嫉恶如仇的本性,而“空怀忠义气,为君等闲流涕”的慨叹也仅仅是他在落寞时暂时的心灵参悟罢了,终究“虽不能拜将封侯,也当轰轰烈烈做一场”的抱负才是他终生的理想。但这一个林冲,同时也是深具士大夫情怀的忠臣义子。他出身于簪缨世家,其祖乃著名隐逸诗人林和靖,其父乃成都太守林皋,幼承家学,习读诗书,孔孟经学无不充溢其血脉。“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时时牵扯他的心灵,当“眼见得太平非昔”,朝廷奸臣高俅、童贯等“拨置天子采办花石,荒淫酒色”,致使“百姓流离,干戈扰攘”时,他愤懑难抑;面对朝廷人人“上下怀利,惟钱而已“的丑恶现状,他怀念“贤如颜孟”、“伊尹扶汤”的前世贤明。在他的心中“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是所有士子应具备的行为准则,而那种难以克制的忧患情结、当仁不让的士气禀赋,则是他的英雄血脉中挥之不去的悲剧元素。英雄的悲剧性往往恰源于此。我们或许可以否认《水浒传》中林冲的悲剧性,毕竟逆来顺受、处处隐忍、被逼无奈的苍凉难以与为了众生社稷而主动承当相类比,但我们无法否认《宝剑记》中林冲的悲剧性,李开先完全跳出前人对林冲这一落草为寇人物的演绎,将林冲的动机置于社会冲突而不是简单的家庭冲突的基础上,不落窠臼地上演了一幕震撼人心的“献祭”悲歌。
与小说中的“宝刀”不同,《宝剑记》中的“宝剑”作为道具,它似“草蛇灰线”游弋于全篇,它无疑是林冲处境的隐喻。因为,宝剑自古就是贵族的佩剑,不仅可以防身,更是其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而武将之剑好似文臣之笔,剑既是武将的生命也是武将的精神所在。剧中宝剑与林冲的分分合合暗合林冲命运的起起落落。剧之初始乃“顿闲”之宝剑,日久未用的蒙尘之剑自然是林冲现状的比拟,因毁谤大臣之罪,被谪降巡边总旗,幸蒙张叔夜举荐,做了禁军教师,提辖军务。久而不见用的林冲仿佛匣中宝剑蒙尘,但是依旧掩饰不住他的踌躇满志。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子,并不因为自己的一时失意境遇而对自己的信仰有所犹疑,只是空怀忠义,感叹宝剑在手却“不能指挥将士,扫除边疆,虚负此剑”。待价而沽的宝剑和等待时机的士子,岂不是同命相连吗?所谓“剑有用处,但不遇时”,正是林冲彼时的心声。
是剑就会有剑气冲天的时刻。李开先笔下的林冲满身浩然正气,咄咄逼人,儒家的正统观念使他不能坐视朝廷积弊,他不顾自己曾经被贬谪的经历,再次弹劾奸佞,也不顾黄门官劝阻,誓“将颈血一腥腥把龙袍溅,望天颜不由我一声声分辨”。“士子献祭”的悲剧精神关键就在于献祭者的主动性。《宝剑记》林冲的反抗完全挣脱了小说中的被动,一个与奸臣势不两立的忠义谏臣,始终相信“吾皇听微臣短谏”,“剪除逆党”,“浮云扫除,重开日光”,始终坚持以个体行为来扭转整个朝廷的黑暗,他因此得罪了权柄而身陷白虎堂,遭遇宝剑的“尘埋”,成为孤臣孽子。他与古今忠义士子一样,在权奸横行的时代,以螳臂挡车之力来捍卫自己的忠节,因为他相信“忠心,自有神明鉴烛”。林冲深陷囹圄,无限感慨:“不想遭逢刑宪,难捱苦万千。怎遣夜如年?封着一盏孤灯,半明半暗。相伴着些罪徒囚犯,吃苦招愆。英雄到此展挣难,肢体不禁寒,从教饿鼠餐。”尘埋宝剑与末路英雄一样,不可谓不悲凉。林冲在野猪林被害的一刻,无限伤怀,“平生豪气,为皇家争南战北。做英雄死在无名地,不由我感叹伤悲”。一个极具士大夫情结的儒将在刑役折磨、苦不堪言之时,依然高唱“为国输忠惹寇雠,追思日夜总悲愁;悲同夜雨千行泪,愁染西风两鬓秋。报主空存苏武节,思乡懒上仲宣楼。天如留我残躯在,不斩奸臣誓不休”。其执著、倔强、刚烈的抗争精神,并未在逆境中遭到丝毫的毁损。
李开先的林冲带着明朝士子特有气质而来,坚韧与患难同在,忠贞与屈辱并行。正像赵园所言:“无可比拟的残酷,反而鼓励了明清之际的士人对理想政治、理想人格的向往,甚至可能正是这种残酷,使有关的向往及其表达明晰化了。”(27)此语虽然是对明清之际士人的概括,大抵也可以窥测明代酷政在明清之际的贯穿性,因此无以复加的磨难和对理想的追求是明代士子的最佳注脚。穷途末路的林冲,如鹰投罗网、虎陷深坑,依然难免奸谗之害,发配沧州的途中被权奸步步为营的迫害加剧了他内心的煎熬,草场地大火的嫁祸更加剧了他对现世希望的破灭,但理想就此泯灭吗?绝不会。“寻个出路”可谓是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的林冲投奔梁山的无奈选择。“挺身撞破漫天网,回首君亲遥想。寻思脱难总无方,忙投水浒暂潜藏”。一个“暂”字即泄露了林冲的内心,一个忠臣义士却最终落草为寇,在李开先看来并非首选,却流露出作者在现世中无路可走的悲悯,梁山这个曾经在林冲心中遥远但又近在咫尺的地方,此时彻底成为林冲绝境下的惟一选择。《宝剑记》第三十七出对林冲有国难投、仓皇出逃、踯躅前行的心理抒情,表达了明代士子对君、对国、对自我出处之间的强烈矛盾。这出戏被改为昆曲折子戏[夜奔]而传唱不衰,只是曲文中有一个“梁山”在,现实中却真真正正的无路可走。
[点绛唇](生上唱)数尽更筹,听残银漏。逃秦寇,好教我有国难投,那搭儿相求救?
[新水令]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驻马听]良夜迢迢,投宿休将门户敲。遥瞻残月,暗度重关,急步荒郊。身轻不惮路迢远,心忙只恐人惊觉。魄散魂消,魄散魂消,红尘误了武陵年少。
[水仙子]一朝谏诤触权豪,百战勋名做草茅,半生勤苦无功效,名不将青史标。为家国总是徒劳,再不得倒金樽杯盘欢笑,再不得歌金缕筝琶络索,再不得谒金门环佩逍遥!
[折桂令]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恰便似脱扣苍鹰、离笼狡兔、摘网腾蛟。救急难谁诛正卯?掌刑罚难得皋陶!鬓发萧骚,行李萧条。这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
[雁兒落]望家乡去路遥,想妻母将谁靠?我这里吉凶未可知,他那里生死应难料。
[得胜令]呀!唬的我汗浸浸身上似汤浇,急煎煎心内类油调。幼妻室今何在?老尊堂恐丧了!劬劳,父母恩难报;悲嚎,英雄气怎消。
[沽美酒]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哭号啕。拽长裾急急蓦羊肠路绕,且喜这灿灿明星下照。忽然间昏惨惨云迷雾罩,疏喇喇风吹叶落,振山林声声虎啸,绕溪涧哀哀猿叫。吓的我魂飘胆消,百忙里走不出山前古庙。
[收江南]呀!又只见乌鸦阵阵起松梢,数声残角断渔樵。忙投村店伴寂寥。想亲帏梦杳,空随风雨度良宵!
本是朝廷臣子,却成了孤独天涯客,林冲彷徨而惊恐,“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疾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犹豫和矛盾溢于言表,一个蔑视俗流的士子豪杰由于不畏权奸,秉承正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却遭遇权奸爪牙的追捕,慌不择路,全然“顾不得忠和孝”。一个本想做“封侯万里班超”的报国者,却“生逼做叛国的红巾”,暗夜疾行之时,百感交集,英雄长叹“百战勋名做草茅,半生勤苦无功效,名不将青史标。为家国总是徒劳”。对于中国儒家正统熏染下的“粹儒”来说,像《宝剑记》中公孙胜那样“丹心为国怀忠谏,朝奏九重夕贬,设饵苦贪禄位,不如归去田园”的挂冠参悟,恐怕只会是挫折时刻的偶然灵犀一现,林冲“红尘误了武陵少年”的悔意就如是,归隐或许是他暂时的停歇,也或许是他无奈的喘息,却绝不是他心中的终极追求,看似绝意脱离朝廷的林冲,却一步一回头地投奔梁山,依然唱出“救急难谁诛正卯?掌刑罚难得皋陶!鬓发萧骚,行李萧条。这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纵然个体的谏诤处处碰壁,那就借助梁山的英雄正义之师剪除朝廷黑暗,“博得个斗转天回”。林冲投奔梁山并非逃避,也并非造反,其真正所怀的依旧是忠臣义子的拳拳之心。梁山在李开先笔下无疑是与暗无天日的朝廷政治相对照的,是“屯兵欲剪滔天害”的光明之地,也是一个“英雄处处望风来”、义气豪杰啸聚之所,借助梁山十万雄兵打回汴京,扫清地界,救天下苍生,是林冲的救国方式,也是为自己报仇的惟一方式,当然这也是李开先“补现实之恨”的虚幻之举。林冲在真正落草之际,对天盟誓:“上苍!上苍!背主为寇,非是林冲不忠,乃被高俅逼迫,略无喘息之地。龙居浅水真非计,终归大海作波涛。专望招抚,再报君恩。不免望阙遥拜上几拜。”这也为之后林冲的被招安埋下了伏笔。宝剑“尘埋”良久,终有冲天一刻,龙居浅水,终有归入大海之时,英雄末路,终有壮志酬展的时机。在《宝剑记》中,这个时机并非源自皇恩浩荡,而是源自打家劫舍、哄州劫县的绿林英雄,这之于李开先无疑是大胆的。林冲统领梁山豪杰“同擒四囚,先索高俅。扶持宋明君,必斩佞臣头”;咆哮着“跋扈强良,当吾者死。風霆迅急,直抵汴京”。这一切都是为了“谢吾皇涵养林冲雨露仁”,士大夫情怀的林冲当然难以更改他对正统君王的笃诚,因此,剪除奸佞后的林冲接受朝廷招安甚至于渴望被招安的心理行为注定了这是李开先笔下之林冲而非施耐庵之林冲,同时这也显露出李开先对政治澄明、道尊于势的幻想表达。无疑,这样的林冲是更加“崇高”的,更加具有复杂的心灵世界和悲剧内涵的。
三、《清忠谱》:“目之信史可也”
就是在明亡到清初之际,一个堪与元代大都书会才人相媲美的戏剧作家群落出现了。这个作家群落,就是以李玉、朱素臣等为代表的“苏州作家群”。这些剧作家基本生活在明万历到清康熙年间,创作活动从明崇祯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康熙中后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群落中人共同的创作理念、相似的气质旨趣、极高的艺术成就和注重场上搬演的创作目的,使他们的剧作更为耀眼。
吴伟业在为李玉《北词广正谱》做序时说:“今之传奇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较昔之歌舞更显而畅矣。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于是乎热腔骂世,冷板敲人,令阅者不自觉其喜怒悲欢之随所触而生,而亦于是乎歌呼笑骂之不自已。则感人之深,与乐之歌舞所以陶淑斯人而归于中正和平者,其致一也。”(28)在虚幻世界中寻找彷徨的自我,在文字的演绎中寻找精神的补偿,是彼时的作者努力探寻的创作旨趣。“苏州作家群”的作者们,在入清后已绝意仕进,通过对“道”、“势”观念的重整,他们的剧作,无论是时事剧抑或历史剧,均深深地烙上明清易代之际“遗民”的痕迹。《如是观》的岳飞与作者张大复、《清忠谱》的周顺昌与作者李玉、《朝阳凤》中的海瑞与其作者朱素臣、《埋轮亭》中的张纲与其作者朱佐朝、《党人碑》中的刘逵等四秀才与作者邱园等,实际上反映出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难分彼此的处境。入清以后,这些被历代一书再书的士子英雄自然会成为他们重要的剧作选材的对象,并进而注入较史实更为丰满深厚的思想与更为悲凉肃杀的情节。可以看到,秉承文人独有的社会责任感,遵循“以史入戏,以戏写史”的创作理念,借以抒发自己的故国思恋与亡国痛楚,也从英雄遭遇的衰世浊道、昏佞主政的血腥后果中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悲剧原因,已经成为明清鼎革时期这批江南才子群体性的艺术取向。
《清忠谱》由李玉主撰,朱素臣、毕魏、叶时章等参与创制。剧作以明天启年间“阉党”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导致的以五义士为首的苏州市民暴动的史实为依据,开始将时事戏剧(29)引入一个更加纯熟的境界。明末清初学者张岱曾言:“魏珰败,好事者做传奇十数本,多失实”(30);惟《清忠谱》被吴伟业称为“事据按实,其言也雅训,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31)。能够“目之信史”,是继《鸣凤记》之后时事戏剧的一个新飞跃。其最关键的特色在于,之前“士子献祭”戏剧的故事主人公,基本局限在读书人这一群体,或者将“士子”阶层的性格灌注于“他者”之身。因此,其悲剧精神与庶民意识的疏离可能导致曲高和寡,“献祭”者死难的醒示大众功能也不免有所折扣。而《清忠谱》不仅将“阉党”之蛮横猖獗、东林党人的嫉恶如仇渲染殆尽,更重要的是,代表广大百姓的“市民”这一角色登场,与读书人共同谱写了一曲“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32)的悲歌。而当“士子”精神真正融入更广阔的社会群体中时,正义必将变得不再那么孤独。剧作中,以“述珰”、“缔姻”、“骂像”、“忠梦”、“就逮”、“叱勘”、“囊首”一条线与“书闹”、“义愤”、“闹诏”、“捕义”、“戮义”、“毁祠”另一条线,双线平推,交叉有致,内容丰厚,节奏紧张,却无一折为赘笔,而最终汇集于“魂遇”、“表忠”两折,为明末江南无数不屈抗争的市民凝聚了一幅艺术的缩影。《清忠谱》中的“主脑”人物周顺昌,一位因“疏逐东林”、“株连削夺”的被黜官员,他代表的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知识群体。他“冰心独报,挺然傲雪孤松;介性不和,矻尔颓波一砥。读圣贤书,凛凛纲常昭日月;负须眉气,冲冲忠义满乾坤”(33)。通常的“士子献祭”戏剧中,这样的角色一以贯之并不鲜见。鲜见的是,与东林党人素昧平生的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生于编伍”,“生平任侠,意气粗豪。闪烁目光,不受尘埃半点;淋漓血性,颇知忠义三分”。也就是说,他们不谙诗书但渴求正义的心灵,是与周顺昌等辈完全相惜相印的。他们是“士子”精神的崇仰者,但其血性、其激情、其“成仁取义”的豪杰之气,丝毫不弱于前者。有学者言:“儒者的豪杰想象,与世俗想象又未必全无关涉。士大夫的英雄情结与世俗民众的江湖向往之间,一向没有太远的距离。这或也可以归于为数不多的精英与民众共享的领域。无论在儒者还是俗众,‘豪杰’无不是综合了精神、意气、能力等等的评价。儒者所欣赏于其‘豪杰’者,无非是那种发扬蹈厉的精神状态,强毅果决的意志力量;与此相对的,则是为他们所鄙的‘拘’、‘陋’、‘琐’。”(34)颜佩韦、杨念如等的“世俗民众”与儒者的“豪杰想象”,确实没有多少“距离”。中国历史一再证明,没有这些“市井”英雄的参与和支持,孤掌难鸣的“士子”,很难圆满地实践自己的理想使命。
必须看到,《清忠谱》中五人的“豪杰”之气,显然不能等同于古典戏剧中“投桃报李”的感恩之举,也不能等同于那些为报答“恩主”轻易付出生命的“义仆”们,因为明末的文化启蒙思潮同时推进民间的启蒙,曾经居高临下的士子精神经过时代的淘洗,开始向底层渗透。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平等与独立等观念,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庶民的行为。颜佩韦、杨念如为代表的五人,显然属于近代社会思潮的产物。他们并不依附任何“主人”,他们独立表达自己的意图,向往和追逐“大义”;他们为了理想信念无畏无悔的“献祭”精神,其渊源则依然来自于孔子“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和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思想熏陶,依然浸染着儒家文化的色彩。
《清忠谱》中的颜佩韦,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剧中成功塑造的最早的“市民”形象。此人素来“敬得是有仁有义,有些肝胆便投机”,钦佩的“专诸是市井屠夫,拼命献鱼肠,赢得雄名万古;要离乃吴门一介,残形施匕首,传来义气千秋”。在“书闹”一折中,说书人说到此段,曰:“圣旨读道:‘韩世忠按兵不举,丧师辱国,失守封疆,囚解来京。’读诏才完,众将官推着一辆囚车到帐。广阳王道:‘奉圣旨,速将韩世忠跣剥,上了刑具,钉入囚车。’众军士就将韩元帅剥下盔甲,上了镣杻,推入囚车,四面把铁钉钉了。韩元帅那时真个是浑身是口不能言,遍身排牙说不得了。”这时,颜佩韦怒不可遏,情不自禁就砸了书场。显然,身份的卑微并不能磨灭他的侠肝义胆,近代社会的平等理念已经给予他强大的精神支撑。他是一个“怀公愤,是忠义俦”的血性男儿,却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顺民或义仆。因为这种出于公义的“献祭”性行动,与那些出于私德的报恩性“牺牲”,已经有了关键性的区别。因此,他在听说校尉要来苏州捉拿乡宦之时,尽管“未知所拿何人”,却也心急如焚,“倒教俺一夜放心不下”。在他的眼中,周顺昌这样清廉正直、不惧“阉党”的乡宦,恰恰又是他钦佩的“清官”。心灵中的敬仰,情感上的倚靠,促使他决意挺身而出,集结群众,誓与官府理论,即使有一线希望,也要竭力救援。故此,就有了“闹诏”一折中颜佩韦等与缉捕差役们的正面冲突。而他的这种“舍生取义”的“献祭”,无疑已经完全打掉了地位卑微的自怯,彰显着一种自身价值的肯定,一种或许多少尚显朦胧的平等意识的觉醒,以及具有近代理念萌芽的底层社会尊严的表达。以“崇高”的悲剧形象标准衡量,颜佩韦肯定是当之无愧的。
显然,这种市民阶层对官家的反叛,也绝不同于农民的起义与造反。与那些“心怀帝阙”意在打倒“皇帝坐江山”的农民领袖不同,与那些“啸聚山林”的草寇不同,具有商品社会背景的最底层人士与思想超卓的“士子”阶层联手,追求剪除“阉党”,清明社会,其意义可能是划时代的。在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就义时刻,剧作是这样表现的:
[泣颜回](合)痛哭断人肠,无罪轻罹法网,哀哀死别,那堪死别云阳。君门万里,呼冤叫屈难稽颡。(内鸣锣击鼓介)(生)你听锣鼓之声,一定绑赴市曹来也!(急奔介)(合)霎时间,天日为昏,百万姓,暗中称枉。(下)(净、末、丑、旦、贴绑缚招旗,付、小生、外扮刽子押上。)
[泣颜回](合)刚强,仗义久名扬,说甚身遭无妄。权党肆虐,堪嗟毒流天壤。(刽)自己惹出来的祸,说他怎么?(末)呸!我杨念如是怕死的么!(净)我颜佩韦打死校尉,万民称快,死也瞑目了。(合)锄奸击贼,五人儿也不愧东林党。只可惜救不得周吏部,死有余恨。痛孤忠万里俘囚,枉吾侪一朝倾丧。
[越恁好](合)市曹忙赴,市曹忙赴!急煎煎,苦怎当!听神号鬼哭添痛伤,倍凄怆。(老跌介)(生扶起急行介)苦颠连体僵,苦颠连体僵!见乱纷纷万千人,流涕道傍。扑簌簌泪抛,扑簌簌泪抛,痛杀杀一会儿割断寸肠。
[红绣鞋](合)头囊三木,悲伤!悲伤!血流一派,汪洋!汪洋!魂缥缈,魄飞翔,情惨切,恨绵长。兄撇弟,子抛娘。
[意不尽](合)侠肠一片知何向?热血淋漓恨满腔,一时鲁莽,博得个义风千古人钦仰。
在过去真实的历史上,草野之民的死微不足道,也很难获得应有的崇敬。“献祭”的“士子”,因而也往往是孤独的。他们赢来的,更多的是事不关己的冷漠看客,很少有践行者的追随。五义士的行为则深深触动广大百姓久已麻痹的神经,也可以看作是对他们心头“民”之意识的一次呼唤。当“蓼洲周公”周顺昌“忠义暴于朝廷”、“荣于身后”的时候,五义士也“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35)。五人得到平反昭雪,也获得了死后的荣耀。时代在前进,人心在前进,率先吸纳进步思想的底层先行者、拥有独立意志的平民清醒者,虽然是少数,但正是这些少数者的胆气和热血,才可能换得再不是芸芸众生麻木不仁的静默,而是在杀气腾腾的专制政治面前的风起云涌、前赴后继,最终争得“顺昌”、“逆亡”的浩浩荡荡的辉煌。
明清易代之际的李玉,“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36);复因其遗民和“申相国家人”的双重身份,成就了其异于正统“士子”的独特视野。入清之后,又“即当场之歌呼笑骂,以寓显微阐幽之旨,忠孝节烈,有美斯彰,无微不著”(37),取代了自己此前温婉旖旎的风格,假借周顺昌、方孝孺、岳飞等一个个鲜活的戏剧形象,揭示了山河动荡时刻明清之际的社会真实。
明末清初的“苏州作家群”才俊们,在江山易代的特殊境遇之下,被慷慨卫道继之隐逸的狂潮裹挟着,纷纷主动远离清廷,力求洁身自好,守忠尽节,其本身就带有某种“义不食周黍”自甘“牺牲”的悲壮精神。所以,绝不能因为他们的“绝意仕进”而漠视其“士子”襟怀。相反,天翻地陷的历史动荡,更加滚沸了他们血脉中灼热的“献祭”激情。于是,除《清忠谱》外,李玉的《两须眉》,以李自成入戏;李玉、朱佐朝的《一品爵》,邱园的《蜀鹃啼》,以张献忠入戏;朱素臣的《朝阳凤》,以海瑞入戏;李玉的《千钟禄》、叶稚斐的《逊国误》,以明初被朱棣逐走的建文帝入戏。他们极善于将特定时期的重大事件与广阔的下层生活紧密结合,极善于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活灵活现地点化于笔端。可以说,正是这个延续半世纪的戏剧作家群落,用自己的才情挑起了乐感文化孕育下民间百姓的时代感和使命感的神经,用戏剧形式打通了知识层与俗众群的精神渠道,在思想动荡之际开启了一扇启蒙的大门。也正是这个戏剧作家群落第一次“把文人的戏曲创作从官僚士大夫家庭戏班的红氍毹引向社会舞台”(38),将明末清初辉煌一时的“士子献祭”戏剧推上了巅峰。
注释:
①以忠奸对立、正邪冲突为主题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主要人物为两大阵营:一是忠臣义士,一是权奸邪佞。情节发展是从邪压倒正转化为正压倒邪。以明清传奇居多。郭英德在《论明清文人传奇的忠奸斗争主题模式》(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一文中言道:“在明清文人传奇中,大多数历史剧和时事剧都呈现出忠奸斗争的主题模式。”
②郑文龙编《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188页。
③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90页。书中提到谭嗣同的思想层面是由他的世界意识、唯心倾向和超越心态熔铸成一种特有的理想主义精神。在戊戌死难时所表现出的烈士精神可以说是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他生命中的体现,震撼了一个时代,同时也为早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典型。也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回响。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4)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1页,第323页,第177页,第145页,第92页,第355页,第475页,第402页,第210—211页。
(12)(1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2页,第321页。
(15)(1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一三第225页,卷八第113页。
(1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吴斗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7页。
(18)周敦颐:《周子通书》志学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汪尚书(甲申十月二十二日)》,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299页。
(20)《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
(21)赵园:《再说想象与叙述——以明清之际、元明之际为例》,《想象与叙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22)(23)雪蓑渔者:《〈宝剑记〉序》,吴毓华编《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7页,第46页。
(24)李开先:《宝剑记》,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嘉靖原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以下唱词均出自此剧。
(25)李开先:《塞上曲序》,《李中麓闲居集》卷五,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刻本。
(26)殷士儋:《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李公墓志铭》,《金舆山房稿》卷九,明万历十七年刻本。
(27)赵园:《说“戾气”》,《明清之际的思想和言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页。
(28)(36)(37)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吴毓华编《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第319—320页,第320页,第320页。
(29)值得一提的是,《宝剑记》假借林冲之躯写明代弊政,为时事剧的先声之作。而之后无名氏创作的《鸣凤记》则比《宝剑记》更进一步,以嘉靖朝严嵩弄权,杨继盛、邹应龙等八义臣谏诤的政治事件为叙述本体,以真实的人物为依托,彻底颠覆了文人隐晦托古的撰曲方式,记述了一段尚未尘封的历史,为时事剧真正的开山之作。《清忠谱》则是继《鸣凤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时事剧。
(30)张岱:《陶庵梦忆·西湖寻梦》,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31)吴伟业:《〈清忠谱〉序》,吴毓华编《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第318页。
(32)(35)张溥:《五人墓碑记》,阙勋吾、许凌云、张孝美、曹日升译注《古文观止》,北京: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43页。
(33)李玉:《清忠谱》,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10页。以下唱词或宾白均出自此剧。
(34)赵园:《易堂三题》,《聚合与流散——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6页。
(38)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