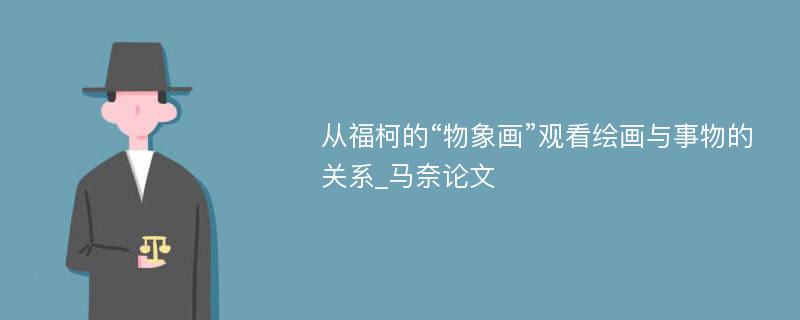
目光的追问——从福柯“实物—画”概念看画与物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物论文,目光论文,概念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马奈绘画的讲座中,福柯指出:“自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就存在着这样一个传统,即试图让人遗忘、掩饰和回避‘画是被置放或镶嵌在空间的某个片段中’的这个事实。……因此,自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这种绘画试图表象的是置放于二维平面上的三维空间。”①这段话使我意识到,在我们沉睡的意识之中似乎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误区,即想当然地认为那种在二维限度之中力图树立起一个三维世界的努力、那种总是试图凭借其巧夺天工的技艺来使自身摆脱作品身份而跻身于自然物序列的努力是属于绘画艺术本性的。这样的理解,会使得人们认为绘画自其根本处意味着一种致力于遗忘和摆脱自身的活动,其全部努力即在于让人忘记其自身固有的物质属性,在于让人以为它是自然真实之物,而不是画,不是某种复制品、某种表象。然而这种理解,无论如何导致了一种倾向性,即把自然真实之物,即绘画希望人们看到的样子,摆在较高的位置上,而把仍然带着其自身物质属性的绘画,即绘画试图遗忘和摆脱的样子,置于附庸的位置上。长久以来,人们痴迷于对绘画如何在二维平面上树立起一个三维世界的研究,或视其为制造假象的幻术,或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魔法,却往往不追问:为什么那个二维平面却是应当被抛弃和遗忘的?为什么绘画只有掩藏自身才能成为好的作品?绘画为何不能宣示其自身的存在?绘画之为绘画的本性究竟何在? 一、画之物性 一切仍需从绘画自身的物质属性说起。在这一话题上,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对海德格尔来说,谈论艺术及艺术作品,不可避免地要从其物因素(das Dinghafte)着眼。然而艺术作品之所以成其为艺术作品,却断然非纯然物自身所可造就。为了说明这一点,海德格尔试图首先透过物的概念的考察来澄清所谓作品之物因素者为何,唯此,在他看来,才能进而考察“艺术作品是不是一个物,而还有别的东西就是附着于这个上面的”,以及“根本上,作品是不是某个别的东西而绝不是一个物”②。然而随着对传统物概念的检讨,海德格尔也立即发现,各种既有的物的概念非但不能够清晰地表明物之物因素本身,反而总是阻碍着人们去发现它。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上面这些关于物的概念,为的是在这种知道中思索这些关于物的概念的来源以及它们无度的僭越,但也是为了思索它们的自明性的假象”③。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对既有的物概念的考察,在于彰显这样一种困难,即“毫不显眼的物最为顽强地躲避思想”④。正因如此,海德格尔不得不怀疑“纯然物的这样一种自行抑制,这样一种栖息于自身中的无所促逼的状态,恰恰就应当属于物的本质吗?那么,难道物之本质中那种令人诧异的和封闭的东西,对于一种试图思考物的思想来说就必定不会成为亲熟的东西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可强求一条通往物之物因素的道路了”⑤。面对物对思想如此顽固的抵抗,海德格尔试图说明两件事情,一方面,他指出“对物之物性的道说特别艰难而稀罕”⑥,想要直接从物之物性出发而达到对艺术作品的解释,目前看来是不太行得通的;另一方面,他也并不由于这条路不通就避过不谈,恰恰相反,海德格尔刻意以如此有分量的篇幅将困难彰显出来,让人们随同他一起经历一次对物之物性的遮蔽的发现,即一种看似清晰且流行的思想,或许正是对事物真相的掩藏,而我们必须“防止这些思维方式的先入之见和无端滥用”⑦。海德格尔随即转换角度,展开透过器具之器具存在寻求通向物的道路的考察。而本文却并不打算沿着海德格尔的讨论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在其对物之物性道说的困难中,已经出现了对本文讨论最有启发的信息。 当海德格尔指出“毫不显眼的物顽强地躲避思想”时,他事实上已经在以一种非概念的方式为我们描画出物之本性。物或者物性恰恰意味着一种在其自身内部的封闭性,意味着它不可被化约,意味着其无可辩驳地“有”和不会以任何方式全然转化为“无”。无论在具体事物身上有多少令我们感到亲熟的东西,最终规定着物之物性的,恰恰不是这些亲熟,而是那些令人惊异和感到陌生的东西。既然物恰恰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思想的躲避,意味着某种自身带有封闭性的陌生者,我们的确不应当将之强行纳入我们自己的体系中,使之成为朝向我们完全敞开的、与我们亲密无间的东西。应当允许在我们的世界中依然葆有这样一极,它是完全异于我们的,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他者,即便我们能够与之发展最和谐的关系,它也依然在其本性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对于物和物性在一般性上、而非就其具体现实形态的规定,在海德格尔对“大地”的描述中更加清楚地展露出来。他自己也指出:“为了规定物之物性,无论是对特性之载体的考察,还是对在其统一性中的感性被给予物的多样性的考察,甚至那种对自为地被表象出来的、从器具因素中获知的质料—形式结构的考察,都是无济于事的。对于物之物因素的解释来说,一种正确而有分量的洞察必须直面物对大地的归属性。大地的本质就是它那无所迫促的承荷和自行锁闭,但大地仅仅是在耸然进入一个世界之际,在它与世界的对抗中,才自行揭示出来。”⑧大地在本质上意味着自行锁闭。海德格尔认为:“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乃是作品之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休戚相关,处于作品存在的统一体中。”⑨而艺术作品所谓的制造“大地”,恰在于“把作为自行锁闭者的大地带入敞开领域之中”⑩。亦即,正是大地带着其自身的闭锁和坚固突兀地展露在一个敞开的领域之中,大地让自己公布于众,不是以解开其自身闭锁的方式而成为公开的,而是将自己公开为某种闭锁,因为“唯有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退遁于任何展开状态,亦即保持永远的锁闭——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11)。 带着这样的理解,让我们返回对画之物性的考察,或许我们会看到一些过去忽略了的问题。通常而言,当人们谈论画的物性,不外乎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绘画不能够脱离其物质材料,譬如画布、颜料之类;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把绘画作品与其所表象的对象联系起来,认为画的“内容”是物,而画是物的表象,是对物的描述和揭示。即便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亦是如此。绘画唯被视为从一般性上谈论的艺术作品之际,才是那个建立世界和制造大地的东西。而在具体谈论中的梵高画作,却更被称作是“一双鞋子”,更由于其提供了对于某种器具的描画而被选中。可以看出,绘画本身,画之为画的存在,是并未进入海德格尔考虑之中的。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尽管现代绘画的变革正在蓬勃、丰富地开展着,而对他而言,作为作品的绘画更多地是在其过去性中,作为已经终结的艺术、作为摆放和辗转于博物馆之间的作品形态呈现着。对于画之为画的反省不是海德格尔本人会考察的问题,但却不妨碍在上述海德格尔对物与物性的理解中获得一种解释的可能。 二、画之为物 倘若我们能够不把绘画当作物的表象,而是把它看作同样在其自身之中有着某种坚固性的、自行锁闭的物,那么我们对于画之为画的本性的考察或许会有所突破。福柯对绘画的反省,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在20世纪60、70年代,福柯的写作表现出对绘画艺术特别的关注,譬如,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1968年发表、并与1973年作为单行本发表的《这不是一只烟斗》,以及在70年代所作的几次关于马奈绘画的演讲。对于作为哲学家的福柯而言,会在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一个较为成熟和关键的阶段,对绘画问题展开相对集中的研究和讨论,这表明绘画对他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闲谈之间牵涉到的话题,而是归属于其此阶段关于事物秩序考察脉络之中的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亦试图追寻福柯论画背后的哲学关怀,来看待他的“实物—画”概念及其在关于绘画的反思上所做出的贡献。 在谈论马奈绘画的演讲中,福柯认为:“马奈所做的(我认为,无论如何,这是马奈对西方绘画最重大的贡献和变革之一),就是在画中被表象的东西内部凸显油画的这些物质方面的属性、品质或局限,绘画、绘画传统可以说仍然以回避和掩盖这一切为己任”,“马奈重新发现(或许应当说发明)了‘实物—画’,即,作为物质性的画,被外光照亮的、有色彩的物的画,观者面对着或围绕着去看的画”(12)。他看来,在马奈绘画中出现了对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传统始终难以摆脱的对其自身特质的回避和隐藏的一种实质性的挑战。马奈的绘画似乎终于宣告了绘画对其自身的反省和揭示的开始,故而福柯特别痴迷于马奈绘画,并指出“‘实物—画’的发明,这种油画物质性在被表象物中的嵌入,正是马奈带给绘画变革最核心的价值所在”(13)。 借助福柯对马奈绘画的分析,我们也有机会能够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去了解福柯在此所提出的“实物—画”的概念。福柯借助马奈的十三幅作品,从几个方面勾画出马奈绘画所揭示的“实物—画”特质。在此,本文不可能细致地追随他对每一幅作品具体的画面分析,而仅仅希望从福柯所关注的问题、或者说他希望人们去关注的问题的角度入手,来看待这种“实物—画”。 (一)距离 古典绘画的杰作,往往巧妙地经营画布空间,以一种合理、严谨又和谐的方式,让画布变成一个有着无限景深的景观的入口。透视法的运用——视角(光源)的选择、距离的营造——乃是成就一幅古典油画之关键。而马奈绘画的突兀之处则恰恰在于对那片景深的封闭。福柯注意到,马奈总是利用某种大块面的东西或是黑暗和混乱的场景来封住人们的视线。譬如《杜伊勒利公园音乐会》中拥挤的场面和树林,《歌剧院化装舞会》中黑色礼服和礼帽组成的嘈杂纷乱的人群,更典型的譬如《马克西米利安的处决》中直接利用了一堵墙。事实上,借着福柯的眼睛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情形不仅仅出现在福柯所选取的几幅画作之中,翻看马奈的画册,这样的封闭几乎随处可见(譬如说福柯所未曾选取的《左拉像》)。对福柯而言,马奈的这种对于景深的刻意封闭,意在停止对距离的表象。原本可以安稳有序地排列在画布所经略的空间中的人物,此刻被驱赶到画面的最前部,拥挤在一起,似乎即将要被赶出画面来了。他们不再归属于我们现实生活的空间,不再好似投影一般被排列在画布上。画面上人物之间的比例和位置关系不再被自然而然地提供给观者的感官,而是似乎总是带着什么秘密,总是有待解释。同时,福柯特别在意马奈对纵横线的使用,在他看来,纵横线正象征着画布的纹理,它们不断地增强着画布的平面效果。这样一来,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奈的画面中似乎有一种平面的力量,由内里向外推动着,想要把一切人物和场景推出来,而只保留平面的画在其中。福柯认为马奈画作中所营造的距离是绘画自身的空间语言,而不再是可供感知的距离:“在此,我们进入一个绘画空间:距离不再为观看服务,景深不再是感知的对象,空间位置与人物的远离只是被一些符号所确定,这些符号只有在绘画中才具有意义和功能(就是说,这些人物的身材与那些人物的身材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纯象征意义的)。”(14) (二)不可见者 出现在马奈绘画中的这种起封闭作用的背景式的块面,在取缔了景深和感官距离表现的同时,也在塑造某种障碍,视看的障碍。古典绘画总是试图把自身变成一片景观,这片景观不仅仅是我们透过画框看出去的景象,而且还要利用一切合理而可能的手段,譬如镜子,譬如窗户,尽可能地去表现那些在其所选取的视角下原本看不到的事物的面向。因为一种多面向的展示,似乎才能够掩盖绘画之为平面的缺陷。然而马奈却恰恰运用各种起阻隔作用的图像封闭了这一切。没有窗的墙壁,嘈杂拥堵、不留缝隙的事物,栅栏,即便栅栏可以从缝隙望过去的部分也会用人的身体、甚至一团雾气(在《铁路》中)遮挡起来。这样一种阻隔意在道出一个事实,即,这只是一幅画,而不是景象或现实自身。在画框所限定的平面里,在画布和颜料的质地的限度中,能够展示的只是这么多。空间的无限延伸不再归属于绘画本身。绘画的任务不在于尽可能地将一切皆纳入眼中。对福柯而言,马奈的绘画恰恰在向我们展示一种不可见性。即原本我们希望能够突破画框的表面望进去看到的景象,此刻被各种障碍遮挡了起来。马奈让我们只能去看那些他想要我们在画布表面上看到的东西,而不再满足我们目光无度地要求画画布后面或被设想为在画布深处应该有的东西。如福柯所言:“马奈正是在画中发挥用油画面积本身提供的不可见性的游戏。……这是绘画第一次向我们展示某种不可见物:目光在此是要向我们表明,有某种应该看到的东西,从定义,甚至从绘画的本质、油画的本质上讲,这种东西必然是不可见的。”(15) (三)光照 从关于马奈绘画对感知距离的取消的讨论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一种感知传统原则解体、重构的进程之中。在这样一个进程中,我们不难体会到,绘画的大厦原来构建得如此精致和严格,一个基本原则的松动必然导致全体的崩溃。马奈画作《吹笛的少年》似乎毫无遮掩地向我们展示着这一切。按照之前的方式,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封闭的布景,没有空间,没有距离,只在画面下方有一道并不清晰的交际线,似乎让人松一口气,这少年凭借着这道线以及短短的影子,还有几分像是站在地面上的样子。对福柯而言,这幅画向我们提示的,是“被照亮的方式”。马奈完全放弃了人们熟悉的各种可能的光照系统。在画面内部没有任何关于光源的暗示。没有光,没有让光得以投射或散发出来的任何符号,更加没有光照的原则和系统可循。只有少年脚下的一点点影子提示着人们,光来自少年的正对面。 继而在《草地上的午餐》中,我们再次看到这样一种来自正面的光照。所不同的是,在这幅画中更加复杂地体现了两种光照的方式。画面后方传统的来自画内的光照和前方被正面光照亮的赤裸的女人。两种光照的交汇在同一画面中,造成强烈的冲突和不协调。 正面的光照给人造成某种不安。因为这样一种光照的来源恰恰与我们观看的位置重合。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好比一幅本在黑暗之中的画突然被观者的目光照亮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奥林匹亚》在展出时遇到如此大的争议。人们勉强可以接受《吹笛的少年》,《草地上的午餐》由于毕竟在画面中,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从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空间和光照手法在其中,也还没有到令人无法直视的地步,而《奥林匹亚》让观者如此切近和直接地去注视一个赤裸的女人的身体(并且在此形象上还重叠交织着各种复杂的刻意安排),这便把绘画的问题从感知原则的冲突上升为某种道德情感上的挑战了。本文并不希望由此卷入关于这几幅画作复杂的讨论中去,却也希望从表面上借这一现象表明,光照系统的转变对于绘画而言可以是多么强烈的变革。来自画作外部的正面光照,不但完全改变了画面中光照的语言,而且由于与观者目光的尴尬重叠,也将观者卷入画中,改变了人们对观画活动的理解。 (四)观看 随着传统绘画空间语言的解体,马奈的绘画也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逻各斯。《弗利—贝尔杰酒吧》这幅画就体现着这种成熟和充满复杂性的空间语言。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那些已经熟悉的表现方式。由整面镜子取代了墙放置在背景的位置,依然禁止目光向深处发掘。而镜子的使用也是如此之吊诡,它不遵循常规向人们展示事物的背面,而是在制造迷局。如果我们要存心陷入这一迷局,就会纠结于这幅画的光源和观看者的位置——究竟是由我们自己的位置出发,从正面出发(因而无从解释女招待在镜中的影像位置),还是从画面右侧那个顾客的位置出发(因而镜中不应该有顾客本人的侧影,画中大部分形象的角度也应当随之调整)。感知距离的封闭、来自画外的正面的光照以及对不可见性的直接体现,最终走向了对观看的颠覆。人们无法确定一个画家借以完成画作的视角,也无法确定一个观者观看的视角,甚至,在具体而细致的检视之下,人们不得不承认,也许应当接受这幅画并不是固定站在一个位置上看到的景象,即使人们在画前走来走去,也不可能确立一个最佳的观看位置。传统的空间秩序实际地消散了。在福柯看来,马奈“使用了绘画的基本物质元素,他正在发明一种……实物—画或画—实物(peinture-objet),而这正是人们最终可以摆脱表象本身,用油画纯粹的特性以及其本身的物质特性,发挥空间作用的基本条件”(16)。 人们完全有理由对“实物—画”的概念不以为然。这一概念仅仅出现在福柯关于马奈的演讲中,而且目前我们看到的根据录音和笔记所整理的演讲稿,从文献的角度看也不是理想的形态。然而这一概念的出现毕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绘画的新视角,即,画是作为物存在的。画之为物不仅在于在它身上凝聚着具体的物质特性,譬如画布、油料的质地或画框的形状,亦不仅在其所表象的事物。画不是飘浮在其物质材料或表象的上空,并非在这些材料和所表现的内容之上,才有一个层次被称作是“画”。而根本是画本身裹挟着这一切,有血有肉地带着其真实的质地和纹理现身。画之为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凸显出画的物性特征,更在于其对于这些物性特征和事物表象的吸收,画由于让这些东西成为自身之中的成分,而非外在地与物发生联系,而真正成为一种坚实的物,成为“作为实物的画”或“作为画的实物”。 三、目光的追问 “实物—画”的概念或许会引起人们另一种疑问:是否只有对马奈而言才存在着“实物—画”?这一概念是否也可以很好地用于表述其他的绘画? 显然马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在现有的画史研究中,人们往往把马奈与现代城市生活结合起来,把马奈作为某种现代性的表征来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在马奈的绘画生涯与其绘画所展示的现代巴黎生活场景之间建立起一些外在的联系,譬如透过铁路、城市场景等意象讨论现代人眼中的世界形象等等。反倒是福柯对马奈的分析采取了一种内在于画史的视角,完全从马奈绘画对绘画传统的变革的角度揭示出一种在绘画内部完成的对绘画的反思。在此意义上,福柯虽选取了马奈绘画作为研究主题,却避开了从具体现代生活器具和场景切入马奈的路径,而选择纯粹从绘画的基本要素(基本语言)出发去理解马奈的方式。在这样一种纯粹由对绘画的内在反省而来的研究中,一种作为一般性的物的特质反而更加凸显出来。为了考察这种更在一般性意义上起作用的“实物—画”概念,我们需要离开马奈,而透过其他绘画来检验。幸运的是,福柯刚好为我们提供了对马奈之前和之后的不同画家作品的解释。 最著名的例子显然来自于《词与物》中对维拉斯凯兹名作《宫娥》的解读。《词与物》的出版(1966年)是早于马奈讲座的,所以现在我们是在由后来的观念出发追溯一种较早的见解。然而倘若比照关于马奈的讲座,我们很容易在对《宫娥》的分析中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结构。 (一)遮蔽 再一次地,我们以一种追溯的方式看到了许多大块面的阻隔出现在一幅绘画作品中。画面前部左侧的画板,画面后方的墙壁,壁上的画框,以及镜子。这种遮蔽对福柯而言颇具深意。他认为:“在这幅画中,表象在每时每刻都被表象了:画家、调色板、背着我们的画布的巨大的深色表面、悬挂在墙上的画、观察着的观众以及那些环绕并观察着他们的人;最后,在中间,在表象的中心,接近重要的东西,是一面镜子,它向我们显示什么被表象了,但是作为反映,这面镜子是如此远、如此深埋在一个不真实的空间中,对指向别处的所有目光来说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它仅仅是表象的最微弱的复制。画中所有的内部线条,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央反映的线条,都指向那个被表象但不在场的东西。”(17)在此,福柯把这些出现在画面中的大块面的表现视为各种表象的化身。正在创作中的图画,用以悬挂图画的墙壁、画框,以及代表着一种特殊表象方式的东西——镜子。这些代表着各种表象的东西皆以一种被遮蔽的方式出现在这幅作品中——画板只显露出背面,画框中的画处在黑暗中,而镜子也没有以反照的形式展现我们设想它应该展现的景象,而是“不真实地”反映出国王与王后的形象。表象的功能在此显得如此的微弱,甚至可以说是虚幻的、近乎无效的。它们现身于画作之中,但却并未成为作品引人注目的核心,而是因着这种微弱和无效自动呈现为某种背景。 (二)光照 画作之中仍然存在着几处开口(在对马奈画作的分析中同样存在着关于开口的讨论)。右侧的窗户为画作设定了一个内部的自然光源,而正对面敞开的门又造成了另外一束意外的光,此外便是后面墙壁上画框所反射的一道莫名的光亮。并非来自同一光源的光线系统,为图画营造出一种奇特的光线的交织。福柯格外重视这种横向和纵向贯穿着画面的射线,因为射线的两端刚好指向画中画家试图表象而却又没有出场的东西。 (三)目光 在福柯看来,这幅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那面镜子以及镜中现身的国王菲利普四世及其妻子。在他看来:“在这个中心,恰好重叠有三种目光:当模特被描摹时,是模特的目光,当目击者注视着这幅画时,是目击者的目光,当画家构作他的图画时,是画家的目光。”(18)三种目光在画作中表现为对于其所缺乏的东西的恢复。即,画家目光中的模特——应当出现而不可能出现在画面中的、在画家前方、亦即观者目前所处的位置的盛装的菲利普四世及其妻子;国王目光中的自己的肖像——原本应当在国王所看不到的、画家正在创作的画板的另一面;以及目击者目光中的景象——原本应当刚好与我们目光中的景象相反,是不能够呈现在同一幅画面之中的。如今,三种目光中原本不能直接呈现在同一画面上的景象,在这面镜子中重合了。于是在这幅画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表象的苍白,另一方面则是各种目光的交织所激活的新的空间秩序。 或许福柯为这幅画赋予了太过现代的解释。对他而言,在这幅画中,“似乎存在着对古典表象的表象,以及古典表象对其所敞开的空间的限定”,并且,“在由表象既汇集又加以散播的这种弥散性中,存在着一个从四面八方都急切地得到指明的基本的虚空:表象的基础必定消失了,与表象相似的那个人消失了,认为表象只是一种相似性的人也消失了……因最终从束缚自己的那种关系中解放出来,表象就能作为纯表象出现”(19)。即对福柯而言,这幅创作于17世纪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宣示着古典秩序(其语汇、其表象基础及其空间系统)的消解,与一种新秩序的构建。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把这种用17世纪的作品支持20世纪哲学家的学说看作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并以艺术史的文献考察说明了这种危险(20)。然而对他而言,福柯的这种冒险,或者以他的话说,福柯所犯的这种“错时论的错误”,却意味着一种悖论——“这个错误可能是迷人的、灿烂的、有趣的,同时也是主观的、危险的”,“哲学家搞错了,却错得不无道理”(21)。由文献方面考察而来的艺术史的事实,并不会取消福柯对于画作的分析。镜中国王与王后画像无论承载着怎样的社会意义,其在画面中的独特位置、其所揭示的不可见性和目光的交织、由其所开敞的奇特的空间秩序,都依然意味着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悖论”,恰恰因为福柯不是在绘画之外解释绘画,他的解释不依赖于作品与其环境的外部联系,而是在作品内部、在绘画之为绘画的自身的各种语汇与原则中考察其运作的机制。无论《宫娥》这幅画有着怎样的社会历史意义,对福柯而言,它都以另外一种形式呈现着,即纯粹作为绘画,仅在观者注视的目光中展示出其自身内部的各种关系和秩序。在这幅仅为目光存在的作品中,不是我们习得的各种物理的、几何的或感知的空间秩序在引领着我们的视线,而是作为目击者的我们被它捕获,被作品中画家的目光所捕获,被安放在画家所指定的位置上,从此参与他所要构造的位置关系和空间秩序。 尽管在写作《词与物》时,福柯还没有使用“实物—画”这样的概念,我们却可以比照其关于《宫娥》和马奈绘画的研究,看到一种致力于仅将绘画理解为绘画自身、寻求绘画之为绘画的内在机制的努力。或许对福柯而言,纯然在其内在的传统中延续着、而不被视作任何其他东西(话语、表象、思想)之附庸的绘画,有可能成为一种值得考察的文献档案,可以以一种与话语、知识或经济结构等并列的形态为我们展现世界秩序的缔造。另一方面,“实物—画”的概念,虽然对于福柯的研究而言,更加指向一种古典语言的结束和现代秩序的构建,但对于我们理解绘画本身——不是将绘画视为艺术的某一个具体门类或分支,亦非任何附属于其他传统的东西,而是将绘画自身看作一个古老的传统——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它使得人们终于看到在绘画被赋予的各种似乎应当如此的身份和功能之下,还有着绘画自身的封闭性和坚固性,有着绘画之为绘画的内在的原理和力量。绘画从根本上说亦是一种物。作为物存在着的绘画,不会仅仅是可无限度复制的图片或仅具有图像指示的意义,它没有也不会被其他科学技术取代,没有也不会被思想吞噬,它自有其存在的根基及运行和持续运行的机制。 注释: ①Michel Foucault.La peinture de Manet.suivi de Michel Foucault.un regard.ed.Maryvonne Saison.Paris:Seuil.2004.p.22.中译参见福柯《马奈的绘画:米歇尔·福柯,一种目光》,谢强、马月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译文有所改动。 ②Martin 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in Julian Young and Kenneth Haynes(eds.).Off the Beaten Trac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1.中译参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编译《依于本源而居——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依于本源而居——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第22页,第23页,第23页,第23页,第22页,第49页,第34页,第34页,第34页。 (12)Michel Foucault.La peinture de Manet.suivi de Michel Foucault.un regard.p.23.24.中译参见福柯《马奈的绘画:米歇尔·福柯,一种目光》,第15、16页。本文的“tableau-objet”概念,意在说明画自身即作为“物”存在,笔者倾向于译作“画之为物”,但过于拗口,故参考中译本作“实物—画”。 (13)(14)(15)(16)(17)Michel Foucault.La peinture de Manet.suivi de Michel Foucault.un regard.p.23.24.p.29.p.35.p.47.p.319.中译参见福柯《马奈的绘画:米歇尔·福柯,一种目光》,第15、16页,第21—22页,第28页,第43页,第401页。 (18)(19)Michel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Paris:Gallimard.1966.p.30.p.31. (20)阿拉斯指出:“有件福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在最近一次修复《宫娥》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宫娥》其实是两幅画叠加而成的。透过X光分析我们看到,第一版的画面中并没有正在作画的画家,有的只是镜子、大红窗帘,还有一个青年男子正在把一根似乎是指挥棒的东西交给小公主,而这时小公主正处于画面的正中心。很明显,这是一幅‘王朝接替画’。画中有小公主,她是王位的继承人;画面深处有一面镜子,映射出国王与王后的形象,他们是王室谱系中的奠基人。这种构图非常聪明地反映了王朝接替画的原则。不过,几年后,另一个继承人出生了,他就是普洛斯佩罗,这样,王位自然就转向了这个男继承人,而不再属于女继承人。前一版的王朝接替画失去了价值。这时,维拉斯凯兹在国王的要求下,修改了左侧画面(从我们的方向看的左侧),去掉递交指挥棒的小男孩,添上了自己的形象——画家似乎正在画位于画面景深处的国王与王后。”(阿拉斯:《绘画史事》,孙凯译,董强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同时,阿拉斯也指出,从文献和艺术史的角度说,国王与王后同时出现在一幅画中的肖像画也无迹可考。亦即是说,事实上从艺术史的角度对这幅画的解释,由于其空间语言和形制上的奇特性,反而可能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21)阿拉斯:《绘画史事》,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