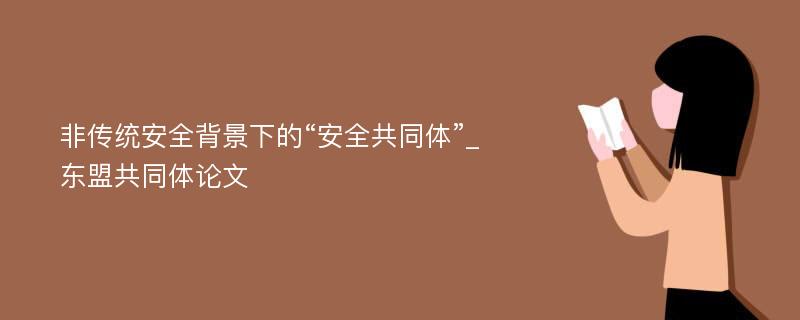
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安全共同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共同体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03-0054-08
当下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探索中,建立在合作和共同认同基础上的安全共同体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安全共同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怎样的影响、能否突破传统安全观下的安全共同体无法摆脱安全困境的局限并成为非传统安全维护乃至创建和谐世界的有效途径等等都引发了关于共同体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做尝试性的探讨。
一 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
(一)共同体
共同体(community)一词内涵宽泛,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指国家和民族,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①但无论种类、规模和层次,这些共同体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在不安全的世界里寻求安全感。”②
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方式,提供安全保护是它的基本功能。通过它,人们寻求安全感,获得安全保护,谋求自身发展,即共同体是人们生存的庇护所、发展手段和安全感的慰藉所在。这里的安全是广义的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观相契合,即强调以人为基点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而不仅仅指传统安全观下以国家为基点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具有过共同体生活的天然倾向。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本能地要过共同体的生活,通过两性结合组建成家庭,由家庭组成村落,再由村落组成城邦(国家)。人参加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对至善生活的追求。③霍布斯从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贪欲和对死亡的恐惧分析指出,人必须选择有公共权力的共同体生活才能避免人与人之间像狼的自然状态,得到生存和发展的安全保障。④梁启超先生也认为人注定要过共同体的生活,而且共同体的层级有着进化的趋势,从小团体到大团体,从氏族部落到国家,再从国家到国家之上的国家联合体。因此,他对刚诞生的国联坚持当时国人无法理解的欢迎和乐观态度。⑤
在德国古典社会学那里,共同体是由个人之间的共同忠诚、价值和血缘联系在一起的有机统一体,“共同情感、经历和身份纽带”是其建立的基础。在本质上,共同体寄托着人们对安全、温暖和情感的追求,由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彼此关系非常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这种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共同的保护和捍卫,占有和享受共同的财产、朋友,保护和捍卫免受敌人和祸害的侵扰。⑥用鲍曼的话来形容就是“‘共同体’一词传递的感觉总是很美妙的,它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⑦这表明共同体不仅意味着群体成员间的身份认同,还意味着成员间必须彼此承担责任,即在共同体内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认同,而共同利益和共同认同的基本指向就是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共同体在本质上都是安全共同体。
在人类发展史上,共同体呈现出一个层级递进和不断扩展的历史轨迹:从血缘共同体到地缘共同体再到精神共同体,表现为人类组织化生存方式从小到大、由低到高的演进过程。以国家为界,在国家内部呈现为:家庭—村落—部落—国家,在国家之上呈现为:国家—国家联合体(地区—国际—全球)。它既可以是“一种有机的、前现代的小规模社会联系纽带,尤其表现为小团体与部落”,⑧是前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可以是高于社会的组织发展形式,比如,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谱系里,国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顺序,国际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高级阶段。⑨而本文探讨的安全共同体则是国际共同体的一种,它是普遍意义上共同体的一个缩影。
(二)安全共同体
国际政治学中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概念最早由理查德·瓦根伦提出。⑩长久以来,安全等于国家安全,而安全共同体则是指国家之间以军事安全为目标的国家联合体,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是其基本的着眼点。对安全共同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20世纪50~70代卡尔·多伊奇等学者以科学行为主义为方法的研究以及90年代以来阿德勒等建构主义者的研究。(11)
多伊奇认为,“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integration)’的集团,集团内的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以武力相害,而是以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12)在《政治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区域》一书中,多伊奇指出安全共同体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主要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共同的反应性,而建立共同的沟通与交流是实现安全共同体的可靠路径。多伊奇等人倡导的安全共同体是建立在国家避免战争这一最根本的、一致的和长期利益汇合点基础上的。成员间的“非战争性”是它的本质特性,换句话说,维护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是多伊奇安全共同体建立的主要动力和根本目的。
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在冷战后才得到更多重视。建构主义者阿德勒和巴尼特重新定义了“安全共同体”,认为它是指“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在该地区内的人们对和平变革有着可靠的预期”,它具有三个特征:成员拥有共享的认同、价值观和意图;成员拥有多方面直接的联系和互动;该共同体展现出一种在面对面接触中产生的、通过某种程度的长期利益和利他主义表现出来的互惠性。(13)在他们看来,增强认同和消除军事冲突仍是安全共同体建立的根本途径和重要目标,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仍是主权国家采取合作和妥协的根本考虑要素。比多伊奇更进一步的是,他们强调对于共同威胁的认知激发了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渴望,从而通过对观念和认同的侧重以建构主义的角度丰富了多伊奇的“我们感”。
巴里·布赞提出的安全复合体(security complex)是对冷战后安全内涵的扩展与安全维护层次上多样性的理论回应。它被定义为“一组国家,它们的主要安全认知和利害关系是被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它们的国家安全难题除非彼此远离,否则是不能被理性地分析或解决的”。(14)安全共同体由于积极交往和共同认同而排除了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而在没有形成安全共同体的安全复合体中,虽然也有紧密的安全互动,但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竞争和敌对。(15)
东盟安全问题专家阿米塔夫·阿查亚沿用建构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观念是将国际关系看做是一个交易、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化驱使下进行社会学习和形成认同的过程”。(16)他的贡献在于突破了早期安全共同体理论只被应用于西方发达地区的局限,认为东盟所走的是一条与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实现途径截然不同的道路,东盟的区域合作是在功能性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高度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的,东盟共同体首先来自于观念,而不是政治、战略和功能性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即“东盟方式”突破了传统安全共同体较为严谨的一体化要求,并提供了一种如何理解和分析国际关系中和平变革的理论视角。
从多伊奇到阿德勒和巴尼特再到布赞、阿查亚,我们注意到安全共同体研究的坚持和变化。一以贯之并不断得到深化的是关于安全共同体本质的认识,其中建构主义对此产生了重大影响。(17)我们可以就安全共同体研究历程做这样的归纳: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共同认同,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共同命运感等而形成的共同认同(外在压力)。第二,成员角色身份认同和学习,呈现出友善的成员间关系和价值观的趋同走势(内化动力)。第三,共同体内长期、稳定的合作行动和机制(共同行动)。这三方面在顺向上存在着因果关系,在逆向上也存在增进和互构的因素。也即在最初外在压力下的共同认知促使成员个体的身份认同和学习并形成物质化的合作机制和行动,而长期的行动和稳定的机制则会强化成员共同体内生活的责任和习惯,在观念上进一步积累着共同认知。
变化的部分是更为显著的:安全共同体在性质上从功用型的物质存在向更强调“我们”情感的观念性存在提升;在范围上从北约扩展到西方其他区域再扩展到西方以外的区域;在安全目标和内容上从单纯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扩展到经济贸易等其他领域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变革,等等。导致这些变化与不变的根本原因则是安全概念本身,也就是说,安全共同体的内涵、性质和功用随着安全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悄然发生着改变,探讨的语境正逐步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过渡。
二 语境的转换: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
(一)“威胁论”下的安全共同体
共同体或安全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维护安全的重要途径,其根本目标在于保障安全、保持发展,但不同安全语境下的安全共同体显然有着不同的使命和功能。
“安全”是个不清晰的概念,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最早使用了“国家安全”的提法。(18)从此,安全概念就等同于国家安全。这个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观就是我们说的传统安全,它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价值目标是领土安全与主权安全,权力、军事、武力、战争是安全的核心体现,保障的是免于由战争造成威胁的自由。在传统安全语境下,“安全研究的主要焦点是战争现象”,(19)面对的始终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安全共同体是避免战争、维护主权领土安全的重要途径,它的建构是通过成员间军事上的互信和集体认同来实现的,所追求和实现的安全也只能是内部的安全、局部的安全,体现了一段时期(如冷战)某些区域、国家(如东西方、美苏)突出的安全维护需求,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消弭或缓解安全困境,甚至还会加剧这种趋势,例如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的对峙。
这种安全共同体的基本属性是非战的或和平的,其安全主体是国家、国家联盟,换句话说就是部分人、部分地区的安全,形成的是“战争-和平-不可持续安全-新的战争”的循环式安全维护路径。(20)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国家和所形成的安全共同体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就必须通过不断地发展军事实力,力图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基础上达到一种对峙性和暂时性的和平与安全,或者是主动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取和平与安全。由此带来的是更加的不安全感,各国及其安全共同体被迫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军备竞赛,世界陷入“安全困境”而无法自拔。因为这种安全共同体是“威胁论”安全观的现实体现,即一定要划定我、你、他明确的安全界线,进而制定出相应的对抗性策略,扩充军备以防最坏可能等,这恰恰限制了安全在本质上实现的最大可能性。“威胁论”的安全观和北约安全共同体反映了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危态对抗(dangerous confrontation)”式的安全思维。
一个真正的安全共同体不仅仅是非战的或和平的,传统安全下的安全共同体带来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与和平,而是更大规模的敌对和不安全。按照共同体的本意,安全共同体应当拥有生存与发展基本内涵的多种安全诉求,而当下能源、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大量凸显对安全维护的重要方式——安全共同体——提出了重新认识的现实要求。
(二)“和合论”下的安全共同体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大量的非传统问题开始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诸如核扩散、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传染性疾病、移民难民、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电脑黑客、种族部族冲突,等等。其中有些问题由来已久,只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带来普遍威胁,且往往与传统安全相缠绕并附属于后者。但是一旦经由安全化的过程而上升为安全问题,就需要以更宽泛的安全视野来应对,不仅“各个领域都是一种多样的、不同价值的安全话语领域”,而且“各个领域都有它自己的行为主体、指涉对象、动力和矛盾,需要以它们自己的术语加以理解”。
与传统安全的“威胁论”相比,非传统安全观具有“和合论”色彩。“和合论”来自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主张和“天下大同”的普世主义人道理想,前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化而为一,后者强调人与世界的合而相同。以“和合论”观之,安全的实质就是“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优态”是安全指向的对象,表征的是行为体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境况,把“优态”作为对象的安全置于发展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前提上,不仅表明国际关系理论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开始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思考,而且标示出安全所要达到的更深远的价值目标是“发展与安全”。“共存(co-existence)”是安全获得的条件,表征的是行为体追求安全历史性条件,在全球体系中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达到“共优共存”,这就需要国际关系任何一个层次中的“自者”与“他者”间的共同努力。(21)以“威胁不存在”来界定安全与否,其安全的可能性边界永远划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其安全也只能是相对的安全。而以“优态共存”来界定安全,其安全的可能性边界就拓展到了安全建设的双方甚至是多方,其安全就有了某种绝对的意义,恰如巴里·布赞所说:“理想的世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功地确保安全的世界,而是不再需要去谈论安全的世界。”(22)
非传统安全语境中安全研究的主要焦点是“非战争”现象,或者说面对的是“非军事武力”的“和谐与发展”的安全问题,关注的价值核心在于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作为安全维护的重要途径,安全共同体在维护目标、内容和手段上具有更宽泛复杂的内涵。在维护目标和范围上,它超越了传统安全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目标的维护向度,以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和平与良性发展作为安全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寻求的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地区安全、部分人的安全,而是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全人类的安全,它着眼于基本的生存与发展,关心的是小到每一个个人、大到全球整体的命运走向,追求的是世界社会的和平与和谐。在维护内容和主体上,超越了以往单纯的非战目标与军事结盟和对抗的方式,扩大到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在存在形式上扩大到小到个人团体大到全球共同体的各个层面不同的组织形态,形成“发展—和谐—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上升式安全维护模式。(23)在维护手段上,传统安全下的安全共同体主要采取自助、威慑、结盟、集体安全等方式,呈现出独立性、排他性的特点;而非传统安全下的安全共同体,更多地采取多层次的他助、共助、对话、沟通、合作等方式,呈现出关联性、依赖性、渗透性的特点。
安全语境的转换引发我们关于共同体问题的两方面思考:
一是在理论上,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安全共同体是一种朝着广义安全的回归。它打破了传统安全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目标的程式,它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指向是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即回归到共同体广义的安全维护意义里去。就此而言,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安全共同体是从国际政治学意义下的安全共同体向政治学、社会学原初意义上的回归。这种回归并不是一种简单还原,不是回到“有机的、小规模的、前现代的”的组织化生活模式,而是以国家为中心,向国家之下寻求以个人为本的各层级的共同体模式,向国家之上寻求各层次的安全共同体,最大的则是以类为核心的全球安全共同体。追求“世界大同”、“世界国家”的理想以及“国家之后”的探讨起起落落,但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伴随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就这一问题的重新思索,甚至有人认为“全球共同体正在解决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关切方面迅速生成”,(24)这个过程本身体现了人类在共同体问题认识和实践上的尝试与更新。共同体生活是我们必须要过的生活,共同体是我们永远无法割舍的物质和心灵之乡。而当安全从传统安全狭义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向外流溢到广义的生存安全、发展安全,安全共同体则从单纯的军事安全共同体向宽泛的文化安全共同体、环境安全共同体、经济安全共同体等扩展开去,特别是恐怖活动泛滥、流行疾病传播、生态条件恶化、经济危机爆发等公共威胁的加剧使得全球正在变成一个风险社会,共同的风险和威胁则促使全球变成一个安全共同体,它是人类生存的安全寄托。正像鲍曼所表达的那样:共同体总是过去的事情或总是将来的事情,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找到的天堂。(25)
二是在实践上,中国“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的提出是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积极回应,为当下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一条有益思路。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传统文化中共有、共生理想的弘扬,就开创安全新思维、拓展安全新内涵所做的积极尝试,同时也说明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全球面临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前的一种责任担当。
1997年,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其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认为安全内容是多维的,国家安全应坚持平等原则,主张建立共同合作安全模式,以对话、谈判取代对抗和冲突,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联盟集团安全,才能摆脱安全困境,实现世界的稳定与和谐。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他延续了新安全观的主旨,指出:“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26)以“和合论”为价值核心的新安全观反对强权政治下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希望改变冷战以来一直延续的以军事对抗为重点的安全共同体的陈旧方式,而应当创建“和合共建”的安全共同体模式,不设定和寻找国家及安全共同体的“假想敌”,以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全球安全为精神指导,重视灵活多样合作途径的建构、多重合作领域的开拓、多方面合作对象的建立以及多层次合作机制的创造,从而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中国近十年来对联合国在推进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强调,在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与地区组织中的积极参与和建构,在南沙海域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案,北京奥运会所彰显的“我和你、同住地球村、天下一家”的思想理念以及主办亚欧会议倡导“亚欧携手、合作共赢”,以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态度立场等都是“和合论”安全观关于“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27)的具体践行。
三 建构新型安全共同体:可能与类型
(一)建构新型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
安全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共同认同,如果说外在压力和内化动力所形成的共同认同是观念上、价值上的构成因素,那么持久稳定的共同行动和行动机制则是构成安全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峻的当下,这三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使新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不仅具有现实可能性而且也是必需的。
首先,非传统安全威胁把生存与否的严酷挑战摆到全人类面前。整个地球变成一个蓝色救生艇,其上的人们也就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地区和人群可以幸免,只是存在面对的问题种类不同或威胁程度的差异(例如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等),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是唯一现实的、理性的选择。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其应对使人类的“我们感”(共同认同)前所未有地高涨,极大地推进了相互依存的加深、共同合作的可能以及自我约束的确立,“人类的共同体意识正在非传统安全努力中空前觉醒”。(28)可以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是一种逼迫,逼迫人类对自身的反思和类意识的觉醒。这种逼迫成为新语境下安全共同体生成的外在压力和条件,反之,建构内容更宽泛、层次多样的安全共同体也是人类社会摆脱安全困境、应对各种非传统威胁、追求“优态共存”式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
其次,各国在共同命运下的身份认知与行动选择上的自我内化和集体趋同。在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命运与共的政治共同体——民族自决的集体——的观念再也不能有意识地仅仅定位于单一的民族国家。某些决定生活机会性质的最为根本的力量和进展——从世界贸易到全球变暖——现在已经不是单个民族国家仅凭它们本身的力量就能解决的,21世纪初期的政治世界是以一系列新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外在性或‘边界问题’为特征的”。(29)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具有全球性,且多发在人类公共领域,因此非传统安全的维护必须要更多地站在全球立场从公益角度出发,而“从全球的角度思考和行动是政府的自然能力所不及的,确切地讲,原因在于民族国家是受到疆域限制的。超越国界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比如企业或者市民社会组织,有时会具有一个更为真实的全球性视角,譬如在环境问题上”。(30)这使得“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一方面,民族国家已经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另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共同体”。(31)介于对共同命运的群体认知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不足的自我认知,国家都不得不采取互助合作的姿态和行动,寻求国家之外的安全共同体来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另外,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多涉及公共利益,一国单独处理和参与共同应对都能使他国受益并因此得到相应的回报,于是多领域、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就会使国家学习并习惯创造“利他”文化,并不断内化,加强共同认同。对此,阿查亚指出,共同认同可以导致更深的相互依存,发展“我们感觉(we feeling)”,使国家最终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而“国际关系可以重新概念化为政治共同体的世界社会,其中包括社会群体、政治交流的过程、强制的方法以及屈从于最为大众化的习惯”。(32)
最后,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各层面的安全合作普遍展开。因共同威胁而生的共同命运感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从共同认同到共同行动和共同行动机制的建立更需要一个过程。加之非传统安全问题多发生在公共领域,常会出现可以共享却难以共同负责和维护的尴尬局面,在现实中共同行动和共同行动机制的建立成本较大、推进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观地看到,在气候、能源、水资源、粮食、反恐、疾病等各领域的安全合作与制度建设在不同的层次努力进行着,并有进一步扩大加深的趋势,例如联合国主导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反恐、东盟2020年建成“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目标、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水资源、减贫等多方面的合作等。全球性合作有其客观的困难:成员过多、关系复杂、谈判成本较高等,往往难以有高效的合作行动,全球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有些可望而不可即。比较而言,目前地区范围的安全共同体是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地区性合作既使国家摆脱了孤军奋战的窘境,又使国家数量相对稳定适中,因而在共同威胁、共同命运的驱动下,集体认同比较容易形成,合作也更有成效”。(33)
(二)新型安全共同体的多种类型
在近期建构一个全球安全共同体显然过于乐观,但是非传统安全的行为主体大大扩展,形成多元化的态势却是客观现实。我们把非传统安全的主体划分为五个层次,即个人、地区(包括国内)、国家、国际、全球。相应的,在非传统安全维护主体上就形成了除国家之外的各层次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地球就是最大的人类安全共同体。具体而言,除国家之外,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安全共同体及其安全维护范围是:个人和全球层次上的全球治理,其主要代表是(国内、国际)非政府组织;地区和国际层次上的国际治理,其代表是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我们可以将维护非传统安全的多层次非国家行为体(除了地区安全共同体之外)也都称为安全共同体。比如,我们可以说欧盟、北约、东盟是安全共同体,它们担负着维护成员国政治、经济、军事、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安全责任,我们也可以说绿色和平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也是安全共同体,对环境、生态保护、人权保护、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这样有将安全共同体泛化之嫌,并与一般国际组织混淆在一起,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安全维护现状。因为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下,非军事的安全共同体占据主导地位,一个“完全的安全共同体”应该是“军事和非军事安全共同体”,而后者正是安全共同体演化的方向。(34)而且从具体问题领域看,如以生态安全为例,像绿色和平组织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也完全符合新语境下安全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并满足了安全共同体建构的观念和物质条件:“我们感”(共同认知)和稳固的实践平台(共同行动和行动机制)。
我们可以尝试着把目前安全共同体的演化及方向做一个简单分类:
第一类,仍以传统安全为主要关注内容的安全共同体。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或后者取代前者,而是相互交织,体现了安全概念和现实的动态发展。因此重视非传统安全并不是无视传统安全,这类安全合作还将持续存在。例如当前的北约、美加安全共同体、美以安全共同体、南美洲安全共同体、瑞典—挪威安全共同体等。
第二类,综合类的国际组织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安全责任,向安全共同体过渡。像联合国、欧盟、东盟等一些全球性、区域性综合性组织,以往侧重的是高级政治问题,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更多地关注环境、能源、移民、贫困等低级政治问题,成为全球和地区层面重要的安全共同体。
第三类,新兴的专门致力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安全共同体,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机制、朝核六方会谈机制等。它们往往因为某种非传统安全问题而生,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同时又是地区内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容易达成共识与合作,具备高效能的基础。预计这类组织还会进一步增多,它们将是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力量。
第四类,专注于某一问题领域的各种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往往擅长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当该领域经由安全化而演变为安全问题时,从事该领域维护的非政府组织也应当被视为安全共同体,在裁军、环保、人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是一支不可小视的非传统安全维护生力军。例如,在环境安全问题上做出杰出贡献的绿色和平组织、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国际禁雷组织等。
这种分类虽然不尽科学,却反映了当下安全共同体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态势,并还会有更多不同类型的模式出现,而最终的指向当是全球安全共同体。
四 结语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主权国家体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主导方式,国家是最重要、最显然的共同体,而国家安全也就成为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维护的最重要或唯一的安全目标。非传统安全的凸显则将这个程式打破,传统安全的目标、手段、方式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安全共同体的意义和范围从国家之下的每个个人到国家之上的全球得到全面的延伸,大大突破了以国家为轴心的安全共同体的视野,超越了传统安全观下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和政治安全为目标的安全共同体,具有更为复杂宽泛的新内涵,凸显的是生存安全、发展安全,关注的是人的安全、全球安全。因此,笔者认为,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安全共同体是向政治学、社会学原初意义上的共同体的一次回归,体现了人类在共同体问题认识和实践上的更新与突破。当然,本文只是从安全共同体概念拓展、理论变迁和现实应对的角度进行了尝试性探讨,至于新语境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途径、方式和困难以及与一般国际组织的区别等更多问题则有待于下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收稿日期:2008-01-09]
[修回日期:2008-10-21]
注释:
①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此为《共同体》一书的英语原名:Commumity: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④参见[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4~132页。
⑤参见梁启超:《国际联盟论序》、《国际联盟评论》,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卷《欧游心影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⑥参见[德]斐迪南·腾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94页。
⑦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第1~5页。
⑧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fter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1,No.1,January 2005,pp.31~52.
⑨参见郭树勇:《论国际政治社会化对国际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第8~14页。
⑩Richard W.Van Wagenen,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ield:Some Notes on a Possible Focus,Princeton,NJ: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rld Political Institution,1952,pp.10-11.
(11)多伊奇把安全共同体分为合并与多元两种类型,阿德勒、巴尼特又把多元安全共同体分为松散型和紧密型两种。限于篇幅内容,本文的探讨更多集中在安全共同体本身,对其分类不做详细展开。
(12)Karl W.Deutsch and Sidney A.Burrell,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p.5-6.
(13)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0-35.
(14)[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15)Mohammed Ayoob,"From Regional System to Regional Society:Exploring Key Variab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3,No.3,1999,p.250.
(16)[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7)郑先武认为建构主义在四个方面对改变“安全共同体”研究的新语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安全共同体的社会建构,即安全共同体是社会建构的过程,避免战争的惯例主要来自互动、社会化、规范和认同的建构;二是更加重视国际组织和制度的作用,组织和制度在导致国家间和平行为的社会化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三是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超越了改变国际政治的物质力量的影响,尽管物质力量仍然重要,但观念、文化和认同等主体间因素在对外政策的互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四是超越了欧美中心的地域和自由、民主、相互依存的理论模式,在缺乏民主和较低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第三世界里依然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参见郑先武:《“安全共同体”理论探微》,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2期,第55~61页。
(18)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2页。
(19)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1991,pp.211~239.
(20)余潇枫、林国治:《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载《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04~112页。
(21)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260页。
(22)Barry Buzan,"Response to Kolodziej," Arms Control,Vol.13,No.3,1992,p.485.
(23)余潇枫、林国治:《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载《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04~112页。
(24)[埃及]萨阿德·纳吉:《迈向一个具有解决之道的全球共同体》,载哈佛燕京学社主编,[美]雅克·布道编著,万俊人、姜玲译:《建构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25)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第1~5页。
(26)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chn/xw/t212461.htm,2005-09-16。
(27)参见余潇枫:《国际关系伦理学》,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31页。
(28)朱锋:《非传统安全呼唤人类共同体意识》,载《瞭望》,2006年第4期,第54~55页。
(29)[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著,陈志刚译:《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30)[美]英格·考尔等:《如何改善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载[美]英吉·考尔等编,张春波、高静译:《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31)[美]梅尔·格托夫著,贾宗谊译:《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2)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第2页。
(33)刘兴华:《非传统安全与安全共同体的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41页。
(34)Ole Weaver,"Insecurity,Security,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Security,"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p.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