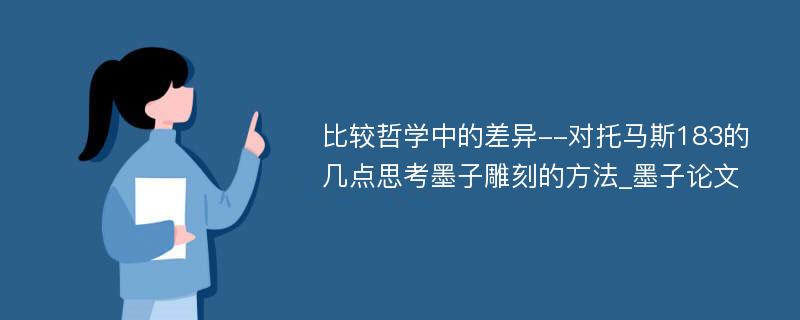
比较哲学中的分化——对托马斯#183;墨子刻之方法论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托马斯论文,方法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9)01-0004-06
在托马斯·墨子刻的权威著作《飘越太平洋的云》(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一书开头,他如此概述了他所谓的“反思性与文化模式的悖论性结合”:
这本书基于如下这一前设,即对于如何推进政治生活的思考既不可能是一个封闭文化系统的产物,也不可能来自于一种作为普遍认知能力的理性——借助这一理性,所有的人都试图把握并反思客观实在性或普遍的原则。我坚持认为这两个维度在每一个人的思想中悖论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我反对以下两类人的观点——那些只沉迷于文化的西方学者,以及那些忽视了反思性如何被不同的文化模式所塑形的西方及中国知识分子。[1](P13~14)
墨子刻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对“话语”(discourse)的关注,他用该词来标记各种“我们群体”(we-groups)所分享的语言、所关切的事物以及“毋庸置疑之事”(indisputables)。换言之,那些把彼此看作共同体一部分的人们分享了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合理的、无须加以辩护的约定(commitment)。①《飘越太平洋的云》一书的一个中心论题在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们——无论他们存有何种差异——实际上均是一个单一共同体的成员,他将这一共同体的表达模式标记为“话语#1”。与此相对,大多数西方政治思想家则参与了“话语#2”,在其中毋庸置疑之事主要来自于他所谓的“伟大的现代西方认识论革命”,或GMWER(Great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而另有一些西方思想家则坚持一种更为古老的对真正政治原则的探寻,墨子刻将其称为“话语#3”。②
而墨子刻自己在这一图式中位于何处?尽管他把自己看作伟大的现代西方认识论革命(GMWER)的后裔,但他也同时对“话语#1”中的若干重要方面感兴趣并从而排斥“话语#2”中的核心结论。那么,谁又构成了他的“我们群体”呢?本文在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和笔者是同一话语共同体的成员,或我们至少属于两个高度重合的共同体。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论述,笔者从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那里所获得的对话语和约定的理解极好地与墨子刻的目标相吻合;事实上,笔者认为甚至比他自己正式提出的方法论还要更好些。在说明了这一相合后,本文将进一步探究“包容性背景”(inclusive context)相对于“分化”(disaggregation)的价值,并从而表明,笔者和墨子刻之间的这一差异既是一个规范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种经验上的意见不和。实际上,在观察到了相同的事实整体并在其中存有多少趋异这一问题上我们并没有产生分歧。相反,我们原本就是带着不同的问题和目标去探究这一可能事实的整体。设想某人在寻找一块能够坐上去的平坦地,那么他可以在象背上找到它;假如某人正寻求一个危险处,大象的蹄子也能帮助他。我建议,我用“分化”一词所标示的方法必须谨慎地得到使用,同时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墨子刻所极力向我们表明的主张。然而,如果我们希望从另一个人那里学到什么——而不仅仅是了解他——分化是我们最好的策略。
让我们从墨子刻有关语言的若干重要论断开始。他认为在历史或当下的话语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的自身理解:(1)这样一种信念:理性能够提供有关现实的知识,而语言则无法阻碍这一进程;(2)一种被他称作“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态度:意见与任何客观实在性都无必然的联系;(3)他所倾向的观点,也即这样一种信念:我们的语言必然被我们的“毋庸置疑之事”所塑造,但除了我们所使用的语词本身,语言与现实之间并无可靠的联系。他指出,唯一在经验上可行的对规范(norms)之本质的假设在于:“一些口头表达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而另一些则是毫无意义的”。[1](P535)尽管墨子刻倾向于上述第三种观点,但该观点也令他感到不安,因为它切断了与一种根基的联系,这一根基是一些中国思想家(如唐君毅)为了促成坚定的进步——也即,为了看到“事情应当怎样”——而坚持的真理。此外,在本文看来,选择第三种观点虽然回应了已存于我们毋庸置疑之事中的张力,但它很难使我们看到“反思性”或“批判理性”的意义所在。但假如我们的毋庸置疑之事彼此之间处于紧张关系中,它们还真的是毋庸置疑的吗?的确,在《飘越太平洋的云》一书的较后部分,墨子刻同意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观点:“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是轻而易举获得的,尽管并不是一下子”。[1](P727)其中的问题在于,第三种观点因此而陷没在了上述观点(2)之中,并且在我们的批判理性中将不存在任何至关重要的东西,除非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语词的确关涉(about)某种东西:除非我们的断言并不仅仅为了与我们毋庸置疑的事情相符合,它们同时也是为了能够真正地说出某种正确的或真实的事情。
但是,难道这不意味着回到了上述观点(1)?并非如此,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它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两难问题而度身定做的。罗伯特·布兰登的语言哲学是建立在约定间推论性的联结(inferential ties among commitments)这一观点之上的,它很好地取代了墨子刻所谓的毋庸置疑之事。一些约定将会较强地被保留,另一些则不然。奎因(Quine)著名的例子“网”——在网中核心的信念比另一些更难被驱逐——有助于我们此处的理解,尽管约定和信念并不相同。我们通过所做的事情而践履着约定,这并不仅仅包含我们说出的话语,同时也包含了行动。约定通常来自于我们的话语和行动,而我们却没有明确地觉察到这一点,尽管一旦它们被明确化,我们也常常会赞同它们。③的确,布兰登的模型所提供出的重要好处在于:通过将语言使用看作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他得以把语言活动理解为一件始终缠卷在实践世界中的事情。语言并不是自由地飘浮于世界之上,而是世界的一部分。
同时,布兰登的理论又在两方面兑现了墨子刻对于文化差异的关注。首先,它根本上是对语言活动的一种透视性(perspectival)理解。也即是说,在其理论中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你从某种表达或行为中获得的和我从中获得的总是存在着那么一点差别。在两个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人那里,这样的差别会非常显著。而这些差异通常会像墨子刻所巧妙展现的那般很快地分枝错节,就如在那些看似简单的政治论调中推论性地隐含着的本体论约定。其次,我们需要说明自己如何受到文化间共享的规范的约束,而其巨大的惰性是墨子刻解释不同话语间持久差异的一个核心层面。虽然加入某个特定社会实践中的每一项行为,都是一种个人的、积累性的行为,并且是对于该实践的一种重新认可(reauthorization)(时而也是一种小幅度的调整),然而重要的在于,要意识到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并不仅仅是自主的决策人,而且是一个已存在的、浸润了规范意义的实践的参与者。
简言之,我从布兰登那里借用来的观点所给予我们的既是一种整体论(holism),又是一种沟通;既有个人主张,又有社会惰性。它表明了将话语带离它们的背景错在何处,忽略了与我们的外在表达系缚在一起的潜在约定错在何处。此外,它把如下这些问题作为语言哲学的出发点:我们和谁一同在说着“我们”,以及通过我们的实践而共同认可某些规范将意味着什么。④布兰登的观点因而向我们道出了墨子刻所需要的一切。
因此,在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层面上,本文认为墨子刻和笔者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然而,在他为笔者的《人权和中国思想》一书所写的一篇富有思想性的综述中,墨子刻不断地指出在我们之间仍然存有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它所针对的问题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背景。笔者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分歧,且它来源于我们对如下问题的不同见解:如何在视话语为整体和分化(disaggregating)之间取得平衡。把话语(或文化、共同体、我们群体)看作一个单一体(monolithic)兼具优势和劣势,正如仅仅关注一种话语中的一派或是共同体中不同的声音而非主流立场同样兼具优势和劣势。我们需要意识到正反双方的立场,并且根据学术或实际的目标、听众以及有关某个主题的现有文献来调整我们的研究进路。概略地说,墨子刻在他的工作中感觉到,以一种单一体的方式看待话语至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而十分有益。首先,他准确地意识到了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对传统和20世纪中国思想之间的承接性尚未获得充分的理解。一种包容性的观点使得人们强调对延续着的本体论及认识论走向的潜在依赖。其次,《飘越太平洋的云》明确地关注着“今日中国和西方政治理论间的冲突”,以及墨子刻所理解的“相互间对非理性和非道德的感知”。[1](P2)的确,他想要超越这一点并发现“一个太平洋两岸可共同分享的批判性视角,并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弱化这一冲突”,[1](P3)但这本书的主要目标在于说明这一冲突所具有的深层缘由。一种包容性的观点在此适用于这一任务,它显示出,甚至那些看来跨越文化边界的思想家实际上也潜在地受缚于一种单一的话语,但通常他们对此却并不自知。
不过,单一体观点也具有不足之处,其主要在于:(1)它使得人们很难谈论或意识到参与一种单一话语的思想家之间的差异。(2)存在着一种相关的倾向使得人们对差异进行二分而无法看到一系列的差异,因为分析者会试图将每一个人归入一种或另一种完整的意义系统中。(3)单一体观点使得人们更难去公正地对待话语的变化。当然,人们仍然能够谈论在一个特定话语范围内的自我批判,笔者将此称作“内部批判”。然而,最为显著的变化通常发生在不同话语或共同体的边界上。在别的地方笔者曾经出于同样的原因批评过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对于传统如何改变的讨论。一种特定类型的内部批判如何引导着人们理性地为自己选择并接纳另一种传统,对于这一问题麦金泰尔有一个富于创见的理论。⑤但转变几乎不可能是这样纯粹的事情,仿佛人们只会在其中选择一整个传统、语言或话语而非另一个。相反,正如笔者对中国人权话语的论述所表明的,同其他传统的批判性相遇总是更为琐碎和常见,它部分地借助于现有的语言和概念并且具有更多含混的后果。即便墨子刻对于话语包容性的单一体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已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未来获得改变的可能性——却仍然被蒙蔽了。
能表明墨子刻单一体观点之缺陷的一个有趣例子是他对于牟宗三——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儒学家之一——的解读。尽管墨子刻并没有在《飘越太平洋的云》中详细地对其思想加以阐述,但他却多次谈及了牟宗三,并且也曾在它处论述过他。在笔者看来,墨子刻对牟宗三的讨论是敏锐的,它表明了牟宗三对“理智直观”的肯定(以及他对于GMWER认识论的相关批判)如何隶属于话语#1这一认识论的乐观主义。不过本文并不关心墨子刻已说出来的东西,而是他并未表达出的东西。虽然《飘越太平洋的云》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但让人惊讶的是,墨子刻几乎没有涉及牟宗三的政治思想。事实上,牟宗三在其同代人(如徐复观)的思想基础上作出了一个重大突破,而这一突破显然无法被归入到话语#1之下,正因为如此,墨子刻对其政治思想的忽视是致命的。在他为笔者的书所写的综述中,墨子刻指出,儒家传统强调“德治的可实践性,并且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中很难发现与这一观点的相违背”。[4](P10)但牟宗三却以敏锐的洞察力去看待信赖德治的问题,并且进而提出了一种方案,也即道德必须部分地自我坎陷;换言之,道德必须受到独立的、客观的制度例如法律和权利的限制。⑥笔者相信牟宗三在此处的观点极富洞察力,它能够同他的另一个听起来相似、但却较成问题的论断——为了达到“智的直觉”的“良知自我坎陷”——相分离。虽然此处并不是详尽探究牟宗三之主张的合适场合,但必须清楚的是,我们不应当认为他仅仅表达了一种单一的话语#1。
现在让我们转向分化的优势所在。当某人试图与来自其他背景的人们交往时,以一种分化的方式思考其自身的价值将有助于他获得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或认同。米歇尔·沃泽(Michael Walzer)称此为“稀薄的”价值(thin values);与“浓稠的”价值(thick values)不同,当我们谈论稀薄的价值时我们并没有关注于其潜在的辩护、全部的意义或宽泛的推论性联系,我们只是在寻求表面上的和他人共有的根基。[9]这一策略被“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付诸实行,并且由雅克·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一位总结了全球思想家对人权看法的哲学家——明确地提出。他的著名论调是:“是的,我们赞同权利,但前提在于没有人问我们为什么”。[8]实际上我们可以走得更远,而且,从一种分化的立场出发,当某人开始重视某种在其他群体中具有更大重要性的事物时——例如,当一位穆斯林的政治思想家开始信奉人权的价值时——他或她可能会被迫使着去重新鉴察其自身的传统并且考虑它们是否能够得到修正,从而在地方的传统中给予这一价值以一个更为稳固的根基。⑦换言之,首先我们要暂时地分化我们的价值,并且注意到不同传统在一个或多个“稀薄的”价值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这可以作为最初的沟通桥梁,并且引导我们去经历一种“增稠”稀薄价值的过程,以便重新将其纳入本土的传统之内。但在这一过程中,本土传统的价值将自行得到发展。我们不能保证这一过程必定成功(这里所指的是,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被某人所属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所接受),但没有一种初始的分化策略,这类渐进的过程将是不可能的。
此外,分化的立场更多地赋予了少数派的声音有被倾听的机会。例如,在笔者的那本有关人权的书中,笔者曾指出在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和不同中国思想家的权利概念之间有着一些显著的重合。倘若美国人被激发着在人权问题上去独立地寻求一个与中国人共有的根基,那么我们应当会去认真对待拉兹的工作。根据上文谈到的,很显然牟宗三是另一位无论美国人和中国人均要对其思想加以细致考察的人物。
当然,人们不能把分化推进得太远,毕竟,它依赖于对许多推论性关联的暂时抵制,而这些关联又赋予了我们的语词以意义。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暂时脱离社会常规的尝试,这些社会常规的“惰性”对我们能够向他人说什么以及理解什么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就此而言,分化的视角是脆弱的,并且容易导向错误。[这些讨论与哲学比较方法论皆相关联。]因此,作为跨文化对话的参与者,以及试图理解这些对话的分析者,我们必须谨慎地在单一体和分化的视角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平衡是笔者有关人权一书的核心目标,并且体现在笔者对开篇所列的刘华秋的两个论点的回应中。一方面,笔者同意他(以及墨子刻),中国的人权话语是独特的,尽管笔者并不是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上这样说。另一方面,笔者坚持认为中国的人权话语并没有因此与来自中国外部的交流、对话和批判相隔绝。笔者的口号是:“保持独特性的交流”(communication despite distinctiveness)。
本文的任务在于更清晰地表明为跨文化理解和对话的尝试奠基的方法论。墨子刻教授的理想是一个“由学者所组成的全球哲学会议,它的动机来自于一个理性的约定,即批判性地鉴察在文化中所固有的一切哲学”[即将出版,29][10](P29),这一理想本质上与笔者所说的“有根基的全球哲学”(rooted global philosophy)相一致。在这一哲学中,我们从自身的传统出发,并且以某种向其他传统的洞见和理性开放的方式前行。最后,笔者重申一下自己的信念:墨子刻和笔者分享了许多看法,同时,笔者感谢他对于此书的关注。笔者期待着对话的继续进行。
收稿日期:2008-07-17
注释:
①英文commitment一词含义甚多,在本文的语境下,它更多地意指在文化共同体中被分享的潜在(及可公开的)观念、信念和思想。本文将其统一译作“约定”,愿读者参考英文原意来理解此词。——译者注
②实际上,墨子刻说“我的印象是,当前美国的学术主流倾向于一种折衷的、分析不全面的言谈#2和言谈#3的混合体,而并不只是言谈#2”。[1](P90)但即便如此,他却几乎完全关注于西方的言谈#2。
③两个简短的例子:(1)当和我的妻子出门时,我抓起了我的伞。“你真的认为天可能下雨?”“是的,我听说今天下午将有气流锋移来。”(2)在某个手工吹制玻璃的工艺展览会上,我说:“它是亮绿色的。”我的妻子回答道:“真的么?它有颜色?”“当然——很淡但却是绿色的,任何绿色的东西当然是有颜色的啦!”我对于下雨的可能性的认定并不是那么强烈地持有,但对于从“它是绿的”到“它是有颜色的”这一推论的认定却十分强烈。同样这也可以应用于规范约定,例如墨子刻惯常使用的例子,以及从“那是种族主义”到“那是错误的”的推论。
④布兰登的书名为《付诸言表》(Making it explicit),第一部分题为“说‘我们’”(Saying 'We')。
⑤参见[MacIntyre 1988][2]和[Angle 2002b]。[3]
⑥参见[Mou 1991,59][5]和[Li 2001,11~16][6]中有益的探讨。
⑦对于这一过程的重要例子,请见[An-Na'im 1990][9]以及我在[Angle未发表][10]中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