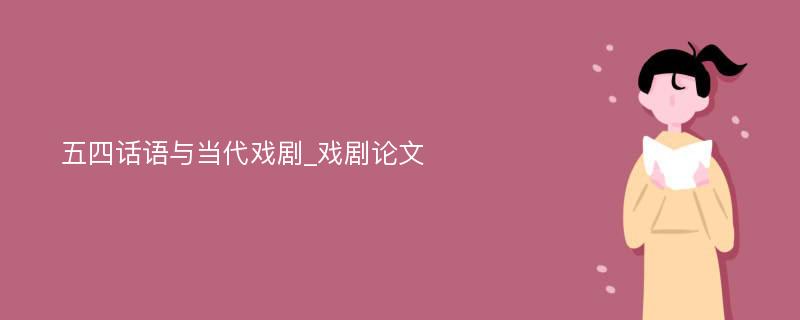
“五四”话语和当代戏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话语论文,当代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正成为消失在我们视野中的一个历史背影。世纪之交看中国戏剧,可以发现其被某种浓厚的意绪环绕着,这就是标志着现代史帷幕在中华大地上拉开的“五四”话语。检视当下中国剧坛可知,20世纪初文化启蒙先驱提出的若干话题,穿越了近百年沧桑岁月,依然为世纪末戏剧所津津乐道,并被后者在舞台上不断予以情节化复制和符码化演绎。
在第六届中国戏剧节和首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好些投入重呼声高影响大的剧作即呈现出某种非偶然的趋同性。先看文本主题,“新版越剧《红楼梦》,写的是封建家族对爱情的毁灭。(它在演出形式上放大了原版,但思想上丝毫没有放大)京剧《宝莲灯》也写了以二郎神为代表的家族势力对三圣女爱情的打击。在艺术节上众口叫好的川剧《金子》也是焦家抢去金子,毁灭了仇虎的爱情。花灯戏《卓梅与阿罗》更是家族毁灭爱情的莎翁名剧的翻版。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先是很有趣,写了一个美丽聪明的女人设下‘肉色陷阱’,但作者最终却把一出女性主义的题材重新纳入‘封建势力压迫人间爱情’这一经多次重复的文化主题。”被当下中国戏剧创作者到处“克隆”的这揭露国民性的反封建主题,却非今人原创性思想结晶,而“其实是‘五四’文化巨匠们思索的成果”。再看题材来源,世纪末走红的话剧《生死场》、越剧《孔乙己》、京剧《骆驼祥子》和川剧《金子》的身后,站立着的是萧红、鲁迅、老舍和曹禺,不过是这些个领受“五四”新风的作家们20、30年代作品的改编搬演;即便是并非改编之作的黄梅戏《徽州女人》,其写家族礼教对女性青春的压抑,也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五四”之前。由此看来,尽管时代和社会已然不同,虽“时隔数十年,我们仍没走出‘五四’精英们的文化视野”(《上海戏剧》2000年第1期桂荣华文)。论者出语虽重,却非没有道理。
若把目光不仅仅停驻在1999这年头,把20世纪最后20年纳入视野,你会发现,对此话语的迷恋于当代中国戏剧可谓是由来久矣。以戏曲为例,作为对“文革”逆流的文化反拨,沐浴着思想解放春风的新时期戏曲正是以重拾“五四”启蒙大旗再奏反封建进行曲为标志的,其突出代表可举一部来自西部却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的荒诞剧《潘金莲》。80年代中期上演后引出“众声喧哗”的舆论褒贬继而又被国内近百家剧团争相移植搬演的该剧,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927年冬在大上海由进步的南国社演出的同名京剧《潘金莲》。而创作后一出戏并给前者以直接思想启迪的非他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当年,随着中国史从古代向近代再向现代翻页,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积极引领下,女权问题于20世纪初在本土剧烈的社会和思想变革中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身为“边缘人”、“第二性”的女性开始走上不甘寂寞的历史前台,妇女解放成了那个时代个性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女权主义成了中国社会反封建先驱者们手中的锐利武器。一个异邦的易卜生,一部舶来的《玩偶之家》,以女权问题为导火线在彼时国人心中唤起的高亢的反封建激情,迄今犹让我们感慨不已。作为领受“五四”运动新风的剧作家,欧阳前辈率先提出了重新认识“千古淫妇”潘金莲的问题,他以现代目光从这女子身上读出一个心理苦闷变态的女性,认为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礼俗的可悲牺牲品,于是奋笔写出了翻案戏《潘金莲》。虽然这翻案话语有拔高之嫌,却向全社会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并成为后来蜀中怪才魏明伦再写同名川剧的重要契机。“五四”先驱者们播下的思想火种不灭,新时期以来,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和对封建主义残余的猛烈批判,女权意识在神州大地上再度觉醒,成为呼唤人文主义的社会思潮的鲜明标志之一,并直接投射在当代戏剧创作中。尽管魏氏剧作在叙事走向、手法运用等上并未驻足于世纪初戏剧前辈的格局,但连魏氏本人也不讳言,促使他奋力创作此剧以“透视中华‘妇女病’的动因之一”,恰恰是“五四”运动吹响的妇女解放“号角”。
事实上,正是这种以文化复兴和人文复归为使命的“旧话重提”,为20世纪80年代以“探索”为特征的新时期戏剧输入了迅速崛起壮大的生命“荷尔蒙”;新时期戏剧前所未有的先锋气质和叛逆精神,就在向世纪初启蒙话语的主动拾取和积极认同上凸露出来。
步入90年代,中国戏剧对“五四”话语的热情依然不减。这是因为世纪初“五四”先驱者们针对封建陋习、国民惰性、文化劣根等提出的某些革命性话题,到了世纪末由于种种原因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譬如“女权问题”,该问题在新时期重新提起,正为的是扫荡以男权为主即西人所谓“菲勒斯中心”的封建意识。不必怀疑,“五四”新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妇女观的转变,新中国建立更给妇女们带来了翻身解放,使她们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站到与男子共享平等权利的经济和政治地平线上。但在意识和观念深处,她们乃至整个社会还不能一蹴而就地摆脱性别歧视的沉疴,此乃传统的惯性使然。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者们在超越传统思维定势代女性公正发言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瞩目成就,但远远不能说这使命业已完成。因为,封建社会虽已一去不复返,但夹带封建色彩的男权沙文主义意识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却未必轻易随之消失,后者还像梦魇般缠绕着现代人的思想并投射在文艺作品中。反封建倡文明树新风的文化启蒙使命在吾国吾土依然任重而道远。国情如此,现状如此,再回过头来看世纪末戏剧何以迷恋世纪初“五四”文化话语这现象,对某些问题也就容易理解。
当代戏剧重拾昔日话语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也自会有新的文化解读和题意发挥。世纪末戏剧仍旧以不变应万变的痴迷态重复着前10多年已重提的世纪初的话题和话语,就难免要遭到主张“向前看”的批评家抨击而被斥之为患上了“文化失语症”。因为,从负面看,世纪末的剧作者老是去“克隆”世纪初前辈所提出的文化思想和文化主题,未尝不是一种悲哀,它多多少少透露出当下本土剧坛原创性思想和作品“贫血”的严峻现实。正像有人指出,“‘五四’的文化巨人们最大的成就是反封建和揭露国民性。这无疑十分深刻。但是‘五四’巨人们又恰恰是在痛恨中国文化无法进入世界‘文化平台’,无法取得和世界‘文化平台’对话的地位之下,才奋然而举起反封建大旗来揭露国民性的。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文化平台’和‘五四’时期文化巨人们所面临的文化平台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剧作家却以为‘五四’话语是进入世界‘文化平台’的永恒话语。岂不是有点失笑于大方之家!”(同前,桂荣华文)当今中国戏剧凭借过去时代话语能否实现“国际接轨”的梦想,我们暂不讨论,但须承认,忽视发话背景差异的话语重复,这多少反映出迷恋世纪初话语的世纪末戏剧的某种文化尴尬。难道说,有思想有价值的话都被聪明的前人说尽道绝了,剩下的就只有鹦鹉学舌的份儿?……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戏剧对“五四”话语的深深迷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如何从社会学和艺术学角度就此事实进行认真研究和作出辩证评价,是告别旧世纪跨入新世纪的我们所不可回避的课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