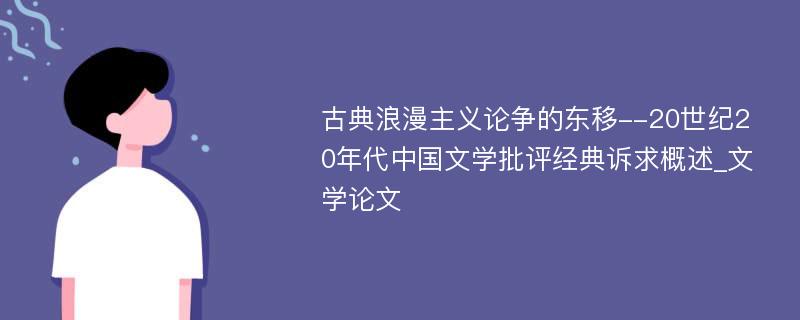
古典浪漫之争的东移——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古典主义诉求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古典主义论文,之争论文,中国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6-0075-05
五四初期,陈独秀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变迁为参照,断定中国文学尚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并表达了告别古典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强烈愿望。胡适对陈独秀的观点深表赞同,并撰文《易卜生主义》,大力提倡“写实派文学”。其后,在创作上,文学研究会写实主义日渐盛行,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该思潮具有唯美颓废的色彩)异军突起;在文学史写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成为确定中外文学经典、构建中外文学史的主要标准。这一切,使中国的古典文学大有日薄西山之势。
面对文学革命势如破竹的攻势,一批颇具古典情怀的知识分子,围绕中国新旧文学的评价问题,进行了悲壮而无力的抵抗。过去学术界倾向于把这场争论看做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近年来,许多学者又把它概括为学术立场与启蒙立场的冲突。后一种概括,在解释新文化倡导者在学术研究上的重大成就与古典者浓厚的文化启蒙色彩时,显得无能为力。事实上,在这场争论的背后,既有中国传统学术内部的冲突,又有异域异型文化资源的较量。论争双方为确立各自主张的合理性,纷纷奔向西方文学寻求文化支援,结果正如李怡所言:这场争论“将中国文学建设引入到一个相当宏阔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上”。[1]如果从世界文学的背景上看,我们不妨说这场在中国大地上复演的是一场古典与浪漫相角逐的长剧。
19世纪初,当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普遍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的文学信条时,雷纳·韦勒克认为这场变化“决定性”的迹象是“一种情感说的诗歌观念的产生,历史主义观点的确立,对模仿理论,规则及体裁说的隐然否定”。[2](P2)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古典主义诉求,恰与这种迹象相反:他们肯定宗教道德的价值以对抗情感的泛滥,他们否定“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辩护;他们坚守文学的模仿论,发出了不同于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声音;他们维护体裁的纯净说,试图纠正新文学体裁类型混杂的偏差。由此可见,这种文学古典化的精神诉求和形式诉求,与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注: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曾指出“学衡派”、林纾、章士钊的文学主张与西方古典主义的相似性,并叹惜他们“未能像西洋似的形成一种古典主义的文艺思潮,而且没有什么作品”。)
一、咎欲的心理基础
肇始五四的文化激进与保守之争,是百年文化、文学研究中一个长期难以摆脱的困境,对于激进与保守的褒贬,随着政治处境与社会状况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我们不必因此心存惶恐而无所适从,我们可以视之为不同时期的研究者,由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对自身文化观念的一种自觉调整。如能正视古典主义诉求者的问题意识,或许会少些纷争,多些理解。
问题意识是一种忧患意识,它产生于研究主体对不合理现实、对未来隐忧的深切体验,它时刻萦绕于研究者的脑际,并给其切实的喜怒哀乐。问题意识往往影响研究者哲学、文化、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创作的形成与发展,并使研究者的学术活动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与一致性。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鲁迅能够在《新青年》通力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他们有相似的问题意识。时时触痛他们的是中国一潭死水的现状,是中国国民的愚昧、迷信、奴性,以及无声的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认为症结在于封建的纲常名教抹杀了国人最基本的欲望,“旧理学崇理而咎欲,故生出许多不近人情的东西,甚至吃人的礼教”。胡适在以“理学反动”的立场进行中国传统学术史的研究时,排斥程朱,盛赞清代汉学家惠栋、戴震、焦循、阮元冲破宋儒理欲二元论、从正面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的贡献。他对戴震“理者,存乎欲者也”,“理者,情之不爽失者”[3](P74)的理欲之辩,给予较高的评价,并且把“欲”与求知的热情、个性解放的愿望联系了起来。胡适对“欲”的看法,在新派知识分子中比较具有代表性。这是他们严厉拒斥西方重理性的古典主义文学,大胆吸纳西方走出古典主义之后的重个性与情感的文学思潮的深层原因。
再看另一类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林纾以为丧权失地不足为患,“所患伦纪为斯人所坏,行将侪于禽兽”。[4](P95)章太炎忧虑世道人心学术的败坏,“睹异说之昌披,惧斯文之将丧”。[5]胡先骕痛感“人欲横行,廉耻道丧,已至于极点”。[6](P85)吴宓观美国电影“作艺术及舞蹈之少女,在剧中脱去外衣,仅余短裤,上及腰,下及股际,余皆裸露”,[7]闻陈寅恪言巴黎裸体美人戏园“密室之中,云雨之事,任人观览,甚至男与男交,女与女交,人与犬交,穷形尽相……如身游地狱,魔鬼呈形”[7],备感充斥美国的私娼、婚外恋使“人欲日盛,货利是趋,又肆意放纵,一无拘束”[7],更让他痛苦的是,大量留学生步西人后尘,而国内也对欧美恶俗吸取尤速。
欲望的极度膨胀可能导致的危险,致使他们程度不一地认同了宋儒的理欲二元说。有人据此指责他们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当时中国除极端落后闭塞的乡村外,确实也局部存在都市的畸形繁荣与欲望的膨胀。我们不同意的只是吴宓等人对当时现实所作的“博放之世”的整体评价,借吴宓的说法,用“精约之世”概括当时社会也许更合适,在纲常名教的严酷统治之下,又有何“博放”可言呢?
咎欲的心理基础,使他们认同了白璧德节制欲望的新人文主义和传统的义理之学,并以此作为评判东西方文学的标准,从而对东西方文学作出了完全不同于新文学家的描述。“物欲横流”的意念,填满了他们大脑的空间,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并局限着他们的学术思路,使他们无暇正视“欲”的复杂性与合理性:除了他们所指责的堕落为兽的冲动之外,人类追求知识、幸福和个性解放的愿望,也是人欲的一部分,在当时,这部分实际上更应得到重视和强调。他们所崇之理,指那种能使我们区别于禽兽而成为人的先天能力,指人性中能够辨别是非、兽恶、美丑的普遍永恒的存在。这种理,不能开拓出新的知识领域,并且常常限制个体精神自由和创造力的发展,无力去应对当时中国的严峻现实。
二、古典的批评立场
从歌德、席勒起,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分野开始引起作家们的重视,经施莱格尔兄弟对这两种不同艺术特质的详细阐释(如“超乎利欲”与“关乎利欲”,人的有限性与人的无限性,模仿与创造,体裁的纯净与混合等的对立),西方文学批评已形成一种在古典与浪漫对立的框架中思考文学现象的习惯性思维模式:杰弗和雪莱,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司汤达和雨果都在这种思维模式中阐释自己的文学观念,甚至著名的意象派诗人庞德、休姆,象征派大师艾略特都自称在文学精神上接近古典主义。
崇理咎欲,正是学衡派以及和他们有着相近精神血缘的梁实秋,沿用西方的古典浪漫对立的思维模式,并倾向于古典批评立场的心理基础。在引进西方文学方面,他们批评自卢梭以降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学,他们批评在道家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消极浪漫特征。对于新文学,他们把一切有悖于自己理欲观的文学原则(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看做浪漫主义而加以批判。例如,吴宓指责西方写实派文学“脱胎于浪漫派而每下愈况”,“只有淫欲,毫无知识义理”[7]。胡先骕则认为,从表面上看,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正好相反,“实则不过浪漫主义之变相”,在否认人类固有的美德与自治能力上,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相同的: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浪漫主义“否认人文之要素,而以顺随内心之冲动为宗旨”,而“写实主义之失在知人性之恶而不知人性之善,在知人之情欲殊无异于禽兽,而不知人类有超越于禽兽之长,有驾驭控制遏抑其情欲之冲动使归于中和之本能。在认定恶为固然,因而以克己复礼为徒劳,节制嗜欲为掩饰”。[8](P272)郭斌和则更为干脆地说“两派外表虽异,然其不衷事理,好趋极端之心理同,浪漫主义以纵情恣欲为至善,写实主义把人看做兽类一样,尤属荒谬。”[9]应注意,胡先骕、郭斌和等人不仅把写实主义,而且把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也视为浪漫主义的变种而横加指责。
在与学衡诸君相同的思路下,梁实秋全面引进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更猛烈地阻击新文学的浪漫趋势。如果说前者的批评与新文学创作还存在较大隔膜的话,曾经厕身新文学阵营、专攻西洋文学批评史的梁实秋,其批评就明显切近新文学的实际和文学创作的规律了。《现代文学论》认为,新文学的固有血统——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是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而远离人生的浪漫派文学,在性质上很像西洋文学中最极端的浪漫主义。《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文学的纪律》、《文学批评辩》等文紧扣创作主体的情感、想像方式的特征,剖析新文学对情感、想像的无限推崇所导致的极端浪漫的症结。为辩证施治,他主张引进西方文学应有一最低限度的共识:“与西洋文学中应采取其切于实际人生的一部分,并排斥其脱离人生之极端浪漫的一部分。唯美派的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享乐的颓废派的文学,以及印象派的文学,这都是缺乏严重的人生意味的东西,正合我们的消极懒惰的民族心理,但是决不合我们现代的需要,我们中国文学已有太多的逃避现实的气息,何必再加上外国的不健康的质素。”[10](P338)
在对新文学重情抑理的极端浪漫趋势的制衡上,在对西方文学较为冷静的审视上,古典主义的诉求,功不可没。但古典与浪漫(情与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难免简单化倾向:对“欲”的节制,而看不到新文学求新求变求自由求个性解放之“情”的现实合理性,使他们失去了与变革的现实对话的权利;对“理”的推重,而忽视人类非理性层面这一至为宝贵的艺术源泉,以及西方文学走出古典主义后,在这一源泉浇灌下在艺术方面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三、质疑“历史的文学观念”
19世纪末科学崇拜的潮流,使自然科学的势力迅速向人文学科渗透,其在推动人文学科发展的同时,也给它带来负面影响。简单地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概念方法与成果搬用到人文学科的“科学主义倾向”,使哲学、文学、艺术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困境。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赛先生”,使沉闷的中国焕发了勃勃生机,但人文学科的困境也因之而生。面对科学势力向一切学术领域的推进,古典主义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姿态:在学术方法上,他们以义理之学对抗考据之学;在人生哲学上,他们极力为宗教和道德的合理性辩护,企图为信仰保留一个生存的空间(梁实秋认识到科学取代宗教、哲学的必然性,同时也能够容忍诗与宗教、哲学的分离,但他反对心理学、社会学对文学的侵袭,坚守文学表现人性的底线);在文学史观上,他们质疑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进化论经严复创造性阐释而大行中国。严复把达尔文生物进化的规律转化为宇宙万物进化的普遍法则,使进化论成为推动国人思想变革的有力武器。胡适进一步把进化论的观念引入文学领域,提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并把它作为清算整理旧文学、张扬文学革命的理论武器。在进化论的支配下,“破旧立新”、“弃旧图新”的思维模式,成为20世纪追求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一个较为普遍的心态。这种心态,是诉诸古典、到古典文学中寻求精神资源的一个重要障碍,只有突破这种新旧对立的观念,古典主义的诉求才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性。
20年代,章太炎主编的《华国》、吴宓主编的《学衡》、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不满多数新文学杂志仇旧趋新的价值取向(这种倾向确实程度不一存在),因而着力为旧辩护。《华国》责编汪东兴主张“新文化固当虚心容受,旧文化也断不可以一概抹杀,如果一个人能够新旧兼贯最好,不能,便联结两派学者通力合作,重在互相引证发明,不要互相诋毁”。[11]章士钊则上溯达尔文天演论的远祖近宗,以论证其“新与旧之衔接,其形为犬牙,不为栉比”的“妙谛”,指责新文化运动“离旧而顺驰,一是仇旧,而唯渺不可得之新是鹜”,而致“精神界大乱”。[12]
《学衡》对盲目趋新的批评更是不遗余力。除大力介绍亚里士多德、浦伯、安诺德、白璧德等古典主义者外,他们还译介柯克斯的《论古学之精神》、《论进步之梦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葛兰坚论新》,吉罗德夫人的《风俗道德论》等大量古典倾向的欧美文化论著,以阐明进化论的真意及其适用范围。他们反对把物质之律的进化论凌驾于人事之律(哲学、文艺、美学)上,从而对文艺、美术造成不应有的破坏。
学衡派同仁普遍认为,文学革命的立论基础是“历史的文学观念”。他们多从文学表现对象与文学本体特征的恒久性角度,反对这种观念。吴宓认为“文学所表现者,乃人生与人性之常,兼及其变”,反对“浪漫派、写实派、自然派皆只注重表现人生人性之变,而遗弃其常”。[13]吴芳吉从文心的恒久性与变异性出发,反对“旧者唯旧,不复知新,新者唯新,悍然拒旧”的文学退化说和文学进化说的偏颇,指出“文学唯有是与不是,无有新与不新……文学乃古今相孳乳而成”。[14]胡先骕《文学之标准》、
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认为文学为情感与艺术之产物,其身无进化天演可言。
缪凤林、幼南、薛鸿猷等人在“迷恋骸骨”的讨论中,主张诗之精神即男女怨慕、喜怒
哀乐等人生情绪,并无古今之异。这些观点,与梁实秋的文学表现普遍永恒的人性说,
已经非常相似了。
梁实秋在对西方文学思考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文学不一定新的就是好的,19世纪的文学不见得就比18世纪的好,20世纪的也不见得就比19世纪的好,我们若要公正的鉴赏研究文学,先要打破这一重‘新’的迷信”。[15]他把新文学的创作实际置于西方文学的背景中进行比较,发现“文学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16](P4)新文学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创作莫不如此。针对现代一定胜于古代的文学史观,梁实秋强调文学的永久性,因为思想、技术可以进化,而表现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情的文学是没有进化的。
“文学无新旧”的诉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反复出现。尽管这些诉求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也可能对现代性的价值追求有所偏离,但他们要求文学创作摆脱贫瘠、沟通新旧文学联系的愿望,以古典文学支援当代创作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
四、坚守文学模仿论
文学的本质在于模仿,这是西方古典主义者对文学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取代古典主义时,模仿说曾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20年代中国的古典主义者同样对模仿说情有独钟。
在20年代初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中,文学模仿说并非作为一种创作原则或方法而受到重视。以胡先骕《评<尝试集>》为例,他阐明了亚里斯多德模仿论的真义,并且能
够看出:“模仿风景与人情”与“模仿古人典籍”是西方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重要
区别。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主要兴趣,仅仅是以模仿说为武器论证模仿古人的重要 性
,以反对胡适“不模仿古人”的观点。
20年代中后期,古典主义批评的重心开始由“典籍的模仿”向“艺术的模仿”转移。在当时,写实主义的再现说和浪漫主义的表现说,深受新文学家欢迎。因为再现说要求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能够有效疗治中国传统文学“瞒”和“骗”的弊病;而表现说重视真切地抒发内心的情感与理想,能够有效冲击传统道德理性对个人情感的过分束缚。但在实际创作中,再现与表现是很难判然分开的。单方面强调任何一方,都可能使文学创作产生新的偏差:或拘于客观现实,忽略主体情感和理想;或囿于主体情感理想,脱离现实人生。吴宓、梁实秋反复阐释亚里斯多德模仿论的本义,其出发点合辙而同归:在认识到盛极当时的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艺术观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弊端时,他们试图在再现与表现间保持一种中庸化的姿态。
吴宓认为“世无绝对主观亦无绝对客观之文学”,[13]在亚里士多德艺术不仅模拟具体的现实事物,而且模拟现实事物的普遍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模仿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艺术的“三境”说,他的“实境”说,反对凭空虚造,坚持艺术反映现实,“诗为社会之小影”,“苟舍去社会生涯而言诗,则无论如何雕琢刻饰,搜奇书,用僻典,皆不得谓之诗”;他的“幻境”说,强调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的选择与剪裁,从而与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划清了界限,他认为艺术模仿人生“非以印板写照,重拓复本、毕肖原形,毫厘不爽之谓。盖如是,则理固不宜而势亦不能”。他的“真境”强调艺术的永恒性,即艺术描写或达到“天理人性物象今古不变,到处皆同,不为空间时间等所限”的最高境界。[17]这也是亚氏模仿中已有之意。
梁实秋在告别或否定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论之后,转向并折服于亚里斯多德。他从亚氏模仿论中抽取出“文学表现普遍永恒的人性”而大力强调(这种强调未必与亚氏原意完全吻合)是有其现实考虑的,他说:“所谓文学模仿者,其对象乃普遍的永久的自然与人生,乃超于现象之真实;其方法乃创造的、想像的、默会的;一方面不同于写实主义,因其模仿者乃理想而非现实,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迹;一方面复不同于浪漫主义,因其想象乃重理智的而非情感的,乃有约束地而非扩展的。”[18](P59)显然,梁实秋与吴宓对模仿论的坚守,其主观目的是大同小异的。
五、维护体裁的纯净
文学革命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实现了文学观念的更新,而且打破了传统文体间的界限,在散文诗、诗化小说等新体裁上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体现出创新的激情,并显示出应有的实绩。
文学型类的清楚划分,是西方古典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也不乏反对“以文为诗”的呼声)。同样,现代的古典批评者也视新文学体裁创新为文学型类的混杂。针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理论倡导,胡先骕强调诗的声调格律音韵,吴宓主
张以音律作为诗文之别的标志,并在区分诗文之别的基础上提出“以新材料入旧格律”
的诗学理论。在“迷恋骸骨”的讨论中,薛鸿猷、缪凤林、幼南援引亚里士多德、斯蒂
提森、约翰逊、圣伯甫、安诺德、温斯特等人“韵文与散文二元分立”的诗学主张,坚
持“诗必有韵”、“无韵则非诗”,以对抗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新文学家则以西
方由韵趋散的浪漫主义诗学理论以及惠特曼、屠格涅夫、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创作实践,
为散文诗创作辩护。
在现代文学作家中,梁实秋是维护体裁纯净说的最有力者。借鉴西方古典主义者的经验,他把新文学创作中韵文与散文的结合(散文诗)、诗与小说的联姻叫做“文学型类的混杂”,认为“诗,小品文,小说,这几种型类的文章的区分,是有划分的必要的。型类的混杂,是变态,不是正则”。梁实秋虽然承认散文诗在文学里可备一格,但又说“这是一种变例,不是常态”。[18]他对当时流行的“西方诗已经由韵趋散”的论调,提出质疑,反对以此为借口,回避新诗必须面对的形式、格律建设的难关。另外,他极力反对新诗创作受西方印象派诗歌的影响而出现的“以文字作画”的倾向,因为他们所模仿的对象、工具与方法各有不同。如果把图画的艺术不加限制地应用在诗里,同样会产生型类的混杂,使诗丧失自身的独立的品格。
注重故事性是古典小说的基本特征。在评品西洋小说时,吴宓始终主张“情节一致为佳小说所当具”,[19]他不赞成以过多的议论、景物描画、心理分析破坏小说的故事性。从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角度,他把短篇小说看做文学的衰象之一,“小说究以长篇章回体为正宗”,并提倡写作“外示环境之沿革,内示个人身心之发育成长的纲鉴体小说”。[20]梁实秋也认为小说适于叙事不适于抒情,没有故事便没有小说。他对新文学创作中大量出现的书信体、日记体、游记体小说深为不满,因为它们“没有故事可说,里面没有布局,也没有人物描写,只是一些零碎的感想和印象”。[21](P16)他认为“好的小说必需要有一个故事做骨干,结构要完整,要有头有尾有中部,然后作者再凭借着这故事来表现作者所了解的人性,这人性的刻画才是小说的灵魂”。[10]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戏剧艺术分为诗的艺术与演剧艺术两部分,认为诗的艺术比演剧艺术更为重要。胡先骕、吴宓、梁实秋沿用亚氏的思路,对中国现代戏剧
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从不同角度强调戏剧的诗性特征。对于新剧运动初期致力于布景、
灯光与化妆等舞台艺术(即演剧艺术)而忽视戏剧艺术(指诗的艺术)的偏差,梁实秋反复
强调戏剧是“艺术的一种,是诗的一种,绝不容许把戏剧艺术与舞台艺术混为一谈,由
最高艺术变为混合艺术,由混合艺术将有沦为技术的倾向”。[22](P36)
从维护各种文体最基本的特质角度而言,体裁纯净的诉求,有其部分的合理性。但是,不同文体间并无不可跨越的鸿沟,如果看不到不同文体间相互借鉴的可能性,无视文体创新的意义,亦非明智之举。联想到新文学家在创新体裁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再看胡先骕“中国诗之体裁既已繁殊,无论何种题目何种情况皆有合宜之体裁”,“尤无
庸创造一种无纪律之体裁以代之也”[23](P33)的观点,难怪会有人目之为厚古薄今 了
收稿日期:2003-07-20
标签:文学论文; 梁实秋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新古典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人性论文; 吴宓论文; 胡先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