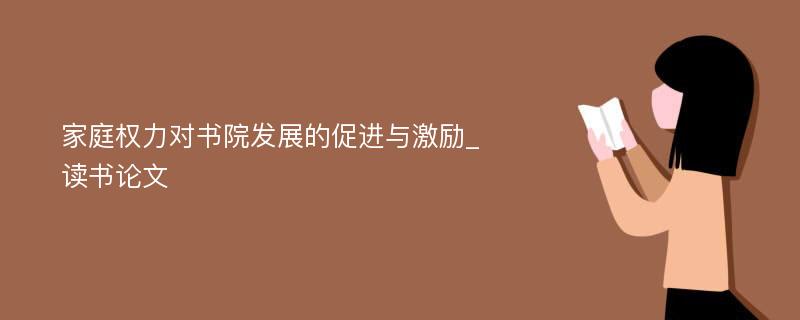
家族力量对书院发展的推动及其动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院论文,动机论文,力量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的发展,有赖于官方及民间多种社会力量的推动。其中,家族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宋明以后,家族制盛行。许多家族聚族而居,同姓至数十甚至数百家,成为具有较大规模和势力的社会基层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发挥着重大作用。为了教育本族子弟,达到家族内部的和睦融合,保持家族的长盛不衰,扩大家族在地方的影响,许多家族对教育相当重视。他们创设书院,兴办书院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一 家族书院的发展概况
书院起源于唐代,书院制度则成熟、定型于唐宋之际。在书院兴起之初,就可以见到家族书院的存在。在《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九、卷六百四十中分别有卢纶《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曹唐《题子侄书院双松》二首,其诗题中出现的两书院,从书院名称本身并结合诗作内容看,视为家族书院的雏形,应该大致不差。同时,据一些学者研究,中国最早的聚徒讲学的书院之一——唐代桂岩书院,就是唐代中后期高安人、曾任国子监祭酒的幸南容为给本族子弟创造读书求仕条件而创立的。(注:参见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2。)又据范仲淹称,五代时曾任左谏议大夫的范阳窦禹钧“诸子登进士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致仕后,“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注:范仲淹:《窦谏议录》,《范文正公集·别集》卷四。)北宋学者杨亿曾谈到唐宋之际鼎峙于江南的三所在当时社会享有较高声誉的书院:江州陈氏义门东佳书堂、南康洪氏义门雷塘书院、洪州胡氏华林书院,这三所书院都是由家族所创立的。(注:杨亿:《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武夷新集》卷六。)其中,江州陈氏,合族同处,众至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爨。南唐时,陈衮“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注:徐锴:《陈氏书堂记》,江西《德安县志》卷三,清同治年间刊本。)“建昌县民洪文抚,六世义居,室无异爨,就所居雷湖北创书院,舍来学者。”(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一,至道三年六月已亥。)南昌胡氏家族,一门守义,四世不折,得到旌表,建构胡氏书堂,“筑室百区,聚书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从学者数千人。”(注:徐铉:《骑省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从这些书院建筑、藏书、从学者的规模,可见家族书院在唐宋之际的兴盛状况。
在此后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家族书院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波兰学者琳达·沃尔顿(Walton Linda A.)对南宋书院的研究表明,在12、13世纪,不仅那些同理学相关的书院数量激增,而且家族书院也有急剧增长。(注:Linda A.Walton,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P122.)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一著中也指出:“元代书院的基本类型是以教育宗族和乡里子弟为主要目的的宗党书院”(注: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另据有关学者的统计,清代湖南新田一县的书院中,家族兴办的有13所,占总数的81%(注:参见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88页。),这一数字虽然并不具有普遍的统计学意义,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家族力量对书院的推动之功。
历代家族书院的创设,情况各不相同。不少家族中有名望、社会地位较高、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族人往往以个人或数人之力创设家族书院。据宋人欧阳守道《巽斋集》卷二十二称,醴陵李文伯于莱山创办莱山书院,作为“其一族子弟隶学之所”,“莱山书院为其族公之,屋宇旧敞,田畴日辟,器用日备。延师取友,有以为礼;书籍纸笔,有以供费”。“凡兄弟之子孙皆受之而教之”(注:欧阳守道:《题莱山书院志》,《巽斋集》卷二十二,《四库全书》本。)。这是一所由个人创办,且教且养的家族书院。这类书院,历代史志多有记载。宋淳祐间,曲江仁化邹氏兄弟建青云峰书院,“以为诸子藏修游息之所……买田其中,收其收入,专以给游学之书费。”(注:王畿:《瀛山书院记》,浙江《遂安县志》卷十,民国十九年刊本。)宋嘉泰间,安福周奕彦建秀溪书院,“讲经有堂,诸生有舍,丛书于间,旁招良傅,以训其四子。”(注:杨万里:《秀溪书院记》,《诚斋集》卷七十七。)宋代东南吴氏为诗书传家的世居之族,建札溪书院,“肇造书宇,讲堂其中,扁以达善。……两庑旁翼,为东西斋,斋上为阁,左曰‘明经’,经史子集之书藏焉;右曰‘见贤’,古先贤哲之像列焉。……仲伯子姓,肃肃雍雍,蚤夕其间,以修以游。”(注:程珌:《札溪书院记》,《洛水集》卷七,《四库全书》本。)宋德祐元年,著名理学学者舒璽(广平)归老故里,创广平书塾,“游于斯,讲于斯,群聚辩于斯”,去世后其后人“乃遹追先志,奂饰堂序,帅子若孙,暨宗族之秀,朝益暮习,春秋舍菜先圣,岁时朔望谒祠。齿拜讲说,冠履翼如,弦诵蔼如。”(注:王应麟:《广平书院记》,《深宁先生文钞》卷一,《四明丛书》本。)元代曾氏武城书院乃江西南丰曾氏兄弟所建:“兄弟俱仕翰苑,其父前进士,宋之监察御史,元之儒学提举也。因子贵,追封武城郡伯。于是设书院,祠先圣、先师以及其考,以处宗党来学之人。”(注:吴澄:《武城书院记》,《吴文正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本。)
创建书院、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转往往耗费甚巨,需要相当强的经济实力。这对于一般人而言是难以承担的。因此,也有不少家族书院乃合一族之力、集一族之财兴建而成。如宋代北溪崔氏是一个“藩衍炽昌”的大族,“希易又知学非特以自淑,亦将以淑人,……乃集其宗族之亲而议之,协众力,鸠众财,即其祖居之旁创为书院,规模甚巨,萃诸子侄就学其中。”(注:包恢:《盱山书院记》,《敝帚稿略》卷三,《四库全书》本。)又如福建建宁蒲城为宋代大儒真德秀故居所在地,元延祐年间,“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筑室祠公,相率举私田,给凡学于其宫者,而请官为之立师。”后江浙行中书省上报其事,得到朝廷嘉许并获“西山书院”之名。(注:虞集:《西山书院记》,《道园学古录》卷七,《四库全书》本。)
也有一些家族书院乃当地政府为尊崇、纪念某些家族先辈中的历史文化名人而主持或倡导兴办的。如宋景定年间,判府提刑杨允恭于道州修葺濂溪旧宅,“合谏议(周敦颐之父)、元公,俾祠于正堂。就立儒学斋于其右,求周氏之族龆龀以上者,得二十余人,选族之长主祠,提其纲,专教谕之责……凡异姓之子弟愿附斋就学者,亦听焉”,并奏请皇帝亲自题写“道州濂溪书院”院额。(注:滕巽真:《判府提刑高峰先生寿祠之记》,《湖南通志》卷二百七十九,商务印书馆1934年排印本。)又如元至正年间,吴郡郡守吴秉彝建议将宋初名儒范仲淹在吴中故里的祠宇改为书院。此议得到朝廷批准,“不设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注:郑元祐:《文正书院记》,《侨吴集》卷九,《四库全书》本。)。这种家族书院,性质较为特殊。它虽属家族书院,但其设立却是政府行为,这种行为所体现的崇德报功,彰显道统的意味非常明显。这类书院兼有祠祀与行教双重使命,且相对而言祠祀的功能更为重要。
家族书院的教育对象也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家族书院大多面向本族子弟,以本族子弟为主要的教育对象。但许多家族书院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在教育本族子弟的同时,往往也对乡里子弟乃至外地求学者开放,以扩大家族办学的影响,同时营造一种相互切磋交流的学习气氛,对本族子弟的教育产生促进作用。南宋贵溪高氏可仰未仕时“刻苦学问,作书院于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乡人子弟教之,因名曰‘桐源书院’”。“高氏特以教其家与一乡之子弟,有古人吕塾之遗意。”(注:汪应辰:《桐源书院记》,《文定集》卷九,《四库全书》本。)元代吉水张文先创白沙书院,“教其族里俊秀子弟”(注:刘岳申:《白沙书院记》,《申斋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不少书院本为家塾,后来扩大规模,变为书院,成为宗族子弟与乡里子弟共同的就学场所。如元代庐陵万安县刘氏“赀甲一乡”,“乃设塾延师,凡党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许来学”,后扩大规模,扁曰“儒林义塾”(注:吴澄:《儒林义塾记》,《吴文正集》卷四十一,《四库全书》本。)。元代至正间新乐县赵氏璧里书院,“赵氏兄弟作之以晦来学者也”。最初,其父母“延师以教其子,久之,乡邻从学者众,黉舍至不能容,始捐家赀修建书院”(注:苏天爵:《新乐县璧里书院记》,《滋溪文稿》卷三。),历时三年多建成。明代四川丰都平山书院,本为丰都人杨孟英家塾,后来杨氏改建为书院,以“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之子弟诵读其间,翘翘焉相继而兴。”(注:王守仁:《平山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学校志》。)琳达·沃尔顿(Walton Linda A.)对南宋时期书院的研究表明,在当时家塾转变成为家族书院,并非个别而是颇为常见的现象。(注:Linda A.Walton,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PP.126-149.)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也指出,元代“以教育宗族和乡里子弟为目的所建的书院,大多数由私塾和义塾发展而来。”(注: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也有一些家族书院是主要面向外族子弟的,如元代山东巴约特氏建历山书院,“聚书割田,继以廪粟,以曹人范秀为之师,其子弟与乡邻凡愿学者皆集。”(注:程文海:《历山书院记》,《雪楼集》卷十二,《四库全书》本。)明代山西路仇氏,四世同居,“兴建义学于其舍旁,以教乡之子弟者盖五六十家矣。犹以为未也,乃于雄山之东巅建书院焉。”(注:吕柟:《东山书院记略》,山西《长治县志》卷二,光绪二十年刊本。)
由于不同家族具体情况互有差异,家族书院的规模、档次、影响也各不相同。受经济实力的限制,一些家族书院规模有限,规制也不一定完整。如元至正年间建于吴郡的文公书院,乃由范仲淹祠改建而成,且不设教官、不任命山长,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当时范氏家族“仰食于义廪,食指几千余,使建书院,则官除山长,有山长则有禀稍之奉矣。今藐焉义禀不自给,使但建书院以祀公,慎选族人之贤者充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长则乞免矣。”(注:郑元祐:《文正书院记》,《侨吴集》卷九,《四库全书》本。)许多家族书院往往仅房舍数间,生徒数十人而已。但也有不少规模较大、规制较为完备的家族书院。唐宋之际的一些著名的家族书院,如江州的陈氏东佳书堂有“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五代范阳窦氏书院有房屋“四十间,聚书数千卷”。洪州胡氏华林书堂“筑室百区,聚书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从学者数千人”。这些书院,房舍面积、藏书数量、从学人数都已相当可观,其中的东佳书院已有固定的学田作为经济保障,胡氏华林书堂在宋淳化间得到皇帝旌表并有自相司空而下三十余人作诗夸赞其事,其社会影响可以想见。家族书院的这种规模与影响,在书院发展早期无疑是非常引人瞩目的。
后来许多家族书院规模也相当可观。宋代大家族崔氏所办的盱山书院“规模甚巨,会讲有堂,肄业有舍,休宿有室。廊庑之宽,门庭之严,疱湢之备”,“希易既自以身教之,次有堂长、学长、斋长诸职”(注:包恢:《盱山书院记》,《敝帚稿略》卷三,《四库全书》本。),从书院建筑规模、房舍面积、教学生活设施到日常管理,都比较完备,并得到了朱熹所书的“盱山书院”四大字,可见也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元代婺源胡氏明经书院,有屋三百间,有捐田三百五十亩充祭祀及师生廪饩,还有朝廷的赐额,有著名学者吴澄等为之作记,影响也相当大。可以说,这类家庭书院构成了当时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它类型书院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二 家族力量致力于书院教育的动机
家族兴办书院,致力于书院教育,可以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层面考察其动机。本文认为,家族力量致力于书院教育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敦亲睦族。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许多家族数世同堂,数百人同财共爨。如何谐调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保持家族的和睦与融洽,使之长盛不衰,是家族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正如李文治、江太新在谈及唐、宋宗法宗族制的变化与差异时说:“唐代以前门阀贵族等级性的宗法宗族制的持续,依靠国家政权的维护,宋代一般官僚及庶民户类型的宗法宗族制的持续,则靠情理说教。”(注: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5页。)自宋代以后,情理说教已成为维系宗法宗族制度的重要方式。许多家族力图通过尊亲敬祖、孝悌忠信等宗法血缘伦常原则的灌输与教导,增强家族成员的宗法观念与伦常道德意识,使家族成员将宗法观念、人伦原则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以礼相待、和睦相处,从而增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克服由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矛盾所导致的离心倾向,达到“千百年犹一日之亲,千百里犹一父之子”(注:光绪:《石埭桂氏宗谱》卷一,《潘永洛叙》。)的效果。为此,各种家族教化手段纷纷出现、应用。有的进行推心置腹的劝诫和开导,重在晓之以理,以情感人,在这方面有各种道理平易浅近的《家训》等;有的以条文形式对日常生活进行具体规定、限制,如各种族规、《家范》等。当时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即进行人伦道德教育,是敦亲睦族的有效途径:“学然后知礼义孝弟之教。故一子为学则父母有养,一弟为学则兄姊有爱,一家为学则宗族和睦。”(注:《嘉定赤城志》卷三七,《仙居令陈密学襄劝学文》。)自然,家族兴办书院以教育本族子弟也被视为敦亲睦族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点,应该说是家族书院本质的、共同的特点。如五代时江州陈氏家族“合族同处,迨今千人”。陈兖之所以创设东佳书堂,是因为他意识到,为了维持家族的这种和睦共处的繁盛局面,需要施以诗书礼乐之教。“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注:徐锴:《陈氏书堂记》,江西《德安县志》卷三,清同治年间刊本。)。元代巴约特氏兴建历山书院后,历山公“为书与昆弟约,……相与为忠信孝悌之归。又与子侄约,凡胜衣者悉就学,暇日习射御备颜行,曰毋荒毋逸,毋为不善以忝所生也。”(注:程文海:《历山书院记》,《雪楼集》卷十二,《四库全书》本。)所突出强调的是伦常道德观念的规范和践履。
第二,提高本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并从中培养出本族的知识精英,通过科举入仕,提高家族的地位。家族成员的文化知识水平,关系到他们在当地社会公共事业中的组织、参与、处理能力,从而影响着家族的地位与声望。更为重要的是,本家族成员能否出人头地,取得青紫,成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也是关系到家族的地位、荣耀与声望的大事,是衡量家族是否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因为家族成员入仕,不仅可以带来许多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有许多相应的政治特权。家族成员跻身官场,就意味着家族与国家权力处于更加接近、亲和的位置。在专制王权高度膨胀、影响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中,该家族在地方社会就会因此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家族成员在心理上也会很自然地产生某种荣耀感。而在传统中国社会后期,实现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基本途径就是科举。许多家族都希望本族子弟通过读书应考获得功名,踏入官场。吴仁安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的研究中指出,与当时皇族、贵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世袭不同,不仅明清时期望族创始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主要是靠科举入仕方式谋取的,而且其子孙后代也需要继续走读书应考的科举入仕道路来使得簪缨联翩而支撑家门长期不坠,否则,就难以维持望族地位。(注: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5页。)望族著姓如此,寒门细族更是只能寄希望于本族子弟发奋读书,以显亲扬名,光宗耀祖。正因为如此,许多家族对于教育子弟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认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注: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饶州风俗》。)其直接目的多为光大门第。许多家庭兴办书院,为本族子弟创造入仕条件的目的也十分明确。宋淳祐间曲江郭氏所建青云峰书院,以科举为鹄的性质甚浓,以致其主办者请学者欧阳守道撰写书院记时,要求揭示书院之名的主旨:“峰以青云名,决科者以为祥也。……揭斯名也,亦以动策励之心焉。”(注:欧阳守道:《青云峰书院记》,《巽斋集》卷十六。)又如宋代浙江詹氏家族的瀛山书院,其得名也与对科举登弟的向往推崇有关。詹氏筑书院于山巅,合族之子读书其中,“祥符淳熙间第进士十八人,而名骙者居殿试第一,故有取于‘登瀛’之意,而以‘瀛’名之也。”(注:章之鼎:《重葺瀛山书院记》,《瀛山书院志》卷六,道光十六年格致堂本。)正如吴霓在论及家族教育特点时谈到的,科举入仕是家族教育的热点,“就家族教育的整体来看,强调科名,注重入仕是家族教育最主要的目标。”(注:王炳照主编:《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虽然并非所有家族书院的兴办均以科举为鹄的,敦亲睦族是不少家族书院最为重要的根本的使命,但毫无疑问,家族子弟读书应考,科举入仕,显亲扬名、光大门弟是很多家族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向。汪应辰在为贵溪高氏家族的桐源书院作记时,虽然一方面希望“高氏子孙读书于书院,当以古圣贤心学自勉,毋以词章之学自足”,但同时也提到,“他日有此而达于郡邑,上于国学,赫然名闻于四方,则书院不为徒设矣。”(注:汪应辰:《桐源书院记》,《文定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第三,扩大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提升、树立家族形象。家族生活、居住于一定社会区域内,同周边社会息息相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地方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该家族的经济实力、政治文化地位、道德声望,同时也与该家族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相关。许多家族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力图在地方慈善救济活动、教育事业、文化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等方面发挥作用。书院的兴办,也是家族融入地方社会,参与地方公共事业的重要方式。许多家族书院尤其是那些同时面向乡里子弟的家族书院对当地的人才培养、风俗的改善、社会秩序的维护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在陈氏东佳书堂中,“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注:徐锴:《陈氏书堂记》,江西《德安县志》卷三,清同治年间刊本。)元代吉水文昌张文先所创白沙书院,将为天下国家育才作为宗旨:“延名师与族里讲求圣贤之学,将以为天下国家育材。”(43)明代浙江归安朱氏长春书院,其文化辐射作用相当明显:“奉前人之家法规矩而俎豆之,虽其乡邻族党有遗风焉。”(注:唐枢:《重修长春书院记》,《浙江通志》卷二十六,光绪二十五年刊本。)五代范阳窦氏书院实际上已带有某种慈善救济性质:“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需者,公咸为出之。”元代巴约特氏所创的历山书院,不仅为乡邻提供学习机会,“复藏方书,聘定襄周文胜为医师,以待愿学者与乡之求匕剂者。”(注:程文海:《历山书院记》,《雪楼集》卷十二,《四库全书》本。)这就已经直接参与地方的医疗福利事业了。家族书院这些功能与举措,对于扩大家族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获得地方公众认可,提升、树立家族形象,无疑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琳达·沃尔顿(Wslton Linda A.)在研究南宋书院与社会关系时指出:“建立一个向士人社会开放的书院,是一个家庭提高自身声望,表明其对于地方精英身份诉求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文化与社会资本的投资,以财产来交换地位。”(注:Linda A.Walton,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PP.122.)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