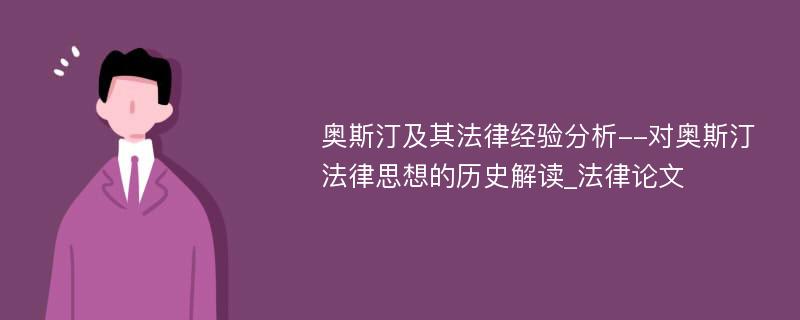
奥斯丁及其实证分析法学——奥斯丁法学思想的历史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学论文,奥斯丁论文,实证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790-1859),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法律哲学家,又被尊称为“现代法理学之父”,其思想独树一帜,开创分析法学一派,影响巨大。本文拟从历史的视角,解读奥斯丁法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对当前的法理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奥斯丁的思想简介
奥斯丁一生著述不多,代表作主要有两部;1832年出版的《法理学范围之确立(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逝世两年后即1861年出版的《法理学讲义(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其思想核心有以下几点:
(一)法律命令说
奥斯丁认为,“每项实在法都由一位主权者或一个由人们组成的享有主权的机构制定,并且是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社会中某一成员或许多成员而制定”,法律是主权者(Sovereign)的一种命令(Command)。
“命令”是奥斯丁关于法律定义的核心。所谓“命令”是指一个理性的人怀有的愿望或希望,而另一个理性的人应该由此去做某件事或被禁止去做某件事;若后者不顺从,前者将对其实施一种恶或不便利;该希望通过语言等标志宣告或表达出来。立法者确立一种或一类行为、一般和无限种类的禁止行为,具有一般特征的违法就要受到惩罚含义的命令,就是一种法律或规则。
主权者和法律制裁是奥斯丁法律定义的两个基本要素。所谓主权指政治优势者对劣势者的关系。优势即强权,是以恶或痛苦施诸他人的权力,及通过他人对恶的恐惧来强制他们按照本人的希望去行为的权力。法律和其他命令来源于“优势者”,而约束或强制“劣势者”。所谓法律制裁是对不服从者以刑罚方式出现的法律责任。
(二)实在道德论
实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又称实在道德的规则或实在道德规则,指非由政治优势者建立,但具有法律能力或特点的法。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仅由观念建立或实施,例如,荣誉法、风尚之法和国际法等。有两种意义的实在道德,即严格意义法律的实在道德和非严格意义法律的实在道德。
严格意义法律的实在道德不是由政治上优势者设定,也非由实施法律权利的私人设定,而是人对人设定的命令性的规则。尽管它由“确定”的个人或团体确立,但不具有明确的法律制裁,因而不是实在法。非严格意义法律的实在道德,是由“一般观念(General Opinion)”设立或设定的法律,也即由任何阶层或任何人类社会的一般观念设定的法律。其本质在于:它不是明示或默示地发布的命令,仅仅是就某种行为,一个“非明确团体”或一个明确当事人持有或感受的“观念”或“感情”。例如,某个职业团体,一个民族或独立的政治社会,及由诸个民族形成的较大社会的一种观念。
(三)法律学范围之确立
通过对法律与实在道德的定义和分析,奥斯丁认为,在二者实然或应然的问题上,涉及到:(1)实在法与立法科学的混淆;(2)实在法与实在道德的混淆,以及二者与立法和伦理学的混淆。为澄清这一混乱,奥斯丁明确划分法理学与伦理科学之间的理论界限,认为,“法理学科学所关注的乃是实在法,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不考虑法律的善或恶”;对法律应当是什么的研究则属于立法学,而立法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针对当时“法理学”一词词义的模糊性,奥斯丁将其分为“一般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和“特殊法理学(Particular Jurisp-rudence)”。一般法理学,又可称为“比较法理学(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或“实在法哲学(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是对存在的各法律体系制度中的共同原则、概念、特征等进行抽象、分析和阐释。特殊法理学则是研究一个任何实际法律体系或其任何一部分的科学,是关于一个具体法律体系的“法律的知识”及其适用艺术,例如对罗马法的研究。奥斯丁认为,虽然法律的每种体系有它特殊的和不同的性质,但在各种体系中存在其共通的原则、概念和特征;这些共通的原则中有很多对所有体系——简陋社会的贫乏的和粗糙的体系及文雅的公社的丰富的和成熟的体系——是共通的。因此,奥斯丁认为所谓“法理学”应是对一般法理学的研究。
奥斯丁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观点,坚持将法理学的研究局限于实在法的范围之内实证分析方法,深入研究罗马法、英国法及德国法等,分析出六项法律的共通原则:(1)义务、权利、自由、伤害、惩罚、赔偿的概念与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及它们与法律、主权和政治社会间的各种关系;(2)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理解不适当而作出相反解释的区别;(3)权利的特征;(4)权利的限制;(5)责任的特征;(6)损害和不法行为的特征。奥斯丁的这种实证式的分析方法,开分析法学之先河,使法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因此,奥斯丁亦被视为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注:参见徐爱国:《奥斯丁和他的分析法学》,载《法律史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09-642页;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7-106页;《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525页。)
二、奥斯丁法学思想与其历史背景
(一)社会背景
奥斯丁生于1790年,卒于1859年,主要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这段时期正是资本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巩固、上升时期。经济上,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于19世纪20、30年代基本完成。政治上,英国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已经大体建立,并于1793年参加反法同盟。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出现经济大萧条,阶级矛盾尖锐化,发生了1832年议会改革等一系列运动,使得英国的政党制度、政府结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显著的发展并趋于成熟,并出现了一批为成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辩护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家。从奥斯丁强调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不难看出,奥斯丁顺应了当时社会的政治需求,以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的新生制度和秩序。
(二)思想文化背景
工业革命的进行,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方面一系列的伟大发现,促使人们将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仔细观察经验事实与感觉材料和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与此相呼应,在法律领域里,出现了对古典自然法学的反动,反对传统的、散乱的,依附于神学、道德学的不确定之法的运动。1750年至1850年间的100年恰好是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政治和法律秩序的实施时期,当时正在实现战略设想通过立法手段重建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一种新范式。(注:[葡]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19世纪初,以法、德等国为首的法典编撰运动方兴未艾,冲击着有古老判例法传统的英国。当时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判例,法律杂乱无章、模糊不清,不利于法律秩序的建立。奥斯丁之前,就有杰瑞米·边沁重视实在法,极力主张法律改革,进行法典编撰。
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功利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斯丁极为推崇边沁,是边沁的忠实信徒。边沁提出了法律的功利原则,认为人的本性在于求乐避苦,法律源于人的这一本性,其目的在于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同时,边沁认为,法是一国主权者意志的宣示、表明的集合(Anassemblage of signs,declaratory or a volition conceived oradopted by the sovereign in a state),对法律应当“严正地服从、自由地批判”。奥斯丁关于法的定义在实质上与边沁的定义一脉相承,并来源于后者。20世纪70年代,哈特(H·L·HART)教授发现边沁的《法律概要》一书,此书即为对一个法律体系特征和结构的定义和分类研究。可见,奥斯丁对边沁思想的因袭。
值得一提的是,奥斯丁的分析实证的方法论思想,亦有其独特的哲学背景。英国自17世纪以来就有着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以贝克莱、休谟为代表,主张“存在即感知”,“物为观念的集合”。奥斯丁认为法理学乃是关注实在法的科学的思想,即是对英国传统经验主义哲学的承继和新利用。与此同时,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英法两国哲学界和整个科学界出现了一股实证主义哲学运动。实证主义哲学家强烈反对行而上学,把自己严格限制与经验的观察,排除价值考虑,主张“中立哲学”。这种哲学渗透了所有的科学领域,对法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李龙主编:《西方法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三、奥斯丁的法学思想与其人生经历
奥斯丁1790年生于英国福萨克的克雷丁密尔的一个磨坊主家庭。1806年,年轻的奥斯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官。这5年的军官生涯对奥斯丁的性格和脾性留有深刻的痕迹。终其一生,奥斯丁都对军人性格抱有深深的同情和尊敬。(注:See Sarah Austin,'Preface'in
Lecture on Jurisprudence,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3.)。而对权威和纪律的尊重和服从是一个士兵的天职。可以说,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的提出并非偶然,与他的一段军旅生活有必然的联系。
退伍后,奥斯丁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开业律师,并在大法官法庭实习,广泛接触了纷繁复杂的英国法律。然而,奥斯丁不仅身体上无法负荷这项工作,而且他的思想结构、他的高度敏感性格更使得他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注:See Sarah Austin,'Preface'in Lecture on
Jurisprudence,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4.)在此期间,新婚的奥斯丁夫妇在伦敦的皇后广场定居下来,与边沁为邻。奥斯丁师从边沁、密尔,成为功利主义思想者。
1826年,奥斯丁被任命为伦敦大学的第一位法理学教授,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之前,奥斯丁曾去德国,并考察了德国大学的法学教育及法律科学的情况,为后者思辩式的教育和研究方法所吸引。当时,历史法学派在德国为主流,以古罗马《学说汇纂》作为历史基础,重视概念的分析、阐述,注重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注重研究其法律体系的历史基础,大学教育明显区别于英国的注重法律实际技巧的判例教育方法。奥斯丁认为,应比较研究各国法律,从中抽象出法律的一般原则;英国大学生掌握了这些基本的共通原则,即可理解外国法律体系。这也许就是奥斯丁法学研究的思想起点。
法理学当时是新开辟的一门学科,其范围、内容等均不明确。而一个学科的建立,需要明确具体的研究对象,否则,与其他学科无法区别,不成其为独立的科学。当时的法理学即处于与伦理学、政法学、哲学等尚未完全分离的混沌状态,对“法理学”本身的理解就莫衷一是。因此,奥斯丁的首要工作就是澄清法理学的范围,确定法理学的研究领域。他深切认识到法律与道德边界的清晰观念对于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并抱有以己为媒介将观念传输给大众而在英国造成一定影响的想法。据此,奥斯丁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区分实在法与实在道德,摒弃了对法律的道德评价内容,将法理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使法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可以说,奥斯丁的教学生涯真正形成了他的分析法学思想,若无此经历,奥斯丁也许难以突破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而开创分析法学派。
奥斯丁身材瘦高、灰色头发、皮肤苍白,一双大眼渴求真知却又露出些许胆怯,但讲话铿锵有力。(注:See W·L·Morison,'Introduction',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by John Austin edited by David Compbell and Philip Thomas Dar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8)P9.)尽管奥斯丁对这门新兴学科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责任,但因授课过于艰深而不实用,听课学生越来越少,最终于1832年被迫放弃教学。也是在这一年《法理学范围之确立》一书正式出版。1833年以后,奥斯丁曾担任英国刑法委员会委员、英国驻马耳他特使等职,进入具体法律领域的研究。然而,终其一生,糟糕的身体状况一直影响着他的法学研究。
即使在一个为科学本身而进行研究的国度,也不能期望对实际生活无直接影响的研究能够吸引众多的听众,更何况当时绝大部分的英国法律系学生将他们的职业仅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因而奥斯丁曾感叹说:“我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我应当是一名12世纪的学者,或者一名德国教授。”(注:See Sarah Austin,'Preface'in Lecture onJurisprudence,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12.)然而,奥斯丁在其生前虽未获得应得的荣誉,但其思想在他身后却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和研究,他的思想也获得了继承和扬弃。
四、奥斯丁法学思想的解读
奥斯丁的思想扭转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单一的价值论研究方向,使法学研究从古典自然法学的不确定状态中解脱出来,变为明确实在的法理学实证分析研究。它流行了近一个世纪,20世纪法理学从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到现在的后现代法学,可以看成是围绕着如何理解法律实践与政治、道德等其他各种实践的关系这一问题设定而展开的。同时,奥斯丁的理论已成为英国法学中法理学教育的基础。(注:[日]中山龙一著,周永胜译:《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载《外国法译评》,2001年第3期。)
中世纪以后,法学从神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并未形成独立自足的体系,仍受政治学、伦理学的左右。奥斯丁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法学与伦理学彻底分离,使其成为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科学体系。奥斯丁对法律本身精确的描述和分析为以后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秩序是人类法律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奥斯丁以国家权力(法律命令说)为着眼点,构建国家法律秩序的结构体系。这种思想对于任何国家均是有益和有利的,尤其对于刚刚建立、正在建设的国家而言。因此说,“奥斯丁的理论是19世纪所特有的英国理论。……什么人掌握国家的权力,他利用国家权力干了什么事,这些是在所有一切历史时期都须探究的问题。但是像奥斯丁那样以这类问题为法理学唯一正当的探究,只显示出一种信念,即资产阶级业已具备掌握权力并确立其对法律秩序的要求的能力。……倡导了全球第一场产业革命的那个阶级,其权力和一致性已确定无疑。法理哲学因此便注重于权力结构的问题。”(注:[美]泰格、利维著,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后来的法学实证论者的态度已不再那么僵硬。凯尔森继承奥斯丁的思想,彻底排除一切外在于法律的因素,试图建立“纯粹”的法律科学,但也已经考虑到,一种法律意识形态可能会由于公众对君主的命令冷漠而终止其为“法律”。新分析实证法学的哈特则明确反对奥斯丁关于法律的定义,认为奥斯丁命令说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用于构造这一学说的因素,即命令、服从、威胁的观念,均因缺少“规则”的概念而不能阐明任何法律,并提出了“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
因此,由法律命令说自然推导出的“恶法亦法”的结论,二战以来受到了各派的攻击,奥斯丁的法学理论也因此遭批评的场合居多。实际上,奥斯丁并不否认对实在法进行一定标准的评价,他的标准就是功利原则;也非不关切法律意识形态的变化,只是在法律学任务的问题上,认为法理学就是研究实在的制定法,将法律规章和其他种类的命令和要求划分开来。虽然奥斯丁将对法的价值追求外科手术式地切割出法理学的研究,但他并未丧失对他所摒除课题的兴趣。奥斯丁更像是一个管家,试图通过将一些东西送给邻居的办法来清理房屋,然后又不时地拜访邻居去看一看他先前抛弃的东西。奥斯丁认为背离或违背正义的实在法是非正义的,并且他也乐意承认在神法与人法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具有反抗的道德权利。奥斯丁将恶法纳入法律体系,能帮助我们看到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将对恶法的救济引入法律内部,促使法律依照功利原则向善。他在形式上、实质上对恶法客观存在的法律性的承认,有利于法律的自我救济、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而古典自然法学派主张“恶法非法”,使我们对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视而不见,也导致人们在现实遭受恶法压迫的同时,只能求助于不确定、无形的“自然法”。这种思想虽然在社会改革阶段有推动作用,但也往往带来混乱和无序。由于奥斯丁所处的历史时期客观上的迫切要求是社会的有序性,尽管他所采取的方法颇为极端,但其思想的起点却与历史要求相暗合。
事实上,对法律本身结构体系的研究和对法律的价值探求对法律的发展同样是缺一不可的。人类法律经过漫长的发展,其独特的特质伴随着社会的演进亦日趋显现,体系也日趋完整和详尽。奥斯丁扎根于现实的法律土壤,剖析其自身的逻辑结构和体系,可谓法学大厦的首位建筑师。但对秩序、正义、平等、公正等法律价值的探究是人类永恒的理想追求。法学研究丧失这一点,犹如一个没有理想追求的人,只是无意义的客观存在而已。因此,17、18世纪的哲学把人类的智慧分析得过于精细,把人类的理智发展到近于神经过敏的地步,以至人类思想自然而然地趋向于怀疑主义的途径。(注: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5页。)社会法学、新自然法学等由此产生。而真正健全的法理学则是二者的有机、互动的结合。
作为一种方法工具,奥斯丁的实证分析,是建立和发展一国法学理论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之一。实证分析,是西方自古罗马以来重逻辑精神的体现,对现代西方高精密度与思辩性相结合的法学系统的形成有重大作用。这对我国法理学的发展也是一大启示。我国发达的律学和法律实用主义的传统使得我国的法学也较为注重实在的制定法,但这种影响更多的体现在具体的部门法学当中。在法理学的领域内,研究者对法律终极价值的关怀重于对法律结构体系的建设;对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的借鉴多于实证分析方法的运用。学术争鸣热烈,但许多是基于对基本概念的歧异理解上的。因此,引进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于增强我国法学的发展基础,完善我国法理学研究体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阳光的另一面即为阴影。奥斯丁的根本性错误在于,他将法律和国家权力实物化了,这显然是为求更准确地描述它们,但由于实物化这一做法本身会融合到对法律的了解之中,所以最终所得乃是扭曲了的法律描述。(注:[美]泰格、利维著,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法律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且受多种外在社会因素的作用,奥斯丁决断式的定义与法律的多样现实常常存在抵触。社会法学、经济分析法学等新法理学派就是对这一缺陷的弥补研究。
历史总是呈螺旋状向前发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跨学科法律研究,对法律有这样一种结构主义的关怀,即意图描述法律的内在逻辑或“结构”。像19世纪的理论形式主义者试图描述法律的“本质”或在“真实”的分类一样,当代的法律学者们在以非法律的方法确定法律的结构时,似乎提出了一份类似的形式主义议程。而在美国,后现代法理学新的运动,已经向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法律是区别与政治学和道德哲学的独立学科——发起了挑战;一个表明多样性和文化的话语,多元文化主义,也在挑战着现代法理学中普适的概念和观念的地位和尊严。(注:郑强:《美国后现代法理学概观》,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2期。)这种法律话语的扩散现象在我国当前法学界亦初露端倪,但扩散式的法理学则侧重于微观、局部的分析,而非对法律的整体的解释,不利于我国新时期法学的系统发展。因此,在对动态的法学研究之外,奥斯丁式的整体分析思路仍有利用的必要。
无论如何,“……一种法律应该不断扪心自问,正如一个社会的生存只能建立在它对自身及其制度所进行的研究之上一样”。(注:[法]迪迪埃·埃里蓬著,谢强、马月译:《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页。)
标签:法律论文; 法理学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奥斯丁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法律学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边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