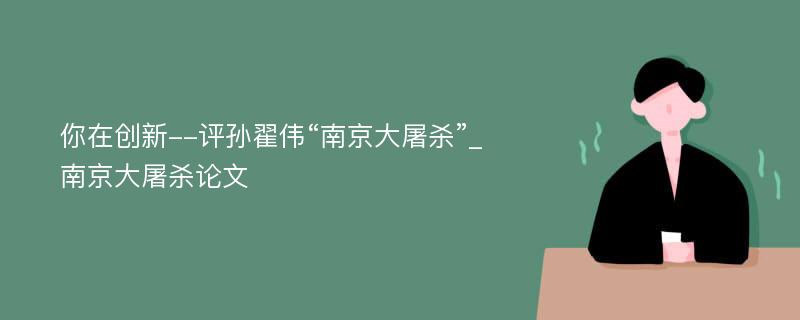
贵在创新——评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大屠杀论文,评孙宅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60周年之际,我高兴地读到由孙宅巍主编的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最新学术专著《南京大屠杀》。该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10章45节,计50余万字。著者运用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丰富的历史档案和口碑资料,论述了30万南京同胞惨遭日军屠杀的确凿史实,有力驳斥了极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翻历史定案的谬论,论述了南京大屠杀的背景、范畴、内容和历史影响。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日益重视,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其中主要著作有: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自印);高兴祖著《日本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徐志耕著《南京大屠杀》(1987年昆仑出版社出版);胡菊蓉著《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198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孙宅巍著《1937南京悲歌》(1995年台湾先智出版公司出版);陈辽著《南京大屠杀真相》(1995年香港昆仑制作公司出版);章开沅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199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孙宅巍主编的新著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了这些研究成果的营养,但是又没有简单汇辑、重复别人的成果。该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创新。全书从观点到资料、结构,都突出了一个“新”字,给人以强烈的清新的感觉。
一 新的观点
关于30万以上南京同胞被屠杀问题。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其焦点便是被屠杀的人数。他们或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或以一个极小的被屠杀人数,混淆视听。该书运用两种方法,相辅相成,科学地计算出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人数,确如当年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出的“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的认定。其两种方法:一是举出千人以上的屠杀10起,遇害人数为19.5万人;3个较大慈善团体在上述10 起集体屠杀地点之外共收埋分散屠杀尸体7.7万具。以上两项合计已达27.2万人。 二是对分类人员埋尸的数字进行统计、归纳,共有慈善团体收尸18.5万余具,市民私人收埋3.5万余具,伪政权收尸7400余具,日军焚尸灭迹15万具, 简单相加为37.7万余具(实际应扣除交叉部分)。对于遇难同胞人数的讨论,著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写道:
死难同胞的人数,受到各种档案资料记载、当时的环境条件,尤其是南京沦陷前夕人口数的制约,把它估计少了或者估计多了,都会出现逻辑上的混乱和矛盾。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即:一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任意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二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大规模地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数字,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当然是可以讨论的。(该书第9—10页)
我以为,这种冷静与客观的本身,便是一种创新。
关于屠杀前的南京人口。日本少数右翼分子,为了推翻30万南京同胞惨遭屠杀的事实,在屠杀前的南京人口问题上大作文章,甚至不惜歪曲史实,将当时的南京人口缩小为25万人。以往有关论著在论及沦陷时的南京人口时,多将目光只集中于常住人口的变化上,而忽略了其他的人口因素。该书根据当时南京市政府的人口统计资料和国民政府的军史资料,采用新的统计办法,将沦陷前的南京人口分为常住人口、滞留军人和流动人口三部分。著者写道:
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除了和平的居民外,还包含了已经放下武器的军人……因此,在考察沦陷前夕南京人口数时,必须把守城官兵的人数考虑在内……除此而外,还有为数众多、滞留南京的流动人口,其中包括从上海、苏州、无锡等沦陷区陆续逃至南京的难民,以及前方不断运来南京的伤员。(该书第514—516页)
该书认为:当时南京除大批逃难者外,常住人口仍有50余万人,守城军人除战死及安全撤离者外,还滞留有9万人左右,此外, 还有逃难滞留至此的流动人口数万人,总数应在60万人以上。这使日本侵略军完全有可能在南京这片土地上,对30万以上无辜人民进行罪恶屠杀。该书对沦陷前夕南京人口的分析和论断,较为科学和准确地向人们揭示了南京的人口状况,也更加有力地戳穿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在南京人口问题上制造的谎言。
关于大屠杀的时空范畴。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件怵目惊心的重大历史事件,自应有其起迄时间与涵盖范围。对这一事件时空范围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遇难同胞人数的统计。以往史学界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在具体表述上也多少有些混乱。该书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一般说来,系指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之日起的6 个星期左右时间。严格说来,它开始的时间,比城陷之日要早,早在攻陷南京的日军临近南京时,即12月上旬,在其郊县即已大量发生屠杀等暴行;其下限,则可延伸到1938年二三月份。大屠杀的地域范围,一般说来,应以当时南京市政府管辖的12个行政区为限。但是,考虑到暴行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方面的因素,位于南京周围的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等县,也应包括在内。这一时空范畴的界定,为进一步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迈出了新的一步。
关于“安全区”国防委员会。以往有些论著中,过分强调了“安全区不安全”这一面。其实,在任何情况下,安全与不安全都是相对的。在战争环境下,在强暴的民族敌人的铁蹄之下,本来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该书全面、公正地估价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在肯定“安全区”内仍发生了不少捕杀事件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国际委员会在保障难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供给和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著者写道:
国际委员会的努力,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军暴行。总的说来,日军残暴成性,国际委员会没有能够完全阻止日军在安全区滥施暴行。但是,由于国际委员会的干预和牵制,使他们不能不多少有些顾忌,因此在安全区内的暴行,相对安全区以外要轻些,拿安全区与非安全区相比,难民们确实多了一层保障,少了一份侵害。(该书第498页)
该书认为,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短暂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西方人民共同为维护人类尊严和人类正义而作出的努力和奉献”。
关于南京军民的反抗。以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著中,往往对于南京军民对屠杀的反抗反映不够充分,以致使人们误认为当时南京人民面对日军凶残的屠杀完全没有进行反抗。该书对南京大屠杀中屠杀与反抗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即“屠杀与反抗同在,屈辱与光荣并存”。著者就此写道:
这是同一历史事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任意缩小其中一个方面的影响,甚至抹去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都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该书第24页)
该书对于城陷后的巷战与战斗、屠杀中的抗争、惨案后的持续斗争都列有专节叙述。著者针对有些人担心论述了南京军民的抗争会不会“授人以柄”的问题,毫不含糊地认为:
承认这种抗争,丝毫也不影响对于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声讨。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管这种抗击激烈到什么程度,都是中国人民正当的权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中国国土上来,不管遭到多么沉重的打击和损失,都不能掩盖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宣扬这种抗争,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 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该书第24页)
该书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屠杀与反抗关系的辩证阐述,是较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
二 新的资料
该书主编孙宅巍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有长期的积累,三位副主编陈娟、胡菊蓉、段月萍,分别任职于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因而他们在占有资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经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各方面的资料约1040余条,其中引用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以及近年来德国、美国国家档案馆披露的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约380条, 引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幸存者、见证人的证言资料约130条。上述引用档案、口碑资料, 有些尚属首次披露,为今后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鲜的信息。据笔者所知,在同一本学术著作中,引用如此众多的原始档案、口碑资料,在迄今已经出版的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中,恐怕还是第一次。
90年代初,刚刚公布的德国国家档案馆中珍藏的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许多国内外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专著还未及对其充分利用,该书则已将其充分吸收消化,分别运用到关于日军暴行预谋、屠杀、奸淫、纵火、抢劫的描述中。如该书引用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致外交部的秘密报告:
水塘前有两个端着步枪的日本兵,他们根据站在他们后边军官的命令开枪射击,直至这个人倒下……
部队始终是其军官的写照。一个以政治谋杀而闻名于世的青年军官团要求它的属下所做的无非是南京所发生的一切。(该书第99页)
这种来自日本盟国的德国方面的资料,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绝非士兵们偶然无纪律行为所致,而是士兵们根据军官的命令,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的。该书还引用了来自德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件外交文书,其中列举了南京东郊在1938年一二月间遭日军杀害的46名遇难者名单,并附有遇害日期和遇难者的年龄。在一份前期档案资料中,一连列出46名遇难者名单的情况,尚不多见;同时,著者又利用这份外交文书提供的信息,印证了幸存者陈光秀老人的证言,使对日军在南京东郊一带屠杀暴行的揭露更为确凿无疑。此外,该书还引用来自德国国家档案馆的多条资料,证明了日军在南京强奸、纵火、抢劫的暴行,进一步充实了日军对南京居民施以各种暴行的记录,以致德国外交官员称:“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这样的结论,出自一名德国外交官的口中,更增加了对侵华日军暴行证实和谴责的份量。
1994年9月9日,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了1934年7月至1938 年7月间的3000余份日本外交文件, 经著名历史学家吴天威教授将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6件资料翻译发表。该书采用了这一最新资料, 加强了对日军屠杀人数的论证。该书还引用了日本广田外相于1938年1月17 日转发给驻美大使馆的一份题为“特别消息”的上海第176号电。 该项“特别消息”内称:
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的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睹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attila)及其匈奴人。不少于三十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该书第436页)
著者在引用这条重要的资料后,指出:该项“特别消息”“由外相广田转发给日本驻外使馆参考用,足见其内容已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电文所述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已屠杀‘不少于三十万的中国平民’,且强调此系‘据可靠的目睹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该书第436页)在这里, 著者并没有仅仅依据这一条资料来认定南京大屠杀30万人遇难的规模,而是谨慎地认为:“这应当成为今日史界研究南京大屠杀规模的重要佐证。”我觉得,这反映了作者对史学研究的严肃态度。
同样是在1994年刚刚公布的满铁档案中一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该书中也被多处运用,为有关收埋尸体和南京沦陷后的社会组织的论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红卍字会是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收埋尸体的一家重要慈善机构。仅这一家机构,就收埋了4.3万余具尸体。 红卍字会收埋尸体的记录本身,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有力证据。以往史学界在论述红卍字会的埋尸活动时,主要依据中国方面保存的红卍字会埋尸统计表和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关于红卍字会埋尸活动的报道。现在该书中又根据满铁的有关档案资料,引用了日本特务机关内部的极密报告。报告称,至1938年3月15 日红卍字会已在城内埋尸1793具,在城外埋尸29998具。 该书写道:日本特务机关的报告“再次肯定了红卍字会在城内埋尸的数字为1793具,这与前述红卍字会本身的统计表及《大阪朝日新闻》的报道都完全一致;同时,它关于红卍字会截至3月15日止,在城外共埋尸29998具的说法,也与红卍字会本身的统计数35099具比较接近。” (该书第401—402页)此外,该书援引日本特务机关的报告,还在“伪自治委员会”一节中,大量介绍了在伪自治委员会控制下,南京市行政区划的构成及各区的人口数字。这类新资料的运用,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南京社会情况,大有助益。
该书还从一些基层单位挖掘到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新资料。这些首次披露的资料,可以进一步证实并校正南京大屠杀的某些情节。例如在煤炭港集体屠杀中,以往论著中有引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关于“首都电厂工人许江生等四十五人”遇难的判词。著者从当年首都电厂“死难工人纪念碑”上搜寻到45名死难工人的姓名,又从今南京下关发电厂保存的《扬子电气公司首都电厂人口伤亡调查表》中查得45名遇难工人的姓名。两相对照,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当年首都电厂确有45名工人惨遭日军屠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由于两份名单中均不见“许江生”的名字,著者经过细心考证,认为:“许江生”可能是另一名死难工人“徐京生”之误,“今后在简述首都电厂工人遇难人数时,似不宜再以‘许江生等45人’来表述”。(该书第120 页)虽然上述事实只是南京大屠杀中一个较小的情节,但该书著者认真挖掘,精心考证,增加了全书所引资料及论述的可信度。
三 新的结构
该书在综合考察南京屠杀事件全貌的基础上构筑了全书新的结构。
加强了背景部分的论述。该书系统回顾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从淞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的史实。因为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日本侵略战争发展的必然。要论述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对历史背景的介绍,就不能只是一般的铺垫,而必须交待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该书绪论中写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简单说来,就是日本的侵略、暴行和中国军民的抵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格局和环境之下,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该书第2 页)著者正是按照这一认识和思路,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自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以来60多年对中国武装侵略、施暴人民的历程,以及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和斗争。该书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疯狂性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是南京大屠杀得以发生的“基本原因”。(该书第10页)
用新的条块来论述屠杀暴行的基本事实。以往论著一般都按集体屠杀与分散屠杀两个部分来介绍日军的屠杀暴行。该书将其分成长江边、西部、南部、东部和安全区几大块,使论述的条理更加清楚。读过全书,我感到著者采用这种新的论述方法,确是匠心独具。因为所谓集体屠杀与分散屠杀,本来就没有一个公认的区划标准,在划分上不易掌握;同时,按块块论述,也可以避免将同一个地区的屠杀事件拆散,前后互相交叉,地区不断重复。“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一章,在全书10章中,占有1/4的文字量,地位举足轻重,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这一章论述格局的改变,使全书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
增加了对南京社会组织和人口变化的研究。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南京沦陷、日伪统治和存在着一个中立的“安全区”的特定情况下,因此对于这一悲惨事件发生时社会组织,包括伪自治会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等的论述,无疑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南京大屠杀发生过程中实施和制约的社会条件。南京人口的变化,如前所述,直接关系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也是国际上争论的焦点之一。“社会组织与人口”一章的设立,使人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观察和认识更具有立体感。
列出纪念专章。该书明显地增加了一项内容,即列出专门章节介绍纪念馆、纪念碑的建立,对幸存者、见证者的调查,以及人们对遇难同胞凭吊与祭奠的情况。“永久的纪念”一章,超越了南京大屠杀本身的历史时期,甚至也超越了对南京大屠杀案犯审判的历史时期。用这一章来作为全书的结尾,起到了缅怀死者、告诫后人的作用。
我在对该书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感到它还有些不足之处。例如:部分外国人名的翻译不够规范,“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H.D.Rabe,目前通行的中文译名为“拉贝”,而该书却仍运用了抗战时期出版物中的译名“雷伯”。在当今《拉贝日记》已产生全球轰动效应的情况下,陈旧的、不规范的译名,给读者带来了不便。再如:该书既按序列为10章,在正文中“第十章”前,却又注明该章为“附录”,这样处理似不合通常的编辑体例,是“附录”就不应按序列章,按序列章了就不应称为“附录”。又如:某些地域的划分似不准确,将发生在清凉山的屠杀列入“安全区”屠杀的范畴就是一例。另外,由于该书是多人执笔,各章行文风格不够一致,少数资料有重复引用,少数翻译人名有前后不一的现象。当然,在一部洋洋50万言的巨著中,出现上述问题,在所难免。相信著者在该书再版时,定能将其妥善处理,使该书的内容、风格更臻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