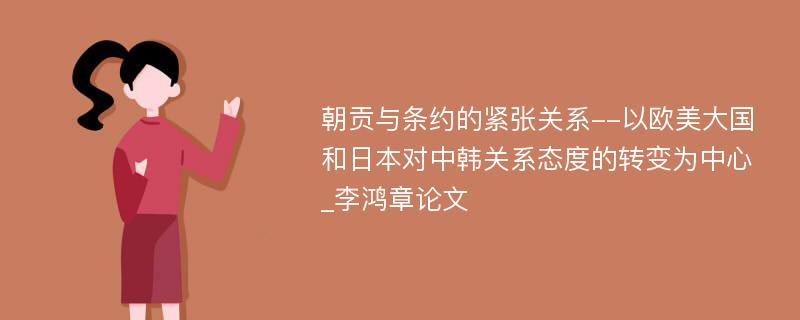
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列强论文,日本论文,条约论文,中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3)06-0001-12
一、前言
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tension),可以说是与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始终相伴,构成了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下则是理解与诠释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视角。韩国学者金容九就曾指出,朝鲜王朝末期的外交史便是“充分体现事大秩序与公法秩序相互冲突之各种特征的历史。”①日本学者冈本隆司也曾指出,“西方近代的国际关系和东亚传统的、具体说来就是清朝和朝鲜的宗属关系一大体上来看,19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史是以二者互相关联的‘并存’为主轴展开的。”②与此相关,笔者也曾指出东亚世界的近代化实际上包括如下的三个不同层面,一是全球(global)层面的近代化,即东亚地区以及东亚各国与东亚区域以外世界及各国(以欧美列强为代表)关系的近代化,二是东亚区域(regional)层面的近代化,即东亚地区秩序的近代化,三是东亚各国国内(national)层面的近代化。③
具体到19世纪末的中韩关系的近代化过程而言,实际上也包含着内外两个方面的不同内容。在外部方面,表现为以欧洲列强以及明治日本所主张与坚持的条约关系对中韩两国传统朝贡关系的挑战、冲击乃至最终取而代之的过程,在内部方面则是中韩两国在上述冲击与刺激下各自试图改变传统双边关系模式的努力,其中既有清政府从所谓“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的对外关系新模式来对朝鲜采取“政经分离”方式的政策变化④,也有朝鲜高宗政府在俞吉浚所谓“两截体制”⑤的框架下试图突破朝贡关系的限制而寻求更多国际空间与对外主权的努力。上述内外两个方面的内容相互关联、互动、影响,构成了19世纪末中韩关系由朝贡而条约之近代转型过程的真实历史图景。
仅就目前中、韩及日本、欧美等国学界的研究现状而言,基于有关上述外部方面内容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远远超过了基于上述内部方面内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对近代中韩关系史的深入研究,因为正如有关亚洲近代化的研究首先要从亚洲内部的视角来进行⑥、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首先要从中国内部的视角来进行⑦一样,有关近代中韩关系史的研究当然也应强调“内部的取向(internal approach)”,即应当将近代中韩关系史本身当做一个独立和自律地变化的历史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⑧本文的研究着眼于19世纪末欧美列强及明治日本对中韩传统关系的态度变化,尽管在其内容上仍是基于上述外部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在问题意识上却试图结合上述内部方面内容,以期进一步促进有关19世纪末中韩关系近代转型过程的深入研究。
二、武力的冲击:丙寅洋扰与辛未洋扰时期法国与美国的态度
1866年法国舰队入侵韩国的“丙寅洋扰”,不仅是近代韩国与欧美列强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同时也是中国中心之东亚传统朝贡关系体制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通过“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所推行之近代条约关系体制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事件,从而也预示着19世纪末中韩两国传统朝贡关系近代转型过程的开始。⑨对此,韩国学者李元淳也曾经指出:“丙寅洋扰虽然是在东北亚的小王国朝鲜一隅发生的小规模战争事态,却是由于积极向亚洲推行东方殖民主义侵略的近代西欧国家与基于斥邪卫正政策而固守‘斥洋’、‘孤高’、‘隐仙’之对外封锁的东洋封建国家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战争。”⑩当时朝鲜王朝大院君政权坚持对西洋国家的所谓“锁国护国”外交政策,借口作为中国的“属邦”而拒绝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接触,(11)因此通过中国而试图与朝鲜开展外交接触便成为西方列强国家的唯一选择。
早在丙寅洋扰发生前一年的1865年,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Jules Francois Gustave)就曾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13条有关法国在华传教权的规定(12)而要求允许法国传教士前往朝鲜传教,同时要求总理衙门给前往朝鲜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颁发护照并向朝鲜政府进行通报,却遭到了总理衙门的拒绝,其理由则曰:“朝鲜虽系属国,向祗遵奉正朔,岁时朝贡,所有该国愿否奉教,非中国所能勉强,碍难遽尔行文。”(13)总理衙门的上述态度,其实主要不是由于对当时近代国际法及条约关系体制的无知,而是“因为中国历代的宗主权未曾因国际的承认或否认而发生问题。照传统的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14)问题在于,当时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列强所主张的近代条约关系体制并不认同总理衙门的上述模糊立场,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传统中华世界秩序的属邦体制(政教禁令自主)与近代国际法秩序的属国(属国的政治外交都受到宗主国的控制)体制之碰撞。”(15)
正是基于上述的历史背景,1866年7月初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Belonnet,Claude Henri Marie)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通报准备出兵朝鲜以“惩罚”大院君政府迫害天主教的同时明确指出:“据言虽高丽于中国纳贡,一切国事皆其自主,故天津和约亦未载入,是以本大臣于存案牢记此言而未忘。兹当本国于高丽交兵,自然中国亦不能过问,因与彼国原不相干涉也。”(16)
查该照会的法文本则更是明确地表达了法国政府对中韩传统朝贡关系根本予以否认的立场:“尽管朝鲜小王国曾作为属国而隶属于中华帝国,却因此次的野蛮行为而永远分离出了中华帝国……我们记录了上述的宣言(秀按:指总理衙门1865年有关中韩关系的照会表述),并宣布不再承认中国政府对朝鲜王国的任何权威。”(17)
韩国学者张东夏认为,伯洛内的上述宣言相当程度上是对当时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一种误解,而且并没有与法国外交当局政府的官方立场。(18)韩国学者金容九的新近研究也指出,伯洛内与法国舰队司令罗兹其实是在没有本国政府明确训令与指示的情况下悍然实施了所谓“朝鲜远征”,此后伯洛内与罗兹分别遭到罢免就是因为他们对朝鲜的擅自越权行为,而法国政府依然主张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是“成功的军事措施”。(19)即便如此,否定中韩传统关系的立场事实上仍是成为当时法国方面公然对清政府的朝贡国家—朝鲜发动战争的主要国际法依据,而清政府坚持与朝鲜的传统朝贡关系却不肯承担实质性责任与介入行动的消极不干涉政策则成为导致法国方面能够公然对朝鲜发动战争的一个客观原因。(20)如果考虑到法国舰队两次对朝鲜的武装侵略行动都是以中国东部沿海的烟台(芝罘)港为基地而实施的事实,(21)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进而阻断清政府的介入可能性对于法国方面发动丙寅洋扰的重要性之所在。
到1871年辛未洋扰之际,中韩朝贡关系再度成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外交争端。(22)早在1866年9月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在平壤大同江被朝鲜官民烧毁的事件发生之后,同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代理公使卫廉士(Williams,Samuel Wells)就在北京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请求协助调查事件真相。总理衙门在复照中尽管表示通知盛京等地方官“查照妥为办理”,同时又指出“朝鲜虽系臣服中国,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概由该国自行专主”,(23)实际上是在表明中韩传统朝贡关系并不能对事件调查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24)到同年11月20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Anson)根据美国政府指令再度访问总理衙门时,总理衙门领班王大臣恭亲王奕再度表示中韩传统朝贡关系不过是一种礼仪性(ceremony)的关系,因此清政府不能为朝鲜承担任何实质性的责任。(25)正因为如此,蒲安臣公使于访问总理衙门一个星期后的11月27日致函美国亚洲舰队司令贝尔(Bell,Henry H.)建议出动军舰赴朝鲜调查事实真相,并在同年12月15日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Seward,William H.)的报告中,指出中韩传统关系其实是一种礼仪性关系,进而建议第二年春天动员大规模舰队远征朝鲜。(26)蒲安臣公使的上述报告已经在预示着美国舰队入侵朝鲜西海岸的1871年辛未洋扰事件,而当时清政府的消极不干涉政策则成为导致这样一种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27)
到1870年4月,美国政府新任国务卿菲什(Fish,Hamilton)指示新任驻华公使镂斐迪(Low,Frederick Ferdinand),一方面赋予镂斐迪决定远征朝鲜行动的具体时机及其规模的全权,同时要求与清政府交涉以获取在朝鲜问题上的“善意的(good will)居中斡旋(good offices)”。(28)同年5月初到北京履任的镂斐迪公使却在7月16日致菲什国务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朝鲜对清朝的朝贡“与其说是表明政府对清政府(的服从)的贡物(a governmental tribute),不如说是为和中国人交易的特权提供的抵押品……清朝对朝鲜并不主张和行使任何形式的统治。似乎朝鲜也认为清政府完全没有对本国政府的统治进行干涉以及加以统制的权力”,(29)进而开始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罗杰斯(Rodgers,John)策划对朝鲜的军事远征计划。韩国学者朴日根曾指出,镂斐迪公使的上述报告内容尤其是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的观点,对于此后美国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0)事实上,清政府总理衙门不仅反对镂斐迪公使访问朝鲜计划,而且再三拒绝了向朝鲜政府转达美国方面外交文件的请求,在1871年5月至7月的辛未洋扰期间也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有效的干涉行动。(31)
到辛未洋扰结束后,镂斐迪公使对中韩朝贡关系做出了如下的评价:“我们很有理由设想中国正在并将要利用除激起西方列国敌意以外的一切方法,来维持和保全就该两国关系而论的状态。只要朝鲜保持它目前不与外国交往的态度,中国的上国地位就会被承认和尊重。这按照就可以扩大中国在它人民眼里的重要性,并据官员们的看法,可以增加他们的尊严和重要。倘使朝鲜开放对外国的交通,则维系它对中国藩属关系的纽带,即便不完全破碎,也会被削弱,并且目前每年对北京的进贡,立刻会变为陈迹。北京的官员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而希望朝鲜能够一切照旧不变。”(32)正因为如此,此后美国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便是向着“承认朝鲜王国为有别于中国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方向”而展开。(33)
三、条约的否定:1876年时日本以及1882年时美国的立场
如果说1866年与1871年法国与美国否认中韩传统朝贡关系主要是出于对朝鲜发动报复性军事侵略行动之目的从而具有典型的“炮舰外交”色彩的话,1876年与1882年日本与美国在与朝鲜签订条约时竭力否认中韩传统朝贡关系之举,则更多地体现了近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两种不同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冲突。日本与美国则是充分利用上述的紧张与冲突关系,而获取了各自的外交利益。其实,清政府早在1871年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之际,就已经有过针对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相关努力措施。(34)至少按照担任清政府全权代表之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理解,《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句,便是“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35)然而,明治日本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一个最初目的就是要落实“日清两国平等”,进而要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对于对清恪守事大藩属之礼的朝鲜,日本在名分上就取得了优越地位,这应该说也就打开了与朝鲜建交的方便之门。”(36)
1874年台湾事件前后中日两国有关“所属邦土”句的纷争,在其前因上与中日两国对《中日修好条规》的不同目的与意图直接相关,在其后果上则是成为1876年《江华条约》之际中日两国有关“所属邦土”句纷争的一个先声。(37)到1875年9月20日云扬号事件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在决定“与过去柏利提督来到下田时(对日本)的先例”一样,向朝鲜派出武装船队护卫下的外交使节进行交涉,同时于11月10日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前往中国开展交涉,(38)其目的就是为了迫使清政府就中韩朝贡关系问题表明立场进而阻断清政府对日朝交涉的干涉。(39)事实上,森有礼与清政府的交涉,尤其是1876年1月24日至25日在保定府与李鸿章之间有关中韩朝贡关系的著名争论,(40)并没有对随后在朝鲜江华岛开展的日朝两国交涉产生直接的影响,却仍不失为中国清政府所坚持的传统朝贡关系体制与日本明治政府所坚持的近代条约关系体制在对朝鲜关系问题上的第一次公开冲突。(41)
到1876年2月27日在朝鲜江华岛签订的《朝日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或《江华岛条约》)12款中的第一款,则明确规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42)关于这一条款的意义与影响,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等指出:“由于缔结《日朝修好条规》,日本的大陆政策便迈出了第一步。此外,这个条规否定了清帝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对东部亚洲华夷秩序的国际体系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自不待言,清帝国是不肯承认这个条约的。于是,围绕着朝鲜问题,日清两国就不能不形成严重的对立关系。”(43)事实上,这个“自主之邦”句是模仿1874年3月《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第二款有关“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阁下面对一切外国,无论哪一个国家,承认安南王的主权和他的完全独立”的内容。(44)旅日华裔学者彭泽周曾对这一条款与中国的关系做出过明确的解释:“根据上述的江华岛条约第一条,清韩两国之间的宗属关系从根本上遭到了否定,其政治意义极为重大。换言之,无论今后日韩两国之间发生任何的纠纷,日本不仅可以抑制清国对朝鲜问题的发言权,还可以对李朝政府为所欲为地实施强求。这一点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日本对韩交涉史上最大的成果。”(45)总之,1876年《朝日修好条规》中有关“朝鲜国自主之邦”的内容,使日本明治政府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立场得到一种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明文表述,从而不仅成为近代日本与朝鲜关系史上的一个长期争端问题,(46)而且也成为近代中国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争端。(47)正如韩国学者金基赫所指出的那样,《朝日修好条规》“是不仅在韩日两国关系而且在东亚国际关系方面带来划时代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48)
到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之际,中韩传统朝贡关系再度成为中国与美国以及朝鲜与美国之间的一个重要争端问题。有关《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研究,在近代韩国历史以及韩美关系史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迄今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先行研究,(49)本文的考察重点则在于关注其中有关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内容。众所周知,有关朝美条约的交涉,至少在中韩两国层面可以说是清政府与李鸿章自1876年以来对朝鲜政府实施“列国立约劝导策”的结果。(50)早在1881年初,李鸿章就已经指派具有留学法国经历的外交幕僚马建忠等人拟定了一份《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约章节略》,(51)其中第二条限制各国驻朝鲜外交代表层级为总领事并接受其驻华公使指导,第十条则规定汉文本为作准文本,试图借以强调中韩传统朝贡关系,从而“在将朝鲜纳入近代条约关系框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清朝的传统朝贡关系。”(52)到1882年有关朝美条约草案的交涉,首先是通过李鸿章的安排与主导而在天津展开了中、朝、美三方的多边会谈,至于后来在朝鲜仁川的交涉则不过是根据上述天津交涉的结果而落实条约签署事宜,而清政府与李鸿章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起到了重要的斡旋乃至“代为主持”的作用。(53)
根据李鸿章主持确定并获取朝鲜领选使金允植同意的朝美条约草案,其中第一条就是明确规定朝鲜为中国属邦,(54)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出现1876年《朝日修好条规》第一条那样的尴尬局面。(55)然而,在1882年3月开始的天津交涉过程中,美国政府代表薛斐尔(Shufeldt,Robert Wilson)却根据近代国际法有关主权国家与“半主权国家”的原则,拒绝在朝美条约中插入承认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内容,最终经过与李鸿章及其幕僚的多次会谈而以所谓“属邦照会”方案达成了妥协,(56)亦即“薛斐尔在坚持不能在条约正文直接反映韩中两国之间朝贡关系的同时允许采用上述的间接表现方式,李鸿章则在条约正文插入上述间接表现(秀按:条约文本使用汉文并采用清朝纪年)之外又通过专门的属邦照会来宣示朝贡关系。”(57)于是,在1882年5月22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之后,朝鲜方面随即向薛斐尔转交了国王高宗对美国总统亲笔函的复函以及仍以国王高宗名义的所谓“属邦”照会,其中声称“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由大朝鲜国君主自主。今大朝鲜、大美国彼此立约,俱属平行相待……至大朝鲜国为中国属邦,其分内一切应行各节,均与大美国毫无干涉。”(58)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对于清政府与李鸿章精心设计的这一“属邦照会”只是加以存档“而始终未予发表”,(59)从而并未能起到预期的实际效果。关于《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对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冲击与破坏意义,美国学者丹涅特(Tyler Dennett)早在1922年就已经做过如下明确的分析:“一八七六年的日、朝条约已经是凿开朝、中两国的第一个楔子;薛斐尔条约虽然是第二个楔子,可是却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根据这件条约,中国承认了日本在六年前提出的朝鲜是和日本同样独立自主的主张。薛斐尔条约的确是走向瓦解中华帝国的一个步骤,其的确的程度绝不亚于英国和法国有关缅甸和安南的条约。”(60)
四、“参入”性利用:1885年巨文岛事件时期英国、俄国及日本的态度
1885年4月英国远东舰队为遏止沙俄势力南下而突然占领朝鲜西南海域巨文岛,直至1887年2月撤出,巨文岛事件遂成为1884年12月甲申政变之后有关朝鲜半岛的最大国际冲突事件,并成为“导致东北亚国际政治结构变化的”(61)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62)在为时近两年的巨文岛事件过程中,围绕着英国占领巨文岛以及后来撤出巨文岛相继出现了所谓“占领外交”与“撤出外交”之复杂的多边外交活动,其中有关中韩两国朝贡关系的态度遂成为一个焦点。
英国方面在占领巨文岛之后,最先通报了清政府并试图利用中韩传统朝贡关系来获得清政府的事后承认。1885年4月28日,英国外交当局在伦敦向清政府驻英公使曾纪泽提交了一份中英协议草案,主要内容为如下三条:“一、中国不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秀按:中英)两国同意对巨文岛进行合法占领与管理;二、英国在占领满12个月后将巨文岛所产收入全额交付朝鲜政府,并在此后的占领期间每满12个月都将交纳上述额数;三、至朝鲜向中国交纳朝贡额数,英国将在上述交纳额内直接交付中国。”(63)这样一种协议内容,不仅完全承认中韩朝贡关系现状,甚至愿意代为朝鲜交纳对中国的朝贡费用,正如曾纪泽公使向总理衙门报告的那样,是要以“保全中国上邦之权利,则尚不至大伤中国体制”(64)的代价来换取清政府对占领巨文岛的承认与支持。然而,清政府与李鸿章首先是从所谓“变形的事大秩序框架”(65)视角来把握巨文岛事件,并坚持反对占领巨文岛的外交立场从而破坏了英国政府试图争取清政府外交承认的如意打算,而后在中韩朝贡关系框架下展开了有关巨文岛占领外交的对应过程。(66)
同年7月,英国政府还曾在给驻华公使欧格讷(O' Conor,Sir Nicholas Roderick)的训令中提出,为避免清政府反对占领巨文岛,“英国政府准备全面承认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a full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uzerainty of China over Corea)”,(67)却未能得到清政府的同意。接着,英国政府先是提出以五万英镑总价或每年五千英镑的代价租借巨文岛的方案,而后又提出了将巨文岛转交清政府海军占领的方案,始终是坚持无视当事国朝鲜而与清政府交涉的立场。有关巨文岛问题的交涉也主要是在中国天津、北京及英国伦敦展开,足以表明英国政府试图利用中韩传统朝贡关系来维护其全球战略利益的外交策略。到1886年初英国政府开始所谓“撤出外交”之际,还曾向清政府建议缔结一个国际条约以保障朝鲜领土不再遭受侵犯(an 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 guaranteeing the integrity of Corea),终因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积极呼应而未果。(68)
直到1886年12月24日,英国政府先是通过其驻华公使华尔身(Walsham,John)向清政府总理衙门通报撤出之意,并特别向朝鲜政府声明“现经中国公行担保,以倘能将暂行据守之事停止,中国亦可担保别国不取巨文岛及贵国他处土地之语,是本国退出巨文岛之意益固”(69),才在翌年2月27日实施了撤退行动。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在整个巨文岛事件中不仅没有反对中韩传统朝贡关系,而是始终利用中韩传统朝贡关系来加强本国的外交立场,进而维护其全球战略利益。韩国学者金容九就指出当时英国是从世界政治尤其是与俄国对抗的角度来认识朝鲜的地缘战略位置,因此“热中于开拓中国市场的英国就成为中国韩半岛政策的忠实支持者,比任何国家都希望韩半岛维持现状,因为担心改变现状会导致俄罗斯的介入。”(70)
众所周知,英国舰队占领巨文岛的名分就是防止以海参崴为基地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南下,因此沙俄在有关巨文岛事件的多边外交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然而,当时的沙俄政府无论出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还是远东地区海陆军实力的薄弱现实,都无法采取针对英国占领行动的实力对应措施,对于巨文岛事件只能采取消极的“谨慎政策(cautipis policy)”。(71)因此,俄国“为促使英国撤出巨文岛,就必须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72)也正因为如此,俄国政府通过驻华代理公使拉德仁(Lady Jensky,N.)与李鸿章交涉,商定了通过声明俄国无意占领朝鲜领土以促使英国撤出的方案。
1886年10月,拉德仁公使向李鸿章提交了有关巨文岛事件的中俄秘密协议草案,具体包括如下三条内容:“一、中俄两国为捐除彼此误会起见,议明朝鲜一切情形,以后无有更变,均照历来及现在办法……二、俄国除担保太平外,并无他意,不愿取朝鲜土地,中国亦自不行如此之事……三、日后如有意外难于预料之事,与朝鲜现在情形大有关系,或与俄国在朝鲜之利益有碍,致使不得不变更朝鲜现在情形,中俄两国或由彼此政府,或由彼此驻韩大员公同商定办法。”(73)不难看出,俄国政府试图在承认中韩朝贡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与清政府的外交合作来确保俄国在朝鲜的现实利益,并促使英国撤出巨文岛。正如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所指出,“俄国只能决定:暂时先以李鸿章—拉德仁的君子协定为一种限度,对中朝关系‘不指手画脚’、尽量避免这一‘问题’才是上策。”(74)尽管由于清政府担心上述第三条内容容易引起中俄对朝鲜共同保护而最终拒绝签署这一协议,而拉德仁与李鸿章仍是就上述内容达成了一种默契即所谓“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75)并成为清政府与李鸿章借以敦促英国及早撤兵的一个重要外交手段。
日本政府在得到英国有关占领巨文岛的外交通报后,首先是通过正在天津进行有关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谈判的伊藤博文,于1885年4月12日向李鸿章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询问“如有他国水师屯聚于巨磨岛,窥伺朝鲜,与日本大有妨碍,日本亦可派兵往援否?”(76)应该看到,关注巨文岛事件对日本影响的上述态度,与十天后的4月22日日本外务省向英国政府正式转达的外交立场完全一致。(77)外务卿井上馨尽管认为“围绕朝鲜的国际紧张局势是‘瓜分朝鲜’政策的开始”,却依然坚持当时“日本的情况不允许采取强硬方针介入,为防亚洲受‘虎狼的侵袭’,他选择了同清政府妥协的道路。”(78)于是,同年7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梗本武扬奉井上外务卿的训令专程来到天津,与李鸿章商谈有关巨文岛事件的应对问题,并提交了井上馨关于中日两国趁机加强对朝鲜问题介入的建议即所谓“朝鲜办法八条”,要曰:“一、李中堂与井上伯爵密议朝鲜外务主意,办法既定之后,由李中堂饬令朝鲜照办,务使其办到。二、朝鲜国王不得与内监商议国政,应将内监与闻国政之权除去,一切国事均不准内监干预,国王当与其照例委任之大臣商议。三、朝鲜大臣中必择最为忠荩者托以国政,国王如有擢用重臣,无论如何必先与李中堂相商,中堂再与井上伯爵斟酌。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诸人,皆可托以国事者也。四、国事之最要者,如外部、户部、兵部事务,均应委托以上所举之忠荩重臣办理。五、应择美国之有才者一人,令朝鲜政府委用,以代穆麟德。六、中国驻扎汉城之坐探国政大员,急宜遴派才干较长于现在驻扎之员。七、中国委派之坐探国政大员,并荐与朝鲜替代穆麟德之美国人,必奉有中堂详细训条,俾晓日后办事主意。其赴朝鲜时,可令其顺途过日,往见井上伯爵。八、中国坐探国政大员,必与日本署理公使情意敦笃,遇有要事,互相商酌办理。”(79)
尽管李鸿章与清政府并未接受井上馨的上述共同干涉朝鲜建议,(80)而这一份出自日本外交大臣之手的《朝鲜办法八条》,较诸日本政府此前的一贯外交立场不啻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默认清帝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提议以清政府为主导,把朝鲜置于日清两国共同保护下,以抵抗俄国的入侵。”(81)这样一种承认并试图利用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立场,较诸1876年《朝日修好条规》之际处心积虑地否定中韩朝贡关系的做法,可以说是天壤之差,足以表明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机会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外交倾向。
五、代结语
毋庸讳言,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在19世纪末中韩关系史领域的反映与体现,是一个极其复杂与艰深的研究主题。上述的考察显然不够充分与全面,不无管窥之嫌,却仍不妨得出如下的三点结论:首先,条约与朝贡尽管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关系体制而互相对立(82),在19世纪末的中韩关系领域却是一度共存与兼容,在中国清政府则表现为笔者所曾指出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one diplomacy two systems)”,在朝鲜王朝则表现为俞吉浚所谓“两截体制”。(83)换言之,近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两种国际关系体制一度共存甚至兼容,才是19世纪末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中韩关系史的真实状态。
其次,欧美列强与新兴日本尽管坚持近代条约关系,并通过武力乃至条约的方式来冲击并否定中韩传统朝贡关系,却在涉及自身实际利益的事件上采取了承认甚至利用中韩传统朝贡关系的现实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巨文岛事件之际英国、俄国及日本的态度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关于西方势力以“参入”亚洲传统朝贡贸易市场的形式促成近代亚洲市场之形成的观点(84),应该也能适用于有关中韩朝贡关系以及东亚国际关系近代化过程的研究,本文便是出于上述问题意识的一个阶段性产品。
再次,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irbank)所谓“条约取代朝贡体制(the treaties succeed the tribute system)”(85)固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结局,但至少在19世纪末中韩传统朝贡关系问题上,欧美列强与明治日本就先后有过武力冲击、条约否定及“参入”性利用等三种不同的态度与立场。换言之,在19世纪末中韩关系乃至东亚国际关系领域的“条约取代朝贡体制”,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曲折的动态历史过程,显然有待于更加深入与全面的探讨与诠释。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朝贡关系体制的消亡过程及其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近代条约关系体制在东亚世界的形成过程。
收稿日期:2013-10-20
注释:
①金容九:《世界观冲突与韩末外交史,1866-1882》,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1年,第67-68页。
②冈本隆司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438页。
③权赫秀:《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代前言,第17页。
④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有关晚清对韩关系史的研究,参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权锡奉:《清末对朝鲜政策史研究》,首尔:一潮阁,1986年;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首尔:白山资料院,2000年;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韩关系と东アジアの命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Kirk W.Larsen,Tradition,Treaties,and Trade: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ǒn Korea,1850—1910,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⑤有关近代韩国“两截体制”的研究,参见原田环:《朝鲜の开国と近代化》,广岛:溪水社,1989年;郑容和:《文明的政治思想:俞吉浚与近代韩国》,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4年。
⑥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际契机:朝贡贸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
⑦参见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⑧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10页。
⑨权赫秀:《丙寅洋扰与中国清政府的对应研究》,韩国《白山学报》第65号,2003年。
⑩李元淳:《丙寅迫害、丙寅洋扰已经外奎章阁图书》,载权熙英、李元淳、张东夏、赵珖:《丙寅洋扰的历史照明》,城南: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2001年,第29页。
(11)董德模:《朝鲜朝的国际关系》,首尔:博英社,1990年,第7-9页。
(1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07页。“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全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
(13)《总署发英国照会》,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29页。
(1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第223页。
(15)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16)《总署收法国照会》,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27页。
(17)韩国教会史研究所译:《韩佛关系资料1866-1867—丙寅洋扰—》,载韩国《教会史研究》第2辑(1979年3月),第205页。另据韩国学者柳洪烈著《增补韩国天主教会史》下(首尔:Catholic出版社,1984年四版)第97-98页有关该照会的内容则如下:“朝鲜虽然称为向清国献纳朝贡的国家,而贵衙门已经声明该国一切事务由其自主,即便我国与朝鲜交战,清国自不能干涉。”
(18)张东夏:《法国对丙寅迫害的对应与占领江华岛事件》,载权熙英、李元淳、张东夏、赵珖:《丙寅洋扰的历史照明》,第71-72页。
(19)金容九:《掠夺帝国主义与韩半岛:世界外交史大势中的丙寅、辛未洋扰》,首尔:图书出版圆,2013年,第57-58页。
(20)权赫秀:《丙寅洋扰与中国清政府的对应研究》,韩国《白山学报》第65号,2003年。
(21)详见张东夏:《法国对丙寅迫害的对应与占领江华岛事件》,载权熙英、李元淳、张东夏、赵珖:《丙寅洋扰的历史照明》,第79-91页。
(22)权赫秀:《1871年辛未洋扰与中国清政府对应研究》,载权赫秀:《近代韩中关系史的再照明》,第51-77页。
(2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5,丙寅十月辛卯给美国卫廉士信函;No.34,Williams to the foreign office,Peking,October 23th,1866,转引自朴日根:《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26页。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353页“照录美国卫廉士信函”中却没有关于中韩朝贡关系的表述内容,疑误。
(24)朴日根:《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26页。
(25)No.124,Burlingame to Seward,Peking,December 15th,1866,转引自朴日根:《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26-27页。
(26)No.124,Burlingame to Seward,Peking,December 15th,1866,转引自朴日根:《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28页。
(27)权赫秀:《1871年辛未洋扰与中国清政府对应研究》,载权赫秀:《近代韩中关系史的再照明》,第57页。
(28)Fish to Low,Washington,April 20,1870(Received July 16),FRUS,1870,China,p.334;《赋予与朝鲜的交涉全权及签订条约方针》,《近代韩国外交文书》第2卷,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第55-58页。金容九教授寄赠《近代韩国外交文书》,谨此鸣谢。
(29)No.37,Low to Fish,Peking,November,22th,1870,转引自金源模:《近代韩美交涉史》,第238-239页。
(30)朴日根:《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65页。
(31)有关清政府在辛未洋扰期间的消极不干涉政策史实,详见权赫秀:《1871年辛未洋扰与中国清政府对应研究》,载权赫秀:《近代韩中关系史的再照明》,第60-69页。
(32)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d)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Japan and Kore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72页。
(33)朴日根:《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114页。
(34)详见王玺:《李鸿章与中日订约(一八七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
(35)《日本约章缮呈底稿折》,载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8,台北:文海书店影印本,1962年,第47—50页。
(36)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1853-1972)》上册,东京:朝日新闻社,1974年,第86页。
(37)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10页。
(38)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1853-1972)》上册,第100页。
(39)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の研究》上卷,京城:朝鲜总督府中枢院,1940年,第407-409页、第417-421页。
(40)有关李鸿章与森有礼保定争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以及中韩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参见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の研究》上卷,第538-544页;Frederick Foo Chien(钱复),The Opening of Korea,A Study of Chinese Diplomacy,1876-1885,The Shoe String Press,Inc.,1967,pp.36-39;彭泽周:《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の研究》,东京:塙书房,1969年,第66-67页;Key-Hiuk Kim(金基赫),The Last Phase of the East Asian World Order,Korea,Japan,and the Chinese Empire,1860-188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237-242;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27-31页。
(41)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30-31页。
(42)国会图书馆立法调查局编:《旧韩末条约汇纂》上卷,首尔:国会图书馆立法调查局,1964年,第12页;崔德寿等:《从条约来看韩国近代史》,首尔:株式会社开放书籍,2010年,第766页;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1965年,第65-66页。
(43)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1853—1972)》上册,第100页。日本学界有关该条文的进一步分析,参见冈本隆司著,黄荣光译:《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第38-39页。
(44)高第(Cordier)辑,《一八七四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张雁琛译,载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1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619页。
(45)彭泽周:《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の研究》,第73页。
(46)金容九:《世界观冲突与韩末外交史,1866-1882》,第200-201页。
(47)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36-37页。
(48)金基赫:《江华岛条约的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载金基赫:《近代韩中日关系史》,首尔:延世大学出版部,2007年,第126页。另外,中国学界的研究也关注到《朝日修好条规》作为“被迫开国条约”而与中国、日本的比较,参见张岩、黄定天:《近代中、日、朝“被迫开国条约”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49)金熙一(音译):《美帝的朝鲜侵略史》1,平壤:劳动党出版社,1961年;Lee Yur-Bok,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Korea,1866-1887,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70;金源模:《近代韩美交涉史》,首尔:弘盛社,1979年;朴日根:《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首尔:一潮阁,1981年;宋炳基:《近代韩中关系史研究—19世纪末的联美论与朝清交涉》,首尔:檀国大学出版部,1985年;金源模:《近代韩美关系史:韩美战争篇》,首尔:哲学与现实社,1992年;李民植:《近代韩美关系研究》(增补版),首尔:白山资料院,1998年;李民植:《近代韩美关系史》,首尔:白山资料院,2001年。
(50)详见权锡奉:《清末对朝鲜政策史研究》,第79-116页;宋炳基:《近代韩中关系史研究—19世纪末的联美论与朝清交涉》,第12-121页;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38-91页。
(5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函附件五: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约章节略》,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472-475页。
(52)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74页。
(53)参见辛胜夏:《朝鲜的门户开放与马建忠的作用》,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1989年7月号;权赫秀:《马建忠与朝鲜》,载李钟殷、郑判龙主编:《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冈本隆司:《马建忠の中国近代化》,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第87-172页;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ぃだ:近代清韩关系と东アジアの命运》,第35-69页。
(54)《筹议朝鲜与美国定约》,载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3,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第7-8页;金允植:《阴晴史》上,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8年,第58页。
(55)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83-85页。
(56)详见奥平武彦:《朝鲜开国交涉始末》,第94-96页;朴日根:《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194-210页。
(57)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87页。
(58)《军机处交出署理北洋通商大臣张树声抄折附件三:朝鲜国照会》,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675页。关于该照会的递交日期,日本学者奥平武彦著《朝鲜开国交涉始末》第136页及韩国学者朴日根著《美国的开国政策与韩美外交关系》第224-225页,均认为是在条约签订两天后的5月24日,而韩国学者宋炳基却根据马建忠《东行三录》等记载而主张是在条约签订当日即5月22日,详见宋炳基:《近代韩中关系史研究—19世纪末的联关论与朝清交涉》,第270、页注释125。
(59)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著,《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译,第395页;陈伟芳著,《清日甲午战争与朝鲜》,权赫秀译,首尔:白山资料院,1996年,第76页。
(60)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第391—392页。
(61)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首尔:西江大学出版部,2008年,第43页。
(62)有关巨文岛事件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参见渡边胜关:《巨文岛外交史》,载《普专学会论集》第1卷(1934年3月),第223-281页;李用熙:《巨文岛外交综考》,载《李相伯博士回甲纪念论丛》,首尔:乙酉文化社,1964年,第459-499页;朴日根:《巨文岛事件与李鸿章之对韩政策》,载中华民国韩国研究学会编:《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1年,第205-229页;林子候:《朝鲜巨文岛事件(1885.4-1887.2)之探讨》,载《国立编译馆馆刊》14/2(1985年12月);朱永夏(音译):《19世纪后半叶韩英俄关系—巨文岛事件》,首尔:世宗大学出版部,1987年;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等。
(63)F.O.405/35/15。Granville to Tseng,Foreign Office,April 28th 1885,转引自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76-77页。
(64)《总署收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文》,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826-1827页。
(65)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70页。
(66)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166页。
(67)FO405/35,Salisbury to O' Conor,No.316,Confidential,Dec.12,1885;转引自冈本隆司著,黄荣光译:《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第416页。
(68)《总署收出使大臣曾纪泽文》,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115-2116页;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171-172页。
(69)《总署收英使华尔身照会附件一:华大臣致朝鲜通商衙门督办公文稿》,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179-2180页。
(70)金容九:《掠夺帝国主义与韩半岛:世界外交史大势中的丙寅、辛未洋扰》,第8-9页。
(71)Andrew 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1881-190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8,pp.34-35.
(72)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99页。
(73)《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函附件三:译九月初九日俄使续交改订照会内三条》,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143页。
(74)冈本隆司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第426页。
(75)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178页。
(76)《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函附件三:照录与日使伊藤问答纪略》,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738-1742页;《伊藤大使李鸿章天津谈判ノ件(五)》,载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18册,第276-298页。
(77)《英国ノ巨文岛占据ハ日本ニ取リ重大关心タルヲ以テ之レ真相ノ充分ナル报道ヲ得ル迄ハ本件ニ关シ意志表示ヲ留保スル旨回答ノ件》,《日本外交文书》第18册,第600页;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178页。
(78)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33页。
(79)《论朝鲜国政附日本公使榎本武杨钞呈外务井上函》,载吴汝纶编:《李文忠公(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1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影印本,第3272—3273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03页;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明治年间追补》第一册第十五编,东京:日本联合国协会,1962年,第380—381页。该文件原为日文,其原文与上述中译本内容略有歧异:“第一 朝鮮ニ対スル政策ハ総テ最秘密ノ手続ニテ常ニ李鴻章ト本官ト協議ノ上李氏之ヲ施行スベシ;第二 朝鮮国王ヲシテ現今ノ如ク内廷ニ於テ自ラ政務ヲ執ラシメズ且内官ノ執権ヲ剥キ其政務ニ関スルノ途ヲ絶ツベシ;第三 挙国第一等ノ人物ヲ撰ンデ之ニ政務ヲ委任シ之ヲ進退スルニは国王必ラズ李鴻章ノ承諾ヲ得ベシ右第一等ノ人物トハ金宏集金允植魚允中ノ如キ其人ナルベシ;第四 右ノ人物ニ委任スル政務トハ外交軍事會計ノ三務ヲ以ラ主要トス;第五 可成速ニモルレンドルフ氏ヲ退ケ至當ノ米國人ヲ以テ之ニ代ラシムベシ;第六 陳樹常ハ篤学ノ人物ナレドモオカ足ラズ他ノ有力者ヲシテ之ニ代ラシムベシ;第七 右陳氏ノ跡役ヲ李鴻章ョリ任命シ米國人ヲ朝鮮ニ推薦シタル上ハ将来ノ政策ニ付十分ノ訓令ヲ與ヘ其物ヲ日本ニ送リ本官二面會セシムベシ;第八 陳氏ノ跡役京城ニ在留ノ日本代理公使ト深ク交誼ヲ結ビ諸事協議シテ事ヲ執ルベシ。”日本大学郭海燕教授提供该史料日文原文,谨此鸣谢。
(80)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第202页;金容九:《巨文岛与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韩半岛的畸形世界化过程》,第109—111页。
(81)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33—134页。
(82)详见金容九:《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首尔:罗南出版,1997年。
(83)权赫秀:《两截体制与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对华外交—以首任天津驻扎督理通商事务南廷哲的活动为中心》,《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史研究》第51号(2007年6月);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84)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85)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reaty Ports,1842~185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462-468.按此为该书的“结论(conclusion)”。
标签:李鸿章论文; 总理衙门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中国朝鲜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朝贡体系论文; 清代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中韩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