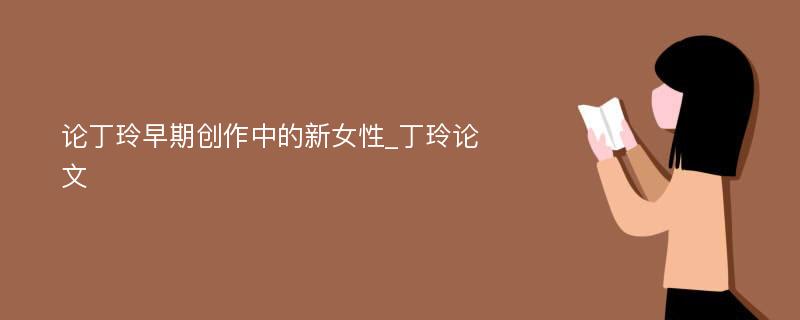
论丁玲早期创作中的新女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 1000—5110(1999)05—0077—04
以觉醒了的新女性在现代社会的沉沦、挣扎,以她们对生的困惑、对死的叩问为艺术视界,这是丁玲早期创作的整体审美追求。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体验人生、寻问人生、探索人生、超越人生的特点。在审美意向上,丁玲孜孜以求的就是生存的实质问题。本文拟从生存形态、生存意识两个方面分析丁玲早期新女性生命追求所展示出来的生存状况的基本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丁玲早期作为一个“人生派”艺术家,对人的生存命运的艺术探究所达到的高度。
一
丁玲早期新女性生存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被抛掷性。被抛掷性是具有清醒内省意识和反思精神的现代人的生存特质。它表现为人在自我生命、自我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中处于劣势情境,呈现为一种张力感。作为张力形成的主体,人被自身所弃,丧失自身,陷入命运的迷茫与不可知中,从而导致人的生存更深层次的被弃“悲境”。
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如梦珂、莎菲、嘉瑛、佩芳,在现实中总处于一种与环境格格不入,被抛弃的境地。这是因为她们所理解的爱和友谊并不是世俗的爱和友谊。她们要求心心相印,真诚无私的心灵契合,而这正是为世人所忽视和难以做到的。她们的痛苦、孤独和不幸其实源自她们的自为,自我心灵意识的细敏、真纯,对自我形象被理解、被认同的焦灼,使她们痛恨灰色、庸俗的生活,憎恨虚伪、矫情的人生。不是生活、社会主动遗弃了她们,而是她们在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上,自己使自己产生了被放逐感。莎菲痛彻心肺地意识到:“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
丁玲强烈地关注着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探寻着什么是人的最自由最完善的生存方式。她笔下的新女性都怀着一缕隐隐的乡愁冲动,寻找着家园,寻找着自我的归宿和本真的存在。她们把自己最本真的生存实现看作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在她们的意识结构中渗透着一种清醒冷峻的反思精神和自我意识。凡事她们都要问之所由,凡情她们都要寻之所发。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总要来细细地观察一遍”,“把别人的说谎处、假情处、浅薄的可怜处都裸露的看了出来”。莎菲们极为憎恶庸俗、恶浊、虚伪的世俗生活,造成她们心灵上和周围环境的疏离和隔膜。她们自身能够意识、认可自己生存的真挚和坦诚,但于她们生存的现实环境,她们却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被遗弃、被抛掷。把追求个体人格的独立、尊严和价值完满实现的自我意识,看作个体本真生存方式的展开和对个体终极和谐存在的把握,是莎菲们所理解、所追求、所认可的自我生命回归终极存在的最本真的途径。但这种清醒冷静、真诚无私的自我意识的结果,却使梦珂沉沦于社会,使莎菲幻灭绝望,使阿毛投入死神的怀抱。
既然具有反思精神和本体力量的自我意识不能使人自救,那么人无疑是异于自己生命、异于存在的存在物,他不能认识自己的生命及价值,更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存和命运。由此,莎菲陷入了对生命的不可知和对冥冥力量的迷茫中:《自杀日记》、《阿毛姑娘》、《小火轮上》突出地表现了莎菲型女性对偶然性命运对人生的决定力量和生存的荒谬性的宿命意识。宿命是人对自身生存力量、生存选择的茫然无措和软弱无力,它相信在人的生命之外,存在着一种冥冥的力量,掌握、控制着人的生存。阿毛的各种令人哀怜扼腕的悲剧性挣扎、努力和梦想,丝丝缕缕地透露出了人对自身命运的枉费心机,他不能也不会成为自己应是或所是的东西。伊萨绝望中的希望是自杀,认为自杀是最本己最无关涉的生存权利,唯有她自身才能体验、拥有这种权利。但小说令人震惊的是,伊萨非但没有获得自杀,而且为房东老太所缠,把自己的《自杀日记》交给老太太去换钱付房租。这个戏剧性的结尾,具有强烈的反讽意义,生存的荒谬,人的一无所是,被暴露得淋漓尽致。人连自杀的权利都无法得到,这一发现使你从头寒到脚根!《小火轮上》的节大姐不怕世俗的道德指责,大胆和有妇之夫昆山相爱,终于等来昆山的离婚再娶。可新娘不是节大姐,而是昆山一次酒醉胡闹认识的女性。真诚去爱者得到的是命运的捉弄和欺骗,而节大姐在认清了昆山虚伪、市侩的嘴脸后,还是向昆山住处走去。人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生存就是荒谬,人生就是无意识的,这就是《小火轮上》所要表现的意旨。
当丁玲把阿毛、伊萨、节大姐置于不可知的命运、荒谬的人生的运转中时,她是想在这冥冥如幽灵般的神秘力量面前,探索、解释人的命运的存在。但这种探索,这种解释太残酷了,人失去了他最后那一点自信,他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包括选择自杀的权利。在神秘、荒谬、偶然的命运面前,人彻彻底底地变成了造化的玩物。丁玲和她的人物“陷入了极深的悲境中”。
和被抛掷的命运相联系,莎菲等新女性生存形态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她们的边缘性处境。边缘性是人在实存的生存境况中的生存特征。居于现实境域的人,从自己此在式的生存情境中来认识自身、领会自身,一方面认识到自己此在式生存的必然情境;另一方面则在这种必然情境中意识到了自己生存位置的不确定,自己生存形象的疏离,由此产生了人的边缘性命运特征。这种命运特征表现出的是人在既定的生存环境中已在中的不在,已是中的不是的生存矛盾。具有边缘性的人在生存形式上和现代主义中的“局外人”极为相似。但他们没有像“局外人”那样在生存意志上导向对自我的虚无和荒诞。
丁玲的“莎菲型”形象既没有子君们摆脱不了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挣扎的尴尬处境,也没有郁达夫的“零余者”们在异性、情爱面前的自卑和软弱。她们是现实人生的热烈追求者,也是自我感性生命的大胆表现者。莎菲在凌吉士的美貌和风雅面前的如癫如狂,似痴似醉的内心情热是子君、露沙(庐隐《海滨故人》)、华(冯沅君《隔绝》)所不能比拟的。她没有传统十字架的牵累,凭着自己的理性和直觉去把握生活,而也正是这种坦荡直率、无饰无伪的人生态度造成了莎菲们和现实环境的距离。尽管纯洁天真的梦珂幻灭之后在“这种纯肉感的社会里”能够“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了”,但她并没有被恶浊的社会所吞噬、同化。作者在结尾用六个“隐忍”,来强调梦珂在黑暗人生中心灵的纯洁,这就形成了梦珂身居此在而又“不在”的边缘性。《暑假中》的那群女教师,同性恋的非正常生活方式已使她们和现实生活、周围环境相背离;而同性恋的岌岌可危则使她们面临着失去自己精神、情感的依托。在生存感受上,她们越来越发现自我空间的缩小,内心情感、心灵意识不为人所知。像莎菲、伊萨们都是现实人生的执著者,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人生就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真诚地做人,真诚地生活。本真自然、纯朴未凿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使莎菲们照见了现实社会的虚假外表,看清了他人庸俗、卑劣的内心。而她们并没有设想在自我生存之外还有另一存在,另一理想梦幻。她们认为一切本真的都应该在现实中敞开,而她们身属的实际生存境况掩盖了生存的本来面目。这造成了莎菲们生存的分离,自我形象的不确定。
二
莎菲们的生存意识具有本体性和意向性。她们不是以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的二元眼光、二元判断去认识自我,去看待人生,而是以存在即本质、现象即本质的一元眼光,一元价值去透视生存。莎菲们生存意识的实质在于,她们不把生命看作任何具有他律性的实体存在,也不把其视作具有某种规范性的理性行为的主体。生命存在于意向性行为的过程之中,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在过程中自我呈现的。下面我们分别就爱情、存在、苦恼三个意识范畴来分析、论述莎菲们的生存意识。
丁玲笔下的新女性所理解、所认识的爱情仅只是一种美好纯洁、天然未饰的自然情感,它不属于什么,也不成为什么,它的存在即是自己的最高目的,最高价值,最高理性。莎菲们心灵的渴望与追求、冲突与骚动、孤洁与傲世最真切、最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种爱情意识。对莎菲爱情追求的评价,涉及到人们对爱情本身的看法。我们并不否认爱情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但爱情的社会制约因素并不是对爱情自身的界定,而是人们对意识现象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认识,而且是在普遍的抽象意义上来概括的。任何一种事实和现象都有自己特定的质素和生存原因,对它们的把握必须回到事物中去,爱情作为人类与生俱有的情感现象,它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自律性。它源自内心,清纯自然,真挚动人。这种自律性难以用一般的社会理性、道德、价值去认识和评价。完全可以把莎菲看作“爱情至上主义者”,但这只限于莎菲和爱情的关系,而不包括她所有的人生内容。在莎菲眼中,“至上的爱情”是两颗纯真心灵、美好情感自然的“灵与肉”的融合。她嘲笑毓芳和云霖苍白无力的爱,惊讶他们“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会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在莎菲看来,只要爱的情愫已在两颗心灵间流淌,已使两个人情投意合,心领神会,那么爱的行为的自然表现和自我选择即是最纯洁、最道德的。对真正的爱情来说,美好的情愫和自我选择的行为,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前者,爱会失去生命的依托和信念,变成无所顾忌的粗鄙兽性的泛滥;而没有后者,爱又会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苍白空泛。莎菲对毓芳和云霖的嘲笑,实际上否定了柏拉图式的虚无飘渺之恋和为各种礼义道德所困囿的爱。缺少爱的激情和表现,那只能说明心智的贫瘠、性格的萎缩。那是不能正视自我,也不敢承担自我的逃避自由的表现;也是生命处于自在状态,屈从于外部世界的非理性反映。莎菲即使在明白了凌吉士“高贵的美型里”“安置着如此一个卑劣灵魂”,她也毫不掩饰自己因情愫的狂涌而带来的强烈欲望,接受了凌吉士的拥抱和亲吻。和庐隐笔下的“海滨故人”在精神爱的幻影中逃避现实的痛苦,和毓芳循规蹈矩、清淡呆板的爱情相比,莎菲对爱情的大胆自白和表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旺盛健全的生命所具有的强大激情和自我力量。
莎菲在狂热的情爱面前,并没有导致自我人格的沉沦。这是因为在她本真自然的爱情意识中蕴含着自我人格、自我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和执着。在激情洋溢的感性生命追求中始终有着理性之光的烛照。正是充满激情而不致沉沦,闪烁理性而又不显迂腐的爱情意识,使莎菲在对凌吉士美貌的迷恋中能保持一种自我反思,自我审视的理性精神,保持了自己人格的独立与清白,保证了自己爱情理想和爱情追求的不受玷污。莎菲的爱情意识是充实灵魂充实生命的自我显现,它是本真的、自足的。它的表现和追求的失落,并不是因为爱情自身的虚妄,而是因为丑恶卑劣,凡庸虚伪的生存环境无法使这种爱情理想与之同流合污。莎菲的爱情理想具有永恒价值,它照示,启迪着现代人的追求。
使“莎菲型”女性保持着自我生命的主体性,保持着自我生命与生存意向的一致性的决定力量,就是贯穿奔流于她们生命之躯中的存在意识。存在是什么?它是和自我生命最本己、最相关的根基性的东西。莎菲的存在意识表现为对生命现实圆满的追求。她们没有在现实的生存境况之外,为自己构建一座“爱”与“美”的乐园。对她们来说,“佛在心中”,“我即是佛”,生存即人的美的存在。她们把自我的生命表现、生存形式看作本真理想的原始展开,并以此去体验、实践人生。《梦珂》中的“红鼻子教员”具有隐喻和反讽色彩。欺侮女模特是他对自己所代表的正真、良善、道德的嘲讽。梦珂由此感到的是整个学校教育思想的虚伪,它不能培养一个健全、充实的生命。伊萨在日记中一再强调:“我并不是一个娼妓,我无庸去敷衍许多人。我应当有我自己的意志。”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真诚地生活,这种把自我生命表现和生存理想看作同源同构的存在意识,一方面使她们保持了自我生命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则使她们避免了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从而导致人沦为自身生命玩物的悲剧。
在莎菲们的心灵意识中,隐隐地执着地回荡着和谐的呼唤,对家园、对故土的依依恋情。梦珂深深地感到:“那自由的、坦白的、真情的、毫无掩饰的生活,除非再转到童时”;莎菲对和蕴妹曾有的美好时光念念难忘;嘉瑛则沉醉在自己回到家园后的浪漫诗意情调中;家园仅对游子存在,而孤独仅因曾有过欢乐。对过往一切的怀念,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怀旧心理。莎菲们缱绻思情的底蕴恰恰是对曾有的生活,曾有的体验理智上的认同。现在与过去生存的分裂,使莎菲们幽幽的乡愁中透现出一种对历史的沉郁感知。它“不仅感知过去性,而且感知过去的现存性”。(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既然没有未来, 它只存在于现在;既然现实已使莎菲们困惑,已使莎菲们分裂,那么她们能从逝去了的过去中找回自己的存在吗?
自己所理想新生的无法实现,使阿毛对幸福究竟存在不存在产生了怀疑,“我本以为幸福是不久的,终必被死骗去,现在我又以为根本就无谓幸福。幸福是在别人看去或羡慕或嫉妒,而自身始终也不能尝着这甘味。”对幸福存在的虚无,意味着自己否定了以前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过去的自己已无可返回;现在与未来,在自我的探求与寻找中又被自我否定,生存彻彻底底变成了虚无。阿毛也以死对自己寻找存在,寻找和谐,寻找幸福的生命历程作了注脚。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对存在的意识及探寻,具有形而上的悲剧色彩。存在何在?莎菲们以过去和死亡回答了这一最本己的问题。“莎菲型”女性形象的心路历程,昭示了存在与虚无的生存哲学。
“莎菲型”新女性存在意识的又一重要特征是苦恼意识。苦恼意识是人的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存在与虚无、规范与自由的二元对立;是人的尽善尽美的精神价值指向与有限、缺漏的现实存在的矛盾;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人在其认识对象、意识对象、理想对象面前的无能为力。苦恼意识的根源并不在于外部现实、客体对象的制约性与他律性。苦恼意识的本源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之人对自我的无可奈何的绝望。“莎菲型”新女性苦恼意识的主体成因在于她们自身。作为苦恼意识的统一体的自我意识并不仅是意识“自身以外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以感觉知觉世界的存在反思而来的,并且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自我意识在对对象—客体的认识中看到了主体的力量,也意识到了主体的有限性。它是人对自身能成为什么,不能成为什么的自我认识和判断。作为完美和谐,“灵肉一致性”的理想生命已成为莎菲们人格结构的基质。在潜意识里,这种理想生命已决定着她们的立身行事、生存选择。莎菲们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人的生存价值是依赖于她们人格结构中的精神生命指向;而且这种精神生命理想于她们自身具有实体性质,他们的生存方式,对现实境况的主体价值判断,都是这精神生命的实体表现。从一个主体的人对自己生存理想受挫的自我反思中,莎菲们看到苦恼、孤独的本源正在于自我。对自我的否定,虽然摆脱了苦恼焦虑,但也取消了自己在现实中的主体存在地位、生存价值。莎菲们千般焦虑、万般愁苦,都是由此而来,她们处在一个极难为其力的两难处境中,要么泯灭意志,忘掉自我,在“常人”、“庸人”的生活中苟活;要么保全真性,为自我的最高生存理想而毁灭。作出选择是极为困难的,作者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把一群新女性在苦恼的情感氛围中挣扎、徘徊、孤独、寻觅的心灵轨迹透视给我们。
丁玲早期创作中“莎菲型”新女性的心路历程,沸盈着丁玲对人的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生命存在的强烈关注。在创作中,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艺术视界和人的生存理想、生存命运联系在一起,显露出了丁玲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敏锐、深邃的现代意识。她的早期创作因之而获得了久远醇厚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