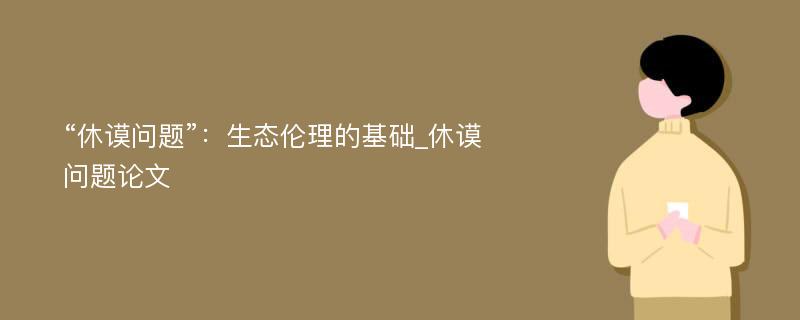
祛魅“休谟问题”:生态伦理学的奠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生态论文,休谟论文,祛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8)06-0040-04
在生态文明已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有关生态伦理学的广泛、激烈而持久的学术论战却愈演愈烈,难以达成伦理共识。各方为之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在于相互指责对方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人类中心论认为,生态中心论把自然的存在属性当作自然拥有内在价值的根据的观点,“显然是把价值论同存在论等同起来了”,犯了摩尔所说的从“是”推出“应该”的自然主义谬误[1]。非人类中心论反驳说,割裂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是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哲学的传统,只是逻辑实证论的一个教条。事实上,人类中心论也在做着同样的推理,“即把人的利益(实然)当作保护环境这一伦理义务(应然)的根据。”[2]人类中心论同样犯了自然主义谬误。
自然主义谬误的实质是“休谟问题”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或能否从“是”中推出“应当”的问题。如果不能,“应当”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对“是”作“应当”判断的伦理学就不能成立,生态伦理学也必然随之土崩瓦解。能否解决“休谟问题”,直接决定着生态伦理学的命运。
一 休谟问题的附魅及其实质
休谟以前或同时代的不少哲学家认为,道德可以如几何学或代数学那样论证其确实性。然而,休谟在论述道德并非理性的对象时却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与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该举出理由加以说明。”[3]。这段话便是公认的伦理学或价值论领域“休谟问题”的来源。就是说,休谟认为,在以往的道德学体系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从“是”或“不是”为系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或“不应该”为系词的伦理命题(价值命题)的思想跳跃,而且这种思想跳跃既缺乏相应的说明,也缺乏逻辑上的根据和论证。
休谟之后,英美分析哲学家门试图把这个问题逻辑化、规则化。元伦理学的开创者摩尔认为,西方伦理学自古希腊以来大致可分为两类:自然主义伦理学,即用某种自然属性去规定或说明道德(或价值)的理论;非自然主义伦理学或形而上学伦理学,其特点是用某种形而上的、超验的判断作为伦理或价值判断的基础。自然主义伦理学从事实中求“应该”,使“实然”与“应然”混为一体;形而上学伦理学又从“应该”中求实在,把“应该”当作超自然的实体。这两类伦理学都在本质上混淆了善与善的事物,并以自然性事实或超自然的实在来规定善,即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4]。这就是生态伦理学各方所谓的自然主义谬误的理论来源。后来,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家黑尔(R.M.Hare)沿袭了休谟与摩尔等区分事实与价值以及价值判断不同于、而且不可还原为事实判断的观点。他认为,价值判断是规定性的,具有规范、约束和指导行为的功能;事实判断作为对事物的描述,不具有规定性,单纯从事实判断推不出价值判断。在《道德语言》中,他具体地研究了他称之为“混合的”或“实践的”三段论的价值推理。这种三段论的大前提是命令句,小前提是陈述句,而结论是命令句。黑尔提出了掌握这种推理的两条规则:(一)如果一组前提不能仅从陈述句中有效地推导出来,那么从这组前提中也不能有效地推导出陈述句结论。(二)如果一组前提不包含至少一个命令句,那么从这组前提中不能有效地推导出命令句结论。黑尔认为,在伦理学或价值论中,第二条限定性规则是极其重要的,根据这一规则,从事实判断中不能推出价值判断[5]。至此,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就被具体化为一条逻辑推导规则——“休谟法则”。事实与价值二分对立的图景随着分析哲学的盛行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哲学界盛极一时,其影响迄今仍根深蒂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相互指责对方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就是受其影响的结果。
黑尔站在非认知论立场上思考价值或道德问题,否认价值判断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他囿于其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企图仅仅通过分析价值语言来解决一切价值问题,从未考虑价值语言的实践根据,也谈不上从实践中去寻找作为大前提的价值原理,结果并没有说明推理中作为大前提的价值判断从何而来,即那种基本的、具有“可普遍化性”和规定性的价值判断从何而来。其实,休谟问题的真正内涵在于:从两个单纯的事实判断中不能推导出价值判断。我们可以由此引出如下结论:(一)和价值无关的纯粹事实或者不进入研究主体领域的事实,既不是有价值,也不是无价值——这是休谟问题的消极意义。(二)价值(判断)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它与事实(判断)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因此,价值科学(伦理学)不能用和事实科学一样的方式来建立。哲学史上一直有人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价值科学(伦理学),例如,笛卡儿试图建立一门类似数学自然科学的道德科学;莱布尼兹发展了霍布斯“推理就是计算”的思想,企图把一切科学包括道德科学都归于计算;斯宾诺莎曾依照“一切科学的范例”——欧氏几何的方法,推导、建构其伦理学;休谟直接以“人性论——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作其《人性论》一书的全部标题,等等。然而,这一系列的尝试都归于失败了。这从反面警示我们,价值科学(伦理学)的研究需要有不同于事实科学的方法和途径,因为伦理学研究对象遵循的是自由规律,事实科学研究对象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这是休谟问题由其消极价值通向其积极价值的中介。(三)休谟问题的积极价值: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正是基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有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的,因为如果二者毫无关系,它们之间就不会存在着所谓区别。如果能够在寻求事实和价值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把二者统一起来,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就具有了可能性。休谟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问题,而是伦理学的元问题。换句话说,休谟问题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的终极内涵是自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这正是生态伦理学的根本,其内在根基在于它们都是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同一个主体对同一个对象做出的不同层面(事实或价值)的判断。
表面看,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价值,事实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的和价值无关的事实。实际上,在所谓逻辑推理的背后潜藏着其价值根基,凡是进入研究领域之中的事实都必然渗透着研究主体的目的、精神和价值理念。和价值完全无关的纯粹事实是没有进入研究领域的事实,人们既不会对它作价值判断,也不会对它作事实判断。没有任何一个事实(判断)是和价值完全无关的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本身正是价值判断的产物,研究它、知道它都是研究主体的价值理念在起作用。就是说,任何研究事实判断的科学(自然科学)都同时渗透着价值判断,反之,任何研究价值判断的科学(人文科学)包括伦理学都是从渗透着价值的事实中做出价值判断的。没有研究和价值无关的纯粹事实的自然科学,也没有研究和事实无关的纯粹价值的人文科学。正如休谟法则所表明的:和价值无关的纯粹事实与和事实无关的纯粹价值一样,都是无意义的。所以,马克思曾说,在终极的意义上,真正的自然科学就是真正的人文科学。
这样,把逻辑和感性实践相结合、在研究自然和自由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解决休谟法则的途径(这也正是解决生态伦理学奠基的途径)就呈现出来了。
二 休谟问题的祛魅
人们通常从外延的角度,把自然看作由人和非人自然组成的整体,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这种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论的观点把人的感性存在抽象掉了,他们只看到人的存在基于他人(父母、祖父母等)的存在、基于与人相外在的自然界的存在,因而陷入了自然因果律的无穷追溯。一方面,这个过程在人提出谁产生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一问题之前会驱使人不断地寻根究底,造物这个观念就会出现于人们的意识中,这就必然导致神秘论。诚如康德所说:“一切成见中最大的成见是把自然界想象为是不服从知性通过自己的本质规律为它奠定基础的那些规则的,这就是迷信。”[6]自然主义谬误或休谟问题本质上正是这种神秘论的当代产物。另一方面,由于仅仅局限于二者的外在关系,割裂自然和人的内在关系,必然导致否定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念对自然事实的深刻影响。休谟问题就是对这种观念的逻辑化、抽象化、理论化的产物。
但从内涵上看,自然是外在自然(非人的自然)向内在自然(人的自由)生成的过程。整个自然界潜在地具有思维的可能性,人是自然界一切潜在属性的全面实现和最高本质,因为只有在人身上才体现出完整的自然界。由于人是全部自然的最高本质,全部自然都成了人的一部分或人的实践的一部分。我们可从世界历史、人的本性和感性实践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从动态的世界史的角度看
一般说来,“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立足于自身的时候,才被看作独立的,而只有它依靠自身而存在时,才是立足于自身”[7]82-83。整个自然界只有产生出了人,才真正是立足于自身的独立存在。在此之前,各种自然物不是独立的,每个自然物都完全依赖另一个自然物而生成和瓦解,或者说,自然界的独立性还是潜在的,是未得到证明和证实的。潜在于自然本身之中的自然的最高本质属性,是有待于产生出人类并通过人类而发展出来的“思维着的精神”。自然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不会丧失任何一个属性,它必定会以“铁的必然性”把“思维着的精神”产生出来(恩格斯语)。就是说,“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7]82整个自然界成为一个产生人、发展到人的合乎目的的系统过程,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全部世界史就是自然界通过人的感性实践对人说来的生成。
(二)从人性的角度看
人是自然的本质部分,人性问题也就是自然的本质问题。人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唯一具有自由和理性的自然存在者。
从静态的角度看,人集自然和自由于一体,同时具有物性和神性两个要素。人的物性不仅仅包括生理和心理要素,因为各种感官的功能视觉、听觉、嗅觉等不仅仅是感官自身,而是感官和自然的光线、光波、震动频率等连接在一起的,时间和空间作为人的内感官和外感官的形式本身也是人的感官的构成部分。可见,人的物性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生理和心理要素)和人之外的自然。同时,基于物性的人的理性或神性也就不仅仅是人自身的理性,而是自然之灵秀即本质上是自然的理性或神性。
从动态的角度看,人性是神性不断扬弃物性的过程。它有两个基本含义:自由不断扬弃人之外的自然的过程;自由不断扬弃人自身的自然的过程。具体说来,完整的实践的人(我)有三个层面:抽象的我——我的精神、身体和另一个身体即自然;社会的我——我和另一个我(他人);本质的我——包括前两个环节于自身的独特的具有个性的我。正是实践的人使自然成为自然,使人成为人,使人和自然成为本质的我。或者说,本质的我是“创造自然的自然”,是自然的最内在的真正本质。自然的内在本质最终体现为人的自由,体现为自由和自然的统一即世界历史,但它同时又是感性的实践自我证明的人性和历史。
(三)从感性的实践角度看
人的感性实践是具体生动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这也是联结事实与价值的桥梁。不与人的感性实践发生关系的抽象的自然界本身是无目的、无意义的即和价值无关,因而它是一种“非存在物”——这就是休谟问题的消极涵义。与人的感性实践发生关系的感性自然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和无机的身体,同时也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或“精神食粮”,因此具有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休谟问题的积极涵义即从事实推出价值的根据。
感性实践既是感性知觉或感性直观,又是感性活动,所以它同时具有一种证明和肯定客观世界的主体性能力。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并不仅仅把自己的某个肢体当作工具,也不仅仅把某个自然物当作工具,而是能够把整个自然当作工具,如嫦娥一号奔月,就是有意识地利用了天空星体的位置关系。另一方面,整个自然也只有通过人才意识到了自身、才能支配自身,才成为了自由的、独立的自然或内在的必然[8]。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把外部对象世界(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作为自身内部的一个环节包含于自身,它是包含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内的单一的(直接感性的)全体。感性在自己的活动中证明了在感性之外有一个自然界存在,它为自己预先提供出质料。这个证明不是逻辑推论,而是他直接体验到他自己就是这个质料(物质)的本质属性,他在对象上确证的正是他自己。因为这个对象由他自己创造出来,所以在自己之外的对象仍然是对象化了的自己:自然界是自己的另一个身体,他人是另一个自己,自己则是在包含自然界和他人于自身的全面的完整的自我。主体(主观)的感性活动唯一可靠地证明了客体(客观)世界在主体之外的存在。自然界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彻底的独立性,人(包括他的“无机身体”的人)也具有了本质的自然丰富性和完整性。
从完整的意义上看,本质的人即实践的人既然就是自然本身,所以他的超越性就是自然界本身的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过程。人自己的这种超越正是自然界最内在的真正本质。由人的感性活动所证实的这个客观世界、自然界,反过来也就带上了人化的感性的性质。它不仅为人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定了位,而且本身也成了为人的存在而存在、以人的存在为目的。这样,实践的人的感性实践证明它自身就是作为价值判断的大前提的主体性根据,本质的人就把自然和自由、事实和价值联结起来了。
可见,自然和自由的关系在于,自然是自在的自由,自由是自为的自然,整个自然史包括世界史就是自然通过其本质部分人的感性实践而不断自我否定不断深入自由的过程。正是感性实践把非人自然和人的主体性连接起来,把非人自然作为人自身的一个环节而成为和主体相关的事实即成为包含着价值的事实,而不再是和价值主体无关的非存在。就是说,价值的事实根据就在于感性实践之中,这就是人性的神性扬弃物性或自由扬弃自然的实践所证明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就是作为价值判断的根据的大前提即人性的自由完善对自然的扬弃——它同时既是事实又是价值,因此,价值判断可从这种(非命令句中的)大前提中合乎逻辑地推出,从事实判断推不出价值判断的休谟问题也就不能成立了。
这就是我们对由“是”推出“应该”的理由和说明,即对休谟问题的回答。
三 结语
休谟问题的解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消极意义:自然主义谬误本身也是谬误,其谬误在于把感性实践抛开,人为地把事实和价值绝对分开而无视二者的内在联系。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相互指责对方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实际上就是因为都没有搞清楚休谟问题,要么割裂存在论和价值论的关系,要么否定利益和价值的内在联系。(二)积极意义在于,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人和自然的内在关系,把实践的主体立足于感性的实践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或抽象的自然,进而深入把握伦理学或价值论乃至自然科学的本质,为研究生态伦理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三)祛除了自然主义谬误的神秘色彩,就可以走向伦理学本身——人的存在,它既是事实(实然)的前提,又是价值(应然)的根基。因此,生态伦理学关注的生态平衡(事实)的实质是“为人”的生态平衡(价值),我们绝不应当为保护生态而保护生态。相反,应当为人而保护生态——这就是生态伦理学的根基和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