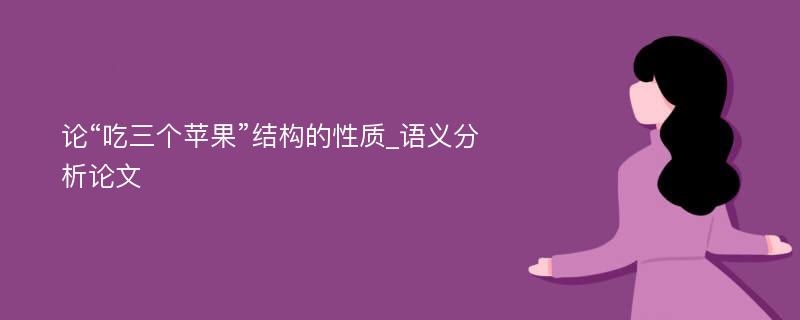
再谈“吃了他三个苹果”一类结构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吃了论文,再谈论文,性质论文,苹果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先前的论证所遇到的挑战
“吃(了)他三个苹果”,这是一个单宾结构还是一个双宾结构?语法学界意见不一。按“单宾结构”说,认为“他三个苹果”只能被分析为表示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作“吃(了)”的宾语;按“双宾结构”说,认为“他三个苹果”可以不分析为偏正结构,而将“他”分析为“吃”的与事宾语,“三个苹果”分析为“吃”的受事宾语。(注:持“双宾”说的学者,并不认为“吃了他三个苹果”只能分析为双宾结构,而认为既可以分析为单宾结构,也可以分析为双宾结构,二者含义不一样。我要补充的是,如果在它前面加上“总共/一共”,那么“总共/一共吃(了)他三个苹果”里的“吃(了)他三个苹果”就只能分析为双宾结构。这是由“总共/一共”的语义指向特点所决定的。)
我在《关于语义指向分析》(陆俭明2000)一文中指出,语义指向分析可以为“双宾”说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角度——利用“总共”、“一共”一类副词在语义指向上的特点,说明把“吃了他三个苹果”分析为双宾结构也是可取的。具体论证过程是:
1.“总共”、“一共”在语义指向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作状语时所指向的成分一定是个数量成分,而在这个数量成分之前,不能带有限定性定语成分,包括表示领属关系的定语。例如:
(1)总共/一共三个苹果。
(*总共/一共红的三个苹果)
(总共/一共三个红的苹果)
(2)墙上总共/一共贴了三幅画。
(*墙上总共/一共贴了齐白石(的)三幅画)
(墙上总共/一共贴了三幅齐白石的画)
2.“给了他三个苹果”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最典型的双宾结构,而“总共/一共”可以修饰这种双宾结构。例如:
(3)总共/一共给了他三个苹果。这是因为其中的“他”跟“三个苹果”没有直接的句法关系,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三个苹果”的定语成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宾语成分。
3.“总共/一共”同样能修饰有争议的“吃了他三个苹果”。例如:
(4)总共/一共吃了他三个苹果。这说明,“吃了他三个苹果”里的“他”和“三个苹果”,虽然从语义上看彼此有领属关系,但从句法上看彼此没有直接的句法关系。因此,“他三个苹果”可以不看作偏正结构,“吃了他三个苹果”有理由分析为双宾结构。
以上论证,一般认为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去年十月我在教学过程中有位学生举出了下面一个实例,向上面我们所作的论证提出了挑战:
(5)总共/一共修了王家三扇门。例(5), 当然更顺畅的说法应该是“总共/一共为王家修了三扇门”,或者说“总共/一共帮王家修了三扇门”,但经调查例(5 )的说法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按前面讲的论证思路,例(5 )里的“修了王家三扇门”也该看作双宾结构,因为它可以受“总共/一共”的修饰;但就一般人的感觉,似不会把它分析为双宾结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前面的论证有问题,还是说前面的论证没有问题,“修了王家三扇门”也可以分析为双宾结构?如果“修了王家三扇门”可以分析为双宾结构,那么怎么解决一般人的“感觉”问题?
二 用“语法的动态性”理论解释“修了王家三扇门”
“语法的动态性”理论是郭锐(2002)提出的,这个理论对解决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很有帮助。什么叫“语法的动态性”呢?郭锐指出,词在句法层面上会产生词汇层面未规定的语法性质,这种语言现象称为“语法的动态性”。(注:这不是郭锐(2002)的原话,他的原话是:“词在句法层面上会产生词汇层面未规定的性质,我们把这种性质叫语法的动态性。”)先前郭锐(2000)就认为,词语的语法性质应区分为“词汇层面的语法性质”和“句法层面的语法性质”。词语在词汇层面的语法性质,是词语固有的词性,可以在词典中标明;而词语在句法层面的语法性质,是词语在具体使用中产生的,由句法规则控制。词语在上述两个层面的语法性质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例如:
(6)小王有一撮黄头发。例(6)里的“小王”、“黄头发”在词汇层面是名词性的, 在句法层面,即具体在上面这个句子里呈现的也是名词的语法性质。但有时会不一致,例如:
(7)小王黄头发。例(7)里的“黄头发”就跟词汇层面的词性不一致, 它在上面这个句子里,即在句法层面呈现的是谓词性质。
归纳郭锐(2002)所说的语法动态性的种种表现,我们把“语法的动态性”主要概括为以下两方面的表现:
一、某词类里的词在语法功能上发生变化。例如区别词,从词汇层面说,它固有的语法功能是只能作定语或跟助词“的”构成“的”字结构(朱德熙1982);但是,有些成对的区别词,如“急性”、“慢性”等,到了句法层面,在一定条件下(含对比意),可以作主语。例如:
(8)肝炎,急性好治,慢性难治。
(9)那柜子,我觉得框式好看。[意味着板式不好看]
二、动词或形容词的论元数(或说“配价数”)发生变化。例如:
(10)张三跑了一身汗。
(11)张三高李四一个头。例(10)里的“跑”,从词汇层面说,它是一价动词,不能带宾语,但在这里增加了一个论元(或说“配价成分”)——“一身汗”。例(11)里的“高”,从词汇层面说,它固有的语法功能是一价形容词,但在比较句里它后面可以带上两个论元——“李四”和“一个头”。换句话说,“跑”由一价动词变成了二价动词;“高”由一价形容词变成了三价形容词。
现在回过头来看例(5 )“总共/一共修了王家三扇门”里的“修”和例(4)“总共/一共吃(了)他三个苹果”里的“吃”。 这里的“修”、“吃”就表现出了语法的动态性,它们原先在词汇层面都是二价动词,后面只能带上一个宾语;而在这里则表现为三价动词,后面带上了两个宾语。但它们跟“给”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给”,从词汇平面说,本来就是三价动词,到句法层面也实现为三价动词;而“修”和“吃”,从词汇平面说,本来是二价动词,只是到了句法层面才表现为三价动词。这样看来,依据郭锐的“语法的动态性”理论,不仅将“吃了他三个苹果”分析为双宾结构是可取的,而且将“修了王家三扇门”分析为双宾结构,也是可取的。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修”和“吃”所形成的“动词+名[,1]+名[,2]”双宾句式,有共同的特点:第一,“名[,1]”和“名[,2]”之间一定有领属关系;第二,“名[,2]”一定是个数量(名)结构。请看:
(12)修了王家三扇门。
(13)吃了他三个苹果。例(12)三扇门是王家的门,例(13)三个苹果是他的苹果。正由于“名[,1]”和“名[,2]”之间有领属关系,所以一般人认为“名[,1]+名[,2]”只能是偏正结构。殊不知由于存在着词语“语法的动态性”,所以例(12)、(13)里的“王家”、“他”,在这里具有双重语义身份——从某个角度说,它是“名[,2]”的领有者,从某个角度说,它又可以成为动词的一个论元(与事);作为双宾结构时,“王家”、“他”都是以动词的与事身份出现的。
朱德熙先生(1982)在谈到“表示取得”双宾结构时,所举的实例是:
(14)买了他一所房子。(16)娶他家一个闺女。
(15)偷了我一张邮票。(17)收了你两百块钱。朱先生认为,如果中间有“的”,或者虽然没有“的”但最后的名词之前是指量词“那所”、“那张”或“那个”等,那末分析为单宾结构;如果中间没有“的”,最后的名词之前是数量词(如例14—17),则分析为双宾结构。朱先生没有说明理由,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的”且最后的名词之前是数量词时可以分析为双宾结构。郭锐的“语法的动态性”观念实际上也为朱先生的说法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三 关于非“给予”义双宾结构
上面所讨论的例(12)、(13)跟朱先生所说的“表示取得”的双宾结构显然属于同一个大类,因为彼此在语义、句法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平行现象:
第一,“名[,1]”和“名[,2]”之间一定有领属关系;
第二,“名[,1]”在语义上为动词的与事(dative);
第三,“名[,2]”得是个数量名结构,在语义上为动词的受事;
第四,它们都能受“总共/一共”的修饰。请看:
(18)总共/一共吃了他三个苹果。(21)总共/一共偷了我一张邮票。
(19)总共/一共修了王家三扇门。(22)总共/一共娶他家一个闺女。
(20)总共/一共买了他一所房子。(23)总共/一共收了你两百块钱。我们不妨把符合上述四点的双宾结构称之为“名[,1]”和“名[,2]”有领属关系、“名[,1]”为与事的非“给予”义双宾结构(简称为“非‘给予’义双宾结构”)。其格式为:
(总共/一共)动词+名[,1](指人与事)+名[,2](数量名结构)注意:我们所以要在“动词+名[,1](指人与事)+名[,2](数量名结构)”前加上“总共/一共”,目的是为了确保“动词+名[,1](指人与事)+名[,2](数量名结构)”只能理解为双宾结构,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指出,在受“总共/一共”修饰的情况下,“动词+名[,1](指人与事)+名[,2](数量名结构)”只能分析为双宾结构。
朱德熙先生(1979,1982)先后谈到过表示“取得”义的双宾结构。朱德熙先生(1979)曾把“拿”归入“表示取得”义动词。“吃了他三个苹果”,按广义的理解,其实也可以看作表示“取得”义一类的双宾结构;“吃”可以跟“拿”看作一类。朱先生(1979)曾把“表示给予”义的动词分为“显性的”(如“给”、“送”、“卖”等)和“隐性的”(如“写”、“搛”、“留”等)两小类;其实“表示取得”义的动词,也可以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小类。就“买”、“偷”、“抢”、“娶”等动词来说,“取得”义是显性的,固有的;就“吃”、“拿”、“喝”等动词来说,“取得”义是隐性的,非固有的。“修了王家三扇门”跟“吃了他三个苹果”还有些不同,并不表示“取得”义,应看作另一种非“给予”义双宾结构,这种双宾结构前人还没有注意到,有必要加以考察研究。
现代汉语里的双宾结构有多种多样。这里只考察、分析上文已加以限定的非“给予”义双宾结构。对于这类双宾结构,着重研究两个问题:(一)上面说了,“名[,1](指人与事)”与“名[,2](数量名结构)”一定有领属关系,可是领属关系也有多种多样,那么什么样的领属关系才能使“(总共/一共)动词+名[,1](指人与事)+名[,2](数量名结构)”构成双宾结构?(二)能在“动词”位置上出现的,具体是那些动词?
四 非“给予”义双宾结构里“名[,1]”和“名[,2]”之间的领属关系
现代汉语里的领属关系多种多样,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16小类:(注:关于怎么确定一个“名[,1](的)名[,2]”是或不是领属性偏正结构,我们将在《确定领属关系之我见》一文中详细讨论。)
(24)a.称谓领属
我的父亲 他的老师 小王的朋友 老张的徒弟 我们的邻居
b.占有领属
他的房子 小李的笔 我的自行车 爸爸的计算机 姐姐的手表
c.器官领属
他的眼睛 弟弟的手 猴子的尾巴 大象的耳朵 松树的叶子
d.构件领属
书的封面 房间的门 衣服的领子 桌子的腿儿 饺子的馅儿
e.材料领属
桌子的木头 衣服的布料 画报的纸 啤酒瓶的玻璃
f.属性领属
他的脾气 小王的性格 糖的价格 烤鸭的味道 桌子的长度
g.特征领属
弟弟的个儿 妹妹的穿着 孩子的长相 箱子的形状 衣服的颜色
h.观念领属
他的观点 我的看法 校长的意见 朋友的劝告 佐藤君的见解
i.成员领属
北大的学生 清华的校长 美国的总统 夏普公司的职员
j.变形领属
土豆儿丝儿 黄瓜丝儿 萝卜块儿 羊肉片儿
k.成果领属
他的文章 李白的诗 齐白石的画 王羲之的字 茅盾的小说
l.产品领属
东芝公司的计算机 中国的人造卫星 浙江的茶叶 新泻的大米
m.状况领属
北大的现状 他的前途 张教授的水平 我们的条件 李老师的病情
n.创伤领属
张三的伤口 他的口子 老张的胃炎 小李的包
o.事业领属
我们的事业 小王的工作 郭老的研究 他们的调查 他的考察
p.景观领属
苏州园林 九寨沟风光 桂林山水 西湖景色
q.处所领属
张三的面前 小王的身后 王大爷家的房后 北京大学的隔壁经考察,“(总共/一共)动词+名[,1](指人与事)+名[,2](数量名结构)”双宾格式里“名[,1]”和“名[,2]”之间的领属关系似只限于占有领属、成员领属、产品领属和部分器官领属。(注:拙稿送给《中国语文》编辑部后,编辑部针对我这里的说法,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文章中发现的这个现象,其实大致与领属关系当中的“可让渡/不可让渡”关系相对应:占有领属、成员领属和产品领属关系属于一般语言学领属关系研究当中的可让渡关系,器官领属类属于不可让渡关系。文中归纳的现象似可概括为:
名[,1]和名[,2]之间为可让渡性领属关系时,进入双宾语结构比较自由;名[,1]和名[,2]之间为不可让渡性领属关系时,进入双宾语结构有一定限制。
《中国语文》编辑部的这个意见很好,特在此转引说明,并表示感谢。)例如:
(25)占有领属:总共/一共买了张三五亩地
成员领属:总共/一共录取了北大附中164个毕业生
产品领属:总共/一共采购了东芝公司50台计算机
器官领属:总共/一共剁了那家伙三个手指头值得注意的是:“(总共/一共)动词+名[,1](指人与事)+名[,2](数量名结构)”双宾格式里“名[,1]”和“名[,2]”之间似乎可以是成果领属关系,例如:
(26)(那小偷)总共/一共偷了齐白石三幅画。其实,例(27)里的“齐白石”和“画”只能理解为占有领属关系,不能理解为成果领属关系。我们不妨把例(26)跟下面的例(27)对比一下:
(27)(那小偷)总共/一共偷了三幅齐白石的画。例(27)“偷了三幅齐白石的画”是一个单宾结构。我们曾作过粗略的调查,一般人听到例(27),都认为句中所说的画是齐白石先生所画的画;而听到例(26),都首先认为齐白石先生家遭偷了,而被偷走的画,可能不是齐白石所画的画,也可能是齐白石所画的画。当我们问被调查人,“你为什么会认为例(26)句中那被偷的画也可能是齐白石所画的”,回答说:“齐白石不是大画家吗?”可见,大家所以会想到被偷的画可能是齐白石所画的画,这想法不是来于例(26)句子本身,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齐白石是大画家。而像下面那个跟例(26)结构相同的例(28):
(28)(那小偷)总共/一共偷了王老师三幅画。被调查人听到这个句子,只会想到王老师有三幅画被偷了,而没有一个人认为被偷的画是王老师所画的画。
五 非“给予”义双宾结构里的动词
为了客观起见,我们以孟琮等编著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1999年版)里所收的动词为考察对象。该词典共收动词1223个。我们按“(总共/一共)动词+名[,1](指人与事)+名[,2](数量名结构)”双宾格式的要求,逐一进行考察(只按词项,不按义项),能进入“(总共/一共)动词+名[,1](指人与事)+名[,2](数量名结构)”双宾格式的动词共98个。现列举如下(按音序排列,为节省篇幅,例句里的“总共/一共”以“一共”为代表):
(29)安插(一共~了王家五个人) 安排(一共~了王家五个人) 安置(一共~了王家五个人)
霸占(一共~了王家五亩地) 拔(一共~了王家五个白薯) 罢(一共~了他们五个人)
搬(一共~了王家五张床) 表扬(一共~了一班五个人) 采购(一共~了方正五台计算机)
采用(一共~了他五个建议) 踩(一共~了王家五垄地) 查(一共~了王家五个房间)
拆(一共~了王家五垛墙) 拆除(一共~了王家五间屋) 铲除(一共~了敌人五个据点)
承担(一共~了国家五个项目) 盛(一共~了她两条鱼) 吃(一共~了她三个苹果)
抽查(一共~了一班五份试卷) 出版(一共~了王教授五本书) 处罚(一共~了一班五个人)
处分(一共~了一班五个人) 穿(一共~过他三件衣服) 打(一共~了王家五个碗)
打破(一共~了他五个碗) 逮(一共~了他们五个人) 逮捕(一共~了王家五个人)
耽误(一共~了他五年时间) 得(一共~了他五百万元) 调(一共~了北大五个人)
斗(一共~了王家五个人) 读(一共~过鲁迅五篇杂文) 端(一共~了王家五把椅子)
夺(一共~了齐国三座城) 剁(一共~了那家伙三个指头) 发现(一共~了王家五个密室)
罚(一共~了她五块钱) 分(一共~了王家五亩地) 俘虏(一共~了敌人五个连)
抚养(一共~了王家五个孩子) 改(一共~了他五个句子) 改正(一共~了她五个病句)
勾引(一共~了王家五个姑娘) 雇(一共~了王家五个人) 拐(一共~了王家五个孩子)
花(一共~了她五百块钱) 夹(一共~了她家三个煤饼) 捡(一共~了王家五块砖)
剪(一共~了她十公尺布) 接(一共~了他三个球) 接受(一共~了他三笔赠款)
借(一共~了她九本书) 纠正(一共~了他五个错误) 砍(一共~了王家三棵树)
扛(一共~了国家五根木头) 扣(一共~了他们三条船) 扣留(一共~了他们三个人)
捆(一共~了他们五个人) 买(一共~了农民四只鸡) 没收(一共~了他们五辆车)
拿(一共~了小王五个苹果) 挪(一共~了公司十万元现款) 挪用(一共~公司十万元现款)
骗(一共~了他三十万元现款) 欠(一共~了她一百块钱) 抢(一共~了王家三头牛)
敲(一共~了他三十万块钱) 敲诈(一共~了她八万块钱) 撬(一共~了北大五个房间)
请(一共~了清华十位专家) 驱逐(一共~了美国三个记者) 杀(一共~了齐国十万人)
烧(一共~了他们三间瓦房) 少(一共~了你8块9毛钱) 赊(一共~了公司三万元货)
收(一共~了他三笔赠款) 撕(一共~了她九本书) 算计(一共~了王家三亩地)
抬(一共~了王家四张桌子) 贪污(一共~了公家九十万块钱) 提拔(一共~了附中三个干部)
挑(一共~了北大十个学生) 挑选(一共~了北大十个学生) 偷(一共~了王家三辆车)
吞(一共~了公家三十万块钱) 挖(一共~了王家十公斤山药) 修(一共~了王家五扇门)
选(一共~了他们三个人) 修改(一共~了他五个病句) 修理(一共~了王家五扇门)
邀请(一共~了北大八位教授) 咬(那狗一共~了王家三个人) 要(一共~了他三件衣服)
赢(一共~了她七千块钱) 用(一共~了他三百块钱) 运(一共~了煤矿十万吨煤)
砸(一共~了她四个杯子) 糟蹋(一共~了公家三万斤粮食) 摘(一共~了他五嘟噜葡萄)
占领(一共~了敌人三个据点) 抓(一共~了王家三个人) 赚(一共~了他五万块钱)
捉(一共~了丐帮十二个人) 租(一共~了王朝饭店三个房间)可能有遗漏,也可能判断有误,把不该列入的列入了,但无碍大局。这104个动词,有其共同性, 那就是它们在句法层面都可以有三个论旨角色——施事、受事、与事。但就它们的语义性质看,又不完全一样,像“买”、“出版”、“糟蹋”显然不能一视同仁,所以这104 个动词有必要再分分小类。该怎么分?自朱德熙先生(1979)运用语义特征分析后,说到给某类词分小类,往往从词的语义特征的角度给词分小类。这在多数情况下是可行的,但也不是哪儿都适用。上面这104 个动词就很难依据它们的语义特征来给它们分小类。最近詹卫东(1999)为研究中文信息处理中的短语结构规则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配价模式”这样一种语义知识表达框架。作为广义配价模式的内容之一,就是充分注意词语配价成分在行为动作进行或完成之后的变化情况,譬如动词“洗”和“晾”都是二价动词,都有一个受事角色,但这两个受事角色在受到动作支配后所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洗”的受事,其变化只是性状的变化,而“晾”的受事,其变化除了性状的变化外,还有位置的变化;二者虽都有性状的变化,但还有区别,“洗”的受事的性状变化通常是从不干净到干净,而“晾”的受事的性状变化通常是从湿到干。上述不同,在语法研究中不能忽视。詹卫东的“广义配价模式”跟前面介绍的郭锐的“语法的动态性”,从某个角度说,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需考虑词语在动态运用中的变化与影响。这里我们想吸取他们二位语法思想里的某些精神,来考虑那104个动词的分类问题。
上面说了,这104个动词,有其共同性, 那就是它们在句法层面都可以有三个论旨角色,在句法上表现为一个主语和两个宾语;但从动态的角度看,即从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对各个论旨角色的影响看,则并不一样。例如“吃”这一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将使施事有所获取;“糟蹋”这一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则使与事有所损伤;而“出版”这一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使施事、受事均有所得。据此我们可以将那104个动词分为以下六小类:
Va类 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将侧重使施事有所获取。最典型的是动词“吃”。例如:
(30)我吃了小王三个苹果。例(30)其意只在说明“我”有所获取。这小类包括“吃”在内有24个动词,现列举如下:
(31)搬、盛、吃、穿、得、调、读、端、夹、捡、剪、接、接受、借、砍、扛、拿、赊、收、抬、要、用、运、摘
Vb类 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使与事、受事有所获取。最典型的是“表扬”,例如:
(32)林校长表扬了一班五个人。例(32)那“五个人”受表扬,当然光荣,他们所在的班也光荣,所以说这小类动词的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将使与事、受事有所获取。这小类包括“表扬”在内有6个动词,具体如下:
(33)安插、安排、安置、表扬、抚养、提拔
Vc类 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使与事受益。这类有6个动词, 具体如下:
(34)改、改正、纠正、修、修改、修理
Vd类 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则使与事有所损伤。最典型的是“打/打破”,例如:
(35)打/打破了她两个碗。例(35)意在说明“她”受损。连“打”、“打破”在内,这小类有16个动词,具体如下:
(36)罢、踩、拆、拆除、处罚、处分、打、打破、耽误、花、烧、少、撕、咬、砸、糟蹋
Ve类 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使施事、与事均有所得。这小类动词所表示的意思比较明显,不需要再举例说明。这类有12个动词,具体如下:
(37)采购、采用、承担、出版、雇、买、请、挑、挑选、选、邀请、租
Vf类 行为动作的进行、发生,使施事有所得,使与事有所损伤。这小类动词所表示的意思也比较明显,也不需要再举例说明。这类有40个动词,具体如下:
(38)霸占、拔、铲除、抽查、查、逮、逮捕、斗、夺、剁、发现、罚、分、俘虏、勾引、拐、扣、扣留、捆、没收、挪、挪用、骗、欠、抢、敲、敲诈、撬、驱逐、杀、算计、贪污、偷、吞、挖、赢、占领、抓、赚、捉
六 余论
本文只讨论“名[,1]”和“名[,2]”有领属关系、“名[,1]”为与事的非“给予”义双宾结构。其实,“名[,1]”和“名[,2]”有领属关系的非“给予”义的双宾结构,不限于上述那一种。譬如说例(39—41)就是另外一种“名[,1]”和“名[,2]”有领属关系的非“给予”义的双宾结构:
(39)(总共/一共)拉了我五个口子。
(40)(总共/一共)烫了我三个大燎泡。
(41)(那蚊子总共/一共)叮了我五个包。这种双宾结构里动词的三个论旨角色分别是施事、受事和结果;“名[,1]”和“名[,2]”之间是创伤领属关系。这种双宾结构,都是使受事受损的双宾结构。
⑤“发现”有点例外,行为动作的进行,有时会使与事受损,有时并不会使与事受损,如“我一共发现她三个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