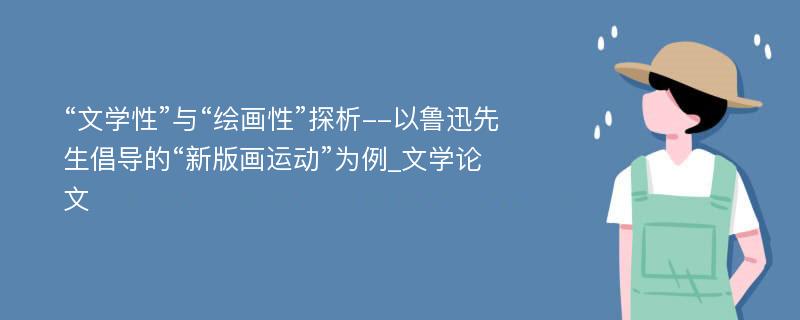
对“文学性”与“绘画性”的探究——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版画论文,为例论文,鲁迅先生论文,文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1)03-0088-05
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绘画与文学一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潜在关系①。
“五四运动”以后,革命的主题、文学性的叙事与意识形态的表达成为中国绘画的重要特征之一。当绘画承载起文化制度革命和救国救亡的历史使命时,绘画就成为其他“非绘画”的附庸。这一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为显著特征的“十七年美术”时期和以“红光亮”、“三突出”为显著特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绘画创作中发挥到极致。
笔者尝试运用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概念来对中国绘画史上的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视觉文化语境下,分类学意义上的文学受到来自网络、图像、影像、媒介的巨大冲击,以“语言逻各斯”为标志的传统印刷媒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从昔日的文化中心滑向边缘。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文学模式[1]正在被广告、影视、新闻、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等学科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形式所采用,分类学意义上的“文学”在消解自身的同时,通过一种更为广泛,更加发散和扩张的态势,通过一种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学性”体现出来。尽管“文学性”这一概念由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家提出,但是“文学性”向绘画领域的“蔓延”[2]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客观地发生在中国绘画史上。由此来思考文学对绘画创作与发展的潜在影响,在绘画创作中应该如何借鉴“文学性”表达方式的优势,而又不能伤害“绘画性”,如何合理设置“文学性”要素在绘画作品中的比例就成为绘画创作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笔者认为基于“种差”分析的绘画与文学的本质界定有利于澄清以上问题。本论文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为案例来分析这一问题。
“本质”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的重要理论,他认为“本质”与“现象”是互为辩证的双方,“现象”是一种直觉性的存在,“本质”则是一种预先设定的思维。据此笔者认为依据于现象,由直觉导向的结论,其正确性必然受到理性的制约,只可能是相对的,权宜的和过程性的;依据于本质,由本质导向的结论,其正确性必然受到预设性的制约,如果预设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结论便充满假定和不可信。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现象导向的结论,还是从本质导向的结论都无法保证结论正确的恒常性和终极性。以此为基础来分析“文学本质”的诸种理论,不管是反映论、情感论、审美论、意识形态论,还是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话语实践等观点,都是人类在预设思维下对文学的抽象性把握。如果抽象思维预设存在问题,那么以此来推断文学的本质是非常危险的。在以上关于文学的本质理论的影响下,中央美术学院的王宏建教授在《美术概论》一书中对美术的本质做了折中式的阐释,他认为美术的本质主要体现在社会、认识、审美、历史四个方面[3]。比较文学的意识形态论与美术的社会本质,文学的反映论与美术的认识本质,文学的审美论与美术的审美本质,笔者发现两者在内容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同质化特征。据此是否可以得出文学与绘画具有相似的本质的结论?答案是否定的。
武汉大学的邓晓芒教授认为“对文学本质的把握必须是一个‘属加种差’的把握”[4]。“属”即所属,是“高于文学的上位概念”[4],而“种差”的界定必须立足于事物的本体,摆脱他律的干扰,重视其自律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学“种差”界定的惟一性。文学本质界定的这一“属加种差”原理同样适应于对绘画本质的界定。由此可见,文学与绘画具有相同的“属”——文化、精神文明属性,但却具有不同的“种差”。因此对文学和绘画本质的界定必须要搞清楚其各自的“种差”,避免同质化的“属”的干扰,只有发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而不为其他和绘画之所以为绘画而不为其他的“种差”所在,才能正确界定文学与绘画的本质。埃亨鲍姆在《关于形式主义的方法理论》中提出“文学科学的宗旨,应当是研究文学作品特有的、区别于其它任何作品的特征”[5]。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6]。绘画亦然。可见“文学性”和“绘画性”是两者最大的“种差”,确立这一点是科学认识两者本质的前提。
何为“文学性”?“文学性”即文学性成分、要素,也即文学模式、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做了如下规定:“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②。可见不管是将“隐”阐释为“文外之重旨”、“复意”、含蓄、润色取美等意,还是将“秀”阐释为“篇中之独拔者”、“卓绝”、警句、自然会妙、“有警策而文采杰出”[7]等意,都是从文本、语言、形式、风格,以及修辞、意象、文采等方面来对“文学性”进行阐释,而这些概念便构成了古人对“文学性”范畴的理解。由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篇》所推出的结论来比较西方解构主义学者对“文学性”,即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概念构成的文学模式的界定,笔者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何为“绘画性”?即绘画独立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征。唐焘认为“‘绘画性’用美学语言来说,就是包括主体旨趣在内的专业媒介特征,是主体观念和表现材料外在统一规律的结合,也就是绘画专业特性。这是个与模仿自然形相联系而又相对立的概念”[8]。“绘画除了综合自然形表达思想感情之外,还有技术方面的形、色效果;或者这种形色本身就具备可以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和本质的东西”[8]。荷兰风格派认为艺术应该摒弃同自然之间的任何联系,只有最小的视觉元素(例如直线、方形等)和原色(例如红黄蓝三原色以及黑白灰等)才能真正传达“宇宙真理”,才能真正实现一种终极的、绝对的、纯粹的客观实在。据此,以荷兰风格派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家将“绘画性”界定为绝对抽象的形式元语言。美国当代画家卡伊欧·方塞卡认为“与寻找我想表现的题材相比,对我无意去画的东西作出取舍尤为困难”③。方塞卡有意放弃预先设定对画面表现的影响,重视直觉、无意识、即兴想象造成的未曾预期的视觉可能性,追求“荻俄尼索斯式的生命热情的释放”[9]。他的这一绘画理念跟康定斯基的热抽象绘画以及波洛克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滴洒法绘画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可见“绘画性”可通过技术之美、材料之美、形式之美,非预设性、直觉、无意识、即兴想象之美等范畴表现出来。
中国绘画史经历了一个“绘画性”由三代秦汉的被抑制到魏晋隋唐之后的并重,再到“五四”以后的被抑制的过程。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就文学与绘画的差异首次道出“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④的主张。不过非常遗憾的是陆机的这一科学的艺术分类学论断并没有引起绘画史家和画家的重视,其后的中国绘画史仍然沿着“文学性”的道路发展。“中国的绘画,由于民族历史在艺术上有一个先决因素的强大影响,不久就形成了它不再单纯地追求写实的倾向”[8]。秦汉时期的绘画更多地承载着维护礼制、载道、兴废鉴戒等社会功能;魏晋南北朝以后,神、韵、骨、心以及由笔、墨之技而萌生的对道的追求成为“绘画性”的重要体现;“五四”以后,“中国画颓败极矣”,美术革命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而浩浩荡荡地展开,汲取西方的写实技法来改良孱弱的中国画造型,“绘画性”再次受到意识形态的压抑。可见绘画的社会功能在近现代社会的回归更加剧了其向“文学性”靠拢的力度和强度。
由此可见,基于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文学模式的“文学性”,与基于技术、材料、形式,非预设性、直觉、无意识、即兴想象等范畴的“绘画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中外绘画史的发展用鲜活的史实证明了这一差异不仅是作为门类的“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最大差异,而且是绘画借助“文学性”来发展自己的前提。中外绘画史的发展是一段“文学性”与“绘画性”相互博弈的历史,“文学性”与“绘画性”始终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不平衡的变化中。要么绘画臣服于道德宗教,成为道德宗教言说的视觉载体,一如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绘画和“明劝戒,著升沉”⑤的中国人物画;要么绘画服膺于历史和现实,成为历史记忆和再现现实生活的视觉工具,一如西方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绘画,北宋及其以后的风俗画,“文学性”要素共同成为中外绘画史追求的目标之一。要么绘画将造型和色彩彻底解构,以至完全消解了物象,一如立体主义、抽象主义绘画以及中国画中的泼墨、泼彩;要么绘画将情感肆意弥散,以至完全消解了形体和结构,一如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以及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⑥,“绘画性”要素成为绘画追求的目标之一。可见,极端化地追求和片面强调作为门类的绘画的“文学性”要素和“绘画性”要素都是不合适的,要么成为“混杂着任何规范”[10]的“依存美”,要么成为充斥着“毫无内容意义的形式”[10]的“纯粹美”;要么过于重视“文学性”而丧失“绘画性”,要么过于重视“绘画性”而失去“文学性”,以上两种极端化偏向都很难实现真正的和谐之美。
基于以上两种认识来分析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它改变了中外美术史上“文学性”与“绘画性”相互割裂的偏向,探索到了“文学性”与“绘画性”要素合理配置的理想方法,并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从而创造出一种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时代精神、时代主题,崭新的审美趣味、形式风格的新兴版画风格。
“新兴版画运动”的“文学性”要素主要通过革命性、战斗性的主题及功能,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三方面体现出来。鲁迅说:“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刻招人猜忌”[11]。木刻版画自被鲁迅先生引入中国之初,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思想宣传的主力媒介之一,就承担着救国救亡、开启民智、揭露社会黑暗、唤醒大众、传播革命思想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从创作主题上来说,“新兴版画运动”与同时代的“左翼文学”具有相同的表达主题,多是表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中国社会的生灵涂炭、黑暗腐败、民间疾苦、激越愤懑,人民改变现实的理想愿望以及民众的反抗斗争等。以上“文学性”主题的美术表现可以由鲁迅先生从欧洲引进的一系列版画作品及新兴版画家创作的作品中得以验证。无论是珂勒惠支的《农民战争》,《织工一揆》,还是麦绥莱勒的《我的忏悔》、《一个人的受难》,都是以组画或连环画的形式,采用小说的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文学模式来组织画面的视觉结构。他们的作品超越了单幅作品的空间性,凸显出多幅联画的时间性,呈现出很强的叙事性,这一“文学性”的处理方法从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国人的观看阅读习惯。例如,《我的忏悔》以自传的方式通过“复杂纷繁的身世起伏,与夫热情的变幻高潮”[12]来表现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争斗、心酸,纸醉金迷、悲哀失望、恋爱神曲、皈依宗教与回归自然的灵魂追求[13];《一个人的受难》通过“一个人”流离困顿而后奋起反抗的一生,来表现被斥逐在街头彷徨的母亲,遭抛弃而流浪街头的儿童,不堪重负遭受虐待的童工,因偷窃被捕关进牢狱的少年,受恶友诱惑而沉沦声色犬马的工人,因奸细出卖而被捕杀害的工人阶级领导者[13]。这一创作主题的表达方法对中国新兴版画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烟桥的《拉》(1934年)具有鲜明的描述性,焦心河的《商定农户计划》(1938年)具有鲜明的叙述性,李桦的《怒吼吧!中国》(1935年)运用想象、隐喻等手法来表现启迪民智的主题。从创作主体上来说,木刻艺术家是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与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国统区左翼木刻家和解放区延安木刻家,当时活跃的木刻团体有“上海一八艺社”、“春地美术研究会”、“铁马版画会”等,活跃的木刻艺术家有江丰、古元、李桦、彦涵、力群、黄新波等。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14],“以刀代笔”,“放刀直干”[15],社会功能彰显。从接受主体上来说,“新兴版画运动”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目不识丁的工人和农民,“绘画性”(图像化)和“文学性”(叙事化)被强调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与以社会精英为创作和欣赏主体的中国绘画史的“被抑制→并重→被抑制”的“绘画性”演变过程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新兴版画运动”的“绘画性”要素主要通过艺术性的追求、西方版画技法与民族化的创作图式的融合两方面体现出来。尽管新兴版画较其他艺术门类在革命性、战斗性等社会功能方面呈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但是不能由此否认其对艺术性的追求,这一点可以从鲁迅先生跟李桦先生的通信中得以验证。“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16]”,“木刻的美半在纸质和印法”[16],“木刻究以黑白为正宗”[16],“艺术要更好地为革命服务,必须使它成为具有艺术性的工具:它的艺术性愈高,这个工具就愈锋利,不应片面强调哪一方面”[17]。这可能是“新兴版画运动”在中国绘画史上最大的价值,由此也可解释传统复制木刻不能进入新时代视野的主要原因。鲁迅先生主张“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16],青年木刻艺术家以此为指导,创造出了喜闻乐见的新兴木刻语言。延安木刻“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艺术形式的日趋民族化。延安木刻民族化的探索,有明确的目的,是以群众化为前提,促进木刻作品适应工农兵群众的欣赏习惯,更好地成为激发他们革命觉悟的精神粮食”[18]。陈烟桥的《拉》借鉴了麦绥莱勒在《我的忏悔》中的表现技法,李桦的《怒吼吧!中国》则运用中国画的线条与人体解剖结构来造型,《识一千字》则直接吸收了民间木版年画的用色方法。可见,在艺术语言上,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采取“以洋入中”、“以古入今”的改进策略,既发展和超越了民间复制年画“严谨、严格、近乎苛刻的制作程序和工艺特点”[19],与落后、媚神、娱乐的民间传统作别,又改良了西方木刻的明暗对比和阴刻法,与先进、民主和开放的革命精神拥抱,迎合了国人向往先进、民主、自由的时代需求。尽管“新兴版画运动”经历了一个“洋味太重,老百姓不易接受”[20]的早期阶段,但经过一大批新兴木刻艺术家们的努力,最终满足了国人新的欣赏和审美习惯。“新兴版画运动”以“绘画性”来带动“文学性”,以“文学性”来引导“绘画性”,通过木刻新技法的发明创造,确立了木刻版画的新主题、新风格和新的审美趣味,进而实现为革命宣传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下的绘画创作中要合理配置“文学性”要素与“绘画性”要素的比例。既不能因为重视“文学性”要素而轻视“绘画性”要素,也不能因为重视“绘画性”要素而轻视“文学性”要素。割裂“文学性”与“绘画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都是不合适的。理性地看待“文学性”对绘画创作发展的潜在影响这一文艺现象,这既不是毒蛇猛兽,也不是可有可无,在绘画创作中既要发挥“文学性”作为成熟学科对绘画主题深度、广度、功能表达的指导作用,又要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尺度内,不能牺牲“绘画性”,而侵占和破坏绘画的本质。
注释:
①从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对《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的视觉呈现,到曹植“存乎鉴戒者,图画也”,王微的“以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再到王维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张彦远的“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洞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以至由魏晋南北朝萌芽的“书、画、赞”(“灵帝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传统发展到元代逐渐确立的“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中国文艺审美系统,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文学对绘画发生潜在影响的关系脉络。
②刘勰.文心雕龙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引自2004年美国华盛顿考克兰艺术画廊的展出“创造:方塞卡绘画新作展”中的一次对卡伦·赖特的采访,卡伦赖特是驻扎在纽约的一位独立的馆长和评论家。
④陆机语,参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
⑤谢赫.古画品录,文渊阁四库全书。
⑥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
标签:文学论文; 版画论文; 木刻版画论文; 鲁迅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绘画史论文; 美术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