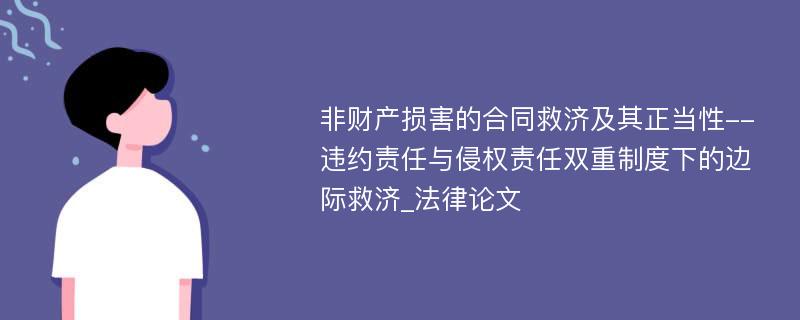
非财产性损害的契约性救济及其正当性——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二元制体系下的边际案例救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际论文,契约论文,违约责任论文,财产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问题的说明
契约的全部意义在于履行,因为它不仅是当事人满足自己需要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协作之必要途径。而违约除了破坏这种个人的期待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外,还可能导致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非财产性损失,那么对于这种损害是否给予救济以及给予什么样的救济,在生活逻辑中似乎没有什么疑义,但在法律逻辑世界中,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民事法律救济制度主要是采取违约与侵权的二元制救济体系,合同法的功能被经典性地限定于期待利益或者信赖利益的赔 偿。按照美国学者贝勒斯的观点,合同法的功能在于保护“正值”的交易。而对于就固 有财产权及人身权的损害则归入侵权法的救济范围,即贝勒斯所谓的侵权法的功能在于 保护“负值”的交易。(注: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蒋兆康等译,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如果违约行为不仅侵犯了非违约方的合同之期 待利益,并且也侵犯了其固有利益,特别是非财产性的利益时,就会出现契约与侵权的 边际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国家立法、学理和判例看法不一,而且欠缺使其赔偿正 当化的理论与实证法上的说明,故有论述之必要。
那么,因违约而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可能会以什么形式表现于现实之中呢?对于这些因违约造成的损害是否给予赔偿,以及给予什么样的赔偿?这将要是本文论述的主题。
二、学说与判例的历史与现状
(一)英国的判例与学说
1.否定性的经典性判例规则
可以说,确认非财产性损害不予以赔偿的著名案例,来自于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于1909年审理的阿迪斯诉格兰冯(Addis v.Gramophone Co.Ltd)一案的判决,该 案被称为英国合同法上的经典案例。该案的案情是:原告由被告雇佣为经理,经营被告 在加尔各答的事业。被告与原告约定采用周薪制,每周为15英镑,并且每做成一笔生意 便有相应的提成。如果被告想解雇原告,必须提前6个月通知原告。后来被告提前6个月 通知原告,但却以粗暴的、令人感到屈辱的方式立即解雇原告并指派另外一人取代他。 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其6个月的薪金和提成,同时要求赔偿由于被告“突兀 的、压迫性的、难以忍受”以及“屈辱性和粗暴性”的解雇方式所造成的情感和名誉损 害。(注:Smith & Thomas:A casebook on Contract,Tenth Edition,Sweet & Maxwell ,p.608.)
尽管对该案是否真正确定了因违约而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不予赔偿的规则,尚有争议,但英国绝大部分法官与学者认为,阿迪斯案的判决结论是:非金钱损失在合同法上是不可赔偿的。也就是说,对于第一损失(薪金和提成)是可以赔偿的,而对于第二损失(情感与名誉伤害)则不能获得赔偿。(注:[英]纳尔森·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489页。)学者基缇(Chitty)也指出:合同中不能给原告的情感伤害,或者违约造成的精神痛苦、烦恼以及名誉损失予以赔偿。(注:Chitty on Contract (1994),Sweet & Maxwell,27 th Para 26-041.)其实,在阿迪斯案以前,英国的许多判例已 经给予因违约而造成的情感和精神损害以赔偿,由此发生的争论和分歧似乎已经获得解 决。(注:[英]纳尔森·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于梁慧星主 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513页注释(15) 。)但阿迪斯案似乎毫无疑问地使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而且这一判例对于英国,甚至 可以说对于整个英美法系国家产生了基础性影响。对此,英国学者指出:如果认为现代 整个合同法的基础的生长奠基于上议院于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中所作判决,这种说法并 不为过。许多判例一再重申这一规则:对于因违约导致的创伤、精神痛苦、情感伤害或 者烦恼不允许给予一般的赔偿。(注:[英]纳尔森·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 ,肖厚国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 00年版,第488页。)
2.否定性学理
为了解释并对违约中的非金钱性损失不予赔偿提供正当的说明,学理上出现了各种各 样的理由,大致有:
(1)证据障碍理论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非财产性损害(特别是精神伤害)是无形的、主观的,因而缺乏客观的证据加以证明,没有科学的方法实现这一要求。因此,为防止许多虚假的、微不足道的精神伤害案件被赔偿,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大门全然关闭。
(2)计算障碍理论
拒绝给予违约中的精神伤害以赔偿的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计算困难的理由,即非财产性伤害不同于财产性伤害,其难以精确地计算。
(3)惩罚性赔偿禁止障碍理论
这一理论以下列理由来反对对违约中的非财产性损害给予赔偿:合同法上的赔偿仅仅以补偿性赔偿为原则,如果给予非财产性损害以赔偿,无异于对违约处以惩罚性赔偿。对此,巴克马斯特尔在一则判例中指出:在侵权法中我们所熟悉的惩罚性赔偿于合同中没有适用余地,对情感或者尊严的伤害也因此不被考虑。
(4)风险分配与成本障碍理论
对非财产性损害不予赔偿的又一理论是风险分配问题,即精神伤害或者焦虑几乎是基于合同许诺所产生的期望的必然伴随物,因此缔约方必须加以承受。如果允许对精神伤害等进行赔偿,违约一方的责任将变得模糊不清,它会随着受害者一方的主观感受而不断波动,其结果是契约的缔结与契约权利的分配将面临新的风险,商业和贸易会因之而严重受阻。另外,还会导致缔约成本的加大而又不能使双方获益。
(5)“可预见”障碍理论
这一理论主张,不给非财产性损害(精神伤害或者情感伤害)以赔偿,是因为在一般合同中,尤其是商事合同中因违约产生的精神伤害不在合同双方的考虑之内,即是不可预见的损害。(注:[英]纳尔森·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于梁 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499-501 页。)
3.肯定性学理
虽然说英国主流观点认为,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确立了法律拒绝对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进行赔偿的规则,但现在已经有许多学者对该案是否确立了这一基本的原则提出质疑和批评。垂特尔(Treitel)教授指出:严格说来,Addis v.Gramophone Co.Ltd.案仅为限制不当解雇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威案件,但是在过去该案亦被认为是广泛支持合同诉讼中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然而这样概而括之的推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并且于现今受到诸多之限制。首先,在违约导致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时,可以就疼痛(pain)与痛苦(suffering)获得损害赔偿是非常明确的。这样的损害赔偿考 虑了原告的精神痛苦(mental anguish),同时亦包括了情感损失(injured feelings)赔 偿。进一步言之,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应当包括因情感受损而产生的肉体与心 理疾病,而基于此等疾病可以获得损害赔偿,只要该等疾病的产生并不太过遥远。其次 ,对于身体上的不便(physical inconvenience)亦可要求损害赔偿。(注:G·H·Treitel:The Law of Contract,Seventh Edition,Sweet & Maxwell,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p.762.)有的学者经分析后认为: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并不存在一般 地否定非财产性赔偿的规则性基础。例如,纳尔森就认为: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不应成 为对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给予救济的障碍,该案判决的真正宗旨是:在违约之诉 中原告只能就违约造成的损失获得赔偿,他不能就非因违约发生的损失获得赔偿。也就 是说,一般规则是合同中的损害必须是因违约而自然生发的损失。(注:[英]纳尔森· 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 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490页、492页。)
按照纳尔森的观点,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并没有确定什么损害是不可以赔偿的,即不是从损害的结果来考虑赔偿问题的,而是关注什么原因引起的损害是不可以赔偿的。即使是非财产性损害,只要是由违约原因引起的,也是可以赔偿的。实际上,其与富勒所说的“附带的信赖”在什么情况下受法律保护有相似之处。
不仅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没有成为对非财产性损害进行赔偿的规则性障碍,而且所有的反对理论都缺乏说明力。首先,证据障碍的理由无法为绝对的、完全的不赔偿的做法提供合理的解释,有许多不予赔偿的例外已经使法官们相信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是真实而且严重的。其次,计算问题根本没有说服力,“不可计量”的问题是实际的困难而非原则性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法官已经完全习惯了用数字来表达无形的东西。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操作上的不精确应成为赔偿的障碍,实际上法官一直在努力解决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再次,违约赔偿中禁止惩罚性赔偿是一般原则,但这并不等于说对违约造成的情感伤害就不予赔偿,对此赔偿不等于惩罚性赔偿。第四,至于风险分配与成本障碍,也存在另外一面,假如一个人知道法律不会忽视一方违约带给他的精神伤害,那么他将更愿意与他人缔结契约,并进而信赖契约。故通过赔偿规则对精神伤害提供保护会鼓励人们缔结契约,也因此会促进而不是阻碍商业与贸易。最后,“可预见”障碍被许多日常经验表明,情况常常相反,甚至那些反对给予赔偿的支持者也已经承认:痛苦、受挫、焦虑等不是不可预见的,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在对所有的反对理论与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的判决进行分析后,纳尔森认为:就非财产性损害赔偿问题,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的判决并不是一个障碍,反对理由也都缺乏说服力而不能令人满意。最好的方法应是通过创造和扩张例外规则,以超越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适用的范围。(注 :[英]纳尔森·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 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499-503页。)
4.肯定性判例及其发展
同纳尔森一样,一些联邦法官也认为,拒绝对精神伤害进行赔偿的规则,缺乏原则上的有效基础。因此,英国判例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突破阿迪斯诉格兰冯一案的困扰,创造了许多对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救济的例外,翟维斯诉天鹅旅游公司(Jarvis v.Swans Tours Ltd)一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外。被告,某旅游公司,刊登广告 说以丰厚的条件提供瑞士家庭式晚会,承诺将会有非常美妙的时光。原告支付了63.45 英镑向被告预定了一个假期,并于其年度两周的假期时去度假。第一个星期只有13个客 人,第二个星期连一个客人也没有了。假期在许多方面均与广告小册子中描述的不相符 合。一审法院法官判决原告获得31.72英镑的损害赔偿。原告提起了上诉。上诉法院法 官丹宁勋爵(Lord Denning)在判决中说道:法律的立场是什么?我认为广告小册子中的 说明构成了陈述或担保。对陈述或担保的违反给予Jarvis先生以一项损害赔偿请求权。 那些说明究竟是陈述抑或是担保,并无区分之必要,因为根据1967年之不实陈述法案(Misrepresentation Act),对于不实陈述与违反担保均可获得损害赔偿之救济。
丹宁勋爵指出,本案的问题是:损害赔偿的数额是多少?他指出,本案中的法官似乎采取了受害人实际支出的数额与所获之数额差额的立场。而丹宁勋爵认为,通常以为基于违约行为不能取得精神损害赔偿的看法早已过时。在一个适当的案件中能够基于合同而获得精神损害(mental distress)赔偿,正如基于侵权行为可以就所受之惊恐(shock)获得损害赔偿的道理一样。度假合同、或者其他有关提供娱乐及享受的合同,就是这样的案子。如果缔约方违反了他的合同义务,那么就应当对相对人因此而遭受之失望(disappointment)、痛苦(distress)、悲伤(upset)以及沮丧(frustration)提供赔偿。 基于这一观点,他认为对本案中的原告的损害赔偿金应当是125英镑。(注:参见Smith
& Thomas:A casebook on Contract,Tenth Edition,Sweet & Maxwell,p.609-611.)
在英国判例中,给予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赔偿的这些例外主要有三种类型:(1)合同的目的就是提供安宁和快乐的享受;(2)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痛苦与烦恼;(3)由于身体上的不便所造成的非财产损害。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个人购买房屋的案件中,由于被告的过失而没有将房屋的缺陷告诉原告,使原告对房屋大失所望,因此给原告及家人造成的极大不便并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与烦恼。(注:程啸:“违约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5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版,第77-79页。)苏格兰法律委员会还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出于怀旧的原因,A想要用来自其出生与成长之家乡的大理石来建筑其新住宅的底墙。为此他与建筑人B签订了合同,并将石头之来源对于他的重要性告知于B。B使用了价值相同但更为优质的当地大理石进行了建筑。B的一个雇员于住宅落成之后将石头的来源告诉了A。法院不会作出实际履行的判决,因为这样既不合理又相当艰难。法院亦不会允许给予拆屋并予重建之费用的损害赔偿,因为这同样是不合理的。此住宅的价值并不比使用其他大理石而建成的低。因此基于价值减少的理由,将无法获得赔偿。然而大多数人认为对于B的违约行为A应当获得一定的赔偿。(注:Scottish Law Commission:Report on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Part 3(3.2),1999.)这种赔偿显然是对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的合同性救济。
在苏格兰,虽然判例对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给予赔偿几乎成了一种规则而非仅仅是例外,但是,是否通过立法改革明确这一规则,却存在争议。法律委员会(Scottish Law Commission)的立法建议认为:应当明确规定,除了受限于通常之遥远 性规则外,由违约行为引起之损失或损害均可获得赔偿,包括任何类型的非财产损失或 损害,尤其应包括缔约所意欲获得之满足的丧失以及表现为疼痛、痛苦或精神痛苦等的 损害。然而建议委员会(Faculty of Advocates)对此却持怀疑态度,认为合同法乃是规 范经济关系的法律,鉴于对于违约行为所引起的非财产损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已经能够 获得赔偿,因此建议关于此点法律应当通过个案的方式予以发展。而法律委员会(Scottish Law Commission)却坚持承认,鉴于该领域内长期以来所存在的种种困难, 通过立法进行改革乃是一个更为迅速、更为可靠的方法。(注:Scottish Law Commission:Report on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Part 3(3.7,3.8),1999.)
(二)美国的判例与学说
美国的判例、立法与学说对于此一问题的态度与英国基本相同,即作为一般原则不承认对非财产性损害的合同救济,但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对其给予救济。《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353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不允许对因情绪受扰产生的损害(Loss due to Emotional disturbance)获得赔偿,除非违约同时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或者合同或者违约是如此的特殊以至于严重的情绪受扰成为一种极可能发生的结果。
美国判例也支持对非常情况下因违约引起的非财产性损害如精神损害等给予法律救济。在卡拉诉音乐公司一案(Carla Deitsch et al.v.The Music Company)中,原告与被告签定了一份合同,双方约定被告为原告即将举行的婚礼招待会提供一支四人组成的乐队。婚礼招待会预定从早上8点举行到午夜,合同约定费用为295美元,原告在订立合同后预交了65美元。另外,原告还为婚礼聘请了一名招待、一名摄像师和一位独唱者,以便与乐队共同演出。然而乐队却没有来,原告与被告多次联系均未成功。在哀叹与愤怒之后,原告只好请一位朋友帮助拿来设备播放音乐,等到安装好这些设备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法院认定了被告的违约行为,并且认为单纯地赔偿原告遭受的定金损失或者聘请其他替代乐队的价金都不能充分地补偿原告遭受的损失,原告有权获得对其精神的痛苦、不便的赔偿以及对招待会价值降低的赔偿。(注: 程啸:“违约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5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版,第83页。)
当然,对于什么样的非财产损害给予赔偿,什么样的非财产损害不给予赔偿,法官之间也存在分歧。例如,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1973年审理的沙利文诉奥康纳(Sullivan v.O'connor)一案中,法官之间就存有争议。不过,最终法院采纳了肯定的 观点,即应对手术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但应限于违约人可预见到的精神 损害。(注:Sullivan v.O'connor,Massachusetts Supreme Judicial Court,363 Mass .579,296N.E.2d 183(1973).)
(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说与判例
1.法国
法国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合同关系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当事人的人身利益而仅仅在于保护其经济利益,故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人身损害不属于赔偿的范围。但现在人们改变 了看法,谁也不会怀疑合同关系中的人身损害可以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人身损害那样得 到赔偿。这就表明,就损害本身来说,合同中的损害与侵权中的损害并无本质的不同。 (注:[法]卡尔博尼,Les obligations,转引自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 社1995年版,第320-324页。)法国的判例也承认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是可以赔偿的。 (注:[英]纳尔森·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于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506页。)
2.德国
德国学理与立法一直比较顽强地坚持债务不履行责任仅限于财产性赔偿,而对非财产性损害不予赔偿。虽然其判例也对诸如“非财产性损害的商业化”予以承认,但仍然没有超出财产性赔偿的限制。而所谓“非财产性损害的商业化”是指凡交易上得以金钱支付方式购得的利益(例如享受愉快、舒适、方便等),依交易的观念,此种利益具有财产价值,从而对其侵害而造成的损害,应属于财产上的损害,被害人得请求金钱赔偿。(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7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这种做法主要用于旅游合同。德国曾经有一判例确认了这种损害:原告预定与妻子 于1953年3月27日开始搭乘轮船前往国外度假18天,其于3月23日将装有衣服的行李箱报 关检验。由于检验员的疏忽,致使行李被另一海关官员怀疑报关手续尚有欠缺,予以扣 留待查。之后经核对确认手续无误后,海关答应继续运送行李。在海上旅行起程后的4 月7日以空运送达原告。原告主张因行李迟到,使夫妻二人无法于旅行途中正常地换穿 衣物,要求海关赔偿其由此遭受的损害。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不便。法院 认为,原告所遭受的实为财产上的损失。原告与船运公司缔约,其目的不仅在于送二人 到达目的地,而且在于提供包括原告夫妻在内的所有游客享受不受干扰的旅行快乐,原 告用总额1800马克“购得”这一享受。由于行李箱被扣,致使原告遭受严重侵害。这种 侵害属于对具有财产价值对价的侵害。(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7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1页。)
在这里可以这样认为:德国判例已经通过将非财产损害商业化的理论对非财产性损失给予了实际的合同救济,只不过其根据是“财产性损害”。特别是在旅游合同中,适用这一理论已经等同于英国判例中的第一种与第二种类型,即“合同的目的就是提供安宁和快乐的享受、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痛苦与烦恼”。1979年德国民法典修订时,已经将这种思想贯彻于第651条。
通过以上对许多国家的学说、判例的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违约损害中的非财产损害已经被许多国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予以承认并给予契约性救济。但是,传统的违约与侵权二元制救济体系仍然存在,对于诸如人身伤害与精神损害等非财产性损害给予合同法上的救济不过是一种例外的处理方式,它是判例与学理对于这种违约救济二元制体系划分的僵硬而不能适应边际案例的一种补充而已。即使极力主张对违约中的非财产性损害给予合同救济的英国学者也承认这是例外。(注:[英]纳尔森·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503页。)而上面已经提到,美国缺乏统一的规则。
三、对非财产性损害给予合同救济的理论依据与实证法依据
(一)从理论与实证法上解释对非财产性损害给予契约性救济的必要性
虽说许多国家的判例给予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以合同性救济,但如何从理论和实证上给予其正当化说明却并非易事。纳尔森教授虽然极力主张对于这种损害给予赔偿,他也是从反面来论证,即认为阿迪斯一案没有确立给予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以合同性救济的规则性障碍,各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不具有充分的说明力,但是,他却没对为什么给予合同性救济提出正面的合理说明。他指出:即便是那些认为阿迪斯 一案确立了对精神伤害不予赔偿规则的判例也认为,这一规则也有一些例外。但为什么 有一些例外,这些判例尚未给予满意的解释。但是,如果不能在理论与实证法上给予正 面的合理说明而仅仅是法官自己凭着什么是合理的想象而裁量与司法,极有可能造成权力滥用,最终会破坏这一制度的内在价值。因此,有必须从理论和实证法上给予正面的正当化说明。
(二)“预期利益 + 可预见性”公式的涵摄范围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对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救济的例外主要有三种类型:(1)合同的目的就是提供提供安宁和快乐的享受;(2)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痛苦与烦恼;(3)由于身体上的不便所造成的非财产损害。那么,这些情形能否被纳入到“预期利益 + 可预见性”公式下解决?
其实,我们可以把前二种非财产性损害称为“目的性合同范围内损害”,即这种合同的目的就是要为当事人提供非财产性享受,一方支付价金,另一方为其提供非财产性对价。许多英美法系学者都主张对这种“目的合同”之目的不达时,提供合同法上的救济。例如,秉哈姆(Bingham)法官在布里斯一案(Bliss v.South East Thames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y)中指出:如果合同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快乐、放松、心灵宁静或者摆 脱悲伤,在合同目的不达或者效果相反的时候,违约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注:(1987)ICR 700。)垂特尔教授也认为:在这类合同中对违约造成的目的受挫给予(诸如精神伤害)赔偿实属正当与合理。(注:G·H·Treitel:Treitel On Contract,Eighth Edition.London:Sweet & Maxwell Press (1991)877.)在德国,判例也将这种 损害作为“财产性损害”而予以合同法上的救济。那么,这类非财产性损害是否是“预 期利益损失”?
我觉得,这种利益损失应当是预期利益损失。因为预期利益就是指缔约人对合同的期待价值,法律保护这种利益的目的在于使缔约人处于如同合同得到正常履行后所应处的处境。而在这种“目的合同”中,预期利益实际上就是非违约方在这种合同得到履行后所应处的精神状态(非财产性状态)。例如,旅游合同是典型的“目的合同”,旅客向旅游公司支付费用,目的就是得到约定的服务而达到心理愉快和精神放松。如果旅游公司违约而使这种目的受挫,其受到的真正损失不仅仅是其已经支付的费用,而是对“合同得到履行后精神应处的状态的预期利益”的破坏。因此,法律对这种非财产性损失的合同救济,正是对预期利益的保护。不能仅仅因为这种预期利益的特殊性,就把它排除在合同救济大门之外。还可能有一种情形,即不仅应当得到的精神状态没有得到,反而使自己的精神或者心情或者身体比缔约前还要糟糕。这一问题已经是“加害给付”的问题了,我们下面讨论之。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判例又重新回到“预期利益”规则中去为这种救济寻找基础根据,即以当事人对精神利益的预期或者期待为前提。也就是说,将发生赔偿责任的前提建立在双方在合同中允诺的当然预期之上。依照这种标准,只要违约行为所违反的一方的某种精神利益是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合同的预期并可以成为合同履行利益时,就可以此标准得到赔偿。皮特森(Peterson)法官在迪森(Diesen v.Samson)一案中指出:婚礼照片可以使新娘与新郎及其亲属朋友重温美好的瞬间并获得愉快的体验,而对于其他人并不具有利益。双方在合意中明显表示要使一方在数年之后还可以享受这种愉悦。被告的违约行为使这种体验的可能性永远消失。因此,此案适合精神损害赔偿。(注:宁红丽:“旅游合同研究”,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2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版,第65页,注释第52。)
我们也可以说,对这种预期利益的保护不在于仅仅对“客观财产利益”的保护,而在于对于“主观性非财产利益”的保护。在英美法系,还有一种支持法院依违约判决一方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合同对于原告而言意味着一种主观价值,这种主观价值与由市场价格所代表的合同的经济价值截然不同。法律必须支持在某些场合中允诺的价值对于该方而言通过完全履行可能获得的经济价值的超出部分,这个超出部分就是“消费者剩余”。确切地说,“消费者剩余”代表着一种个人的、主观的、非金钱的收益,因此不能用金钱衡量其确切的 价值。但无论如何,法律应当承认并在不当履行出现时给予赔偿。(注:这是马克斯狄 尔(Mustill)法官在“电子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诉孚斯”一案中的判决意见。见Electronics and Construction Ltd v.Forsyth,(1995)3 All ER 268,289;宁红丽: “旅游合同研究”,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2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 公司2002年版,第48页。)
由此可见,对“目的合同”中违约所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害的赔偿并没有超出传统合同上的预期利益的保护范围,只不过这种预期利益的确有许多主观成分,因此,在计算与证明方面有许多困难。但绝不能因技术上的原因而否定对其赔偿的合理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这种损失的赔偿有没有突破“可预见性规则”?
一般来说,为了防止对违约人之赔偿责任范围的无限扩大,许多国家的合同赔偿一般限制在违约方在缔约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其违约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的范围内。在此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一般来说对违约的损害赔偿不能超出期待利益的范围。美国学者富勒在论述为什么合同法以预期利益作为最高赔偿额时,曾经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富勒看到:《德国民法典》(第122条、179条、307条)规定信赖利益的保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赔偿均不得超过期待利益,而美国的判例暗含与德国民法典相似的处理方法。基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永远不得超过期待利益的价值,这一观念有什么依据?富勒通过分析认为:信赖利益超过被告允诺的合理价值时就表明原告从事了一项亏本的交易,而允许原告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大于期待利益(约定的合同价格),那将意味着法律允许原告将一种亏本的交易的风险转嫁给被告。因此可以得出这一公式:在对因信赖某合同而发生的损失寻求赔偿的时候,我们不会使原告处于一种比假定合同得到了完全的履行他所应处的状况更好的状况。(注:(美)L·L·富勒:“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443页。)我 们可以对富勒的话作一个简单的解释:一种赢利的交易应该是这样的:合同约定的价格 (期待利益,富勒称为“毛期待利益”)不仅包括当事人为此支出的费用和成本(信赖利 益),而且,还应当包括扣除了这些费用和成本后的利润。因此,一种赢利的交易的信 赖利益不会大于期待利益。如果信赖利益等于期待利益,则说明这一交易是不赔不赚的 。而如果信赖利益大于期待利益,说明这一交易是亏本的,也就是说假如对方不违约, 非违约方获得合同履行也是亏本生意。假如在信赖利益赔偿中,使被告的赔偿额大于期 待利益,无疑等于将原告在一宗交易中的亏损转嫁给被告。富勒的这一精彩的论证在合 同赔偿仅仅限于物质赔偿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旦承认合同对包括精神损害的非财 产损害给予赔偿的时候,可能就要超出期待利益。对此,阿蒂亚指出: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损失可能是超出了预期的合同履行的范围,因此可能导致远远超过合同价值的损失 赔偿责任。那么,在合同法中运用的原则是被告要对他能够合理预见的其行为导致的全 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注:[英]P·S·阿蒂亚:《合同法导论》,赵旭东等译,法律 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498页。)在这种基础上,对于第三类非财产性损害,也可以包 括进来。
第三类非财产性损害是指由于身体上的不便所造成的非财产损害。这种损害很难将其归入“预期利益”中去,但是,它却可能是超出预期利益的那一部分可预见的损害。其 实,这已经属于“加害给付”的问题了。但是,在英美法系,“加害给付”问题是通过 “损害的可预见性”与“损害是否由违约行为自然引起”等方法进行救济的。在英国19 78年的一个著名案例H·Parson(Livestock)v.Uttley.Ingham & Co.Ltd中,被告向原告 (养猪场场主)提供并安装了一个大漏斗来装动物饲料。不幸的是被告忘记了打开漏斗顶 部的通风设备,结果一些饲料开始发霉,猪开始生病,接着由最初的疾病引发了非常严 重的猪瘟,造成许多头猪死亡。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全部赔偿,法院判决养猪场场主得 到了全部赔偿。因为这些损失是可以预见的结果。(注:[英]P·S·阿蒂亚:《合同法 导论》,赵旭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这在大陆法系为典型的加害给 付制度。
由此可见,预期利益与可预见规则能够解决英美法系中所谓的非财产利益的基本问题。但是,在大陆法系,却可能不能包括“加害给付”类型中的所有问题。因此,还需要特别讨论。
(三)加害给付案件中的非财产性损害问题
加害给付是指债务人所为的履行不合合同的本旨,除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外,尚发生对债权人固有利益的损害。也就是说,债务人的给付行为有悖债之主旨,除有可能造成债权人契约利益的损害外,尚有对债权人契约利益外的固有利益的损害。它实际上是合同法与侵权法作用范围的一个重合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可能导致对方所有权或者人格权损害,可能因为损害人格权而引起精神损害。对于这些非财产性损失,非违约方是否可以依违约之诉要求赔偿?
我认为,应当区分两种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1.如果给付中的“加害”行为,符合侵权行为之要件从而构成独立诉因的情形
如果加害给付中的加害行为能够作为独立的诉因,则除了精神损害之外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损失可以请求合同法上的救济,例如给付行为造成了他人的身体和财产所有权损害可以请求赔偿外,就精神伤害不能提出合同法上的救济。他可以在合同法上的救济之外,另行提起侵权之诉要求赔偿精神损害。当然,他也可以首先请求合同履行利益的赔偿,然后再以侵权之诉要求赔偿固有利益与精神损害。例如,一个顾客到一家商店购买了一台热水器。由于该热水器存在质量问题,使购买者在洗澡时被烫伤身体,遭受了履行利益、身体和精神伤害。在此,顾客有两种选择:(1)他可以直接要求履行利益和身体受到伤害的赔偿,而精神伤害另行以侵权起诉;(2)他只要求合同上的履行利益损害的赔偿,身体与精神伤害另行提起侵权之诉解决。第三种选择,即以违约之诉要求解决履行利益、身体与精神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存在的。
2.如果给付中的“加害”行为不能构成侵权之诉的独立诉因的情形
如果加害给付中的加害行为不能作为独立的诉因,则精神损害、财产性和其他非财产性损失可以请求合同法上的救济。例如,在合同履行中,仅仅违反了因“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附随义务,从而导致对方的财产、身体或者精神伤害的,可以违约之诉要求合同法上的救济。否则,受害方就得不到有效的救济。
这种区分观点可能会招致非议和批判,更有“教条主义”之嫌。虽然我也愿意承认将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所有损害统统纳入违约之诉下面得到赔偿,但是,既然我们仍然承认违约与侵权的二元救济体系,就不能仅仅以诉讼的方便为由要求用违约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即使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是否用违约解决这些问题,也存在不同看法。例如,阿特金森(Atkinson)法官对于将两种诉因合二为一表示忧虑:在诉讼中人们试图将诽谤或者侮辱之诉作为违反合同之诉的进一步恶化来处理。我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令人不愉快、令人尴尬的事了。正如被告在法庭中必须被许可一样,他被允许反驳诽谤观念、信赖权利或者提出一些他在因诽谤或者侮辱而提起的单独诉讼里他能提出的事实。纳尔森虽然主张对于违约中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但他也不主张将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合二为一。(注:[英]纳尔森·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于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497-498页。)
四、对非财产性损失进行赔偿的限制
(一)商业合同与非商业合同的区别
即使在英美法系国家比较多地承认对违约中的非财产性损失进行赔偿时,也担心这种做法会造成滥用而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因此,对违约中非财产性损失给予合同救济的第一个限制就是区分商业合同与非商业合同。一般来说,仅仅承认在非商业中存在非财产性损失,而在商业合同中则不存在这种非财产性损失。例如,在英国,法院首先认定系争合同涉及到原告的商业利益还是私人利益、社会利益还是家庭利益。由于商业合同的违反常常被视为商事交易的风险,法院一般不支持此类合同当事人基于违约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但如果合同涉及到私人利益、社会利益或者家庭利益,法院就会援引双方预期的通常标准,查明损失,然后决定赔偿数额。(注:见Ruxley Electronics and Construction Ltd v.Forsyth,p.280;宁红丽:“旅游合同研究”,载于梁慧星主 编:《民商法论丛》第22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版,第49页。)阿蒂亚 也指出:现在已经很清楚,这种损害(精神损害)在普通的商业交易中是不可能给予赔偿 的,即使原告属于普通消费者。(注:[英]P·S·阿蒂亚:《合同法导论》,赵旭东等 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页。)
我认为,这种区分是一个重要的和必要的限制规则,如果在纯粹的商业合同中也被允许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则任何情感和不愉快都会得到赔偿,最终将使合同这一交易工具不堪重负而死亡。
当然,也有人认为,商业性合同与非商业性合同的区别,实际上是可预见性的问题。例如,苏格兰法律委员会指出,在苏格兰亦有这样的案件:合同的性质已经表明在合同订立之时违约所引起之精神痛苦或精神损害是可以被合理预见的。其中有些案件表明应当对商业合同与社会合同进行区分,但是该种区分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是有疑问的。真正应当予以区别的似乎是那些于缔约时(因违约造成的)精神痛苦或损害已经被预见到或有理由被预见到的案件与那些无法预见到的案件。心理痛苦或精神损害是无法发生在公司或其他法律团体上的,尽管法律团体是能够感受到不安(trouble)与不便(inconvenience)。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商业合同(由法律团体参加的)中不可能存在精神 损害赔偿。(注:Scottish Law Commission:Report on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Part 3(3.3),1999.)
(二)可预见性和因果关系的必然性
如果以违约提出对非财产性损失的赔偿,应当注意这种损失是否是违约人在缔约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或者在加害给付的情况下,是否是违约必然(或者称为自然)引起的结果,以防止损失范围的任意扩大。就如丹宁法官所言:精神烦恼和痛苦是由被告契约不履行的行为所导致,这是判决赔偿的先决条件。(注:[英]纳尔森·厄农常:“违 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507页。)
如果一项损失不是被告之违约行为当然或者自然引起的结果,则不能将此责任强加于被告(违约人)。例如,一方违约,致使非违约方气愤而自杀身亡。在这种情况下,则不能要求赔偿因死亡而导致的损害结果。
(三)非财产性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
这里的非财产性损失主要是指精神伤害。应该说,在任何一种违约案件中,都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情感损害、失望和精神的不愉快,是否应当对这些损害都给予赔偿?答案 当然是否定的。在英国,只有当精神伤害达到一定程度,即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违约 不仅会导致精神伤害,而且还会导致比在普通案件里更深一层的精神伤害,即超过最低 限制水平的伤害时,才能获得赔偿。只有当原告使法官相信他所遭受的精神伤害是巨大 的时候才能得到赔偿。梅勒法官就指出:就单纯的烦恼、情绪的失落或者苦恼,或者就 某一特定的萦绕心头的情事所招致的失落感而言,如果没有导致现实的具体的麻烦,就 不能获得赔偿。(注:[英]纳尔森·厄农常:“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肖厚国译,载 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6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版,第504- 505页。)但什么是“巨大的”,什么“微小的”,什么是“具体的麻烦”,则是一个经 验的判断问题,也无非是用一个“第三人”标准进行衡量而已。
在我国台湾,只有当违约造成对债权人人格权的侵害时,债权人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在其他情形,即使债务人违约造成非违约人的巨大精神痛苦,也不能获得赔偿。
任何合同的违反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精神受挫,交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被认为已经对因违约造成的一般性精神损害之风险进行了默示性承担。只有当因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伤害超过“默示性承担”的限度,才能给予赔偿。
(四)原告减轻损失的义务
同财产性损失的赔偿规则一样,在一方违约后,非违约方应当采取适当的必要措施以防止损失的继续扩大。否则,就扩大部分,他无权要求赔偿。例如,在存在替代机会的情况下,非违约方应该抓住这一机会。比如,一个游客预定了一辆出租车去旅游,结果出租车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到来,他一等再等,结果出租车仍然没有来,直到他耽误了火车,从而错过了这一次旅游机会。他就无权就因此而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因为他不应该一直等下去,而只能等到时间允许的限度,留出足够的时间再打一辆出租车而不至于耽误火车。
五、我国对非财产性损失合同救济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学界之态度
我国民法学界对违约中的非财产性损失不一般地否定,但对于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主流观点却是否定的。例如,王利明教授认为:“有一种观点主张:具有侵权行为性质的违约行为造成他人非财产损害时,即使提起合同之诉,也能获得赔偿。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精神损害是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难以预见的,同时这种损害又难以通过金钱加以确定,因此,受害人不能基于合同之诉获得赔偿。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可以基于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而不必提起违约之诉。假如合同责任也可以对精神损害作出赔偿,就使得责任竞合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同时,王利明教授也反对在加害给付中对精神损害给予合同救济。(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74页。)另外,1999年《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2辑刊登了几位民法学者对一起“婚礼胶卷丢失案”的分析评论意见,三人都反对给予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失以赔偿。但最近也有学者对这种绝对反对给予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失以合同救济的做法提出批评。例如,有学者指出:对非财产性损害的赔偿根本不是先验地永恒地属于侵权法的问题,这种反对给予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失以合同救济的做法是法学中的“原教旨主义”。在一定情况下必须给予违约造成的非财产性损失以合同救济。(注:程啸:“违约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5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版,第105页。)宁红丽也认为:对于旅游合同中的精神损害应当给予赔偿。具体来说,如旅行社不完全给付造成旅客人格权受损的,旅客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旅行社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没有造成旅客人格权受损,但导致合同目的严重不达的,旅客也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应当限制赔偿数额。(注:宁红丽:“旅游合同研究”,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2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版,第55页。)
(二)判例之态度
我国法院判例对此一问题,有的肯定,有的否定。让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1.肖青刘华伟婚礼彩色胶卷丢失案(注:见《北大法律评论》,1999年第一卷第2辑,第679页。)
1992年9月3日,原告肖青将一卷拍有其与刘华伟举行婚礼活动的彩色胶卷交给被告旭光彩色扩印服务部冲洗,并预先交付服务费用18元。第二天,肖青依约取照片时,被告知照片可能被他人误领,让原告等等再来。后原告多次催要无果。为此,原告要求赔偿损失,而被告只同意退回预先交付的18元费用及胶卷费用。协议不成,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
该案的法官认为:丢失他人的结婚活动的纪念胶卷,不仅给消费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精神伤害,应当给予精神赔偿。这一判例结果与前面提到的皮特森(Peterson)法官在迪森(Diesen v.Samson)一案中的判决结论一样:婚礼照片可以使新 娘与新郎及其亲属朋友重温美好的瞬间并获得愉快的体验,双方在合意中明显表示要使 一方在数年之后还可以享受这种愉悦。被告的违约行为使这种体验的可能性永远消失。 因此,此案适合精神损害赔偿。
2.冯林等出国旅游被扣案(注:刘琨:“旅行社未尽义务被判罚”,载于2001年9月9日《人民法院报》。)
原告冯林与段茜倩2000年1月12日与自称是海峡旅行社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张某签定了有偿出国旅游合同。后来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张某又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招商国旅总公司所组织的马来西亚旅游团。招商国旅在接受原告参加其旅游团后,没有审核二人的手续和签订的书面合同,也未将原告列入其旅游团的名单,以至于原告二人在马来西亚的滨城刚下飞机就因证件不符而被当地政府扣留,后被遣送回国。原告向北京市朝阳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双倍返还旅游费用以及利息,并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因疏忽导致原告人格权受到损害,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20000元。二审法院认为数额过高,减至5000元。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加害给付的案件,在这一案件中法院也给予精神损害以合同法上的救济。
3.骨灰丢失赔偿案(注:转引自程啸:“违约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于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25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版,第102页。)
1987年1月16日,原告艾新民之兄因病去世,遗体在青山殡仪馆火化。火化后,死者亲属用90元购买了一个骨灰盒,将之存放于青山殡仪馆寄存处,寄存期为5年,交付寄存费用10元,并领取了骨灰寄存证。每年死者忌日亲属都去祭奠。1989年当死者忌日,其亲属再去祭奠时,被告知骨灰丢失,青山殡仪馆表示尽力寻找。其后多方寻找终无结果。1992年1月,死者骨灰寄存期已到,死者亲属要求青山殡仪馆归还骨灰未果。死者之弟诉诸法院,要求青山殡仪馆赔偿死者亲属1000元精神损失费,并修一座坟墓下葬死者生前遗物。
该案最后虽然采取调解解决,但法官已经肯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4.因旅游景点减少而引起的纠纷赔偿案(注:见《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6民事卷),第618-624页。)
原告李海健等9人利用春节假期,参加被告羊城旅游公司组织的南岳衡山旅游活动。被告在其刊登的广告上称:此次旅游活动旅游景点8处。然而开始旅游后,不但景点仅有3 处,而且居住条件恶劣:男女8人混住一屋。在事先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导游未随团同 行而让原告自行返回。于是,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全部旅游费用、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及未观赏5个景点的误工费用。
该案中,法院只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请求,特别是没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认为该案并不构成民法通则上所称的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德国、法国等被给予合同救济的“目的合同”在我国竟然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三)立法规定
我国《合同法》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主要有两个条文值得研究,即第113条与第122条。
1.对《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解释
该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这是一个典型的“预期利益 + 可预见性”公式,它应当能够解决诸如旅游合同等这种“目的合同”之目的不达所带来的非财产性损害的问题,也应当包括因目的不达而造成的精神伤害。因为在这种合同中,其预期利益显然是精神问题而不是财产性问题。
2.对《合同法》第122条规定的解释
该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的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从法律解释 的角度看,(注:我一直坚持法律解释中以客观解释为主的原则,即应着重从法律条文 的文义所表达的意思解释,而不是主要从立法者的目的去解释。因为,大陆法系中,谁 是立法者,一直是个不清楚的问题,即使是参加立法的人,他们之间的意见和看法也不 一样。特别象我们国家,对于同一条规范,参加立法的人的解释也不同。因此,不能依 立法者之主观方面进行解释。在这里,我仍然是从《合同法》第122条所表达的而非想 表达的意义来解释。)应当作以下理解:
(1)该条既是对于加害给付的规定,也是关于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
因为,它规定因违约造成人身、财产权益损害的,受损害方有权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见,违约之诉已经可以解决对固有利益——人身与财产损害的赔偿问题。这显然已经是对加害给付的规定,显然已经承认了对非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赔偿。
它同时又规定:因违约造成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违约人承担侵权责任。这显然又是竞合的问题。
(2)这一规定否定了在加害给付中对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的合同救济。
从该条文的规定来看,如果违约的受害人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就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如果非违约方能够以违约之诉请求违约方承担因违约造成的人身、财产权益和精神损害的,就没有必要再规定“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显然,该条对“或者”部分的规定,主要在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这与王利明教授的 主张是一致的。
但我认为,该条规定似嫌不足。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答案:一是如果是加害给付,既有合同履行利益损失,又有人身权侵害,既有固有的财产损害,也有精神损害的话,既然违约之诉不能解决精神损害,则在提起违约之诉讼并获得胜诉判决后,是否还 可以另行提起侵权之诉要求违约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二是如果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 不能构成独立的侵权之诉,则这种情况能否直接在违约之诉中判予精神损害赔偿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应当可以。这里不能简单地套用“责任竞合”,如果仅仅利用所谓的“责任竞合”理论,就使得当事人无法获得所有损害的赔偿:要么只获得合同 利益和固有利益受损的赔偿而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要么仅仅能够获得固有利益与精 神损害的赔偿而不能获得合同利益损害的赔偿,这种选择无论如何是不合法律之本旨的 。所以,我觉得,在加害给付的情况下,在违约诉讼胜诉后,仍然可以提起侵权之诉, 要求违约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违约中虽有精神损害赔偿但不能构成独立之诉时,我觉得应当允许利用违约之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冯林等出国旅游被扣案中因旅游公司对游客安全的照顾注意义务来自于合同中的附随义务,而非一般的法定义务。这种损害不能单独提起侵权之诉。在这种案件中,不给受害人以精神损害赔偿,显然是不合理的。
六、小结
从实质上说,违约中非财产性损害赔偿之争议,实际上触及了传统民法上违约救济与侵权救济二元制体系分离的一个边际问题,它既是合同问题,又涉及侵权问题。因为这种法律关系是存在于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非纯粹合同关系,因此,就必然涉及不同法律救济领域的重合问题。实如中国古代的一则笑话:一个人死在了两县的交界处,头在这一县,而脚在另一县,此一人命官司由哪个县管辖?为此,两个县令争吵不已。 由此可见,人的死亡这种生活世界的逻辑与行政区划这种人为之事之间确有不合之处。大概法律这种人为之物与生活逻辑之间也常有边际性不符的情形。这时,应当通过扩张合同法之领域来解决一些看似应当由侵权法解决的问题。
从我国立法上看,找不出否定对“目的性合同”中非财产利益损害进行赔偿的规定。对于加害给付中的固有财产利益损害可以给予合同法上的救济,对于人身权这种非财产利益的损害也可以给予合同法上的救济,但对于因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应区分是否构成独立的侵权之诉而为处理。从判例看,我国法院实践中有的给予合同性救济,有的否定合同性救济。但是,在我国对这种偶然的判例研究并没有多少具有代表性的说明意义,因为法院在判决这些案件中,是否有意识地依照某种思想来判决,甚有疑问,可能基于公平因素,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如果是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出现的,就难以作为研究和说明的模型。
但无论如何,在遵守限制规则的前提下,在一定条件下应给予因违约造成的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非财产性损害以救济,是生活逻辑的必然要求。
标签:法律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法律救济论文; 精神损害赔偿论文; 合同目的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契约法论文; 法制论文; 违约责任论文; 法官论文; 民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