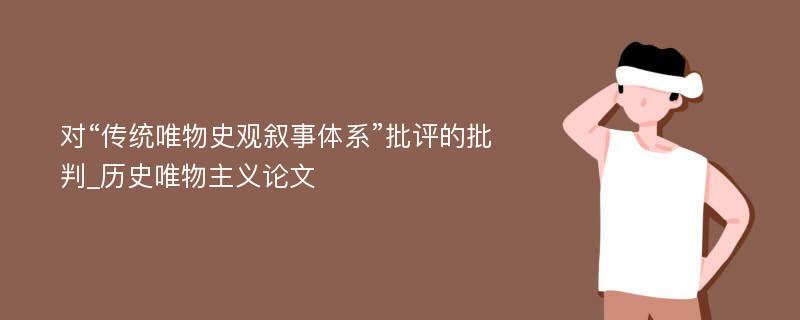
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批判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体系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俞吾金的论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以下简称“俞文”),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的挑战,并对“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否定。
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②的著名论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等重要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科学把握了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如果我们把“俞文”的观点一贯始终,不难发现,作者未能正确地看待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及自身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缺陷。因此,我们一旦指出“俞文”第一部分的认识是不恰当的,第二、第三部分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
“俞文”第一部分提出,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第一个从未引起人们深入反思的理论前设是:“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也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俞文”议论道,“这一理论前设是‘非生态学的’(non-ecological),亦即它没有考虑到人类在无限发展的生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总体性的生态危机。”“要言之,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始终缺乏一个必要的生态学的背景,这正是这一叙述体系必须在当代得以改革的重要理由之一。”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指出以下两点:第一,“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始终缺乏一个必要的生态学的背景”的判断,是“俞文”作者过分狭隘地理解生态学研究造成的,由此歪曲了事实和历史;第二,“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也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之“理论前设”,是“俞文”作者以违反科学论证原则的方式炮制出来的。
“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866年首先提出的,定义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目前,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然而,“俞文”作者把生态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生产、增长和发展的极限问题,地球资源和人口负载的有限性问题,生存环境的污染问题”。④如能正确理解生态学研究,“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始终缺乏一个必要的生态学的背景”的判断就是错误的。
“俞文”囿于对生态学研究过分狭隘的理解,不仅歪曲了事实也有悖历史的公正。1995年9月27—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一些学者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个生态哲学家,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蕴藏着许多闪烁着生态哲学思想的观点和主张。同时,马克思也是第一个社会生态学家,他率先把生态问题看成是社会问题,认为生态危机是社会危机的表面折射,主张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下去解决生态问题,只有消除了社会的异化现象,才有可能消除自然的异化现象。⑤可见,“俞文”断言“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也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理论前设”之一,这是作者违反科学论证的逻辑法则炮制出来的。在引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的论断后,“俞文”作出了如下议论:“显然,恩格斯的这篇讲话依然蕴含着这样的理论前设,即地球上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也是能够无限地向前发展的。”⑥任何人都不难看到:恩格斯的论断与“俞文”的议论之间根本没有逻辑联系!人们同样可以说,恩格斯的论断蕴含着“地球上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旦地球的资源枯竭了,人们也就不能吃、喝、住、穿了”之理论前设。所以,该议论中的“依然”二字用得很巧妙,正是它遮盖了“俞文”的循环论证。
“俞文”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第二个理论前设,即“科学技术从属于生产力的范围,正如生产力始终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一样,科学技术也始终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⑦并从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异化现象出发予以否定,进而否定了“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阐明以下三点。
第一,就观念形态或理论形态而言,科学技术仅仅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属于一般社会生产力范畴。作为精神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一旦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同物质生产活动相结合,就将发挥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转化为物质生产力或称直接生产力。历史上,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都是如此把握的结果。因此,“俞文”所说的“正如生产力始终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一样,科学技术也始终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是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扭曲后的观点。科学技术只有转化为物质生产力或称直接生产力,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才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反之,当科学技术的不恰当运用导致“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影响着人体健康和人类社会发展,破坏着社会生产力,此时我们绝不会说它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应该明确的是,指出“俞文”所说是不恰当的,并不等于否认“科学技术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的运用在历史上曾导致过“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了技术异化现象,就否认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学技术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
第二,我们不能从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异化现象出发,否认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学技术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更不能因此否认恩格斯作出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⑧论断。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把马克思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科学家”,⑨其中的“科学”二字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同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草稿》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看成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在此意义上,并为此目的,运用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生命要素。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比他更积极的战士”。⑩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终生致力于以科学研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的思想家、革命家、科学家,竟然在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科学巨著中,包含着否认“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倾向,这无疑是明显的悖论。这个悖论根源于“俞文”作者对马克思著作的断章取义和曲解。
第三,笔者有必要指出:“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并且永远是进步的、革命的因素”,与“俞文”所说的“科学技术始终是进步的、革命的力量”是不相等同的。前者是由“科学精神”所保证的。对此,李醒民写道:“科学精神以追求真理作为它的发生学和逻辑的起点……彭加勒明锐地指出,科学精神的这一逻辑起点对科学是至高无上的,他把‘追求真理’视为科学活动的‘目标’和‘唯一目的’,认为‘唯有真理才是美的’。萨顿径直视追求真理的忘我精神为科学精神:‘科学方面的舍身忘我精神是为真理而热爱真理,追求真理。一个人必须学会热爱真理,不问其利益和用途——无论是否有利可图,是否令人高兴,也无论是令人鼓舞或使人沮丧’”;“科学的光荣不在于它从未犯过错误,而在于它有错必纠、知错必改。科学理论具有可错性并不是科学的缺陷,识错和纠错恰恰是它通向真理的必不可少的阶梯。赖兴巴赫一语中的:‘如果错误一被认出为错误就得到纠正,那么错误的道路也就是真理的道路了’”。(11)可见,对科学、技术不作区分,简单地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科学”,是“俞文”陷入诸多混乱的原因之一。
“俞文”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第三个理论前设是:“作为观念形态或理论形态的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或者换一种说法,科学技术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12)并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关于“自然科学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观点进行了贬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阐明以下几点。
第一,“科学技术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不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观点,更不是其理论前设。如果否认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又何以理解“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13)论断呢?1996年2月,江泽民指出:“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14)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出台,200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都是努力推进科技兴国、科教兴国战略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实现良性互动的重大举措。在这里,科学技术承担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第二,作为观念形态或理论形态的科学(不是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这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的一个基本观点。它阐明了“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还是在现代西方学术传统中,意识形态一词都有反映或体现特定社会集团利益的含义,是一种与‘科学意识’不同的东西”,(15)“历史上和现实中,并没有什么封建主义的自然科学、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主义的自然科学的区分。因此,自然科学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16)自然科学“在其可能性上一般地服务于任何社会集团”。(17)
进一步讲,从思维和存在、观念与现实的一般关系看,意识形态也像科学一样是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但意识形态是按特定阶级的价值尺度去描述或解释世界,而科学则要求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去描述或解释世界;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是维护特定阶级的价值标准并使之普遍化,科学的核心原则是符合客观世界的真实联系及其规律性。这些本质的区别,决定了科学是不能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
“俞文”力图反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科学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观点,但因其对科学、技术不作区分,简单地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科学”,从而变成否定子虚乌有的“科学技术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令人十分遗憾。
第三,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科学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也不为特定的上层建筑服务,然而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利用科学技术为政治服务,科学技术就不可避免地与上层建筑相联系。正如前述拙文所阐明的:无论科学转化生产力还是为意识形态服务,都是以技术为中介实现的。在当代,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第一生产力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手段服务于政治,作为文化成果服务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没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是难以进行的。因此,科学技术在一定条件下执行着某些意识形态功能。应该明确,“俞文”未能正确对待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也是其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对问题的阐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辩护,这并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只有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才有决定性的影响。科学技术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样的角色出现,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下的人,取决于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操纵与控制,使人们失去自主性而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社会日益能够为广大居民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产品,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于是,在尽情消费、纵情享乐中,消除了社会的否定因素,达到和统治制度的和解与协调。在这里,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表现为对社会中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的压制,成为维系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发展的意识形态。但是,当他们一般地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也就把科学技术本身同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混淆起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和压抑,表面上看似乎来源于科学技术,而实际上它恰恰来源于由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把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说成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撇开资本主义制度来谈科学技术的所谓“罪恶”,把科学技术当成一切罪恶之源,这是根本错误的。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除了厌恶和空洞的否定外,根本找不到任何拯救人类的途径。
最后,我们要指出:“俞文”出现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违反科学论证的逻辑法则”的错误,与其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可谓相得益彰。“俞文”的第三部分写道:“意识形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断言意识形态是遮蔽真实情况的‘虚假的意识’了。虽然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意识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倾向,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却不再是‘虚假的意识’,而是反映自然规律的正确的认识。这就表明,即使是正确的认识或观念,当它被确立为绝对的权威,当它成为一种统治形式,或当它超出自己原本适用的范围被使用时,也完全可能被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在这里,意识形态的性质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重要的不再在于: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而是在于:它是统治人、支配人的观念性的力量,还是解放人、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精神性的力量。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即现代意识形态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统治人的观念的力量。”(18)据此,人们可以这样说:在摆事实、讲道理、辨明是非的科学论证中,遵从逻辑法则是“正确的认识或观念”,但是“当它被确立为绝对的权威,当它成为一种统治形式……也完全可能被意识形态化”,成为“统治人、支配人的观念性的力量”,而非“解放人、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精神性的力量”。于是,为了彰显“解放人、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精神性的力量”,“俞文”作者也就实践了“违反科学论证的逻辑法则”的“正义之举”。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③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32、133页。
④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33页。
⑤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⑥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33页。
⑦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3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2页。
(11)李醒民:《科学精神的规范结构》,陈光主编:《科技文化传播》,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12)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35页。
(13)江泽民:《论科学技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14)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68页。
(15)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9页。
(16)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17)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第373页。
(18)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