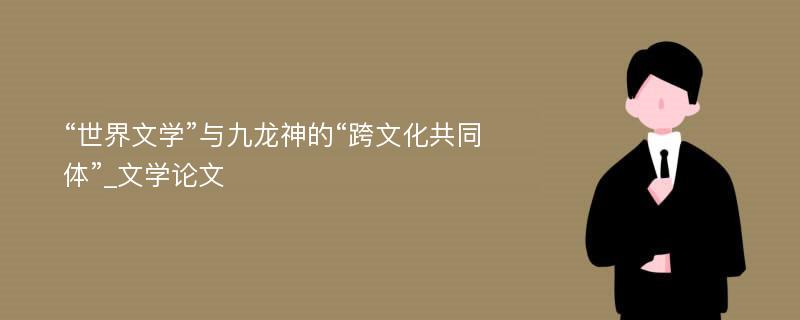
“世界文学”与久里申的“文际共同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久里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27年歌德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继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又再次使用了该术语,但时至今日,学界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与阐述并未达成共识。一种理解是:世界文学就是各国文学的总和;另一种理解是:世界文学是指那些超越族界、超越时代、广为流传并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优秀作品;第三种理解是:世界文学意味着世界各国文学将成为一统的时代,它表达各国文学将熔为一体的伟大理想。这是一种理想的人类文学与文学研究,但世界文学的时代还未到来。
尽管对世界文学的概念理解不一,但《世界文学史》这类著作却频频诞生。八九十年代,俄国与东欧学者正是在撰写世界文学史的实践中深刻体会了这一概念的困惑,他们通过不断的探索,在理论上进行了修正与创新,最后又把探索的成果具体运用于世界文学史的新型编写方法之中。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前苏联科学院在组织撰写9卷本《全世界文学史》的过程中,曾对世界文学的概念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不应把世界文学看作是各国文学的总和,而应把它看作是由历史流动的低级“文学单位”所形成的现象,这一现象复杂地互相制约,并在世界历史过程的系统内发展着。而每个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方式,不仅以其个别作家的名字与作品,而且还以它与其他文学的相互关系——发生学、接触学及类型学上的关系——所构成的有分支的系统。[①]这一观点突破了上述对世界文学的第一和第二种理解,强调了世界文学的动态性,但对这个“复杂现象”在理论上还没有作具体深入的论述。《全世界文学史》这部多卷巨著正是从文学与文学之间的过程角度撰写的,它是“总结苏联文艺学所积累的大量经验的一种尝试,这些经验既有研究世界国别文学史方面的,也有理论方面的,其中包括制定对人类艺术演进的比较研究原则”。[②]但这种尝试性总结的结果却并不理想。1989年11月14—16日,前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召开了题为“比较文艺学的现状与任务”的全国代表会议,主持人IO·维珀(一译维普勒)院士在开幕辞中指出:《全世界文学史》一方面在单独的章节中发展并加强了历史比较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又孤立地看待各个过程,以致造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材料堆砌。可见对世界文学提出理论上的认识是一码事,要把这一认识得心应手地运用于实践,则还存在一段需要克服的距离,其原因在于有关认识还有待于深化。因此维珀在闭幕辞中强调说,今后的理论研究应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揭示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建立“理论上的文学史”。
对世界文学过程的研究,一直是俄国学者感兴趣的课题。例如,B·沙伊塔诺夫在《作为概念的世界文学过程与历史现实》中就提出,正是在18世纪产生了关于文学世界性的意识,所以重点应研究18世纪。而Π·格林采尔在《比较文艺学与历史诗学》中,从历史诗学出发,对世界文学过程作了具体的较大范围的分期。依据他的观点,世界文学过程可划分为三个时代,而划分的原则首先是共同的艺术意识,其次是相应的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向和结构、范畴等级相似的共同诗学。第一个时代是艺术意识属于神话诗歌类型的古代,它包括古代的口头创作以及近东、中国、印度、前古希腊还未完全与口头创作分离的古文学。这个时代在欧洲大致结束于公元前6—5世纪,在近东结束于希腊化时期,而在印度与中国则结束于公元前后之交。这一时期的古文学与口头创作依赖于共同的神话诗歌观念,在诗学性质上十分接近(当然,是指实际的诗学,当时还不存在理论诗学)。它们基本上不知道著作这一范畴(口头创作是匿名的:文学中作者的概念被声望的概念所置换),而且也没有体裁范畴,体裁结构离不开文学之外的情势,有关文学作品的成分与容量的观念纯粹是功能性的,不符合我们的体裁标准。由于文学还没有从精神活动的其他形式中分离出来,所以语言具有记忆、魔法、表现、交际的功能,却绝无美学功能——至少没有意识到这一功能。第二个时代,其艺术意识属于墨守成规、即规范化类型。这一时代在欧洲持续到18世纪下半叶前,在东方则至19世纪前。在这一时代之初,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分离出来,出现了文学的自我意识,随之形成文学理论。但如同认识论中一般凌驾于个别之上,这时代的文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标准的概念,这种典范性的标准反映了某种文学理想。理论诗学很大程度上消溶于雄辩术之中,文学实践上居于首位的是风格与体裁的标准化范畴,从而限制了作者个人的意愿。文艺复兴、巴罗克、古典主义是欧洲这一时代的顶峰和结束时期,同时也是转入下一个艺术意识新类型的过渡时期。欧洲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东方始于19世纪——部分是由于欧洲的影响),文学过程的性质及相应的诗学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这就是第三个文学大时代的开始,其艺术意识属于个人创造类型,或称历史(即依据历史主义原则)类型。墨守成规、雄辩式的公设渐渐从文学理论与实践中退出,历史的和个人的视觉替代了修辞与体裁的论据,作家个性的语言替代了华丽的“现成话”。文学过程的“主角”不再是屈从于既定标准的作品,而是作品的创作者;诗学的中心范畴不再是风格或体裁,而是作者。由于这一时代的文学过程前所未有地与作家个性、周围现实同时紧密相连,所以艺术意识中起首位作用的是文学手法以及将美学理想与世界观相似的作家连在一起的文学流派。从以上简单引述中不难发现,这两位俄国学者的视角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都是在探索文学与文学之间的“共性”,认为各国文学发展的“共性”就意味着世界性。探索世界文学就是探索这种“共性”。但究竟什么是世界文学?理论上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直到90年代初,这种探索才有了新的进展。
有趣的是,取得这一实质性进展的带头人并非俄罗斯学者,而是斯洛伐克的著名学者季奥尼斯·久里申(一译杜列新)。久里申已出版过几十部著作,在研究文学联系及影响的规律方面具有国际威望。1975年出版了著名的《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该书的俄译本与英译本先后于1979年、1984年问世)、1988年出版了《文际过程分类法》、《文际过程理论》,并发表了重要论文《文际共同体是全世界文学规律的表现》,而1992年他与斯洛伐克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合作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是他多年探索的结晶。由他主编、有俄罗斯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参与的一套六卷丛书《独特的文际共同体》,于1993年出齐,同时译成了多种文字。同年,还出版了由他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切雷舍夫共同主编的《独特的文际共同体问题集》。随着又出版了探讨世界各别地区的文际共同体的其他著作。久里申依据自己的理论模式及发表的系列著作,建立了世界文学的新概念,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已被验证并投入实际运用,这在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的比较文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俄罗斯学者P·库兹涅佐娃评价说:在文艺学中还很少有如此规模的发现,久里申第一个揭示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真实本质,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一现象的历史——艺术的丰富内容,建立了如此大容量的文际共同体的内结构。
久里申认为,整个文学过程由两个部分组成:“民族文学过程”和“文际过程”。所谓文际过程是指文学与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而“独特的文际共同体”是指这样一些文学之间的联合体,该联合体具有某种由不同情况所制约的紧密而直接的相互作用。种族、语言、地理、意识形态等等是形成文际共同体的条件。而独特文际共同体的特点在于:某个共同体具有的一些规律是其他共同体所没有的,或者有,却带有别样的性质。例如“雌雄异株”规律(двудомност),即某种文学现象存在于两种或几种民族——文学语境中,但在每一语境中又各不相同。这种现象往往见诸于单语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文际共同体中。久里申强调独特文际共同体具有历史制约性:它们不是一劳永逸的建构,而是活动易变的阶段性发展形态,是对发展进程中极多样的历史决定因素的反应。这类系统往往是“多民族”的阶段性发展形态,特点是既保留各别的民族——文学成分的个性特点,又具有得以相连的共同特性。按照久里申的理论,民族文学只是文际共同体的一个成分,而世界文学即是文际共同体中的“终极”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久里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组成独特文际共同体的文学,其发展具有分化性:共同体内既联合具有分支传统及重大创作成果的文学,又联合这样一些文学:它们的发展进程较慢(“分化性较小”),同时却与“分化的”文学(这种文学具有丰富的发展进程、发达的风格与体裁特点)相接触。这种联合的基础是相互交流,以自己的创作成果丰富共同体。这里需要着重注意的,是每种独特文学特殊发展的能力,以及它给文际过程的宝库提供独特贡献的可能性。在久里申看来,文际过程在独特文际共同体的范围内具有三种基本功能: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在文际共同体历史形成的一定阶段占主位,此时进入共同体的文学显示出愈来愈强的接近趋势;分化功能,这表示各文学的发展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分道;互补功能,它反映出文学价值相互补充、相互替换和补偿的趋势,这是文学相互作用中最重要的功能,它能够补偿独特文际共同体成分之间文学过程发展中的某些缺失现象与环节,是整合趋向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传统的比较文学学者致力于确立文学的民族发展与总体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是民族特点清楚了,但文际过程的规律却只是“顺便”显露出来。久里申则向前跨了一步:他克服了民族文学边界的局限,打开了建立世界文学在其进化中的普遍适用的分类法之路。久里申及其领导的研究集体在比较文艺学方面的成果,其学术价值首先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从高层次的范畴”研究民族文学的必要性,提出必须跳出单一民族文学的界限,进入高层次的文际共同体乃至世界文学来进行研究,因为没有一个文学是孤立存在的。久里申认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不是两个界线分明的概念,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赖。接触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具有局限性,因此研究必须从“文际性”(меж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ъ)出发。他强调不只是民族特点具有可变性,文际共同体也具有可变性。价值交替、功能更新、联系等级的机动性,最后会引起文际现象的类型学的改变。因此如果不考虑文际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仅在文学比较层面上分析文际联系、对新现象定位,同样是不妥的。
如前所述,久里申提出世界文学是文际共同体中的“终极”共同体,它是一个开放性系统,是动态的、发展的。他肯定了Φ·沃尔曼在1936年的著作《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中提出的“补充接入”(донолнителъноевключение)范畴,并且认为“补充接入”在历史—文学实践中是不断发生的,不使用这一范畴的历史的研究,将会是无定形的研究。所以他非常重视非欧洲的“文学中心主义”:非洲中心主义、亚洲中心主义等等,认为它们给世界文学的内容及历史提供了很多东西。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久里申不仅揭示了“世界文学”这一现象的含义与内容,而且相当明确地划出了进一步研究并从理论上阐释文际共同体发展的道路。他提出,世界文学今天与明天的发展前提,是通过对文际共同体的分析,引向建立带有另样成分等级的新的概念系统,因此必须对一系列的传统范畴作出相应的变异与解释。
以久里申为首的一批俄罗斯、东欧学者关于世界文学的探索成果,并没有停留在清淡上,由久里申主编、分别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出版的那套《独特的文际共同体》丛书,就是这种成果在实践中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就是维珀提出的“理论上的文学史”的开端。就这样,俄罗斯、东欧学者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探索,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第一个循环。
注释:
① 参见Неугюкоева и.г.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итератуы.Проблема системного и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М.1976.C.185-186.
②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1983.T.1.C.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