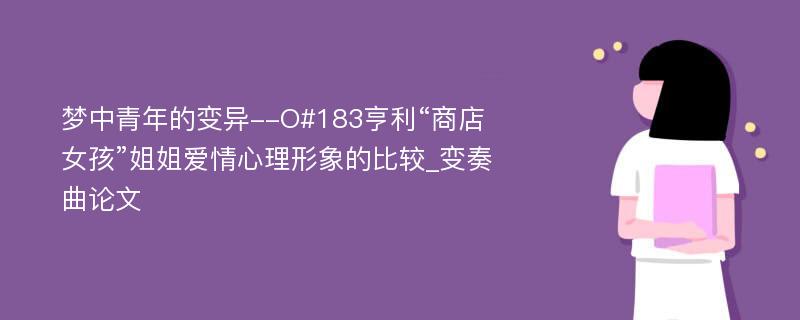
梦幻青春的变奏曲——欧#183;亨利《商店女郎》姊妹篇爱情心理形象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利论文,姊妹篇论文,变奏曲论文,女郎论文,商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老汇路的电灯光亮夺目,招致几英里、几里格、甚至几百里格以外的飞蛾从黑暗中扑来,参加焦头烂额的锻炼。
——《没有完的故事》
商店女郎,是欧·亨利“小职员小说”系列的艺术形象。这类小说主要收集在以纽约为创作背景的三部小说集中:《四百万》(1906)、《剪亮的灯盏》(1907)和《城市的声音》(1908);小说名篇《没有完的故事》、《剪亮的灯盏》和《吝啬的穷情人》则依次为三部小说集的代表作,可以视为“商店女郎”的姊妹篇,小系列。
这一时期,欧·亨利在“每一所屋子都藏有戏剧”的纽约,找到了他底层社会小人物的新的戏剧主角,而以纽约大都市舞台的一角,演出他笔下商店女郎的悲喜剧。这些商店女郎,大多生长在贫困的城区和穷苦的乡村,绮年妙龄而天真烂漫,天姿丽质又聪明能干,只因生活所迫,又经不起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中心的诱惑,背井离乡,朝纽约奔涌而来,向曼哈顿直冲而去——因为,曼哈顿“这朵晚上开放的仙人掌花”,“那颜色死白、气味浓烈的花瓣”,是如此带有刺激性;而百老汇路,“电灯光亮夺目”,又是那样富于迷惑力:开篇所引一段文字,就是她们这种人生境遇的一幅生动、形象的素描。她们就像《餐馆和玫瑰》里的波茜小姐——“一朵土生土长的美丽的少女之花,就这样拔离故乡故土,抛向花花世界非人性的土壤”〔1〕, 把自己美好的天性失落于变幻莫测的大都市。因而,这些商店女郎,孤苦无靠而向往着富贵生活,尝遍辛酸却抱有太多幻想,她们永远在生活苦海中浮沉,只能以自己的青春为代价,演奏自己的爱情之梦与命运之曲。她们的爱情之梦,既喜且悲,悲中有喜,喜中见悲,悲喜交集,表现了复杂的心理形象;她们的命运之曲,以喜衬悲,寓悲于喜,则有着喜剧与悲剧的交相变奏。《没有完的故事》里的达尔西,《剪亮的灯盏》里的南希和她的同乡友伴芦,《吝啬的穷情人》里的麦茜,就是典型的代表。
十九岁的南希和二十岁的芦,两个“农村姑娘”,就是“因为家乡不够吃”才来纽约打工的。南希周薪“只有八块钱”,只能住“过道房间”,“吃不饱”,“穿不好”。十八岁的麦茜也一样低薪,贫困,一家“五个人住三间屋子”,因而街角是她的“坐谈室”,公园是她的“客厅”,马路是她的“园径”。达尔西更苦,周薪只有“五、六块钱”,因而要研究她如何维持生活竟成了“一件给人启发的事”,就连欧·亨利也“没法算下去”,只好“搁笔长叹”!这种低薪与贫穷,正是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美国社会现实和雇佣劳动者生活现实的真实写照。这“四姊妹”主角,与《警察与赞美诗》追求犯罪判处三个月监禁以避冬寒的流浪汉苏贝们,与《两位感恩节的绅士》等待一年一度感恩绅士恩赐饱腹之乐的失业者皮特们,与《天窗室》饿昏虚脱的丽森小姐们,正构成纽约“四百万”饥寒交迫的悲惨世界。而“四姊妹”正挣扎其中,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又不纯粹是一种“穷则思变”的苦斗,这里还揭示了“环境怎样影响人”〔2〕的深层意蕴。 她们从早到晚接触的都是“高尚富有的人”,周围尽是那些“带有高雅精致气息的漂亮东西”,以至“你处在奢华的气氛中,不论你还是别人花了钱,那种奢华就属于你的了”。但南希又不想一辈子站柜台,很想“碰碰运气”找一个“阔佬”——这正是商店女郎的心态,她们都“沉浸在这种雍容华贵的气氛中”而不可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她们都经不起“百老汇路的电灯光亮夺目”的诱惑,正像“飞蛾从黑暗中扑来”,争先恐后参加“焦头烂额的”命运大搏斗。凭什么呢?凭年轻,凭美貌。她们都是迷人的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和罗马神话中艺术和商业的保护神,连欧·亨利都要发出警告:当她们“微笑”时,“除非你有所戒备”或“对爱神的挑惹无动于衷”,不然,“我劝你赶快避开”!但是,在色情世界,少女的美貌只是一种灾难。而她们却醉心于打扮,甚至对贵妇们的服饰风采一味摹仿——南希和芦是够突出的了,就连半饥不饱的达尔西,也都要到便宜的旧货商店“买一条仿花边的纸衣领”什么的。这种“穷讲究”和“穷打扮”,来自噪杂的纽约市声的震荡,有着内在性格心理的回响,正是她们青春梦幻和爱情变奏的开端。
南希是浪漫型的,颇有诗人气质。她有“直率的妩媚”,却从不夸耀自己的美貌与长处,经常带着“讥讽而又甜蜜的微笑”,而且这种微笑“仿佛从你身边掠过,像白蛾似地扑翼飞过屋顶,直上云霄”,似乎可望而不可及。而作为对比人物,芦则是现实型的,很有生活能力。她勤劳,肯干苦活,只要“能挣钱”就行,认为“当熨衣工”不见得就没有出息,对南希又能像妹妹一样关心,爱护,既温和,又直爽,多少保持乡野的人情味。但这一对拔离故乡故土的少女之花,在纽约的花花世界,却难以保全自己的本色。由于“各种各样值钱而漂亮的衣服”都在芦的熨斗底下经过,她对这种衣著的“有增无已的喜爱”,也就连同城市的铜臭味和市侩意识一起,由她手中的“导热金属传到她身上去”了。她是“四姊妹”中的高薪人物,每星期可以挣到“十八块五”,净替自己添置“花哨好看的衣服”——一件绣花坎肩,仿佛一张“任何苍蝇都愿意粘上去的蛛网”,就“值二十五块钱”,貂皮手筒和围脖也是“花了二十五块”买的,经常穿的是“鲜艳美丽的衣服”或“不称身的紫色衣服”,被南希讥为“审美力太差”。然而她却浑身散发出“心满意足的气息”,“面颊红润,淡蓝色的眼睛晶莹明亮”,为自己的“鲜艳美丽”而“得意扬扬”。而注重审美艺术的南希,则是芦所指责的“爱面子”而“愿意饿着肚子摆阔”的一类女郎。她善于用最省的钱来最有效地仿做贵妇的衣服,“坚定不移地吃她节俭的饮食,筹划她便宜的服饰”,或从“伺候”的贵妇们身上学到新的东西,把她们的衣著风度和社交界的地位“引为典范”,从她们身上“撷取最好的地方”,“取长补短”,“得风气之先”而独领风骚。她毕竟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她也有芦的那种虚荣的表现,这在两人一场反唇相讥的舌战中,已见端倪:
“你那种握手的方式也是从范·阿尔斯丁·费希尔太太那儿学来的吗,南希?”她问道。
“假如我是学来的,你更可以放心大胆地照搬。”南希说。
“唷,我根本不配。那种方式对我来说就太花哨了。那种把手抬得高高的架势是为了炫耀钻石戒指。等我弄到几枚之后,我再开始学。”
“你不如先学着,”南希精明地说,“那你就更有希望弄到戒指。”但两人的生活意趣、心理气质毕竟是不同的。服饰表现个性,本身也会说话。正如“夜间消遣”图景所显示的:引人注目的芦,衣著鲜艳“有点像孔雀”,提供的是“色彩”;而“窈窕纤弱”的南希,则打扮得“像麻雀那般朴素”,提供的是“情调”。也正如两个青春形象所预示的:一个喜“露”,花枝招展,全是为了漂亮,其虚荣是根深蒂固的,终于陷入痛苦的深渊;一个善“藏”,朴实平淡,追求着艺术美,其虚荣是浮于表面的,最后“抽中婚姻的彩头”。两种爱情结局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着对立的象征:“孔雀”玩赏自己导致被人赏玩;“麻雀”机灵自持而飞向认定的目标。
然而“麻雀”却是从大学飞出来的。大百货商店是培养南希的大学,整天“交头接耳”开“碰头会”的女伴是她的老师,“课程是包罗万象的”,是她“学问的源泉”。欧·亨利说:“女人是所有小动物中最荏弱无助的——她们有小鹿的优雅,却没有它的敏捷;有小鸟的美丽,却没有它的飞遁能力;有蜜蜂的甘酿,却没有它的……”因而对女人来说,“成功的防御就意味着胜利”。南希正是在她的大学里,由“见多识广”而学会“防御”。由学会“防御”而表现高傲的——连她把头发梳成“蓬松高耸的庞巴杜式”,“趾高气扬地”穿着一件短大衣,都带有高傲的神气。就如芦批评的:“假如你能多挣一些钱,你也就不至于那么高傲了。”但挣钱少却又高傲,这也许正是南希性格的可贵之处,正可代表商店女郎的本质特征——因为这是“典型的商店女郎”的“高傲的反抗”,可以“使男人们自惭形秽”!不错,南希也有过芦的那种“野心”,曾经声明非得打中“最大最好的猎物不可”,所以她“剪亮了灯盏”,一直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如意新郎。因而她最先给读者的印象是比不上芦的。这是一种“先抑”,但这正是为了铺垫,正是为了“后扬”。难得的是她对“别有用心地奉献鲜花”的男人都学会了“识别的窍门”,先后就曾看透谎骗“瞎说”而拒绝了两个百万富翁的求婚,被女伴骂为“精神病”。对此,南希又曾发表声明:“并不完全是为了钱……我待价而沽,决不挑一个大拍卖的日子。总而言之,我非得找一个坐在椅子上像是男子汉的人。”因而她“日复一日地啃着干面包,束紧腰带,披星戴月地追踪”——百货商店是她的猎场,有好几次她“举起来复枪瞄准”,但由于“某种深刻而正确的本能”总是阻止了她,使她重新“追踪”。她的“价值标准”正开始转变,“金元的符号”变得模糊而成了“真理”、“荣誉”的字样,以至变成“善良”二字,所以才出人意外地追踪到了被芦甩掉的丹恩,一个理想的“猎物”。最后她又对丹恩声明自己跟百万富翁“毫无关系”。南希的三次声明,是她隐秘的爱情心理形象发展变化的三部曲,其间梦幻青春的变奏,几经蓄势,由“抑”到“扬”——其“后扬”,是来自“先抑”。而芦的“变奏”则恰恰相反,是由“扬”到“抑”——对她的“后抑”,也来自“先扬”中的铺垫:丹恩曾“老实而惶恐地”朝她“越来越刺眼”的衣服“瞥一眼”,而她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劝告南希对百万富翁不要轻易放过,“即使他的身价只差几块钱而不够格的话”;对百万富翁敬畏到连“跟我说话”都会“吓得手足无措”,又暗示“说不定”会比南希“先找到一个”百万富翁……这种心理意识,早已伏线暗埋,造成蓄势,所以芦才跟南希的由“浪漫”面向“现实”相反,是从“现实”变为“浪漫”,由喜剧酿成悲剧。
“四姊妹”梦幻青春的变奏,都有各自的基调——在同一篇小说中的一对“姊妹”,南希是高傲的,芦是虚荣的;而处于不同小说的另一对“姊妹”呢?麦茜是狡黠的,达尔西是懦弱的。她们由各自的基调,发出各自的声音,唱出各自的旋律,在三姊妹篇的相互对比、多种对比和交叉对比中突出各自的心理性格和爱情形象。
“四姊妹”中能在百货商店大学里学到防御艺术的,称得上是南希的师妹的,只有麦茜——她除了学到类似南希那种“有关人类的广泛知识”以外,还学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并能及时贮藏在她那个“马尔他猫似的隐秘而谨慎的脑袋里”。她长得很美,“有红有白的脸上”,一双蓝眼睛的神色就像“夏季的阳光闪射在南海冰山上那样凛冽、美丽而又热情”,“淡红的嘴上的酒靥”很深,也有芦的“像普赛克一般的胳臂”,一头“黄橙橙的头发”,“可爱而纯洁”。她的微笑也像南希那样迷人,容易招来周围的“媚眼”或者“色眼”的“调情”。她的手套柜台也像南希的手帕柜台一样诱人,经常是俗不可耐的公子哥儿扭捏作态闲逛游荡的场所。但南希更具“识别”的慧眼,麦茜却多有世俗的“猜疑”。南希的“识别”养成她的“高傲”,而麦茜的“猜疑”则来自她的“狡黠”。正如“识别”,应当看成为南希善于自卫的一种武器,“猜疑”,也可以说是麦茜保护自身的一种甲胄——因为“造化也许预料到她没有聪明的朋友可以商量,于是在赋予她美丽的同时,也给了作为补救的狡黠,正如造化把贵重的毛皮赋予银狐时,也给了超出一般动物的狡猾”。在这一点上,处于两篇小说的不同百货商店的一对“姊妹”,是相通的,好像是心有灵犀,因而都能躲过“捕获物”的厄运。只不过,具有“识别”慧眼的,“抽中婚姻的彩头”,是一个喜剧;带有世俗“猜疑”的,丢掉“婚姻的彩头”,是一个悲剧。麦茜的悲剧,是错把“猜疑”当聪明,却聪明反被聪明误。可以说,在“四姊妹”中她的机遇最好。卡特是个有文明教养的诗人,画家,百万富翁,他像丹恩爱芦那样,爱麦茜也是“忠诚不渝”的,而且还是他“有生二十九年以来”的初恋。这都是芦、达尔西和南希所遇不到的天赐良缘,实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何况他俩的恋情已发展到“两星期”以后的卿卿我我——公园“树荫遮蔽”下的紧紧依偎,他的胳臂“温柔地搂着她”,她“舒适地倚在他的肩膀上”,连麦茜自己都“快活地叹口气”说:“你以前怎么没有想到啊?”但即使如此亲热甜蜜,也都无法逃过她的偏见和猜疑,竟把诗人真心的表白和坦诚的求爱看作是诱骗少女的手段。甚至当诗人发自肺腑的动人爱情诗篇已经触及了她那难以开启捕捉的小灵魂,深受打动而唤醒了初恋的真情,抬起了“含情脉脉”的眼睛,面颊“泛出了红晕”,就像蝴蝶颤抖着翅膀即将停憩于爱情的花朵,眼前已经闪现一线美的憧憬的黎明……可是黎明之光只是电光一闪,浪漫蒂克奇迹只是闪烁了一下——她突然又缩回到自己阴暗的世俗世界里去了。这里展示了人物爱情奥秘的心理历程,又相当含蓄地凝聚为性格的焦点,透过这一焦点即可对其内心世界作一番远眺近观:由于太多类似的经历,使她看透富家子的玩弄成性,对种种“花言巧语”的逢场作戏一眼看穿;而习俗之见带来物极必反,使她错把真诚当虚伪,错把富有的诗人当“吝啬的穷情人”。一个是诗情洋溢,一个是疑云遍布;一个是执意追求,一个是变化莫测;一个是货真价实,一个是有眼无珠。比起南希和芦,这种梦幻青春的变奏,显然也有她俩的那种荡漾,回旋,却更为顿挫,杂错——其情调是由“现实”到“浪漫”又由“浪漫”到“现实”,其旋律是由“抑”到“扬”又由“扬”到“抑”,因而麦茜的爱情心理形象就表现得特别复杂多变。
爱情心理形象复杂多变而又与麦茜遥相映衬的,还有达尔西。她也是“四美图”之一,仿佛是从“仙境里”走出来的天仙,又好比是“刚从大梦中醒过来的公主”。可是她最贫穷,一直在饥饿中生活,衣服非常陈旧,手套也“有点脏”,“这一切都代表苦苦地省吃俭用”。她也最不幸,一开始就被猎艳老手皮吉跟踪看中而带来悲剧。一提起皮吉,连“高贵的猎族”都要蒙上“不应有的污名”——他长得“肥胖”,衣著“华贵”,是“鉴别饥饿的专家”,只要朝一个商店女郎“瞅上一眼”,他就能告诉你,“她多久没有吃到比茶和棉花糖更有营养的东西了,并且误差不会超出一小时”。因而他老是在商业区“徘徊”,在百货公司里“打转”,以“一顿丰盛的大餐”作诱饵“相机邀请女店员们”,从中渔色得利。他有着“耗子的心灵,蝙蝠的习性和狸猫那爱戏弄捕获物的脾气”。就连“遛狗的人”都瞧不起他。欧·亨利说他“是个典型”,极为憎恶,怕玷污自己的笔,说“我不能再写他了”,“我的笔不是为他服务的”,“我不是木匠”。就是这么一个猪狗不如的家伙,把美丽纯洁的达尔西诱骗了,玷污了。诱骗并玷污芦的那个“百万富翁”,也是一个“皮吉”——皮吉是趁人饥饿之危,他则是投其富贵所好,作为典型,都是蹂躏少女的禽兽!这一对不幸的“姊妹”:一个是美得鲜艳,虚荣而被色狼击中;一个是美得纯朴,懦弱而为色狼所欺——她俩都没有学到南希和麦茜那样的识别技巧与防御艺术。但达尔西却比芦来得“浪漫”,她有较为丰富的感情世界和内心活动,气质上似有南希的一点诗意,心灵里也有过麦茜那样的浪漫蒂克。为什么她刚要应约吃饭又突然不去了?原来有一个人正带着“忧郁、美妙而严肃的眼神”在“瞅着她”,带着“伤心和谴责的神情”在“瞪着她”,把她留住了。他就是挂在梳妆台上镜框里的基钦纳将军画像,她理想中唯一的知心朋友,亲人,情人,只有他,关心她的行为,“或是赞成,或是反对”,而且在她的饥饿中曾带给她私下多少美妙幻想的情思恋意……这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感情力量。可是现实,毕竟是一个饥饿的世界,一个色狼的世界,因而基钦纳将军的目光只能把达尔西留住于一时,小说到此也只是一个“没有完的故事”。此后,达尔西这一只饥饿的羔羊,又怎能敌得过色狼的再次猛扑?在这里,达尔西梦幻青春的变奏曲,也跟麦茜一样的顿挫,杂错,其情调也是由“现实”到“浪漫”又由“浪漫”到“现实”,其旋律也是由“抑”到“扬”又由“扬”到“抑”。对比之下,麦茜丢失诗人的悲剧是因狡黠产生猜疑而显示出太多的警觉,达尔西投入狼口的悲剧却是因懦弱经不起诱惑而表现了过分的单纯:一个缺少的就是单纯,一个需要的正是警觉。相对而言,同是百万富翁的“捕获物”,虚荣的芦是有意追求而甘心“被捕”的结果,懦弱的达尔西却对“被捕”曾有内心搏斗挣扎的过程:一个出于主动,一个纯属被迫。两相对照,“四姊妹”唯一得到如意爱情的南希,她的高傲倒是有点达尔西的单纯,但一点也不懦弱;而“四姊妹”中最不幸的达尔西,虽然比南希更吃苦更朴素,却没有南希的广泛知识、逃遁能力和应变技巧,更谈不上应有的高傲。
欧·亨利通过对“四姊妹”爱情心理形象的扫描,揭示了商店女郎被剥削被损害的命运,对她们寄以无限的爱护与同情,把批判矛头指向造成她们各种悲剧灾难的美国资产阶级——在达尔西所在的小说《没有完的故事》,开头与结尾有关“末日审判”的梦境中,警察挟着罪犯的胳臂问他:是不是同那群每星期只给雇佣女工“五、六块钱维持生活”的老板一伙的?罪犯说:“对天起誓,我绝对不是。我的罪孽没有那么重,我只不过放火烧了一所孤儿院,为了少许钱财谋害了一个瞎子的性命。”资本家的罪孽,比杀人放火、谋财害命还要深重!这一梦境,由商店女郎的血泪构筑而成,有三篇小说思想主题的闪映。欧·亨利说“能海阔天空地信口开河”而“不致于遭到驳斥的”,是“叙说你梦见的东西”,因而他在小说构思中用幻觉虚构梦象,以此特有的曲笔,代表“四百万”对“四百个”作了无情的揭露,提出有力的控诉,表达了强烈的爱憎感情。这“四姊妹”,可以说是美国“垂死的资本主义”特定时期下,纽约“四百万”底层社会小人物中最真实最具体的商店女郎形象,是欧·亨利小说中的另一种艺术典型。就是屠格涅夫所说的:“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3〕也即恩格斯那句经典性名言所指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
三姊妹篇是一个多声部的变奏曲。这里有达尔西与芦异中有同的变奏,也有芦和南希异中有异的变奏,又有南希同麦茜同中有异的变奏,还有麦茜跟达尔西大异小同的变奏,更有芦、麦茜以及达尔西、南希有同有异的变奏。而变奏的中心即在《剪亮的灯盏》,它集“四姊妹”爱情心理形象“异”“同”于一身。“四姊妹”遇到的四个对象,三个百万富翁,一个电工——其中残害达尔西和芦的两只色狼,一在《没有完的故事》,一在《剪亮的灯盏》,两只色狼本性一样,两个“捕获物”命运相同,这是两篇小说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之处;另一个百万富翁是诗人,同那个电工一样,都是忠诚的情人,一在《吝啬的穷情人》,一在《剪亮的灯盏》,对麦茜和南希都没有任何伤害,而且南希还与电工喜结良缘,这又是这两篇小说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之处。因而《剪亮的灯盏》,好像是它前后两篇小说的“后补”与“前续”,又好像是它前后两篇小说的“合集”,对多声部的梦幻青春的变奏起“前伸”、“后延”的作用,在商店女郎的爱情心理形象系列中有“承前”、“启后”的联系,可以看成是三姊妹篇的“代表”之作——“四姊妹”的多声部集中在此交响,变奏,合唱,扩大,高扬,汇成一片,聚为一体,演唱出百老汇路灯光“飞蛾”的一部“焦头烂额”的悲剧史,命运曲。
命运之曲飘荡着爱情之梦,喜剧与悲剧的多重变奏突出的是微妙而复杂的爱情心理形象。因而根据梦幻青春的变奏所决定的内容的需要,就跟欧·亨利含笑带泪的“孪生小说”《华而不实》与《汽车等待的时候》〔5〕一样, 也采用了“隐蔽的”心理描写手法——作家不充当“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而闯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作直接的心理描写,也没有让人物自己作内心的独白,而是以精练的文字,简朴的白描,寥寥数笔,写出人物的言行举止、表情动作以至神态变化,让读者窥探到人物的心理愿望和意识情绪,把人物最隐秘的内心世界隐晦而含蓄地揭示出来。这种“隐蔽的”心理描写手法,正是欧·亨利弹唱商店女郎梦幻青春变奏曲的高明技巧。欧·亨利早于西方作家半世纪所运用的这种描写手法,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欧·亨利手法”,而且它又常与欧·亨利的“事与愿违式”或“背反规律式”的结构方式巧妙结合在一起,构成别具一格的“欧·亨利结尾”艺术,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小说主题的深化。这在“孪生小说”中已明显可见,在三姊妹篇中更有突出表现。所谓“事与愿违式”或“背反规律式”,即指小说人物为了实现自己强烈的主观愿望或某种个人目的,在人物活动轨道的进程中,想尽一切办法,做出许多努力,却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主观与客观的距离,所出现的偶然或突然的因素,终于使人物的愿望落空,甚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违背了最初的意旨。这里提到的“孪生小说”,还有《麦琪的礼物》、《爱的牺牲》、《警察与赞美诗》、《女巫的面包》等,就是名篇典范。可以说,假如没有欧·亨利的“事与愿违”或“背反规律”的结构方式,就没有饮誉世界文坛的“欧·亨利结尾”,也就没有这些典范名篇的问世。同样的,三姊妹篇中“四姊妹”的爱情心理形象,之所以如此鲜明、生动,成为典型,又都是得力于这种结构方式与“隐蔽的”心理描写手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紧密结合——因为有了“事与愿违”与“背反规律”,才有“四姊妹”多声部的梦幻青春变奏曲;有了多声部的梦幻青春变奏曲,才有典型的爱情心理形象的展示。试想:假如即将应约吃饭的达尔西不是一下子又被精神情人的眼神留住,得以逃离狼口而躲进内心情爱意识的太虚幻境,最后又掉进狼口;假如早就想找个阔佬而一味摹仿贵妇装饰的南希,最后不是意外爱上芦的电工情人而结婚;假如勤劳内向而正与电工相爱的芦,不是突然跟百万富翁私奔而抛弃情人却最终又被抛弃;假如戴着世俗猜疑眼镜看爱情的麦茜,于约会中不是被诗人感人的初恋诗情开启了闭锁的心灵,却又一刹那间关闭了美好的爱情世界:那么,怎会有懦弱的达尔西的典型?怎会有高傲的南希的典型?怎会有虚荣的芦的典型?怎会有狡黠的麦茜的典型?一句话,怎会有欧·亨利笔下商店女郎的典型?
1995年10月上旬写于华侨大学西苑
注释:
〔1〕阮温凌:《人性艺术的动情力——欧·亨利小说名篇〈餐馆和玫瑰〉艺术探赏》,《名作欣赏》1992年第1期。
〔2〕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转引自钱谷融《文学的魅力》一书,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3〕屠格涅夫语。转引自《译文》1956年1月号,第15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1页。
〔5〕《名作欣赏》1995年第1期,“欧·亨利小说名篇探赏系列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