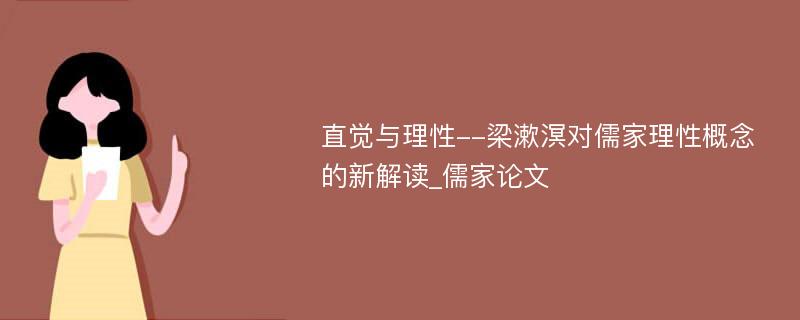
直觉与理性——梁漱溟对儒家理性概念的新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理性论文,直觉论文,概念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B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5)02-0009-05
在西方哲学中,理性是与非理性相对的一个概念。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分,使西方哲学往往倾向于既把“情”排除在理性之外,又把“知”排除在情感之外。儒学亦言“知”、“智”。这“知”或“智”,与西方哲学所言之“理性”相通,但又与之有相当大的区别。儒家论人心,其核心的概念是“情”;“知”、“智”乃是情之发用自身的一种自觉和智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的“知”“智”,儒家又常常称之为“明”。儒家的整个思想,都建基于对人的“理性”的这种独特的理解。现代以来,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地位使得儒家“知”“智”概念的本真意义隐而难明,这也常常影响到对儒家哲学精神的理解。梁漱溟早年提出“直觉”,三十年代后又转而使用“理性”一辞来诠释儒家“心”的概念。梁漱溟的诠释,以现代哲学的理论形式,揭示了儒家“理性”概念独特的理论内涵。这对我们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哲学,把握其精神实质,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在形上学的意义上,梁漱溟把宇宙理解为一个动态流行的生命历程。所以,他的形上学,实即一种生命哲学。梁漱溟认为,人心乃是宇宙生命的最高体现。而“直觉”或“理性”,则是人心或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直觉”或“理性”乃表现了宇宙生命的本性。
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使用“直觉”和“理性”两个概念,就是要说明,儒家所理解的“知”“智”,乃是一种“情意之知”,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
梁漱溟的早期思想,用“直觉”来理解人的心性。这直觉的内容即是传统儒学所谓的“良知良能”。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对这一点有很多论述。他说:“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页。)又:“能使人所行的都对,都恰好,全仗直觉敏锐,而最能发生敏锐直觉的则仁也。仁是体,而敏锐易感则其用;若以仁兼赅体用,则寂其体而感其用。若单以情感言仁,则只说到用,而且未必是恰好的用,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寂之义。”(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我们人的生活便是流行之体,他自然走他那最对,最妥帖最适当的路。他那遇事而感而应,就是个变化,这个变化自要得中,自要调和,所以其所应无不恰好。所以儒家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只要你率性就好了,所以又说这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的。这个知和能,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2页。)在这里,梁漱溟用“直觉”一概念对儒家的心性论作了现代意义的诠释。
儒家的心性论,其着眼点在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完成和实现。因此,儒家虽然极重“情”,但其所言情,非一般所谓“情感”,而是即情显“性”。梁漱溟早期理论中的直觉说,对这一点作了透彻的说明。一方面,梁漱溟强调,儒家的“仁”作为直觉,乃首先是一种情感表现。而这种情感表现,乃是人排除理智分别或思虑计较,对其所面对的周遭世界之纯任自然的随感而应和敏锐感通。另一方面,梁漱溟又从寂感、体用统一的角度对这直觉感通的存在实现义的内涵作了阐发。他认为,“情”流行感通,有其形上的根据。这感通流行之体便是“仁”,是“良知”、“良能”。感通的生命存在乃是仁体或良知之体的发用流行。仁或良知之“体”是“寂”。这“寂”表示超越之体,仁或良知由体而发用,即“情”的流行和感通。梁漱溟讲,孔家“相信恰好的生活在最自然,最合宇宙自己的变化——他谓之‘天理流行’”(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6页。)。而人心在“情”的流行感通中,方能体证“天理”。我们要注意的是,梁漱溟此所言“直觉”,非心理学的讲法,而完全是一种心性论的讲法——并且是宋儒那种本体化、宇宙论化了的心性论的讲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指出人类生命是宇宙大生命本性的最高体现。《人心与人生》里说:“此不落局限性的心,无所限隔于宇宙大生命的心,俗不有‘天良’之称乎,那恰是不错的,它是宇宙大生命廓然向上奋进之一表现,我说人心是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者正谓此。”(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0页。)梁漱溟认为,宇宙生命存在的进化,表明万物莫不有“心”,有一种趋向于“通”亦即“理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人的存在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所以,可以说,人类生命乃是宇宙大生命本性的最高体现,而“人心”则“是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者”。人心所能透露“生命本原”者,即“仁心”、“良知”、“天良”。
“良知良能”之能代表生命向上创造和“通”的本性,乃在于它是“情意”之实现义的体证和感通,而非对象性的认知。梁漱溟在1922年所作《评谢著阳明学派》的讲演中指出,儒家所谓“良知”,非指感觉作用和理智所成之知识、观念、概念等知解性的知,而是人以好恶之情迎拒事物之即时当下那种“天机神应”的觉知,或可称为一种“有情味的知”或“有意味的知”。“这种有情味的知,或有意味的知,在今日则所谓直觉。直觉不待学虑而世所谓半情半知的。”(注:《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直觉所得,异乎抽象静态的概念,而是一种“活形势”。“凡直觉所认识的只是一种意味精神、趋势或倾向。”(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0页。)比如,我听见音乐觉得甚妙,看见绘画觉得甚美,吃到糖果觉得好吃,这些意味,皆由直觉所得。“这种意味,既不同乎呆静之感觉,且亦异乎固定之概念,实一种活形势也。”(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0页。)故对于那生命流行的宇宙,亦只能由此“直觉”来呈现。直觉所以能够呈现宇宙生命,乃是因为它在存在的意义上体现着生命的本性。
30年代以后,梁漱溟论人心,乃提出“理性”来代替“直觉”这一概念。用语虽有不同,但其思想脉络却是一贯的。曾为梁漱溟作传的美国学者艾恺指出,梁漱溟后期所言“‘理性’,有着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仁’及‘直觉’相同的功能。”(注:[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页。)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用“理性”来代替“直觉”,亦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置换,它表现了一种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深化。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使用直觉概念,乃相对于“理智”而言,他认为孔家生活是纯认直觉,而排斥理智。这显然是受了西方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他后期提出“理性”概念,以代替“直觉”,就是既要贯彻儒家“情意之知”的心体论思想,又要自觉地与西方哲学尤其是生命派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划清界限。
梁漱溟早期的新儒学思想,以“直觉”与理智相对来理解人心,尚未把儒家的“情意之知”与“本能”概念区分开来,而是将“本能”混入“直觉”的概念以理解良知本心的内涵。30年代以后,他对自己思想中这种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对这一点作了反省:“二十七年前我还不认识理性。但颇有悟于人类社会生活之所以成功,有远超乎个人意识作用之外者,遂因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而信‘社会本能’之说。……但一经晓得人类生命原是从本能解放出来,其重点宁在本能之外,则说人类社会出于智力故非,说它筑基于本能,尤觉无据。……人类自从本能解放出来,生命乃不复局于其身体,而与其他生命相联通。特别是与其他人的生命相联通,彼此感应神速,有非一般物类所及。《孟子》书上‘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一段话,指点甚明。……此际一片天理流行,无彼我之见存,是曰‘无对’,表现在意识上,即是理性。”(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262页。)从这一段反省的文字可以看出,梁漱溟提出“理性”概念,意在把良知本心的表现方式与“本能”区分开来,修正他早期把人类生命之“通性”建基于“本能”的思想倾向,从而进一步凸显儒学以“情意之知”的感通体证方式建立形上本体的哲学精神。
梁漱溟晚年在谈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直觉”思想时说:“我说孔子的仁是一种极其敏锐的直觉。孟子不是使用过‘良知’这样的词么?这就是今天所谓的‘直觉’。直觉在英文中称为intuition。本能在英文中称为instinct。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是在用现代的名词来解释孔子和孟子的思想。现在,我感到我错了。这些现代名词在意思上非常相近,但并不等同,也不是真正正确的。然而它们又不是完全不正确。”(注:[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这里所说的“错”,显然并不是指“用现代的名词来解释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因为用“理性”、“理智”,也是在用现代名词解释孔孟思想。这“错”就错在他以前把intuition和instinct混同来使用。英文的intuition和instinct,汉语皆可译为“直觉”,但前者注重在感官的反应,后者强调的是内在的本能。他早期在解释儒家良知本心概念时混淆了二者的意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本能与直觉,确实亦未加区别,而且明确讲,“‘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而用“理性”一词并对“仁”、“良知”等概念的内涵加以界定,正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儒家的良知心体概念。其前后期用语上的差异实更表现了其思想本质上的一贯性。
梁漱溟后期论良知本心,不再使用本能、理智的两分法,而是在本能、理智之外增用“理性”一概念,形成了有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能、理智、理性的三分法。他认为,这样,就既能坚持他的原有理论对良知心体那种“情意之知”的理解,同时又能够清除自己早期在“直觉”观念中混入“本能”的思想因素。
梁漱溟说:“在动物本能中同样涵具知、情、意三面……然其特色则在即知即行,行重于知;而人类理智反之,趋于静以观物,其所重在知焉而已。理性之所为提出,要在以代表人心之情意方面;理性与理智双举,夫其可少乎?”(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0页。)“我乃于理智之外增用理性一词代表那从动物式本能解放出来的人心之情意方面。”(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0页。)从这里可以明确看出,“理性”的概念,既与其早期之“直觉”在思想上具有连续性,又与“本能”的概念有严格的区分。
在《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都以“无私的情感”界定“理性”。他特别指出了克鲁泡特金、索照蓝、麦孤独把人的道德心与本能相混同的错误。认为克鲁泡特金与索照蓝把道德心看作一种本能和“官能”,麦孤独把承认人心的道德直觉(良心)看作一种神秘主义因而反对人性善之说,从人心进化的自然史角度,把人类的道德心看作是从动物本能发展而来,都是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把良知本心超越于本能之“无所为”的自由,等同于动物本能那种有外在目的的“有所为”的行为(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5页。)。
梁漱溟提出理性,本为表现“人心之情意方面”,但本能亦包涵情意。梁氏早期的直觉学说受西方思想生命哲学的影响,混同仁心良知与本能,与此有关。因此,他在后期的著作中,对理性与本能的区别,作了详细深入的分析。
梁漱溟认为,人能成就理智,而理智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倾向。人类理性或那“无私的情感”,正是在人由乎理智,因而作为动物的本能逐渐减弱才呈现出来的。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此一体之情,发乎理性;不可与高等动物之情爱视同一例。高等动物在其亲子间、两性间至同类间,亦颇有相关切之情可见,但那是附于本能之情绪,不出乎其生活(种族蕃衍、个体生存)所需要,一本于先天之规定。……动物之情,因本能而始见;人类感情之发达,则从本能之减弱而来,是岂可以无辨?”(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无私的情感,同样地是人类超脱于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理性既然是由理智之发展减弱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它作为人心情意的表现,与本能之情意表现便有了本质的区别。
由此,理性作为情意表现乃一种内涵自觉判断,“不失于清明自觉的情感”(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3页。),是一种“清明安和之心”(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与本能性的盲目冲动不可同日而语。梁漱溟说:“情理,离却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物理,则不离主观好恶即无从认识”(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理性包涵有“知”、有“理”;但理性之“知”和所知之“理”,又与理智不同,是一种以情的关照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知”、所把握到的“理”。他讲,理性是“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这也就是儒家讲的“良知”。梁漱溟说,王阳明“以知是知非归本好恶之情,那都是对的。盖于此情理的认识原不同于物理……而情理却本乎人心感应之自然,恰是不学不虑的良知,亦即我前文所说‘无私的情感’。”(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5页。)王阳明讲良知就是“是非之心”。而这是非之心,乃是以好恶之情随感而应的一种当下的判断,而非认知意义上的分别认定。王阳明常引《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语,以知好色而当下即已“好”之,知恶臭而当下即已“恶”之来说明良知是非之心的表现方式(知情合一、知行合一)。梁氏颇肯定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他以现代人们所说的正义感为例对此做了说明:“现时流行有‘正义感’一句话。正义感是一种情感,对于正义便欣然接受拥护,对于不合正义的便厌恶拒绝。正义感,正是正义之认识力;离开此情感,正义就不可得。一切是非善恶之理,皆同此例……善,即存乎悦服崇敬赞叹的心情上;恶,即存乎嫌恶愤嫉不平的心情上。”(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这说法与王阳明的良知为是非之心的思想一致,是对传统儒家良知心体思想的现代理论诠释。在梁漱溟看来,“理性”作为情意的表现,就是这种在情上随感而应的自觉判断,其所得之“情理”亦非对象性客观性的理,而是因于物之“宜”而与物乃至整个宇宙的沟通和感通。
梁漱溟在他的论述中反复强调,“理性”作为“情感之知”,是人心因理智发展,自然本能随之弱化而呈现出来的,因而与本能之情感表现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简言之,理性作为一种情感表现,是一种自觉的澄明状态,非如本能之盲目冲动。他说:“一切情理虽必于情感上见之,似动而非静矣却不是冲动,是一种不失于清明自觉的感情。冲动属于本能。”(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3页。)又说:“忿与欲是激越之情所谓‘冲动’者。冲动附于本能而见,本能附于官体而见。前已言之,各种本能皆有所为,即有所私的;而理性则无所为,无所私。”(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冲动属于本能,属于身体性,不能从身体性解放出来,故缺乏自觉的规定,是盲目的。这实质上就是西方哲学家所讲的“情”。此“情”属于非理性。梁氏此一分别,就很好地突出了儒学所言情感的理性特征。这很有独到之处。
正因为如此,理性之情感表现,是无限向上的“通”,是与宇宙生命的“无对”和通而无隔;而“本能”的情感表现不能脱离身体性,故仍是“局”和“隔”。比如,动物从乎本能,虽亦有“不私其身”以为种族的表现(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1页。),这可说已具有不同程度的“通”性,亦是宇宙生命之“通”一面的表现。但因其是出于身体性的固定化的东西,故其本质上仍属“局”(可视为“较大范围的本位主义”),故不能视为“无私的情感”。人心之“无私的情感”,乃出乎人类理性之发用流行,故无不“通”。
这表现为“无私情感”的理性,乃体现了人的存在之自由的本性。梁漱溟说:“无私的情感虽若禀赋自天,为人所同具,然往往此人于此发之,而彼人却竟不然;甚且同一人也,时而发动,时而不发动,没有一定。此与动物本能在同一物种彼此没有两样,代代相传如刻板文章者,显非同物。……而此(指理性——引者)恰是从本能解放出来的自由活动,旷然无所为而为。“本能”则是于生活上有一定用处的,亦即必有所为的(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5页。)。这就是说,出乎身体性之本能的情感冲动,皆为一外在的目的(即维持种族蕃衍和个体生存)或“有所为”而发,系属于固定的自然锁链,不能达于自由。而理性的情感表现则是打破自然锁链以后事,故是当下“无所为而为”的自由。
这样作区分,并不是说人的理性是孤立存在的。人作为有机体的存在,亦有本能和理智。理智与理性在“理”、“知”的意义上乃一体之两面,为体与用的关系。而本能亦为人的具体存在所必有。本能是人类生活的“工具”,乃“从属于理性而涵于理性之中。”(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3页。)人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但人之为人,理性是其本质,而贯通体现于理智与本能。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论人心,乃单以理性言之:“一切生命均限于‘有对’之中,唯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只有理性是人类生命‘无对’一面之表现……故于此言心,即单指理性。”(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正因为如此,人类生命、人类理性,乃是宇宙生命本性的体现。
人心本体既然是以情为核心的自觉与感通作用,那么,其发用便不能只是一种向外的认知,而是一种依于工夫历程的、实现义的拥有和自觉。梁漱溟说:“人有无私的情感存于天生的自觉。此自觉在中国古人语言中,即所谓良知(见《孟子》)亦或云独知(见《大学》《中庸》)亦或云本心(宋儒陆象山、杨慈湖)者是已。……良知既是人人现有的,却又往往迷失而难见,不是现成的事情。孔子之学就是要此心常在常明,以至愈来愈明的那种学问工夫。”(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理性作为一种人心“情意之知”或“无私的情感”,虽为人心所本具,为人先天所有,但却必须经由修炼或修为的工夫才能实现出来。传统儒学的“知”论,与其修养论和工夫论为一体之两面。这一特点,在梁漱溟的“理性论”中得到了现代意义的理论诠释。
西方哲人看人的理性,常与非理性相对;理性就是“知”,“情”便只是内在的感受性、盲目的冲动性;“情”中无“理”,“理”中亦无“情”。梁漱溟的后期思想,对此点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人心与人生》中专门对这一点作了讨论,指出:“克鲁泡特金、索照蓝、麦孤独之伦,矫正一般偏重意识(理智)之失,而眼光之所注不出本能,抑亦末也。”(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7页。)。认为西方“主情”一系的思想家,虽认识到西方思想太重理智之偏失,但矫枉过正,乃以非理性救正理智,故又陷于对“本能”的偏执。梁氏后期以“理性”、“情理”论良知心体,把他早期直觉理论中所坚持的儒家心性思想纯粹化,彻底化;同时,亦以一种新的形式,凸显了传统儒家心、理性思想的特色和独特理论价值。
上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以来,中国哲学界基本上是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来研究和理解中国传统的思想学说。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因而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在现代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学科接受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似已不可避免。这样,在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下,如何对中国传统思想学说的固有精神进行现代诠释,以构成中国现代哲学之活的生命基础和精神资源,便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现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几代学人进行了不解的努力。梁漱溟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贡献。梁漱溟对传统儒学良知心体学说的现代诠释,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学说,在借用不得不借用的西方哲学概念时,往往颇费踌躇。比如,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概念,西方哲学“理性”一辞可与之相应。这良知本心,如再作限制,即西方哲学所说的“道德理性”。但良知本心作为一种因情而发用的自觉方式,既与西方哲学所谓“理性”相关,又与其所谓“非理性”相关,并且与二者的内涵都有重要的区别。梁漱溟的直觉和理性论,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亦同时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梁漱溟对儒学思想的新诠,其内容我们可以进行商榷讨论,但它所指出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标签:儒家论文; 梁漱溟论文;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论文; 梁漱溟全集论文; 人心与人生论文; 中国文化要义论文; 国学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