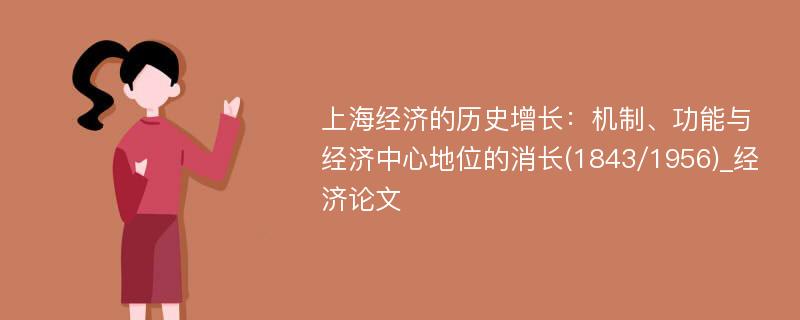
上海经济的历史成长:机制、功能与经济中心地位之消长(1843-195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上海论文,地位论文,机制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11-0126-11
一、开埠前期上海贸易的发展及城市经济功能的变化(1843-1894)
位于太平洋西海岸、中国沿海南北海岸线中点的上海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黄浦江的优良港湾,吴淞江等大小内河水道将上海与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紧密联成一片;广阔的经济腹地,赋予了上海开展贸易、发展经济的巨大潜质。从宋元至明清,开埠前的上海曾先后有“小杭州”、“小苏州”、“小广东”之美誉①,并且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在传统社会中的自身两大经济支柱产业——手工棉纺织业和沙船运输业。开埠以前,西方商人虽还未直接到上海贸易,但上海口岸与东南亚各国(如暹罗)的海上贸易始终没有间断。当时的上海县城,各地商贾汇集,城厢内外已建有26个工商业会馆公所。县城外沿黄浦江一带,行肆林立,码头泊位占据了大部分江岸。上海已是当时中国南北贸易的最大商港,江南以至东亚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②。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向西方世界开埠。上海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1847年,上海进口外国船舶102艘,载重26735吨,1855年已达437艘,157191吨。1853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已从开埠初期不足全国外贸额的10%猛增至占全国的50%以上,超过广州而雄踞全国第一③。自此,上海的对外贸易额基本上都要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50-60%。外贸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贸易。上海的进口商货,除少数留存本埠消费,大部分都经上海转销国内各地;上海的外贸出口货,一半以上是来自国内其他口岸的转口货物。1894年,上海从国外进口货物总值9326万海关两,其中67%、6261万海关两货物转运至国内其他通商口岸;出口总值5842万海关两中,来自国内其他通商口岸,通过上海转口的有2095万两④。
贸易的发展也推动城市经济组织和经济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首先是西方商人开设的洋行的出现。1847年,上海租界内已有进出口洋行24家,1895年增加到116家⑤。早期西方洋行多为代理或自营进出口以及与之有关的事务,范围涉及贸易、航运、金融汇兑、保险等等。60年代后,洋行总揽进出口以及关联业务的局面发生变化,各种专业的轮船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纷纷出现。到1885年,上海已先后有7家外商轮船公司,资本额达白银89.4万两。1850年,上海出现第一家外商银行——丽如银行,到1893年,先后设立的外资银行达16家。其中1863年开设的汇丰银行很快就在上海新兴的金融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贸易的发展也改变了上海旧有的商业经营方式和商业组织,刺激了新兴商业行业的产生和新式商业资本的兴起。它们主要集中在与外贸有关的洋布、百货、五金钢铁、颜料、洋广杂货、西药等经销进口货的商业行业,以及生丝、茶叶等与出口紧密相关的行业中。其商业组织形式如“清洋布店”、“洋货店”,以及“丝栈”、“茶号”等等,不仅已成为国际产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延伸,而且经营方式也渐向西方企业制度靠拢。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了近代上海工业的产生。上海最早的近代工业是由外商开设,与外贸有关的船舶修造厂、缫丝厂、打包厂,以及与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的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等等。之后,除了官办、官督商办的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外,上海的本国资本工业企业也在船舶修造、缫丝、木材加工、面粉、印刷等行业中相继出现。最后,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1894年,上海租界屡经扩大,人口已近30万,华界人口则在50万以上。城市面积的扩大,市政设施的完善,城市人口的增加本身即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们反过来又创造出新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概括此期上海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开埠以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使上海地理区位的潜能得以逐步发挥,以外贸为先导的产业格局推动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并由此而引起经济机制转换以及经济功能和地位的变动。上海开始从前近代社会的传统城市向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近代城市转化。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渐渐显露。
二、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1895-1937)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上海城市和上海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上海经济中心地位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这可以从近代制造业的发展及工业中心地位的形成,贸易的发展以及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1895年后,上海的外商工业企业,首先是棉纺织业得到较快发展。1895-1913年,全国开办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商工厂共有91家,其中上海占了43家,占总数的45.1%⑥。1913年,上海英商怡和纱厂、英美烟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耶松船厂,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等35家主要外商工业企业资本总额达5436万元,加上其他规模较小的工厂,资本总额达6346万元。1931年,在经上海市社会局调查的1500家工厂中,资本总额2.03亿元,工人总数22.26万人。其中外商工厂资本1.9亿元,华商工厂资本1.03亿元⑦。上海的本国资本工业在1895年后发展也很快。1911年,上海已有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工厂90余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列强忙于战争,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及资本输出,上海的民族工业更是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时期”的发展阶段。20世纪以后,上海已经逐渐形成了较具规模的杨树浦、闸北、沪南、沪西四大工业区。1912-1928年,上海新开设的本国资本工厂总数在1000家以上,并且形成了以轻纺为主、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1928年,上海工业已有纺织、化学、印刷、机器、食品、器具、日用品以及其他8大类54个行业,各类工厂1781家。至抗战前夕,上海全市已有近代工厂5500余家,手工工厂16851家,手艺作坊35615家⑧。上海的近代工厂、产业工人数量,以及工业产值大致已占到全国近代工业的50%左右。
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使得上海在20世纪前期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具体表现在:第一、近代上海工业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已占有绝对优势。1933年,上海有30人以上的华商工厂3485家,占全国十二大城市同类工厂总数的36%;资本总额1.9亿元,占总数的60%;生产净值7.28亿元,占总数的66%。第二、上海机制工业品的市场覆盖面遍及全国,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品生产、供应基地。1912年,上海工业产品总输出额为0.81亿海关两,到1921年已增至2.76亿海关两,增长了2.3倍。第三、上海拥有当时中国数量最多,整体素质最高的企业家阶层,以及稳定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队伍。第四、上海工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上海工业的资本规模、技术构成、经济效益等等都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五、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本国资本工业,同时也是外商在华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城市,许多国际大资本都以上海为主要工业投资地区。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外商在华工业投资的67%集中在上海。上海已是名符其实的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
贸易的发展以及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表现在三大贸易市场的扩大、近代贸易机制的确立以及贸易条件的完善等三个方面。
近代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量,1894年时还只有1.55亿海关两,1913年已增至4.21亿海关两,1931年更增加到11.11亿海关两,较1894年增加了6.1倍。1895-1906年间,上海直接对外贸易额始终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以上。此后,比重略有下降,但除1922年外,大体上都保持在40%以上⑨。30年代后,上海外贸占全国的比重又有上升,1936年占全国外贸总额的55%。贸易总额持续增长的同时,贸易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进口商品品种从19世纪70年代的近百种猛增到20世纪的1000余种,其中应国内制造业发展需要的生产资料类的机器、五金电器材料,以及生产原料类的钢铁、矿砂、农产品等进口数量增加更快。出口商品中,传统丝、茶出口比重下降,豆、豆饼、桐油等农副产品以及加工产品的比重上升。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本埠生产的机制轻工业产品向香港、南洋等海外市场的出口迅猛增长。1913年上海口岸轻工业产品出口只占出口总额的0.17%,1936年已上升到3.95%⑩。
国内贸易中最重要的是埠际贸易。20世纪后上海与国内各口岸的埠际贸易发展很快。在与外贸相联系的国内埠际转口贸易中,大体上在福州以北、山东以南的沿海区域,以及内地各省区的土货出口以及洋货输入都必经上海口岸。1860-1930年间,在国内一个口岸到另一个口岸的再出口商品总值中,上海平均要占到68%。上海生产的纺织品、药品、水泥、火柴、皂烛、搪瓷、橡胶制品、面粉等几十种产品有一半以上都是运销内地市场。上海的埠际贸易总值1913年为4.25亿海关两,1921年为6.47亿海关两,1930年已达9.44亿海关两。20世纪30年代,国内埠际贸易的18种最主要商品中,除花生仁一项外,其他都是以上海为最主要的输出或输入商埠。总计1925-1935年,上海与国内各通商口岸的埠际贸易大致要占到全国埠际贸易总额的38%左右。1936年,上海埠际贸易出口额为4.63亿元,占全国的39.1%;进口额为4.28亿元,占36.2%。上海埠际贸易在全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11)。
本地批零商业在20世纪上海人口迅速增加,以及南来北往流动人口为上海集聚巨大购买力的背景下,造就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本地商业消费市场。20世纪20—30年代,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先后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开张,南京路已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商业购物街。市区内公馆马路、霞飞路、静安寺、小东门等处也已形成主要的商业街区。市区周边沪西、沪北、沪东等地也兴起、形成了一批以中下层市民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商业中心。1933年,上海已有大小商业店铺7.2万户,其中公共租界2.28万户,法租界1.12万户,华界3.8万户。1936年,全市商业店铺再增至86639户(12)。一个从批发到零售,门类齐全的商业网络在上海已完全形成。上流社会新奇时尚的时髦消费,中产阶层追奇猎新的消费倾向,以及下层居民广泛的生存消费需求,造就了一个国内最大、最重要的消费社会。
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上海近代贸易机制的确立和完善。对外贸易中,主要的贸易机构仍是进出口商行,但与19世纪后期西方洋行在外贸中一统天下不同,20世纪后,上海华资外贸商行逐渐增多。1936年,上海917户专业进出口商行中,西方洋行559户,日商洋行116户,华商进出口行已有296户。国内贸易中,上海不仅有大量的本埠批发字号,经营国内埠际贸易,而且还汇聚了被称之为“客帮”的大量外地商帮。各省重要的批发商号或大型零售商店多在上海长期驻有俗称“庄客”的“申庄”派遣人员。上海的商业贸易通过洋行、本埠行庄、批发字号、外地坐庄、客帮贩商以及零售店铺、收购商贩等等,在上海口岸到内地之间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流通网路,从而保证了上海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
近代上海商业贸易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城市港口、航运、邮电通讯等现代贸易条件的完善。进入20世纪后,上海的港口码头、泊岸仓库、航运水道、交通道路、邮电通讯等等都有极大发展。1936年,全国拥有船舶吨位500吨以上的华商轮船公司,总部设在上海的占62%。上海港吞吐能力19世纪末仅为350—380万吨,1931年已激增至1265万吨;同年,上海港进出船舶总吨位达42万吨,创历史最高记录。20世纪30年代,上海外贸货物吞吐量平均占全国的55%,内贸货物吞吐量占38%,上海港已跻身世界十大海港之列(13)。此外,如铁路运输、邮电通讯等等也为上海的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30年代的上海已经名符其实地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
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可以从三大金融势力的并存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育及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诸方面加以观察。
20世纪前期,上海金融业发展的特征之一是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以及钱庄三大金融势力的并存。19世纪后期,上海外商银行一度是英商汇丰银行的天下。1895年后,上海外资银行纷纷设立,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及美国花旗银行与原先的汇丰银行一起形成了外商银行六强并存的局面。1935年,上海共有外商银行28家,占全国主要通商口岸外商银行总数的33%。上海的华商银行自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发展速度极快。1921年全国27家重要银行中有22家总行设在上海,业务比重达3/4以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组、设置国家银行系统的“四行两局”,总行或总管理处也都设于上海。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上海实有华资银行80余家,其中总行设在上海的52家,总行设在外埠而在上海设立分、支行或办事处的29家。此外还有总行另设的分行或办事处80余家。钱庄是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20世纪以降,钱庄以及其主要的信用工具庄票在上海的金融业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抗战前夕,上海加入钱业公会的汇划钱庄约有46家,另外还有兑钱庄70—80家。1925年,在上海金融势力的资力构成中,外商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占48%,华资银行占37%,钱庄占15%。存款总额中,华资银行占40%,外商银行为25%,钱庄为33%(14)。三大金融势力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业务范围各有侧重。外商银行主要分布于外滩;华商银行主要分布于江西路一带;钱庄则主要集中于宁波路、天津路周围。外商银行在国际汇兑中占有优势,华资银行在吸收存款以及对工商业投资、贷放款中居领先地位,而钱庄则在商业贸易的结算、埠际资金汇划以及银拆、洋厘等传统金融业务方面居主要地位。
金融市场方面,20世纪20—30年代,无论是以同业拆借、票据贴现为主要内容的短期货币市场,还是中长期借贷,或者公债、股票交易等长期资本市场都已初具规模。国家银行、外资银行、华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等各种金融机构皆以上海为大本营,上海已成为中国以至远东的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中心、汇划中心、融资中心以及证券交易中心。上海的外汇交易20年代以前主要以汇丰银行挂牌汇率为准。汇丰银行买卖的外汇总额经常占社会外汇成交额的50%—70%。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总行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挂牌汇率成为全国统一的官定汇率。上海的黄金交易主要在1921年成立的上海金业交易所内进行,主要交易品种为0.978成色、漕平10两1条的“标金”。1924年,交易量为2870万条,1926年增至6232万条。交易量之大,在世界黄金市场上仅次于伦敦和纽约,是远东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上海在国内贸易中汇划中心的地位主要是通过“申汇”而与各地维系。上海钱庄开出的庄票称之为“申票”,是国内贸易主要的信用工具和汇划票据。20年代末、30年代初,每年市面上流通的庄票数额高达白银20亿两以上。上海与国内各主要通商口岸的内汇汇率都以上海钱庄挂牌行市为准。
此外,还有以上海为中心的银行系统的资金汇兑。抗战前,仅中国银行在全国就有分支行及通汇点200多处,每年8亿元左右的国内汇兑额中约60%是内地汇到上海的汇款。20世纪前期,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融资中心不仅表现为社会游资、银行存款、同业拆放、长期借贷的资金融通中心,而且还是国债、财税资金的流转中心以及证券交易中心。上海银钱业的同业拆借以及贷放款中,大量的是向外埠拆借以及向外埠工商业的贷放。上海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内外债融资的重要场所。清政府举借外债的款项往来多通过上海的外资银行进行;北洋时期历届政府发行公债,上海银行也是重要的承销物件;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历次举债更都是以上海为中心进行。近代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开始于19世纪末,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是1891年开设的外商上海股份公所,交易证券主要为外商公所股票以及租界当局发行的各种债券。上海最早的华商证券交易机构是1913年成立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1920年更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交易证券有政府公债、铁路公债以及华商公所股票。上市公司包括外埠的大企业如汉冶萍、大生纱厂等等。1920年11月,上海又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1933年,该交易所证券交易部分归并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后者成为上海唯一的华商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品种以公债居多,成交额中98%以上为公债,1927年公债成交额达2.39亿元,1931年增至37.57亿元,几为全部公债发行额的2.3倍。1934年,公债年成交额高达47亿元。交易数量和规模都远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之上(1933年上半年,北京证券交易所成交额仅0.17亿元),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证券交易中心。
凭借数量众多的各类金融机构以及遍及全国的分支机构和同业行庄,凭借日渐扩展的各级各类金融市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已完全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龙头所在。上海金融银根的紧松,汇价的涨落,利率的变动,存银的多少,证券行情的上下,信用的张弛,一举一动都维系和左右着全国的金融行情、市场行情和经济局势,上海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金融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已形成了多元化、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以上海城市总体的产业结构以及演进轨迹观察,金融业、商业贸易以及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仍是上海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首先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都市,其次才是一个工业城市(15)。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也表现为既是商业贸易中心,又是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合而为一、多元化的经济中心。上海不只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同时还是国际资本在中国以及远东的汇聚点,是世界市场的东亚枢纽。
三、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城市经济功能与地位的起落(1937-1949)
近代上海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八年抗战期间,上海的社会经济环境,城市的经济功能与地位都发生了极大变化。战争初期上海经济遭受重创。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上海经济在战火中损失甚巨。上海毁于战火的工厂合计多达2270余家,资产损失至少在8亿元以上(16)。1937年下半年,上海对外贸易也因为港口封锁、航运断绝等原因急剧下降。外贸重心呈现出向天津和广州转移的迹象。沪战爆发前后,上海又有150多家重要工厂内迁,中、中、交、农等国家银行也相继迁往内地,上海的资金、设备暂时都发生分流。华界沦陷后,沦陷区内工厂企业多被日军以“军管理”、“委托经营”、“中日合办”等方式控制。战前上海作为全国以及远东经济中心的地位受到重创。
1938年后,战事西移,上海租界因为有国际条约的保障,战火未及,租界与国内外海路交通也很快重新畅通,东南诸省避难人口、社会资金汹涌而入。处于日军包围下的租界孤岛出现了一时的工商业繁荣。
首先是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租界地区新建的大小工厂达1900余家,公共租界及租界越界筑路地区所设的大小工厂总数已达4250余家。其中尤以战前多为进口洋货竞压的化学、造纸、五金、机器等行业发展最快,进口洋货的替代产品以及行销南洋市场的日用生活消费品生产量增长最速。其次是商业贸易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1939年,上海租界房地产成交金额高达4266万元,仅次于战前最高年份的1933年,建筑业的开工、竣工数量也达到5年来最高的水平(17)。对外贸易1938年虽有较大萎缩,但到1939年,情况已有很大改观。1940、194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超过战前1936年的水平(18)。进口商品中,因日军统制以及国内来源受阻的粮食、棉花、燃料等生活用品及工业原料大幅度上升,进口值居进口商品之首;出口商品中,仰仗内地供应的农副产品出口下降,上海本埠生产的轻工业制成品上升,香港、南洋等海外市场扩大很快,对外贸易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出超现象。1937年,上海至香港、南洋的出口额仅占上海出口总额的11%,1941年1—10月间已猛增至45%。1938-1941年间,棉纱、布、针棉织品等9种主要轻工业品的出口值已占到上海全部出口值的22.88%。国内埠际贸易中,上海通过香港以及东南沿海宁波、温州等口岸向内地的贸易也旺盛不衰。1940年,上海的国内埠际贸易总值高达13.15亿元,其中出口额9.56亿元,占全国埠际贸易出口总额的63.98%,进口3.59亿元,占全国埠际贸易进口总额的24%,出超额高达6亿元之巨(19)。再次是资金的集中。1938年后,不仅内地富户多携资金来沪避难,内地银行迁至租界继续营业,而且原来流入香港、南洋一带的海外资金也多回流上海。1939年下半年,仅从香港一处流入上海的资金即达15亿元,全市中外银行存款高达30亿元,约占当时全国存款总额的60%。1941年上半年,上海的游资总额已达57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1940年底法币发行总量78.7亿元的2/3以上。资金的集中一方面极大增加了上海金融业的资力和对社会工商业的投资、贷款能力,支持促进了工商业繁荣;另一方面,大量游资也刺激了战时物资紧张情况下,以囤积居奇及黄金、外币、证券买卖为主要内容的投机事业,形成了史学家们常称之为的“孤岛繁荣”。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租界。租界内的英美等西方国家企业皆被日军当局以敌国财产封闭或没收。同时,日军又从侵华战争需要出发,对金属、棉纱等几十种重要的工业原料、工业产品实行统制。上海的海上交通也被封锁管制,原料进口断绝,海外市场丧失,工业用电因燃料缺乏受到严格控制。这一切使得上海工业在1941年后顿见中落。以工业用电为计算口径的上海工业生产指数,1941年还有1936年的80%,到1943年只及40%,而从1944年到1945年8月,在燃料来源断绝,电力限制极严的经济统制背景下,上海工业生产量还不及1936年的1/4(20)。
对外贸易在太平洋战争后,由于海运不通,商轮绝迹,远近洋贸易一概停止。上海完全丧失了作为中国以及远东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国内贸易也由于日军严厉的物资统制以及流通运输上的困难而萎缩停滞。上海市内物资紧缺,物价飞涨,黑市盛行。物价指数若以1936年为100,1942年已达3452.6,1944年更高达100739.4。1944年的货币购买力仅及1936年的0.0993。与此同时,上海市面上游资充斥,黄金、外汇、股票买卖风行,房地产交易兴旺。新设的工商业企业中,以与金融、房地产有关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各类企业公司为数最多。1942年,上海共有大小银行、钱庄402家,其中银行208家,钱庄212家,较战前分别增加了134家和120家。上海的证券交易在孤岛时期已私下授受。1940年,上海信托业同人联欢会自设中国股票推进会,介绍买卖股票,品种达85种。同时,租界内还有外国商人的“上海众业公所”,上升交易外商企业股票、债券达150多种。日军进入租界后,西商上海众业公所被勒令停止交易,华商股票公司却逐年增加,1942年已达142家。1943年9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被允准重新复业,很快成为上海游资重要的投机场所。与战前的上海证券交易以债券交易为主不同,战时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品种已经是以股票为主,上市交易的公司股票最多时达190余种。房地产交易,1942年全年交易额为1亿元,1943年达5亿元。1944年,全市房地产公司仅加入房地产同业公会的有300家之多。各种名目的企业公司竞相开设,最多时也达300余家。这些企业公司既不同于战前的工厂企业,也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公司,它们从实业到贸易,从金融到证券、房地产,经营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并且还形成了诸如新亚集团、中法集团之类跨行业、跨部门的资本集团。企业公司的组织形式成为战时上海企业制度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上海一扫八年战争之阴影,力图重振经济,再展东亚经济中心之雄风。以工业而论,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上海约有工厂4100家。到1947年,上海已有工厂7738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54.9%;产业工人36.74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53.8%。上海近代工业的机器设备为全国各大城市工业设备的65.7%。1948年,上海88种工业行业有大小工厂12570家,产业工人45万。上海棉纺织业拥有占全国总数50%的纱锭,60%左右的织机;毛纺业拥有的纺锭占全国的80%;卷烟工业占全国的70—80%;面粉工业产量占全国的近40%,上海继续保持着全国工业中心的地位。以贸易而论。1946年上海进出口贸易额高达6.68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额的80.3%。1947年,上海华商进出口行最多时达1464户,为抗战时期1941年613户的2.39倍。以后数年,上海外贸在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仍占全国的61.7%,远远高于抗战前水平(21)。从市内商业来说,战后的上海商业已有20多个大类、200多个行业,每个行业又有门类齐全的内部分工。全市除了数以10万计的批发企业、百货公司、商业店铺外,还有面粉、金业、纱布、杂粮油饼、证券物品等交易所,以及七八十个各种行业的茶楼交易市场,其交易量之大,在全国首屈一指。再拿资金来讲,1946年后,内地战区有产阶级掀起携资迁沪高潮。上海人口1947、1948年高峰时曾达600万人。1946年最后3个月中,全国各地流入上海的资金高达法币6000亿元,加上上海原有的2000亿元,上海集中的游资高达8000亿元(22)。1946年底,上海有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合作金库等大小金融机构564家,占全国金融机构总数的10.4%。1947年8月间,上海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数额高达14000亿元,占全国存款总额的56%。
战后上海虽然仍然保持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但与战前相比,国家资本、官僚私人资本的膨胀,以及国家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影响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一度实行放松进口管制以及低汇率(1美元兑2020法币)的双重外贸、外汇政策,上海对外贸易出现巨额入超。1946年,上海外贸进口额竟是出口额的5倍,入超金额高达4.46亿美元,占全国入超总额的94%。形成巨额入超的进口商品绝大部分是美国的战后剩余物资及倾销物资,大至汽车,小至口红,充斥上海市场。上海的本国资本工业因进口货物的冲击苦不堪言,纷纷倒闭破产。1947年后,国民政府提高外汇汇率,并改行进口配额制,外贸入超始有改善,但直至解放前夕,外贸入超局面并未改观。1948年,上海外贸入超仍达0.44亿美元。
货币金融政策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莫如通货膨胀。上海的通货膨胀在战后不久即初见端倪。1945年9—12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已上扬71.5%。此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上海已成通货泛滥的基地,逐日增大的发行额有一半以上从上海发出,各地的新发行额以及社会游资也因时局变化等原因迅速流向上海,上海的通货膨胀扶摇直上。1946年,物价指数上涨了7.7倍,1947年上涨14.7倍,1948年头8个月又上涨56倍(23)。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又以1∶300万收兑法币,发行金圆券,并且强制民间低价兑出金银、外币,并限制物价,冻结工资。到10月底,共收兑民间金银外币1.9亿美元,其中上海收兑量占全国之半。1948年11月,国民政府被迫放弃限价,上海物价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当月物价指数较9月份上涨了1123%。进入1949年后,上海物价更以惊人速度上涨。总计1945年9月到1949年5月的3年零9个月中,上海物价指数上涨了3.5万倍,如果加上法币折合金圆券300万:1的因素,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的物价指数已是抗战前1936年时的363660亿倍(24)。
在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上海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极大干扰,社会工商各业在国家掠夺性的通货政策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社会工商业者以及各阶层人民在1948年8月的币制改革中,被迫兑出近亿美元的金银外币;同时期限制物价激起的抢购风潮又使上海工商业损失资金高达2亿元金圆券,折合黄金200万两。在通货膨胀越演越烈的1948年下半年及1949年上半年,上海工业生产萎缩,停工倒闭时有发生。近代上海经济在经历了近百年发展后,又一次面临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国家资本大规模外移台湾;民营资本一部分外流,一部分也是消极彷徨,外商企业也开始大规模收缩。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上海经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四、上海经济功能、地位之再造(1949-1956)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标志着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开始。与新旧政权更替,旧国家机器被彻底粉碎而代之以新政权不同,解放后的上海,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旧经济格局仍是上海经济的主体,这种旧有经济格局与特点主要反映在:由于上海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是以商成市、以港兴市,贸易→金融→工业→经济中心的发展道路,上海经济结构中,商业贸易及金融业始终占有极大的比重,反映在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上,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更是一个贸易、金融、经济中心;在上海的工业结构中现代工业虽已占84%的比重,但轻纺工业长期以来一直占有绝对的比重,特别是纺织工业几乎要占到全部近代工业的60%;与前述工业结构特点相联系,上海城市经济,特别是近代工业对国内外市场的相关程度极高,国内市场既为上海工业提供大量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同时也是上海工业制成品最大的销售市场,国外市场则是上海工业机器设备、重要生产原料的主要供应者,国内外市场的些微变化都会使上海经济格局,特别是工业格局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与上海的发展历程及产业结构和经济地位相适应,上海既是一个工商业生产性城市,同时更是一个消费性城市,各阶层社会人口的大量聚居,以及相应购买力的汇集,使得上海城市经济中的消费服务行业特别发达,新政权建立后,由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这些行业已失去了昔日稳定的消费主顾,整个城市的消费行业,特别是奢侈性消费行业面临历史性的大改组。
解放初的上海,在骤风暴雨式的政治变革之后,暂时少有变化的经济格局已经呈现出与新生政治制度和社会阶级变化不相适应的状况。新旧政治、经济制度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就是上海解放后不久即出现的,工厂生产开工不足,市面滞缓,以及物价上扬的三大经济问题。工业生产开工不足在1949年下半年及1950年上半年尤为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外市场变动后,昔日依靠海外市场供应的工业原料来路断绝,国内市场也因局势未平等原因,一时难以为继。1949年7月,上海87个工业行业13647家工厂中,开工厂家仅占25.9%,停工的达74.1%。即使是开工厂家,开工率也只有生产能力的20—50%。1949年底,68个工业行业10078家工厂中,开工率也只有61.7%(25)。市面滞缓的突出表现是外埠市场销路不畅,市场交易萎缩,货物积压严重。1950年3月初,上海商品市场总成交额仅及前2个月的30%左右。上海六大百货公司3月份的营业额仅及1月份的50%不到。其中尤其是高消费行业营业更为清淡。与上述经济不景气相随的还有物价的大幅上扬。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20倍。1950年上半年物价继续看涨,6个月中又上涨了40%(26)。这些都给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恢复上海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就必须实现对经济局势的控制,首先就是对旧有金融、商品投机势力的管制和取缔,以及对市面的控制。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公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命令》,规定以金圆券10万元折合人民币1元的比价进行旧币的收兑。7天中,收兑金圆券36万亿元,占金圆券发行总额的53%。然而即使如此,社会上以银元黑市买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投机势力仍然十分猖獗。为了根绝与人民币流通相抗衡的地下金融势力,6月10日下午,上海军管会一举查封了汉口路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取缔了银元的黑市交易。至此,人民币遂成为上海市面上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在对市面的控制方面,新生政权在解放后的半年内,除了上述取缔银元投机商外,还经历了在商品市场上与粮棉投机商的斗争,以及组织制止波及全国物价大涨风的斗争。三次大斗争沉重打击了市场投机力量,从根本上平稳了上海的经济局势。
经济局势平稳之后,经济工作的重心就开始转向对私人工商业的控制。这主要从两个环节入手:一是凭借国家政权以及国营经济的力量,通过控制市场来控制私营工商业;二是利用国家法令、法律直接干预工商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如规定私营金融机构不得从事金融投机、商品投机等等。表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就是著名的“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就是要在国有经济尚未能占绝对优势、私营经济又尚未能完全取消的情况下,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起一定的作用;而限制是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不是任其自由的“天高任鸟飞”,而是在国家允许和规定的范围内延续;至于改造则明白无误地表明利用、限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也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对当时的新生政权以及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定优于和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和国领袖们来说,是坚定不移的。
在对私人工商业实行控制的同时,新生政权也开始了更为重要的新国有经济的建设。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迅即没收了上海境内全部前旧政权以及旧政权官僚的财产,在此基础上,组建起了上海解放后最初的新国营经济。工业方面,没收接管了157个前政权的轻重工业企业单位,1949年底,在没收接管基础上形成的上海国营工业在上海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已占16.5%。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已上升到全市工业产值的27.7%(27)。国营商业方面在接收前政权贸易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起了以商业批发为主的国营贸易机构——上海市贸易总公司和国外贸易总公司,粮食、化工原料等专业公司以及下设批发站和基层商店。1952年,国营商业批发额已占上海批发总额的56.3%,零售额占23.4%。
国有经济建设之外,要真正实现上海经济功能地位之再造,更重要的还是要对总量庞大的私营工商业(或者称之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主要形式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以及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
上海私营经济中的公私合营早在解放后不久的1949年下半年即已出现。为数不多的合营企业主要是国家通过没收旧政权资本在私营企业中的股份,并将其转化为国家公股而实现的,方式也仅是一家一户分别进行。1949年,上海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仅15家,产值只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0.4%;1951年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产值也只占上海工业产值的4.3%。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即成为上海经济工作的基本任务,公私合营步伐加快。在此之前,1952年底,上海的私营金融业已在中央“坚决淘汰私营行庄”的决策下,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已全面确立了在上海金融业市场上的领导权和经营权。1954年,上海又有211个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实现公私合营,合营工业企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0.3%。1955年,上海棉纺、毛麻纺、卷烟等8个行业率先在上海私营工业中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一个全面公私合营的高潮已在上海出现。1956年1月20日,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上,除过去已经实现合营的企业外,全上海205个私营工商业行业,106274户私营工商业企业被一次性批准实行公私合营(28)。在此同时,上海的个体手工业、摊贩等也以合作社、联营等方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原定用3个五年计划,大约15年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在3年不到的时间里,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轰轰烈烈地提前完成了。
以对资改造的完成为标志,上海工商企业的企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合营以后的工商企业,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均由国家有关部门委派任命,公方代表作为党和国家的派出人员,在企业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企业的生产经营逐步听命于国家主管机关的指令性计划,企业利润上交国家,企业所需资金、设备、原料、物资皆由国家按计划调拨。上海的工厂企业已从原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独立自主的经营法人逐步转变成为计划经济下的国家生产供应部门。这是上海企业制度发展历史上意义极为深远的历史性转折。上海已经从旧日市场经济下多功能的经济中心逐步开始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工业基地转变。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上海的社会经济将以新的路径和特点开始新的成长。
五、简短的结语
19世纪中叶之前,上海还完全是一个传统社会。依托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以及上海港的有利地位,上海在国内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基本上处于分离的状态。上海开埠以后,19世纪后半叶,在以外贸为先导的推动下,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与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并且在内外贸易一体化的推动下,开始了近代经济的初始化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条约口岸的特殊地位以及上海本身优越的地理区位,使得上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城市面貌发生极大变化,并迅速成长为中国以至远东的工业、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成为国际资本在中国以及远东的汇聚点、世界市场的东亚枢纽。20世纪3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上海城市的经济功能与地位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抗战时期,上海经济对全国的影响力、辐射力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数年,上海经济历经艰难曲折,几近崩溃局面,历经百年成长的上海经济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1949-1956年,对上海经济来说是旧时代结束、新纪元开始的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上海经济不仅完成了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渡;并且随着这一历史性过渡的完成,上海的经济功能和经济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843到1956年,一个多世纪的上海经济,先后经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两大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年代和发展阶段,上海经济具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内涵和发展经验。在前一个时期,贯穿始终的中心内容是上海如何成长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而后一个时期,贯穿始终的中心内容则是如何在对资改造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和企业制度,并且向日后的“老工业基地”过渡的问题。
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经济的成长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上海经济的历史成长不只是上海自身要求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客观的自然、社会、历史、现实因素交会、融合的结果。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以及怎样充分发挥这一地理区位优势在上海经济成长中的基础作用。其次是上海经济之所以能够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内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与其生生不息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着莫大的关联。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冲动以及创新的环境,即全方位的全面创新,对于上海经济的百年成长始终具有首推的重要意义。再次,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经济的成长,与高度的对外开放具有极为重要的关联。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是世界的上海,这绝不是流于形式的纸面文章,而完完全全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经济成长的真实写照。正是在“海”一样广阔的要素高度流动和高度开放中,上海才能在激烈的海内外竞争中永葆创新活力,在百年内崛起于中国,雄起于东亚,成为中国以至远东的工商业、金融、经济中心。最后,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一向尊重历史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经验,开放的上海也应是善待自身历史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一切于己有用之物的上海。面向新世纪,再现上海雄风,再塑上海的经济功能与地位,上海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思索和汲取。
注释:
①参见绍熙《云间志》卷下,《隆平寺藏经记》;陆楫:《兼葭堂杂着摘抄》;李星沅:《李星沅日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208页。
②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498页;张忠民:《从“小苏州”、“小广东”到“大上海”》,《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252页。
③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1页;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版,第90页。
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⑤陈文瑜:《上海开埠初期的洋行》,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7页。
⑥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11页。
⑦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
⑧叶笑山、董文中:《中国战时经济特辑》,中外出版社1939年版,第77页。
⑨参见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版,第90页;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统计》商业,上海市地方协会1933年版,第1、4页;上海市地方协会:《民国三十三年编上海市统计补充材料》商业,上海市地方协会1935年版,第40页;上海市地方协会:《民国二十五年编上海市统计第二次补充材料》商业,上海市地方协会1936年版,第56页。
⑩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198页。
(11)郑友揆、韩启桐:《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中国科学院1951年版,第Ⅲ、Ⅳ页。
(12)上海市地方协会编:《民国二十二年编上海市统计》商业,上海市地方协会1933年版,第1页;叶笑山、董文中:《中国战时经济特辑》,中外出版社1939年版,第124页。
(13)上海港史编写组:《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263、290-296、360-361页;董文中:《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续编》,中外出版社1940年版,第229页。
(14)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0-20页。
(15)1933年,在上海的工商业资本中,工业资本大致只占到资本总额的33.2%,而商业资本则要占到资本总额的66.8%。论者皆以为“上海为吾国第一大埠,其所以成为经济中心者,赖其贸易之发达”。参见王季深《战时上海经济》第1辑,上海经济研究所1944年版,第60页。
(16)《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续编》,中外出版社1940年版,第213页;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0、92-93页。
(17)《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续编》,中外出版社1940年版,第222页。
(1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9)《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中国科学院1951年版,第Ⅱ、Ⅳ、10-13页。
(20)田和卿:《上海之战时工业》,载朱斯煌《民国经济史》,银行周报社1948年版,第475页。
(2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22)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60年版。
(23)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3-96、98页。
(24)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25)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计划处编:《上海私营工商业分业概况》,上海市人民政府1951年版,总第6、8-9、86、60、67-74页。
(2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27)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上海私营工商业分业概况》,第4、149-150页。
(28)申请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家数,公私合营申请书上为85个工业行业35163户,120个商业行业71111户。以后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行业数和工商业户数都有调整。一次获得批准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共计203个行业、88093户,其中工业94个行业、25852户(包括带进公私合营的个体手工业户7674户),商业(包括饮食、服务业)96个行业、58978户,运输建筑13个行业、3263户。参见《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2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