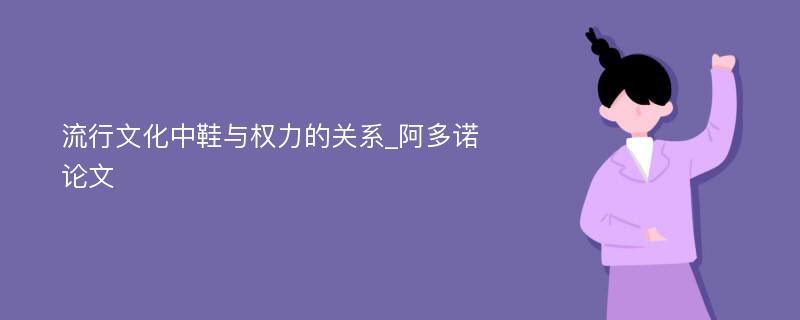
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鞋论文,权力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想通过对“波鞋”的解读,来讨论当代流行文化。
街上流行波鞋,已有十多年了。波(ball)鞋就是球鞋,只是一中文名儿、一英文音译名儿而已。但我的小孩儿不这么看。有一次她让我给她买一种鞋,我嫌贵,要给她买另一种,并希望通过“思想工作”让她同意我的选择。我说,都是球鞋,有多少差别呢?她一听,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我说:“你有没有搞错?你那是球鞋,我这是波鞋!”
“球鞋”与“波鞋”原来有这么大的不同!从孩子的语气里我知道,把“波鞋”当成“球鞋”,或者搞不清楚波鞋与球鞋区别的,肯定是老土。
其实,市面上被称为“波鞋”的球鞋与被称为“球鞋”的球鞋,二者表层的区别我是知道的—不然,我也不会企图给孩子做“思想工作”—它们是不同质量档次和不同价格档次的两种球鞋。穿不同鞋的人,自然也分出了不同的档次。在大街上,你其实不用看别的,只看脚,就可以将人分出贵贱。以穿球鞋而论,那些有“款”的味,大款或者中小款,那些有“酷”味的,酷哥或者酷妹,穿的准是“波鞋”。而那些建筑工地的民工,低下工作的打工仔,贫民小区里拿着报纸垫在屁股底下在树下度光阴的老大爷,穿的准是“球鞋”。
球鞋是没有影响力的,因而时尚潮流被“波鞋”引领着。一个东西成为时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不管经济能力是否允许,人们都争相“波”将起来。这时尚的力量,你在大路上可以看到,在商店也可以看到。一进商店你就会发现,“波鞋”都在名牌商店、精品小屋的大柜台里醒目地摆着;而“球鞋”,早已被挤到不起眼的商店的不起眼的角落。
一双鞋的质量等级被名称、符号的等级所取代。一类商品,质量、价格档次有高低是很正常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波鞋”与“球鞋”本来是一个概念,外延与内涵都没有任何区别,它们本来只应有一个所指,它们之间也谈不上什么档次,怎么就在一个名称里弄出两个所指、弄出两个等级来了呢?
我曾经想,能不能将“波鞋”换一个能区分档次的中文名儿呢?但瞬间我就否定了自己的书呆子气—即使为高档球鞋找到了一个中文名儿,它也未必能流行起来。这里的关键不在“档次”,而在“流行”。它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商业机智或者说商业秘密:同一类东西,有的要用中文名儿叫之,有的却必须用英文名儿称之。二者的差别之大,足以在流行观念里成为两种东西。这就有点意思了:同一类东西,为什么一被冠以英文名儿,其身价就不同了、就能流行起来呢?
二
“波鞋”并不只是波鞋。美国西北大学梁伯华教授把流行文化分为八类,以服装为重要内容的时尚文化被排在第一。霍克海默曾说过,“必须搞清楚,口香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
正当我准备对“波鞋”的“形而上学”皱眉头的时候,另一意象突然撞进我的大脑。中国历史上,与球鞋相关的,曾经还有个对子:球鞋与解放鞋。解放鞋也是一种球鞋,但它是解放军穿的球鞋,坚实、耐用。那时一般的球鞋质量不高,不耐穿、不耐脏,穿上几天,要么鞋帮破损了,那么鞋底穿洞了。而解放鞋就不同了,即使颜色穿白了,鞋面也不会损、鞋底也不会坏。我当知青的年代,在我下放的地方,包括解放鞋在内的所有军用品一定比民用品好。那年月,能用上军用品是十分荣耀的。一顶军帽、一套军装、一个军壶、一条军用条带,这些都不用说了,即使你有一双解放鞋,走在大街上,你的感觉就会比平常不同。脚有时会不自觉地抬高了。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军用品的。那么,你是军人家属,那自然是光荣的,有一些军用品用,也理所当然。但那年月,并非军人家属、能用上军用品的,大有人在。这才是本事!你得有地位、有身份、有关系、有路子。或者说,那年月,能用上军用品,比如,穿上一双解放鞋,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表征。解放鞋,将你和穿一般球鞋的人区别了开来,它显示了人物的身份、背景等鞋之外的很多意义。因而在那时,“解放鞋”与一般球鞋之间,有一种等级、一种特权。
这种等级、特权里往往暗藏着一种政治权力。有一个小故事今天听来是可笑的,但这笑却并不轻松。我当知青时农村里运动也多,一有运动,就会拉几个地富反坏右出来批斗一番。一次运动又来了,队领导正准备将一个劳动不积极的人定为“坏分子”拉出来批斗,却发现他穿了一双新解放鞋。领导们警惕了,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果然,有消息传来了,说是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早年被国民党拉了壮丁,人们一直以为他死了。其实他没有死,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官儿,最近联系上了。就这么一个传闻,对一个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传闻中的官儿一直未见回来,但当时,那场批斗却落到了别人的头上。那时的坏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是不可能穿上解放鞋的。而穿上解放鞋的,就不可能是坏人。今天,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柏是很难理解,鞋里,还能藏着这样的政治玄机!
更重要的是,解放鞋里的等级、特权,与当时的政治观念紧密相联。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穿上了军装。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4年的卫士钟顺通回忆,196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一天,早上临出发前,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这下让工作人员着急了,因为平时并没有为主席准备军装,而且临时要找到主席这种身材穿的军装并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满足了主席的愿望。毛泽东到达天安门城楼时,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林彪一看主席的穿着,慌神了,立即让他的警卫秘书回家取来军装。林彪是穿好军装之后,才出去同主席一同接见红卫兵的。
毛泽东的突然穿军装与林彪的敏感,都是极有深意的。从那时起,军装、军用品便与革命、革命资历等紧密相联。不仅要穿军装,而且要穿那种被洗得发白的军装—那是革命资历的象征。当时的小青年可以为一顶军帽打架,更可以为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杀人。一双解放鞋的价值,也就当然远远不只是其质量高于一般的球鞋。
历史翻过一页。球鞋与波鞋这个对子在历史上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波鞋”是对“解放鞋”的冲击。波鞋一上街,解放鞋便立即失去了原有的亮度。以它卓杰的风姿,波鞋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它真皮的质地、优美的外观、极佳的弹性和良好的透气性能,以不可阻挡之势征服了人们的脚。
在某种程度上,原有的等级失效了、原有的特权丢失了,有钱就行。商店并不因为你是老革命或者你革命意志坚定,就让你享有穿用波鞋的权利,而一迭人民币则可以赢来店家灿烂的笑容和优质的服务,并让你的脚踩在时尚的大地上。
新的观念也形成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阶级斗争的被废止,“阶级”、“革命”等字眼的使用频率急剧下降,“经济”、“商品”等字眼却大红大紫起来。越穷越光荣的时代过去了,越穷越革命的时代过去了;富,成为可以自豪的事情,甚至成为推动民族强大的动力。以前,将几百元乃至上千元钱变成鞋踩在脚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现在却成为一种时髦。
然而,新的等级也形成了。并不是任何人都穿得起“波鞋”,你得口袋里有大把的钞票。一双波鞋是一个农村孩子一年的学费,甚至一个农民一年的总收入。商店的门是可以自由出入的,但农村孩子却没有买波鞋的自由。在波鞋面前,或者说在新的等级面前,有钱,你就有享受的特权;没钱,你就只能看着别人享受。
于是,在“球鞋时尚”从解放鞋到波鞋的历史里,我们看到了两种权力关系:政治权力关系与金钱权力关系。在这两种权力关系里,我们都看到了等级、特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扩大,从脚到全身,或者说,从鞋到全部服装,我们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曾几何时,街上除了少数军装之外,就是满地的蓝布中山装。统一、单调。蓝布中山装将数亿人统一包裹着,人们的鼻眼都淹没在那无变化的色调之中。本来是千姿百态、无法一致的个性被强制性地一体化了。没有个人、没有个性。走在大街上,你只能昏昏欲睡。与蓝布中山装不一致的花里胡哨的服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弄不好,轻则被批判,重则被专政。蓝布中山装里,隐藏着你无法逃脱的政治权力关系。
时装上街后,情况不同了。当你从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时装伸出梦幻般的手抚摸着你的眼睛。那温柔的抚摸使你的耳边似乎演奏着轻音乐、嘴里仿佛嚼着口香糖。你得承认,真舒服。那么五彩缤纷、那么丰姿绰约!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穿得起时装。一套时装在一个农民眼中往往是他一生都不敢想像的天文数字。有钱人有权支配时装,可以在时装的大海里畅游,一天换三套乃至多套;穷苦农民却连时装的边也摸不着。时装里,隐藏着金钱权力关系。你也许意识不到,但没有一个人不生活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中。
三
从解放鞋到波鞋的“球鞋时尚”演变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政治权力关系还是经济权力关系,之所以能在时尚中运行,得力于一组二元对立的文化机制:好/坏,新人日,进步/ 落后,新潮/落伍……
时尚总是用“好”、“新”、“进步”、“新潮”吸引着人们、推动着人们。时尚利用人们的欲望。欲望总是追求“好”、“新”等等。在某个时期、某个时代,某种东西成为“好”与“新”之后,它就会成为人们的追逐目标。在“文革”时期,解放鞋好,人们追逐解放鞋;80年代后,波鞋好,人们追逐波鞋。“文革”时期,“革命”好,人们追逐革命;80年代,金钱好,人们追逐金钱。
时尚也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或者说,利用人们的被认可的欲望。某个时期、某个时代的人们总希望被那个时期、那个时代的“好”所认可,在那个“好”中展示自己的才干和实力。
而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诱惑里,隐藏着另一组字眼:大众/个人、制约/自由。在时尚里,“好”,并不是个人认定的。什么东西形成了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好”的潮流,它就把个人卷了进去。在大众对那个“好”的追逐中,“个人”消失了、个性淹没了。在时尚中,你没有选择的自由,你在潮流的制约之中。时尚把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统一的群体、把有个性的“人”变成了群体的“类”。“人”被“类”的置换,是在对时尚的“好”的追逐中不经意地完成的。
“个人”在“类”里消失后,是谈不上个人权利的。因而在时尚里,个人永远只在权力关系之中被权力所左右。在政治权力关系时期,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是政治,而不是任何个人;在经济权力关系时期,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是金钱,也不是任何个人。这是流行文化中权力关系的本质!
以前我们反思“文革”,往往从极左、政治迫害、欺骗与受骗等角度反思。这是对的,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深入。但还有另一个角度是我们忽略的,那就是,时尚。当从时尚角度反思“文革”时,我们会有新的发现。“文革”时期,为什么千百万青少年争当红卫兵?为什么千百万红卫兵涌向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为什么面对昔日的同学和朋友,只因为观点不同,红卫兵就可以像对待敌人一样,真刀真枪的干,致使那么多人慷慨赴死?仅仅用欺骗与受骗解释是不够的。即使就“欺骗”而言,对一代人的欺骗是如何得以完成的?原因之一是,文革”时期,革命,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裹挟千百万青年去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每一个人都以为他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其实每一个人都失落了自己。每一个人都以为是他选择了“革命”,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被“革命”所选择。在红卫兵中,也有司令、革命委会成员等叱咤风云的权力拥有者,但那都是假象。他们都只在当时的权力关系之中。那时的最大权力拥有者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人,而是“政治”!他们都是被政治运作的卒子。
进入商品经济时代,金钱成为新的时尚。挣到钱的人都以为是自己挣了钱,其实,是钱挣了人。金钱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诱惑力,让人们为它去奋斗、拼搏。时装、名车、别墅,有钱人可以拥有这一切,但他并不是这一切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金钱。因而,在金钱权力关系中,人可以得到一切,惟独难以得到的,是自我。
四
文章写到这里,批判态度似乎已经明显了。我们似乎该走向法兰克福学派了。但是,不。我要说的恰恰是,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对任何理论的借用也应该是复杂的。近年来对中国当下流行文化持批判态度的观点,大多受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影响。但这里却潜藏着危险。陶东风先生曾对这一危险进行过认真的学理性的分析。陶东风先生批评某些中国论者在借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理论框架时,说他们“没有对这个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省”。除了“适用性”问题之外,对法兰克福学派部分学者的理论本身,陶东风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阿多诺等人“混淆了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商品经济制度在文化上的极重要的区别”,“没有清晰地分辨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如极权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其典型)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所以常常把极权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
这些论述是很精彩的,我十分赞同。而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使在当时的法兰克福学派内部,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的观点,也并未得到普遍认同。本雅明与阿多诺等人的看法就有很大不同。本雅明对电影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把电影作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典型代表。本雅明对传统艺术作品是有留恋的。他认为,传统艺术作品有着“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这种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原真性作品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它的“韵味”。而“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韵味”。
本雅明丝毫不否认这一“凋谢”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因为韵味的衰竭“与大众运动日益增长的展开和紧张的强度有最密切的关联”。但本雅明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认为这是艺术的一次“解放”。本雅明在他的论述中多次用到“解放”这一词汇。他说,“复制技术把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把一件东西从它的外壳中撬出来,摧毁它的韵味,这是感知的标志所在。它那‘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增强到了这般地步,以致它甚至用复制方法从独一无二的物体中去提取这种感觉。”
明明知道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而大众文化遭到阿多诺等人的严厉批判,本雅明还是把它视为一种“解放”。本雅明与阿多诺等人的分歧就是不可避免的。对本雅明的这一研究,阿多诺很不赞同,他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持否定态度。阿多诺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致力于调和广大观众和现存秩序”。他说,艺术作品应该是对“被当代环境否定了的‘彼岸’世界的暗示”,而大众艺术却是与这一“否定”功能对立的。
阿多诺等人的反对,并没有改变本雅明的思考。他在给阿多诺的信中解释二人分歧的原因时说:“在我的研究中我追求阐发肯定的因素,而你显然是揭示否定的东西。”
这一区别是重要的。为什么产生了这一区别?美国学者、《法兰克福学派史》的作者马丁·杰认为,这是因为阿多诺以研究音乐为主,而本雅明“对音乐不感兴趣,特别是他无意将它作为批判的潜在媒介”。这里有着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对象问题,其二是研究进路问题。马丁·杰敏锐地看到了这两点,但却都没有说到位。
在研究对象上,我以为,除了本雅明对音乐不感兴趣外,更重要的,是本雅明对电影感兴趣,这决不是玩文字游戏。电影是当时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它尽管幼小,却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研究对象的不同里,隐藏着本雅明与阿多诺等人最深刻的区别之一。
把思想的义愤和研究的重心始终聚焦在对法西斯极权的批判上,是阿多诺等人最大的特色和最深刻之外。当然,它也限制了他们思想的视野。这便出现了陶东风所指出的没有分清“极权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问题。本雅明却不同,他在对法西斯进行批判的同时,把目光敏锐地投向了新兴的艺术。它给他的思想带来新活力,使他的思想在时代的进展里推进。
而在研究进路上,本雅明对我们的最大启发,在于他对艺术进行的历史思考。本雅明不否认他对传统艺术作品“韵味”的喜爱。但“韵味”意味着什么呢?正是从这里,他走进了历史的思考。他说,
艺术作品在传统联系中的存在最初体现在膜拜中。我们知道,最早的艺术品起源于某种礼仪一起初是巫术礼仪,后来是宗教礼仪。在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艺术作品那种具有韵味的存在方式从未完全与它的礼仪功能分开,换言之,“原真”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根于神学。
因而本雅明说,“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他把艺术作品分为两种价值: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传统艺术属于前者,复制艺术属于后者。“膜拜价值要求人们隐匿艺术作品:有些神像只有庙宇中的高级神职人员才能接近,有些圣母像几乎全被遮盖着,中世纪大教堂中的有些雕像就无法为地上的观赏者所见。”随着时代与历史的进展,对艺术作品展示性的要求越来越大。“能够送来送去的半身像就比固定在庙宇中的神像具有更大的可展示性,绘画的可展示性就要比先于此的马赛克或湿壁画的可展示性来得大。
本雅明指出,“随着单个艺术活动从膜拜这个母腹中的解放,其新产品便增加了展示机会”。“艺术品通过对其展示价值的绝对推重便成了一种具有全新功能的创造物。”而电影达到了当时“最出色的途径”。
研究者说了什么,是重要的。如何说,也是重要的。本雅明关注新艺术现象的敏锐、他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进行历史思考的研究进路,在这里向我们显示了它特别的意义。
五
对中国的流行文化、对中国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也不能只作现实的理解,而应作历史的理解,应该看到当下流行文化从历史中走来的足迹。当我们试图去作这种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下流行文化对原有的政治权力关系、原有的价值观念都是一种巨大冲击。它曾经起过并仍在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比如波鞋对解放鞋的冲击、时装对蓝布中山装的冲击。把千姿百态的人生强制性大一统的政治权力关系遇到了强有力的瓦解力量。波鞋与时装在新时空里翩翩起舞,街面美了,生活美了,生命美了!
看不到这一历史过程,简单地套用某种理论,对中国流行文化进行整体的批判与否定,是有欠公允的。比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曾对流行文化中的“娱乐消遣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认为,“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他们说,“欢笑在娱乐工业中成了骗取幸福的工具”,娱乐活动是“进行公开的欺骗”。它的意义是“为社会进行辩护”,因为“观乐意味着满意”。因而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破坏了文艺作品的反叛性”。
这些分析是深刻的。但运用于中国,就要看历史语境了。它显然不适于对中国80年代前后的流行文化进行讨论。
人们无法忘记,在耳朵被语录歌磨出了老茧之后,某天早晨醒来,突然听到港台文化工业送来的邓丽君歌曲时的欣喜、听到李谷一不同于常人的演唱法时的兴奋。就在那样的早晨,你觉得传送歌曲的空气特别清新,手伸出被窝的感觉特别美妙。推开窗户,你发现天特别蓝、云分外白。那感觉是真实的,绝对没有一点“欺骗”。也正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娱乐、消遣,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发现!人们发现,人除了是政治的、阶级的人之外,还可以是个人的、自己的。人除了为革命工作拼命之外,还可以有娱乐、还可以有消遣。这也是人生的权利!中国人通过对娱乐、消遣的发现,发现了人生的真正含义和人生的丰富性。从政治的战车上松绑之后,人向自由的方向走去了。自由原来是这般美好。人,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向自觉的。对娱乐与消遣的发现与进行着娱乐与消遣的人生本身,就是一种批判与反叛!它不仅没有为社会辩护,而且本身就发泄着对极左时期政治权力关系的不满。它不仅没有逃避思想,而且本身就是思想。
正是这样的“发现”、“自觉”与“思想”,成为商品经济的文化基础,并适应了商品社会的运作。流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文化力量。
自然,中国社会进入商品经济之后,语境也发生了变化。但即使在今天,也不能对中国的流行文化的娱乐性进行全盘否定。因为中国的文化消费者是多层次的。娱乐性的文化产品不同程度地满足了某些层面人群文化消费的需要,甚至,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我曾到过珠三角地区的打工仔、打工妹居住区。那里街道的地摊上几乎全部都是娱乐性的读物。看到成百上千的少有文化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工厂里走出来,围在地摊前翻阅时兴高采烈的情形,你该说些什么?那些娱乐性的读物自然并不高雅,但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德里达,包括詹姆逊、萨义德,他们是读不懂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包括鲁迅,他们大概也不大读。你让他们读什么?他们也需要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当然,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要提高。但那“提高”在过程之中,而不在空话里。
六
然而,问题是复杂的。我们同时不能忽视在今天流行文化背后新的权力关系:金钱权力关系。人们从政治权力关系中挣脱出来获得的自由,又可能不由自主地丢失在金钱权力关系之中。表面看来,今天,有钱,你就在享乐的海洋里如鱼得水;没钱,你就在生活的艰难中寸步难行。但其实,有钱也未必真有自由。任何个人,在金钱权力关系中都是受制者。比如,人与广告。当中国大地初现广告时,你觉得广告给你提供了购物的指引,是一种方便。但现在,当你走在大街上一睁眼,就有几十条乃至上百条广告涌进你的眼帘时,当你开启信箱就有一迭花花绿绿的广告与报纸放在一起时,当你打开电视在频道上换来换去就只有广告时,“方便”便被“左右”所取代了。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有没有时间和心境,你不得不被动地阅读大量广告。而当你购买商品时,你会自觉不自觉地受着广告的指引。你选择的自由消失在广告的左右之中了。
而且,商品社会有强大的吸附力,能把一切不从属于金钱权力关系的东西吸归于其权力之下。网络写作最初是不为金钱只为发表的,但金钱却能使最优秀的网络写手投入金钱权力的怀中。目前,网而优则“纸”。优秀网络写手都以能出传统纸质书籍为荣,越优秀的网络写手所出的纸质书籍卖价越高。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的商品经济建设,实际上伴随着西方国家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张。因而,在今天中国的金钱权力关系中,实际上隐藏着中西权力关系。在流行文化的观念中,西方的东西就是好的。即使不是西方的东西,叫一个洋名儿,身价也就不同了。比如,汗衫不叫汗衫了,要叫“T恤”(T-shirt);出租车不叫出租车了,要叫“的士”(taxi);现在有谁穿“汗衫”吗?没有了,都穿T恤,后者比前者高雅。但是人们忘记了,T恤就是汗衫。只不过一是英文名儿、一是中文名儿罢了。我们在这里看出了西/中,好/坏,时髦/落伍等一组等级二元。二元中的一项对另一项具有着极大的优势和威权。
让我们来看一个广告。麦当劳有一则广告做得是极为精彩、成功的。一个婴儿坐在秋千式的摇篮中。摇篮在一扇窗户旁边。摇篮摆起,看到窗外的麦当劳标志"M",婴儿就甜甜地笑;摇篮摆下,看不到窗外的"M"了,婴儿就伤心地哭。很逗、很好玩儿,也很有诱惑力。
把这则广告作为文化隐喻来读是意味深长的。首先我们看到,它是那样的好,以至于婴儿一刻也不能离开它。第二,这个“好”是在窗外的,是窗外的世界。第三,那窗外的是什么?"M"。那是一扇门,一扇通往西方世界的门。第四,婴儿,祖国的未来,向往的,是那窗外的世界,是通往西方世界的门。
你还不得不承认,这则广告在多个层面上揭示了现实的真实。首先在浅层面,有哪一个孩子不喜欢麦当劳?在深层面,又有谁能否认,向往西方世界是目前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这也就是高档球鞋为什么要叫“波鞋”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一件东西只要叫一个英文名儿就身价百倍的原因。
金钱权力关系里隐藏着中西权力关系正是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金钱与西方在这里结成了友好联盟。在现阶段,它正推动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我们需要它。但它埋伏的陷阱却又是不能不令人警醒的。
七
对中国流行文化的历史理解需要我们同时看到其关涉到的两种权力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只看到一种权力关系是没有历史眼光、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看不到极左时期政治权力关系的存在,对中国流行文化进行简单的批准,会走进理论陷阱;只看到中国流行文化对极左时期政治权力关系的反叛而看不到其金钱权力关系,从而对其进行全盘肯定,同样是危险的。
更重要的是,从当前中国的现实看,两种权力关系仍然同时存在。中西权力关系、或者说金钱权力关系对政治权力关系形成过冲击,但并没有使之完全消失。而且两种权力关系正在联手运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权钱交易。它使我们的社会进入了十分复杂的状况之中。
我们怎么办?我们首先得发展商品经济,因而我们无法阻拦流行文化的潮流。同时,对新的金钱权力关系和权钱交易,必须作有力的解毒工作。或者说,我们一方面不得不借助流行文化的力量,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金钱等权力关系中争得一个空间。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但我们无法逃避,无法简单化。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需要复杂的思考。我们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