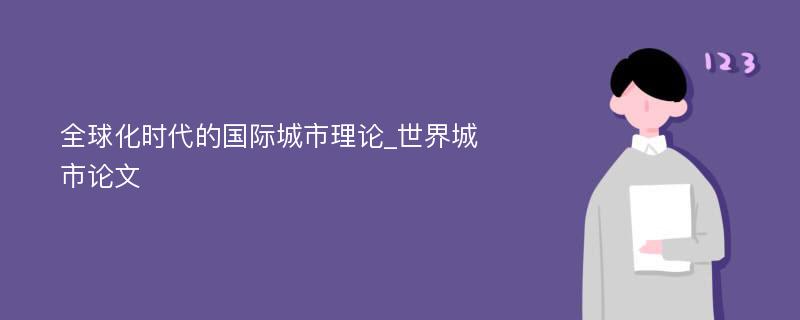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城市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时代论文,城市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史学科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范围广阔、研究方法灵活,因而,在其他相关的社会人文学科中出现的新思想、新理论会对它产生影响。近年来,在社会人文科学中讨论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是全球化问题了,全球化趋势是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现实。它既是一种发展趋势,也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角,或者说一种理论,它已经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其他许多学科中有所反映。毫无疑问,它也必然会影响到城市史学科。
1997年,美国波特兰大学的卡尔拉波特(Carlabbott)在美国《城市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际城市假说——美国近年城市史的一种研究方法》(注:Carlabbott,"The International City Hypo-thesis,An Approach to the Recent History of U.S.Cities",in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November 1997,p.31)。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的全球化趋势给不同规格的城市,特别是超级大城市和次一极的城市所带来的变化。他以美国为例进行了考察,认为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依附论的衰退以及世界多元化和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世界城市”理论应该让位于“国际城市”理论,他把这一新的理论作为一种假说提了出来。
概括的说,卡尔拉波特的理论认为现存的这种等级式的城市网络系统是与殖民体系以及依附理论相适应的。随着全球化的扩展趋势和后现代理论的出现,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与世界紧密相连的国家,可以按照城市在复杂的全球化系统中的独特功能,更多地考虑它们的横向联系、多元性,甚至等级关系上的跳跃等特点。他比较了世界城市模式理论与国际城市模式假说所强调的重点的不同,认为前者强调的是城市关系中的等级制和极为有限的几个城市对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决策权;后者强调的是在复杂的全球交换系统中,每个城市都可以发挥多重的作用和功能。这两种理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区分,在广义的社会科学领域提倡结构或提倡机构的区分中,世界城市模式基本是结构主义的,它强调用结构方法来分析世界的城市,认为世界级的城市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国际城市模式更多的是从机构方面来考虑问题,它相信人类行为和公共决策在新的时期会具有不同的结果,某些城市的跨国组织和世界性机构可以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关于“世界城市”理论
首先,卡尔拉波特追溯了“世界城市”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产生的过程。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当时,J.F.歌德(J.F.Goethe)把罗马和巴黎描述为世界城市(weltstadte)。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德国和英国的作者都用这个词来说明工业欧洲帝国的首都在国际上经济扩展的规模和程度。以伦敦为例,1862年,有人称它为“世界的中心”;19世纪80年代,有人称它为“世界的都市”;1841和1912年有人称它为“世界的城市”。到20世纪中期,美国人认为未来的世界城市不应该位处泰晤士河,而应该在圣路易斯附近。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了他特别消极的看法,认为世界城市是即将毁灭的世界文化堕落的中心。在英国,这一术语与集合城市的概念一起发展,城市规划师帕德里克·杰德斯(Patrick Geddes)在1915年用“集合城市”去说明城市化过程中地域范围日益扩大的城市,用世界城市去说明国家首都的统领作用(如巴黎、柏林)和商业、交通网络系统中的工业中心(如杜塞尔多夫、芝加哥)。1966年,地理学家彼得·豪(Peter Hall)在对杰德斯的网络体系进行研究以后,用范围的大小和强度两个概念来衡量城市的功能,认为世界城市基本上是欧洲单一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顶尖级的产物,日本和北美是它繁衍的后果。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球城市”、“世界级城市”这类术语很快的从学者的假说转变成人们的流行语,然而,最普遍的是杰德斯—豪的术语开始适应了世界经济的等级制模式,也就是适应了由都市从中心到外国实行强制控制的单一经济系统。约翰·福里德曼(John Friedman)致力于解释当代的全球资本积累体系和通过“世界城市”系统来清晰的说明这一理论。国际银行和多国公司总部的集中以及支撑这些机构的专家的集中是世界城市的主要特点。关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方式和位置、通过阶梯状组织机构和交通网络进行传送的方式,这些事务都在小一点的二等城市决策。世界城市的作用类似于向全球辐 射出一种电能的传导,电力传播的能力越大,世界城市集中控制的功能和权力也就越大。
世界城市模式认为外围城市只有有限的自由意志,它们的作用由统领它们的世界城市的政治、经济权力所规定,由国际金融结构和多国公司来行使。二等城市只能就它们在等级制网络中的功能进行解释。为此,有人把这个体系分为世界城市、地区—国际城市和地区—国家城市,有人称为全球中心、区域中心和地区中心;总之,在这一系统中,外围和附属城市没有什么独立处理事务的机会。世界城市理论致力于一种全球化的中心地点理论,全球城市,例如纽约,位于城市阶梯的顶端,它们分享所有次级城市的功能和活动,同时,它还容纳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殊活动。如,伦敦的银行家和纽约的艺术商人所提供的服务极为特殊,他们需要以整个世界为市场。
在概念上,世界城市模式也与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理论相联系。依附理论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的工业中心作为世界一类城市,如伦敦、东京、巴黎和纽约等所制定的秩序的接受者。安东尼·金(Anthony King)认为,殖民地城市为现行的根据西方价值观念、资本主义的商业组织和工业化的生产系统所进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作建立了空间,因此,世界城市的理论又为实行等级制的控制证实和描述了一种机制和途径,而这种等级制的控制是通过城市发展为世界范围的商业模式来实现的。(注:Anthony D.King,Urbanism Colonialism,and the World-Economy:Cultural and Special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Urban System,London 1990.)
从卡尔拉波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世界城市理论,实际上就是自近代以来欧洲以及后来延伸到北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建立的等级制的城市网络系统。这一系统,一方面是过去几个世纪历史发展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在城市史学领域被广为认可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按照经济、金融、交通、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及城市的功能,全世界的城市网络可以分为四级:最低一级是地方城市及其腹地,也就是小城市及其周围的城镇和乡村;第二级是地区,可能是一个省,也可能包括几个省,在地区这样一个范围内,有一个大城市,一方面它与上面国家范围内的更大的都市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支配着下属的小城市,吸收着它们的资源,并管理和为这一地区服务;第三级是国家范围内的城市网络,一般以首都或国家最主要的商业城市为中心,上面与世界级的都市发生联系,下面与地区级的城市发生联系;最上面一级是世界级的都市,一般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和东京等。这一理论是一个大致的框架,每个国家并不一定都具有三级网络,按幅员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可能是三级,也可能是两级。此外,有的国家与世界都市有联系,有的则没有。总之,自近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阶梯状的等级制城市网络。(注:这方面的理论可参考加拿大史学家凯尔莱斯的著作 J.M.S.Careless,Frontierism,Metropolitanism,and Canadian History,i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Vol.35.1954;Metropolis and Region:the Interplay between City and Region in Canada History before 1914.in Urban Histo-ry Review Apr.1979.No.3)
二、关于“国际城市”理论
从世界城市理论向国际城市理论的转换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所发生的变化引起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在地域上的重建在有关城市理论方面也有所反映。一些学者强调世界城市发生的新变化,他们试图去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多元性与早期统一的跨大西洋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不同。在所有的变化中,最明显的是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崛起。首先是东亚城市,特别是东京,它已经作为与伦敦、纽约相匹敌的具有竞争性的经济决策的中心而出现;其次是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在那里也集中了许多世界城市才具有的新利益。在欧洲,高速公路和铁路的改进更加强了欧盟的联合,使一些欧洲城市在欧洲范围或世界上发挥作用。欧洲、北美大陆之间的竞争对原来某些城市的稳固地位也提出挑战,新兴工业的出现为一些城市新的专门化功能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为一些城市的崛起创造了机会。总之,从广义上说,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已经引起国际新的劳动分工。在这种新分工下面,跨国公司把生产的功能从欧洲和北美东部这些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地区转移出来,却把跨国公司的总部留在了这里,使这些地区已发展起来的许多城市专门从事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或者是信息交换技术等新兴工业。这样做的结果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其特征是生产的扩展造成了全球的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控制权却掌握在为数极少的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几个关键城市手中。
卡尔拉皮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面,世界城市网络的理论为一种新的理论所代替,这就是国际城市理论模式。这一理论是一种宏观理论,是在世界市场的运作中对城市作用及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即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在更复杂的商业和信息活动中对更具有专门功能的城市系统进行考察。国际城市理论注重研究城市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它强调国际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交叉关系和相互影响。此外,它不仅只关心少数几个超大城市,而且关注那些以前不曾受到世界资本涉及的中等城市。
其实,对于这样一种图景,美国人文生态学的社会学家早有预见。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家罗德里克·麦肯齐(Roderick McKenzie)就最先勾画了国际城市的图景。那时,他思考了日本和东方经济的兴起,指出新的城市“重心”将会出现,也会有新的交流“路线”,他预料到跨国和跨地区疆界的多边交换将变得越来越复杂。他还预料到由于现代交通手段的进步将赋予个别城市或城市链以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专门功能,也就是说,他已经预见到城市在信息时代的专门功能。他认为,到那时候,城市间的空白将会消失。(注:Roderick D.Mckenzie,"The Conc-ept of Dominance and World-Organiz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July 1927.Cited from Carlabbott,op.cit.p35.)
卡尔拉波特从不同方面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区别。首先,注意不同城市的不同功能是国际城市理论模式的一个特点。世界城市模式注重于城市网络的等级制,即上级城市对下属城市的控制行为,注重于某一级城市在它所处于的网络级别中的作用,如在地方、地区、国家或世界,一般来说,下级城市不会越级发挥作用。国际城市模式却注重于城市的开放程度,国际城市在本质上是对世界市场开放的,是外向型的,它不必严格遵守过去等级制城市网络的次序。此外,等级制的城市网络不是完全建立在真正交换的基础上,有一种强制性的功能。国际城市理论却注重交换城市双方的平等和互惠。在全球化时代,可进行交换的种类大大增加,有实在的商品(包括个人消费品),也有移民、旅游者、商业信息、正规教育等。国际城市模式承认像纽约这样的国际城市在国际金融、商业和移民等项事务中的统领作用,也就是它们在世界阶梯状城市网络中处于顶级位置,但与此同时,它还承认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它希望不同的城市,也能像日内瓦、布鲁塞尔或迈阿密那样,在国际经济中发展独特的功能和具有独特的地位。由于在功能和地位上的要求不同,在数量上,国际城市可以比为数极少的几个世界城市要多得多。
其次,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创造经济上的奇迹,因而,国际城市理论承认在一些专门的功能上,一些新崛起的城市可以超越城市网络的原有等级次序,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现代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和金融、商业、经济机构在世界范围的重组,使世界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城市的国际作用也大大加强。世界上许多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现代技术的进步和机构的重组可以使金融和商业产生瞬息万变的效果。由于大量信息的瞬息传播,已经改变了世界城市之间原有的竞争先后顺序,在金融和教育等方面,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国际城市理论在承认世界城市理论的同时,也承认城市次序的多元的、经常性的变化。
城市地位的变化是由于城市所获得的专门功能决定的。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功能越来越趋向于专门化,这是进行交流的基础;而交通革命和旅游无疑大大促进了交流的速度。卡尔拉波特认为,按照经济的专门化功能,20世纪后期美国的国际城市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际型生产城市;二是国际型通路城市;三是国际型交易事务城市。
国际生产型城市直接为世界市场服务,致力于出口成品的商品、生产的专门化或拥有大国际企业的分厂。19世纪的曼彻斯特和20世纪的底特律是这类城市的典型。由于世界贸易对于美国越来越重要,也由于经美国有大量的转口贸易,自6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的国际作用大大增强,国际管理的职能和大量的信息活动直接支持着这些生产类型的城市。国际通路城市是指历史上欧洲人进行海外定居的地区和殖民地的一些城市,如美国历史上一些商业城市和19世纪欧洲扩张时一些殖民地城市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城市的作用既是文化渗透,也是商业渗透。在美国历史上,这些城市联系着东北的工业中心,也连接着南部和西部的资源。在20世纪后期,除了历史上的交换移民和商品的作用以外,又增加了新的交换内容。国际交易事务型城市,用吉恩·哥特曼(Jean Gottmann)的术语是指向跨国市场提供专业技术、金融服务和个人服务的城市。这些城市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化最大的地方,吸引了城市研究者和改革家的最大注意力,并在新的世界城市系统中位置最重要。交易事务型城市在经济信息、政治、组织信息,或文化信息方面实现专门化。(注:Gottm-an,Coming of the Transactional City;Matthew P.Drennan,in"Gate-way Cities:The Metropolitian Sources of U.S.Producer Service Exports,"Urban Studies 29,April 1992,Cited from Carlabott,op.cit.p.39.)
为了对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进行衡量,卡尔拉波特指定了衡量这三类城市的一系列标准,其中包括衡量这些城市进行国际联系的标准、衡量为首的国际城市的标准等。他列表把美国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迈阿密、芝加哥、洛杉矶、休斯顿、新奥尔良、旧金山及亚特兰大等城市在许多方面的指标进行了比较,如外国出生的人口、外国银行数量、外国旅游者、新移民数量、进口物资的价值、具有外国领事馆的数量以及与国外建立姊妹城市关系的数量等。经过比较,纽约的确在许多方面名列前茅,当之无愧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城市;华盛顿由于是首都,在获得国际信息方面独立鳌头;在60-80年代,美国西部和南部城市的国际作用大为加强,其他地方的城市却相对发展缓慢。作者认为,到80年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多少具有国际作用,每一地区都有自己专门化的功能和通往国际的通路。
三、“国际城市”理论研究的意义
以上,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世界城市”理论,什么是“国际城市”理论,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区别。那么,为什么会有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呢?
从历史背景上来说,国际城市理论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当前时代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两种理论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第二个问题是当前的时代与以前的时代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从根本上说,世界城市理论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与殖民主义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首先是从欧洲开始发展的,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横跨大西洋和深入亚洲、非洲的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来说,毫无疑问,在20世纪以前,欧洲是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独一无二的中心,而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洲在内,不过都是这一中心的外围或边缘地区。如果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看成一个不断向外扩展的同心圆的话,那么,这个同心圆所包括的城市就处于这一多层次圆环的不同层次上,就处于以欧洲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世界城市网络的不同“节”和“点”上。而圆心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处于等级制的世界城市网络金字塔顶尖的伦敦。
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人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是看它崛起,看它称霸世界的世纪”。这一说法虽然过于绝对,但不是全无道理。总之,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现实,如果说在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只有一个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就向北美扩展和转移了,虽然欧洲还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现代科技的最新成就通常首先是在美国出现。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位于世界等级制城市网络金字塔顶端的城市也就变成了两个,作为北美第一现代都市,纽约成了与伦敦相抗衡的另一个世界中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崛起,日本、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了继欧洲和北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尽管在中国和印度等地农业人口仍占多数,但是,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大大超出了世界发展的平均速度。这一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发展,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殖民主义政治体制的瓦解,也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利用跨国公司,把一部分工业生产从资本主义原有的心脏地区转移到这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作为世界上第三个经济发展热点地区的中心,东京成了与伦敦、纽约相匹敌的世界城市。1991年,萨斯齐亚·萨森(Saskia Sassen)出版了《全球城市》一书,对世界城市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伦敦、纽约和东京是世界经济三足鼎立的首都,三者各执一个地区,是对全球经济进行管理和服务的金融中心。(注:Saskia Sassen,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这种情况表明,世界城市理论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着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现实。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毕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变化是多方面的。首先,市场经济的世界体系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地区扩展了。这种扩展给世界等级制城市网络带来的变化是一个顶尖级世界城市变成了三个,于是,其下属的代表世界——国家——地区——地方四级城市的金字塔状网络也就从一个单一的体系变成了三个等级制的网状体系,一元制变成了多元制。这是全球化经济发展给世界城市格局所带来的第一个重要变化。
其次,在亚洲,殖民主义政治体制的瓦解对世界经济的改变是巨大的。在殖民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商品的交换是不平等的,欧洲对亚洲实行超经济的掠夺。因此,欧洲的世界级城市对亚洲的国家及地区级城市实行的也是不平等的政治统治,没有市场经济的规则可言。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之后,亚洲各国人民推翻了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各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不必非受西方强国的摆布。而且,尽管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还存在着种种表面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如对亚洲地区原材料的掠夺;利用亚洲廉价的劳动力;跨国公司把金融、管理和高科技部分留在西方,把工业生产转移到亚洲,这样,既可以获得利润的主要部分,又可以使西方本土不受污染,等等),但是,以往那种超经济的掠夺毕竟消失了,亚洲与西方的贸易实行了商品交换。此外,各种各样国际商贸组织的出现,使亚洲国家可以利用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不断争取各方面的平等权利。总之,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建立。在这样的形势下,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国际交往的扩大,原有世界城市网络的等级制统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与等级制并存的权力因素也随之大大消弱或消失。下级的城市不必只能与它的上级城市或它的下级城市发生单向联系,而是可以在同级之间、跨地区之间实行横向的和多向交往,城市关系中出现了更多的灵活性。这是国际城市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然而,国际城市理论的现实意义主要不在于实际应用,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样,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理论方面。它对现在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城市理论进行了批判,从而,也就是对现存的等级制式的城市关系进行了批判。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也不能进行根本的改变。但是,它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上,从人类更长久的利益出发,对现代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因而使人们耳目一新。在批判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为人们指出了一些未来的方向,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环保主义。而这些措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所实施。
国际城市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样,它的积极意义主要也在理论方面,它启发人们去思考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原有的世界城市格局是否已经改变?与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时产生的世界城市等级秩序是否依然合理?是否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当代世界城市的格局?如果说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去描述当前的态势?世界城市格局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的图景?我们从卡尔拉波特关于国际城市的理论中可以受到上述启发。
总之,国际城市理论的提出,不仅可以使我们改换一种视角来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给世界城市格局所带来的变化,从而推动我们的城市史研究;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根据国际城市理论中的一些新观念,如,怎样使城市的发展与国际相联系?怎样利用当前世界城市格局的这种多元性、横向和多向联系的灵活性积极的开展多元的国际交往?等等。
这是当前国外城市史研究中的新视角。
标签:世界城市论文; 纽约论文; 全球化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欧洲城市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