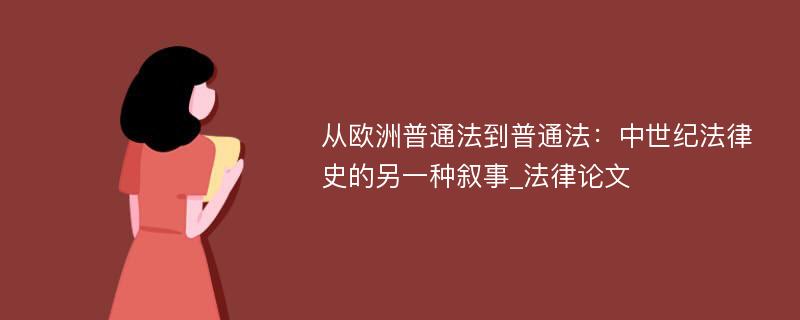
从欧洲普通法到共同法——中世纪法律史的另一种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通法论文,欧洲论文,中世纪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欧洲中世纪的法律发展中,一个难题始终困扰着法律史研究者:为什么会在11、12世纪左右英国和欧洲大陆在法律发展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经久不决的难题吸引了无数法律人的目光,对之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但是几乎所有的回答无不受限于“英国的独特性”这一基本的论域,无论是赞成者抑或是反对者,都是围绕着英国的独特性问题而展开的。这一研究的路径的基本缺陷在于,其往往套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法律思维方式,将不列颠岛与欧洲大陆割裂开来,认为两者都有意无意地偏离对方,进而导致了近代意义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分野。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回溯性的历史观,从而使得对于中世纪欧洲法律史学的考察陷入到民族国家的法律范式之中,错失了欧洲中世纪法律的世界性特质,造成了诸多误解。虽然有论者意识到英国普通法的真正起源在于欧陆的封建法,但是对于这种欧陆的封建法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于11世纪以前的欧洲大陆,却语焉不详,从而错失了对这一问题的准确定位与回答。①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法律思维定式在欧洲法律史的研究中常常造成这样一种危害,即将英国与欧陆割裂开来研究,最终将欧洲法律史分割为国别法律史,丧失了对于欧洲法律史的整体把握。 摆脱民族国家的法律思维范式,以世界主义的思维去考察欧洲中世纪法律史的演化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有研究的困局,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欧洲中世纪的法律史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加以考察:一是4世纪到11世纪的欧洲普通法(European Common Law)的发展历程,正是这一历程构成了英国普通法发展的欧陆版本;二是11世纪之后欧洲普通法逐渐在欧陆为共同法(Ius Commune)所取代,但却在英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保留下来的历史演化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基督教所力图建构与维系的神圣的基督帝国(Christendom)观念对于法的世界主义属性的理解提供了基础。从基督教帝国的视角看,欧洲法律史的统一并非基于现实的政治权威,而是基于一种信仰权威。罗马法中的“首席公民”的普遍支配在“基督帝国”中被置换为“上帝”的普遍支配。与“首席公民”的普遍支配不同,“上帝”的普遍支配缺少政治支配的意涵,而仅仅体现为文化的、宗教的以及社会秩序的支配。②在基督教帝国的框架下,我们力图凸显欧洲法律史的发展之动力因素除了通常所谓的社会政治结构外,更多地展现为主教与法学家们的个体化努力,从而呈现出欧洲法律史发展的另一种叙事模式。 二、欧洲普通法叙事的基本要素 为什么将4世纪至11世纪基督帝国中的法律形态称作欧洲普通法?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我们对于普通法这一法律形态生成之方式及其对于政治秩序之构建的理解。从法律史的视角来看,我们通常所谓普通法通常指的是起源于英国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形态,这一特殊的法律形态依赖于英国特定的政治结构。依据约翰·道森对英国普通法形成过程的研究,普通法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国王利用法律人群体逐渐获得政治上的统一的过程,也即,普通法大体上是在碎片化的政治现实中努力寻求统一性的法律形态。在其中,法官和高级律师成为国王对抗地方政治精英的重要依靠。③与此同时,由于普通法的生成方式不是基于对于普遍的法律规则或学说的阐释和适用之上,而是基于针对特定类型的案件事实所给出的法律裁决之上,所以,这种法律裁决所依据的基本观念不是法的观念,而是正义,因此,这就要求共同体必须共享一种正义的理念。就此而言,所谓欧洲普通法,不过是主教们的“判例法”。要对这一“判例法”进行历史叙述,必须从判例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背景、规则形成方式与司法制度影响三个层面进行。而在这三个层面上可分别呈现为:政治权力的不充分性、主教的布道即是立法以及司法集会制度等特征。 (一)政治权力的不充分性 日耳曼人对于西罗马帝国的入侵终结了罗马帝国基于普遍统治权所形成的普世性的政治秩序。到了5世纪的晚期,诸多日耳曼王国在西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建立起来,填补了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所留下的政治权力真空,整个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向。这是因为在日耳曼人的政治传统中,并没有如同罗马人的那种将国家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并将其限定在特定领域内的政治意识,其政治结构乃是由经由国王或领主的个人人格魅力所形成的对于特定人群的统治。日耳曼人的政治秩序所关注之中心根本不在领土之扩张,而在人口之迁移。在迁移的过程中,日耳曼法必须随着迁移的地域和所迁移之地的不同风俗而发生变化,从而具有相当强的任意性和开放性。 就政治秩序的构建与维系来说,日耳曼法的这种任意性和开放性并不构成其缺陷,而恰恰能够展示出其对于政治秩序构建的世界性的意象。这种世界性意象的表征就在于日耳曼人透过不断地扩张和迁移将其民族的政治秩序的想象扩展到欧洲的各个角落。并且,在迁移的过程中,日耳曼人第一次系统地展现出来一种体现法的世界性的“好客”原则。在日耳曼人的语境中,所谓“好客”就是在特定的土地上短暂地停留。但随着日耳曼人在整个西罗马帝国的扩张,这种“好客”的原则逐渐发展处新的意涵,即透过好客的原则,可以实现民族的融合、战争的消弭和土地的获得,进而使得日耳曼人与罗马人能够在欧洲普通法的语境中成功地融合。④ 在碎片化的政治秩序中,政治权力所具有的根本性特征就是其不充分性。所谓政治权力的不充分性,乃是指日耳曼的诸国王缺乏对于社会行动进行整体性控制与调节的能力与意愿。所以,整个中世纪早期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氛围乃是各种不同的权力相互竞争的状态,这恰恰为主教权力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提供了契机。罗马教会的组织化权威系统逐渐在与日耳诸王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主教们在人际间的纠纷解决上取得了管辖权。⑤ (二)主教的布道即是立法 作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是帝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社会团体。在帝国晚期,基督教的教堂已经成为诉讼的公共场所,主教们获得了“处置私人纠纷的权力”,在优士丁尼对此一术语的描述中,主教们依据这一权力甚至可以采取反对行省总督的行动,以保证公正在帝国的范围内得以实现。⑥相对于罗马皇帝的普遍统治权而言,主教的“处置私人纠纷的权力”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同于普遍统治权的“公共支配”特性的“私人支配”。这种新型私人支配使得帝国晚期的社会不再是普遍统治权之下的一个整体,而是各个不同“私人支配”之下的地方性的法律秩序。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中世纪碎片化的政治秩序中,主教们的“私人支配”在整个社会政治的治理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主教们的“私人支配”使得其权力运作呈现个别化的特质,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中世纪早期,教会在地方层面是一个立法机构,其所订定之法律很快就透过国王的敕令被安置在王国的法体系中;二是主教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密,这样一来,有关神学和法律的问题最终都受教宗的统辖;三是主教们的司法活动遍及地方法律的各个面向,并为人们广泛地接受。主教们透过自己地方性的司法活动不断地影响着各个王国中的法律秩序,但主教们的司法活动又受制于教宗的最高管辖权。所以,主教的司法活动成为罗马教廷与各个地方的王国的法秩序的纽带,因而构成了早期中世纪的欧洲普通法的最为重要的基础。⑦这与英国普通法的形成过程几乎如出一辙。 基于此,教会起码在两个层面实现了碎片化的政治秩序在宗教层面的统一:第一,是教会本身在不同的王国法秩序中本身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加以立法,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地参与到地方事务的司法实践中;第二,是教会透过罗马法在日耳曼王国中的本土化,也即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罗马法的粗鄙化,几乎使得所有王国中的臣民都受其规制。⑧而这种粗鄙的罗马法恰恰是这一时期的法律体系所偏离的原点,其所要达到的终点恰恰是欧洲普通法。⑨在对粗鄙的罗马法的偏离过程中,教会发展出了切合于其治下所有人的共同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欧洲普通法的宗教面向。从而也使得教会的普世性观念有着区别于罗马的独特性:罗马帝国的普世性观念是基于普遍统治权的普世性,其从来没有要求治下的居民去遵守统一的规则,而只是要求其治下的臣民必须认可罗马人的普遍统治权,至于他们自身的生活,则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参考适用何种规则。与此同时,透过万民法的适用,罗马人又将自己有关法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渗透进各个地方的法律观念和规则体系之中;但教会的普世性所要求的是一种被认可并接受的普世性,这种普世性观念的传播依赖于效仿与自愿顺从这两个基本要素:当教会详细解说宗教行为的认知对象时,其同时也是在宣布法律行为的规则。这种解说本身就是在粗鄙的罗马法的任意性上施加一种统一性,而无需正式地创造新的规则或用一套外来的原则重新组合既存的规则。⑩ 由此可以看出,教会不是作为一个立法者去创造新的统一性的法律规则,也非单纯地作为真理的宣谕者去阐述一种指引人们如何统一理解现有法律规则的新原则或新理论,而只是以践行者的身份去实施传教行为,藉由这一传教行为的权威性与普遍性去整合碎片化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由于这种权威性和普遍性是在传教者与信教者在具体的传教行为中所形成的,因此,在早期由欧洲普通法所维系的政治秩序的类型所强调的是主教或教士与信教者之间的联结的个体性。这就意味着,基督帝国的世界性特质必须深入到每一个个体之中。现存的粗鄙的罗马法的任意性之所以能够被消除,不是因为一种理性的统一的规则或学说使之合理化,而仅仅是在于主教或教士本身的对于上帝律令的宣谕,也即最终依赖于主教或教士自身的意志,依赖于他所宣谕的法律。正是在这个环节中,早期基督教透过其具体的传教实践否定了罗马万民法中的另一个普世性的要素:理性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统一性和权威性的根基不在于理性本身,而在于信仰,更确切地说,是在于对罗马教会的信仰。上帝的意志透过教宗和主教型塑了此种统一性。由此观之,欧洲普通法不过是神圣化的英国普通法,或者更确切地说,英国普通法不过是世俗化了欧洲普通法。 (三)司法集会制度 在中世纪早期,日耳曼统治者之政治决断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作出:通常是国王与一直在其周围的大臣们来作出,偶尔则是由人民全体以集会的形式作出。(11)但不管是以何种方式,日耳曼政治统治的结构中存在着一个沟通的渠道,即透过人民的政治集会,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性诉求能够获得其表达的机制。但是最能体现日耳曼人的法观念对于欧洲普通法形成之贡献的,当属日耳曼人在一个社会碎片化日益严重,人口迁移非常频繁的时代为将不同类型的人民——最为典型的就是罗马人和非罗马人——整合进同一个政治秩序中所采取的一种司法审判的类型——司法集会制度。这与国王作为法官,从而为王国内部带来和平与正义的观念不同。 在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之后,其目标不仅仅在于维系对于本民族的人的统治,而更在于维系对于其所征服的地域内的罗马化的人民的统治。这样一来,日耳曼人就必须放弃原先政治性的集会制度,而采取一种司法集会的制度来实现其整合的目标。透过司法集会所设定的口头的程序形式,新的人民或民族能够顺利地进人日耳曼人的政治结构之中。而国王作为法官的观念则更多地着眼于在王国内部形成一个有效的阶层化的统治,其对于人口和民族之间的融合并不给予太多的关注。(12)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集会取代了政治集会成为日耳曼人进行政治治理的主要方式。原因即在于,政治性集会的基础在于由武器武装起来的自由人的观念在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之后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忆了,日耳曼人所面对的乃是一个高度阶层化的后帝国时代的罗马社会。(13) 这种司法集会由国王或领主主持,早期是要求所有的自由民都参加,但是后来只要求特定的自由民参加,进而作出裁决。必须指出,中世纪早期这种以司法集会的方式来作出裁决的主要目标在于使得日耳曼人的政治秩序能够为西罗马帝国疆域内的罗马化的人民所接受,因此其在司法集会中所追求的不是现代人意识中的那种司法的功能。更多地,司法集会所扮演的角色在于透过特定的正当程序来确认当事人的权利。(14)这样一来,日耳曼法的生成方式就不再是一种对于普遍规则或原理的宣谕,而是更多地基于裁决来保护权利或是对既有权利的确认。其基本目标即在于维系罗马人和非罗马人在日耳曼的政治秩序体系中能够和平地共处。所以,其也不可能具有一种对于政治秩序的统一性的理性诉求。日耳曼法所展现出来的凌乱与任意不能单从法体系自身的逻辑性和整全性的要求来审视,进而将其贬斥为庸俗、粗鄙、落后的法律。我们必须从当时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具体理解日耳曼法在欧洲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是透过这种凌乱与任意,不同类型的人们才能够在当时的碎片化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获得整合。透过日耳曼法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欧洲普通法的观念的所展现出的另一种世界主义的面向:即透过不断地流动、迁移来实现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融合,进而为一种新的具备世界特质的法观念的成型提供准备。 三、共同法叙事中的理性问题 欧洲普通法的形成有赖于主教们个体意志行为的宣示,经由这一宣示,欧洲普通法中的诸规则现实地发生效力。这种将个别化的、碎片化的规则之效力寄托于意志行为之上的理念无法形成一种体系化的法律思维。主教们的意志行为受制于奥古斯丁式的意志观。对于奥古斯丁式的意志观来说,法律不向心灵或理智敞开,而只是有在“意志”的层面才展现自身:心智本身不会主动的运动,只能被动地呈现一种僵化的统一性,但意志则不同,其能够透过个别化的运动方式去容纳诸多相互矛盾的异质性要素。因此,不同类型的人民所构建的地方性的法律有着根本的差异,乃在于他们所具有的个体或集体的意志之故。即便是在基督教所构建的解释地方性的法律的共享原则那里,也体现了一种统一性的意志行为。正是在这种统一性的意志的驱动下,欧洲普通法的成立与生效才有可能。(15)但是,这种基于个体意志行为的欧洲普通法在11世纪之后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最终被理性的、体系化的共同法所取代。 因此,从欧洲普通法到共同法发展的历程不过是理性的统一性取代基于传教行为的意志的统一性的历程。那么,理性对意志的取代这一欧洲法律史中的叙事模型受到哪些基本要素的影响呢?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政治的现实与想象促成了理性权威的树立;二是罗马法学家和教会法学家自身的职业劳作使得他们能够成为适格的理性主体,从而具备智识的权威;三是法律层面的理性受制于宗教与哲学层面的理性观的发展,也即亚里士多德式的基督教哲学是共同法理性面向的最为坚实的观念基础。 (一)政治想象的变迁促成了理性统一性权威的确立 11世纪以后,维系欧洲普通法的旧有的社会和政治想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贵族和教士阶层所赖以维系他们之支配的两种理念:战争的技艺和智识的优越——都被原本处于下位阶的劳动理念所吸收:劳动不仅意味着体力劳动,更包含智识的讲授与传播行为、职业性的活动以及商人的活动。(16)这种劳动观念的转化成为了新的社会和政治想象的引导性理念。与此同时,透过欧洲普通法所达成的不同类型的人民之间的融合使得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愈为频繁。在这种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下,原本相互隔绝的、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愈为紧密。经济交往的增多、城市文明的兴起都吁求一种中心化的、有确定边界的政治权威来调整并规制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教会也力图对这种新的需求作出回应,因此其脱离了早期个别化的传教行为所形成的支配形态,而要求在普遍且公共的面向上拥有统治权。但却都受到越来越深入的封建化进程的阻碍。伴随着封建化进程的,是教权与王权之间持续的争执。(17)因此,政治权力的不充分性依然存在于11世纪之后的欧洲政治与社会结构中,但是其再也不可能如同11世纪之前那样发挥着积极的功能,而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和难题。 这种挑战和难题分为两个面向:一是旧有的基于教士传教这一具体行为的权威性的欧洲普通法无法应对新形势;二是11世纪的欧洲根本无法发展出一个充分的政治权威去主张罗马意义上的普遍统治权。中世纪欧洲人的处理方式比较特别,其将整个基督教帝国内的共同体想象成最终的权威来源,用中世纪的术语来说,最终的权威在于universitas。universitas有着双重意涵:Macrocosm与Microcosm。从其最广阔的意义来说,universitas意味着上帝之城,包含了天国与尘世,进而其能够包容整个的神圣秩序,这个universitas是一个Macrocosm。与此同时,人类的共同体,包括作为个体的人,都是这个macrocosm的镜像与摹本,是一个Microcosm,这两者统一于universitas。这种统一非常完美地阐释了基督教帝国中一与多的关系,基督教帝国“从整体开始,但却赋予整体的部分乃至于个体以内在的价值。”在这个秩序中,“每一个存在整体中都有其位置,并且存在之间的每一个联系都对应着一个神圣的命令”。(18)由此,所有作为部分的universitas都起源于一个作为整体的universitas,并且都复归于这个整体的universitas。 按照欧洲中世纪的法律理论,此处的universitas是一个虚拟的“人”:“从法律上讲,一个universitas是被构想为不同于其个别成员的具备法律人格的团体。……universitas不会消亡,即使其组成成员发生了变化,其仍然是与先前相同的法律实体。”(19)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秩序的整合就不能基于个体而展开,而必须基于代表这个法律人格的教宗、皇帝或国王而展开。这就在理论上出现了一个难题,即作为自然人的教宗、皇帝和国王与作为universitas首脑的教宗、皇帝和国王之间的区分。前者是教宗、皇帝或国王自然的身体,而后者则代表了整个universitas的有机体,是一种政治的身体。基督教帝国秩序的精神面、物质面和制度面的整合不仅有赖于作为自然人的教宗、皇帝或国王的能力,更依赖于那个不受自然身体之生死所限制的永恒的政治的身体。于精神秩序层面,则形成了教会的神秘身体(corpus ecclesiae mysticum)的概念,于世俗秩序层面,则形成了共和国的神秘身体(corpus reipublicae mysticum)的概念。(20)这两者最终在神圣秩序中统一于基督的神秘身体的概念。基督的神秘身体是一个有机体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所有人都从属于这个神秘的身体,基督是这个有机体的“头”。因为,如果universitas是一个有机体,那么这两个神秘的身体就应该如同自然的身体一样,只可能拥有一个“头”。皇帝不可能是另一个“头”,否则这个有机体就成了一个“双头怪”。(21)这个“双头怪”无法保证有机体的正常运转,从而也就无法保证这个秩序的和谐,因而也就不能提供统一性。正如库萨的尼古拉所言:“我们可以说基督是道,是真理,是永生,是所有受造物的头。如同丈夫是妻子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而这是由所有受造物的和谐一致所构成的,在基督自身为一,而在受造物中间则于不同的阶层级和阶段上展现为多。”(22) 而对于universitas的这种权威性和统一性之论证却是教会法学家与罗马法学家合力的结果。他们借助于对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体系化阐释为这个univerisitas寻得了正当性说明。所以,universitas在没有充分政治权威保障的前提下,逐渐转向统一的理性权威与智识权威,这就是11世纪之后共同法得以产生和演化的政治与社会背景。 (二)法学家的职业劳作使其成为是理性统一性的适格主体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教会法学家与罗马法学家在智识的层面发展出了一套理性的法律体系来证成这种最高且普遍的权威,也即上文所言的universitas。两者都诉诸各自的权威传统:教会的正典和罗马法中的《学说汇纂》。(23)11世纪以后,在宗教和世俗层面发展出了两套对于西欧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罗马式的世俗共同法与教会共同法。为了叙述的方便,学者们将其统称为“共同法”。这个共同法的生成过程就是一个新的统一的智识权威形成的过程,透过这一理性上的智识权威,欧洲能够在新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在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权威的情况下,维系其自身在法律上的统一。欧洲普通法所依据的那种抽象的正义的观念最终转向了共同法所依据的抽象的概念和规则之权威性。透过共同法的生成,法的世界性特质从一个“矫正”的时代转向了一个“权威”之生成的时代。(24) 经由教会法学家与罗马法学家共同的理性化作业,共同法最终以普遍化的规则形态呈现于《民法大全》与《教会法大全》。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共同法形成的历史现实,而在于在缺乏统一政治权威的框架下,世俗的罗马法与教会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如何?以及两者所构成的共同法与封建化的政治结构下各个地方的“自生法(ius proprium)”呈现出何种体系架构? 首先,就共同法内部的关系而言,罗马法和教会法同时作为共同法构成了一种互补并竞争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基督教帝国的utrumque ius(二元的、二者择一的法)。互补关系意味着,透过utrumqueius,整个基督教帝国的都处于共同法的观念的影响之下。这样一来,整个基督教帝国秩序所体现出来的统一性和世界性就能够在法律的层面得到保障,utrumque ius的世界性特质也能够得到彰显。但问题在于其中的竞争性关系,就其实际运作上来看,罗马法所处理的是人们世俗生活,其要实现的是人们在帝国权威之下的自由和自主这一共同的善,而教会法处理的是精神生活,其要防止的是人们被罪恶引诱,并保障他们最终得到灵魂的拯救。(25)表面上来看,二者并行而不悖,但事实上,教会法所处理的精神生活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教宗可以以罪的理由介入所有事务”,“教会可以以罪的理由获得所有的管辖权”。这种渗透性帮助教会法侵入了本由罗马法所规制的诸多领域。(26)因此,两者相互竞争的关系上,教会法相对于市民法一直占据着优先的地位。 其次,就共同法和自生法的关系而言,重要的问题在于阐明自生法的概念并讨论中世纪日常的法律实践是如何看待共同法这一观念的。所谓自生法,乃是与共同法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欧洲各个地方各不相同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7)于此,“自生”即意味着属于自己的,并且具有与他者不相容的异质性。所以共同法与自生法的这种对立所展现出的是基督教帝国秩序中的统一性与多元性对立。 按照传统的看法,在中世纪的法律实践中,法院在解决案件时首先适用的是自生法,而非共同法。只有在自生法无法解决案件时,才转向共同法。所以,共同法是作为一种补充性法律而存在的,在中世纪的法体系中仅占据次要的地位,因而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28)这其实是与中世纪的封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世纪的政治结构中,公共支配与私人支配相比,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在各种封建式的私人支配盛行的时代,诸多地方性的自生法是维系封建式的私人支配存续的重要法律体系。因此,在法秩序的阶层上,国王、封建领主们所适用的法律就不可能首先是基于罗马法学家和教会法学家基于普遍性的公共支配观念而编纂的共同法。 但是,即便是处于补充性的地位,我们也不能忽视共同法对于自生法的影响。如论者所指出的,即便我们承认共同法仅仅是一种次要的法源,但是其地位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在中世纪的法律实践中,共同法之地位与《圣经》的地位类似,虽然法官不能直接将其适用于地方的、王室的和习惯规范之中,但是其一直对于他们的心智有着深刻的影响。(29) (三)亚里士多德式的基督教哲学是理性统一性确立的观念支撑 从法律位阶的层面来理解共同法与自生法之间的关系固然切合了中世纪政治结构的封建化特质,但是仅仅从位阶的层面来理解共同法观念,却有可能使我们丧失对于共同法本身在基督教帝国秩序的统一性之维系上的诸多功能,更重要的是丧失共同法所具有的世界性特质,进而无法将11世纪以后的中世纪的法律观念的发展与哲学思维的变迁联系起来。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脱离于法律位阶层面的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理解并认识共同法观念。如果我们不纠缠于共同法到底是如何被适用的这一司法问题,而着力于共同法究竟为11世纪以后的中世纪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实践带来了什么这一更为宽泛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将共同法观念的世界性特质完全地加以揭示。 如我们所一再强调的,法的世界性特质之发展与延续与西方哲学观念的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罗马法的世界性特质与希腊—罗马的自然理性哲学息息相关,欧洲普通法与基督教传统中的意志论纠葛不清的话,那么共同法在11世纪以后的中世纪政治与社会结构中能够得到全面的铺展则与基督教传统中的理性论有着深刻的关联。这种深刻的关联主要表现在基督教哲学在“存在”与“存在者”的性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讨论中所阐发的原理对于共同法和自生法之间关系的巨大影响。在中世纪基督徒的观念中,上帝是唯一至高的存在。吉尔松指出,这一观念包含有两个主张:一是肯定上帝自身的完美,二是肯定上帝的无限。所谓完美即是彰显自身的自足性,不依赖任何内在或外在而存在。这种存在即完美的观念使得上帝的观念具有非常强烈的外溢的特质,并且不受任何限制,因而能够推导出其无限性的特质。完美与无限这两个特质使得上帝作为最高的存在能够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去对任何不完美和有限的存在着施予恩典。(30)但问题在于,上帝这一完美与无限的最高存在以何种方式施惠于那些不完美与有限的存在者?对此,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于中世纪思想中被发现之前,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圆满的解说。直到阿奎那以降,基督教思想家才完全吸纳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论说方式,将此种关系解说清楚。首先,透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维,基督教思想改变了以往意志论传统对于“创造”概念的理解,即“创造”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上帝这个至高的存在为每一个存在者“赋因”,进而使之“存在”。(31) 换句话说,存在者自身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促使自己存在,其存在的意义并不由他自己所占据,而只能透过上帝的创造行为才能加以理解,这样一来,整个世界便在上帝这个最高存在那里体现了统一性;其次,在存在者趋向存在的进程中,由于每一个人都被上帝这个最高的存在“赋因”,所以每一个存在者之间的联结就是透过上帝这一最高存在对于他们的赠予来达成的,所以,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哲学理论中,因果关系就被当然地理解为一种“类比”关系,由此每一个存在者都天然地具有类似性,并且这种类似性不是一种附加或偶然的性质,而是存在者所分享的存在之共同本质的显现;(32)第三是基督教传统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观念的改造。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理论中,目的因是最高的善,因而吸引着所有不完善的存在者趋向于它,从而成为一个不动的推动者,进而所有的存在者最终都趋向于这个最高的存在。但是基督教的目的因观念则正好将此逻辑反转过来,由于上帝是最高的存在,因而是最完美的存在,由此,目的因的观念就并不是为了上帝自身,因为他本身就是最完美和无限的存在,而只能是为了诸存在者自身。诸存在者并不是为了见证存在的荣光而存在,恰恰相反,存在是为了诸存在者的福乐和完善而存在。目的因的观念最终所指向的不是存在,因为存在已经拥有一切,而是指向存在者,将存在的完美与无限传达给诸存在者。(33)从12世纪开始,这种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的演说对于共同法和自生法之间关系的界定有着深刻的影响。有论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论述。(34) 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与存在者的特性及其关系对于共同法和自生法的关系有着全面且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后来的法律家们逐渐将共同法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确切来说,共同法就是法的存在,而自生法即是法的诸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共同法是无限且完美的,不可能存在任何缺陷的。而诸存在者则是有限和有缺陷的,其需要分享共同法的完美与无限。这在巴特鲁斯对共同法和自生法的比拟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在巴特鲁斯看来,共同法和自生法的关系就像太阳与行星之间的关系一般。太阳是无生命的,但却是所有生命的源泉,太阳是所有其他行星及其上的生命得以存续的条件,只有分享了太阳的光辉与无限,诸行星上的存在者才能够获得生命的维系。(35)这样一来,共同法虽然在法律位阶的意义上是无现实的效力的,却是所有自生法的效力得以存续和实现的根源所在。也即,只有经由共同法的赋因,自生法才能够获得具体化的表达并不断地完善自身。与此同时,经由作为法的存在之共同法的赋因,原本多样且异质性的自生法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中都与共同法呈现出一种类似的结构,这样一来,诸自生法之间便存在着天然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性不是归属于其自身的特别属性的类似,而是他们对于共同法之观念的分有的类似,进而所有自生法都在特定的意义上显现出共同法的本质。 从目的因的角度来看,由于共同法作为最高的法律存在,在与自生法这些诸法律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上,基于目的因的理念,并不是自生法之存在为了共同法,而是共同法之存在是为了让自生法分享共同法所具有的完美和无限,进而不断地完善自生法。这在中世纪的法律实践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在13世纪后期的中世纪法律家那里,他们发现原本应该是完美和无限的法律存在的共同法越来越无法适应日常生活的变迁的要求。共同法的“规则体系”很难对应日常生活中变动不居的“权利体系”。这与上文所说的哲学观念有着根本的矛盾。法律家们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得不诉诸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透过论辩术所提供的数十种论辩技巧,共同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无缺漏的“神秘身体”。如此一来,规则体系就能够随时地对应权利体系的变动及其发展。(36)经由基督教哲学观念的这种洗礼,共同法作为一个二元的、相互竞争的最高法律,最终成为一个法的“神秘身体”。这与神圣秩序中的两个二元的、相互竞争的政治性的神秘的身体恰相对应:《国法大全》对应共和国的神秘身体,《教会法大全》对应教会的神秘身体,最终两者统一于基督的神秘身体。 从欧洲普通法到共同法的发展历程主要以两条线索得以呈现:一是从主教们的判例法到法学家的成文法的演化进程;二是从意志的统一性到理性的统一性的演化进程。前者的演化进程表明,民族国家法律思维范式中的英国法问题并不是那么值得加以严肃对待的法律史难题。英国普通法虽然贯彻了英国人的特质和英国地方治理的特色,但就其基本观念和理论架构甚至是具体实践的结构来说,都深深烙上了欧洲普通法的印记:只不过是国王换成了教宗,法官和高级律师换成了主教,地方精英换成了日耳曼诸国王而已。两者唯一的区别是:英格兰很小,而欧洲太大了。后者则提醒我们,共同法的产生并非单纯源于法学家们的智识努力,其对于欧洲普通法的取代也并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强烈的哲学与社会政治背景。共同法中的理性统一性的问题一直影响着世俗化之后的欧洲法律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为欧陆抛弃的法律制度与实践,经过英国人的承继与改造之后,却成为现代早期欧陆哲学家、法律家与革命者所称道的自由制度,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狡计。 ①[英]R.C.范·卡内冈:《英国普通法的诞生》,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②Brett Edward Whalen,Dominion of God:Christendom and Apocalypse in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3. ③John P.Dawson,The Oracles of the Law,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Law School,1968,pp.12-50. ④Maurizio Lupoi,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trans.by Adrian Belt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6,p.15,p.71,p.80,p.82,p.86,p.92,p.98,p.103,p.394. ⑤Paolo Grossi,A History of European Law,Wiley-Blackwell,2010,pp.1-3.. ⑥同前注④,Maurizio Lupoi书,第25~28页。 ⑦同上注,第31~32页。 ⑧同上注,第35页。 ⑨同上注,第38页。 ⑩同前注④,Maurizio Lupoi书,第274页。 (11)同上注,第176、180页。 (12)同上注,第196页。 (13)同上注,第213页。 (14)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就是利益相关方可以在没有被告的情况下在司法集会面前公开地宣读文书,并要求司法集会确认其有效性。很明显,司法集会于此所起的作用是一种“公共性”的确认功能,而非裁决功能。同上注,第219页。 (15)对于奥古斯丁的这种意志理论对于法律观念的影响的阐释,参详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Mind:Willing,New York:A Harvest Book,1978,p.88. (16)Manlio Bellomo,The Common Legal Past of Europe,1000-1800,trans.by Lydia G.Cochrane,Washington: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5,p.57. (17)相关内容可参阅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8)Otto Gierke,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s,tran.by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0,pp.9-10. (19)Brian Tiemey,Religion,Law,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ll50-16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9. (20)Ernst 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p.194-232. (21)同(18),Otto,Gierk书,第22页。 (22)Nicholas of Cusa,The Catholic Concord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7. (23)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Juta & Co,Ltd,1992,Preface,IX. (24)See Randall Lesaffer,European Legal History: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trans.by Jan Arrie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92.及以下。 (25)同前注(16),Manlio Bellomo书,第75页。 (26)同上注,第76~77页。 (27)同上注,第78页。 (28)同上注,第79~80页。 (29)同上注,第95页。 (30)[法]吉尔松:《中世纪哲学精神》,沈清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1页。 (31)同上注,第87页。 (32)同上注,第90~91页。 (33)同上注,第96~97页。 (34)同前注(16),Manlio Bellomo书,第164~166页。 (35)同前注(16),Manlio Bellomo书,第192页。 (36)同上注,第181~182页。标签:法律论文; 普通法论文; 日耳曼人论文; 中世纪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罗马帝国论文; 基督教论文; 罗马法论文; 权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