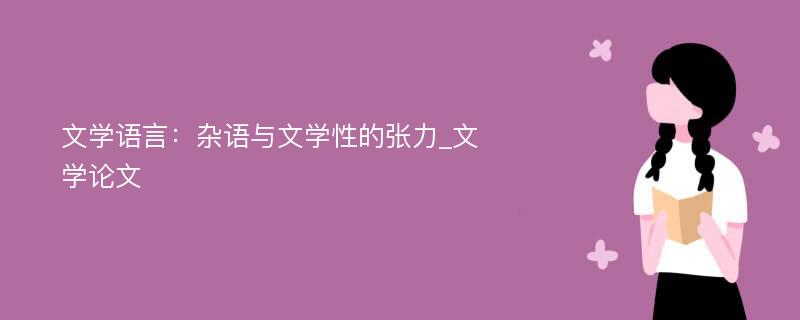
文学语言:杂语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语言论文,文学性论文,杂语性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力”这一概念是美国新批评派主将之一艾伦·退特1937年在他著名的《论诗的张力》(Tension in Poetry)一文中提出的,他以此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指出:“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注:[美]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姚奔译,见赵毅衡主编《“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117页。)他认为“张力”是好诗的“共同的特点”,这一概念由此得到了西方文论界的认同,从而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罗吉·福勒进一步把“张力”界定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认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注:[英]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袁德成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运用“张力”说考察文学语言,人们可以发现它具有明显的张力性质,本文试从“杂语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角度观照文学语言的张力性质。
一
文学以语言为材料,但语言是人类共享的媒介,遍布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同的领域造就了不同的语域和语境,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言语形式和言说方式,在此基础上,不同的领域也就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定的言语类型,即语体,丰富着人类的语言库存,使语言在各个领域获得现实化,从而实现语言的各种功能。巴赫金指出:“语言在自己历史存在中的每一具体时刻,都是杂样言语同在的;因为这是现今与过去之间、以往不同时代之间、今天的不同社会意识集团之间、流派组织等等之间各种社会意识相互矛盾又同时共存的体现。杂语中的这些‘语言’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交错集合,便形成了不同社会典型的新‘语言’。”(注:[俄]M·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标准语本身,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已经不仅有统一的共同的抽象语言特点,也有了对这些抽象因素的统一的理解方法,但在自己具体的指物表意和情味方面却是分裂了的,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杂语。”(注:[俄]M·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但语言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共同体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中现实生成的产物。同时,语言的同质性又使不同的语言现象集合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这一语言事实决定了文学以语言为材料,其语言必然是杂语共存、多语混成的,这就是文学语言的“杂语性”,巴赫金又把它称之为“多语体性”。
“多语体性”这一概念出自巴赫金《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一文,他说:“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切可能有的语言语体、言语语体、功能语体,社会的和职业的语言等等。(与其他语体相比)它没有语体的局限性和相对封闭性。但文学语言的这种多语体性和——极而言之——‘全语体性’正是文学基本特性所然。文学——这首先是艺术,亦即对现实的艺术的、形象的认识(反映),其次,它是借助于语言这种艺术材料来达到的形象反映。”(注:[俄]M·巴赫金:《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潘月琴译,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巴赫金认为,文学只有借助语言这一艺术材料才能达到对现实的艺术的认识,而语言在现实中是一个包含各种言语方式、言语类型和言语特征的同质的整体,文学以语言为材料表达对现实的艺术的认识,必然反映出语言“多语体性”的一面,以“杂语”的形式出现。简言之,“多语体性”是语言现实性的一种体现,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也只有在具备了“多语体性”这一面后,作品才能达到对现实艺术认识的目的。韦勒克、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也指出了文学语言所具有的“杂语性”一面:“因为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不同,它没有专门隶属于自己的媒介,在语言用法上无疑地存在着许多混合的形式和微妙的转折变化。”(注:[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从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全部事实来看,“杂语性”的确是文学语言普遍具有的一个属性,在叙事类和戏剧类作品中,这一性质显而易见,在抒情类作品中有时即使是篇幅短小的诗歌也往往存在着“杂语性”的现象。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对于18、19世纪英国的“幽默小说”代表作品中的“杂语性”现象作了精彩的论述,认为“外观最为醒目,同时历史上又十分重要的一种引进和组织杂语的形式,是所谓的幽默小说提供的”,他指出:“在英国的幽默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口头和书面标准语的几乎所有层次,都得到了幽默的讥讽的再现。我们上面列举的属于小说体裁中这一类型的古典作家代表(菲尔丁、斯摩莱特、斯特恩、狄更斯、萨克雷等人——引者注),其作品几乎每一部全是标准语一切层次一切形式的百科全书。作品的叙述语言随着描绘对象的不同,用讽刺的口气一会儿使用议会雄辩的形式,一会儿采纳法庭演说形式,一会儿又像是会议记录,一会儿是法庭记录,一会儿犹如报章的采访消息,一会儿是伦敦金融中心的枯燥的公文,一会儿好似拨弄是非的闲言碎语,一会儿好似书生气十足的学究讲话,一会儿是崇高的史诗风格或圣经风格,一会儿是伪善的道德说教风格,最后还可能是书中所讲的这个或那个具体人物、带有社会确定性的人物的语言格调。”(注:[俄]M·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译,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3页。)正因为这一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影响到人们对文学语言与日常各种语言用法区别的认识,所以,韦勒克、沃伦提醒人们:“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的语言用法之间的区别是流动性的,没有绝对的界限。”(注:[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页。)
文学作品中语言所具有的“杂语性”,的确容易模糊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之间的界限,它仿佛是一种艺术上的“离心力”,分散着人们对于语言艺术性的注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毕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又有着显著的区别,那么,到底是什么与“杂语性”形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使“杂语性”最终没有摆脱文学语言所具有的“向心力”的牵引?换言之,文学语言的“向心力”到底源自何处?在这里,如果借用雅克布逊的一个诗学概念来说,这就是“文学性”。正是由于“文学性”的存在,文学语言的“杂语性”所体现出的“离心”倾向才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各种不同的语体最终统一于文学文本之中,整体地升华为文学语言。
二
“杂语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有助于人们辩证地认识文学作品中不同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从而克服在语言功能认识上存在着的二元对立的倾向,如把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加以对立,把文学语言的审美功能与认识、交流等功能加以对立,把语言的科学用法与情感用法加以对立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倾向从根本上否定了语言的同质性,否定了语言所具有的各种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杂语性”体现了语言的多功能性,不同的语体或语言类型实际上都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它们同属于人类的言语行为,它们的语体边界只是相对的,并非泾渭分明、水火不容。
人类的言语活动中往往交织着不同的功能,不同功能之间的主次关系视不同的语域和语境而有所侧重,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功能语体。雅克布逊从语言学角度通过组成人类言语交流行为六个因素(发信人、收信人、信文、接触、信码、语境)的图式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六种语言功能的理论。(注:[俄]罗曼·雅克布逊:《语言学与诗学》,佟景韩译,见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182页。)他认为,任何交流都离不开发信人、信文(话语)和收信人三个基本因素,但除此之外,话语还需要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接触,接触必须以信码作为形式,话语不能脱离语境,语境使话语具有意义。话语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意义存在于六种因素构成的全部交流行为中,而在交流行为中这六种因素不会绝对平衡,其中某一种因素会处于主导地位。他指出:“这六个因素各与语言的一种功能相关。但很难找到一种信文(话语)仅仅执行某一种功能。各种信文之间的区别不在某一种功能的单独表现,而在各种功能的不同等级地位。”(注:[俄]罗曼·雅克布逊:《语言学与诗学》,佟景韩译,见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也就是说,任何话语都是多种功能的统一体,它们的区别完全取决于六个因素中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个功能决定了话语的性质。当交流倾向于发信人(addresser),那么表情功能(表现功能)就占主导地位;当交流倾向于收信人(addressee),那么呼叫功能(意动功能)就占主导地位;当交流倾向于语境(context),那么指示功能(交流功能、认知功能)就占主导地位;当交流倾向于接触(contact),那么接触功能(呼应功能)就占主导地位;当交流倾向于信码(code),那么元语言功能(解释功能)就占主导地位;而当交流倾向于信文(话语)本身,那么诗歌功能(审美功能)就占主导地位。雅克布逊认为:“纯以话语为目的(Einstellung),为话语本身而集中注意力于话语——这就是语言的诗歌功能。研究这种功能,如果脱离语言的一般问题,那就很难收到成效,另一方面,分析语言,也必须细致考察它的诗歌功能才成。”(注:[俄]罗曼·雅克布逊:《语言学与诗学》,佟景韩译,见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从雅克布逊的上述分析中,人们不难看到语言的多功能性,语言的各种功能之间既相互矛盾对立,又相互渗透转化,当人类言语行为中的某一因素及其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后,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功能语体。由此他进一步强调:“一切把诗歌功能的领域仅仅限制在诗歌范围之内,或者把诗歌本身仅仅归结为诗歌功能的做法,都是危险的简单化的做法。诗歌功能不是语言艺术的惟一功能,只是语言艺术的核心的、起决定作用的功能,在其他言语活动中,它是第二位的、辅助性的成分。诗歌功能加强了符号的明显性,因此也深化了符号与对象的基本对立。所以语言学家研究诗歌功能不能限于诗歌领域。”(注:[俄]罗曼·雅克布逊:《语言学与诗学》,佟景韩译,见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这段话至少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诗歌功能虽然在诗歌中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但并非诗歌的“专利”,它同样存在于其他言语活动之中,语言具有多功能的本性;二是语言的多功能性决定了诗歌言语的多功能性,诗歌功能如果没有其他功能作为背景或与之对垒,它就无以凸显。
雅克布逊所说的诗歌功能,实际上就是语言的“自指性”和语言的可感知性,它吸引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话语本身,如音响、节奏、格律、措辞、句法等语词形式的选择和组合上,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语言符号所指称的外部现实上,这就意味着语言的其他功能总是指向外部现实,符号与指称趋向对应,而诗歌功能只以话语本身为目的,符号与指称趋向对立。应该看到,诗歌功能的这一特征不仅集中地体现在诗歌文本之中,而且普遍地存在于文学文本之中,功能即用法,语言的诗歌用法使文学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其他言语的语体特征,从这方面来看,文学语言可以视为诗歌功能的功能变体,但由于诗歌功能只是文学中的主导功能而非全部功能,所以,文学语言又非诗歌功能的“特技表演”和单一体现,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用法。诗歌功能与其他功能相互交织和对立,不同语体之间的混合和纠缠,从而导致了文学语言的“杂语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冲突。雅努什·斯拉文斯基在谈及诗歌信息的本质矛盾时对此作了如下一番论述:“诗歌功能的独特性,实际上就是诗歌功能与一般功能概念的特殊矛盾:单就诗歌功能而言,它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只有在目的指向话语外部的另一种功能的背景上,诗歌功能才可能是功能。由于‘诗歌性’的这个本体论的矛盾,诗歌性与非诗歌性之间、专注于自身组织的自私主义与履行外部责任(心理责任、社会责任或认识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张力)成了诗歌的常态。在诗歌中,作为一个系统的各种功能的等级关系,是一个不断求得平衡的动态系统。主导功能的优势经常受到威胁。诗歌信息支配其他信息或其他信息支配诗歌信息的界线是波动的、不确定的。”(注:[波兰]雅努什·斯拉文斯基:《关于诗歌语言理论》,佟景韩译,见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这就使人们不难看到,文学语言中诗歌功能与其他功能之间、专注于话语自身组织的诗歌性与多语体的非诗歌性之间的张力是一种常态。任何把文学语言仅仅理解为诗歌功能的功能变体而无视其他功能存在的看法都意味着这一张力关系的解除,对于文学来说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从言语活动的要素及其关系来理解,语言的多功能性决定了语言多语体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语言的多种功能之一的诗歌功能为什么能在文学中上升为主导功能?换言之,是诗歌功能对语言自身的关注赋予了诗歌(文学)以诗歌性(文学性),还是文学性赋予了语言以诗歌功能?能否将语言的诗歌功能等同于文学性?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文学性。
三
“文学性”这一概念是雅克布逊(《现代俄国诗歌》,提纲1,布拉格,1921年,第11页)首先提出的,他不满于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流行的把传记、道德、政治、心理和历史诸因素置于优先地位的做法,倡导建立一门具有独立系统的文学科学,他说:“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注:转引[俄]鲍·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蔡鸿滨译,见茨维坦·托多罗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雅克布逊所说的文学性是指文学区别于其他话语的本质特性,然而,什么是文学性,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学者的理解都不尽相同。(注:[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史忠义等译,见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4页。)
其中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把文学性等同于雅克布逊所说的语言的诗歌功能,即语言的诗歌用法,如伊格尔顿就持这一看法。他指出:“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文学性’(literariness)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区别性关系(differential relations)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文学性’并不是一种永远给定的特性。他们一心想要定义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语言的某些特殊用法,这种用法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发现,但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之外的很多地方找到。”(注:[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的确,如果把文学性仅仅看成是语言的诗歌功能,那么这一功能也并非仅仅存在于文学话语之中。对此雅克布逊本人也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语言学与诗学》一文中论述“诗歌功能就是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的原理时所举的例证,恰恰就是西方人所熟知的恺撒的一句凯旋辞,而非出自文学作品,“三个双音节的动词以同一个辅音开始,以同一个元音结尾,使恺撒一句简洁的胜利宣告大放光彩:'Veni,vidi,vici.'(‘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注:[俄]罗曼·雅克布逊:《语言学与诗学》,佟景韩译,见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正因为语言的诗歌功能在不同的言语活动中没有明确的边界,卡勒明确反对“把某文本的文学性效应局限在语言手段的表现范畴之内”,他以雅克布逊本人的论述为根据,指出:“某段言语能够使其语言具有感知性这一事实,不足以说明它即属于文学语言。广告语言、文字游戏以及表达错误,都可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却并未创造出文学作品。”(注:[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史忠义等译,见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可见,语言的诗歌功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性,仅从某一因素、某一层面和某一角度出发,都难以揭示文学性的奥秘。
在我看来,文学性的含义是相对的、混整的和流动的,它存在于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和整个流程之中,存在于由此而形成的文学语境之中。文学语境可分为小语境和大语境,小语境是由话语的题材、主题、语词的选择和组合、语词意象、文本结构等上下文关系所组成,最终统一于文本的整体结构和形式;大语境则是由作者、文本、读者以及文学传统、文学惯例、文学范式所形成的文学背景乃至时代、社会、文化背景所组成的。对于文学来说,“语言的诗意用法”总是“诗中的语言用法”的一部分,文学性也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自指性和可感知性方面,语言的诗歌功能只是文学性的表征之一,正是由于文学性及其文学语境的存在,诗歌功能才能在文学中上升为主导功能。卡西尔通过对西方文学史上代表作家的分析指出:“诗人好像是把普通言语之石点化为诗歌之金。我们在但丁或埃瑞斯托的每一段诗中,在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悲剧中,在歌德和华兹华斯的每一首抒情诗里,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点石成金的天赋。他们的一切都有其特殊的声音,有其特殊的韵律,有其无与伦比的、令人难忘的旋律。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都为特殊的诗的氛围所环绕。”(注:[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2页。)从卡西尔的论述中可以得知,诗人之所以能将普通言语点石成金就是因为有“诗的氛围所环绕”,所谓“诗的氛围”即是文学语境。瑞恰慈对词语效果的如下论述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说:“没有一个专门属于某个词语的效果。文字并无任何固有的文学特性。丑或美也不存在本身令人不快或令人愉悦的特性。反之每个词语都有一个可能产生效果的范围,随着接受这个词语的语境而发生变化。……所谓一个词语具有的效果即它能介乎所可能产生的某个效果与它所进入的特殊语境之间。”(注:[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这一论述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语言的效果和功能受制于特定的语境。文学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专门语言,语言也没有固有的“文学特性”,只是由于文学性及其文学语境的存在,人们才能从众多的语言功能中划分出语言的诗歌功能,诗歌功能也才能在文学中得到突出,语言中的其他功能、语体也才会在文学中获得相对的统一性。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可谓涵摄万有(“杂语性”),但语言材料在文学中却又万有归一(“文学性”),在“多”与“一”的辩证统一中,我们不难看到文学语言所具有的张力性质。
